前言:很多人最初接觸遊戲科研文獻時都被它們有趣的題材給吸引,可讀後卻深感晦澀無聊。作為遊戲科研的重要一環,讀文獻甚至超越了打遊戲,成為了我每日的必完成項。與遊戲文獻共存,是作為遊戲科研人員的我,曾經、現在及今後一直努力適應的狀態。
前情
在我的機核第一篇 遊戲科研和打遊戲 中,我就介紹了遊戲科研、遊戲本地化與打遊戲的簡單區別,而在之後與遊戲文化研究者 羅皓曦 的 遊戲思維 VS 遊戲科研思維 的網絡對話中, 我們倆也都提到了作為研究者打遊戲和作為普通玩家打遊戲時不同的心理。
如果說以上的文章更多談到的是區別遊戲研究者與普通玩家在遊戲中遨遊時的主觀心理感受,那麼影響主觀感受的兩個不容忽視的客觀要素,便是遊戲科研文獻和遊戲作品本體。而在此之中,遊戲科研文獻,是我們遊戲研究者的基石,也是我們為之奮鬥的目標——讀文獻,寫文獻,發文獻——是的,這就是科研的“真實奧義”,有“屠龍少女終成龍”那味兒了。
遊戲實踐和科研理論本來就是兩個不可分割的要素,故我自己很排斥“某一方一定優於另一方”的理解。而且在我人生的很多個拐點,我都驚覺實踐和理論兩者一起協作影響著我,缺一不可——雖然其中很多經歷和遊戲並沒有直接關係。而以遊戲科研者身份遨遊遊戲書海之後,我又發現那些前人大牛,無一不是兩者拿捏,這又進一步證明,一個好的內容輸出者,是萬萬不可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的。
然而,很多人也許最初因為喜愛遊戲,所以去接觸了遊戲相關科研文獻,但是淺淺讀後,卻深感晦澀無聊,也許會因此對遊戲文獻乃至於遊戲科研另眼相待。所以,本篇文章也算是一個階段性讀書筆記——我想借此現象,聊一聊我這段時間科研的自我感受。
遊戲科研文獻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遊戲文獻晦澀難懂,甚至另眼相待呢?我覺得,這其中很大的一個印象因素,來自於不同讀者對 文獻 的理解。
文獻是什麼呢?我個人的理解是,從廣義上講,文獻可以泛指“各種有歷史價值和參考價值的資料”,並且這些資料並不一定簡單由文字作為載體,見中央民族大學人類學研究方向 朱靖江 老師的 視覺人類學中的“影音文獻”,挑戰民族誌傳統定義的“虛擬現實影音文獻” 等。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其實我們手頭接觸的,很多影音資料,乃至於自身的敘述,都可以成為廣義的文獻。但是在使用的時候,需要進行嚴格的篩選和詳細的闡述——這些我目前階段並沒有直接接觸到,也不便班門弄斧。
雖然中英文語境下對文獻的理解也許有些許不同,但從academic wirting(學術寫作)成果的角度來探討,很多人接觸到的最直觀的遊戲科研文獻,就是研究者“寫”出來的東西,如essay,article,paper,thesis之類——主要以長度和章節等要素來區分,而發佈的場合也不僅限於journal,也可能是conference,或者book。也正因為這些東西是寫出來並且發在特定刊物上的,發佈的平臺區別於個人的博客,發佈的格式必須遵循特定的規則,還需由editor(編輯),reviewer(審稿人)來一一把關,故一篇文獻從構思到發表,也就是我們所有卑微研究者所說的publication,都要經過很漫長很折磨人的過程。
說到這,想起了一句很有意思的“文字遊戲”
Being rejected is normal. If you successfullyreject the rejection and justify your rejection, you are quite abnormal! 投稿被拒是很正常的,但如果你成功轉變編輯的想法,讓ta從給拒信變為助你發表,那你就太牛啦!

豆瓣:我們reject了editor的rejection 牛!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也簡單提到,雖然網絡論壇上關於遊戲的官方發佈或粉絲帖子也有很高的點贊量和借鑑性,但是遊戲研究者往往會對科研文獻產生更大的興趣——尤其體現在引用量上。當時我和羅皓曦分別從個人閱讀傾向和寫作環節等角度給出瞭解釋,但現在我也想基於publication的環節來聊一聊這個話題。
基於以上的介紹,大家大概都瞭解為了publication而寫作的難度了。但是publication要求下的寫作,僅僅只是學術寫作的一小小部分。在平時的生活中,我接觸到的所有幾乎所有郵件的往來,學術論壇的發佈內容,階段性考核報告,課後的小論文小作業,都屬於學術寫作的範疇。而在我寫作的時候,雖然我也會參考網絡上的一些資訊,但是我必須確保我瞭解這些資訊的來源以及正確性,我還得考慮這份東西是哪一年發佈的,在他發佈了之後,產業中是否發生了新的改變,或者他所做的推斷——雖然符合當時的特點但在現在看來也許是不成熟的——是否存在侷限性……如果真的很離譜,即便是已發表的,那我可能也會考慮暫時不引用。但如果有某些結論和我的東西相關,那我可以在闡述清楚的前提下引用它。
所以,就我個人而言,也許在剛接觸學術寫作時,我還會天真地使用一些網絡報告、媒體發佈作為reference(文獻參考),但在被老師瘋狂打回反饋之後,就立刻打消了此類念頭。根據老師們的教導,其根本原因就在於,“all these can be faked(這些是可以被偽造的)”——當然還是那一個概念,好比《楚門的世界》,偽造的程度是相對的,偽造的結果也會受到推斷過程乃至於審核過程的制約。所以學術寫作中的客觀性,也是相對的。不要槓哦,打咩!
所以,這也導致了很多遊戲科研文獻 不那麼有趣。它們行文往往十分嚴謹,又喜歡擺事實,講數據,一不小心思維跳了,語言跟不上了,這一段就看不懂了。所以,它們就像外表看上去不是很好吃但又可以果腹的壓縮餅乾,往往不是外出野餐的首選。而且,很少有人能僅出於熱愛,投入大量金錢與時間,追根溯源非開源(需購買)遊戲科研文獻——我之前也提到過為什麼我能翻卻不參與文獻的翻譯,那是因為,一,我沒有時間,二,我很容易分不清我手頭的文獻到底是開源還是非開源的,如果是非開源的,那麼我學校的資源庫替我承擔了大量購買費用。
遊戲科研文獻與翻譯:以“遊戲類型”為例
還是那句老話,game studies(遊戲研究)的概念太大了,當我們包容看待時,所有和遊戲相關的研究,都是遊戲研究。自然而然,遊戲研究所產出的文獻,都是遊戲科研文獻。
機核上的有一個很好的板塊叫做 譯介 ,其中包含了我所提到的遊戲科研文獻——那些研究者們發表了的的東西,以及研究者平時的思考感悟(好比我這樣的瞎叨叨)。譯介 的存在固然很好,不光給不太熟悉原語言的遊戲愛好者們提供了一個瞭解國外學者、遊戲製作者等作品的機會,也為我們這些做遊戲研究的小夥伴提供了更便捷的搜索方式。但有時候把從外文翻譯成中文,會喪失一些很重要的關鍵特徵,比如說某些術語在中英語境下的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說混淆了對原文的作者/立場/科研背景等關鍵認知——這些問題,也許可以涉及到翻譯學中domestication(歸化)和foreignisation(異化)的探討,當然,都是後話。
前者主要涉及到一些爭議性的術語的翻譯——因為翻譯而喪失了某些詞彙的重點特徵的情況,並不僅僅只出現在科研文獻中。比如說,我手頭的《電子遊戲微歷史》這本書,原作者為伊恩·西蒙斯與詹姆斯·紐曼,中文譯本由陳厚力和王棟兩位譯者翻譯——多提一嘴,紐曼本人是英國Bath Spa University數字媒體專業的教授,一個橫跨學術寫作和遊戲科普寫作(特指給大眾看的題材)的大牛。在看到《微歷史》這本書之前,我就淺讀了他在2000年前後發佈的很多作品,非常有意思。
我個人覺得,這本書的中譯也很有特色,書裝也非常精美,很適合收藏。但美中不足的是,因為中譯本受篇幅限制,沒有辦法展現大部分(我所感興趣的)關鍵詞的英文,而對於學術寫作的基本要求就是確保詞彙的正確——剛好我又是一個,一看文獻就喜歡extensive reading(精讀)的人,所以讀的時候我覺得又快樂又累,因為在關鍵詞的把控、理解和檢索上,我要耗費很多很多時間。

James Newman受訪截圖
因為我是從翻譯學的角度(遊戲本地化)去探討遊戲研究的,受到翻譯思維的影響,我也在學習和打遊戲的時候,發現了很多有意思的例子,比如說 遊戲類型 這一概念。中文語境中的遊戲類型,真的是包羅萬象。FPS,MOBA這一類按照遊戲大玩法來區別的稱呼,是遊戲類型;街機,PC,主機這些依載體而區分的,也可以是遊戲類型…… 而遊戲類型本身就是一個科研大方向,更別提在英文中“類型”的英文單詞究竟是什麼了。2005年互動媒體研究方向的Lindsay Grace曾經就game genre和game type兩個概念寫了一篇文獻來辨析——對,從翻譯角度來看,genre和type兩個詞,都指的是“類型”。但是實際上即便是“類型”,它們在具體的語境中也是有不同的詞彙去替代的。而Grace的也只是根據前人的依據以及他個人的科研理解,給出了劃分:
We distinguish game type as a description of game play, and game genre as a description of the narrative content of the game. 在討論遊戲故事時,我們將遊戲game type定義為對遊戲玩法的描述,而game genre則是對遊戲敘述內容的描述。
我還在其它科研文獻或媒體報道中,看到過game style等詞彙,沒有細究具體的含義,但實在是種類繁多。由於“類型”並不會成為很多遊戲研究者的重點,所以其中大部分人對於“類型”的劃分,也只是淺淺提到一句——但這不代表,每一個使用這些具體單詞的人都知道它所承載的含義,也不能代表哪一種翻譯或類型分類方式,就一定就是正確的。而且,我們可以假設,這一混淆的現狀並不僅限於中英,也許在西班牙語中也存在類似的問題,也許韓語中也存在——在某些文化中,外來詞的佔比較大,這也許又會給“類型”的辨析增添“本地化後的難度”,當然,這是別人該思考的問題啦!
遊戲科研的目的
遊戲科研的主題、方向、細節,很大程度上都受到遊戲科研者自身經歷的影響。比如上文提到我對“遊戲類型”的思考——正是因為曾今的翻譯學習經歷,我對字詞意這一塊兒抓得很嚴。通過之前的網絡對話我也感受到,遊戲文化研究方向的羅皓曦則更善於從文化角度去探討遊戲因素的關聯性。但我們也都贊同一點,那就是研究者,並不是遊戲收藏家,所以我們所研究的東西,也許並不是我們最喜歡玩的。
問:如果不是喜歡的東西,又為什麼要研究它呢?
答:因為沒什麼人研究,或因為這個東西很有意義——這真是兩個很純粹但又很不純粹的概念。
沒什麼人研究,表示它的研究前景廣,易爭上游,但又需要完全依靠自己搭平臺,很新但是很苦,這大概就是我——我們一群人,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這個東西很有意義,表示它有用,它一定有用,雖然不知道是短期還是長期,是五年還是十年。雖然我有一個師妹並不是做遊戲研究方向的,但是她所從事的科研領域是口述電影翻譯。對於殘障人士來說,也許最直觀的保護是立法、設施等,但滿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後,形而上的娛樂方式,如電影、遊戲等,那麼口述電影,也許在某個特定環境下就有極廣的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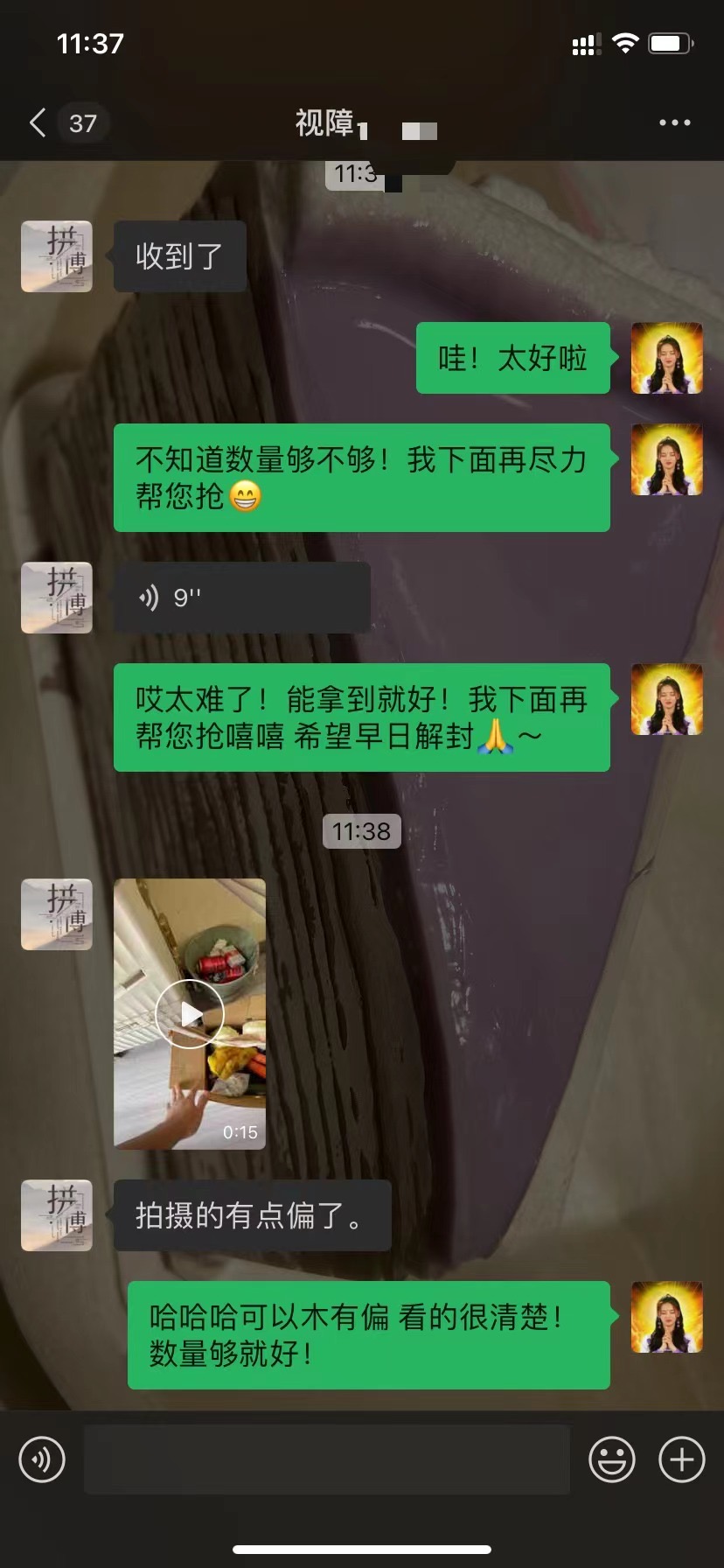
師妹幫助視障人士搶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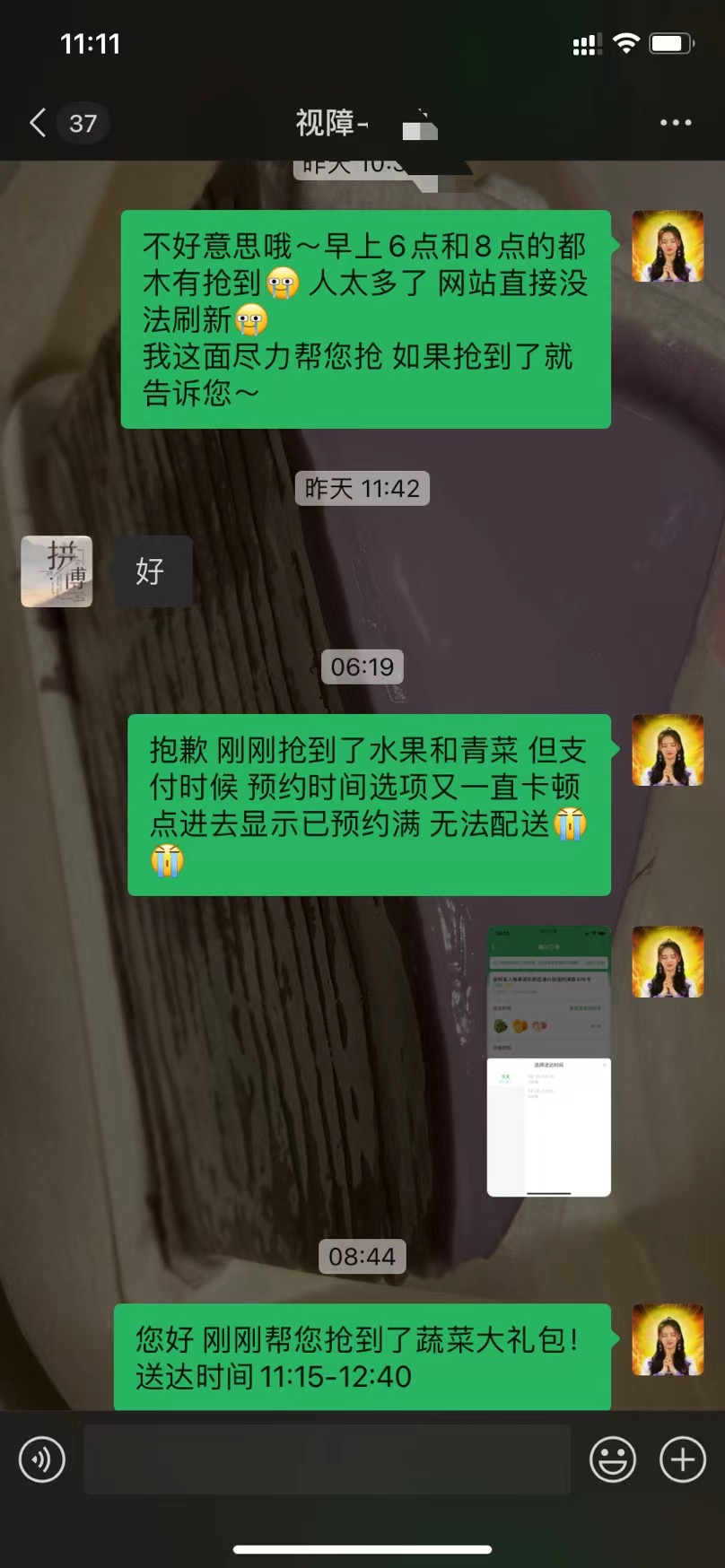
希望大家多關注障礙群體
所以我隱隱覺得,支撐遊戲科研工作者去做遊戲科研乃至於遊戲與其它領域相關科研的內核動力,實在得強大萬分才行。因短期內無物質回報而產生的不解,質疑和嘲諷,因學生title而在社會中被小看的經歷,更不光存在於產業與科研之間,也可能發生在相對純粹的科研環境下。但一切發展的東西,就像《微歷史》這本書裡說的那樣,誰也不知道是幾年、幾十年之後,那些網絡上平臺上的東西會逐漸取代原先特別流行的街機,而未來的一代又將面對怎樣的遊戲呢?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窮。
最初激勵我去做這些事情的,也只是一些關於遊戲的隻言片語。說實話,我真的無法預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後……那時候的遊戲類型、內容、遊戲與媒體的互動,成了什麼樣子的?那時候的科研文獻,又在記載些什麼東西。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很渺小,渺小到在科研文獻中遨遊一小會兒,就變得又激動又膽怯。我激動是因為看到各式各樣的題材湧現,驚喜找到同道中人,驚歎於他們的創造力與行動力,和與此似乎不相匹配的謙遜。比如德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Altmeyer在碩士期間就做了gamified ads——他在得知了我的來意之後,熱情地把非開源稿件發給了我,還解答了我的疑問。所謂的gamified ads,從簡單的彈窗特效、技術文本、乃至於眾嘲之下的“貪玩藍月”,也變成了值得深究的遊戲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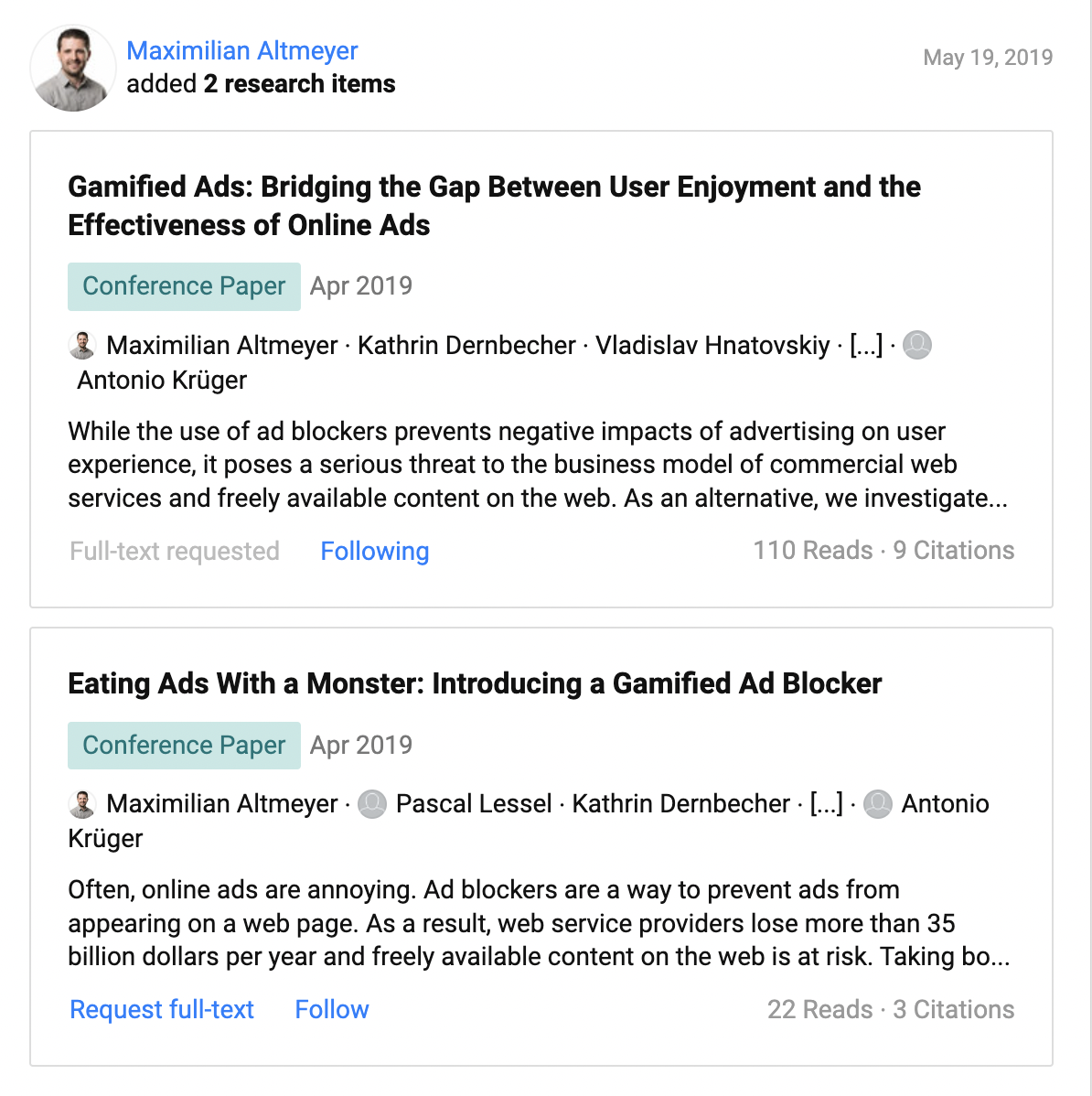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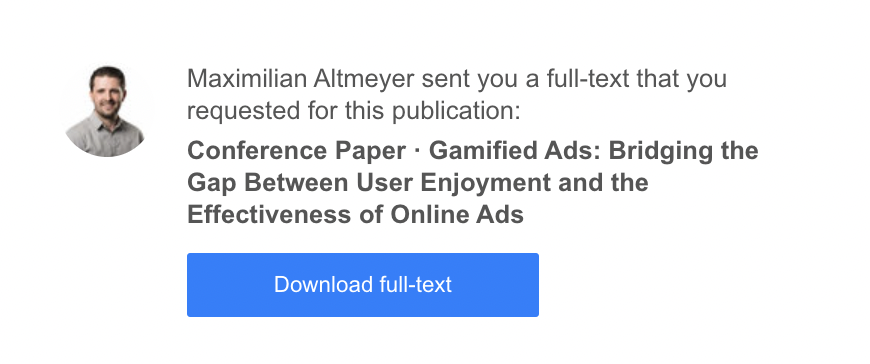
又比如說,還處在PhD Candidate階段的Harkin小姐姐做的“性別身份與遊戲”選題——雖然PhD Thesis,在不同院校都存在著一定的時間保護期,所以即便成稿,往往都要幾年之後才可開源,但我很佩服Harkin在四年前就做出的這個論題決定。

再比如說,2018年《女性媒體研究》期刊上曾發佈關於“鬥陣特攻聯賽”少有的女性選手Geguri的研究,探究了女性與電子競技的關係。也讓我回想起一系列與諸如女流,177與遊戲或電子競技相關的女性選手、女性解說,以及她們如今的境遇。

有關大家廣為熟知的“肉鴿”遊戲科研也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一個月前看到,Call for Abstractes/Chapter Proposals,肉鴿題材,招賢納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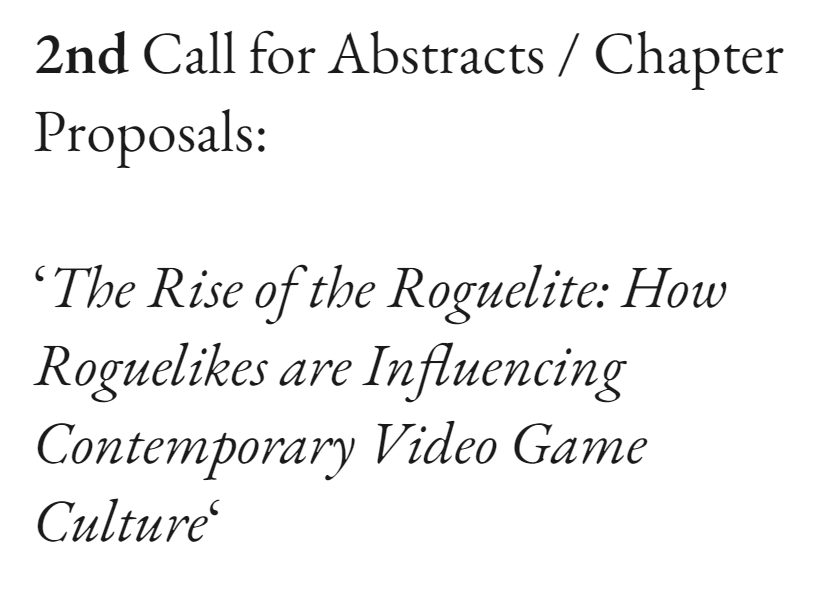
我不常在生活圈發關於學習和讀書的感悟,為數不多的幾條中,有一條記憶猶新。那是一本講寶可夢的英文書。我至今都記得,距離書首版二十多年後,在莫寧頓路旁的一座小小的房子裡,我看著教授寫的序章,體會到了他所說的,“我像喚醒回憶一樣,喚醒它們”般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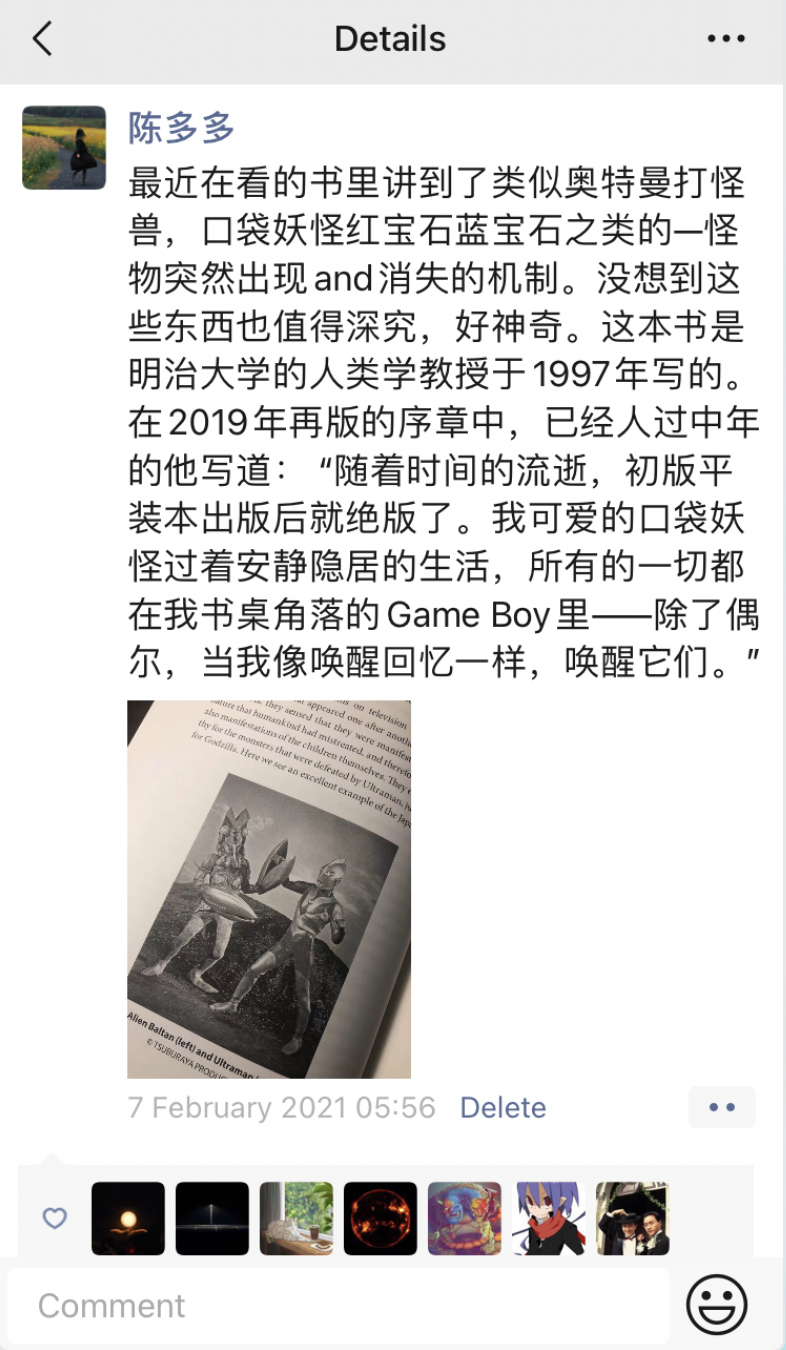
感謝你的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