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I Have No Words & I Must Design: Toward a Critical Vocabulary for Games
- 作者:Greg Costikyan
- 時間:1994
- 期刊:Interactive Fantasy No. 2
導語:本文的作者Greg Costikyan是一個遊戲設計師以及科幻小說家,他最出名的代表作是《星球大戰》,同時也著有《Toon, Web and Starship》等頗有迪士尼動畫風格的角色扮演類遊戲。
這篇文章是他於1994年發表在期刊Interactive Fantasy上,關於遊戲設計以及遊戲定義的論述,併成為自身的遊戲設計聖經。文中提出一個好的遊戲需要的幾點標準,交互、目標、困難、結構、內在意義,也成為現在遊戲設計常關注的焦點議題。本篇閱讀筆記將介紹作者的遊戲定義標準,闡述通過閱讀現代遊戲設計書籍對本文的認知。
1. 遊戲是複合的媒介作品
原文中,作者用plastic一詞來形容遊戲,認為它如同塑料一樣多變的百搭,多變,複合,它從古至今一直存在,不論科技的高低。比如桌遊、戰爭遊戲、電腦遊戲甚至是主機遊戲都屬於遊戲,但是遊戲的界定範圍卻十分模糊。
Greg在1982年應聘雅達利的時候面試被問及一個問題,何為遊戲機制(gameplay),他回答道,《Zaxxon》就是一個好的遊戲機制的代表(注:《Zaxxon》是1982年Sega發行的等距視圖射擊遊戲)。因此他希望通過拆解遊戲機制的方式,得到重要的遊戲詞彙(critical vocabulary),來定義遊戲的邊界。交互、目標、困難、內在含義,即他為遊戲邊界設置的定義。

Zaxxon, Sega, 1982
2. 交互
Chris Crawford在1982年指出遊戲與謎題(puzzle)的不同之處,謎題是靜態的,只有一個解決方案,而遊戲會根據玩家的行為動態變化[1]。以此類推,大多數類型的遊戲都符合這樣的規則,比如冒險類遊戲任務目標與謎題對於玩家幾乎是同樣的含義,即使是第一人稱射擊遊戲,玩家也需要尋找合適的地形和位置擊敗對手。遊戲結果根據玩家不同的選擇有所不同,遊戲和玩家在互動(interact),遊戲機制與遊戲玩家相關。
隨著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社會思潮逐漸走向以人為本的目標。當我們仰望科學技術帶來的便利快捷一步到位的時候,也需要偶爾腳踏實地看向人本身。遊戲作為一種互動藝術形式,它一直被人們所追捧的原因就是它與人相關的性質。假設視覺小說不做任何與玩家選擇相關的不同結局,根據Chris的標準,這不是遊戲而只是一個謎題,玩家只有單一的選擇。2018年發售的遊戲《底特律:變人》(Detroit: Become Human)被詬病為交互電影而非遊戲的理由也與之類似,部分玩家認為敘事電影的交互性比起RPG和ACT弱不少。

《底特律:變人(Detroit: Become Human)》,Quantic Dream, 2018
實際上這種爭論早在遊戲界上世紀末就存在,一部分學者認為遊戲是敘事的,即narratology,另一部分則認為是交互的,即ludology。
敘事為主的遊戲以《行屍走肉》(The Walking Dead)為代表,交互為主的遊戲則以《乓》(Pong)為代表。然而如今眾多在遊戲史上著名的作品並不以二元論的方式割裂遊戲的設計,而是結合二者並平衡之。比如《上古卷軸:晨風》(The Elder Scroll: Morrowind)、《超級馬里奧兄弟》(Super Mario Bros.),都是同時存在交互與敘事的優秀作品。Quantic Dream打破了許多商業遊戲的規則,儘管業界和玩家圈子之間的言論各持己見,但也無法否認這家公司的作品重新把何為遊戲的討論提上議程。

左上:《行屍走肉(The Walking Dead)》,Telltale Games, 2012;右上:《乓(Pong)》,Atari, 1972;左下:《上古卷軸:晨風(The Elder Scroll: Morrowind)》,Bethesda Game Studios, 2002;右下:《超級馬里奧兄弟(Super Mario Bros.)》, Nintendo, 1985
3. 目標
承接前文,Greg指出交互必須具有目標,在不同的選擇之中玩家會根據遊戲的目標選擇一個最優解。以國際象棋為例,每一步玩家都需要考慮遊戲的狀態,也需要考慮對手決定的可能性。
那麼是否所有的遊戲都有目標呢?大部分遊戲是有目標的,而且它們的目標非常明顯,但是某一些遊戲並沒有明確的目標。《模擬城市》(SimCity)就像是一個發光的彈力球,你可以在手裡把玩它,也可以把它當作是籃球或者足球,它本身是一個有玩家定義目標的玩具。
《模擬城市》本身並不具備遊戲設計師定義的目標,而是把決定權交還給玩家,給玩家更大的自由度,遊戲本身更不存在輸贏的判斷。然而,沒有明確的目標並不是指的沒有目標,即使是沒有任務系統,也需要遊戲設計師在遊戲內部設計引導。《SimEarth》是一個反面案例,它和模擬城市都提供玩家許多可以調配的參數,來達到模擬經營或者建造的目的,然而在《SimEarth》裡,玩家只能改變參數,就像是撥動燈泡開關一樣。而《模擬城市》則可以建造一個郊區烏托邦,或者是一個大都市,甚至是一個沒有重工業的中心城市。

《模擬城市(SimCity)》,EA, 1989

SimEarth, Maxis, 1990
在MUD和RPG遊戲中,玩家可以通過網絡鏈接和其他玩家形成鏈接,同時探索這個遊戲世界,這同樣也是一種內在驅動力的遊戲模式。(注:MUD遊戲是指Multiple-user Domain或者Multiple-user Dougeon,是一種以文字為主要模式的虛擬遊戲,可以當作是電腦版的DND。與MMORPG不同之處在於,MUD沒有系統設置的主線支線任務,它是MMORPG的原型,比如EverQuest。)當然這並不是在否定遊戲中目標的意義,遊戲是由目標驅動的,但只有目標是不足夠的。
4. 困難與挑戰
當我們在談論競爭的時候,實際上是在談論遊戲中的挑戰。Greg用《勇敢的小英格蘭》(Plucky Little England)做了一個假設,在二戰法國的失敗後,玩家的目標是選擇自由與民主並且反對壓迫與黑暗,接下來有兩個選擇,投降或者吐痰到希特勒的眼睛上。毫無疑問,第二個選擇會贏得遊戲的勝利,然而這個勝利沒有任何挑戰。
遊戲中的挑戰與困難可以有多種多樣的形式,不僅僅只是一個壞人或者敵人,它也可以是自然的不可抗力、壞脾氣的後媽、或者是玩家不能達到好結果的任何無能的條件。在DND中,挑戰可以是遊戲裡的怪獸,NPC,甚至是遊戲中的劇情敘事,都能阻礙玩家毫無障礙地直達目的。那麼提高遊戲的難度就一定會讓遊戲變得更有趣嗎?當遊戲過於間的的時候,玩家會覺得沒有挑戰性,遊戲過於困難則會擊敗玩家的自信心,做到二者之間的平衡需要設計師根據作品主題把握。
最經典的例子是魂系列遊戲,不少玩家從《惡魔之魂》開始就批評遊戲做得太難。隨著一代代作品的迭代,宮崎英高不斷調整遊戲機制,最終明確了遊戲本身是希望讓玩家從挑戰中獲得成就感,而不是故意為難玩家。《艾爾登法環》(Elden Ring)發售前宮崎英高在訪談中提到:
我覺得不僅僅只是《艾爾登法環》,製作所有遊戲的理念都是設計並鼓勵玩家們克服困難,不會強制難度或者做一些為了難而難的事情。希望玩家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研究這個遊戲,記住發生了什麼,吃一塹長一智。我們不希望玩家覺得遊戲的懲罰機制不公平,而是有更多的機會去戰勝困難並且取得進步。魂like遊戲經常以變態難的關卡和難以上手著稱,但是我們嘗試去設計一個新的越挫越勇的正反饋循環,並讓玩家樂在其中,希望《艾爾登法環》和它提供的新的選擇可以讓它在這方面取得成功。[3]
宮崎英高的一系列作品實際上一直在不斷探討遊戲難度和玩家感受的平衡,從最初的地圖和高難度boss招式,到如今玩家可以通過不同的戰鬥方法獲取不同難度的遊戲體驗,他把挑戰的定義擴展到遊戲的方方面面。

《艾爾登法環(Elden Ring)》,FromSoftware, 2022
5. 結構
Eric Zimmerman說過,遊戲就是慾望的結構(Games are stuctures of desire)。慾望指遊戲的目標,結構指的是遊戲規則對手和軟件本身等的交互所組成的集合。比如《警察捉小偷》,兩隊小孩子會分別扮演警察和小偷,而扮演或者假裝,就是這個遊戲中最小的結構。在桌遊中,遊戲結構通常只包含文字上的遊戲規則,其它的結構都是由玩家自己對於遊戲的理解來構成的。電子遊戲則不同,由於電子遊戲已經在程序中預設好所有的數據和邏輯代碼,這些部分對於玩家是隱藏的,不像桌遊的規則是寫在紙上的。
遊戲結構會影響玩家的行為,在遊戲《Ultima Online》和《EverQuest》兩個MMORPG中,最大的區別是玩家是否可以通過擊殺其它玩家獲取升級資源,因此在《Ultima》裡玩家會選擇殺死其他玩家,而在《EverQuest》裡玩家會互相幫助擊殺其他怪物。
當然,遊戲影響玩家行為並不意味著遊戲會決定玩家的行為,玩家在遊戲中是自由的,不會被設計師直接的獎勵和懲罰指導。設計師不會非常直接地建立一個非常嚴厲的機制去鼓勵玩家互相廝殺,更不會給過分多的獎勵,而是會通過遊戲結構的設計讓玩家可以順著他們的直覺去探索世界。

左:Ultima, Richar Garriott, 1981;右:EverQuest, Verant Interactive 989 Studios, 1999
6. 遊戲內的含義
遊戲內的含義是由遊戲結構製造的,且只在遊戲語境內起作用。這也是作者前文提到的假裝或者試圖成為所構成的遊戲語境,玩家可以意識到遊戲本身是假的,但是在遊戲之中的玩家必須把遊戲這件事情當真。比如在大街上如果有人給一個人大富翁中得100元,這個人一定會覺得很奇怪,而這100元在遊戲中卻是合理的。
人類學家赫伊津哈在《遊戲的人》中指出,遊戲不是真實的生活,而是在時間和空間上剝離於日常生活的活動[4]。遊戲的語境提供了玩家一個環境去探索遊戲本身結構和系統,它不像線性敘事的文字類小說一樣可能性是唯一的,也不像現實生活的可能性是確定的不可逆轉的,遊戲的特性就是可以發掘多種可能性。
《史丹利的預言》(The Stanley Parable)作為一個有代表性的元遊戲,它不僅僅和現實中的玩家有遊戲機制和劇情上的互動,同時玩家還可以通過不斷重複選擇不同的道路來達成不同的結局。元遊戲有趣的點在於,它讓玩家既感受到遊戲本身具有的脫離現實的語境,同時又用巧妙的手法鏈接玩家和現實世界,試圖去打破這個語境的隔閡。
《誰是萊拉》(Who’s Lila?)也運用了類似的手法,最後通過玩家的視角回答了這個模稜兩可的問題,玩家可能是多個萊拉之一。

《史丹利的預言(The Stanley Parable)》, Galactic Cafe,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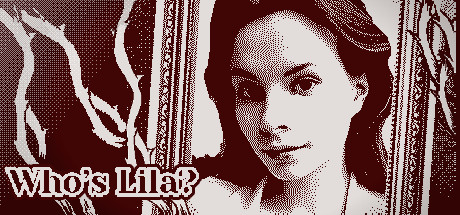
Who's Lila?, Garage Heathen, 2022
7. 何為遊戲
從上個世紀初開始,就有許多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研究何為遊戲,遊戲的邊界是什麼。直到上世紀末的narratology和ludology之爭,玩家和學者對於遊戲的定義依舊沒有達成共識,甚至是如今遊戲種類層出不窮還是沒有解決當年的定義大戰。學者們用無數詞語去定義遊戲,比如Anthropy Anna和Clark Naomi的書籍《A Game Design Vocabulary》也只能試圖使用她們自己的語言去描述遊戲,卻沒有人可以用一個確定的定義去規定遊戲的邊界在哪[5]。我們可以說遊戲是具備某種特性的,卻不能說具備某種特性的一定是遊戲。
Greg在文末提到,遊戲設計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設計師有無數種失敗的方式,只遵循以上的規則是完全不夠的。我們也可以看到,當代藝術,獨立遊戲,Mini Game都在不斷髮現新的規則,又打破規則。我想,去尋找遊戲定義的邊界,不如在做遊戲中理解玩家在遊戲行為中找到了什麼樣的樂子。
參考文獻
[1] Chris Crawford, The Art of Computer Game Design, McGraw-Hill/Osborne Media, 1982
[2]Frasca, Gonzalo. "Ludologists love stories, too: notes from a debate that never took place." DiGRA conference. 2003.
[3] Playstation Blog,徐殊昱 譯,《Playstation Blog1月28日宮崎英高訪談翻譯》,2022.01,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5044030?spm_id_from=333.999.0.0
[4] Johan Huizinga,《遊戲的人》,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10
[5]Anthropy Anna, Clark Naomi, A Game Design Vocabulary, Addison Welsey, 2014
公眾號 三人行CLU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