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katharsis)。 ——亚里士多德《诗学》
Mimesis(摹仿说)是古希腊文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诗摹仿自然。从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文学艺术)怎么摹仿自然,摹仿的究竟是哪种自然,诗摹仿自然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些问题贯穿至今,直到现在仍然被人津津乐道。这句概念本身看似很简单明了:无论画家还是诗人,在创作时想脑海中已经有一副模模糊糊或相对清晰的“相”,他们利用手中的工具尽其所能将那一“相”给记录下来,作品成为了传达这一相的媒介。
摹仿说的一个大前提是人所共同的一些特质与记忆——生理上,人人都具有“摹仿”的本能,所有人的成长几乎全部依靠“学习/摹仿”方能进行,而一些共同的记忆或情感结构则让观看文艺作品的人理解并感受到作家想要传达的“相”。因此文艺作品随时都拥有十分强大的感染力,而它们又是多元的且被交叉的一个一个小群体共同欣赏。这一观点恰好可以同样解释玩家也成为大小不一的多个群体,每个群体特有其游戏品位。
摹仿说从未中断过,它在后来又有了许多阐释,如“镜子”,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们常常如同镜子一般细细描写一个房间的布局、氛围、物品种类及个数、报纸上的日期和标题、装饰性的羽毛被摆放在哪里、五斗柜是什么年代制作及其尺寸……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往往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高清镜子,读者跟着镜子走来走去,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人、环境、道德、恋爱和复仇。时代远逝,镜子却尚能留存,给后来者幻想。即使往后到电影的时代,电子游戏的时代,大多数了不起的作品往往都延续了十九世界小说这种“摹仿”。
即使是在现代主义、表现主义蔚为壮观的“现代”,摹仿说也并未慌乱了阵脚。诗摹仿自然——但从柏拉图开始,自然就并不指向一种普通的现实自然。人的心灵也是一种自然,人的感觉、幻觉、癔梦或者杂乱无章的意识流,都是自然的一部分。甚至那些破碎的记忆片段、不成章法的笔触和意象拼接、痴人说梦般的胡言乱语……这些更是原始的、不经加工的“自然”,荣格拿起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带着极大的厌恶读罢,“我带着失望懊恼把它丢了,就是今天,它同样使我乏味……”但却不得不承认那部作品真正彰显了现代的精神,相反,是我们这些爱看“起承转合”故事的老调读者才是停留在中世纪的泥沼中不愿出来。也就是说,是我们不愿接受那种“自然”,但《尤利西斯》是更“现代地”摹仿了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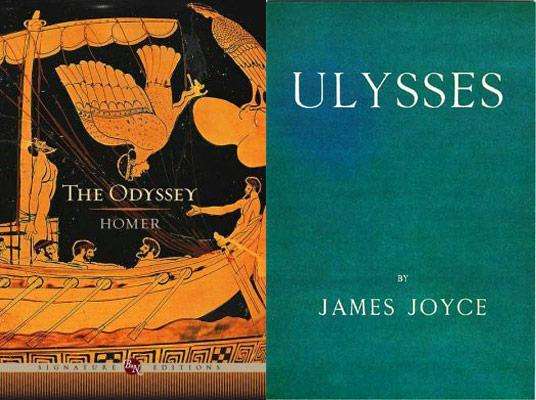
万物皆可摹仿,只是我们自己无法承受许多镜子的重量,我们也因此失去了太多认识到其他“物”的机会。
然而,如上所述,真真假假,都是自然,摹仿无分好坏,只看读者能否体会其中滋味。万物皆可摹仿的同时,人的判断力和衡量尺度又被彻底拿走了。读者也好玩家也罢,没有人想要交出自由评判、批评的权力。喜欢的就是好,厌恶的就是不好,没感觉的就是一般,这是所有人的本能,与“摹仿”本能一样关键。很多时候,别说读者,连作家自己都不知道它的作品在“摹仿”什么,显然摹仿说并不能解释一部作品的特别性。如果强行给一切作品找个一个摹仿对象,那自然就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此除了镜子之外,尚有另一个关键的意象——灯。
灯是作者自身的心灵,是他想要表达自我,所以才造了一盏灯去照耀出去。这灯确立了一个行动的主体——作者自我,这一自我是独特的,是它个人的成长与环境,时代与个人,痛苦与快乐……这一切带有偶然性的组合而形成的一个“整体”。它不是一种客观自然,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每个个体在读、看、玩的时候,都在注视那个作品中的自我,并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借助那个自我完成了自己的自我。这是一个作品的意义,同时也是为什么我们喜欢一部分作品,被它震撼、感染、影响的原因。然而灯是不是也是“摹仿”的一部分?灯照亮了一种实然的世界,但它仍通过一些“集体意识”或传统方能被读者感受和发现。读者在作者的“灯”中发现了一个新的自我。
镜与灯,自然与自我,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解释文学艺术作品的理论体系。如果游戏也能用镜与灯去解释,那么游戏就是艺术这一观点就可以解释通了。
一款常规意义上的游戏由两种摹仿构成——设计师提供第一个完整并带有一定长度的摹仿,通过碎片或线性的方式迈入游戏的各个要素中(界面、音乐、怪物名字、动画),它不断赋予玩家目标。第二个是玩家自己的创造性摹仿,玩家利用游戏中有限的交互规则自行行动,自觉或不自觉地摹仿一种现实的或想象的行动,这些摹仿是玩家个人创作的,摹仿的对象,摹仿是否完整都是不确定的(它不必定是有意义的,现代作家也会这么写作品)。
第一种摹仿表明了游戏所直承的文艺“摹仿说”;第二种摹仿则佐证了人的“摹仿本能”。
《巫师3》中有一个插曲式支线任务,一个青年人总是找杰洛特(你)比武,三番四次,你对这闹剧并不上心,或打架或劝说将那青年人打发。你选择打他几次,他都逃走并说要报仇,直到有一次他又来找你比武,这次你突然发现“剧情活”失效了,年轻人没有过场动画和后续交代,直接死在了你脚下。你对此心生错愕,等待一会,发现设计师没有给你提供新的目标……只有他的尸体仍在脚下。
这场令人错愕的死亡在当时引起了我的恐惧与怜悯,年轻人鲁莽地比武,一招不慎终于失手死去,这本应是合理的事。然而他总能逃过一劫,让我习惯性认为天神本就庇护于他。直到他突然倒在我面前,我才意识到一个青年的生命之花就这样凋谢了,且永远不会再度开放了。无常的命运始终让我们敬畏并恐惧,而渺小之人的脆弱与生命的枯萎则引起我们的同情与怜悯……我们在这种体验中得到了净化(katharsis)。
阅读《伊利亚特》时,每一次战争双方总有死亡,其中一场战争中,无数天真无邪,初尝青春而又充满幻想的特洛亚青年不得已卷入战争,被希腊英雄们接连被杀死,一个又一个倒在了特洛亚城前养育他们的大地上。
游戏在此处失去了目标,我在经过以上震颤后,看到持剑伫立的杰洛特,随意按了攻击键后,发现他似乎在舞剑——这本是一个攻击行为,又是一场表演。我在倒地的青年人周围舞了一圈剑,想象自己完成了一场严肃的比武仪式。这是我的摹仿,而这一悲剧此时在我心中才算完整。
游戏所达成的两种“摹仿”未尝不对应了“镜与灯”。这两种摹仿由此形成了极具叙事张力的“镜子”大作如《战神》《古墓丽影(新)》,也有几乎没有目标或者目标极其延宕的沙盒、开放游戏。当然更有一些想要将镜子与灯都作进去的游戏作品,其成果有佳作,有败笔。
除此之外,游戏在现代的今天,越来越多地获得人的时间(生活),传统意义上的“摹仿”似乎又很难用来去定义游戏了。如果游戏变成了现代生活本身,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极大一部分时,那它还能是古典意义上的摹仿么?想象的空间无比接近现实时,它比现实更加纯粹。
相关书籍:
- <伊利亚特>
- 荷马<奥德赛>与<尤利西斯>
- <镜与灯>
- <诗学>
- <摹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