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是對於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語言,具有各種悅耳之音,分別在劇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動作來表達,而不是採用敘述法;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katharsis)。 ——亞里士多德《詩學》
Mimesis(摹仿說)是古希臘文論中的一個關鍵概念——詩摹仿自然。從德謨克利特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詩(文學藝術)怎麼摹仿自然,摹仿的究竟是哪種自然,詩摹仿自然的意義又是什麼……這些問題貫穿至今,直到現在仍然被人津津樂道。這句概念本身看似很簡單明瞭:無論畫家還是詩人,在創作時想腦海中已經有一副模模糊糊或相對清晰的“相”,他們利用手中的工具盡其所能將那一“相”給記錄下來,作品成為了傳達這一相的媒介。
摹仿說的一個大前提是人所共同的一些特質與記憶——生理上,人人都具有“摹仿”的本能,所有人的成長几乎全部依靠“學習/摹仿”方能進行,而一些共同的記憶或情感結構則讓觀看文藝作品的人理解並感受到作家想要傳達的“相”。因此文藝作品隨時都擁有十分強大的感染力,而它們又是多元的且被交叉的一個一個小群體共同欣賞。這一觀點恰好可以同樣解釋玩家也成為大小不一的多個群體,每個群體特有其遊戲品位。
摹仿說從未中斷過,它在後來又有了許多闡釋,如“鏡子”,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小說家們常常如同鏡子一般細細描寫一個房間的佈局、氛圍、物品種類及個數、報紙上的日期和標題、裝飾性的羽毛被擺放在哪裡、五斗櫃是什麼年代製作及其尺寸……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小說往往是屬於那個時代的高清鏡子,讀者跟著鏡子走來走去,看到了那個時代的人、環境、道德、戀愛和復仇。時代遠逝,鏡子卻尚能留存,給後來者幻想。即使往後到電影的時代,電子遊戲的時代,大多數了不起的作品往往都延續了十九世界小說這種“摹仿”。
即使是在現代主義、表現主義蔚為壯觀的“現代”,摹仿說也並未慌亂了陣腳。詩摹仿自然——但從柏拉圖開始,自然就並不指向一種普通的現實自然。人的心靈也是一種自然,人的感覺、幻覺、癔夢或者雜亂無章的意識流,都是自然的一部分。甚至那些破碎的記憶片段、不成章法的筆觸和意象拼接、痴人說夢般的胡言亂語……這些更是原始的、不經加工的“自然”,榮格拿起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帶著極大的厭惡讀罷,“我帶著失望懊惱把它丟了,就是今天,它同樣使我乏味……”但卻不得不承認那部作品真正彰顯了現代的精神,相反,是我們這些愛看“起承轉合”故事的老調讀者才是停留在中世紀的泥沼中不願出來。也就是說,是我們不願接受那種“自然”,但《尤利西斯》是更“現代地”摹仿了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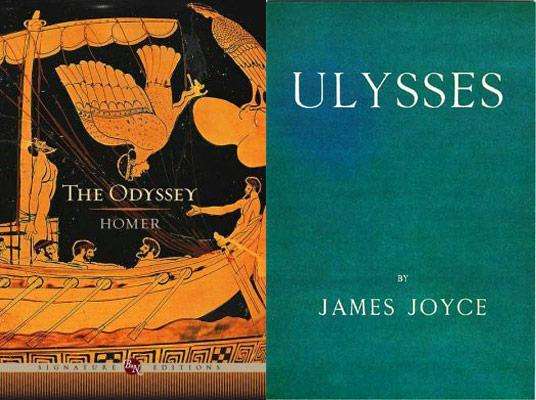
萬物皆可摹仿,只是我們自己無法承受許多鏡子的重量,我們也因此失去了太多認識到其他“物”的機會。
然而,如上所述,真真假假,都是自然,摹仿無分好壞,只看讀者能否體會其中滋味。萬物皆可摹仿的同時,人的判斷力和衡量尺度又被徹底拿走了。讀者也好玩家也罷,沒有人想要交出自由評判、批評的權力。喜歡的就是好,厭惡的就是不好,沒感覺的就是一般,這是所有人的本能,與“摹仿”本能一樣關鍵。很多時候,別說讀者,連作家自己都不知道它的作品在“摹仿”什麼,顯然摹仿說並不能解釋一部作品的特別性。如果強行給一切作品找個一個摹仿對象,那自然就變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此除了鏡子之外,尚有另一個關鍵的意象——燈。
燈是作者自身的心靈,是他想要表達自我,所以才造了一盞燈去照耀出去。這燈確立了一個行動的主體——作者自我,這一自我是獨特的,是它個人的成長與環境,時代與個人,痛苦與快樂……這一切帶有偶然性的組合而形成的一個“整體”。它不是一種客觀自然,但卻是實實在在的。每個個體在讀、看、玩的時候,都在注視那個作品中的自我,並結合自己的生命體驗,藉助那個自我完成了自己的自我。這是一個作品的意義,同時也是為什麼我們喜歡一部分作品,被它震撼、感染、影響的原因。然而燈是不是也是“摹仿”的一部分?燈照亮了一種實然的世界,但它仍通過一些“集體意識”或傳統方能被讀者感受和發現。讀者在作者的“燈”中發現了一個新的自我。
鏡與燈,自然與自我,構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解釋文學藝術作品的理論體系。如果遊戲也能用鏡與燈去解釋,那麼遊戲就是藝術這一觀點就可以解釋通了。
一款常規意義上的遊戲由兩種摹仿構成——設計師提供第一個完整並帶有一定長度的摹仿,通過碎片或線性的方式邁入遊戲的各個要素中(界面、音樂、怪物名字、動畫),它不斷賦予玩家目標。第二個是玩家自己的創造性摹仿,玩家利用遊戲中有限的交互規則自行行動,自覺或不自覺地摹仿一種現實的或想象的行動,這些摹仿是玩家個人創作的,摹仿的對象,摹仿是否完整都是不確定的(它不必定是有意義的,現代作家也會這麼寫作品)。
第一種摹仿表明了遊戲所直承的文藝“摹仿說”;第二種摹仿則佐證了人的“摹仿本能”。
《巫師3》中有一個插曲式支線任務,一個青年人總是找傑洛特(你)比武,三番四次,你對這鬧劇並不上心,或打架或勸說將那青年人打發。你選擇打他幾次,他都逃走並說要報仇,直到有一次他又來找你比武,這次你突然發現“劇情活”失效了,年輕人沒有過場動畫和後續交代,直接死在了你腳下。你對此心生錯愕,等待一會,發現設計師沒有給你提供新的目標……只有他的屍體仍在腳下。
這場令人錯愕的死亡在當時引起了我的恐懼與憐憫,年輕人魯莽地比武,一招不慎終於失手死去,這本應是合理的事。然而他總能逃過一劫,讓我習慣性認為天神本就庇護於他。直到他突然倒在我面前,我才意識到一個青年的生命之花就這樣凋謝了,且永遠不會再度開放了。無常的命運始終讓我們敬畏並恐懼,而渺小之人的脆弱與生命的枯萎則引起我們的同情與憐憫……我們在這種體驗中得到了淨化(katharsis)。
閱讀《伊利亞特》時,每一次戰爭雙方總有死亡,其中一場戰爭中,無數天真無邪,初嘗青春而又充滿幻想的特洛亞青年不得已捲入戰爭,被希臘英雄們接連被殺死,一個又一個倒在了特洛亞城前養育他們的大地上。
遊戲在此處失去了目標,我在經過以上震顫後,看到持劍佇立的傑洛特,隨意按了攻擊鍵後,發現他似乎在舞劍——這本是一個攻擊行為,又是一場表演。我在倒地的青年人周圍舞了一圈劍,想象自己完成了一場嚴肅的比武儀式。這是我的摹仿,而這一悲劇此時在我心中才算完整。
遊戲所達成的兩種“摹仿”未嘗不對應了“鏡與燈”。這兩種摹仿由此形成了極具敘事張力的“鏡子”大作如《戰神》《古墓奇兵(新)》,也有幾乎沒有目標或者目標極其延宕的沙盒、開放遊戲。當然更有一些想要將鏡子與燈都作進去的遊戲作品,其成果有佳作,有敗筆。
除此之外,遊戲在現代的今天,越來越多地獲得人的時間(生活),傳統意義上的“摹仿”似乎又很難用來去定義遊戲了。如果遊戲變成了現代生活本身,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極大一部分時,那它還能是古典意義上的摹仿麼?想象的空間無比接近現實時,它比現實更加純粹。
相關書籍:
- <伊利亞特>
- 荷馬<奧德賽>與<尤利西斯>
- <鏡與燈>
- <詩學>
- <摹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