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游戏本体论的研究都是西方游戏研究的显学。但在发展中国家,历史原因、文化动因与制度特殊性使得我们不可能“只就游戏而谈游戏”,而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游戏的社会影响。
本文围绕着“游戏能在社会中发挥何种作用”梳理了西方较为经典的游戏理论成果,特别围绕游玩(Play)与游戏(Game)的关系、牵涉到社会的本体论核心概念“魔圈”(Magic Circle)的国际学术理论进行批判性研讨,以结合中国的状况进行反思,并通过行动研究,展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作者:刘梦霏
刊载栏目: 《当代电影》杂志社《当代动画》2024年第2期
原文链接:点击跳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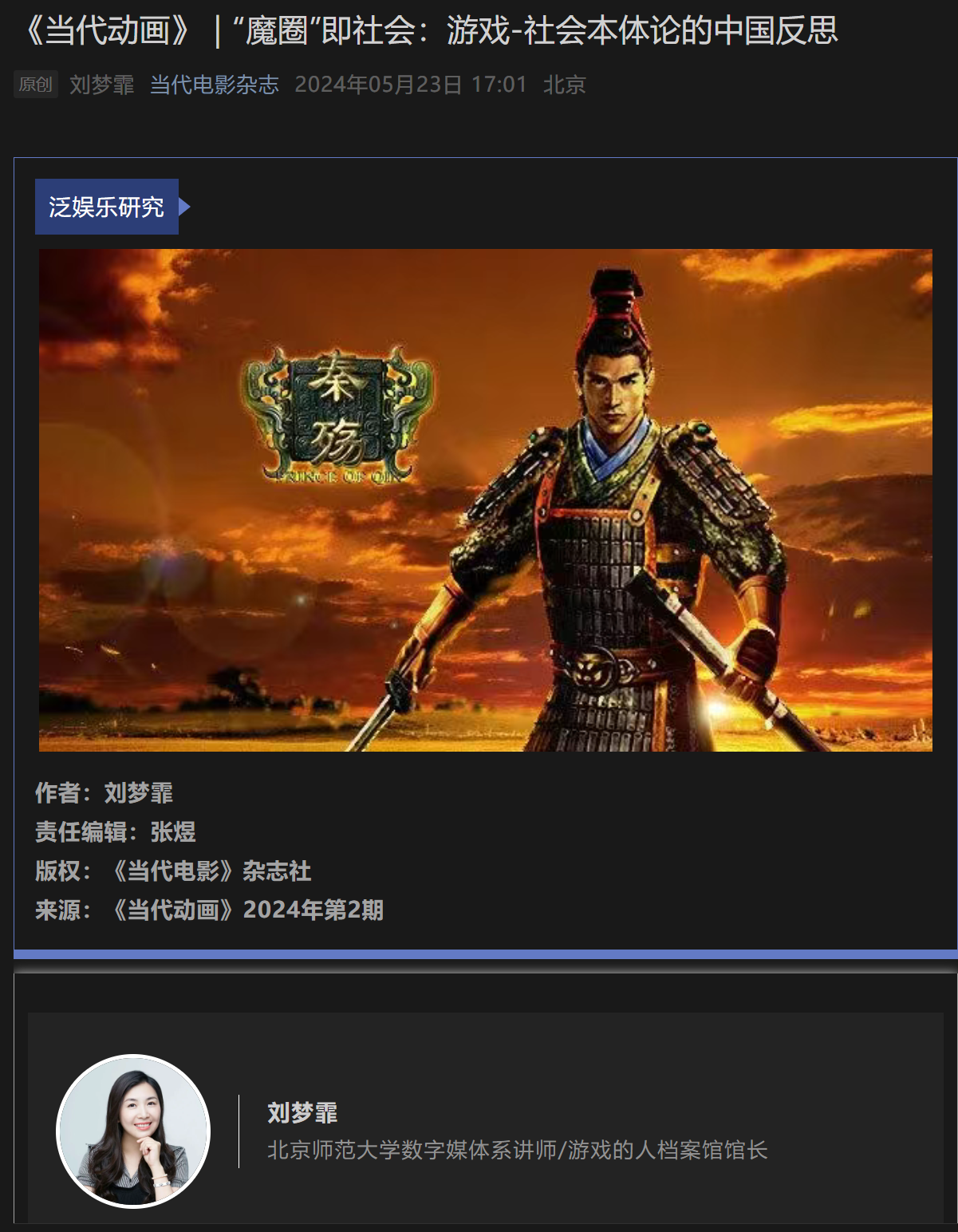
提要:一直以来,游戏本体论的研究都是西方游戏研究的显学。但在发展中国家,历史原因、文化动因与制度特殊性使得我们不可能“只就游戏而谈游戏”,而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游戏的社会影响。本文围绕着“游戏能在社会中发挥何种作用”梳理了西方较为经典的游戏理论成果,特别围绕游玩(Play)与游戏(Game)的关系、牵涉到社会的本体论核心概念“魔圈”(Magic Circle)的国际学术理论进行批判性研讨,以结合中国的状况进行反思,并通过行动研究,展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关键词:中国游戏理论 游戏-社会研究 游戏分类 游戏化 游戏正向价值 中国游戏史
一、Game or Play?
在社会中定位游戏的功能
(一)玩家-规则-世界:游戏本体论的“共识”
要理解游戏能在社会中发挥何种作用,我们首先要理解“何为游戏”。在与本文同系列的对阿尔萨斯教授的访谈中,他谈到“‘游戏’(game)是一个浮动的能指(signifer)……游戏中现象实在是太多样化了,我们无法用某一种模型或理论框架来捕捉它”。无独有偶,同为北欧学者的弗兰斯·迈尔在《游戏研究导论》中也表示“游戏研究的主题的渗透性太强……我们并不认为存在着一个关于游戏的绝对正确、不能从任何角度被驳斥的定义。”(1)
这一说法的背景是游戏研究(Game Studies)作为一个领域建立(2)之后,游戏本体论(Game Ontology(3))在西方蓬勃发展,诞生了数种游戏的本体论。一旦对其进行要素的共性分析,就会发现本体论之间的矛盾几乎难以调和。为建立一套合理的框架,阿尔萨斯教授提出,我们需要建立“元本体论”(Meta-Ontology)架构,并从物理性、结构性、沟通性、精神性四角度对现有的游戏本体论进行梳理(见表1)。(4)

表1.阿尔萨斯元本体论模型层级细分表
这样的元本体论使我们面对纷繁的游戏本体论理论模型时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框架。然而对于本文主题“游戏的社会功能”这样具体的主题却并不适用。阿尔萨斯的元本体论架构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基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原理,展现出游戏本体论可以通过描述性模型,而非定义性模型来进行描绘。意即,并非“拥有了这些特性的就是游戏”,而是“我们观察到的游戏具有这些特性”。这样一来,就可以使用元本体论的方法,围绕具体主题进行聚类整理了。根据研究,最适合本文主题的是阿尔萨斯2003年提出的规则-玩家-世界的三分模型。(5)我们因而基于这个分类,统合了现有的流行本体论,绘制了表2。

表2.从规则-玩家-世界三分所做的游戏本体论聚类分析
表2都是围绕着“Game”所做的定义与结构切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
第一,几乎所有学者都围绕着游戏的规则,或足以表现游戏规则的游戏界面(游戏的形式化部分)进行了讨论。由此可见,游戏的规则是游戏本体论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
第二,部分学者在讨论游戏本体论时,讨论到了玩家的影响,重点在于玩家的动态操控对游戏本体的实现。若我们引入与文学、电影等媒介的综合对比,则会发现,与相对被动的“观众”“读者”相比,主动的“玩家”可能是游戏最大的特点。
第三,大多数学者在讨论游戏本体论时,都牵涉到了“世界”。不过,学者们的重点会依据他们对游戏理解的不同,而在讨论游戏世界时分别指涉游戏内虚构世界的种种设计,或是现实世界的文化与产业影响(如阿尔萨斯、朱尔、康萨克)。
总的来说,如果说上文所总结的第一和第二条的重点是游戏的媒介特点的话,第三条所处理的就是我们作为社会一员而不得不思考的主题:世界与游戏,或者说社会与游戏的关系。与极为清洁、高度一致的前两类不同,学者时而指涉虚构世界,时而指涉现实世界的状况,揭示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分歧。
(二)Game or Play,游or戏?
这种分歧本质上是因为在西方,特别是在英语环境下,game与play这两个概念是分开的。(6)在学术翻译中,我们将前者翻译为“游戏”而后者翻译为“游玩”。(7)游戏研究与游戏设计的经典教科书《游玩规则》(Rules of Play)中将Play定义为“一种在更严格的结构之下的自由行动”,而Game定义为“玩家处于人造冲突之中的一套体系,以规则为特点,可带来可量化的结果,(8)并提供了一张圈层图展示这两个概念同为名词时的相对大小,因为游玩(Play)更松散,所涵盖的人类行为更广,我们通常认为它比游戏(Game)更大。
由于学科发展的历史原因,关于游玩的研究更早。赫伊津哈1938年通过《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成分》(9)一书开启了游玩研究(Play Studies)的领域。他提出,就好像我们是智人(Homo Sapiens)一样,我们所有人实际上都是游戏的人(Homo Ludens)。他指出“游戏,是特殊的行为方式,是有用意的形式,是社会功能”。(10)那么,游戏能起到何种社会功能呢?赫伊津哈认为,“人类社会的重要原创活动从一开始就全部渗透着游戏……文明生活的重要原生力量——法律与秩序、商业与利润、工艺与文艺、诗歌、智慧与科学,都源自神话和仪式,都根植于游戏的原始土壤中”,随后,他还大胆地宣称,不是要把游戏归入文化或者强调游戏的文化性,而是要“把文化归入游戏类别”(sub specie ludi),要指出“游戏与文化确乎彼此渗透交融……我们的全部意图就是要表明,真正、纯粹的游戏是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11)
赫伊津哈开启的游玩研究很自然地讨论游玩的行动如何通过仪式影响社会,且往往覆盖到人类学、民族志等现实中的游玩行动(12);而更晚近的、千禧年后才诞生的游戏研究则将自己与游玩切割开,试图更干净地只讨论数字游戏及其先驱。
实际上,西方能将游玩与游戏分开讨论,部分地也是因为游戏产业的发展以及游戏本身从文化之中汲取能量的通路是通畅的,因而可以容纳更细致的研究。在所有的形式化定义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法国学者罗杰·凯卢瓦于1958年,在赫伊津哈的道路上所做的进一步阐发。他建立了一个矩阵,将人类的复杂游玩形式归入四个主要类别:Agon-竞争类游戏、Alea-机运类游戏、Mimicry-模仿类游戏、Illinx-眩晕类游戏和一个由两极组成的连续统之中,这两极来自于他从古希腊语及拉丁语中打捞的两个概念,一端是戏耍(Paidia,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接近游玩),一端是技游(ludus,一套强制、专断的规则体系,接近游戏)。(13)四个类别中的每个类型都存在着从松散游玩到严格规定的游戏之间的变体与子类型。
戏耍-游玩(Paidia-Play,简称戏游)与技游-游戏(Ludus-Game,简称游戏)构成的连续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从本文的论题来考虑,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从何时起,又是为何,松散的游玩要演变为严格规定限定的游戏呢?
笔者认为,规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难看出,戏游是相当个人化的,它的自由、随心所欲的特点,都在于这是一套在玩家内部的游玩状态。一个在海边玩沙子的人可以毫无目标,也不遵循任何规则,只是自由地玩耍。然而,当有“他者”加入游戏,游戏从私人向公共领域转换之时,规制化的过程就会出现。原本自由的玩沙子的人,需要跟加入游戏的其他玩家商量一套双方都能接受的规则,拟定好像“搭海滩上最高/最丑的沙堡”或“消灭其他人搭的沙子建筑”这样的目标与结局方式,游戏才能在两个人之间存在。哪怕游戏的协约是“我们就这么瞎玩”,这也是一种实质上的规则。
换言之,游戏规制化是为了方便社会协同。戏游成为了游戏,是因为有规则才有社会;一个人的游戏不需要规则或者结果也可以运行;宣之于口的规则和命名了的游戏,说到底是为了社会。强制、专断的游戏体系本身就是社会规制;换言之,社会性天生就是游戏——强规则体系的ludus-game——的本质属性。
若我们回到赫伊津哈的原书,会发现他的母语荷兰语中,游玩与游戏是一个词(Spel)。换言之,英文世界对于Play和Game的区分,以及这两个领域在进行本体论研究时有意为之的区隔,也许是完全无益的纷乱肇始。
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做出的最主要发现之一,是仪式是游戏的等价物。若我们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理解仪式,它本来就是为一系列动作赋予符合社会价值观的反馈。游戏是仪式,是因为它本质上就是由玩家与规则系统互动而生的动态行动体系。游戏“戏假情真”的本能作用,以及塑造宗教、民族、文化等身份认同的作用,(14)实际上都是戏游-游戏一体自然带来的社会影响。将游玩与游戏分开,在不同的领域加以研究,实际上天然地破坏了游戏自生的社会影响。
传统媒介中,我们可以把受众研究与文本研究分开,但游戏其实对所有的传统本体论结构提出了挑战:游戏的本体论,是一种流动的、文本无法抓住的结构,因为它有一大部分是在玩家的精神世界进行的,游戏存在于动作之中。静止的游戏,不过是一套代码,它并不真的“存在”。如果严谨论证的话,游戏存在于玩家开始玩游戏的那一刻,单纯的视觉符号与文本符号所展现的,永远只是游戏物质性的部分,是它的“外部”,而不是它的实质。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为游戏改进本体论结构的话,它势必不是干净切割的实验室标本切片,而一定是一种拖泥带水的体系。赫伊津哈是对的,重要的从来不是游戏,或者游玩。重要的是“游戏的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游戏-人”。
(三)赫伊津哈-凯卢瓦悖论:玩家能否穿透魔圈?
已有的本体论研究,特别是赫伊津哈-凯卢瓦的讨论,就是没有考虑到这种游戏-人的整体,而产生了一个致命的谬误:他们的游戏没有功能,因为他们的玩家没有记忆,也似乎没有穿透魔圈(Magic Circle)(15)的能力。凯卢瓦强调所有的游戏“结束时的状态与其开始时的状况别无二致”,(16)并以此作为游戏“非生产性”的证据,而忽略了玩家本身的主动性,以及玩家会将记忆与技艺一同带出游戏的魔圈的可能性。
实际上,如果玩家真如赫伊津哈与凯卢瓦所承认的一样主动,他们的游戏经验就不会只停留在游戏之内,而是会自然地被带出魔圈,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若非如此,游戏就会永远是儿戏和消遣,而不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的所有社会规则的根基。
就这两位前辈所关心的“游戏精神”,或从玩家的品德培育来说,如果玩家的改造仅限于魔圈之内,那么凯卢瓦最看重的“游戏所贯彻的将行为与结果区分开的超脱精神……游戏调用个人所具备的优势、最大限度的热情、客观存在的机遇、冒险的勇气、审慎的谋略、以及综合运用上述各项的能力······”(17)乃至“把现实视为游戏,以从容姿态摒弃狭隘、贪婪与仇恨······的文明的作用”(18)就不可能实现了。
这种悖论的产生,正是因为两位理论家为了维持游玩/戏的纯洁性,(19)为了让游戏满足“以完美的情境取代日常的混杂状态”的状况,强行剥离游戏的社会性而造成的后果。
理解游戏中魔圈的本质,对我们正确理解游戏的社会作用至关重要。在《游玩规则》一书中,萨伦等提到,当“游戏被当作文化环境,一种与真实世界环境并行的环境”之时,“魔圈会整个消失,游戏本身会与(现实)环境处于同一圈层”。这看起来是对游戏规则的挑战,但实际上,尽管在实境角色扮演游戏(LARP)、游戏化场景及各种融合性的游戏体验中,魔圈的边界会受到“模糊、转换、融合到现实环境中”,但“决定性的游戏结构依然完好无缺”。(20)
一方面,游戏确实具有独立于现实的规则体系,处在单独的魔圈之中;另一方面,那魔圈实际上又是多孔的、渗透性的软壁,能够允许“游戏嵌套于生活方式、媒介、意识形态、历史,以及一系列社会背景之中”。(21)更不用说,自2015年以来,随着Pokemon Go等LBS地理定位为基础的游戏开始流行,数字游戏正式进入虚实相济的新纪元:虚拟世界的规则开始指引玩家在现实世界的行动。社会进入了魔圈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游戏的边界变成了社会的边界。魔圈成为了社会本身。
游戏天然就具有社会性,游戏行动本身就是在形塑现实。而这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为了抓到宝可梦而在现实地图上进行的真实物理位移既带来了Ambient play(22)的新概念,带来了虚实相济的游戏体验帮助身体锻炼、文旅探索、拉动现实经济的可能,也使得玩工(Playbor)(23)及伪装成游戏的现实剥削成为平台资本主义时代“新异化”的恶魔。
二、游戏-社会本体论的文化独特性?
中国游戏何以发挥社会功能
(一)游戏进入社会的“第二次生命”
要对游戏的社会功能趋利避害,就需要我们准确地使用理论工具。而这就会自然带来一个问题:游戏-社会本体论是否具有文化独特性?换言之,西方游戏本体论的研究,是否能指导我国的社会实践?
实际上,如果我们承认了游戏的魔圈就可以是社会本身,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进行思考,就会发现,数字游戏具有两次生命:第一次是我们在第一部分见到的所有本体论学者所积极分析的“作为作品/商品”的生命;第二次生命则是在游戏卖出一段时间,进入到社会与文化中之后,作为一种数字文化遗产而具有的生命。
如果只讨论第一次生命中的游戏作品,那么本体论是不具有文化独特性的。无论何种文化中的游戏,都是由玩家所执行的规则体系而落实的行动体系。但是,若我们讨论到游戏进入社会后的第二次生命,那么社会环境中的游戏无疑就具有文化独特性了。
那么,中国的游戏环境,是否具有文化独特性呢?文化要素是否会影响游戏在中国发挥社会功能?抑或在起作用的是其他因素?接下来,我们需要对中国语境下进入到社会的游戏的作用进行理解与思考。
(二)在中国被矮化的游戏:“君子不戏”v.s.“文明基石”
在中国这样大的游戏经济体中,以“中国并非游戏大国”来开展论述,是有冒犯性的。但事实如此。我们虽拥有一个三千亿的产业,(24)但以游戏产业的文化影响力、社会版图来看,中国游戏起到的文化功能却相当有限。
在中国,游戏是“小”的。一方面,它与“儿戏”常混为一谈,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被宽容忍受的消遣。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游戏属于青少年,甚至通常不认为成年人是游戏的主体。另一方面,游戏作为文化来说,也是小的。中国的数字游戏是实质上的大众文化,文化地位上的“亚文化”。对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游戏只是商品,没有文化。我们重视游戏在社会引发的影响,以“成瘾”形容游戏对人的强吸引力,却从内心深处不认为游戏能够承载文化价值。
日前版署出台的《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第三条[基本原则]开宗明义,网络游戏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随后紧跟的游戏产业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保护未成年人优先”,甚至放在“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之前。游戏产业的管理办法的基本原则不讨论产业的健康发展,不讨论游戏的创作问题,而特别针对青少年来“卡脖子”,就是因为在中国文化里,游戏“不成熟”。
因为游戏“不成熟”,中国知识分子对其充满偏见与鄙夷,不认为游戏是文化,因此也就既不参与到游戏这一载体的创作,也不利用游戏承载与表达价值。游戏成为了某种奇妙的只有游戏人能登陆和建设的“文化月球”。这个社会的其他人似乎都既没兴趣,也无法加入这一媒介的创作,但与此同时还保留着指责和禁止这个媒介的权利。
这种境况既有世界通行的原因——游戏的数字形式激发的新媒介恐慌,也曾在20世纪末期的美国、欧洲、日本,引发种种“教唆青少年暴力、色情”的道德指摘。此外,游戏在大众认知中作为消遣娱乐的最有吸引力的媒介形态,在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work ethic)下,也曾因为占用了工作时间而受到主流言论的抵触。
不过,在中国,我们对于游戏的态度的确额外严苛。笔者2014年曾做过关于《二十四史》中的“游戏”概念在何种语境下、由何种人言说、游戏者的社会评价如何的研究。(图1)当时研究的一个核心发现,就是儒家文化对于游戏的概念,包括语词、文化地位、道德评价上,都是贬义的态度。《二十四史》中游戏的主体—“乱国佞臣、仆、妾、奴、昏君、乱臣、正面人物的幼儿时代”以及《资治通鉴》中的龙,充分体现了一种针对游戏的文化预判:游戏属于动物层面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要低于文化;游戏的成年人绝非圣贤,甚至都不能算合格的社会成员:君主凡游戏者必为昏君,或本身是番邦蛮王。对中文中与游戏相关的字,例如戏、嬉、玩、耍等字的词源学分析,也能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文化中对游戏的认识。笔者将其概括为“玩物丧志,君子不戏”。(25)
笔者认为,这种对游戏的负面认识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集体主义倾向是有直接关系的。游戏是非常个人化的体验;非玩家往往难以理解玩家对于游戏的执著,因为他们本就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对于一个有集体主义倾向的文化来说,其中的部分个人脱离开儒家的世界,沉浸于游戏的魔圈之中是不可接受的;吸引这些人沉溺其中的游戏自然也就是不可原谅的。
中国文化中的另外几支,例如道家和佛家,对于游戏的态度则略有不同。佛教将游戏作为自由的表征,强调佛菩萨“游戏神通”“游戏度人”,这种态度与古希腊关于游戏的一种看法颇有相呼应之处;道家传统与文人雅士们,则在个人生活的层面具有游戏般的人生态度,并不排斥乐趣与享受,也常有各种雅戏怡情,《红楼梦》里的诗社、酒令,李杜都写诗赞颂的斗鸡就是其中几例。
中国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尽管在庙堂之上,他们纵横捭阖,忧国忧民,当他们退回个人的世界的时候,他们当中的很多都是“游戏的人”。例如在文人们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作诗作词,本就是遵循规则,利用有限的汉字,塑造出无限的丰富体验的文字游戏;作诗唱和,则是带有社交性的文人雅戏。古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大多都具有游戏性,或干脆就是游戏。
当儒家对于游戏的负面看法得到觉知时,我们就会发现,游戏绝不“小”,而是一种一直在塑造文化的精神性的动力。这正说明了我们的第二个论点,实际上,游戏是“大”的。它是人类无法抹消的本能,是人类塑造文明的方式,是数字社会中最具统合性、最重要的数字媒体;在一个日益虚实相济,游戏化系统弥散到生活中的世界,游戏素养(Game Literacy)——一种“游戏者批判性认识游戏,社会各界批判性认识与利用游戏的认识与行动体系”(26)便成为数字公民最重要的立身之本。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游戏经济体,拥有连续而庞大的文化遗产的中国,不应再坐视这种文化上的“错位”与“失衡”继续发生。接下来,我们回顾历史,将从产业角度理解中国游戏的发展及其特点,从而更好地定位中国社会中游戏的位置。
(三)有“法”无“道”,有“技”无“艺”的中国游戏产业史
中国游戏产业已近而立之年,但在文化表达上,却仍然青涩。实际上,中国游戏人缺乏将艺术(art)与科学融合一体,具有手工业操练特点的“技艺”(craft),目前可谓有“技”而无“艺”,有“法”而无“道”。
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游戏的发展受到文化的束缚,儒家“君子不戏”的观念限制了游戏的理念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展开,也几乎掐灭了游戏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创作表达能量的通路。20世纪90年代末,被一纸公文、市场不规范、盗版横行,以及网络游戏的新经济模式而压死的中国单机游戏产业,曾有过《赤壁》《秦殇》《大唐诗录》《中关村启示录》这样从中国本土文化中汲取能量的作品。但先行者们戛然而止的探索,配合上知识分子的不理解、游戏档案与历史保护的滞后,也使得中国游戏的“文脉”近乎荡然无存。
在这片文脉丧失的“焦土”上涌现出的下一代中国游戏人,才是当下产业的主流。网络游戏,以及中国游戏人通过聪明才智,后发而领先群伦的持续服务型商业模式,成为了中国游戏产业的立身之本。中国游戏的商业成功是在浅薄文化地层上野蛮生长而得来的艰苦果实。游戏不再是90年代的“创作”,而变成了一种“开发”,一种基于买量算法的“渠道推广”,变成了流行机制的互相借鉴与组合,而这对于提升知识分子与大众眼中游戏的文化地位显然没有太多帮助。
只有“制作”而没有“创作”,会导致中国游戏人同时缺乏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尊。即将而立之年的中国游戏行业,本身也开始谋求创作向的突破与转型。此外,发展中的数字社会要求游戏发挥正向价值,但比起一叶障目的“青少年防沉迷”,比起徒劳无功地强行把“大”游戏塞进“小”框子,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在这一历史节点,立足于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富矿,借鉴西方游戏产业与游戏学术的经验,科学地对游戏,以及游戏的社会功能进行反思。
(四)基于经济模式分类游戏,科学发挥社会功能
结合前述内容来看,中国游戏可以说同时兼具“低游戏素养”与“强社会期待”于一身。这两者的结合使得西方游戏学术传统中的游戏批评、游戏分类学都成为了某种亚文化专精知识;游戏正向价值所欠缺的前置知识太多,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与公众都无力改变游戏的现状;而年轻的中国游戏产业还没有完全诞生属于自己的游戏知识分子;游戏人的社会关怀与创作思考都不够;可以自然发挥积极社会影响的游戏,数量还不多。
在这种状况下,要发挥游戏的社会功能,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游戏素养教育来“开民智”,促进民众认知从“小游戏”向“大游戏”转变。而这又需要更多概念工具的帮助。毕竟,并不是所有游戏都有第二次生命;也不是所有游戏都值得发挥社会影响。
笔者因而遵循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判断,按照游戏被售卖的经济形态,将游戏分为作品游戏、消费游戏、赌博游戏;同时,基于经济性质而进行的划分,也可以指导我们在社会层面针对游戏的“第二次生命”进行利用与再利用(如图2所示)。(27)

图2.基于经济特性而分类的作品游戏、 消费游戏、赌博游戏
一次性买断的游戏是单机游戏玩家、主机游戏玩家常见的游戏形式,这也是在目前缺乏广泛起效的游戏分级体系的状况下,可推荐给家长、教师的一类游戏。一方面,这类游戏购买之后没有后续消费,不易引发家庭纠纷;另一方面,这类游戏比较符合“作品”而非“商品”的创作逻辑,玩家购买游戏后,开发者就可以获得收益,因此有很多精雕细琢的作品,也容易形成系列。这类游戏特别适合作为生命教育的入口,也是美育、德育、各种素养教育的完美载体,能给玩家带来审美、知识、见解、个人成长方面的提升。这类游戏当中,有不少大作可以与文学名著带来的体验相提并论,其上手难度和对玩家的要求也相应提升,是提高“游戏素养”的重要一环。我们可以将这类游戏称为作品游戏。
回看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游戏产业,会发现当时的大部分游戏都是这样的游戏。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作品游戏与文学、电影的“经典”类似,是价值观的承载者,是可以培育下一代审美的数字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因为第一部分讨论过的多孔的魔圈,以及游戏-人的综合状态,作品游戏中玩家积极行动带来的冒险,可以带来某种具有存在主义特性的、通过行动而展现的意义感,从而部分地将玩家变为某种健康的“机器中的狩猎采集人”,进而从量化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工业社会的异化中解放。(28)
F2P(Free to Play,免费下载,道具付费)游戏目前在移动平台上最常见,大多数国产流行手游都属于这个类型。实际上,“免费的才是最贵的”。这类游戏中的商品不是游戏,而是玩家。更具体地说,是玩家的时间和金钱。从开发者的角度来说,要到玩家开始游戏并产生消费之后,才能获得收益,消费点才是真正的收益点。因此,这类游戏往往拥有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消费点,或者说,是故意营造的痛苦与不便,玩家必须通过付费,来消除这些痛苦与不便。这一类游戏,可以称作消费游戏。(29)
在消费游戏中,所有的“免费”都是有代价的。例如用金钱兑换的游戏币来缩短游戏里的“建设”或“战斗”进程,本质上还是花钱买时间,不过与前文所说的直接购买游戏时间不同。直接购买游戏时间的游戏,体验是连续的;用金钱兑换时间的游戏,则会通过频繁打断玩家的游戏体验,达到让玩家痛苦的目的,玩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付费来“加速”。一天只有24小时,在游戏中花钱充时间其实是有上限的,但用金钱兑换时间是没有上限的。这种消费可以持续不断地进行,给开发者带来持续收益。消费游戏的商业模式,有时被称作GAAS(Game As A Service,持续服务游戏)。
由于这类游戏的主控权在开发者手里,普通人较难对消费游戏进行教育方面的再利用。当然,消费游戏是很多成年人的消遣,有一定的社交功能,也有健康的发泄作用,可以促进身心健康。只要对未成年人设置合理的游戏时间,消费游戏是可以存在的。不过,从社会功能来论,消费游戏本质上是一套迷你数字资本主义体系,而且往往是平台资本主义的完美工具。通过操弄游戏中的符号,以及使用一种本身具有异化特性的加速时间模式,消费游戏塑造了某种靠金钱维系的、永不落幕的消费天堂。当这种特性与持续运营的服务体系结合时,这类游戏往往会出现明显的“玩工”特性,在“上班打卡”般维系“日活跃度”“月活跃度”的持续服务体系的引诱下,玩家不知不觉成为了被异化的消费主义养料。
如果说,花钱购买游戏币兑换游戏时间还算是一个对玩家相对无害的设计,“开战利品箱”(Lootbox)则是真正“作恶”的游戏设计。它将玩家在常规游戏中可以通过技巧、努力和才智获得的东西,变成靠几率的赌博。这类游戏表面上有叙事线,有战斗系统,但它们的核心动作循环却是靠“开箱”取得的强力道具卡牌来堆数值。2018年,基于游戏学者的研究,(30)欧盟已将可兑换为现实货币的开箱机制定为赌博机制,加以严格监管。我们将以“开箱”为核心的F2P游戏称作赌博游戏。
赌博游戏不断破坏游戏的社会形象、造成代际矛盾,应当受到严格监管,在分级体系中也应划为禁止青少年进入的最高一级。从社会功能来看,赌博游戏之中的玩家很难说是处于“游戏的人”的状态。作品游戏解放性的主动行动、消费游戏中社交与消费带来的满足,都让位于一种花钱买几率、听天由命的被动状态。赌博游戏的玩家与其说是玩家,不如说是赌徒;他们失去了积极的游戏动机,不断消费投币所换取的并非拯救世界的机会,而是“为了继续玩下去:为了待机器的迷境(Zone)里,把一切都忘掉”(31)的消极心态。
从作品游戏到消费游戏,再到赌博游戏,游戏本身的艺术性是递减的,游戏作为敛财工具的经济效用却是递增的。要让游戏发挥社会价值,确实还需要我们基于科学研究,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游戏进行不同层次的再利用。从这三类游戏来看,可以说真正拥有进入社会后的“第二次生命”的,只有作品游戏。消费游戏与赌博游戏实质上都是持续服务系统,它们的“第一次生命”只要在运营,就不会终结。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游戏也完全无法进入第二次生命循环。
三、中国模式,抑或是发展中模式?
基于经济基础重新分类的游戏,以及在此分类体系上进行的针对“第二次生命”的社会功能的利用与再利用的思考,只是中国背景,或者说低游戏素养社会背景下开始建设游戏-社会本体论的开始。
我们探讨了游戏本体论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适用性,并着眼于中国游戏产业的发展和社会作用。通过对西方经典游戏理论的批判性理解和结合中国本土文化与实践的探索,我们构建了一个基于经济基础的游戏分类框架,强调游戏在社会中的第二次生命和正向价值创造。在探索中,我们发现,对发展中的游戏产业来说,剥离社会功能、精准切割的游戏本体论是难以发展的;反过来,从一开始就将魔圈的弹性考虑在内,让游戏自然发挥社会功能,反而可以带来结合产业、监管、社会各部门,以及学术的新的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
但是,在探索中我们也产生了新的疑问。虽然是基于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检视而探索游戏的社会作用,但最后生成的模式与其说是中国文化的,不如说更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模式。换言之,这次理论探索似乎反过来确证了“游戏的人”不是专属于某一个文化的,而是具有普世性。
其他潜在疑问还包括游戏素养的发展程度与所在社会的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更发达、或更贫弱的地区,文化要素会否起到更大的社会作用,抑或文化要素根本在游戏的社会影响中不起作用,这些问题还有待方家探索。
越是在发展中国家,游戏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无论正向或负面——就越容易被放大。尽管与海外相比,游戏研究在中国的学科建制与规制化发展都非常初步,但由于产业仍在发展,游戏学术以及游戏正向价值的理论、观点与范式也更容易通过游戏档案馆这样的公益-学术机构,而实现对行业、社会的多层次“穿透”。也因此,将社会视角包容进游戏本体论,从社会实践中逐步践行的研究范式,可能反而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为世界游戏研究贡献的一种理论与实践上的“后发优势”。
注释
(1)Mayra F, An introduction to game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 2008, p.31.
(2)其标志是2001年阿尔萨斯教授在北欧建立游戏研究(Game Studies)期刊并撰写发刊词“Game Studies Year 1”,该领域因此而得名。
(3)Ontology一词源自希腊语,由“ont-”(存在)和“-logy”(学科)两部分组成,字面意思是“存在的学科”。在哲学中,本体论(ontology)是研究存在的本质和基本结构的学科。Game ontology则是研究游戏的本质及其基本结构的学问。
(4)Aarseth, Espen and Pawel Grabarczyk, “An Ontological Meta-Model for Game Research.”,DiGRA Conference, 2018.
(5)Aarseth, Espen,“Playing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game analysis.”,Proceedings of the digital arts and culture conference, Australia: Melbourne, 2003.
(6)从赫伊津哈到阿尔萨斯,从语言学角度讨论游戏概念以理解背后的文化观念已成为一种惯例。并非所有语言都用两个词表示这两个概念,在一些语言,如法语、荷兰语、挪威语中,game与play是用一个词来表示的。
(7)将play译为“游玩”,是对中文语境中的游戏概念经过考量后的选择。中文的“戏”接近于英文的game,是有规则之游戏;而play既是动词又是名词,其实更接近中文的“玩”,但为与两个字的“游戏”对偶,同样加上“游”字。其实,中文的“逍遥游”概念中的“游”,也很接近游玩的那种精神性的抽象自由状态。
(8)这当然只是本体论提供的一个定义。我们并不认为这套定义是绝对正确的,在此只拿它作为一种代表来说明这两个概念的大小。
(9)由于中文学界此前对游戏研究所知较少,目前所有版本的《游戏的人》中都把play翻译成了“游戏”,从而造成游戏与游玩的概念在中文中难以区分。本文不同意这种混淆,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体验,涉及该书时延用已有翻译。
(10)[荷兰]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11)同(10),第5—6页。
(12)较出名的研究如格尔兹关于巴厘岛斗鸡游戏与社会结构的研究。
(13)该书已有官方中译本,此处翻译均遵循中译。
(14)详细论述参见刘梦霏《游戏入史:自然祭司德鲁伊形象的古今变迁研究》,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9年。
(15)魔圈是赫伊津哈的核心概念,指被游戏的规则所圈围出的单独的时间与空间。维护游戏纯洁性的理论家,特别是凯卢瓦强调魔圈完全独立于现实,游戏不会对现实造成任何影响。
(16)[法]罗歇·凯卢瓦(Roger Caillois)《游戏与人》,余轶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版,第12页。
(17)同(16),第x页。
(18)同(16),第xi页。
(19)关于赫伊津哈维持游玩“纯洁性”的论述,也受到了Ehrmann, Jacques, Cathy Lewis and Phil Lewis, “Homo ludens revisited”, Yale French Studies 41(1968): 31-57与Espen Aarseth, “Game Histories and the Prehistory of Game Studies”课程讲义的启发。
(20)Katie Salen and Eric Zimmerman, Rules of Play: Game design fundamentals, MIT Press, 2003, p.585.
(21)同(20),第552页。
(22)Hjorth, Larissa and Ingrid Richardson, Ambient play, MIT Press, 2020.
(23)Scholz, Trebor, ed.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Routledge, 2012.
(24)2023年,中国游戏产业实际销售收入为3029.64亿元。出自中国游戏工委《2023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25)刘梦霏《理解游戏素养之力——时代需要新的游戏素养理念》,《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读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3—96页。
(26)游戏的人档案馆《游戏素养行动指南》,https://mp.weixin.qq.com/s/DMafCvaeNfUIkWmfqfAwtg,发布日期2024年1月27日。
(27)刘梦霏《游戏监管,从分类开始》,《环球》2020年第5期。
(28)刘梦霏《寻找游戏精神》,《离线·开始游戏》,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74—95页。
(29)一些买断制游戏表面看起来属于消费游戏。例如,为了促进销售,有些买断制游戏会将自己包装为免费游戏,游戏中实际可玩的内容相当于演示样本,要玩正本需完整付费,这类游戏仍应视为作品游戏。又如,有些游戏内容是免费的,开发者的收益是广告,玩家可以通过付费来永久消除广告,消除后游戏不再有收费点,这也应当视为作品游戏。按时间付费(如包月)的网络游戏,若游戏内不再有其他强制性或引导性消费,也可划入作品游戏。这类游戏的费用,可以看作是持续的买断付费,它是由网络游戏需要开发方持续投入服务器与维护成本的特点而带来的。还有些单机游戏会发售后续的DLC(游戏内可选的追加下载资源,包含新的游戏道具或任务等,如果玩家不下载,一般也不影响游戏本体),并针对DLC单独收费,这也应当视作买断制的作品游戏。
(30)Nielsen, Rune Kristian Lundedal,and P. Grabarczyk, “Are Loot Boxes Gambling? Random Reward Mechanisms in Video Games.” , Transactions of the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2019.
(31)[美]娜塔莎·道·舒尔《运气的诱饵:拉斯维加斯的赌博设计与失控的机器人生》,李奇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