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地而坐新的一期,我們邀請青年學者李典峰、耿遊子民,分享他們在北大做遊戲研究的體驗。
什麼是遊戲?電子遊戲跟傳統遊戲相比,又有什麼區別?在北大做遊戲研究,需要去做什麼,又會遇到哪些現實的困境?本期,典峰和耿遊會從他們為什麼做遊戲研究說起,談到遊戲本身值得研究的內容、遊戲的學科化建設、遊戲在今天遭遇的汙名化。
我們也會討論《失控玩家》這部遊戲化電影,將它與《頭號玩家》、《黑鏡》等電影做對比,討論電影領域出現的遊戲化趨勢,遊戲如何影響我們的當代生活?以及在今天,資本主義如何通過控制“眼球”,來維護它的統治。
在討論的下半場,我們會討論遊戲與青少年成長的關係。打遊戲成癮會讓青少年荒廢學業,但是遊戲對青少年只有副作用嗎?在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兒童沉迷於網絡遊戲的原因又有哪些?如果遊戲不可避免會是潮流,我們今天看遊戲,就像20世紀的人看科幻小說,那麼遊戲該如何與兒童教育、青年教育更好地共生?
討論最後,典峰和耿遊也跟我們分享了國內遊戲研究的代表著作、值得關注的學者,以及一些他們平時喜歡玩的電子遊戲。電子遊戲並非洪水猛獸,它是一場當代的敘事革命,倘若我們能平常心對待,我們或許能開啟一個更豐富的想象力世界。
本期主播 和嘉賓
宗城:寫作打工人,人類觀察員
李典峰:北京大學藝術學博士,研究電子競技與遊戲素養
耿遊子民:北京大學藝術學院碩士,主要研究遊戲文化與遊戲史
正文
Part 1 在國內做電子遊戲研究的真實體驗
宗城:今天我們的主題是“遊戲與青年文化”。我邀請到了兩位朋友,李典峰和他的師弟耿游來一起做客對聊這個話題。兩位嘉賓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吧。
李典峰:《席地而坐》的聽眾大家好,我是李典峰。簡單自我介紹一下,我和耿遊都是北京大學藝術學院的在讀博士研究生。我的方向是藝術批評,現在在一個國家重大課題組,叫《影視劇與電子遊戲融合審美趨勢研究》。
耿遊:我是典峰的同門師弟,是碩士,也在同一個課題組裡,學術上的身份是這樣的。更多想聊的是,我也是一個玩家,平時什麼遊戲都會打,主機遊戲接觸較多的是索尼和任天堂。微軟接觸的少,之前只接觸過Xbox,Xbox 360,然後是Xbox One。也是Steam玩家,《LOL》跟《DOTA》都打過,都不太行。有時候也玩一些氪金手遊。
宗城:遊戲是大家經常聽到的東西,但是一說起遊戲研究,可能對很多人來說還是新奇又陌生的領域。聽說你們在做遊戲研究這個事情的時候,我自己也蠻好奇的。你們能不能分享一下,為什麼北大會開設一個專業來專門研究遊戲?你們又是因為什麼機緣而進入這個專業的呢?
李典峰:說到這個,我需要澄清一下。我們確實在推動遊戲研究學院化,或者說通過學院化落成這件事情。但是實際上,我們學校的藝術學院簡稱MFA,叫藝術學專業碩士,它有很多下設方向,包括廣播電視主持、音樂、舞蹈等等。藝術學作為一級學科,會下分一些二級學科,比如說文化產業、藝術史,史論就是歷史方法論,還有在國外被稱為藝術哲學的藝術理論。明年9月份的時候,我們學院會收一批碩士研究生,他們的方向就叫做“實驗電影”或者“實驗影像與遊戲媒介”。它本身也是一個博士和碩士研究點,博士研究點是設在藝術理論下面的,而整個藝術學院頒發的PHD學位叫藝術學,所以我和耿遊拿的都是藝術學的學位。
根據我們的師資介紹,實際上明年9月份招生的這批MFA,他們在2023年的時候會通過第一學年的基礎學習,然後會選導師進行專業學習。專業學習之後,分到的方向主要是由我們的副院長李陽——大家用豆瓣或微博會知道有一個叫大旗虎皮的學者,就是李陽老師——主要由他來帶這個“實驗電影和遊戲媒介”方向的MFA。這是我們碩士招生的情況。另外本科好像還有一個計算藝術的二專業,那個我不太清楚,因為它是跟軟微工程院,主要由高峰老師他們的項目來做。好像會發一個雙學位,但我不太清楚它的具體學位成分是藝術學還是計算科學。
耿遊:我分享一下宗城提到的另一個問題,怎麼機緣巧合就進入了這個專業。其實剛剛典峰師兄說到的這幾個專業,現在還在招生階段,相當於第一屆還沒有真正地進入學校去上課。目前我們做的這些相關的研究,其實是因為一個課題才開始的,就是之前師兄說的這個國家重大課題。
最開始的時候,我本身讀研的專業是戲劇影視學,是做電影批評的方向,所以更多的是電影理論相關。包括我導師的本行也是做電影理論和電影批評。所以也是機緣巧合,因為恰好開始有了這個項目、這個課題,就認識了師兄。再加上自己本身是一個玩家,最開始肯定是興趣驅動的,於是才進入到這個研究當中。
北大在將來在這方面會有獨立的方向,但目前我在做的就是基於一個課題去展開的這樣一個跟遊戲相關的研究。
宗城:遊戲也分很多門類,而你們主要研究的是電子遊戲。電子遊戲跟傳統遊戲相比,它主要的區別在哪? 在國內研究電子遊戲會有怎樣的困擾?
李典峰:我之前也跟我們學校新傳學院的王洪哲教授聊過這個問題。現在國內的很多學者做電子遊戲研究,如果你盯著他的論文追更的話就會發現,他發的第一篇論文一定是從零開始的,因為我們之前沒有這個學科,沒有學科共識,也就沒有一個專門的期刊去發這些文章。所以大家寫論文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都是先界定什麼是遊戲,什麼是電子遊戲,這個詞它對應的英文單詞是什麼。
另外一個問題是,它的具體對象是什麼?
我沒有看到政府出臺相應的法案、政策,而一些輿論導向又不去談論甚至拒斥電子遊戲這個詞,而是在談網絡遊戲。網絡遊戲就是Internet Game,它的界定比較模糊。你需要界定中國港澳翻譯和中國大陸學者翻譯體系的傳統,實際上我們今天所討論的都是Video Games,港譯直接叫視頻遊戲。中國臺灣那邊更復雜一點,他們不用這個詞,而是叫Digital Games,用他們自己那一套說法叫數位遊戲。大陸和香港在談論這件事情時都用Video Games,它涉及到影像,一定是視頻遊戲,一定是有顯卡或者顯像技術之後的,哪怕試播器上面的那個play的鈕,或者調頻的鈕也叫做Video Games。
更早出現的東西我們可以稱為電動,Electronic games。它是比如說你在賭場會見到的彈球,或者老虎機,或者用電動裝置制動的俄羅斯輪盤賭,背後涉及到更原始的一種gambler商品,所以它其實還不太一樣。當然,我們會發現後來這幾種玩法進行了融合,比如現在的電子遊戲裡面有一些古早的抽卡機制。

電影《失控玩家》劇照
這還涉及到另外一個翻譯問題,比如說盎-撒德語詞源,赫伊津哈用的Ludic,它所指的就是Homoludens那本書它背後拉丁語的意思,它是更泛遊戲化的一個詞。後來到了把電子遊戲看作是一種媒介,是一種文本,還是一種行為方式和人類活動。於是大家從零開始寫完了第一篇論文後,在第二篇裡一般就都會寫到比如Ludology和Narratology的討論,Narrative是敘事學派,Ludology是玩法或者叫做遊戲學派,這就是舶來詞彙的詞源問題。
英文還會又具體的劃分,比如說遊戲活動和建制化的遊戲規則活動。遊戲規則活動,就是今天我們遊戲論壇裡的一個熱頻詞,叫Gamification。Gamific是把一件活動規則化、建制化,或者說是規訓化。而Ludic它更多要講究的是一個遊戲,或者說玩,試探這件事情的邊界,如何去挪動,還有關於交互可能性的挖掘。所以Ludic和Gamific還不太一樣,這個具體可以看我師兄在中傳的博士後的出站報告,之後他應該會系統性地把這些文章發出來,大家讀過會對這些詞源有一個更深刻的認識。
它背後還涉及到赫伊津哈所講的德語中的“Spach-”:爬山,就用一個“玩山”,釣魚之類的也都用類似這樣的一個詞。這些詞在德語中是一個複合結構,它更多的是跟人類前史的一些宗教儀式有關,而跟之後的遊戲活動的關係就不是那麼接近了。這個其實是規則、遊戲活動還有今天已經被商品化的電子遊戲之間的關係,裡面實際上有一個關於載體和介質,還有計算機技術的問題。
但我要講的是在詞源上,“遊戲”這個詞非常值得研究,它甚至比藝術更早地在人類普遍使用的語境出現:在中文有“藝術學”這個詞之前,西方的Art,fineart和craft,還有tech(technic)之間的關係其實是很模糊的,而在所有的這些藝術、技術之前,有一個更早的人類活動叫做遊戲,那是在規則還沒確定的時候,大家互相試探、互相交互的一種普遍的人類活動。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不僅僅研究電子遊戲,現在我寫的論文已經開始脫離電子遊戲的範疇,更多在研究一些比如區域控制戰棋、軍事沙盒之類,它們其實就是對戰爭的模仿。
脫離電子遊戲的語境,往前回溯游戲史。它是一種一般化的人類活動。我們有必要成立一個專門的學院去研究它。小耿可以補充關於當代電子遊戲發展的問題。
耿遊:我先舉一個比較感性的例子。如果你平時去問別人:你玩遊戲嗎?在我們中國的語境下,這個問題指代的基本是電子遊戲,而且電子遊戲大部分指代的是網絡遊戲,甚至可以直接明確地問:你玩《王者榮耀》或者吃雞嗎?這導致了一個問題,就是當你告訴別人或者一個陌生人你做的是遊戲研究時,他們第一個很感性的想法可能就是你是在研究《王者榮耀》,或者你就在怎麼研究如何讓大家更上癮,如何讓公司賺更多的錢之類的。這其實是一個偏見。
不僅如此,當你跟長輩或父輩解釋的時候,他們還會不解,畢竟在他們的認知體系裡,電子遊戲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會跟精神鴉片、電子海洛因這樣詞彙聯繫起來的老生常談。這些的確會造成你在平時跟別人解釋你正在做什麼,將要做什麼時的一個很大的溝通成本。
在當下的學術語境裡,相對於其它學科,它用一種比較好玩的話說就是酷兒研究,或者一種異類研究。它要在人文學科的邊緣做一些事情,就必然會受到一些直接的影響,會不被主流所認可。如果你想要做一篇相關的論文之類的,就一定會有一個依附。舉個例子,在國內,你要寫一篇跟電子遊戲相關的文章,或者說你嘗試去聊這件事情的話,你最終可能會有一個導向,比如更偏重於文學理論或者藝術理論,那麼你可能就要拿中文系或藝術學的一些框架去套,嘗試在這個鐐銬裡面去展示你自己關於遊戲的研究。
我們現在正在做的項目也是這樣,它有一個核心點,是基於影視理論,這個項目叫影視劇和電子遊戲融合,就是媒介融合。其實這個融合也有一種君臣佐使的感覺,首先有影視或者影像作為主導,而電子遊戲作為一種亞文化,要朝那種主流文化靠近,然後它們相互之間借鑑融合。
所以單純從學術生產上來講,現在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附在一個現有的體系之下。之前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同學,孫林祥學者,他將其形容為一種紙巾盒式研究,就是說誰都願意過來到遊戲裡摻和一腳。比如說我是研究心理學的,我就可以把遊戲作為一個例子或者一個基礎資料,但是我所闡發的東西是心理學,我把電子遊戲的例子換成賭博或者其它什麼也沒問題。目前的情況就是這樣。
Part 2 電影遊戲化
宗城:就像你說的,你們研究的範圍既包括遊戲,也包括遊戲與影視的混合。我和典峰之前也談到了最近上映的一部電影,叫《失控玩家》,聊到未來的電影可能會有遊戲化的傾向。兩位可以聊一聊《失控玩家》,我覺得這部電影中游戲與電影的融合這一角度還蠻值得一說的。

電影《失控玩家》劇照
李典峰:我跟小耿第一時間就分別去看了這個電影。我後來用貓眼的影評截圖發了一個朋友圈,說到我們10月初馬上要在信睿週報發出來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剛才小耿提到的孫林祥,他是我們北大社會學系的碩士,本科是元培班的天才高材生。我們讀過基特勒的“軟件不存在”,“軟件不存在”有很多非常好的觀點值得作為遊戲研究發展方向的本位理論,而孫林祥的那篇文章叫做《遊戲不存在》,講的是Bug和Mode,這些對於非電子遊戲玩家來說是具有門檻的詞,我之後會加以解釋。
我當時發的那篇影評裡說,這個電影可以取名叫做《NPC不存在》。因為NPC如果存在,它是以什麼樣的狀態存在呢?它其實是一個程序員的延伸。這個電影的批判程度或者想象力的深度,並沒有《黑鏡》第三季的聖誕特輯裡,我們看到從腦子裡取出來一個思想,然後變成一個小人困在無限循環的模擬器裡,作為家庭管家的那一集那樣給人印象深刻。
對我來說,這種延伸具有非常強烈的物質性。它不過是幾次代碼翻譯之後,人格以文本的形式出現在視頻顯卡和聲卡驅動的一個場裡面。這個場對於玩家來說是另外一個空間,但對於NPC來說是一個封閉的地方,所以NPC自己不可能真正地有感情。雷諾茲飾演的角色對有女主的感情實際上是因為他是一個演員,他不是一個NPC,有一個玩家視角。為什麼一定要找瑞安·雷諾茲來演這個角色?就是因為他必須是一個真人,他的表情才make sense。他雖然是NPC,但在那樣一個領域裡,他要把自己的身體和感情翻譯成人的面部表情,還有人的這種念臺詞的節奏和習慣,這樣才能讓觀眾對他產生感情。
實際上這個NPC並不存在,演員的角色並不存在,那個女玩家能跟他真的發生感情,就必須代入到裡面,而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很少。那個女生喜歡他的原因,其實並不是因為他是個NPC,他跟自己的交互讓自己感覺到多麼舒適,而是在於那個人非常理解她,非常瞭解她。這背後的原因,其實是那個男性程序員對她的一種類似暗戀的、情書似的東西。它就像我們初中、高中的時候,比如你跟一個女生一起看一本書,你喜歡她,就在這本你們平常借來借去的書上,比如《指環王》第三部,你會留一個密碼信給她。她如果能破解出上面的符號,就知道你大概是通過這本書在向她表白。這兩件事就是一樣的。
瑞安·雷諾茲演了一個電子情書,可以被多次翻譯的、對女主敞開的一個情書。對我來說,這就是一個非常陳詞濫調(cliche)的劇本。它並沒有比《頭號玩家》有更多的視覺特效、劇本深度、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可能性的投射,或者是在感情上討論得更深;它更沒有《黑鏡》那麼犀利,那種甚至冷漠和殘酷的,對於人的延續的一種剝削。

《黑鏡》劇照
耿遊:很多人說看到《失控玩家》就會想到《楚門的世界》。其實除了《楚門的世界》,還有一部電影是《失控玩家》借鑑最深的——1988年上映的《極度空間》。它是哲學網紅齊澤克特別喜歡的一部電影。《極度空間》有一個核心的概念,或者說它整個片子的一個核心設定,就是主人公機緣巧合拿到了一個墨鏡。他把這個墨鏡戴上之後,整個花花綠綠、五彩斑斕的世界就變成黑白的了。所有的廣告標語,所有的書籍,所有的雜誌,一切給你傳達信息的東西,都被抹去了那些所謂表面的、表層的信息,而你能夠看到的是一些直接的意識形態。舉個例子,遠處的沙灘上有一個美女,而他戴上眼鏡之後看到的就只有一個詞:繁殖。就是這樣一些很露骨的意識形態話語。
在《失控玩家》裡也用了同樣的梗,就是有一個眼鏡,戴上眼鏡之後就看到了所謂的真實的世界。當然《極度空間》是做了一個減法,把很多最外在的東西減去了,讓我們看到一個充滿意識形態的東西;而《失控玩家》是戴上眼鏡後,看到了一些多出來的東西,但是同樣也看到了一個所謂真實的世界。
齊澤克經常會講一些意識形態批評的東西。他特別喜歡強調這個電影展現出來的一個很深刻的思想,或者說一個想法,就是我們通常認為一個事物擁有一個本質,而意識形態的話語是附著在上面的,我們可以把它洗掉或者扔掉。比如說一個LV包, LV這個東西是社會話語體系賦予它的,我們把這層所謂的建構出來的意識形態之下的產物洗掉,那麼它就是一個普通的包。
實際不是這樣。我們通過這兩個電影可以看到,意識形態,或者我們想要知道的本質,它變成了真實的一部分,你沒有辦法割除它。你戴上眼鏡了,並不是抹除它了,而是真正看到它了,你逃不掉。這是一個比較悲觀的事實。再說得通俗點,我們在尋找一個本質,或者在尋找真相,或者真實。什麼是真實?不管是我戴上了墨鏡,看到的那些充滿意識形態標語的真實,還是《失控玩家》裡面,小賤賤戴上墨鏡,看到了他和NPC的血條,看到了一堆道具,這也是一種真實。
我個人覺得蠻好的一點,不知道是不是出於導演的自知,就是《失控玩家》給了我們一種更積極的面對真實的態度。這得說到另一個電影,這兩天它也發了個新預告片,就是《黑客帝國》。
《黑客帝國》對待真實的態度,顯得過於諂媚,當然這種諂媚自有它的歷史原因,在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為資本主義續了一波命之後,晚期資本主義更加瘋狂且隱蔽的侵入我們,不僅僅是曾經的衣食住行,作為精神食糧的文化產品也浸泡在商品拜物教的海洋中,黑客帝國就是在那樣一種社會環境之下誕生的,他為彼時慘淡的真實提供了一個宗教般情緒宣洩的出口——或許有一個真實的世界在吞下藥丸之後。這個故事我們周圍的道友也常說,只不過錫安被稱作仙界,道友們的紅色藥丸也更大更圓。
說回電影,當我們認清追尋真實是某種虛妄之後就會發現,同樣是探討真實,《黑客帝國》給出了一個現在看來過於諂媚的辦法——在幻覺中成神。而《失控玩家》則給出了一個看似平庸的辦法——活在當下。難能可貴的正是這點,《失控玩家》帶著某種狡黠,嘗試用“躺平”去對抗偽裝得越來越精巧又華麗的泡泡,這泡泡便是《黑客帝國》裡的紅色藥丸,它代表著被設計的“真實”,一個為你我構建出的完美幻覺。可惜你我並非生活在柏拉圖的山洞中觀看影子,也並非反抗世界的救世主。不論是紅色藥丸還是黑色墨鏡,你我還得要繼續生活, 思考一下被幻覺籠罩的我們還有什麼反抗的餘地。
《失控玩家》的意義正在於此,它嘗試為無法奔向“真實世界”的你尋找一條更加務實的路,活在當下,朋友是真實的、大塊頭也是真實的,和女主記憶的同樣是真實的,甚至最後被很多人吐槽的結尾,在我也是足夠真實的,相比幻想一個並不存在的真實,把握當下變成了更積極的選擇。你看痞子都告訴大家,散了散了,沒有使徒也沒有EVA,大家請回到三次元吧。
宗城:它是不是也可以被解讀為一部反烏托邦電影,雖然看似那些NPC自我覺醒之後展開了反抗,但是它其實不承諾一個烏托邦的幻想。它會告訴你,這個遊戲世界確實是虛假的,但你也不能在彼岸找到真實。於是它只能給你活在當下這麼一個看起來有些勉為其難,對普通人來說又非常現實的一個回答。
我看到這部影片結尾的時候,一方面會覺得這是非常閤家歡的一個處理方式,它把一些嚴峻的或者說讓人覺得再走一步就會很困難的命題相對地擱置了。我覺得它有一些困境的轉換,比如說遊戲中角色的自我覺醒之後,他們的一些處理會顯得過於順滑。它很像硅谷程序員的一個童話。你會發現,照著他的故事走的話,這不就是硅谷程序員幻想中的世界嗎?
李典峰:而且不但是硅谷程序員,最後他說我們還要去銀行上班嗎,然後說沒有銀行了。沒有銀行那就烏托邦了。硅谷程序員在西岸跟東岸的金融家們在生態位上其實是有點衝突的,一邊要編制一個扁平、去中心化,但是又可以從後臺進行一些微控操作的一個賽博龐克的世界;而另外一邊是金融帝國的金融家們通過鑄幣稅和軍工複合體去進行奴役的世界。但是他們又必須嘗試去把這件事情抹平,所以就把銀行取消掉,大家都去,你懂的,用虛擬貨幣,搞這種NFT或者讓程序員和金融家有一個和解,然後這事就句號了,烏托邦就實現了,大家就自由了。我就覺得,啊,原來是這樣嗎?就不太理解。
宗城:仔細觀察這個電影最後的走向,它既不符合所謂的財閥或者說政治家的傾向,又不完全符合平民的傾向,它其實是硅谷程序員意識到他在現實裡不可能憑個體之力對抗老大哥,但他可以在他設計的程序裡實現這件事,在潛移默化之間去中心化,就應了那句話,叫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他甚至不會跟你討論真實與虛構的對立,而是跟你說真實就是假的,你不要那麼在意真實這個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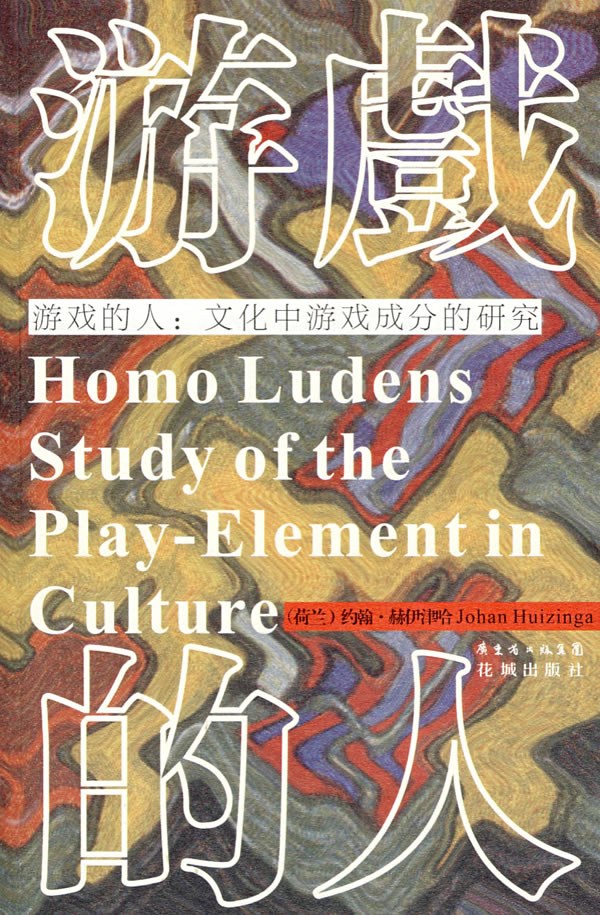
Part 3 眼球控制術
宗城:典峰剛才提到了《黑鏡》的聖誕特輯,可以再科普一下它為什麼會比《失控玩家》更進一步或者說更加嚴肅地討論了這個命題。
李典峰:這裡涉及到一個身體的問題,也是我們之後做遊戲研究的方向。我跟耿遊還有比較志同道合的小夥伴們,我們認為它是一個可能真正屬於電子遊戲,或者從電子遊戲往回追溯,它能夠貫穿很多問題的作為方法論的底色。基特勒、德勒茲和維特根斯坦,包括梅勒·龐蒂,梅勒·龐蒂、德勒茲和基特勒這三個人是可以從他們的方法論和他們討論對象裡貫穿的。
基特勒先談到一個問題,“軟件不存在”。我們看到的那些東西,它具有一個密碼機的本體,那個東西它可以翻譯,而且它一定是物質化的。這裡面計算機是一個非常唯物的東西,你不要用尼奧和matrix涉及到猶太復國主義的那套宗教詞彙去跟它討論一個關於真實和虛假的東西,那沒有任何意義。有核電的地方和沒有核電的地方,你用電的這種放肆程度都不可能一樣。它一定是有物質基礎的,而且不是object的客觀的物質,而是一個material的非常唯物性的東西。
然後它往回推一步,會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計算機跟人的身體之間通過運動影像,通過光子和眼睛之間的關係,它如何能介入到我們的身體裡面,就是我們今天在談“biopolitics”那個詞翻譯來的生物政治,它跟如何去歸訓人的生活方式、監控每一個在計算機網絡裡面生活的個體有關。那麼這件事情它涉及到我們一生的長度和我們每一天注意力集中在屏幕內容,什麼內容和誰傳遞這些內容給我們有關。
再往前推一步,我們的觀看影像和我們的身體在觀看影像的場域裡面如何形成一種行為強化。這涉及到格式塔心理學和行為心理學的一些研究成果,今天是被社會領域所濫用,這些資本,包括這些程序設計,他們在濫用這些人類行為強化心理,包括格式塔心理學、注意力經濟學的這些知識。但他們卻沒有告訴所有人,沒有讓所有人接受這些知識的教育,形成一種從知識上的平等。這就是平權問題,你至少得讓人家知道,讓我有權利選擇拒斥這些,但他沒有。
維特根斯坦在談論遊戲的時候說,很多遊戲活動原始的樣子和目的在今天被偷偷地藏匿到所有的遊戲方式裡面,包括賭博。為什麼會有game disorder這個詞?你通過遊戲喪失了社會功能,並且產生了極大的比如說悔恨、愧疚、無力,甚至精神崩潰,這是你因為遊戲行為而造成的。他說的可不是video game,他說的game是包括所有的casino裡面的那些活動,賭場裡面的gambler,他其實是在毒癮沉溺行為強化裡面造成的一種社會功能紊亂,這個是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對遊戲行為失控紊亂造成的一個嚴格的界定。
這件事情其實是個普遍的社會學問題。它跟今天我們去網癮治療裡面拿電機那個完全沒有關係,它是個廣泛存在的問題。比如說前兩天真實發生在浙江的新聞,一對父母為了去麻將館打牌,把孩子落在車裡面鎖住了之後,孩子就死在裡面了,一個4歲的小姑娘。這就是明顯的disorder,這對父母是一定要接受刑事責問和精神治療的,他們很明顯地由於遊戲行為成癮造成了社會功能喪失。這件事情也是廣泛存在於所有國家的,特別是城鄉結合部,因為城市化發展中很多人的工作強度造成他無法完全去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在勞動和休息之間轉換,這就涉及到很多其它的比如說社會學的一些問題。
《黑鏡》從這裡進行了深度的批判。在聖誕特輯裡它講了兩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未來我們的眼睛會移植一個東西。那是在第三季的某一集裡面,有一個鏡頭就是男女晚上在夫妻生活的時候,兩個人的眼睛都有一個植入裝置,在看著他們倆初次見面時雲雨的那種狀態,但是他們兩個人已經沒法對對方的身體發生這種感情,而只能對那段影像發生生理反應。這個技術就是,我的眼睛會被接上一個互聯網,我能看到的東西是這個軟件下載下來給我看到的。我實際上可以通過我的軟件和互聯網上的一些軟硬件接口的方式,讓我看不到整個肉體能接觸到的外在的現象世界本身存在的東西。
舉一個電影裡面的例子,比如說在一個大的社交網絡上面,你被我拉黑了,或者因為社交網絡的公司評級,你的信用或者其它方面有問題,那麼我就看不到你,你在我面前就是一個像馬賽克一樣的黑影。

《黑鏡》劇照
另外一個方面,它講到你的大腦裡面的一些生物信息可以被提取出來,形成一個具有你的人格和知道你所有行為偏好的生物數據。這個生物數據可以讓你家庭周圍的這些智能家電設備完全按照你的行為習慣來佈置。也就是說把你自己的一個人格切片變成一個管家,來讓他輔助你,管理你的生活。而它體現出來的其實是有一個真正的人的這種,一個精神狀態的小的你被關在這個機器裡,它出不來。那個是真的NPC,但它不是一個AI,而是一個甚至可以說有人類靈魂覺知的一個東西,它被關在裡面。而somehow就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有一個人他精神崩潰了,他回到自己的身體裡還是怎麼樣,去找他的妻子,然後他被評價為非法跟蹤別人。他被整個社會給關在了外面,再也看不到別人,所有人都也看不見這個人。
你說對於人的視覺感官來說,他還是一個人嗎?那一集的結尾就在這個特別恐怖那個地方。它批判了很多東西,關於接口或者叫界面,是電子設備硬件跟人之間的關係。它不再只是一個鼠標,一個屏幕,一個我們生理上可以脫離它,沒有太多問題的一個東西,而是插件式的,嵌入到我們的肉體裡面。當肉體的軟硬件插在一起之後,社會里的每一個個體它其實是受一個更大的終端管理的。如果有一個人被排斥在秩序之外的話,他就是不再在社會里的裸命。
這個裸命是很恐怖的,它跟我們今天理解的三和大神,把身份證當掉之後去廣東那些地方,在黑網吧門口喝大水,然後上網的那些農民工還不一樣。那些人是有social的,而這個人完全被排斥在社會秩序之外,而且是被強制執行的,這是未來有可能的非常恐怖的一個現實。
這裡有很多東西值得討論。我們怎麼去使用這種高度賽博化的社會領域裡面的這種公權力,就是社會網絡資源,讓一個人不說話,或者讓一件事情被取消存在,比如說下架之類的。這些在今天看來都很敏感,都是需要去討論的一個公權力,它的法理性在哪兒,這都是需要去重新討論的。
宗城:我覺得你說的《黑鏡》那一段還蠻有意思的,就是那兩個夫妻,他們眼睛裡裝了一個裝置,它讓我想到了一種認知統治,未來資本主義的統治可能不是通過殘酷的身體上的暴力術,而是認知上的幻覺,通過技術讓你在認知上滿足自己的一些虛假的高潮,從而去緩解你在現實生活中的反抗力。
李典峰:這不是未來,它已經在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