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地而坐新的一期,我们邀请青年学者李典峰、耿游子民,分享他们在北大做游戏研究的体验。
什么是游戏?电子游戏跟传统游戏相比,又有什么区别?在北大做游戏研究,需要去做什么,又会遇到哪些现实的困境?本期,典峰和耿游会从他们为什么做游戏研究说起,谈到游戏本身值得研究的内容、游戏的学科化建设、游戏在今天遭遇的污名化。
我们也会讨论《失控玩家》这部游戏化电影,将它与《头号玩家》、《黑镜》等电影做对比,讨论电影领域出现的游戏化趋势,游戏如何影响我们的当代生活?以及在今天,资本主义如何通过控制“眼球”,来维护它的统治。
在讨论的下半场,我们会讨论游戏与青少年成长的关系。打游戏成瘾会让青少年荒废学业,但是游戏对青少年只有副作用吗?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儿童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原因又有哪些?如果游戏不可避免会是潮流,我们今天看游戏,就像20世纪的人看科幻小说,那么游戏该如何与儿童教育、青年教育更好地共生?
讨论最后,典峰和耿游也跟我们分享了国内游戏研究的代表著作、值得关注的学者,以及一些他们平时喜欢玩的电子游戏。电子游戏并非洪水猛兽,它是一场当代的叙事革命,倘若我们能平常心对待,我们或许能开启一个更丰富的想象力世界。
本期主播 和嘉宾
宗城:写作打工人,人类观察员
李典峰: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研究电子竞技与游戏素养
耿游子民: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主要研究游戏文化与游戏史
正文
Part 1 在国内做电子游戏研究的真实体验
宗城: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游戏与青年文化”。我邀请到了两位朋友,李典峰和他的师弟耿游来一起做客对聊这个话题。两位嘉宾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李典峰:《席地而坐》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典峰。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和耿游都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在读博士研究生。我的方向是艺术批评,现在在一个国家重大课题组,叫《影视剧与电子游戏融合审美趋势研究》。
耿游:我是典峰的同门师弟,是硕士,也在同一个课题组里,学术上的身份是这样的。更多想聊的是,我也是一个玩家,平时什么游戏都会打,主机游戏接触较多的是索尼和任天堂。微软接触的少,之前只接触过Xbox,Xbox 360,然后是Xbox One。也是Steam玩家,《LOL》跟《DOTA》都打过,都不太行。有时候也玩一些氪金手游。
宗城:游戏是大家经常听到的东西,但是一说起游戏研究,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新奇又陌生的领域。听说你们在做游戏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也蛮好奇的。你们能不能分享一下,为什么北大会开设一个专业来专门研究游戏?你们又是因为什么机缘而进入这个专业的呢?
李典峰:说到这个,我需要澄清一下。我们确实在推动游戏研究学院化,或者说通过学院化落成这件事情。但是实际上,我们学校的艺术学院简称MFA,叫艺术学专业硕士,它有很多下设方向,包括广播电视主持、音乐、舞蹈等等。艺术学作为一级学科,会下分一些二级学科,比如说文化产业、艺术史,史论就是历史方法论,还有在国外被称为艺术哲学的艺术理论。明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学院会收一批硕士研究生,他们的方向就叫做“实验电影”或者“实验影像与游戏媒介”。它本身也是一个博士和硕士研究点,博士研究点是设在艺术理论下面的,而整个艺术学院颁发的PHD学位叫艺术学,所以我和耿游拿的都是艺术学的学位。
根据我们的师资介绍,实际上明年9月份招生的这批MFA,他们在2023年的时候会通过第一学年的基础学习,然后会选导师进行专业学习。专业学习之后,分到的方向主要是由我们的副院长李阳——大家用豆瓣或微博会知道有一个叫大旗虎皮的学者,就是李阳老师——主要由他来带这个“实验电影和游戏媒介”方向的MFA。这是我们硕士招生的情况。另外本科好像还有一个计算艺术的二专业,那个我不太清楚,因为它是跟软微工程院,主要由高峰老师他们的项目来做。好像会发一个双学位,但我不太清楚它的具体学位成分是艺术学还是计算科学。
耿游:我分享一下宗城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怎么机缘巧合就进入了这个专业。其实刚刚典峰师兄说到的这几个专业,现在还在招生阶段,相当于第一届还没有真正地进入学校去上课。目前我们做的这些相关的研究,其实是因为一个课题才开始的,就是之前师兄说的这个国家重大课题。
最开始的时候,我本身读研的专业是戏剧影视学,是做电影批评的方向,所以更多的是电影理论相关。包括我导师的本行也是做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所以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恰好开始有了这个项目、这个课题,就认识了师兄。再加上自己本身是一个玩家,最开始肯定是兴趣驱动的,于是才进入到这个研究当中。
北大在将来在这方面会有独立的方向,但目前我在做的就是基于一个课题去展开的这样一个跟游戏相关的研究。
宗城:游戏也分很多门类,而你们主要研究的是电子游戏。电子游戏跟传统游戏相比,它主要的区别在哪? 在国内研究电子游戏会有怎样的困扰?
李典峰:我之前也跟我们学校新传学院的王洪哲教授聊过这个问题。现在国内的很多学者做电子游戏研究,如果你盯着他的论文追更的话就会发现,他发的第一篇论文一定是从零开始的,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这个学科,没有学科共识,也就没有一个专门的期刊去发这些文章。所以大家写论文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都是先界定什么是游戏,什么是电子游戏,这个词它对应的英文单词是什么。
另外一个问题是,它的具体对象是什么?
我没有看到政府出台相应的法案、政策,而一些舆论导向又不去谈论甚至拒斥电子游戏这个词,而是在谈网络游戏。网络游戏就是Internet Game,它的界定比较模糊。你需要界定中国港澳翻译和中国大陆学者翻译体系的传统,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都是Video Games,港译直接叫视频游戏。中国台湾那边更复杂一点,他们不用这个词,而是叫Digital Games,用他们自己那一套说法叫数位游戏。大陆和香港在谈论这件事情时都用Video Games,它涉及到影像,一定是视频游戏,一定是有显卡或者显像技术之后的,哪怕试播器上面的那个play的钮,或者调频的钮也叫做Video Games。
更早出现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为电动,Electronic games。它是比如说你在赌场会见到的弹球,或者老虎机,或者用电动装置制动的俄罗斯轮盘赌,背后涉及到更原始的一种gambler商品,所以它其实还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会发现后来这几种玩法进行了融合,比如现在的电子游戏里面有一些古早的抽卡机制。

电影《失控玩家》剧照
这还涉及到另外一个翻译问题,比如说盎-撒德语词源,赫伊津哈用的Ludic,它所指的就是Homoludens那本书它背后拉丁语的意思,它是更泛游戏化的一个词。后来到了把电子游戏看作是一种媒介,是一种文本,还是一种行为方式和人类活动。于是大家从零开始写完了第一篇论文后,在第二篇里一般就都会写到比如Ludology和Narratology的讨论,Narrative是叙事学派,Ludology是玩法或者叫做游戏学派,这就是舶来词汇的词源问题。
英文还会又具体的划分,比如说游戏活动和建制化的游戏规则活动。游戏规则活动,就是今天我们游戏论坛里的一个热频词,叫Gamification。Gamific是把一件活动规则化、建制化,或者说是规训化。而Ludic它更多要讲究的是一个游戏,或者说玩,试探这件事情的边界,如何去挪动,还有关于交互可能性的挖掘。所以Ludic和Gamific还不太一样,这个具体可以看我师兄在中传的博士后的出站报告,之后他应该会系统性地把这些文章发出来,大家读过会对这些词源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它背后还涉及到赫伊津哈所讲的德语中的“Spach-”:爬山,就用一个“玩山”,钓鱼之类的也都用类似这样的一个词。这些词在德语中是一个复合结构,它更多的是跟人类前史的一些宗教仪式有关,而跟之后的游戏活动的关系就不是那么接近了。这个其实是规则、游戏活动还有今天已经被商品化的电子游戏之间的关系,里面实际上有一个关于载体和介质,还有计算机技术的问题。
但我要讲的是在词源上,“游戏”这个词非常值得研究,它甚至比艺术更早地在人类普遍使用的语境出现:在中文有“艺术学”这个词之前,西方的Art,fineart和craft,还有tech(technic)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模糊的,而在所有的这些艺术、技术之前,有一个更早的人类活动叫做游戏,那是在规则还没确定的时候,大家互相试探、互相交互的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不仅仅研究电子游戏,现在我写的论文已经开始脱离电子游戏的范畴,更多在研究一些比如区域控制战棋、军事沙盒之类,它们其实就是对战争的模仿。
脱离电子游戏的语境,往前回溯游戏史。它是一种一般化的人类活动。我们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学院去研究它。小耿可以补充关于当代电子游戏发展的问题。
耿游:我先举一个比较感性的例子。如果你平时去问别人:你玩游戏吗?在我们中国的语境下,这个问题指代的基本是电子游戏,而且电子游戏大部分指代的是网络游戏,甚至可以直接明确地问:你玩《王者荣耀》或者吃鸡吗?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告诉别人或者一个陌生人你做的是游戏研究时,他们第一个很感性的想法可能就是你是在研究《王者荣耀》,或者你就在怎么研究如何让大家更上瘾,如何让公司赚更多的钱之类的。这其实是一个偏见。
不仅如此,当你跟长辈或父辈解释的时候,他们还会不解,毕竟在他们的认知体系里,电子游戏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会跟精神鸦片、电子海洛因这样词汇联系起来的老生常谈。这些的确会造成你在平时跟别人解释你正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时的一个很大的沟通成本。
在当下的学术语境里,相对于其它学科,它用一种比较好玩的话说就是酷儿研究,或者一种异类研究。它要在人文学科的边缘做一些事情,就必然会受到一些直接的影响,会不被主流所认可。如果你想要做一篇相关的论文之类的,就一定会有一个依附。举个例子,在国内,你要写一篇跟电子游戏相关的文章,或者说你尝试去聊这件事情的话,你最终可能会有一个导向,比如更偏重于文学理论或者艺术理论,那么你可能就要拿中文系或艺术学的一些框架去套,尝试在这个镣铐里面去展示你自己关于游戏的研究。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项目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核心点,是基于影视理论,这个项目叫影视剧和电子游戏融合,就是媒介融合。其实这个融合也有一种君臣佐使的感觉,首先有影视或者影像作为主导,而电子游戏作为一种亚文化,要朝那种主流文化靠近,然后它们相互之间借鉴融合。
所以单纯从学术生产上来讲,现在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附在一个现有的体系之下。之前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学,孙林祥学者,他将其形容为一种纸巾盒式研究,就是说谁都愿意过来到游戏里掺和一脚。比如说我是研究心理学的,我就可以把游戏作为一个例子或者一个基础资料,但是我所阐发的东西是心理学,我把电子游戏的例子换成赌博或者其它什么也没问题。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Part 2 电影游戏化
宗城:就像你说的,你们研究的范围既包括游戏,也包括游戏与影视的混合。我和典峰之前也谈到了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失控玩家》,聊到未来的电影可能会有游戏化的倾向。两位可以聊一聊《失控玩家》,我觉得这部电影中游戏与电影的融合这一角度还蛮值得一说的。

电影《失控玩家》剧照
李典峰:我跟小耿第一时间就分别去看了这个电影。我后来用猫眼的影评截图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到我们10月初马上要在信睿周报发出来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刚才小耿提到的孙林祥,他是我们北大社会学系的硕士,本科是元培班的天才高材生。我们读过基特勒的“软件不存在”,“软件不存在”有很多非常好的观点值得作为游戏研究发展方向的本位理论,而孙林祥的那篇文章叫做《游戏不存在》,讲的是Bug和Mode,这些对于非电子游戏玩家来说是具有门槛的词,我之后会加以解释。
我当时发的那篇影评里说,这个电影可以取名叫做《NPC不存在》。因为NPC如果存在,它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存在呢?它其实是一个程序员的延伸。这个电影的批判程度或者想象力的深度,并没有《黑镜》第三季的圣诞特辑里,我们看到从脑子里取出来一个思想,然后变成一个小人困在无限循环的模拟器里,作为家庭管家的那一集那样给人印象深刻。
对我来说,这种延伸具有非常强烈的物质性。它不过是几次代码翻译之后,人格以文本的形式出现在视频显卡和声卡驱动的一个场里面。这个场对于玩家来说是另外一个空间,但对于NPC来说是一个封闭的地方,所以NPC自己不可能真正地有感情。雷诺兹饰演的角色对有女主的感情实际上是因为他是一个演员,他不是一个NPC,有一个玩家视角。为什么一定要找瑞安·雷诺兹来演这个角色?就是因为他必须是一个真人,他的表情才make sense。他虽然是NPC,但在那样一个领域里,他要把自己的身体和感情翻译成人的面部表情,还有人的这种念台词的节奏和习惯,这样才能让观众对他产生感情。
实际上这个NPC并不存在,演员的角色并不存在,那个女玩家能跟他真的发生感情,就必须代入到里面,而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很少。那个女生喜欢他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是个NPC,他跟自己的交互让自己感觉到多么舒适,而是在于那个人非常理解她,非常了解她。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那个男性程序员对她的一种类似暗恋的、情书似的东西。它就像我们初中、高中的时候,比如你跟一个女生一起看一本书,你喜欢她,就在这本你们平常借来借去的书上,比如《指环王》第三部,你会留一个密码信给她。她如果能破解出上面的符号,就知道你大概是通过这本书在向她表白。这两件事就是一样的。
瑞安·雷诺兹演了一个电子情书,可以被多次翻译的、对女主敞开的一个情书。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陈词滥调(cliche)的剧本。它并没有比《头号玩家》有更多的视觉特效、剧本深度、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可能性的投射,或者是在感情上讨论得更深;它更没有《黑镜》那么犀利,那种甚至冷漠和残酷的,对于人的延续的一种剥削。

《黑镜》剧照
耿游:很多人说看到《失控玩家》就会想到《楚门的世界》。其实除了《楚门的世界》,还有一部电影是《失控玩家》借鉴最深的——1988年上映的《极度空间》。它是哲学网红齐泽克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极度空间》有一个核心的概念,或者说它整个片子的一个核心设定,就是主人公机缘巧合拿到了一个墨镜。他把这个墨镜戴上之后,整个花花绿绿、五彩斑斓的世界就变成黑白的了。所有的广告标语,所有的书籍,所有的杂志,一切给你传达信息的东西,都被抹去了那些所谓表面的、表层的信息,而你能够看到的是一些直接的意识形态。举个例子,远处的沙滩上有一个美女,而他戴上眼镜之后看到的就只有一个词:繁殖。就是这样一些很露骨的意识形态话语。
在《失控玩家》里也用了同样的梗,就是有一个眼镜,戴上眼镜之后就看到了所谓的真实的世界。当然《极度空间》是做了一个减法,把很多最外在的东西减去了,让我们看到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失控玩家》是戴上眼镜后,看到了一些多出来的东西,但是同样也看到了一个所谓真实的世界。
齐泽克经常会讲一些意识形态批评的东西。他特别喜欢强调这个电影展现出来的一个很深刻的思想,或者说一个想法,就是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事物拥有一个本质,而意识形态的话语是附着在上面的,我们可以把它洗掉或者扔掉。比如说一个LV包, LV这个东西是社会话语体系赋予它的,我们把这层所谓的建构出来的意识形态之下的产物洗掉,那么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包。
实际不是这样。我们通过这两个电影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或者我们想要知道的本质,它变成了真实的一部分,你没有办法割除它。你戴上眼镜了,并不是抹除它了,而是真正看到它了,你逃不掉。这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事实。再说得通俗点,我们在寻找一个本质,或者在寻找真相,或者真实。什么是真实?不管是我戴上了墨镜,看到的那些充满意识形态标语的真实,还是《失控玩家》里面,小贱贱戴上墨镜,看到了他和NPC的血条,看到了一堆道具,这也是一种真实。
我个人觉得蛮好的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导演的自知,就是《失控玩家》给了我们一种更积极的面对真实的态度。这得说到另一个电影,这两天它也发了个新预告片,就是《黑客帝国》。
《黑客帝国》对待真实的态度,显得过于谄媚,当然这种谄媚自有它的历史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续了一波命之后,晚期资本主义更加疯狂且隐蔽的侵入我们,不仅仅是曾经的衣食住行,作为精神食粮的文化产品也浸泡在商品拜物教的海洋中,黑客帝国就是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之下诞生的,他为彼时惨淡的真实提供了一个宗教般情绪宣泄的出口——或许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在吞下药丸之后。这个故事我们周围的道友也常说,只不过锡安被称作仙界,道友们的红色药丸也更大更圆。
说回电影,当我们认清追寻真实是某种虚妄之后就会发现,同样是探讨真实,《黑客帝国》给出了一个现在看来过于谄媚的办法——在幻觉中成神。而《失控玩家》则给出了一个看似平庸的办法——活在当下。难能可贵的正是这点,《失控玩家》带着某种狡黠,尝试用“躺平”去对抗伪装得越来越精巧又华丽的泡泡,这泡泡便是《黑客帝国》里的红色药丸,它代表着被设计的“真实”,一个为你我构建出的完美幻觉。可惜你我并非生活在柏拉图的山洞中观看影子,也并非反抗世界的救世主。不论是红色药丸还是黑色墨镜,你我还得要继续生活, 思考一下被幻觉笼罩的我们还有什么反抗的余地。
《失控玩家》的意义正在于此,它尝试为无法奔向“真实世界”的你寻找一条更加务实的路,活在当下,朋友是真实的、大块头也是真实的,和女主记忆的同样是真实的,甚至最后被很多人吐槽的结尾,在我也是足够真实的,相比幻想一个并不存在的真实,把握当下变成了更积极的选择。你看痞子都告诉大家,散了散了,没有使徒也没有EVA,大家请回到三次元吧。
宗城:它是不是也可以被解读为一部反乌托邦电影,虽然看似那些NPC自我觉醒之后展开了反抗,但是它其实不承诺一个乌托邦的幻想。它会告诉你,这个游戏世界确实是虚假的,但你也不能在彼岸找到真实。于是它只能给你活在当下这么一个看起来有些勉为其难,对普通人来说又非常现实的一个回答。
我看到这部影片结尾的时候,一方面会觉得这是非常合家欢的一个处理方式,它把一些严峻的或者说让人觉得再走一步就会很困难的命题相对地搁置了。我觉得它有一些困境的转换,比如说游戏中角色的自我觉醒之后,他们的一些处理会显得过于顺滑。它很像硅谷程序员的一个童话。你会发现,照着他的故事走的话,这不就是硅谷程序员幻想中的世界吗?
李典峰:而且不但是硅谷程序员,最后他说我们还要去银行上班吗,然后说没有银行了。没有银行那就乌托邦了。硅谷程序员在西岸跟东岸的金融家们在生态位上其实是有点冲突的,一边要编制一个扁平、去中心化,但是又可以从后台进行一些微控操作的一个赛博朋克的世界;而另外一边是金融帝国的金融家们通过铸币税和军工复合体去进行奴役的世界。但是他们又必须尝试去把这件事情抹平,所以就把银行取消掉,大家都去,你懂的,用虚拟货币,搞这种NFT或者让程序员和金融家有一个和解,然后这事就句号了,乌托邦就实现了,大家就自由了。我就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吗?就不太理解。
宗城:仔细观察这个电影最后的走向,它既不符合所谓的财阀或者说政治家的倾向,又不完全符合平民的倾向,它其实是硅谷程序员意识到他在现实里不可能凭个体之力对抗老大哥,但他可以在他设计的程序里实现这件事,在潜移默化之间去中心化,就应了那句话,叫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他甚至不会跟你讨论真实与虚构的对立,而是跟你说真实就是假的,你不要那么在意真实这个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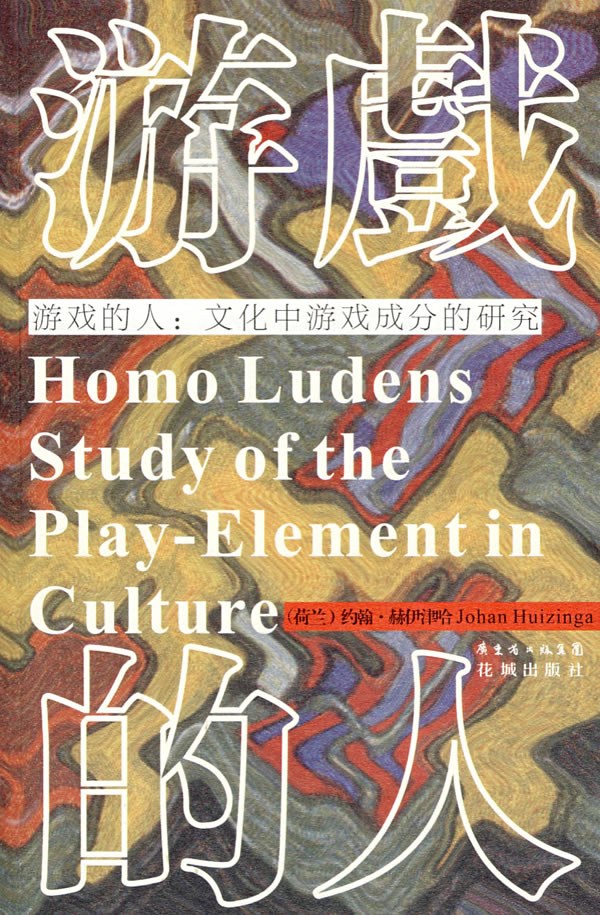
Part 3 眼球控制术
宗城:典峰刚才提到了《黑镜》的圣诞特辑,可以再科普一下它为什么会比《失控玩家》更进一步或者说更加严肃地讨论了这个命题。
李典峰:这里涉及到一个身体的问题,也是我们之后做游戏研究的方向。我跟耿游还有比较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可能真正属于电子游戏,或者从电子游戏往回追溯,它能够贯穿很多问题的作为方法论的底色。基特勒、德勒兹和维特根斯坦,包括梅勒·庞蒂,梅勒·庞蒂、德勒兹和基特勒这三个人是可以从他们的方法论和他们讨论对象里贯穿的。
基特勒先谈到一个问题,“软件不存在”。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它具有一个密码机的本体,那个东西它可以翻译,而且它一定是物质化的。这里面计算机是一个非常唯物的东西,你不要用尼奥和matrix涉及到犹太复国主义的那套宗教词汇去跟它讨论一个关于真实和虚假的东西,那没有任何意义。有核电的地方和没有核电的地方,你用电的这种放肆程度都不可能一样。它一定是有物质基础的,而且不是object的客观的物质,而是一个material的非常唯物性的东西。
然后它往回推一步,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计算机跟人的身体之间通过运动影像,通过光子和眼睛之间的关系,它如何能介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是我们今天在谈“biopolitics”那个词翻译来的生物政治,它跟如何去归训人的生活方式、监控每一个在计算机网络里面生活的个体有关。那么这件事情它涉及到我们一生的长度和我们每一天注意力集中在屏幕内容,什么内容和谁传递这些内容给我们有关。
再往前推一步,我们的观看影像和我们的身体在观看影像的场域里面如何形成一种行为强化。这涉及到格式塔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今天是被社会领域所滥用,这些资本,包括这些程序设计,他们在滥用这些人类行为强化心理,包括格式塔心理学、注意力经济学的这些知识。但他们却没有告诉所有人,没有让所有人接受这些知识的教育,形成一种从知识上的平等。这就是平权问题,你至少得让人家知道,让我有权利选择拒斥这些,但他没有。
维特根斯坦在谈论游戏的时候说,很多游戏活动原始的样子和目的在今天被偷偷地藏匿到所有的游戏方式里面,包括赌博。为什么会有game disorder这个词?你通过游戏丧失了社会功能,并且产生了极大的比如说悔恨、愧疚、无力,甚至精神崩溃,这是你因为游戏行为而造成的。他说的可不是video game,他说的game是包括所有的casino里面的那些活动,赌场里面的gambler,他其实是在毒瘾沉溺行为强化里面造成的一种社会功能紊乱,这个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游戏行为失控紊乱造成的一个严格的界定。
这件事情其实是个普遍的社会学问题。它跟今天我们去网瘾治疗里面拿电机那个完全没有关系,它是个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前两天真实发生在浙江的新闻,一对父母为了去麻将馆打牌,把孩子落在车里面锁住了之后,孩子就死在里面了,一个4岁的小姑娘。这就是明显的disorder,这对父母是一定要接受刑事责问和精神治疗的,他们很明显地由于游戏行为成瘾造成了社会功能丧失。这件事情也是广泛存在于所有国家的,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因为城市化发展中很多人的工作强度造成他无法完全去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在劳动和休息之间转换,这就涉及到很多其它的比如说社会学的一些问题。
《黑镜》从这里进行了深度的批判。在圣诞特辑里它讲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未来我们的眼睛会移植一个东西。那是在第三季的某一集里面,有一个镜头就是男女晚上在夫妻生活的时候,两个人的眼睛都有一个植入装置,在看着他们俩初次见面时云雨的那种状态,但是他们两个人已经没法对对方的身体发生这种感情,而只能对那段影像发生生理反应。这个技术就是,我的眼睛会被接上一个互联网,我能看到的东西是这个软件下载下来给我看到的。我实际上可以通过我的软件和互联网上的一些软硬件接口的方式,让我看不到整个肉体能接触到的外在的现象世界本身存在的东西。
举一个电影里面的例子,比如说在一个大的社交网络上面,你被我拉黑了,或者因为社交网络的公司评级,你的信用或者其它方面有问题,那么我就看不到你,你在我面前就是一个像马赛克一样的黑影。

《黑镜》剧照
另外一个方面,它讲到你的大脑里面的一些生物信息可以被提取出来,形成一个具有你的人格和知道你所有行为偏好的生物数据。这个生物数据可以让你家庭周围的这些智能家电设备完全按照你的行为习惯来布置。也就是说把你自己的一个人格切片变成一个管家,来让他辅助你,管理你的生活。而它体现出来的其实是有一个真正的人的这种,一个精神状态的小的你被关在这个机器里,它出不来。那个是真的NPC,但它不是一个AI,而是一个甚至可以说有人类灵魂觉知的一个东西,它被关在里面。而somehow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有一个人他精神崩溃了,他回到自己的身体里还是怎么样,去找他的妻子,然后他被评价为非法跟踪别人。他被整个社会给关在了外面,再也看不到别人,所有人都也看不见这个人。
你说对于人的视觉感官来说,他还是一个人吗?那一集的结尾就在这个特别恐怖那个地方。它批判了很多东西,关于接口或者叫界面,是电子设备硬件跟人之间的关系。它不再只是一个鼠标,一个屏幕,一个我们生理上可以脱离它,没有太多问题的一个东西,而是插件式的,嵌入到我们的肉体里面。当肉体的软硬件插在一起之后,社会里的每一个个体它其实是受一个更大的终端管理的。如果有一个人被排斥在秩序之外的话,他就是不再在社会里的裸命。
这个裸命是很恐怖的,它跟我们今天理解的三和大神,把身份证当掉之后去广东那些地方,在黑网吧门口喝大水,然后上网的那些农民工还不一样。那些人是有social的,而这个人完全被排斥在社会秩序之外,而且是被强制执行的,这是未来有可能的非常恐怖的一个现实。
这里有很多东西值得讨论。我们怎么去使用这种高度赛博化的社会领域里面的这种公权力,就是社会网络资源,让一个人不说话,或者让一件事情被取消存在,比如说下架之类的。这些在今天看来都很敏感,都是需要去讨论的一个公权力,它的法理性在哪儿,这都是需要去重新讨论的。
宗城:我觉得你说的《黑镜》那一段还蛮有意思的,就是那两个夫妻,他们眼睛里装了一个装置,它让我想到了一种认知统治,未来资本主义的统治可能不是通过残酷的身体上的暴力术,而是认知上的幻觉,通过技术让你在认知上满足自己的一些虚假的高潮,从而去缓解你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抗力。
李典峰:这不是未来,它已经在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