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和游戏有什么关联?本篇文章将从(游戏)规则的角度重新审视学术界的“规则”,可以看作是一篇批评“学术”的文章。批评的意图也更多是希望游戏爱好者与各行业的研究者能从游戏这一独特的视角去反思自己的工作,并且从中找到幸福和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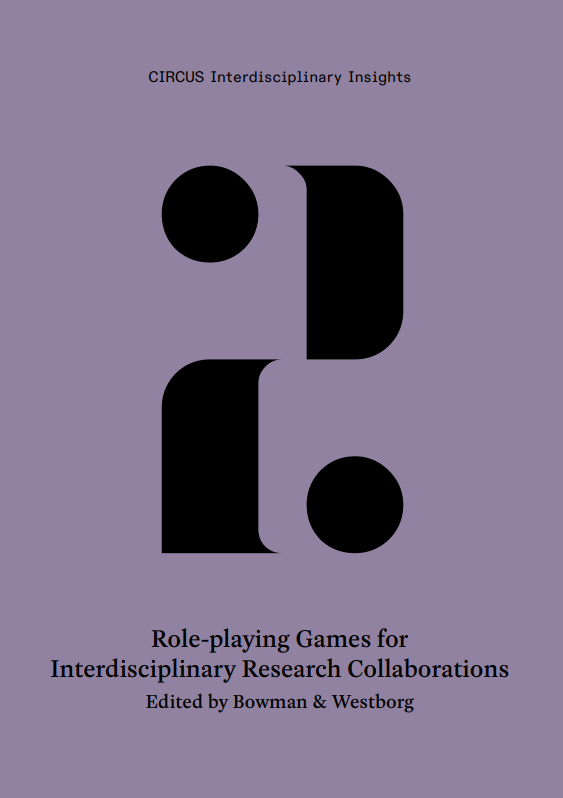
本期文章将基于《学术界的游戏-有质量的玩》这篇文章进行讨论(The Game of Academia – Playing with Quality )。在这篇文章中,乌普萨拉大学游戏设计系教授Doris C. Rusch结合自身的经历,从(角色扮演)游戏设计的角度介绍了她是怎样看待学术这一“游戏”的。
这篇文章来自于2024年Bowman等学者合著的学术书籍《用于跨学科研究的角色扮演游戏》(Role-playing Games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ollaborations),出版于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主要讨论角色扮演游戏与其他领域的关系。
[1]注:由于本文章横跨管理学、游戏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可能存在笔者能力不足翻译有误的名词,笔者在可能有误的名词旁都有标注原文,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搜寻原文阅读比对。本文章也穿插了一些与TRPG相关的讨论,与大家共同思考。
本期亮点
- 学术和游戏的相似点
- 为什么麻省理工的博士后都不想做学术了
- 学术界的内部规则为何引发倦怠感
- 学术界也是“游戏化”的
- “获胜”并不意味着拿出高质量的工作成果
- 自由的规则和严格的规则
- 我们能否追求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 游戏促进社会发展和社区建设
概念:学术界作为一个“大游戏”
作者首先指出,从游戏设计的角度来看,可以把学术(academia)看做一种“游戏”,而学者作为参与游戏的“玩家”来看待。和传统的分析类似,这种视角也会考虑我们如何吸收学术系统(the system of academia)的价值观念(理解规则)、我们对待它的立场、我们如何在(学术)规则的框架下共创。
The game design perspective provokes questions on what experiences academia, momentarily seen as a game, afford its players.
故事:博士后的苦恼

对于Doris C. Rusch来说,她曾经认同学术的价值观念,但又因为学术系统而饱受困扰:
“对于一个从未立志要成为学者的人来说,我最终在大西洋两岸拥有了一段奇怪的画册式(weirdly picture book)学术生涯。这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说真的,在我童年在非洲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的时候,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收集青蛙并把它们带进浴室“洗澡”;高中时期,我在奥地利多伯恩(Dornbirn)乡村一直用“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小说作家”这个问题困扰着职业顾问,16 岁时,我在酒吧弹奏布鲁斯钢琴赚到了第一笔真正的钱。 这些都与“教授”职位无关。但也许——只是也许——教授职位才是关键。即使是现在,在奥地利、美国和瑞典的不同大学学习了这么多年——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后、终身教授、晋升为副教授、成为讲师然后成为教授——我的自我形象也不是学者。好吧,这并不完全正确。在某个时候,我确实相信了这一点。我开始认同“学术”。实际上,这种认同感非常强烈。如果我不能在顶尖机构工作,那么似乎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我不被认可为研究员,那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当我意识到自己(不健康的)认同感的程度时,我决定离开学术界。当时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该机构的声望、期望和压力真的让我很困扰。我并没有为工作本身而苦恼。那部分仍然很有意义和有趣,我为“被一个系统吸收和定义”的感觉而苦恼。”
但真正的困扰来自于,她发现自己被系统局限了,绩效、质量等审稿人的要求像游戏规则一样,限制了自己的探索方向:
被一个系统所定义就像陷入了一场游戏,而“ 赢” 就意味着失去自己的方向感和意义。各种各样的绩效评估和衡量评估生产力、科学质量和影响力的方法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外部结构和规则上。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勾选框的游戏,先问“ 审稿人想要什么? ” ,然后再问“ 探索什么会很酷? ” 。
疲倦:学术界内部规则引发的职业倦怠

Rusch很快对这一问题本身产生了兴趣,她开始研究职业倦怠(这样思考下,不愿意玩游戏和职业倦怠的概念也很类似),学术研究中关于倦怠的原因有这样一些要素:
- 外部控制点(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干预
- 对自己缺乏“内在的肯定”(internal YES)
这意味着:当注意力向外转移,转向系统的期望和要求时,一个人自身的意义和目的就会被掏空。参与工作所固有的回报进一步被对环境的期望所取代,希望环境能够欣赏和承认自己的贡献。人们并不是出于自愿,不是出于好奇心或动力而去做工作,而是因为需要勾选方框(循规蹈矩)或通过外部来源满足需求(很有精神分析的感觉)。
总结学者们的观点可以发现,外部的主导并不会给人带来实打实的幸福感:如果一个人的生活被对事业或社会认可的自恋追求所主导,那么他的生活将缺乏满足感和情感回报(而这些正是存在意义的来源)。自恋的追求需要精力,并会产生压力。一个人不会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兴(joy),只会感到自豪(pride)。骄傲既不能滋养灵魂,也不能温暖灵魂。
[2]注:是的,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学习是为了让知识滋养我们的灵魂。
异同:学术和游戏的差异性
学术界旨在实现什么?人们可能给出产生知识、促进全民健康和福祉等答案。Rusch认为,无论如何,胜利的状态似乎是“ 创造尽可能明亮的光芒” ,这束光芒由最有意义、创新性、创造性、强大、相关的发现、方法和理论组成, 帮助我们解决和应对挑战和问题,并充分发挥人类的潜力,改善整个地球。她准备以这个概念续接分辨学术和游戏的区别。
她把学者比作灯塔中的一束光芒,她发现,如果没有每个学者进行的研究,就不会产生知识,就不会有光明,就不会有灯塔。也就是说,学者在学术这个游戏系统中,既是玩家,又生产资料。但在普通的游戏中,玩家并不生产资料(Caillois和Huizinga的游戏学理论,Les jeux et les hommes, 1961),所以学术可以说是“游戏化”(Gamification)的(因为它确实有规则),但学术本身并不足以构成游戏概念(因为学者并不单纯从中学习和享受,他们还创造)。
游戏:学术的游戏化
将一件事情游戏化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是游戏,游戏化的目的是将“玩家”作为资源,以实现“游戏之外”的某些目标。这一扩展可以将游戏这一概念扩展到任何有规则的行动当中,像戏剧游戏就明显具有教育意义,游戏更少。
Gamification aims to en-list players as resources towards the accomplishment of some goal beyond playing.
正如游戏研究员 StuartBrown 所理解的“ 游戏” (Brown,2009) ——游戏本身不是为了游戏本身,而是为了玩家可能关心或可能不关心的目的。通常的假设是他们不关心这个目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通过游戏这类系统的奖励结构来激励他们。
[3]注:从这里可以看出,Rusch更加关注和认同游戏对人的积极影响,而非游戏本身,譬如现在流行的很多电子游戏都可以帮助人们锻炼反应能能力和决策能力。

Rusch举了一些例子,收集垃圾并投入垃圾桶这一行为并不有趣,像荷兰的 Efteling 公园那样收集垃圾并把垃圾放进童话人物 Hoile Bolle Gjis 形状的垃圾桶则显然很有趣。但研究表明,它们的新奇价值往往会很快消失,人们会恢复到以前的行为。世界上所有的徽章和闪烁的灯光显然都无法补偿人们做一些本质上无聊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唯一能带来可持续变革的方法是让人们真正地、发自内心地关心并接受新价值观。然而,这不可能通过外部结构从外部实现。
从这一现象反观学术界可以发现,制定规则的目的是确保合作,从而确保生产知识的质量。但问题是:规则只能影响行为。无论规则系统多么巧妙,规则激发的动机与研究人员自愿、快乐和好奇地进行研究时所具有的动机截然不同。科研人员对外在事物的渴望可能非常强烈,因此规则系统可能非常强大,但它们永远无法真正吸引人的灵魂。
意外:“获胜”并不意味着拿出高质量的工作成果
对于学术界来说,学术界的游戏被“ 高质量” 研究是什么和研究人员应该进行多少研究才能获得系统奖励的理念支配。这些奖励包括工作保障、晋升,甚至能够完成自己最关心的工作;然而,忽视学术界游戏的要求和奖励可能会以牺牲职业生涯为代价。 只有当一个人作为研究人员的个人目标与系统的目标愉快而自由地一致时,他才能既自由,又获得奖励。
从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 获胜” 意味着例如拥有工作保障、晋升为副教授或正教授以及免除授课。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做最高质量的工作,这是系统的“ 胜利” 状态。工作只要好到系统认为值得就行。它不必尽善尽美。系统没有办法认可,也不会鼓励“ 发挥全部潜力” 。作者对这种现状直言:“真是浪费!”
自由:ludus规则和paidia规则

这两种规则的概念由Roger Caillois提出,简要的说,paidia代表自由,ludus代表规则(当然,ludus也是游戏学的词根,详细可以在这篇文章中找到漫谈“奇珍柜—整体艺术模型” #2)。Caillois说,孩子们刚开始玩耍时,他们做的事情没有条理。他们的玩耍是一种快乐的精力过剩——漫无目的地跑来跑去,扔东西,在假装的游戏中接住、放下和重新塑造角色。这就是游戏。然而,随着重复的次数增加,这种自由散漫的游戏开始呈现出结构和形式。制定规则来规范它。它成为一种通过严格规范的方式应对挑战的专注尝试,这就是游戏。
[4]注:在带儿童游玩TRPG时,确实不需要注意规则,我们也无法要求孩子们遵守规则,但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在恍惚中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与孩子有这么大的差异,连游戏都要遵守如此多的条条框框?
paidia规则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是为了它本身而参与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回报。这些规则更像是指导方针,因此可以更容易地与对工作的“ 内部肯定” 保持一致。这种方案非常平等,能够挖掘研究人员的全部潜力,因为决定什么是“ 足够好” 的责任在于他们。
在TRPG研究领域,有很多paidia风格的个人的、社群化的研究,这些经验非常好,促进了TRPG研究的发展。但我们也可以发现,ludus风格明显走的更加长远,因为符合规制有利于更广泛的传播(登上学术期刊)和引入更多的合作(引入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因为ludus规则下产生的文章能让大众和'专业人士'看懂,没有更多私人化的晦涩语句),当然,两者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很多期刊上的文章都曾经总结过过去的论坛研究。
现实:我们能否追求学术的真北
理想情况下,人们应该保持内心的“ 真北”(true north,意指那个心中的正确方向),只是偶尔检查一下它是否仍然与系统要求人们做的事情一致,然后,如果有必要,就纠正方向。这样做只是为了务实,而且是一种选择。在实践中,规则往往会遮蔽研究人员的“ 真北” ,甚至可能取而代之。这确实是一种危险的交易,因为追求“ 幸福”( Campbell, 2004)被想要“ 赢”所取代。
这通常会导致一种奇怪的行为,一种横向运动,或“ 玩弄系统”。如果满足系统的标准——遵守规则——是获胜之道,那么找出如何满足这些规则而不必真正承诺或屈服于它们就成为首选策略。如果重点是规则,那么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工作是否真正优秀,是否符合自己的标准或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些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如何被外部评估.........这种模式显然会引起倦怠,并且在很多领域都出现了。
思考:一些解决方案

至少作者认为,为了解决这一结构问题(ludus),需要通过学术机构之间的努力,加强以下的要点:
- 研究人员的自控力(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of researchers)
- 个人的诚信(Personal integrity,内在一致性)
- 寻找个人的真北之路
- 一种社区感和归属感,人们的行为不是出于匮乏感(sense of scarcity),而是出于慷慨和相互支持(generosity and mutual support)
- 培育不同类型的知识,将具体实践融入我们的研究/知识生成方式中,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智慧
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很多实践经验,我们可以在她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对于构建了一个没有考核压力和条框限制的社区的自豪感。她在最后以一连串问题做结:
你能做什么或已经在做什么来帮助自己和你所负责的人茁壮成长?你给学术体系带来了什么能量,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立足于什么立场?
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从笔者的角度来看,着手去构建这样一个人们各抒己见,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环境,真可谓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总结
“学术”没有被祛魅,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给大众一种权力的象征,这可能是有意为之,也可能是大众对自己的贬损。学习知识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勋章,而那些不产生实际效益的工作更是应受批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多时候追求智慧也是令人苦恼的,一方面有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仅剩的微薄的空余时间,究人一生能投入到喜欢的事情上的时间不过十之一二甚至更少,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做它呢?也许我们更是想把这一过程作为一个有趣的游戏求索吧,西西弗斯推动石头的时候,应当感受自己是幸福的。
生活是一个大游戏系统。我们遵守规则,但规则有时使我们倦怠我们的生活?这仿佛是抑郁状态的代名词。我们很难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但我们可以一直意识到,很难不代表不能,我们每个人有促进社区和社会进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5]注:最后,我们可以再从“系统”的角度去反思TRPG,我们会发现它很自由(在规则下的),当然,如果我们是为了构建一个有趣的、令人难忘的故事,规则是否又是一种枷锁呢?用paidia规则的心态去游玩是否是更加有益处的? 对于TRPG的爱好者来说,我们也许只是想在生活的条条框框限制之中,在TRPG里找回我们想要的生活,希望有这样一片安宁的空间与几个朋友在一个桌子前度过一个欢乐的下午,仔细思考,参与这些活动本就是一种温暖灵魂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