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和遊戲有什麼關聯?本篇文章將從(遊戲)規則的角度重新審視學術界的“規則”,可以看作是一篇批評“學術”的文章。批評的意圖也更多是希望遊戲愛好者與各行業的研究者能從遊戲這一獨特的視角去反思自己的工作,並且從中找到幸福和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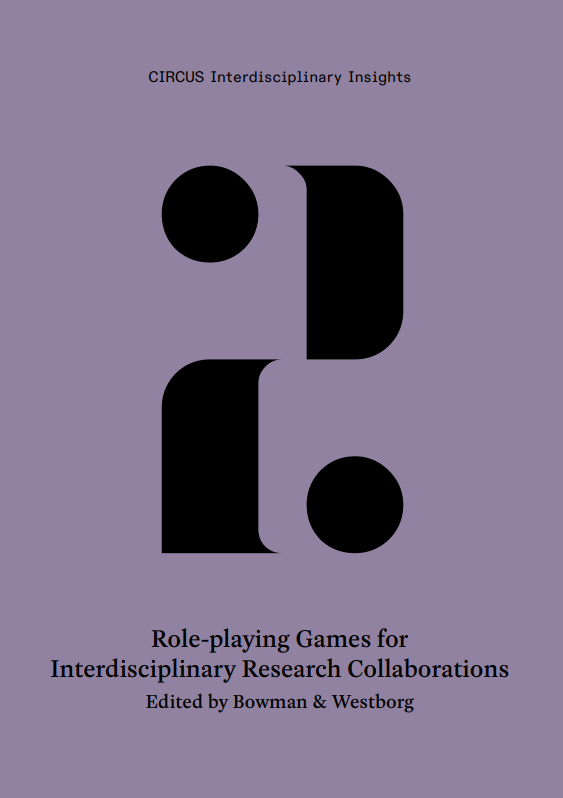
本期文章將基於《學術界的遊戲-有質量的玩》這篇文章進行討論(The Game of Academia – Playing with Quality )。在這篇文章中,烏普薩拉大學遊戲設計系教授Doris C. Rusch結合自身的經歷,從(角色扮演)遊戲設計的角度介紹了她是怎樣看待學術這一“遊戲”的。
這篇文章來自於2024年Bowman等學者合著的學術書籍《用於跨學科研究的角色扮演遊戲》(Role-playing Games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ollaborations),出版於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主要討論角色扮演遊戲與其他領域的關係。
[1]注:由於本文章橫跨管理學、遊戲學、心理學等多個領域,可能存在筆者能力不足翻譯有誤的名詞,筆者在可能有誤的名詞旁都有標註原文,感興趣的朋友也可以搜尋原文閱讀比對。本文章也穿插了一些與TRPG相關的討論,與大家共同思考。
本期亮點
- 學術和遊戲的相似點
- 為什麼麻省理工的博士後都不想做學術了
- 學術界的內部規則為何引發倦怠感
- 學術界也是“遊戲化”的
- “獲勝”並不意味著拿出高質量的工作成果
- 自由的規則和嚴格的規則
- 我們能否追求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
- 遊戲促進社會發展和社區建設
概念:學術界作為一個“大遊戲”
作者首先指出,從遊戲設計的角度來看,可以把學術(academia)看做一種“遊戲”,而學者作為參與遊戲的“玩家”來看待。和傳統的分析類似,這種視角也會考慮我們如何吸收學術系統(the system of academia)的價值觀念(理解規則)、我們對待它的立場、我們如何在(學術)規則的框架下共創。
The game design perspective provokes questions on what experiences academia, momentarily seen as a game, afford its players.
故事:博士後的苦惱

對於Doris C. Rusch來說,她曾經認同學術的價值觀念,但又因為學術系統而飽受困擾:
“對於一個從未立志要成為學者的人來說,我最終在大西洋兩岸擁有了一段奇怪的畫冊式(weirdly picture book)學術生涯。這是怎麼發生的? 因為,說真的,在我童年在非洲達累斯薩拉姆(Dar es Salaam)的時候,我最大的樂趣就是收集青蛙並把它們帶進浴室“洗澡”;高中時期,我在奧地利多伯恩(Dornbirn)鄉村一直用“我怎樣才能成為一名小說作家”這個問題困擾著職業顧問,16 歲時,我在酒吧彈奏布魯斯鋼琴賺到了第一筆真正的錢。 這些都與“教授”職位無關。但也許——只是也許——教授職位才是關鍵。即使是現在,在奧地利、美國和瑞典的不同大學學習了這麼多年——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後、終身教授、晉升為副教授、成為講師然後成為教授——我的自我形象也不是學者。好吧,這並不完全正確。在某個時候,我確實相信了這一點。我開始認同“學術”。實際上,這種認同感非常強烈。如果我不能在頂尖機構工作,那麼似乎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如果我不被認可為研究員,那麼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誰。當我意識到自己(不健康的)認同感的程度時,我決定離開學術界。當時我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後,該機構的聲望、期望和壓力真的讓我很困擾。我並沒有為工作本身而苦惱。那部分仍然很有意義和有趣,我為“被一個系統吸收和定義”的感覺而苦惱。”
但真正的困擾來自於,她發現自己被系統侷限了,績效、質量等審稿人的要求像遊戲規則一樣,限制了自己的探索方向:
被一個系統所定義就像陷入了一場遊戲,而“ 贏” 就意味著失去自己的方向感和意義。各種各樣的績效評估和衡量評估生產力、科學質量和影響力的方法將我的注意力轉移到外部結構和規則上。我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場勾選框的遊戲,先問“ 審稿人想要什麼? ” ,然後再問“ 探索什麼會很酷? ” 。
疲倦:學術界內部規則引發的職業倦怠

Rusch很快對這一問題本身產生了興趣,她開始研究職業倦怠(這樣思考下,不願意玩遊戲和職業倦怠的概念也很類似),學術研究中關於倦怠的原因有這樣一些要素:
- 外部控制點(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干預
- 對自己缺乏“內在的肯定”(internal YES)
這意味著:當注意力向外轉移,轉向系統的期望和要求時,一個人自身的意義和目的就會被掏空。參與工作所固有的回報進一步被對環境的期望所取代,希望環境能夠欣賞和承認自己的貢獻。人們並不是出於自願,不是出於好奇心或動力而去做工作,而是因為需要勾選方框(循規蹈矩)或通過外部來源滿足需求(很有精神分析的感覺)。
總結學者們的觀點可以發現,外部的主導並不會給人帶來實打實的幸福感:如果一個人的生活被對事業或社會認可的自戀追求所主導,那麼他的生活將缺乏滿足感和情感回報(而這些正是存在意義的來源)。自戀的追求需要精力,並會產生壓力。一個人不會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興(joy),只會感到自豪(pride)。驕傲既不能滋養靈魂,也不能溫暖靈魂。
[2]注:是的,千萬不要忘記,我們學習是為了讓知識滋養我們的靈魂。
異同:學術和遊戲的差異性
學術界旨在實現什麼?人們可能給出產生知識、促進全民健康和福祉等答案。Rusch認為,無論如何,勝利的狀態似乎是“ 創造儘可能明亮的光芒” ,這束光芒由最有意義、創新性、創造性、強大、相關的發現、方法和理論組成, 幫助我們解決和應對挑戰和問題,並充分發揮人類的潛力,改善整個地球。她準備以這個概念續接分辨學術和遊戲的區別。
她把學者比作燈塔中的一束光芒,她發現,如果沒有每個學者進行的研究,就不會產生知識,就不會有光明,就不會有燈塔。也就是說,學者在學術這個遊戲系統中,既是玩家,又生產資料。但在普通的遊戲中,玩家並不生產資料(Caillois和Huizinga的遊戲學理論,Les jeux et les hommes, 1961),所以學術可以說是“遊戲化”(Gamification)的(因為它確實有規則),但學術本身並不足以構成遊戲概念(因為學者並不單純從中學習和享受,他們還創造)。
遊戲:學術的遊戲化
將一件事情遊戲化並不意味著這件事情是遊戲,遊戲化的目的是將“玩家”作為資源,以實現“遊戲之外”的某些目標。這一擴展可以將遊戲這一概念擴展到任何有規則的行動當中,像戲劇遊戲就明顯具有教育意義,遊戲更少。
Gamification aims to en-list players as resources towards the accomplishment of some goal beyond playing.
正如遊戲研究員 StuartBrown 所理解的“ 遊戲” (Brown,2009) ——遊戲本身不是為了遊戲本身,而是為了玩家可能關心或可能不關心的目的。通常的假設是他們不關心這個目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需要通過遊戲這類系統的獎勵結構來激勵他們。
[3]注:從這裡可以看出,Rusch更加關注和認同遊戲對人的積極影響,而非遊戲本身,譬如現在流行的很多電子遊戲都可以幫助人們鍛鍊反應能能力和決策能力。

Rusch舉了一些例子,收集垃圾並投入垃圾桶這一行為並不有趣,像荷蘭的 Efteling 公園那樣收集垃圾並把垃圾放進童話人物 Hoile Bolle Gjis 形狀的垃圾桶則顯然很有趣。但研究表明,它們的新奇價值往往會很快消失,人們會恢復到以前的行為。世界上所有的徽章和閃爍的燈光顯然都無法補償人們做一些本質上無聊的事情(對他們來說)。唯一能帶來可持續變革的方法是讓人們真正地、發自內心地關心並接受新價值觀。然而,這不可能通過外部結構從外部實現。
從這一現象反觀學術界可以發現,制定規則的目的是確保合作,從而確保生產知識的質量。但問題是:規則只能影響行為。無論規則系統多麼巧妙,規則激發的動機與研究人員自願、快樂和好奇地進行研究時所具有的動機截然不同。科研人員對外在事物的渴望可能非常強烈,因此規則系統可能非常強大,但它們永遠無法真正吸引人的靈魂。
意外:“獲勝”並不意味著拿出高質量的工作成果
對於學術界來說,學術界的遊戲被“ 高質量” 研究是什麼和研究人員應該進行多少研究才能獲得系統獎勵的理念支配。這些獎勵包括工作保障、晉升,甚至能夠完成自己最關心的工作;然而,忽視學術界遊戲的要求和獎勵可能會以犧牲職業生涯為代價。 只有當一個人作為研究人員的個人目標與系統的目標愉快而自由地一致時,他才能既自由,又獲得獎勵。
從研究人員的角度來看,“ 獲勝” 意味著例如擁有工作保障、晉升為副教授或正教授以及免除授課。這並不一定意味著要做最高質量的工作,這是系統的“ 勝利” 狀態。工作只要好到系統認為值得就行。它不必盡善盡美。系統沒有辦法認可,也不會鼓勵“ 發揮全部潛力” 。作者對這種現狀直言:“真是浪費!”
自由:ludus規則和paidia規則

這兩種規則的概念由Roger Caillois提出,簡要的說,paidia代表自由,ludus代表規則(當然,ludus也是遊戲學的詞根,詳細可以在這篇文章中找到漫談“奇珍櫃—整體藝術模型” #2)。Caillois說,孩子們剛開始玩耍時,他們做的事情沒有條理。他們的玩耍是一種快樂的精力過剩——漫無目的地跑來跑去,扔東西,在假裝的遊戲中接住、放下和重新塑造角色。這就是遊戲。然而,隨著重複的次數增加,這種自由散漫的遊戲開始呈現出結構和形式。制定規則來規範它。它成為一種通過嚴格規範的方式應對挑戰的專注嘗試,這就是遊戲。
[4]注:在帶兒童遊玩TRPG時,確實不需要注意規則,我們也無法要求孩子們遵守規則,但我們有時候也需要在恍惚中思考一下,為什麼我們與孩子有這麼大的差異,連遊戲都要遵守如此多的條條框框?
paidia規則的研究中,學者們更多是為了它本身而參與的,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回報。這些規則更像是指導方針,因此可以更容易地與對工作的“ 內部肯定” 保持一致。這種方案非常平等,能夠挖掘研究人員的全部潛力,因為決定什麼是“ 足夠好” 的責任在於他們。
在TRPG研究領域,有很多paidia風格的個人的、社群化的研究,這些經驗非常好,促進了TRPG研究的發展。但我們也可以發現,ludus風格明顯走的更加長遠,因為符合規制有利於更廣泛的傳播(登上學術期刊)和引入更多的合作(引入政府和社會組織的支持,因為ludus規則下產生的文章能讓大眾和'專業人士'看懂,沒有更多私人化的晦澀語句),當然,兩者並不是相互矛盾的,很多期刊上的文章都曾經總結過過去的論壇研究。
現實:我們能否追求學術的真北
理想情況下,人們應該保持內心的“ 真北”(true north,意指那個心中的正確方向),只是偶爾檢查一下它是否仍然與系統要求人們做的事情一致,然後,如果有必要,就糾正方向。這樣做只是為了務實,而且是一種選擇。在實踐中,規則往往會遮蔽研究人員的“ 真北” ,甚至可能取而代之。這確實是一種危險的交易,因為追求“ 幸福”( Campbell, 2004)被想要“ 贏”所取代。
這通常會導致一種奇怪的行為,一種橫向運動,或“ 玩弄系統”。如果滿足系統的標準——遵守規則——是獲勝之道,那麼找出如何滿足這些規則而不必真正承諾或屈服於它們就成為首選策略。如果重點是規則,那麼從自己的角度來看,工作是否真正優秀,是否符合自己的標準或滿足自己的好奇心,這些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如何被外部評估.........這種模式顯然會引起倦怠,並且在很多領域都出現了。
思考:一些解決方案

至少作者認為,為了解決這一結構問題(ludus),需要通過學術機構之間的努力,加強以下的要點:
- 研究人員的自控力(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of researchers)
- 個人的誠信(Personal integrity,內在一致性)
- 尋找個人的真北之路
- 一種社區感和歸屬感,人們的行為不是出於匱乏感(sense of scarcity),而是出於慷慨和相互支持(generosity and mutual support)
- 培育不同類型的知識,將具體實踐融入我們的研究/知識生成方式中,使我們的研究成果有助於智慧
作者在文章的最後提出了很多實踐經驗,我們可以在她的字裡行間感受到他對於構建了一個沒有考核壓力和條框限制的社區的自豪感。她在最後以一連串問題做結:
你能做什麼或已經在做什麼來幫助自己和你所負責的人茁壯成長?你給學術體系帶來了什麼能量,你的價值觀是什麼?你立足於什麼立場?
這確實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從筆者的角度來看,著手去構建這樣一個人們各抒己見,相互學習、共同成長的環境,真可謂是“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總結
“學術”沒有被祛魅,在某種程度上仍然給大眾一種權力的象徵,這可能是有意為之,也可能是大眾對自己的貶損。學習知識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勳章,而那些不產生實際效益的工作更是應受批評。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很多時候追求智慧也是令人苦惱的,一方面有緊張的工作和生活壓力,另一方面則是僅剩的微薄的空餘時間,究人一生能投入到喜歡的事情上的時間不過十之一二甚至更少,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做它呢?也許我們更是想把這一過程作為一個有趣的遊戲求索吧,西西弗斯推動石頭的時候,應當感受自己是幸福的。
生活是一個大遊戲系統。我們遵守規則,但規則有時使我們倦怠我們的生活?這彷彿是抑鬱狀態的代名詞。我們很難去改變我們的生活和文化,但我們可以一直意識到,很難不代表不能,我們每個人有促進社區和社會進步的能力,而這種能力需要我們的共同努力。
[5]注:最後,我們可以再從“系統”的角度去反思TRPG,我們會發現它很自由(在規則下的),當然,如果我們是為了構建一個有趣的、令人難忘的故事,規則是否又是一種枷鎖呢?用paidia規則的心態去遊玩是否是更加有益處的? 對於TRPG的愛好者來說,我們也許只是想在生活的條條框框限制之中,在TRPG裡找回我們想要的生活,希望有這樣一片安寧的空間與幾個朋友在一個桌子前度過一個歡樂的下午,仔細思考,參與這些活動本就是一種溫暖靈魂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