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黑暗的大鐘鳴響在深淵中。
它的鐘聲響徹無數冰冷絕情的世界,哀悼著人類的命運。恐懼已經被釋放,黑夜中所有殘暴的生物都詛咒著暗影。這裡除了邪惡再無它物。外星怪形隱藏在棺槨形狀的船隻中,觀察著,等待著。貪婪,褻瀆的魔法在濃霧籠罩的森林中低語,光怪陸離的景象在憂慮的頭腦中穿梭。從那被血液浸染的土地之下深邃的虛空之中,窮兇極惡的可怖怪物行走在這無盡的夜晚中,享用著那些無為之人的靈魂。
放棄希望。不要相信信仰。活祭在瘋狂的火堆上燃燒,腐爛的屍體在躁動的墳墓中扭動。如惡魔般的憎惡存在咧開大嘴冷笑著,直視進被指控之人的眼中。而那些毀滅之神漠不關心的轉動著視線。
這是天啟降臨的時代,每一個凡人的靈魂都仰仗著那些藏匿在黑暗中的事物的施捨。這就是永恆的黑夜,怪獸和惡魔的行省。這就是戰錘恐怖。無人可以逃過詛咒。
而那口大鐘繼續鳴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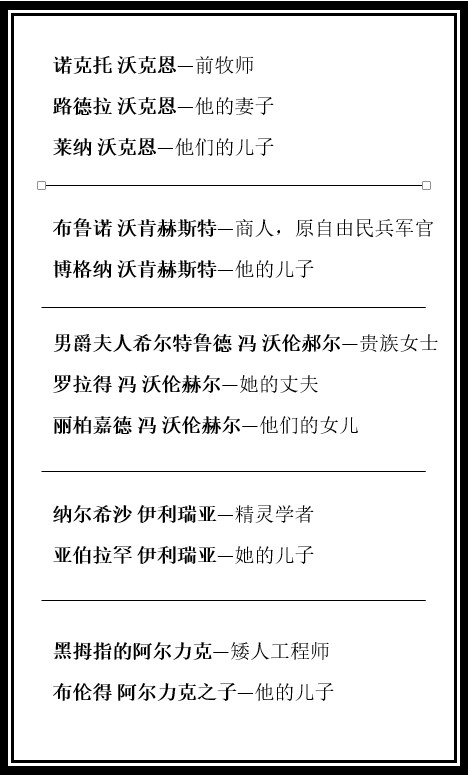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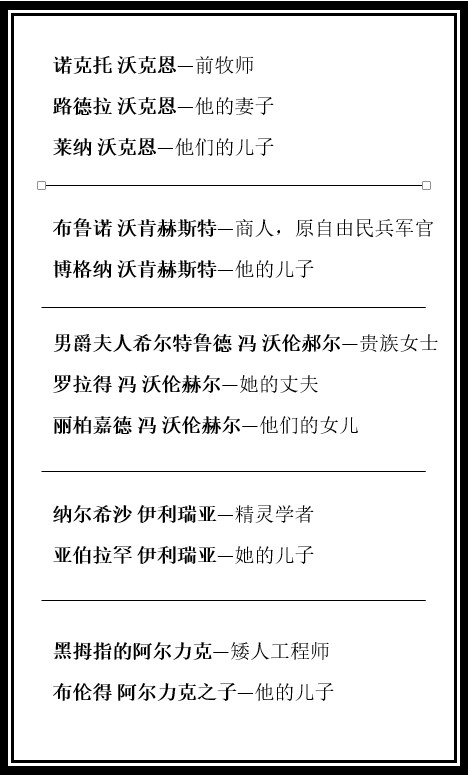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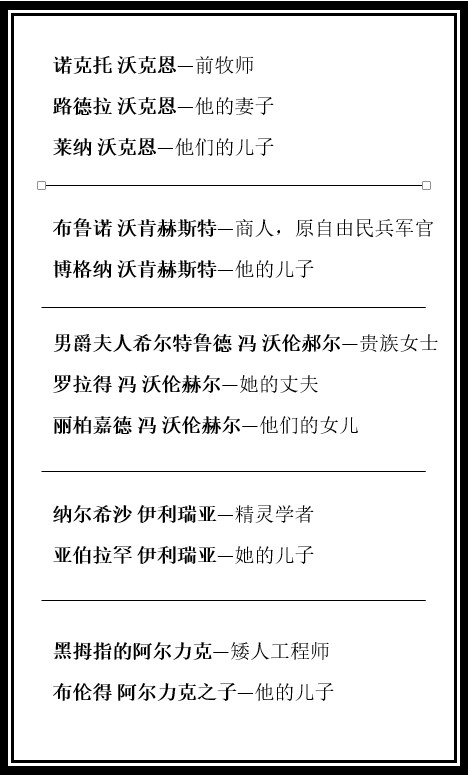
1 / 2
沉重潮溼的黑暗侵蝕著地窖。那股黑色盤踞在天花板上,在地板上環繞著,在一陣厚重的暗影中攀到牆壁上。就連沉寂的空氣都訴說著光芒的缺席,在每一口呼吸中都傳出冰冷和病態。氣氛中瀰漫著隱藏的殘暴,在午夜席捲過大地時一股無名的恐懼刺痛著心臟。
老人瘦骨嶙峋的手更加用力地握住了他的象牙柺杖。他那雙昏花的眼睛望向黑暗,直覺違抗著那告訴他自己什麼也看不見的邏輯。他的耳朵警惕著每一個聲音。他可以聽見蜈蚣在黑暗中追逐老鼠的聲音;滴落到地窖地板上的水聲;害蟲試圖咬進箱子和木桶時啃咬時的低聲嘶吼。房間裡沒有任何跡象暴露了另一個人在等待的身影。但這沒有區別,老人知道那裡不是空無一人。
“他來了嗎?”他輕聲問道,咬著舌頭說出了這些字。
“他到了,”那個站在老人身後銅製臺階上的商人確認道。他從腰帶上抽出一根修長的雪花石法杖,把兩隻手掌撐在了它的兩側。法杖的中心開始發光,一道藍色的光芒飛過了地窖房間。
地窖是一個龐大的房間,牆壁用黑鐵塊堆砌而成。地板是土地,其中混雜著銅的微粒。沉重的拱道支撐著高聳的天花板和銅製的頂板。房間大多數的地方都堆著錫制箱子和銅製的桶子。老鼠和蜈蚣之類的小獸從光芒中逃開。
地窖中有一個生物沒有逃開。他在商人開啟火炬的同時從他剛剛坐在身下的箱子上站了起來。他是如此的高大,看起來幾乎就像是野蠻荒地中生活的食人魔——而這個比較也並無道理。他確實長著一副野蠻的身體。他烏黑的皮膚上紋著白色的圖案,組成了一副致命的畫面。他的臉上沾滿髒汙,染黑的尖牙突出在嘴唇外,一雙眼睛陷在一張畫出的骷顱的眼窩裡。他修長的手指和棕色的臂膀上的每一根骨頭都用白色的塗料勾勒出來。他帶著一隻狼頭形狀的皮毛頭盔,它的鼻子和尖牙耷拉在他的額頭上。一面用骨頭系成的胸甲掛在他的身上。一小塊皮膚環繞在他的手腕上,那個被做成上述裝飾的人那張凋零的臉在這人的手腕上凝固成了一個安靜的尖叫。
“這就是他,”商人說,不能自己地聳了聳肩。
老人蹣跚著走下最後幾級臺階,身體沉重地倚靠在他的柺杖上。他清楚自己和這個野蠻人形成了完美的反差。他的身體搖搖欲墜,那副藏在天鵝絨外套裡的肉體消瘦殘破。乾癟的龜裂遍佈他顫抖的雙手,柚木和桃花心木製成的指環戴在他的手指上。他外套上的紐扣全是象牙製成,而那皮帶扣用的則是拋光的櫻桃木。他那蒼白褶皺的皮膚浸潤著玫瑰香水的味道。但所有的這些,都不如他那顆掛在心口的黃金鶯尾花更能彰顯出他那無窮無盡的財富。在金屬域的這片區域能夠誕生出如此精緻的人實屬罕見。
“這就是他。”他在走下地窖是重複著。他的聲音中沒有擔憂,只有期待。
商人也走下臺階陪同著老人。他幾近中年,棕色的頭髮正快速地從頭頂消失,銀絲已然藏進了他濃密的鬍鬚裡。他的體格沉重,挺著一個大肚子。他猩紅的開衫比起他的同伴少了幾分精緻,但那上面花哨庸俗地裝飾著許多藤蔓與金葉。他的所有衣著都與老人相像,吵鬧地向他人宣佈自己的富足,但缺少了老人那高貴的優雅。對商人來說,財富是需要大力宣揚的成就。但對老人來說,他的財產全都與生俱來。
“陀柯馬為了帶來您所尋找的東西費了許多周折,尊貴的大人,”那商人說。他向老人投去抱歉的一瞥。“恐怕我所投入的費用已經超過了我們之前所達成的交易額。”
老人用一個堅定的注視回應了商人。“你會得到獎賞的,古斯塔夫。”他把手伸向皮帶,解下了掛在那上面的皮革錢袋。他把注意轉向那野蠻人,漫不經心地將那錢袋扔給了古斯塔夫。“金錢對我來說已毫無意義。”
古斯塔夫掂量了一下那錢袋,快速地將它打開。他滿手抓著裡面的柚木錢幣,臉上露出滿意的笑。
“你想要什麼儘管拿去,”老人在靠近野蠻人時說。“你想要多少錢?”他問那紋著身的人。
陀柯馬把手交叉在胸前,目光對上了老人的凝視。野蠻人的眼神充滿力量,瞳孔中放射出原始惡毒的紅色。他頭頂的那隻狼頭的瞪視也充滿了兇狠。老人可以感受到仇恨,在這部落民眼中那股凝聚的狂怒。那股迫不及待想要傾瀉而出的嗜血慾望。
“不要錢,”陀柯馬最後說。他的聲音是一股低沉的嘟囔,就像一面戰鼓那般。“我帶來的你用錢可買不到。”
老人猛地站直了,那根象牙柺杖舉在空中準備打向陀柯馬。“你把它拿來了而它應該是我的!”他吼道,那副蒼老的身體因憤怒顫抖。
“你不能買走我帶來的東西,”野蠻人重複道。他的臉露出一個冷笑,真正的牙齒從那些嘴唇外的利齒後顯露出來。“它只能被贈與。”
“贈與?”老人喃喃道,他的手臂仍然準備著擊打的動作。
陀柯馬點點頭。“我不會賣,”他指向正蹲在地上數著錢幣的古斯塔夫。“他會賣掉它,但我不會。”
“把它給我!”老人嘶吼到。那根象牙柺杖砸向陀柯馬的頭。野蠻人用一隻手抓住它,把它從老人的手裡奪下,彷彿是在與一個孩童嬉戲般輕鬆。老人蹣跚著,失去了平衡,幾乎摔到了地上。他勉強依靠意志力才讓自己沒有傾倒。他不會在一個來自荒野的野人面前示弱。
“你很清楚,” 陀柯馬咆哮到,語氣中帶著欣賞。“你很清楚你要求的是什麼。它所代表的意義。它必須如何使用。”野蠻人把柺杖扔回給老人。“我在你的眼睛裡看見了和我一樣的火焰。你明白它必須如何使用。而你也一定會使用它。”
“它會有用的,”老人再重新倚上柺杖時嘶嘶地說。“它會比你那嗜血的靈魂敢想象的更加有用!”
“這樣做會有代價,” 陀柯馬警告道。
“我願意承擔,”老人說。“完全自願,滿心歡喜地承擔。我等待這一刻已經二十年了,現在我想要的就在我的面前!”他的臉暗淡下來。“把它給我,否則我會從你手上把它搶過來。”
野蠻人也向老人吼道。“血液從那裡濺出都無所謂,”
“但你的神確實關心能有多少血液可以貢獻給他,”老人回應道。“沒錯,你可以殺死我,但我向你保證這麼做會欺騙你的神靈。把它交給我,你的神將享受到一場盛宴。我會奉獻給他無數的鮮血!可以填滿海洋的血!”
陀柯馬又一次端詳著老人的目光。慢慢地,他把手伸向放在他身旁的一個盒子上方的一卷皮。他那髒汙的手指把那繫住包裹的內臟撥開。當他把這些皮移開之後,一件惡毒的物品展現出來。那是一把黃銅製成的長刀,劍刃像劍齒虎的爪子一樣彎曲著,劍柄鑄成了骷髏的樣子。一股邪惡的空氣從這把武器中放射出來,謀殺和屠戮的瘴氣瀰漫開來。
老人趕緊上前,無視著自己蒼老身體的疼痛。他的嘴唇捲成一股勝利的笑。“我終於可以報仇了。”他咯咯地笑道。
野蠻人後退一步,觀察著這位老人。陀柯馬對自己看見的非常滿意。
“看到了吧,尊貴的大人,”古斯塔夫從樓梯盡頭爬了過來。“我向您保證過他會帶來儀式刀的。”他指向陀柯馬露出的惡毒刀刃。“我只需要讓奪顱者部落知道您在尋找它就夠了。”
老人轉過身,用一個陰暗的表情看向古斯塔夫。“現在你知道我已經找到它了。”
古斯塔夫在他合夥人聲音中謀殺犯般的語調中顫抖了一下。“我們…有個…協議,”他在蹣跚站起的時候顫抖地說,他的手仍然緊緊捏著那些錢幣。
“你已經得到報酬了,”老人冷笑道。他的眼中閃出暴虐的火光。“我可以相信你拿到報酬就能給我帶來些什麼,古斯塔夫,但我要如何才能保證你不會告訴別人我買了什麼呢?”
“您可以相信我!您可以相信我!”商人在慢慢向樓梯退去時重複道。
老人搖了搖頭。“一個只看重金錢的人是不能相信的。”他重新看向陀柯馬。“我才剛剛見到你的朋友,但我們互相理解的程度一定超出你的想象。”
古斯塔夫驚叫出聲,轉身逃跑。陀柯馬的手已經伸向了他穿著的骸骨背心。在商人可以跑到最初的一級臺階前,他恐懼的叫聲變成了痛苦的哀嚎,陀柯馬認出了一把用骨頭做柄的刀子,深深插進了他的背部。部落民走到古斯塔夫的身旁,把那把刀拔了出來。他冷酷地把這受傷的人翻了過來,用同一把刀子捅進他的心臟。
古斯塔夫的慘劇沒有引起老人的任何注意。他正忙著重新把皮布重新纏上儀式刀。他在蹣跚走過地窖時緊緊地把這個包裹揣在胸口。
“如果你沒有使用它,我會知道,” 陀柯馬警告著走過他身旁的老人。
“你完事之後可以把古斯塔夫的屍體留在這裡,”老人說。“這裡是他做非法買賣的地方。他的僕人沒有一個知道這個地方。沒有人會發現他。”
陀柯馬扭動他的刀,破開了古斯塔夫的胸膛。他把手伸進商人的身體,掏出那正在滴血的心臟。他把這離開身體的內臟向老人搖了搖。“你向我的神做出了一個保證。若你破誓,恐虐必會發怒。”
老人笑了,那聲音如蟒蛇的嘶聲一般冰冷。“我為了這件事已經等了二十年。沒有任何神明或者凡人的力量可以阻止我的復仇,”他端詳著陀柯馬,高興地注意到野蠻人在遇上他的目光時有著一股不適感。
“我相信你,” 陀柯馬說。“我想我會盡快離開這裡。我會回到我的部落。”他的笑中同時有著殘忍和緊張。“我相信你說的話,也相信殘殺會從中蔓延出來。”
老人轉身爬上樓梯。“對,”他喃喃道。“死神已經降臨在瑞文巴赫的街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