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鮮豔的紅色與藍色與其所產生的二元對立,到“雙城”結構上的“上城”與“底城”之對立,到底在這對立現象的背後隱藏著怎樣“本質”並構成了這一切?在從開頭硝煙瀰漫的戰場到最後金克絲一炮橫貫夜空的觀影過程中,我們不禁會發出這樣的思考。

2021年末,這一籌備多年的動畫一經發布便引起現象級的轟動。它被譽為近幾年來最好的商業性動畫,與其製作精良的畫面、鏡頭與音樂一樣,其劇情中蘊含的意識形態同樣令人著迷。
開頭的鮮紅色硝煙,伴隨著兒童的歌聲作為一種徵兆出現。即便在歌詞中也顯現著明確的要素“一邊與河的另一邊;匱乏與豐盛”。緊接著鏡頭拉近,給出了迷底——一哼唱著與這場景格格不入的歌聲的,在戰爭中失去雙親的姐妹中藍色頭髮的妹妹。

而緊接著的劇情我們都知道了,作為底層頭頭的範德爾收養了這對姐妹。但很顯然,對立依然存在。她們為了錢同時也像所有年齡不大的孩子為了獲得家長的認可,這對姐妹以及其他的祖安(下層)孩子去到皮城(上層)一家大戶人家試圖偷走些值錢東西。

此時,一種重要的客體出場了——海克斯水晶。這種客體同希區柯克電影《後窗》中的結婚戒指一般,基於主體間的符號性關係,這種客體發揮著流通物的作用。它是獨一無二的,逃避二元鏡像關係的,我們能從它的虛假的對立版本上看到它鏡像化的失敗——微光、不穩定的、危險的、人造的、入世的、混亂的。海克斯水晶則是殘餘,是殘跡,重要的是它的在場,即現實碎片的物質性在場。後面的劇情訴說了海克斯水晶的來源——傑斯與他的母親在多年前曾被一個奧術法師所救,在那之後傑斯便想通過科學來控制魔法,通過一種技術將魔法“去神秘化”,藉此造福大眾。而海克斯水晶恰恰是魔法的化身,是魔法在場的碎片,就如同黑格爾意義下的上帝一般:上帝如果想變得有效,他就必須再次向他的創造物顯示自己,以某個入世的、醜聞的、具體的人(基督)為化身。海克斯水晶以及其衍生物的在場,就像是無數個碎片,保證了魔法的有效性。

海克斯水晶
這一客體必須在一系列二元對立中流通,從上層到底層,從姐姐到妹妹等等,儘管它是實在界的殘餘,是“排洩物”,卻充當著符號結構得以復原的積極條件:只有當它化身為這種純粹的物質因素(海克斯科技產品),而純粹的物質因素又充當著它(和魔法有關)的擔保時,主體與主體的符號交換的結構才能形成。在劇中這一交換則體現為在不同主要人物間流通。
緊接著我們便看到了更多顏色的出現,紅色:蔚;藍色:爆爆(金克絲);黃色:(梅爾);綠色(艾克)。我們甚至能輕易在政治光譜中找到其對應項:康米(極端權威左),辣脆(極端權威右),安資(極端自由右),安康(極端自由左)。甚至在上層與下層的分佈也是如此:蔚被關進監獄,出獄後作為無產者;艾克則在“野火幫”,是無政府主義者;金克斯作為希爾科的手下,認為上層人是一切災難的始作俑者;梅爾是議員中最富有的人,錢權均有者。微光的顏色是紫色(藍色加紅色為紫色),而底層的顏色基調主要為綠色(無政府主義)和紫色。上層的基調則是藍色與金色,恰好對應極端權威和資產階級。

蔚

金克斯

梅爾

艾克
在此我們需要注意一個基本機制:意義的回溯性建構,未來決定過去,意義也是回溯性產生的。通過兩句簡單的英語短語我們就能理解這一效果:The weed is getting too high.(植物長得太高了)/ The weed is getting me high.(我溜大了)。在這兩句話中,前半句結構的weed是完全相同的詞彙,其意義究竟如何決定完全取決於語句的後綴,在這一過程中,weed這一詞彙的意義便實現了回溯性建構。我們能從劇中發現太多被壓抑到無意識層面的能指:在第一集中艾克說來了個上層人花大價錢買了一堆垃圾,緊接著在第二集這人便得到了闡釋,他就是傑斯。又或是在第二集中爆爆與麥羅玩的打靶遊戲中,其中一個靶子的形象將在第三集得到闡釋——這一形象恰恰是希爾科的一名手下,甚至艾克這一形象本就具有回溯性的意義。這些原本沒有意義的事物,突然有了意義,只不過是在一個與之大不相同的領域。通過這一機制我們能更好地理解接下來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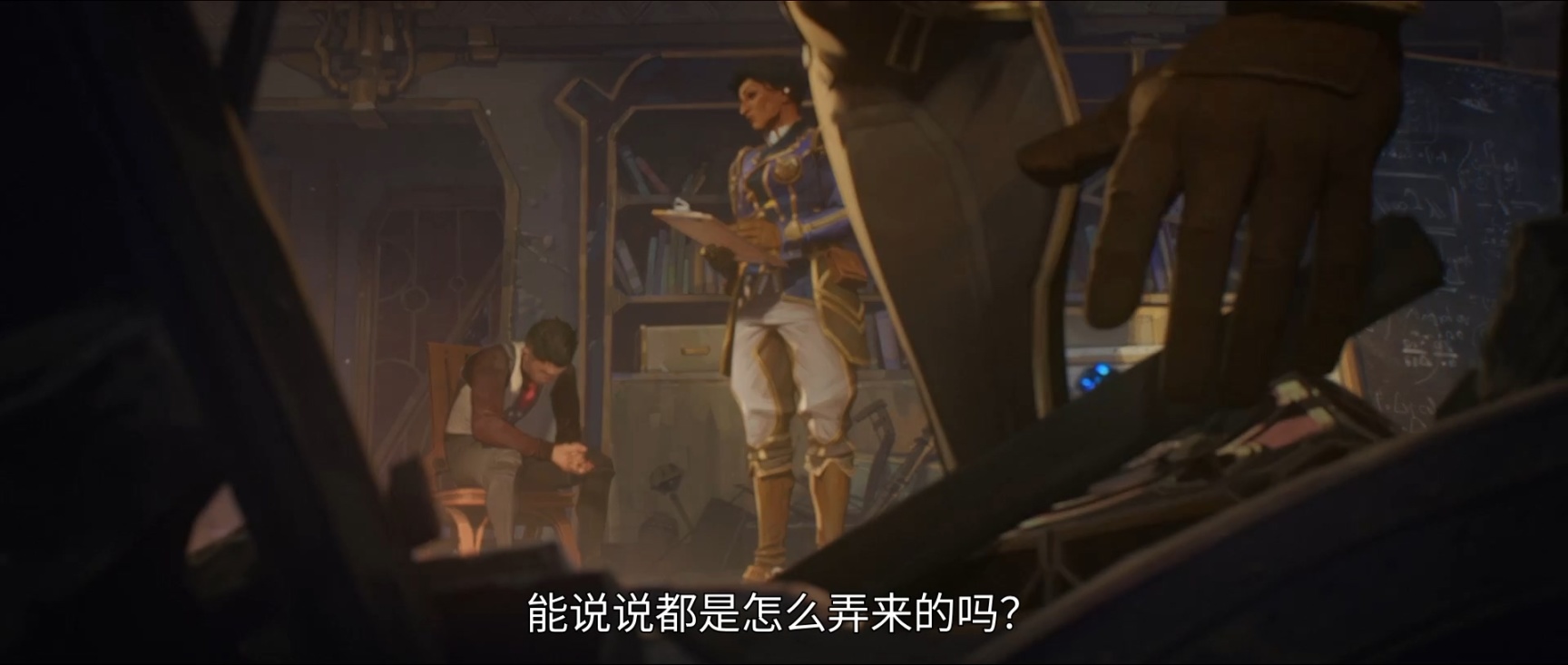


在希爾科通過收買馬可斯得到情報後,又利用微光殺死格雷斯森和本索,並抓走了範德爾。在這一系列劇情中我們看到了“父親”這一位置的替換,範德爾被替換為希爾科,並作為金克絲的父親;格雷森被殺死,由馬可斯上位作為新警長。同樣的,在後面的劇情中,我們也能看到傑斯的上位和黑默丁格議員的退場。同那著名的拉康斷言一般:一個瘋子相信自己就是國王,一個國王也相信自己就是國王——他直接把自己等同於“真命”天子,瘋子與國王相比較,瘋子並不比國王更瘋。角色從“原父”這一位置上退場時,就已經意味著被閹割並剝奪了菲勒斯,成為了“失去國王位置的國王”,即普通人了(即便他活了三百多年也無能為力)。所以黑默丁格在退休後走向無產階級是必然的。菲勒斯在這一置換的過程中似乎轉移到了新上位者的身上,但主體其實從未擁有過菲勒斯。






希爾科這一新父親的形象十分值得推敲,他不斷重複的,不斷回憶的創傷,正是拉康那裡的“聖狀”,失去這一創傷他反而一無所有。這一聖狀完美體現了拉康意義下的“外密性”——在你之內又超於你。似乎把希爾科的其他要素刪掉些也並不會影響到他的創傷性內核——被範德爾背叛並差點溺死在水中。他從頭到尾所做的事情無一不是對這一神聖症狀的再現,即便是他對金克絲的“父愛”也是一樣。希爾科在前期表現出典型反派的形象,坐在高背椅子背後,似乎是一切的幕後黑手,如同經典動畫《神探加杰特》的開頭:從背後看像是椅子上坐著人,從側面看便可看到椅子背後空無一物,有的只是“相信這一表象背後本質”的主體。這一簡單的機制恰恰說明了那椅子背後的純粹效果,“父親”只是純粹的結構性位置,換誰坐上這把椅子都無所謂。但雙城之戰對希爾科的描繪顯然沒有止步於一個“經典反派”的形象,而將他塑造成一個癔症患者:不斷的重複著“我們要他們好看”,並死死的抓住他的創傷不放。



爆爆與金克絲之間的轉換幾乎貫穿了整部作品,作為一個在一開始就表現出精神分裂徵兆的角色,金克絲逐漸代替了爆爆的出場。同她的兩任父親一般,她也要死死的抓住她的創傷——她害死了所有人並遭到了姐姐的拋棄。我們不斷的看到壓抑物的迴歸:死去之人的形象不斷地在金克絲腦中閃爍,並以不同的聲音和她對話。很顯然,金克絲大部分時候處於想象界,就如同未經過符號性閹割的兒童一般,她腦內的形象將會進行無休止的纏鬥。但要注意在片尾時金克絲選擇了寫有“金克絲”字樣的座椅,而並非是寫有“爆爆”的,在此刻她才獲得了整合。那麼這一符號性閹割的契機是什麼呢?——“父親”的死亡讓父之名得以出場。


我們不得不提到兩次死亡——符號性死亡與生理性死亡。齊澤克這樣舉例:在視頻遊戲中,我們真正與兩種死亡的差異打交道:這種遊戲的通常規則是,玩家(或者說的確切些,在遊戲中代表他的那個形象)擁有數條生命,一般是三條;他受到了某種危險的威脅,比如遇到了要吃掉他的怪物,而且如果怪物追上了他,他就會失去一條命,如果飛快地到達了目的地,他就會額外獲得一條或幾條生命。因此,這樣的遊戲的整個邏輯是以兩種死亡的差異為根基的:一般的死亡,讓我丟一條命;最終的死亡,讓我輸掉遊戲。
在安提戈涅那裡,她先符號性死亡,被排除在城邦符號共同體之外,先於她的生理性死亡,並以崇高美澆鑄了她的性格。但在哈姆雷特父親的幽靈那裡,他先生理性死亡,符號性卻未死亡,沒有“清賬”,這是他作為可怕的幽靈歸來,直到他的債權得以償還才肯離去的原因。
很顯然,爆爆夥伴們的死都和哈姆雷特的父親一樣,先生理性死亡,符號性未死亡,所以一直作為幽靈,作為詭異的形式漂浮在金克絲周圍。希爾科的死更是如此,他的死讓真正的“父之名”得以出場——金克絲這一名稱,整合了金克絲與爆爆的不和諧,父之名的在場恰恰是父親的不在場,父之名以符號化的形式代替了父親幽靈般的在場,與哈姆雷特接受了其父親幽靈的詢喚一般(讓哈姆雷特為他復仇),金克絲也接受了希爾科的詢喚,通過接受這種委任,通過在主體間符號網絡佔據某個位置,爆爆才真正成為了金克絲。

蔚作為另一主要人物,和作為資產階級女兒的凱特琳進行了雙向的運動:蔚對上層人進行理解,凱特琳則走向下層。但很顯然,她對爆爆還停留在想象性認同的階段,金克絲的出現令蔚無法接受。金克絲同樣將蔚作為她的創傷,以至於在最後的對峙中還是選擇了蔚。然而有一處需要注意,在蔚受傷以至於精神恍惚時,那被壓抑物,依然以替代物的方式迴歸了,其死去的母親之幻影重現在了凱特琳身上,此時我們才回溯性的發現凱特琳的形象與其母親形象之相似。甚至蔚本身對希爾科和金克絲來說也是被壓抑物的迴歸,正如希爾科在第五集結尾的驚歎:她回來了?從死亡中迴歸?


維克托和傑斯同樣作為上層人物,卻同樣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維克托身為上層人,卻總佩戴著一個標籤——底層人。後面則明示了這一第二標籤的迴歸,通過微光,這一底層獨有的技術迴歸。維克托在某種意義上和金克絲相似,我們都在這兩個角色的身上看到了微光與海克斯科技的結合。微光:所謂的激發人的本能其實是主體性之維的表現,是主體面對實在界之維,無能、失敗歇斯底里的表現。魔法:則是不可觸及的原質,只能憑藉海克斯科技這一符號客體來顯靈。
維克托這一形象是由始至終伴隨著創傷的——他小時候便腿腳不便,即便在通過微光與海克斯核心獲得了某種意義上的健全後,緊接著,新的創傷又銘刻進了這個角色——因為自己的失誤,導致一直對自己有好感的助手斯凱被海克斯核心瓦解至灰飛煙滅,與此同時“斯凱”這一看似默默無聞的小角色從無意識層面迴歸了——維克托兒時在河邊造小船時,從岩石上與他對視的女孩恰恰與這一女助手同名。


在慾望的層面上,正是這種一次次的失敗,帶來了慾望的再生產——再來一次(encore)。拉康在題為“再來一次”的講座中,為我們理解悖論性的對立項契合提供了線索“只有通過形式化這一僵局,實在界才能被銘刻下來,首先,實在界當然是無法銘刻之物,當然‘不會不去銘刻自己’——它是石頭,每次形式化都被它絆倒,不過,正是通過這個失敗,我們才能在某種程度上環繞實在界的空位而行,並最終鎖定它。”通過不斷的失敗,海克斯寶石不斷的丟失、被人搶走,海克斯核心的實驗不斷的失敗,底層與上次的共和幻想不斷的破滅,我們得以鎖定實在界的位置——這一引發了一系列失敗的創傷性位置。實在界本身什麼也不是,只是符號結構中的空隙、空無。
主體的無能給了我們把握這一空隙的方法:維克托想造福底層的失敗,傑斯想帶領大家走向光榮未來的失敗,金克絲想整合自己的失敗,希爾科想統治祖安的失敗,梅爾想推動經濟進步的失敗,範德爾想維持和平擁護周圍人的失敗,黑默丁格想阻止海克斯核心發展的失敗等等,從主體的失敗我們得以看到大他者形式上的失敗:從正面來看,那像勃起陽具般的海克斯飛門,它是極其複雜且擁有卓越性能的機器,是上層人的聚集地,它向世界展示穩定與進步,是為了顯得可愛而被人看到的社會,簡而言之,它是皮城的“自我理想”;但從側面來看,它如同號稱永不沉沒的泰坦尼克號一般,早已面臨來自瘟疫的威脅而不得不面臨關停,“絕不能關閉海克斯飛門!”是上層人維持自我理想最後的歇斯底里,然而它本就建構在最基本的對抗性上——光鮮亮麗的皮城總需要那淫穢的、不可訴說的祖安來做支撐。

海克斯
以至於到最後,這場瘟疫以一種具像化——金克絲完整形象的形成,來進一步描述這種威脅:她無法談判並作為最基本的不可抗因素出場,從上層流落到底層的海克斯寶石,以作為導彈的替代物迴歸了,結尾同開頭一般佈滿紅色,伴隨著那由始至終的對抗性迴歸了。現在我們得以理解齊澤克—拉康意義下“社會不存在”的真正含義:社會—意識形態幻象的關鍵,是建構一個沒有被對抗性分工割裂的社會,在那裡,各部分之間的關係是有機、互補的。但一邊是這種完美互補的社會,一邊是被對抗性鬥爭割裂的現實社會,我們如何解釋他們的對立?答案當然是同辣脆對猶太人的指控相同:一個外在因素,一個外來之物,將腐化墮落帶入了健全的社會構架。這一戀物癖在雙城之戰中同樣出現:在祖安,底層人認為是上層人的問題;在皮城,上層人認為是祖安人的問題;在故事的結尾,我們把這種構成完美社會的不可能性賦予實證的活生生的生命——金克絲。

現在,我們能從拉康的視野發現Marx的“盲區”:在那本著名著作的第三卷中,Marx用這個公式表明Capitalism的邏輯—歷史侷限:“資本的侷限就是資本本身,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然而,Marx口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協調一致可能”永遠不會到來,因為恰恰是這一限制:生產關係的進化跟不上生產力的增長產生了剩餘,驅使著資本主義的永恆發展,從出生起,資本主義就腐爛了,並對平衡充滿了內心的渴望,而這正是資本主義永不停息地變革和發展的原因,同社會建構而起就伴隨的對抗性一般,這一剩餘實現了慾望的再生產,實現了快感的剩餘,就如同你吃到的美食總不如你想象般那麼好吃,這一剩餘構建了慾望,並實現它的再生產。
同雙城間的表象之表象(上層與下層對抗)告訴我們的一樣,社會總是圍繞著某個構成性的不可能性結構起來的,總是被某個核心“對抗”刺穿。而意識形態幻象的功能就是掩飾這種非一致性,然後用失敗的認同補償我們(猶太人、黑人、底層人、上層人、金克絲等等)。
本文首發於公眾號:符號社Antigone
#英雄聯盟#雙城之戰#精神分析#哲學#拉康#符號社antig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