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6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在美國駐日大使館會見了前來拜訪的昭和天皇裕仁。作為剛扔下兩顆原子彈的,戰勝國的意志呈現,與剛吃了兩顆原子彈的,戰敗國曾經的榮耀象徵之間的會晤,瀰漫著一種尷尬的氣息——因為在歷史上的這個時間點,沒有人知道在美國主導下的日本社會將會前往何處。
麥克阿瑟希望打破眼前的尷尬,為裕仁遞上了一根菸。裕仁的內心百感交集,欲哭無淚,他止不住顫抖的手猶豫再三,最後輕輕地接過來,卻不知該說什麼好。因為他不會抽菸*
抽菸*:這個場景根據以下來源撰寫,略有施展“想象空間”。
[日] 野口悠紀雄. (2018). 戰後日本經濟史:從喧囂到沉寂的70年. 後浪丨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ISBN: 9787513913843
看起來“日本戰敗”和“法國人的遊戲回憶”似乎毫無聯繫,事實上這屬於“蝴蝶翅膀的第一次扇動”:也許麥克阿瑟自己也沒有想到,他所引領的變革改變了30年後世界遊戲的格局——在其扶持下的技術官僚*成為了日本政壇與經濟領域的主宰,在這個基礎上以1960年代開始出現的微計算機和基於微機的應用作為契機,一大批代表著“霓虹印記”的日本企業誕生了——
技術官僚*:這批人首先原本就是官僚階層,但一般不來自於日本軍部,或是與戰爭直接相關的部門,這使得他們很難被捲入東京審判。

1960年索尼在加利福尼亞成立美國公司,成為第一家在美國發行預託憑證的日本企業。
1960年,以原夏威夷企業Service Game of JP為基礎合併而成的新公司開始用“Sega”(世嘉)為商標運營老虎機和點唱機。
1963年南夢宮在東京三越總店的屋頂安裝了第一個室內遊園,有木馬、撈金魚等投幣遊戲機,以及場地中央處的汽車遊戲Roadway Ride。1966年他們與華特迪士尼簽約,用於生產遊樂園中的角色。
1969年點唱機出租和修理商科樂美(KONAMI)成立,並於1973年轉為街機制造與服務企業。索尼、世嘉、科樂美、南夢宮,這些名字共同構成了我們所熟知的關於日本遊戲的記憶——沒錯,可能少了一個任天堂,老任在1977年才推出自己的第一臺家用機Color TV,但是成為了那個最終也是最大的贏家。以上面的這些名字作為開始,經過了數十年的發展演變,日本遊戲的影響力如今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是難以忽略的存在。這種存在感在1980-2000年代中伴隨著日本遊戲的崛起被無限放大,那些伴隨著日本遊戲第一次黃金年代(從FC、SFC到PS1)所長大的那批孩子們走進了遊戲或者遊戲相關的行業,有趣的事情開始呈現出來了,那就是——
為什麼法國人的遊戲記憶萬華鏡,滿滿的都是霓虹剪影?
在電子遊戲產品方面的“日本製造”給今天的歐美遊戲界都帶來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比如我們可以看到《馬里奧賽車8》這樣的遊戲在英國遊戲銷量榜上已經霸佔榜單數年之久。如果僅僅是談到玩家對於日式遊戲的追捧,可能英國或者德國在遊戲銷量方面都有更讓人信服的數據例證,但是對於遊戲開發者而言,可能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相較於法國更加喜愛日本遊戲:一個罕為人知的事實在於,“JRPG”這個詞是由法國學者Turcev在《Le JRPG, une Passion française》(JRPG,法國人的激情)一書中提出的。

在大阪產業大學國際學部所舉辦的學術論壇L’ héritage culturel à l’ heure de la globalisation(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遺產)中,提到了法國遊戲製作者熱衷於製作“J”RPG這樣一個有趣的事實——這並非是一直以來的現象,而是從2013年,以Shiro Games的《Evoland(進化之地)》作為開始。隨後,育碧的《 Child of Light(光之子)》(2014)、Kobojo éd的《Zodiac : Orcanon Odyssey(十二宮)》(2015)、Enigami的《Shiness:The Lightning Kingdom(亮晶晶 閃閃王國)》(2017)、The Game Atelier的《Monster Boy and the Wizard of Booze(惡魔男孩與嗜酒巫師)》(2018)和
Midgar Studio*:從Midgar(米德加,最終幻想7中的神羅城)這個工作室名就可以很直觀的發覺工作室對於《最終幻想》的喜愛。
可以看到在過去的十年中,法國遊戲製作者在樂此不疲的製作著“JRPG”,那麼這個時間點出現的原因存在著什麼巧合麼?以他們之中的先行者Shiro Games為例——Shiro Games由兩個出生於法國西南部城市波爾多的孩子Nicolas Cannasse(下圖右)和Sebastien Vidal(下圖左)聯合創辦。

儘管看起來Nicolas Cannasse要比他的創業夥伴年輕的多,但事實上他們都是70年代生人(大概是熱愛遊戲讓他看起來更年輕了)。他的童年時代最大的快樂就是風靡80-90年代的FC,隨後是SFC、GB和PS1,伴隨著日產遊戲機和日式遊戲長大的Nicolas Cannasse加入過Motion-Twin(後來出品了《死亡細胞》)和Haxe Foundation(軟件開發),擁有CS、CS Engineering和IT management三個碩士學位和十年遊戲與軟件開發經驗的Nicolas Cannasse想要重現一個有關“童年遊戲經歷”的遊戲,《進化之地》系列也應運而生。這個念頭讓他和Sebastien Vidal一拍即合,於是他們秉承著對遊戲的熱愛建立了Shiro Games——喜歡RTS遊戲的朋友們對這個名字不會感到陌生。

在2018年,他們推出了備受好評的維京風格RTS遊戲《北境之地》(northgard),這個遊戲在國內得到了熱烈的追捧——在2019年,6%的玩家來自於中國地區,到了2020年,這個數字上漲到了11%。在上個月,Shiro Games又推出了沙丘系列IP的正統遊戲《沙丘:香料戰爭》,也有著不錯的口碑與遊戲質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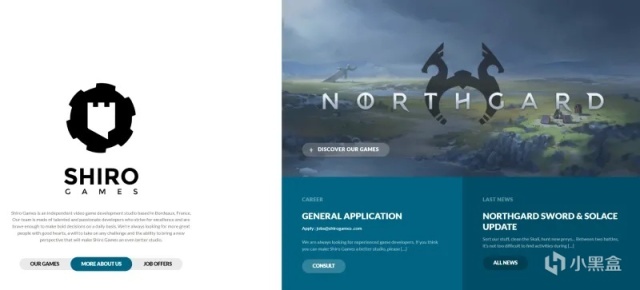
Shiro Games並不是聖莫尼卡、CDPR或者頑皮狗這樣的業界巨擘,但實打實的,屬於電子遊戲業界的“中生代”,這一家位於法國波爾多的獨立遊戲工作室憑藉著《進化之地》系列一鳴驚人,隨後一步一個腳印奠定了如今的地位,和出品了《黑帝斯》的supergiant games、出品了《饑荒》的Klei一樣,都是有著廣泛受眾群體與良好口碑的寶藏遊戲工作室。
Shiro Games的宗旨是帶給玩家們那些讓他們也會感受到快樂的遊戲——在《進化之地》一鳴驚人以後,他們推出了更為成熟,玩法也更為豐富的《進化之地2》:製作組成員們以自己的童年遊戲記憶為基礎,以對《超級馬里奧》、《薩爾達傳說》、《最終幻想》等經典遊戲的致敬為內容,構建了一部堪稱遊戲發展史的,“講述遊戲故事”的獨立遊戲——這樣一種致敬童年遊戲回憶的作品魅力經久不衰,不僅在steam大受歡迎,甚至在近期被引進了國服移動端版本。

“記錄時光”常常會有一種別樣的美感,比如吉姆賈木許、斯派克李、陳凱歌等眾多導演合作的《十分鐘年華老去》,我們如果通俗一點,它的表現形式也可以是B站的“十分鐘帶你看完魔戒三部曲”,那麼對於《進化之地2》而言,它的雅俗程度或許在兩者之間——劇情方面構建了一個《勇者鬥惡龍》風格的,恢弘壯闊的冒險故事,但作為主體故事的JRPG只是串起遊戲內容的“引線”,在遊戲所包含的冒險內容則是一個個“萬華鏡”(玩過《美少女萬華鏡》的朋友懂的都懂)——

無數neta趣味大概是隻有經歷過FC&SFC&GB那個遊戲年代的玩家們才會擁有的共鳴,比如上圖的8位機畫面風格的“樂科美莊園”的戲謔調侃——在遊戲所包含的4個時空中,我們可以領略到FC時代的《雙截龍》、《炸彈人》;SFC時代的《超級馬里奧》、《街頭霸王》;GB時代的《銀河戰士》與《惡魔城》;PS時代的《聖劍傳說》、《最終幻想》等等,每個時空很精巧地對應了遊戲世界的不同時期:FC時空是人魔戰爭時,SFC時空是人魔戰爭之後,PS時空則是人魔戰爭之後商人掌權的時代,而GB時空是馬基傳說時代。

以《進化之地2》作為例子,我們隨處可見它的“JRPG血統”——《薩爾達傳說》風格的紅心表示的生命狀態與主角的攻擊方式、《勇者鬥惡龍》式2D背景+3D角色的經典JRPG呈現形式、而從《最終幻想6》的偽3D俯視視角到《最終幻想7》的3D大地圖也正好呈現了JRPG這數十年間所走過的“進化之路”。以Sebastien Vidal和他的Shiro Games為代表,JRPG和FC/SFC所留下美好回憶的童年大概是他們長大以後在遊戲中重現這樣一種美好回憶的原因,唯一可能讓人困惑的點大概在於——為什麼一群法國遊戲愛好者的童年是被日本遊戲所“佔領”*的,以及,日本遊戲能夠“走出來”的原因是什麼?
佔領*:雖然面對德軍的坦克只需要一週就行法式軍禮,但面對日式遊戲的魅力法國人也沒能抵抗更久(今日乳法1/1)
——上述也許只是玩笑話,但日本與法國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來源不明的“文化親近感”。
Mukokusaki的日本遊戲,學進來與走出去
如同前文所提到過的,在麥克阿瑟主導下的日本經濟與文化變革很明顯的產生了外來文化“入侵”的痕跡,但作為“副產品”之一的日本遊戲可以最終走出去並且風靡全球,可能很大程度的原因在於其本身對於外界文化的包容性:

國民RPG《勇者鬥惡龍》中的惡龍源自一個典型的西式奇幻形象——“龍與地下城”中的惡龍(作為對比,同樣是鳥山明老師作畫的《七龍珠》則使用了東方的龍),《超級馬里奧》或者《薩爾達傳說》中所使用的“拯救公主”這樣的故事邏輯更多的源自於類似於《格林童話》這樣的歐美故事風格,其中的公主形象更多的偏向於歐美風格里,生活在歐式城堡中,以長裙、王冠和一頭金髮為特色的公主,而非日本傳統的以和服妝容為特色的“Hime”形象(比如《竹取物語》中的輝夜姬)。

在2000年以後,以輕小說和網絡化為代表的“二次元”文化成為日本如今主流之前,日本的遊戲和動漫作品中,其實有著非常廣泛的“外化”傾向,比如取材於西遊記的《最遊記》、取材於埃及文化的《天是紅河岸》、取材於印度神話的《天空戰記》等。我們如果拿出《北斗神拳》、《城市獵人》這樣的作品與同期的美漫作為對比,會發現兩者在藝術風格與表現形式上會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雖然在情感內容的呈現上還是保留著明顯的東方特色。
所以很大程度上,日本文化乃至於遊戲對於外來文化元素除了被動的吸收以外,可能還包含著更多“主動出擊”的意味,而正是這樣主動將“舶來品”融入自身血液的遊戲也在世界範圍內獲得了更大的成功——比如歐美化人物造型、“洗剪吹”風格的《最終幻想》是所有JRPG中在日本以外銷量最好的遊戲系列。

一半是日本,一半是美國,對於外來文化的吸收與再呈現讓日本遊戲呈現了一種“Mukokusaki(無國籍)”的特色,這樣的特色讓其在世界範圍內容易獲得更多的認同感——而以“繪畫崇拜”為特色的法國*與“漫畫崇拜”為特色的日本也許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一些“基因層面”的共鳴感,從而讓類似於Shiro games這樣的遊戲製作者們會以日本遊戲作為自己在遊戲領域的啟蒙與對於遊戲美學的追求。
*關於法國本地人特別偏愛JRPG這一點也是學術界所有興趣的議題之一,除了《進化之地》系列另一個相對典型的例子是幾乎原配方模仿《最終幻想》的《永恆邊緣》。
能夠成功“走出去”的原因之一,但日本遊戲成功走出去的原因不止於此,讓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在於在文化的融合中,它更多了形成了一種“工業化”的制式設計——
JRPG,更多的是一種“漫畫+計算機”的工業制式
如同目前供不應求的PS5在日本本土的銷量榜上只能一再成為NS與相關遊戲的陪襯一般,想要制霸市場,最為重要的是產量:而在日本遊戲的上一個黃金年代(1980-2000),日本遊戲廠商平均只需要4個月即可產出一部遊戲作品,這樣的生產速度顯然讓歐美工作室難以匹配。

讓JRPG乃至於日本遊戲的“產業化”從源頭上進行追溯,可能是一次“浪漫的意外”,因為其根源上來自於在產業變化過程中,出版業對於遊戲業的一種“媒體融合”,遊戲成為了整個文娛產業的主導和驅動力而非是衍生品——漫畫等傳統文化消費內容開始作為電子遊戲的衍生品(說人話就是二創)存在,而非是相反,這樣就導致了一種敘事消費領域的變革。
*不同於強調將媒體對象連接在一起的結構網絡,敘事消費——顧名思義,側重於故事在推動離散媒體消費方面的作用。推動這種消費的是角色與世界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宏大的敘事(或世界觀)構建了細碎的敘事片段組合在一起的過程。

角川集團旗下的《Comptiq》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範例來幫助我們理解這樣的變革,11月號上他們開始推出Romancia的月度專題,這是一款來自Falcom(法老控)的動作類RPG《屠龍者》系列第三部作品。宮本茂從中汲取了靈感開發了初代《薩爾達傳說》(Kalata, 2017)。1987年6月法老控的《伊蘇》系列發售,於是1988年5月Comptiq又開始連載伊蘇漫畫,作者是後來的日本著名評論家大冢英志。
用技術力重現童年快樂,大概是屬於現代極客的獨有浪漫
出版業(漫畫)與遊戲業(計算機)的融合,讓日本遊戲JRPG從產能到內容質量上都在一個時間段內擁有了出類拔萃的競爭力——直到過去的十年,隨著移動互聯網與芯片技術的突飛猛進,他們的圖形化技術力長期停滯和大幅度落後於歐美廠商。但在此之前,由《馬里奧》、《塞爾達》和《最終幻想》這些閃亮的名字所構成的日本遊戲黃金時代已經構成了屬於一代歐美玩家的童年遊戲繪卷,並且催生出了Shiro Games的《進化之地2》這樣的佳作作為果實。

在今天這種餘波還在繼續,包括了德國死宅Radical Fish Games開發的《遠星物語》、Sucker Punch所開發的《對馬島》之魂、3D Realms所開發的《影子武士》、Mimimi Productions所開發的《影子戰術:將軍之刃》等等,這種用技術力重現童年快樂,大概是屬於現代極客的獨有浪漫。

而也許以日產的《聖鬥士星矢》和美產的《變形金剛》作為童年的我們,在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間也可以把這些舶來品的文化印象融合進我們原有的文化,以一種適合於自身的產業制式將更多更大量的遊戲作品推廣到神州與神州之外——比如《戴森球計劃》、《煙火》、《籠中窺夢》這些可能已經散播著屬於自己的光芒。

如果類似於Shiro Games的《進化之地2》,在已經成長起來的我們這一代人,可以把腦海內關於遊戲的那些美好回憶以能夠打動自己的遊戲呈現給世界的話,那麼在未來產出於海外的“進化之地3”中,也許我們可以看到屬於自己的遊戲所照亮的那一方星空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