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碎骨者·玛格·乌鲁克·斯拉卡的诞生
因为这场暴风雪,让人目力所及之处全部都是白色,可见度很低。但在距离数英里之外,那有绿色。只是一点绿色,令人不禁在意:一只手。仍然柔软,热气自它长大的洞穴中被抓破的液囊里冒出。那只手不停挣扎。它四处摸索,想抓住点什么东西把自己其余的部分拉上来,但这风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使得地面也坚硬如铁。

兽人都是从蘑菇(真菌)下面长出来的
不过,这只手很幸运。一头饥饿的苔原史古革,在雪雨的间隙中瞥见它,于是笨拙地跑了过去。这大错特错。因为在它还没来得及咬穿手腕之前,那只手就缠住了它的舌根,像一把被启动的链锯砍刀一样猛地抽回,将那头史古革的内脏从其嘴里拽了出来。

史古革又称“跳跳”,是兽人种族的一种伴生野兽,形态多样
现在你瞅瞅,史古革的内脏,美妙又温热。充满汁水。将那只手周围的土地软化,刚好使其变得略微松弛,而后咕噜声伴随着地面隆起,一只兽人于鲜血、胆汁以及真菌之中诞生了。
那并非碎骨者。还不是。不是任何人。但这一小块绿色有可能成为某个大人物——也许成为任何人——如果它能撑过接下来几个小时的话。很多人都熬不过那几个小时,但这家伙做到了。事实上,尽管那风暴从未停歇,但它还是撑着过了好几天。在雪地里艰难地长途跋涉,裹上史古革毛茸茸的兽皮用以保暖,并吃掉其血肉保持身体强壮,直到它出现在戈杜夫的大门口,随着砰地一声放它进去。
戈杜夫是一处高夫氏族要塞。算不上什么好地方,真的——只有一排简陋营房,一个史古革圈,一座酿酒小屋以及一个发电机已经坏掉的技师工坊,全都挤在荒废的城墙内侧。这可不是一个你能无缘无故就走过去的地方,因为高夫们不太喜欢访客。但这个新来者却径直走去,没别的理由,只因它想要如此,跨过一堆堆被子弹打得粉碎的骨头,直到抵达大门口。
戈杜夫的酋长那天就在门楼塔里,因为什么事而在教训守卫们,所以它是第一个看到那新来者的。它显然有些胆量,那酋长估计着,因为它背上的毛皮曾属于一个大家伙,所以它之前肯定也经历了一场恶战。事实上,正是这张毛皮救了新来者一命。当时其中的一名守卫跳上塔楼射击口想放倒它,也期望着借此摆脱身边的酋长,这只为它赢得了另一记耳光。因为酋长觊觎那张漂亮的黑色史古革毛皮,你看,它可不想上面被弄得全是枪眼。故而它就下到大门口直接去取。

高夫兽人,氏族涂装通常为黑色
门一打开,那个新来者便走了进去,却迎头撞上了酋长。当然,酋长对此只是笑了笑,然后将这个年轻兽人一顿臭揍,随后将毛皮拿走并扭头准备回到要塞里。但当大门开始关上时,它却变得心软,并大声喊让戈杜夫的兽医把那个失去知觉的新来者拖进来喂饱。鬼知道因为什么。也许进门的那一撞让它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使其徒然神往吧。高夫们偶尔也会像那样多愁善感。也可能这是诸神的旨意。没准那记头撞就是诸神的旨意。
这个新来者很快便痊愈了,并且让自己在营地里变得足够有用,它成为了一名士兵。这仅意味着一顶锡制头盔,一柄生锈的砍刀,以及每天一块相当于它脑袋重量的肉。但已经足够了。它加入了戈杜夫的一伙暴徒,一次又一次地袭击其他部族的堡垒,这让它们日渐壮大。有次它们在一座古巨圾残骸上与一群恶月进行战斗时,它甚至从一个死掉的敌人那给自己搞到把冲锋枪,并且也学会了怎样使用。

古巨圾,兽人的巨型战争机器,相当于人类的泰坦
虽然在戈杜夫这样的地方找不到多少知识,但新来者还是学到了一些。它知道了作为一个兽人意味着什么,还知道了关于诸神的事情。在战斗棚屋里,它遇见了搞哥。而在酿酒小屋的掷骰桌上,在一圈又一圈咯咯作响的鼻涕精指关节间,它遇见了毛哥。

搞毛二哥,兽人的神祇 - 搞哥既粗暴又狡猾,毛哥既狡猾又粗暴
不过,这个新来者所接受的教育并不全是宗教方面的。它还知道了一种叫做银河的东西,在那里有成千上万其他的世界可以战斗,而这颗星球——尤克,士兵们这样称呼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大多数兽人至此已经满足。但新来者一直追问酋长关于尤克以及银河之类的事情。通常它会因为自己这种怪异的行为而得到一记耳光。但有天晚上,当时所有暴徒都挤在酿酒小屋里,狂饮从一支邪日车队那偷来的烈酒,那个老高夫——它肯定心情不错——决定回答这个新来者的问题。
尤克,那个高夫说,就是一坨臭狗屎。它的正中部分烧成了灰烬,其他地方都冻得硬邦邦,除了以前战斗留下的破烂,几乎没什么可以争夺。但这是属于它们的一坨臭狗屎,所以是个好地方。
银河里还有其他家伙,酋长解释道,他们有时会试图拥有属于兽人(也就是所有的兽人)的地盘,而尤克多年来已经被入侵过许多次了。很久以前,有一次是被长着尖耳朵、戴着愚蠢帽子的瘦皮猴,后来是一些用水晶或者什么玩意做成的巨大蜥蜴,诸如此类。
酋长现在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这个故事里,酿酒小屋里一半的兽人也都停止了摔跤和械斗,专心听着。所有这些帝国都已经消失了,酋长对那个新来者说,被兽人赶走了。注意,并不都是在第一次尝试中。但每次它们被干掉,酋长解释道,从它耳朵后面拔下一簇真菌来进行强调,兽人都会回来。它们从地洞里长出来,就像新来者之前那样,直到有足够的人把活儿干好为止。当一批闯入者被赶走后,他们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不过,人类除外。由于在银河中所有的生物都曾冒犯过搞哥与毛哥,而人类是最频繁的。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相信某件事,那它就一定是真的,就像兽人所做的那样。尽管那实际上对人类不起作用。所以即便已经两次被兽人从尤克踢了出去,他们仍然坚持着那个疯狂的想法,认为这颗星球是属于他们的。
随后酋长安静了下来,透过酿酒小屋的窗户望向外面的群山。新来者也顺着它的目光看去,发现在山脉顶端的峭壁上有一簇微小的冷光,就像垃圾星一样。
“那是座人类的要塞,”酋长说道,随之狠狠地喝干了它的酒杯,然后踢开了一个屁精并将杯子摔在桌上。“鸟嘴头。装备大号盔甲的杂碎们,挤在罐头里。他们留它在这监视俺们,就在俺们眼皮底下,不知咋的俺们到现在都还没把它烧掉。你怎么看,小家伙?是俺们变软弱了还是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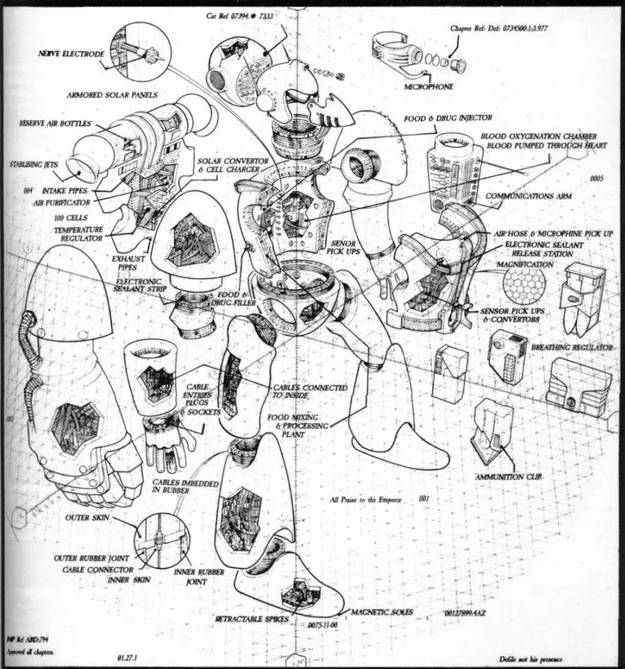
“鸟嘴头”是星际战士MK6 鸦式动力甲的标志性特征
新来者考虑了一下它的选项。它很想侮辱酋长,因为这意味着将有一场好架可打。但它又看了看远处那些灯光,意识到那些可能意味着最好的战斗。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但有关那些东西的事情让它感到脑袋刺痛。所以它便遵从了毛哥,只是稍微侮辱了一下酋长。
“没,”它说道。“没变软弱。虽然老了。打过很多好架,脑袋也挨过不少下。你会忘事。不过没关系。俺们为啥不在日出的时候去把它给碾碎呢?”
当酋长努力想弄清自己到底有多生气时,它的脸皱了起来。但转瞬这个主意便打动了它,使它的皱眉顿时变成了唾沫四溅的狂笑。
“听好了,”它对着拥挤不堪的小屋内咆哮道,四周的家伙们飞快地爬起来,差点把脑袋撞到小屋的椽子上。“诸神给了俺一个好主意,”它半撒谎地说,同时用一只爪子敲了敲它那布满伤痕的脑壳,随后朝着夜色指去。“看到在拉克布鲁德峰上的那个鸟嘴头要塞了没?俺受够了。太阳一出来,俺们就开干。全面进攻。穿重装的到前面去,还有……”它想了一会,“所有人都到前面去。”
“但首先,”它说完,在其战斗铁颚生锈的钢牙后面露出一副狡黠的笑容,“俺们要把这座小屋喝干。酒在用光之前随便饮,所以快去吧——如果明天有谁还没喝到头疼,那俺就亲自给它来一下。”

铁下巴,常见于兽人老大或酋长穿戴
恰巧,这将是那个新来者的最后一战。
起初,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是场徒劳。当全副武装的戈杜夫暴徒们涌入狭窄的山口大门时,除了它们自己所持砍刀拍打在人造金属上发出的撞击声外,没有任何响动,随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失望的吼声。那些人类并没有留下任何同胞跟它们战斗。但虽然这座要塞——或者你们称之为监控前哨站——里面也许没有真正的人类,可它并非毫无防御能力。
当一些家伙试图撬开大门上的装甲以掠夺里面的破烂时,一排低矮的小型炮塔从墙上冒了出来,发出一阵恼人的轻柔嗡鸣。随后它们找到了目标,跟着响起很大,很大声的噪音。
这是那种最糟糕的战斗,死伤惨重,没有哪种暴力比得上灭除机器那般确凿无疑。戈杜夫的兽人们赢了,但战利品并不足以弥补它们的损失。上山的有八个很多很多兽人,当最后一个炮塔被从底座上拧下来时,它们中只有很多很多外加四个还站着。
那名新来者并不在它们之中。
它没死,但它也没走路回家。而既然高夫们不搞搬运,那就意味着它被留在了那里等死。这很公平。当最后一批幸存者们一瘸一拐地离开时,那名新来者甚至听不到它们靴子踩在石板上的声音。因为它一开始就只剩一只耳朵了。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大脑中负责处理噪音的部分在距离三颗长牙那么远之外,与它的半个头盖骨一起飞溅在了岩石上面。它用一只摇摇晃晃、几近麻木的手抓挠着脸上剩下的东西;它看不见的那只眼睛与其周围的脸部不见了,只留下一个凹凸不平的深坑。当它的一条腿开始像只脊背上被插了把砍刀的跳跳一样抽搐时,它才决定停止探究那个坑到底有多深。
它弄不清自己身处何处。它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这来的。它只能看到天空,却不知道那是什么。即使它能看到别的东西,也不会知道都是些什么。新来者还没起过名字,所以至少它不会失去这个。但除此之外,它在这段短暂生命中所学到的一切都被那颗爆弹撕成了碎片。
所有的一切,但除了有关诸神的知识。
不知为什么,除了那颗子弹所撕碎的,其余部分的肉都以搞哥跟毛哥的名义牢牢粘在骨头上。那一小块大脑似乎仍在脉动,尽管向其输送的血液此时正通过新来者脑袋后面的洞滴进泥土里。因此新来者想到了诸神,并需求它们的介入,让其从这一团糟中摆脱出来。没有回答传来,它愤怒地咆哮,但从它嘴里发出的只有微弱的嘶嘶声。
搞哥和毛哥不保持沉默只因它们被冒犯了,对吧?你可以对诸神发号施令,只要记住它们不必听你的。不。它们很安静,因为有时候诸神在保持沉默时才最有发言权。它们告诉新来者,这个困境需要它自己来解决,而如果能够做得到,那么它也许值得被倾听。
这似乎很公平。故而那个锤死的兽人做了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它站起身来,把脑子塞了回去,然后出发去寻找一个能修好它脑袋的家伙。
审讯二
当咬仔讲述这个无名兽人受伤的后续时,法尔克斯发现她的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了那名囚犯自己所说的话语上。尽管她无法听懂,但它说话语气里的热情很吸引人——它津津有味地述说着,舌头舔舐着尖牙,仿佛正在回忆一顿丰盛的晚餐,而非一场灾难性的头部损伤。虽然它自己承认,屁精只是单纯地喜欢看到别人受伤,但法尔克斯觉得事情远不止如此。似乎这伤口在年轻碎骨者的故事里是一次重大的际遇,而并非一场严重的挫折。
不知不觉中,法尔克斯的手伸向了自己脖子的后面,她的手指找到了那个位置,就在颅骨底部的上方一点,头发茬在那里围绕着一片两英寸的椭圆陶瓷抛光体被分到两侧。那是一只科拉克斯水母的杰作,而非子弹,这种生物会在切除头骨后让大脑保持完整,作为其幼虫发育过程中的食物。幸运的是,亨德里克森兄弟在其产下太多卵之前就把那东西从她身上切了下来,而用镜子和解剖刀度过令人不快的个把小时,就足以把损伤的部分清理干净。这伤口真的算不上什么。但即便如此,法尔克斯对颅骨创伤也有足够的了解,知道为此庆祝是件奇怪的事情。

并未查到科拉克斯水母的相关资料,推测是某种外星野生动物
接着,当那囚犯继续叽叽喳喳地讲述时,她注意到那屁精正在抚摸自己所戴的那条脏兮兮的项链,以一种仪式般近乎温柔的细致依次摩挲着每一块金属。而其中的一块,经过多年的摩擦使其变得几近光滑,她发现那东西的边缘看起来像有一把风格化的带翼长剑。

翼剑是黑暗天使战团的徽记
“就是那枚弹壳撕裂了碎骨者的脑袋,对吗?”她问道,同时一边用下巴示意着那件肮脏的饰品,一边把手从后脑勺收了回来。“这些是它的碎片。”咬仔打断囚犯的回忆并转述了这个问题,而那屁精则对这名翻译投去了恼怒又沮丧的一瞥,随后撅起嘴简短的咕哝了几句。
“完全……相反,玛卡伊坚持认为,”咬仔说道,显然省略了一些更为多彩的评论。“它说是这枚弹壳造就了碎骨者。”
“核实,”卡西娅耸了耸肩说。“那条项链具有相当的灵气,自从它登舰后就一直困扰着我。闻起来是绿色的,我猜,这就是原因。我推测这是货真价实的玛卡伊。”
亨德里克森大呼了一口气,从自己一直半坐着的板条箱上站起身,恢复了他习惯性的踱步。
“别忘了,年轻的大石块,我和你一样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串项链的奇异扭曲——尽管我还是一如既往地鄙视你将其称之为气味。不过是的,那必定是用击穿碎骨者的那枚弹壳做的——相信莱昂之子们制造的弹药不幸将大头兵变成了征服者。”他听完自己的笑话高兴地哼了一声,但仍然眉头紧锁。“即便如此也证明不了什么。这个小矮子可能是任何一个渣滓,被投机的劫匪抓住,瞎编了一个荒诞故事,然后给了这个……饰品以证明它们要价的合理。”
“我不清楚,奥姆,”卡西娅向后靠在门框上说道,并将自己那树根般粗壮的双臂交叉在胸前,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这可不是你所谓的普通屁精。而且如果刚才的故事是血斧编造的,那在我听来也太有说服力了。”
“鲁斯的毛手指啊,姑娘,你的脑袋够大了,用它想想看。你没觉得这个故事里少了点什么吗?那种又小又绿,闻起来像卡尼克斯的尿一样臭的东西。”

卡尼克斯无设定图,是原产于芬里斯的哺乳动物,犄角因能做成酒杯或盔甲装饰而备受追捧
“奥姆抓住了一个重点,”法尔克斯趁这对冤家还没陷入争吵前插话道。“这个生物以令人惊讶的细节描述了斯拉卡的生活,但它对自己在故事中的存在却只字未提。”
那个屁精又咕哝了几句,仍因它在描述一场重伤时被打断而闷闷不乐,随后咬仔说了起来。
“因为当时它并未存在,”它含糊地说道。
“那么,这只是道听途说,”亨德里克森讥讽道。“陈腐的传闻,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绿皮那听到,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版本。”
“哦不,”那个兽人以不可思议的微妙语气争辩道。“这是真的。这就是碎骨者所经历的。”
“因为碎骨者是这么说的,对吗?”卡西娅问道,就连她的轻信也渐渐消失了。
“因为玛卡伊看到了这一切,”咬仔用一种可能它认为比较神秘的语调纠正道。
“但它刚才说……”法尔克斯刚张口,卡西娅跟亨德里克森也同时对这一前后矛盾提出了抗议。
“这很……复杂,”咬仔坚持道,同时将它的手背朝上抬起安抚他们,这又是一次它对人类肢体语言的走样尝试。“但如果你们能耐心点,俺会解释的。”
亨德里克森双唇紧闭以抑制自己的爆发,并望向法尔克斯寻求引导。尽管他脾气暴躁,但偶尔还是能想起来到底谁才是管事的人。
“被一个人类已知最典型的鲁莽物种敦促保持耐心,”她半自言自语地说道,同时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靴子想找回点平静。这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新开始。“很好,兽人。毕竟我们不缺时间。但你对作出解释的承诺已被记下。不要对我的仁慈考验太久。”
她一点头,那名囚犯开始继续讲述。但没过多久故事就又被打断了。这屁精声称那个兽人独自穿越两百英里的贫瘠荒野,抵达了一个有人烟的地方叫做锈钉。显然,它不仅一路上都把残破的颅骨严实密封,而中途还停下来与至少三头凶猛野兽搏斗。这对亨德里克森兄弟来说过于无法忍受了。
“兽人们凑在一起很强,”他说道,并用手指戳自己的手掌以示强调,“我会如此评价它们。但我对于在野外驱除野兽这种事上还是略知一二的,自从我取得野狼之魂的那个冬天起……”
法尔克斯,当然,她也知道所有关于与荒原野兽战斗的事,这归功于亨德里克森经常找借口讲述他参加选拔仪式的故事。此时卡西娅看了看法尔克斯并向她脑海里投去一个模糊的画面——一堵已经划损过数百次的墙又被划上了一个憔悴的计数标志——这让她很难不笑出声来。果不其然,亨德里克森接着通过一系列动物谋杀来自吹自擂,每次讲到致命一击都用夸张的动作加以演示,而咬仔那双空洞的红眼睛则一直在旁边注视着。
“没有这样的壮举,”他最后耸了耸肩膀总结道,“能被一个只有半拉脑袋的生物拿来吹嘘。”
当亨德里克森的观点被简短地传达给那名囚犯时,它咧嘴一笑,并在回答时身体前倾,嘲弄般地盯着这位星际战士。
“除非你是那个将成为碎骨者·玛格·乌鲁克·斯拉卡的兽人,”咬仔翻译道,接着看起来有些躲闪,好像不确定是否要翻译那囚犯剩余的发言。“玛卡伊还提到了……哼嗯……太空野狼的耐力,俺……没完全听清。”
尽管咬仔试图从中调剂,愤怒还是令亨德里克森浑身僵住,他的眼睛变得苍白而冷酷,就像透过冰看到的一样。但卡西娅趁他的怒火进一步具象化之前开口说道。
“我听到过另一个故事。那是在卡赫米斯上的战壕里巡逻时,虽然我不知道是从哪传出来的。那个版本说碎骨者在被射中后,它被自己部落的暴徒拖走了。它们听闻有个糟糕的兽人医生会为重伤病患支付好价,所以它们开车载其穿越荒野,用几把子弹的价钱将它给卖了。这于我听来更可信一些。”
“这是真的吗?”法尔克斯厌倦地问咬仔,那兽人与囚犯商量时举起了一只爪子。
“是的,”它简明扼要地说。
“那玛卡伊说谎了?”
“没有,”咬仔说道。
“别再猜谜语了!”亨德里克森咆哮道,他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究竟第一种说法是真相,还是第二种说法?”
那屁精做了一个手势,令咬仔对它怒目而视,随后那个兽人的话语似乎有些怯退。
“是的?”它回答道,而法尔克斯则深吸了一口气。
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情况才得以缓解,而尽管如此,也只是解决争论带给每个人头痛的权宜之计,而非真正的彻底解决。就我们所能理解的而言,兽人种族的头脑似乎能够同时相信不止一个客观真相。的确,它们可以在有意识的思考中同时掌握几个完全相矛盾的事实,而丝毫不会感到精神不适。
最终,带着一丝讽刺意味,他们同意保留不同意见。不过,在那个囚犯继续它的叙述之前,这位死亡守望老兵又找到了一根骨头可挑。
“碎骨者是一个他,”他对咬仔摇着一根手指抱怨道,并得到了几声不确定的咕哝作为回应。“你一直在说它,”亨德里克森阐明道,“但碎骨者是一个他。”
“但……它……他不是一个人?”咬仔说道,它的眉脊因困惑而皱了起来。在另一场潜在的混乱辩论接踵而至前,法尔克斯插话了。
“我们谈过的,奥姆。兽人没有……生殖结构,所以他们对男女和雌雄没有概念。”
“一些俺们已经理解的性别差异,”咬仔打断道,一如既往地热衷于展示它对人类方面的特殊专长。“俺发现这一切……相当有趣。”
“安静,兽人,”法尔克斯厉声道,迫不及待地想让话题回到正轨。“从现在开始,碎骨者就是一个他,不管这是否有意义。”
“如你所愿,”那名翻译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自己大衣袖上生锈的扣子说道,然后转过身用它们的语言对屁精说话。“哒破-屁晶-嗦话。升气-布解。大-大-波士的家伙,睡古折重阻……‘小子’。”
听了这些话,那屁精爆发出一阵狂乱的尖声抽泣,倘若法尔克斯不知道那是笑声的话,她可能会认为是某种精神崩溃的征兆,而这也引起了咬仔的一阵嗤笑。但在看了看法尔克斯的脸后,那名翻译知道自己已将它的好运推到了一边,于是用一种大家都能理解的方式催促这个小家伙继续说下去:对着太阳穴的猛力一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