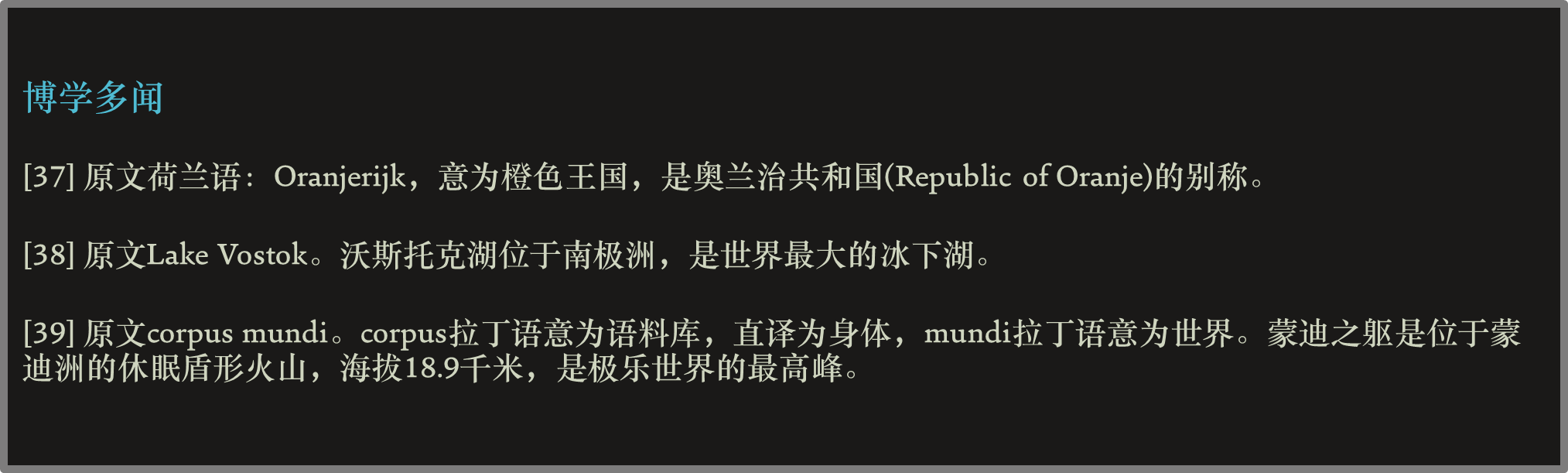12毫米膠片正在放映機中播放。汗和馬切耶克坐在沙發上,詫異地看著方形咖啡碟上的方形咖啡杯。他取了一把勺子攪拌糖,小心翼翼地靠近咖啡杯。叫做“影院”的咖啡館全部由玻璃和白色打造。傑斯帕坐在白色椅子上調試放映機,周圍是玻璃隔音牆。白色畫布落在玻璃的銘牌上,汗和馬切耶克坐的沙發也是白色的。在咖啡館中央的玻璃展櫃裡,有一隻白化老虎的雕像。請小心不要損壞任何東西,賠償的價格會讓你欲哭無淚。
“讓我猜猜。”探員用手指擰轉著他的“阿斯特拉”,使它軟硬程度剛剛好。“你設計的?”
“我一個學生的作品。這地方就像一個電影屏幕,一個空白的幕布,我們現在被*投影*在這裡,你明白嗎?怎麼樣?不是很舒服,一個屏幕,你懂嗎?”
“是有點不舒服。”
“呃,他有點著急了,是的,但那個男孩很有天賦。他需要一個高可視度的項目,這裡也是唯一可以讓他快速躲到投影儀後方的地方。讓我們思維開放些,你懂的。”傑斯帕和老虎看著汗。老虎的玻璃眼睛比室內設計師的更明亮。
“嘿,兄弟,我是這樣的!”
馬切耶克從夾克口袋裡掏出一支鉛筆和一個筆記本。
“那麼,”傑斯帕開始陳述,“我一個同事的親戚是剪輯師,他負責處理資料素材。去年秋天,他給我講了他的新片子。關於蓋斯勒的。你們知道康拉德·蓋斯勒[29]嗎?”
“他基本都在拍犯罪那些事,不是嗎?”
“不僅是那樣。戈斯塔,我那個剪輯師的名字,告訴我他對即將要做的事感到多麼害怕,並問我是否應該接手。他現在有個孩子,之類的。關鍵在於,影片是關於——我聽完就有了興趣——維德孔·赫德的。”
“我的天啊!”
“我不想聽維德孔·赫德!”
“等等,等等!我也是,那事已經蓋棺定論了。他當時在阿爾達,不可能在瓦薩之類的地方。但我還是決定留意他,明白嗎?然後,兩週前,戈斯塔來找我談話。他們在突破的邊緣了。維德孔·赫德和他們一起呆在喀琅施塔得[30]將近六個多月了…”
“不會吧!”
“…而且他們那兒有個策略:去打動赫德。蓋斯勒喜歡赫德,他是北陸人,像雪一樣潔白,博覽群書,還是談判專家。因此,赫德也想要打動採訪者,於是開始聊天,吹噓。蓋斯勒給出的印象是,那裡已經有一大幫有著狂野創造力的強姦犯了,而究竟有什麼是赫德干不出來的?”
“啊噢…”
“前三個月,維德孔只是進行暗示,激發好奇心,隱去可疑的日期,聊去沙灘的事。蓋斯勒沒有在意,只是與維德孔談論哲學,解決善惡之爭,我都寫在這裡了。”傑斯帕輕拍立方體玻璃桌上的文件夾。“直到有一天,赫德滿足了。”
男人輕輕按下開關,放映機中心的一個小燈泡亮了。“現在我必須警告你,”他看向汗,“我們之中主業不涉及臭水溝和失蹤兒童的人,最好把維德孔所說的一些話爛在心裡。”
特雷斯把他滿滿當當的第六勺糖倒進黑咖啡中,愣了一下。在一陣明顯的停頓後,他把針尖一樣鋒利的鉛筆放進削筆器中,假裝自己很忙碌,一絲笑意浮現在臉上。
“兄弟,什麼時候你才能明白?臭水溝和失蹤的孩子——那也是你的項目。”
“好吧,汗,”傑斯帕嘆了口氣,“臭水溝和失蹤的孩子。也是我的項目。”
“敬臭水溝和失蹤的孩子?”特雷斯突然興高采烈地把盛滿糖的咖啡杯舉在空中等待著。
“Skål[31]!”汗大喊道。
“Skål。”傑斯帕說,從玻璃杯中舀出一片檸檬。他嚼了一口,眉頭因為酸味若有所思地緊鎖。
“磁帶,傑斯帕?”
“噢…”
一個超級人類,強姦犯,兒童猥褻者,以及前NFD法西斯黨“赫姆達爾[32]”的成員,維德孔·赫德出現在白色屏幕上。他的一隻手拷在椅子上,另一隻手頗為紳士地扶在臉頰上。未來主義的哲學家留意到相機的存在。意識到這一點,他把他北陸牛頭犬般的下巴抬起到特定的角度;他從眼窩裡上下打量著。他的頭髮以三十歲的方式精心梳到一邊,一條腿搭在膝蓋上。你可以說維德孔是個虛榮的男人。他拒絕穿著條紋監獄連體衣載入史冊,此時身著黑色短袖制服,與康拉德·蓋斯勒講話。這只是他經歷的無數情境之一。
“有的人死後會重生。”他用古阿爾達方言故弄玄虛道。古樸的措辭為他當代的微妙情感注入了大量的田園風情。牆上的六位數時鐘顯示,8月12日第三個小時的採訪正在進行中。
“你知道嗎,維德孔,我完成了古阿爾達語方向的碩士學位論文?我可以為你私運進來一些文獻。”
“哦,你人真是太好了,康拉德。你知道我對這裡的圖書館選書的看法。”他們都輕聲抱怨,似乎心意相通。
“阿爾達語是我們部族固有的語言。”維德孔繼續以陳述性的語氣講話,“它的詞彙經由幾千年前居住在卡特拉平原的古代猛獁獵人改進和發展。在智慧的基本問題上,阿爾達語具有確定的語義優勢,那些大陸人不具備的優勢。阿爾達是我們身邊的自然,而現代瓦薩語——是一個大都市[33]混蛋。它被格拉德語汙染,退化成大陸性的。這種稀釋過的語言無法表述真理。在這個基因紊亂的蜜餞裡,所有語句最終只能表達一件事:國際恥辱。下個世紀將會見證我們部族迴歸原始的語言。這將是遵循智慧的新時代的誕生!”
“對此你已經講了很多了。我也讀了你對這個課題的筆記。都非常有意思,但是你難道不認為你個人的歷史形象,正在破壞學說中更尖銳的觀點嗎?”
“什麼?”赫德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他面部的溝壑伸長,嘴巴輕蔑地變硬。
康拉德假裝沒有注意到維德孔的不悅,繼續說道:“儘管我在你的評述中看到了邏輯,但你難道不認為人們很難從一個被定罪猥褻兒童的人口中,看出科學有效性嗎?”
“與帶著羅曼蒂克主義——我不知道還有什麼——的當代社會情色宣傳相比,交配對我們部族來說是完全不同的傳統。你知道這個的,康拉德。有一天,當性無能的道德引導大陸人走向滅絕時,你就會想起我跟你說的話了。”
“呃,讓我們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角度來看一下…”
“一位普通公民允許他們的女兒去學校,和黑人、吉卜賽人呆在一起,從童年起,她們就身處種族大熔爐中。一位普通公民讓他的孩子在那裡被強姦。你能明白,當四個女孩被送到這樣的學校裡會發生什麼。”
康拉德注意到了哲學家在呼吸之下的呢喃,但選擇忽視。“未來,普通公民可能會被你視為讀者。無論你的遠見是否經過實踐檢驗,普通公民將會進行選擇。你在談論整個民族!你真認為他不會注意到嗎?文章的作者是一名法西斯…”
“民族主義者。”
“一個法西斯和有條不紊的強姦犯。在喀琅施塔得被判無期徒刑,罪名是至少四起的謀殺,還有一本混雜了歷史哲學,優生學和強姦的書!”
“歷史,歷史,康拉德。你是個聰明的人,但你正在展現你受到的娘炮教育。你仍認為歷史由碩士學位論文構成,而我不知道什麼…”
“那麼,它由什麼構成?”經驗豐富的採訪官並沒有亂了分寸。“由強姦?”
維德孔從蓋斯勒鼻子底下的筆記本上抓了張紙。在他突然行動後,一個身著海軍藍制服的男人跳入鏡頭,用橡膠警棍擊打部族人的手腕。赫德痛苦地畏縮著,紙頁飛到了空中。三次提名奧斯卡·佐恩獎,世界著名的紀錄片導演康拉德·蓋斯勒,朝著士兵抬起了手。後者雖然放低了警棍,但依然警惕地站在男人身旁,摸著他的手腕。
“筆。”維德孔對蓋斯勒怒目而視。
握緊的拳頭攥緊了鋼筆,囚犯向士兵投去勝利的一瞥。“你!現在請把我的表單還給我。”橡膠警棍威脅地舉在半空中,蓋斯勒趕忙又撕下一頁,放在赫德面前的鐵桌上。
“現在看到了嗎,十字軍?”維德孔精心梳理的頭髮變得雜亂無章,一個淺棕色的鎖在他眼前晃動。維德孔用手肘固定住紙頁,嘗試把筆移動到紙面上,筆在他的手裡看起來鋒利又危險。男人突然發火:“請解開我的另一隻手,這樣沒法搞。”
在蓋斯勒懇求的目光下,士兵從腰帶上解下一串鑰匙。現在,赫德直接面向觀眾講話:“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來到此地,世界的邊緣,這個小島上。他們用狗拉雪橇來到這裡,穿越了極為廣闊的灰域。唯有意志最堅定的生物,才能在這場英雄遠征中保持精神的完整。而精神脆弱的大陸生物則被留在了那裡,那灰色的空洞裡。我們訓練有素的祖先輕而易舉地將他們從眾人裡區分開。那些發了瘋的人。因此,只有純潔,堅定不移的哈康人[34]、古德倫人[35]和其他先祖,離開灰色隕石坑,踏上了卡特拉的土地。五十年裡,先祖殺光了卡特拉所有的猛獁象,他們蓬勃發展。”赫德伸出他解放的手,開始在表格紙上畫小黑點。
“這是基本優生學法則,康拉德,最基本的。環境挑戰越多,人類就越會趨向高過草牆的方向演化。在這個黑暗的,被雪覆蓋的無垠之地…人們本不該在這裡生活。僅僅為了生存,必將催生出超級人類的趨勢。”
蓋斯勒預料之中地聳了聳肩,理解地點頭,沒有打斷他。“超級人類的進化趨勢可不會被道德約束。超級人類的進化趨勢是解放的渴望。一切皆有可能,萬事皆允。通過血脈,在漫漫長夜裡,一個冬天後是另一個冬天,一代人後是下一代人。甚至在你身上,康拉德,也存在著向超級人類進化的趨勢。”
康拉德點點頭。維德孔的臉色轉為不健康的潮紅,那是一種介於發燒和過敏性皮疹之間的紅色。“我們所有人,包括你,都有增強我們體內的原始獨立個體的責任。就像捕食者的下顎會因為吃肉而變得堅硬一般。責任…盛裝的責任。這樣他們才可能也擁有巨大的下顎,能裝更多肉的那種。”
維德孔露出看起來與面容並不相稱的驕傲微笑,欣賞著那件藝術品。相機還沒有拍到紙面上描繪了什麼,但蓋斯勒已經俯下身湊近那張紙。
“一個珍貴物種。中間的那個。一個獨一無二的寶藏。”
放映機嗡嗡作響,傑斯帕從文件夾裡拿出維德孔的那張紙的塑封複印件,放在桌面上。紙面上精心繪製出一個陌生的星座,一個由數個黑點組成的優雅星座。汗的嘴恐懼地張大了。國際聯合刑警探員特雷斯·馬切耶克認真地在筆記本上做著記錄。
“你不知道,康拉德,我多麼用力地○她,你可以想象…”傑斯帕匆忙關閉放映機時,赫德仍在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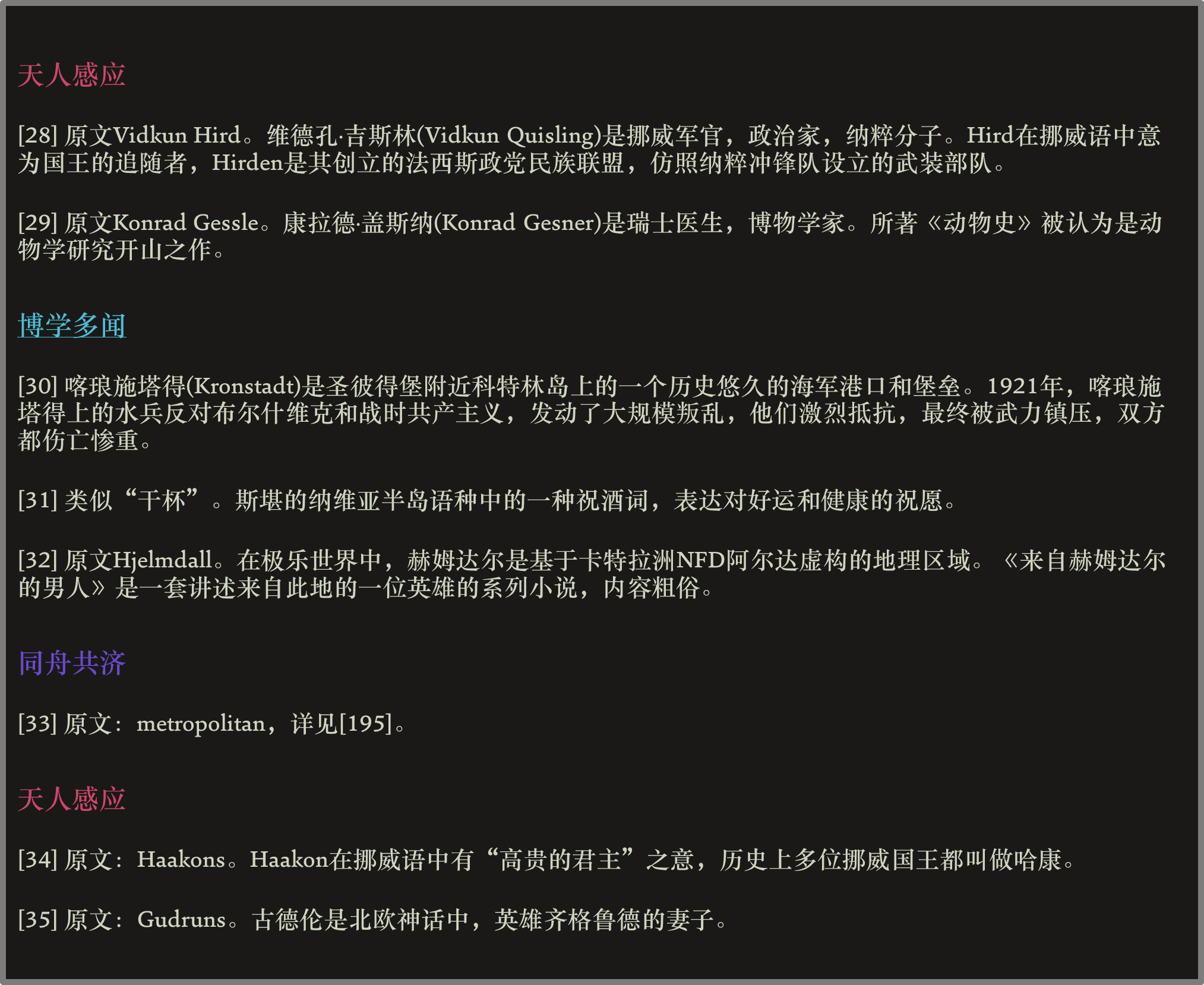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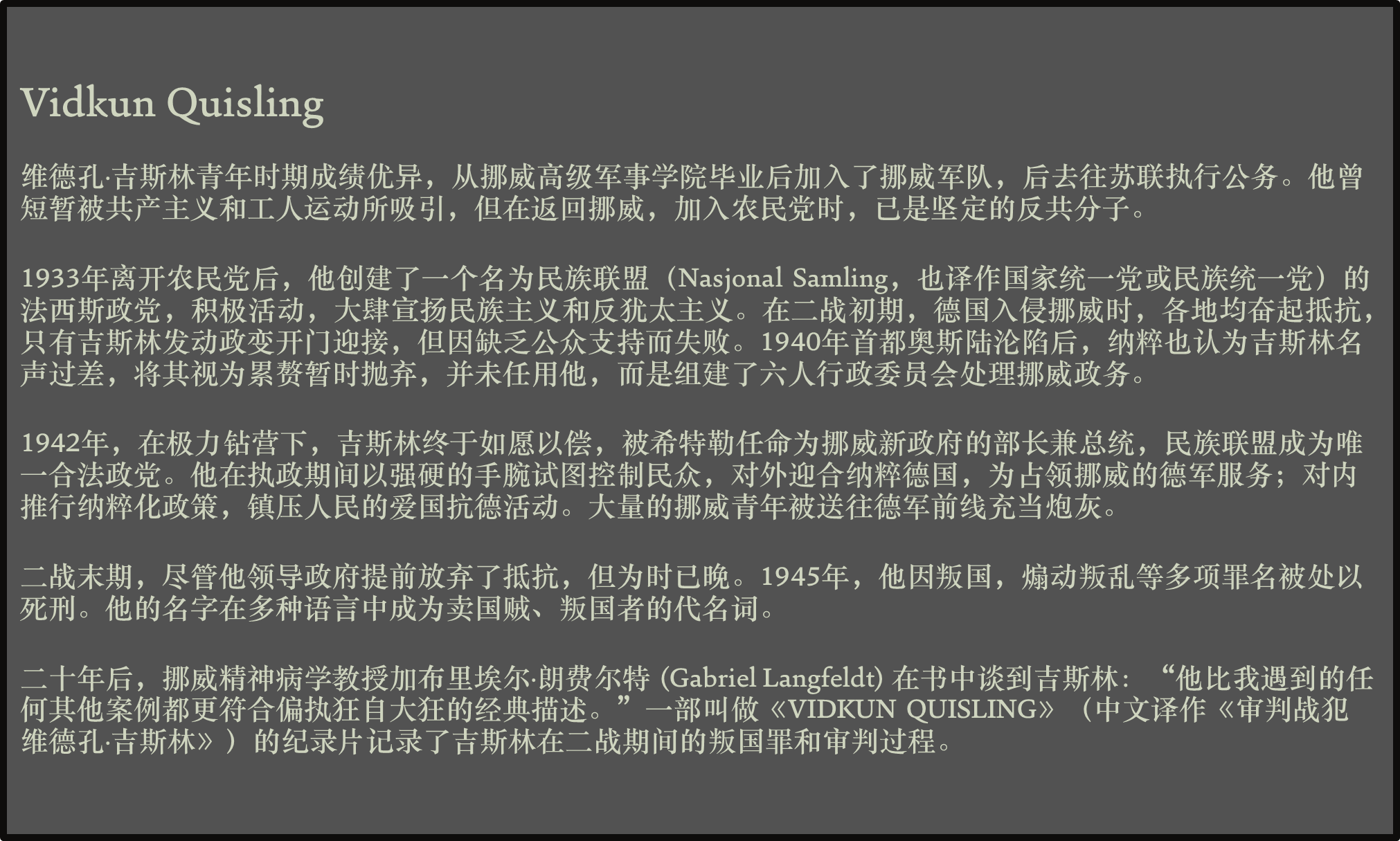
--------------------------------------------
二十年前,五月。
海岸邊,懸崖上的松樹林中庇廕而涼爽。炎炎烈日高掛在松樹頂端,但只有零星光斑穿過交錯的砂石和糾纏的樹根,到達森林地面,如同海面上的粼粼波光。有一陣,樹下鴉雀無聲,你可以聽見幾百米外,在男孩運動鞋壓迫下的石楠的咔嚓聲,直到海洋寒流再次吹動松針沙沙作響。樹幹輕輕搖擺,太陽在互相糾纏的立柱兩側排布出金色的條紋。樹脂香甜的氣息漂浮在森林裡。甘菊花的泥土味道縈繞在特雷斯的鼻孔裡,那是甜蜜而苦澀的芬芳。一根火柴被點燃,濃稠的煙霧從偷來的“阿斯特拉”香菸中迸發,將所有氣味一掃而空。煙霧軌跡在一束孤零零的光下十分清晰。防風衣披在頭頂,特雷斯放鬆下來。他嘗試在光下吐菸圈。他父親的外交別墅就在幾公里外。那座房子,離夏季人氣沙灘是如此之近,也使特雷斯在三週前,暑假開始時,變成了人氣男孩。特雷斯吹動小菸圈從大煙圈中穿過,山坡後的腳步聲愈加清晰。
“啊!我成功了…”他驚呼道,毀掉了他的傑作。
“什麼?”穿著短褲和水手襯衫的傑斯帕,在登上山坡時問道。“你幹嘛了?”
“讓一個菸圈從另一個菸圈裡穿過。”
“你在抽菸?!”傑斯帕問,顯得很意外。
“來一根?‘阿斯特拉’,它是最猛的。”
“給我,特雷斯。我來一根。”汗在傑斯帕身旁出現,大口地喘著粗氣。繫著皮革帶的雙筒望遠鏡掛在汗的脖子上。
“接著。”特雷斯將煙盒扔向汗,煙撒了出來,汗笨拙地用手接著。男孩竭盡全力,把它們舉到眼鏡下,避免掉落。
“酷。”汗對紙盒給出專業的評價。白色的星星從藍色紙板上劃過。
“毫無意義。”傑斯帕從嘴邊擠出這個詞,然後從特雷斯身邊走開,來到另一個山的丘頂端,觀測下方陸地。
“你的那件襯衫,才是毫無意義。”特雷斯懶洋洋地起身,從火柴盒裡拿出一根火柴遞給汗。
傑斯帕像一個船長般抬起手,眯著眼睛,觀測著身前森林的地表。
“毫無意義,是嗎?安妮可不這麼覺得。你知道嗎,她還因此*稱讚*了我,就在昨天。”
“她有嗎?”
傑斯帕轉向汗,男孩試探地吸了一口煙。
“嘿,汗,記得在更衣室裡,安妮說那件襯衫不錯嘛?”
“她說了。特雷斯,她確實說了。”
“菲爾遜像個傻瓜一樣跳進來,先我一步誇讚安妮的裙子很漂亮。還有關於她頭髮什麼的。真是挺搞笑的。”
“永遠不錯過表現禮貌的機會。”汗微笑著宣佈,咳出一些煙霧。
“我們走吧。”
三個男孩穿過光束,在林間滑行,向著山坡的頂端前進。汗試圖彈菸灰,卻失手把它甩飛了,於是開始旋轉帶子上的雙筒望遠鏡。他的揹包在他加速下坡時左右搖擺。男孩們跑下山坡,躍過石楠花從,只有傑斯帕擔心他的白色褲子,手插在兜裡端莊地信步,好像是一次傍晚散步。隨著他們接近懸崖上的據點,森林中海浪的聲音越來越響。
木質圍欄上的標誌寫著崩塌危險,此處一小塊土滾落下去。穿過步行棧道,從標誌底下爬進樹叢,汗向特雷斯解釋道:“看,他們叫它北海,但實際上它是一片大洋。理論上,它貫穿灰域,一直延申到你那邊的伊格瑞斯海。直至格拉德。這使北海成為洲際的。所以它其實是大洋。一個分類的紕漏。”
在一起的第三週,三個人儘可能保持談話的學術性。為了在秋季返回後,用他們睿智的形象驚豔所有人。傑斯帕,從後方的樹叢間小心地滑過,補充道:“在卡特拉我們沒有專門描述大洋的詞,不論哪種都叫‘海洋’。”
海藍寶石般的水體,從高聳的懸崖邊漫延到男孩們的面前。雲朵撕裂了淡藍色的天空,水下明亮的白色太陽倒影如同一根條帶。海浪懶散而又莊嚴地衝刷著沙灘帶。夏洛茨扎爾。風停了一陣,一股熱浪衝擊著男孩們的面頰。昆蟲在開花的野報春花枝葉上忙碌。巖崖下勾勒出海洋形狀的海岸線,通往半島之尖,那裡坐落著夏洛茨扎爾酒店。沙灘上散落著小人點和紅白相間的沙灘傘。男孩們坐在荊棘頂部的一團草上,在那裡,陡峭的沙土懸崖很快在視野裡消失。特雷斯推演過幾次,理論上,一個人可以怎樣跳下這鬆軟的岩石斜坡——他會從三米高的地方降落在略微傾斜的沙丘上,然後用鞋跟滑行。傑斯帕在這種情況下會擔心他的衣服,而汗就是個懦夫。即使是現在,在傑斯帕向汗懇求使用雙筒望遠鏡時,特雷斯坐的地方也離邊緣最近。望遠鏡中,太陽光點反射在昆蟲曲面的複眼裡。在黑暗冰冷的玻璃中心,下方沙灘上的人們,夏季北方的遊客及他們的毛巾和遮陽傘的圖像,被放大呈現。對汗來說圖像會更加清晰,他的處方鏡片左邊矯正了+7,右邊矯正了+4。在瓦薩的一個獵人商店裡,汗用他自己的錢買下了這副雙筒望遠鏡。
當傑斯帕掃描沙灘後,輪到特雷斯了。橡膠墊壓在他的眼眶上,臉頰上的雀斑在陽光下更加明顯,他承認:“還沒來,才十點而已。她們會來的。”
在汗和特雷斯比較香菸品牌時——據說瓦薩的蹩腳貨比較溫和,而來自格拉德的上流貨則更加濃烈——汗對一切急切地點頭。與此同時,傑斯帕鎖定了他在沙灘上的狙擊區域,拒絕放棄。十字準星停在了一個白色沙灘傘上,但上面並沒有在搜索的紅色花朵。垂線經過年輕的女性,倒塌的沙灘城堡,棕色皮膚曬日光浴的人們,繼續移動前,短暫在兩個金髮女孩身上停留了一陣——不是她們。傑斯帕調整著焦點。在大概兩百米外,一個似曾相識的細微感覺喚醒了他的內心,一個遙遠的星座,一種物質的交融。他揮手示意男孩們有事發生。汗和特雷斯在陽光下護住眼睛,向下方的沙灘俯瞰去。
傑斯帕調準了他澤爾牌鏡片的焦點,淡粉色的輕紗在他眼中銳化出肚子的形狀。女孩肚臍處的呼吸將目鏡振盪至上方的太陽神經叢[36],胸部的曲線聚攏成環,撐起日光浴內衣。白色的絲帶勒進她的肩膀裡,布料下的乳房隨著呼吸上下起伏。雙筒望遠鏡中心的齒輪響動兩次,綿延廣闊的畫面聚焦在米白色沙灘毛巾上,女孩在上面翻了個身,肚子朝下。灰金色的頭髮閃閃發光,墨鏡下是熟悉的圓臉。安妮艾琳·倫德慵懶地用手肘撐起身,把頭埋在雜誌裡。在她嬌小的後背上,胎記連成的一個奇異精緻的星座,順著她的脊柱流下,一直延伸到肩胛骨的翅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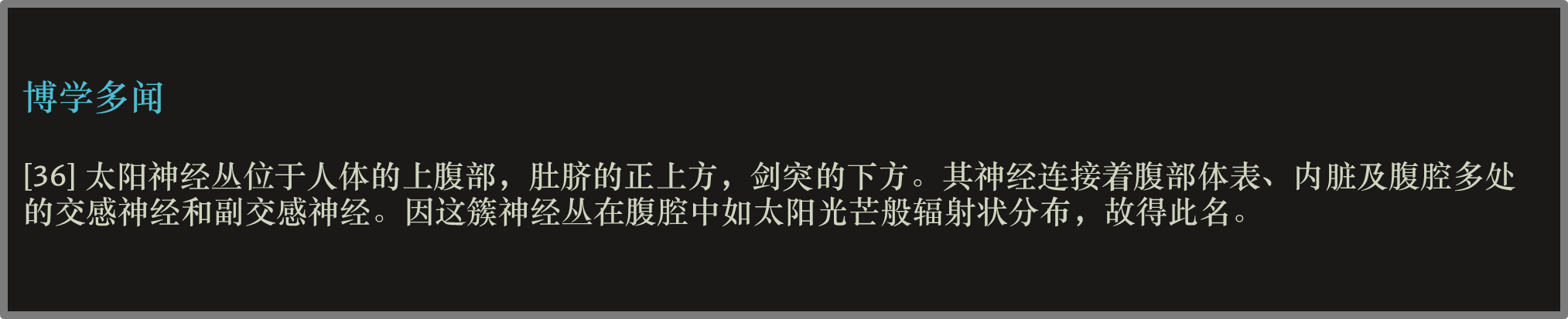
--------------------------------------------
冰冷的恐怖從密封的窗戶中滲進“影院”咖啡館。三個大腦盡力保持著忍耐到第二十年的表面張力。汗聳了聳肩:“誰知道這個?誰知道?我從始至終沒讀到過哪怕一行有關這個的東西。哪都沒寫!”
特雷斯把筆放在桌子上。
“這叫可控事實。它被故意從私人的描述裡隱去了。甚至包括官方文件。那三十個的文件夾都在我的腦袋裡,但是沒有一行字與它有關。他知道的。看看他!”
傑斯帕的表情毫無變化。他已經經歷過一次了。“這就是為什麼戈斯塔來找我。官方只會聳肩。也許他在工作中聽說了我認識那些女孩。他們那邊也都很疑惑。赫德也沒再做任何解釋。順便說一句,我不相信那些鬼話。有些男孩在那兒是因為原則,而赫德是真的喜歡大胸古德倫人。”
“那與簡述不符,在時間順序上不可能。”汗活躍起來,“五個小時之前他在六百公里以外,為他該死的強姦機器購買曲軸和墊片...我不清楚,一些墊片塞子之類的。”
因為製造臭名昭著的強姦機器發出了噪音,維德孔·赫德的鄰居最終報警舉報了他,這是他覆滅的開始。然而,伊納亞特·汗,仍然嚴肅地望向聯合警探的雙眼。
“特雷斯,你現在必須重啟案件。繼續調查下去。不知為何他肯定知道了,而且這是自那封信後唯一可靠的線索。你必須這麼做。”
“你無法想象現在的情況有多麼糟糕。這是挖掘舊事最差的時機。不再有軍隊的支持,一切都處於半戰爭狀態,沒人知道奧蘭治王國[37]是否還存在。如果我重啟這個爛攤子,他們會開了我…”
“不,特雷斯,你還是得為此做些什麼。”傑斯帕現在有些惱火,對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戰沒有任何興趣。“你就是做這個的人。這是你的工作。去完成它!”
“先等等!等等!當然,我會接受它。一開始你邀請我參加同學聚會時我就有這種感覺,你以為我覺得你要懷舊還是什麼?我自己的案子一直在調查中,你知道的,文件夾從未關閉。你最好期望當局會一直沉寂下去。他們全都討厭合作。只在極少情況下他們會不嫌麻煩,檢查所有的審訊文件是否簽了字。”
汗狡猾地笑了。“審訊文件?所以你還要去喀琅施塔得?”
“明天。”
“很高興知道你還是這麼酷,特雷斯。”
傑斯帕也笑了,發紅的臉頰和緊迫的語調讓人覺得有點不舒服。“但是確實酷!這就很好了。”
特雷斯也贊成。“這非常好了。二十年了。在那之後應該不剩任何希望了。”
“但還有希望?”傑斯帕智慧地傾斜著對肩膀來說仍然過於龐大的頭顱。
“是的,很好,傑斯帕。你做的已經很棒了。
“買單,謝謝!”已退出活躍業務工作兩年的室內設計師,對服務員打了個響指,用食指指了下桌子。對他們來說,夜晚從不輕鬆。但今天不一樣。今晚傑斯帕會獎勵自己一些小點心,愚蠢的小點心。立方體窗外,暮色已至,黑暗裡一切皆有可能。有可能在這個世界隱藏角落的某處發現她們,在沃斯托克湖[38]永凍冰層,或是深入格拉德肺部的地方,拉穆特·卡爾扎伊消失地無影無蹤的爾格沙漠裡...你還能找到她們。就像她們那時一樣。微小。而通過那個,自己也會變小。在雲層之上,蒙迪之軀[39]的山腳下,你只需要輕輕撩起雨滴的面紗就能觸碰到她們...“你沒放棄真是太勇敢了!所有人都忘卻了我們,冰冷的星星點綴著夜晚的天空,深藍色的天穹在我們頭頂旋轉,但我們知道你們仍在尋找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