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影子會被踩住?因為你的面前有光——哪怕是一線微芒。

生活本身就是一場巨大的恐怖——名為傑裡的社畜鼠鼠。
人生而不自由,被裹挾著如風滾草隨波逐流,被安排著按部就班地走入一個個新階段,被複制粘貼的日子消磨著熱情和生命。而在這枯燥的現實中,生活在既定軌道的人們便帶著心理上偶爾的小小反抗和掙扎,最終卻依然如同設定好的程序一般——想著“應該如此”,而繼續被推動著運轉。
這就是蓋不住的鍋蓋:具象化來,則是兩年如一日重複著運載車上的等待,維持100度完美微笑的小鍋蓋;致力於為感染的小鍋蓋找尋不知道是否存在的光明未來的阿蘭娜;順從著大家庭的安排,保持著靜默聲量微弱的社畜鼠鼠;常年浸染於井下的黑暗,卻又時刻渴求光明的探井人萊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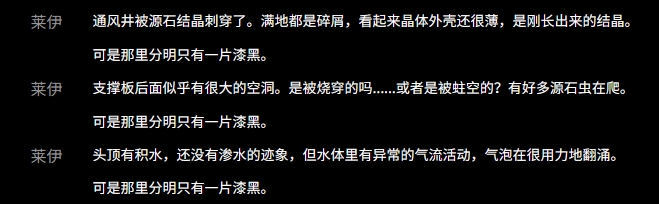
萊伊只是如此生活著,她只會如此,探井散工,獲取工錢,不工作就無法生活,不生活就看不見明天的光。
為了那束光,生活再漆黑她也能忍耐,畢竟她向來對疼痛不甚敏感——本應如此,直到小小的沙地獸死去。
萊伊的生活崩壞了,她習慣了痛苦,卻不願牽連他人,直到為沙地獸求藥無門,她才意識到如此這般的生活多麼荒誕——無能為力,無從求助。她孤身太久,以至於直到失去才認清自己依靠的對象,因此博士和兔兔自然的相互支持,才如此吸引萊伊的目光。
以前,我以為自己不怕痛的......可我現在,怕得發抖。

萊伊看到的,也許是那份彼此依靠,互相信任的光。
忍耐總會滿溢,它可能需要一點變化:比如推遲的實驗,沙地獸之死,又或者沒來由的劫車。一點點偏移牽起了連鎖反應,鍋蓋被頂起,滿地都是生活的殘渣。

當意外真的迫近時,人們又開始猶豫了。偏離了日常的新航線需要一個新目標,此時絆住腳踝的,卻往往是先前厭棄的現實生活和對未知的恐懼。人們渴望著個性,但真要從集體中脫身而出成為一個抽象的人時,這又成了一種新的恐懼。不回頭的車轍,也需要莫大決心。
車轍不停,瓶樹狂奔,這是脫軌的生活在一心一意豬突猛進。咧嘴的礦井,落定的錘子,是對生活惡意的反抗調侃以及用信任回應時間的難題。

而被踩住的影子是什麼呢?提筆停頓許久,我只好粗略地想象:那興許是一種過去,一種生活的象徵。就像小鍋蓋對父親回家的期盼,萊伊對那模糊光芒的幻想,鼠鼠對於家庭安排的順從等等……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博士前人類的身份,以及“羅德島”在過去的意義。
它重要嗎?當然如此,影子是我們自身的投影,我們永遠甩不開它,就像我們無法真正摒棄過去。可若只專注於影子,我們便邁不開步伐,進而忽視了真正重要的,映照出影子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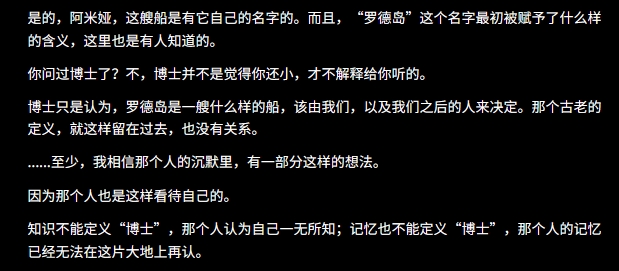
人生不自由,咧嘴谷仍在遠方
可以說人活在世上,往往是為了某一個念想,比如上帝說人世之苦便是為了來生安康。可何為來生呢?有人能看到來生嗎?不知道,但有這個念想便好,人便能慣性般活著,一如小鍋蓋等待的父親,一如鼠鼠推銷的保險金,祥林嫂捐了門檻,也只求一個心安。
門檻能減輕死後應償的罪孽,保險可以讓死人獲得賠償,可難道他們發明了死後還能驗證乃至於享受金錢的方法嗎?沒有,對於生者來說這是荒誕的,為了一個理應無可得見的念想而活著是荒誕的。

自己從不捨得吃藥卻願意為另一個小生命問藥求醫的萊伊是荒誕的,在最後一刻向訂婚屈服上車後卻又陰差陽錯逃婚的鼠鼠是荒誕的,生活在運載車上始終強忍悲傷微笑著等待父親的小鍋蓋是荒誕的,連阿蘭娜——把優惠券分門別類,面對劫車冷靜對話,在檢查關能屈能伸,最會生活的“荒野上的阿蘭娜”也會為了不治之症礦石病而求取所謂的偏方奇藥,偷偷照顧身為感染者的小鍋蓋兩年。她無法再次放棄一個人,哪怕這些努力百分之九十九會白費,哪怕運載車上的生活終有盡頭,那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卻也足以讓她長驅著座駕衝向那個未來,這也是荒誕的。
從概率學上來說,這幾近不可能事件,從理性思考上想,這幾乎是無用功。但是,那個未來不一定要存在,那個念想並非必須是現實,只要有個人願意說:那是存在的。這便夠了。

來生無可追尋,可此生卻有了意義;保險自己無福享受,可卻另有受益人;萊伊沒有找到曾經的奇蹟,卻當真找到了巨獸的光芒。

生活是荒誕,是恐怖,是黑暗,而在這荒誕中尋找意義,在恐怖中尋找慰藉,在黑暗中尋找一線光明,便是人生而為人的自由。那束光甚至不一定要存在,旅途的盡頭也許一無所有,或許最後我們也無從得知這前路漫漫通向怎樣的結局,可那又如何?正如凱爾希萬年的踽踽獨行,博士在異世的孤獨堅守,羅德島的車轍行過理想的荒野,沒人能推演出一個篤定的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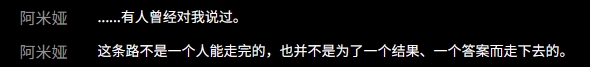
車轍與瓶樹,荒野與天災,成群的沙地獸和地穴的一線光明,

在未失憶的博士看來,舉目所見無不時刻提醒著自己無可挽回的過往,“博士想看到的,都是不可能再看到的”,浩渺的孤獨中,博士向殘骸中的阿米婭伸出了手,一如阿米婭堅定地把手伸向石棺中的博士。遍地的星光裡,博士和阿米婭終於確定了自己最初的座標,名為羅德島的艦船新生之處。
而“羅德島”的定義究竟是什麼?現在我們無從回答,唯有向著未來步履不停。

我們所去往的“咧嘴谷”有許多,它可以是座標,可以是保險,可以是一束光,可以是任何地方任何理想,它並非“一處空間,不是一種物質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恆途”
人為了生存求取理智,卻因理智叩問意義,人生於不自由中,卻以存在對抗虛無,旅者被生活裹挾著偏航了道路,可這趟旅途本身卻有了意義。正如阿米婭所言:“生命有限,生命存續”,因不自由而自由,因有限而永存。錘子落定,鍋蓋平息,越過塵土、意外和黑暗的來路,回頭再看,輕舟已過萬重山。

最後請允許我依然用史鐵生的一段話做個結:
人可以走向天堂, 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著彼岸的成立。走到,豈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終結、拯救的放棄。因而天堂不是一處空間,不是一種物質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恆途。
物質性(譬如肉身)永遠是一種限制。走到(無論哪兒)之到,必仍是一種限制,否則何以言到?限制不能拯救限制,好比“瞎子不能指引瞎子”。天堂是什麼?正是與這物質性限制的對峙,是有限的此岸對彼岸的無限眺望。誰若能夠證明另一種時空,證明某一處無論多麼美好的物質性“天堂”可以到達,誰就應該也能夠證明另一種限制。另一種限制於是呼喚著另一種彼岸。因而,在限制與眺望、此岸與彼岸之間,拯救依然是精神的恆途。
這是不是說天堂不能成立?是不是說“走向天堂”是一種欺騙?我想,物質性天堂註定難為,而精神的天堂恰於走向中成立,永遠的限制是其永遠成立的依據。形象地說:設若你果真到了天堂,然後呢?然後,無所眺望或另有眺望都證明到達之地並非圓滿,而你若永遠地走向它,你便隨時都在它的光照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