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组长
导语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都会就社会制度、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交议案。作为一门迅速发展的文化产业,游戏同样备受“两会”关注,而防沉迷问题则是其重中之重,今年就出现了不止一项有关提议。
今年2月份,中宣部主办的防沉迷实名认证系统企业接入培训会明确表示:2021年5月31日前,所有游戏企业需完成在运营游戏的防沉迷系统的接入工作。6月1日起,未接入防沉迷系统的在运营游戏要停止运营。
与此同时,国内大型游戏公司也在不遗余力地推进防沉迷系统建设,比如腾讯的成长守护平台、网易的家长关爱平台。

防沉迷平台通常都聚焦于亲子关系
游戏防沉迷,似乎一时间又成了游戏行业的“头等大事”。然而,更多的讨论还是聚焦于怎样贯彻种种防沉迷方案,很少顾及和它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后果。为什么文化产业中只有游戏需要防沉迷,影视、网文就不需要?为什么与防沉迷相关的各种制度、技术明明十几年前开始就受到莫大重视,落实起来却一直困难重重?
这些问题让人困惑。原因很可能在于,我们对防沉迷本身仍然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
刘梦霏老师是国内从事游戏研究的一名学者,主要以历史的视角研究游戏的本质与社会影响,长期致力于破除社会大众对游戏的刻板印象。游戏动力最近采访到了这位老师,希望她能够就防沉迷问题聊聊自己的看法。
本次访谈中,刘梦霏老师指出,游戏治理仅靠防沉迷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她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完善的游戏教育和良好的游戏素养,防沉迷系统很难单独发挥作用。游戏是复杂的,防沉迷系统需要有所区分,不能搞一刀切,那样既妨碍了我们更好地认识游戏本身,也会造成不必要的家庭与社会矛盾。
以下为具体访谈内容,经过删简和调整。

刘梦霏: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数字媒体系讲师,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
现在说的防沉迷,和十几年前没什么不同
游戏动力(以下简称“VGN”):最近一年,和游戏防沉迷相关的事件非常多,从去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增加的“网络保护”专章,到今年有关部门明令游戏企业接入防沉迷系统、“两会”的防沉迷提案,你如何看待相关报道?
刘梦霏(以下简称“刘”):我在2007年的时候就看过很多关于防沉迷的新闻,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说要防沉迷,我几乎看不出现在和当时有什么差别。
只不过,那个时候普遍认为防沉迷应该是国家来做的事情,就算政府没有经验,盛大那样的企业会主动站出来说我可以提供帮助。现在有一点很奇怪,似乎不知不觉之间,大家开始觉得游戏防沉迷的问题完全可以由腾讯这样的大公司来解决。人们不仅相信它可以做,还把自己的个人数据给它,还让它的平台来协调亲子关系。
我惊讶于防沉迷总能成为新闻的常客,我没见过这么长寿的新闻。既然我们今天还在讨论同样的事情,这也许意味着防沉迷的实际效果没有我们想象的好。中国游戏玩家的数量、人均游戏时长一直在增长,一味防着游戏可能不是一个好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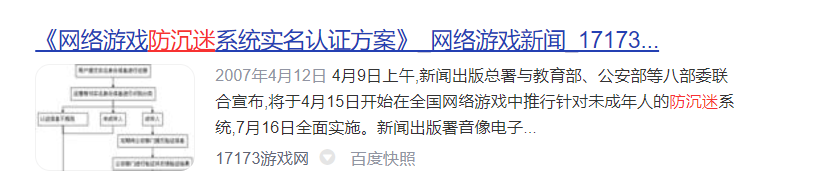
2007年就开始提出的实名认证方案,仍有待完全落实
VGN: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判断?
刘:一直就是这个判断。几年前,我在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里面,对上过某位网瘾专家。我做游戏研究更多地是站在学者的立场,但也考虑玩家的动机。我不太支持用“成瘾”特征去定性所有的游戏,这种对游戏缺乏分类的批判性认识的成瘾研究并不能解决问题,很多时候还会污名化玩家。
我碰上的那位教授就是我开始做游戏研究时想要对抗的假想敌之一,但我没想到自己那么早碰上了他。当时我就和他说,10年前咱们国家就是按照您鼓励的方向发展的,您的意见得到了执行,不仅网瘾戒除中心盛行,国家更是几乎叫停了游戏产业。但是反过来说,您的意见但凡有效,我们今天根本就不需要回到这里,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他当时就梗住了。那时我的立场就和现在一样:游戏治理绝不等于游戏防沉迷,至少不全等于。
VGN:所以防沉迷这些年的发展,反而说明它未必十分有效?
刘:我再举一例。从08年那个时候起,国家建设绿坝系统,要把网络上的不清洁的东西都拦掉,让青少年健康发展。这和现在的防沉迷不是同一个思路吗?但现在有多少人还听说过绿坝呢?包括早年,国家也推行过绿色网游联盟的,也是从同样的角度对游戏进行筛选,现在看起来还比防沉迷系统更容易执行。但是这个体系,现在有多少人听过呢?
就算不谈历史、不说防沉迷实用与否,我觉得游戏的权利就是休闲的权利,你哪怕不提它赋予人意义感,通过游戏学习知识这些的严肃目的,我们就说你通过游戏休闲的权利。这是写在联合国宪章里的人的权利,那我们要限制这种权利的时候就完全应该更谨慎一些。
当然,我认为部分青少年如果因为过度沉迷而受害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青少年——那可以管也应该管。通过三甲医院的专业治疗,或者借助学校教育、家庭研讨、专家辅导,这些都是正常的治理手段。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出于对一个媒介的偏见,做出一个防沉迷系统来限制所有青少年,就有些不合理了。再说,防沉迷很难拦得住要玩游戏的人。上一代人做的东西怎么拦得住在信息环境下成长出来的新一代人?他们总有办法绕过的。
应该对“沉迷游戏”负责的,不只是游戏厂商和家长
VGN:刚才你说到,让企业来主导防沉迷系统建设是很奇怪的,为什么这样讲?
刘:企业当然不应该主导防沉迷,企业是游戏产业的既得利益者,防沉迷系统还要我们把隐私数据全部交给它,这里面的风险其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游戏需要获取的权限越来越多
在游戏沉迷这个问题上,首先要负责的应该是玩家自己。为什么现在玩家自己好像是一个没有自主能力的人一样,全靠家长和游戏厂商?我们社会的普遍认识就是觉得青少年没有自主能力也没有判断能力,这个认识是很有问题的。玩家在游戏中是主动的,我们应当鼓励他们把这种主动的姿态带到现实生活中,为自己的游戏行为负责。毕竟他们才是受游戏影响最大的群体。
此外,我觉得青少年应该细分,16岁以上甚至十四五岁以上的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他该有自主判断的能力了。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去选择。反过来说,有些青少年玩游戏正是因为喜欢自己在游戏之中的自主权。如果从一开始就不让青少年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要什么时候才会学会负责呢?
再次,我们要开始重视学校在游戏教育上的责任。小学生放寒假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好书推荐列表,有时候也会有优秀电影的列表。但却从来从来没出过游戏的列表。那家长又怎么能知道哪些游戏他可以玩呢?家长怎么知道有些哪些是对他孩子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呢?我们也不是天然地就会欣赏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在游戏素养的问题上,额外需要学校发挥教育的功能和作用,作为一个教育上的脚手架,帮助孩子和家长一起更好、更正确、更全面地认识游戏。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很多学校的老师,也都没有更新自己对于游戏的认识,还是停留在“玩物丧志”、“君子不戏”的传统认识上。这种认识又会反过来加剧孩子的无助和家长的焦虑。
VGN:家长这方面,你好像认为他们的角色和防沉迷所说的监护人应该不一样?
刘:我认为家长的负责不是防沉迷说的那种监护人的负责,家长要理解游戏。
其实我真的没有见过一个家长说,孩子一定不能玩游戏。很多时候家长问的是:我们怎么才能保证孩子只玩好的游戏,或者怎么让孩子以更健康的方式玩,这才是一个正常家长的立场。
问题在于,如果你真的站在家长的立场上去看的话,他们没有渠道理解游戏。很多家长也不理解电影,还不理解文学,但他们知道学校会教。可是游戏这个问题,学校好像一点没有责任,背锅的要么是“没公德心的游戏公司”,要么是“不负责的家长”。
我不认为玩游戏的孩子和家长应该对立,因为他们想要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一家人当然都希望孩子能健康发展,只不过在达成这个目标的方式上是有差异的。
VGN:具体有什么办法解决亲子之间在游戏问题上的矛盾?
刘:亲子之间在游戏问题上没有根本矛盾。其实很多时候,家长和孩子斗争的核心是时间管理的问题,家长觉得孩子玩游戏时间太长了,或者是家长觉得孩子玩游戏完全脱离了他们的控制。
但是,很多时候游戏其实是可以创造家长和孩子的共同体验的。而且每个孩子从小都玩游戏,只是不一定是电子游戏,孩子小时候玩游戏也是家长陪他玩的,那个时候就没有问题,怎么换到屏幕里就能出问题?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对游戏的认识不够。
亲子如果能够通过游戏沟通的话,更能放大游戏作为一种沟通工具的价值。试想,在游戏里双方能够以一个摆脱了现实身份的、更平等的方式来沟通,能够彼此互动,然后还能拥有一份共同的体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沟通环境。

通过一些聚会游戏也可以实现“合家欢”
一味硬推行防沉迷会造成什么后果?亲子关系可能会从合作关系变成一种监视者和被监视者的关系,这样很可能会产生一些原本不必要的冲突。
VGN:还有你也强调学校也没能尽到游戏教育的责任,你自己就是高校教师,你觉得学界在游戏教育上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刘:我觉得游戏产业真正需要的,反而就是我们做的这种可能乍一看不是很接地气的游戏研究,但实际上更像一种“内功”的努力。很多时候,产业自己和大众对话时会遇到一些问题,游戏知识分子应该成为一道桥梁。
我看到过太多因为青少年沉迷游戏而起的冲突,家长指责游戏开发者,学校指责游戏开发者,开发者根本没有办法说话。哪怕他开发的根本就不是消费类的手游(指F2P类游戏),他都无法辩解,因为他没法和不懂游戏的人解释自己做的到底是什么。这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游戏研究不发达,整个社会的游戏素养也不高,并没有形成对于游戏的理智理解。不过这种时候,我们作为学者,还是能站在教师和育人的立场上,更容易地跟家长沟通。
我觉得学界的主要工作有几个,一个是做好基础理论的研究,搞明白游戏的吸引力到底在哪里,是如何影响人的,能不能或者能怎样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一个是应用类的研究,就是把一些可以落实的理论或者通过理论研究看到的新方向做成产业或公众可以理解的具体案例,提供一些切实的“抓手”;此外,我们很多时候也可以为产业或政府提供一些专业意见,并在几方之间做一些协调工作;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游戏素养的普及和教育工作,这是需要联动中小学教师来一起完成的。可以说,目前不管是哪一项工作,都有人在推行,但都不能算是做得非常完美,还需要更多时间、更多资源、多方参与来做好这些工作。因为就像习总书记最近说的,游戏的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各方来共同解决。
VGN:也就是说,更理想的状态是,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都能够告诉青少年,什么是好的游戏,如何保持健康的游戏方式。
刘:是的,但现实就是我们很可能处在理想的反面,而游戏本身的吸引力又让人难以抗拒。我还在博士期间,就发现清华北大每年都有一些因为玩游戏玩太多,然后退学的学生。
我后来去了解了这些学生的状况。我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在家教比较严的家庭长大的,从小到大生活里只有学习,缺少娱乐。所以等他到了大学,突然发现所有的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以后, 他控制不了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其实让孩子早点接触游戏,就有点像一个脱敏训练。
我自己从小玩游戏,而且是跟父亲一起玩,他没有对我玩游戏这件事特别大惊小怪,我反而就觉得游戏和读书、看电影、运动、手工、音乐这些事情一样,只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虽然从小玩到大,却从来没有因为游戏耽误学习过。事实上,我会有意识地在上历史课之前玩《文明》,在上世界地理课之前玩《大航海》,结果取得的成绩可能反而比只读书的同学要好。因为游戏里的知识是活的,它需要玩家的行动,它会把玩家放到特定的情境中,给他难题让他解决。这样学到的东西,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当然,这也需要玩家自己懂得反思和利用游戏–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教育缺失的,我试图通过这个访谈提醒大家的也正是这一点:我们要学会利用游戏,避免自己“被游戏玩了”,才能让它为我们自身所用。

《大航海》系列是关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历史向游戏
所以反过来说在大学沉迷游戏的那些孩子们,这个事其实不完全怪他。因为人在游戏里有的那种影响力、那种意义自洽的状态,那种能够对周围环境有积极的影响、大家都需要你的状态,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是非常罕有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他在以前不太玩游戏,然后突然沉迷一段时间,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觉得这是他作为一个正常人有正常追求的标志。只要他最后能从游戏里出来,而且出来的时候带了一点东西不管是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丰富了对世界的了解、学到了新的技能或者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旅程,增加了生命的深度那就是值得的。
为什么游戏就需要防沉迷
VGN:我们注意到,种种文化产品中,只有游戏被强调需要防沉迷,你怎么认识这件事?
刘:我们可以参照兄弟行业,比如说影视。从影视学术界的发展,我们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正规的学科,C刊都是能接受影评的,而且学界和业界关系很健康。
这就形成一种共识:研究影视、评论影视是一个有学术门槛的事情,你也得有阅片量,才能输出靠谱的意见。还有文学评论,你也得学也得多读书,你也得去看各种文学理论;那为什么评论一个游戏就不需要任何专业积累,游戏治理就不需要让游戏经历丰富的人参与呢?
如果真的这么对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游戏领域所有事情都非常奇怪。假如现在防沉迷系统规定,孩子一天只能打一个小时游戏,我就不信这些孩子每天游戏的时间是占他媒介消费的大部分时间的。甚至,他们更多时候可能是在刷小视频,为什么这个就不去治理呢? 此外,大家老说孩子玩游戏毁眼睛,就好像所有游戏都是小屏幕玩的一样。实际上,十年前主机上就有体感游戏了,很多游戏是不需要对着小屏幕玩,而是可以通过健康的身体运动来玩的(比如《健身环大冒险》),这种游戏为什么大家不提呢?还是因为许多在评论游戏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多样化的、健康的游戏的存在。

如今,几岁大的孩子也开始拥有自己的手机
VGN:这其中的根本问题出在哪?
刘:我这些年一直在重复一句话,游戏仍然是一种亚文化。人们看待亚文化总是带一定偏见的,而我们的儒家文化向来又强调积极入世、集体主义,所以玩游戏就被看成是一种消极的、孤立的行为,一种应该被警惕的行为。
游戏实际上是非常古老的东西,但这个古老的东西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很多变化,知识分子不能及时地、积极地参与进去,造成它的概念没有更新。
这也引发了另一个后果,那就是整个社会的游戏素养不足。虽然现在游戏玩家变多了,但是我觉得普遍来说我们的游戏素养降低了。太多的年轻人只知道流行游戏,认为游戏是生命的消遣,他们不认为游戏可以传递思考,可以有现实意义,或者能传递高级的文化体验。但是如果真是如此,那像《刺客信条》这样的游戏的卖点又是什么呢?甚至有些玩家开始认为,作品游戏不如消费游戏赚钱,因此价值就更低。但其实我们知道,就好像文学中有大众文学也有严肃文学,电影中有纪录片、实验电影也有商业片一样,不同的作品本就应该采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不能说《小时代》比《红楼梦》卖得多就说《红楼梦》没有价值。我认为流行游戏可以靠销量,但作品游戏还是需要有文艺评论的高度来认识它才比较合适。
这些我觉得都是比社会对游戏的普遍偏见更令人忧虑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对游戏没有正确的认识,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损失。你可能会说主机玩家呢?主机玩家圈子真的太小了,虽然我真的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
VGN:但是,过度沉迷游戏毕竟还是有一定负面影响的,不是吗?
刘:是的,这一点当然是不容否认的。很久之前,我每一次在公众场合发声的时候,我都是在强调我们应该中性地看待游戏,节制它的消极影响也扩大它的积极影响。但是,因为大家都把游戏看得太负面了,所以我就要多说一点他积极的部分;哪怕《王者荣耀》这样的游戏,我也要更强调他对于青少年团队合作能力和自省能力的培养。
可是我自己就做过一个研究,当时我募集了一些玩《王者荣耀》的孩子,根据统计,他们平均的游戏时间是4000个小时到7000个小时,而且他们多数只玩过这一个游戏。有几个孩子还玩过《英雄联盟》,然后还有一个孩子玩过一点主机游戏,这已经算非常稀有了。而且,他们的学习成绩都不能算好。
我当时就很难受。所以我后来把我本来准备的材料全改了,就不再去强调“研究者应该保持中立,不能影响你的研究对象”,不再把那个实验看成一种实证的科学实验,而是改为采用一种参与主义的视角,去试图让这些参加实验的孩子们能改变自己对于游戏的认识,不让他们生命里的这几千个小时完全浪费。
第二天这个实验就转变成了一个工作坊,我试图引导参与者自己去思考能不能积极地利用游戏,引导他们自己去想自己花在游戏的这些时间,最后到底导向了什么。我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专业工具,帮助他们反思自己在团队中的角色,以及如何通过自省与沟通来更好地与队友合作。我很高兴地看到,当工作坊结束时,之前零零散散的孩子们自发地站成了一个大的圆圈,来友善地互相交流。这次实验工作坊其实也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它让我再次回溯自己做游戏研究的动机:为了一个游戏能让现实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差的世界。
VGN:你接受过一些主流媒体的访谈,多数主题和游戏相关,但在防沉迷这件事情上似乎很少在主流媒体上表过态。这是为什么呢?
刘:其实我还是接受了一些和防沉迷相关的大报采访的。不过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我拒绝过的一家主流媒体的访谈。
我之所以拒绝,就是因为当时他们给我的提纲里主要在问的是:我知道多少种绕过防沉迷系统的方式,我认为防沉迷系统应当怎么样能够让青少年健康发展。我看了以后,就很客气地跟他们说,可能我的研究观点不太能支持你们的方向,建议找别人。
我对防沉迷始终持保留态度。我不会站在玩家的对立面,去提醒大众怎样提防青少年绕过防沉迷系统,因为我认为这不是我们应该面对游戏的态度。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这么武断地把所有游戏都用防沉迷系统一刀砍死。而是应当像面对文学,面对电影一样面对游戏:有能力分辨好坏,尽力利用好的,同时也控制不良的体验。
不过好在这几年,会有更多年轻的记者打电话过来之后就说自己是玩游戏的,然后我就不需要从头跟他说游戏是什么、不是什么了。可以说,事情在慢慢变好吧。
确立游戏分级、分类体系,可能比防沉迷更要紧
VGN:国外也有防沉迷的说法,但在这之外分级制度似乎更为实用。我们国内去年年底由音数协确定了游戏分级标准,但是只分8+、12+和16+,去掉了有争议的18+,你怎么评价这个分级方案?
刘:这个体系我从很早的时候就从内部了解,他们也是经历了各种压力做起来的,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而且他们现在的作用还是很积极的。当然,这个体系不完美,但我相信他们也会继续发展的。
至于分级制度,一方面它是一个行业的自我监控和自我引导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对于不懂游戏的家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你拿到这个游戏,上面写了16+,家长在买游戏的时候就知道我不该给我太小的孩子买。有了分级系统以后,社会的游戏素养是会提高的。
而且,分级系统会逐渐引导人们形成一种认识:游戏是复杂的,因为人也是复杂的、发展的、变化的。

中国游戏分级标准为8+、12+、16+
VGN:除了分级,你也一直在提倡游戏分类。此前,你将玩家们常说的买断制游戏称为作品游戏,免费下载、内购付费的游戏被界定为消费游戏,带有抽卡开箱之类的消费游戏又进一步被分为赌博游戏,分类对于我们认识游戏为什么如此重要?
刘:我是按照游戏的消费模式来划分的,作品游戏、消费游戏和赌博游戏就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那种抽卡游戏,你完全都不能靠技巧赢的游戏,它实际上就是赌博。赌博这种事,别说青少年抵御不了,成年人也抵御不了。
如果没有形成普遍的分类观念,大行其道的消费游戏、赌博游戏绝对会不断造成青少年的消费问题。因为青少年压根没意识到,他玩游戏到底是在做什么。尤其是,游戏中他花的是虚拟货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他对这种消费是比较没感觉的。 可能一直到他真的花了几万,他才意识到完了窟窿太大了,然后跳下去了。回头,家长来怪罪所有游戏的开发者,怪罪所有游戏。
你说这种事儿,他和做作品游戏的人有什么关系?他和陈星汉这样的开发者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不公平的。

陈星汉是主张游戏可以传达丰富的艺术、情感体验的制作人,图为其代表作《风之旅人》
VGN:也就是说,即使要做防沉迷,也应该针对游戏类型有所不同?
刘:我是觉得,消费游戏、赌博游戏不是说你不可以做,但是至少应该有一个单独的审核标准。真正应该贯彻防沉迷的是这些游戏才对,而不是一刀切针对所有“网络游戏”。
此外,好的作品游戏是可以不用“防沉迷”的。就像我们看莎士比亚,看鲁迅,看《红楼梦》,看《史记》,看《权力的游戏》时不会愿意被人规定“看一个小时就不能看了”一样,好的作品游戏也是一种很高级的文化体验,你武断地切断我的体验,我剧情过到一半或者战役打到一半就被迫推出,那肯定是让人很难受的。
VGN:短期来看,防沉迷还是要按照原来的标准继续推行下去。那么你对游戏的未来有信心吗?
刘:其实,我觉得关于游戏的种种问题,绝不会自然而然地变好。这个事说到底,一定要大众都逐渐能够认识到,游戏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东西。知识分子、媒体都应该尽力发声和行动,提高社会的游戏素养。还是像习总书记说的,游戏的沉迷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多方协调共治来解决,大家各司其职,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步,可能还是先从清醒、理智地认识游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