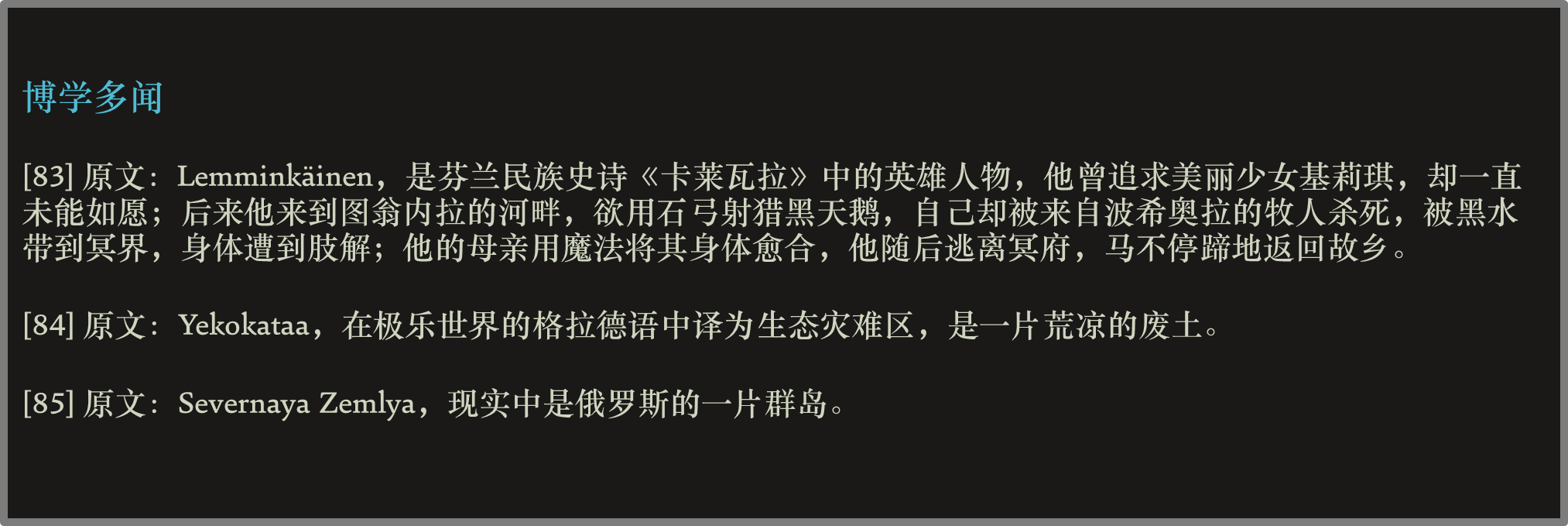油毡推销员在小镇间旅行。在北雪平[78],他沿一条冰封大河的河岸推销油毡。教堂是木制结构的,街道拥挤狭窄。油毡推销员憧憬过木结构建筑和北方冰封的静谧。晚上9点,街上空荡无人,风在城市中穿行。狂风大作,大衣下摆啪嗒作响,厚厚的积雪覆盖在房屋的屋顶。大雪落进了油毡推销员的心里。橘黄色的路灯排列成行。那天下午,他脑海里闪过了什么画面?在他的出租屋的毯子底下。多么戏剧性,多么有耐心。在隔壁的花园里,是油毡推销员敬佩的两兄弟:引擎零件一样的脸,嘴巴抿起,脖颈因为寒冷而冻得通红。而在阿尔达,群山的开始的地方,峡湾切入高峰间的山谷中。雪巨人的脚下容纳了一片陶土红色。而在夜晚,窗格如小眼睛在黑暗中闪烁时,群山发黑的牙齿裸露在天空之下。但它们的笑容根本无法与与油毡推销员的微笑相提并论。
他练习过。像毛毛虫一样放低下巴,抬起上嘴唇。酒店房间镜子前的男人变得狡猾。如果他就这样进来呢?进入天花板低沉的混凝土墙壁地下室。看到这样的东西是什么感觉?现在好好看着,美人,看着我。
后来,在油毡工厂关停后,境况愈发艰难。但油毡推销员用双脚重新站了起来。他培养了新的联系人,结识了进口商。一个全新的油毡工厂开张了。而不论他去哪,不论看到什么,他总想要看到更多。他销售油毡,但以日常摄影师自居。对他来说,世界保存了其他人看不到的隐秘风景和美的熔炉。
像一个拿着万花筒的孩子,他拆解形状。在格拉德,冬季轨道上,油毡推销员曾销售过油毡。磁悬浮列车在北部高原肆虐。那时窗外皆是黑暗,极光凝固在平原上空。他在餐车的卫生间里,漆黑的山脉隧道吞噬了火车。随后,当油毡推销员从隧道里出来时,手里抓满了碎玻璃。迷人的曼陀罗[79]花去哪了?它在呼唤,躲藏,一开始很有趣,但随即对其丑陋的结构感到失望,逞工炫巧。油毡销售员失去了耐心。他贪婪的神经在熊熊燃烧。杰林卡。在玻拉苏尔[80],一个男人把雪涂抹在脸上,但雪只是被他炽热的神经融化。
现在他休息了,尝试照顾好自己。他工作,把油毡卖给建材商店,室内设计工作室和零售商。棕色的油毡。花朵图案的油毡。他从北方南下到瓦萨。在普里奥焦尔斯克,在洛韦萨精英阶层的花园郊区推销油毡时,他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一些他以为自己永远不会看到的东西。他看见了其他的油毡推销员。只不过他们不是真的油毡推销员。在同性恋公园的一张床垫上,他跟检票员聊瓦萨的事,安全的感受,学校,开明的教育。白杨树沙沙作响。其他人也是。他们有新的想法和学识。他们给对方讲自己的故事。园艺设备租赁人,足部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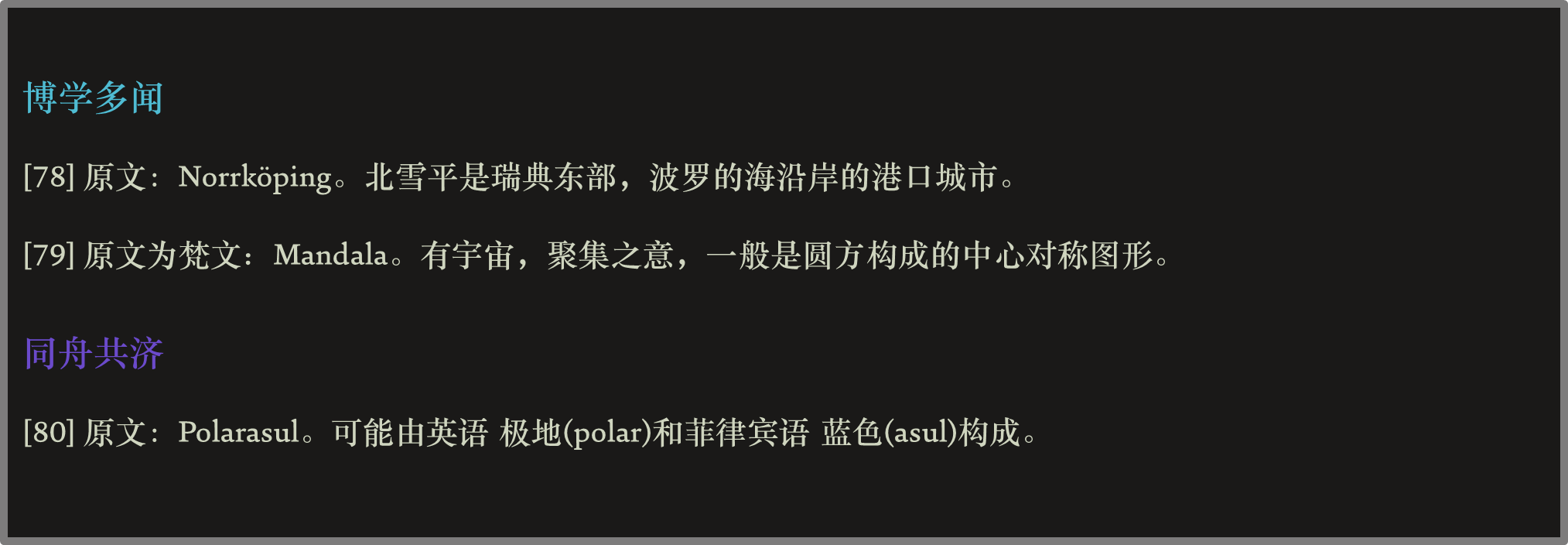
--------------------------------------------
“简短点。”特雷斯看着失踪人口处的同事在他十周年纪念日时送给他的银表。“五分钟。”他和汗,杰斯帕一起大步穿过疗养院的公园,大衣的褶皱噼啪作响。
“好,好,‘简短’”。汗落在了后面,“我很难受,我需要休息。”
杰斯帕催促道:“听着,你有很严重的心脏问题。我想我们都赞同——你应该去看医生。”
“我赞成。”特雷斯附议。栅栏后,房屋白色的窗框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光。杰斯帕麂皮鞋下的树叶沙沙作响。他看着泥土飞溅到鞋尖上,耸耸肩。腐败的甜味。等待让他倍感焦急。
“你们当地的机构应该更包容些。”特雷斯继续道,“缺乏合作精神和国际情怀。”
汗尝试继续推进话题:“你去调查了吗?”
“我去了,去了。”
“昨天?”
“不,今天早上,他们把他拖了出去。没什么我能做的了。昨天一整天我都在打电话,我不知道,就像个杂技演员。打了一百个电话。对不起。”特雷斯是个技艺精湛的撒谎大师。杰斯帕一秒也没有怀疑:“随便了,嘿,赫德说了什么?”
“他没看到她们。”
杰斯帕留意到汗长舒一口气,怀疑地皱着眉。说实话他感到有些失望。这些所有的准备。什么也没得到。啊,让葬礼派对开始吧。
“等等,等等,这不是全部。”特雷斯竖起一根手指。他戴着一双黑色皮革手套,微笑着比着手势。“赫德很贴心,给了我一个名字。迪雷克·特伦特莫勒,这就是他故事的来源。”
汗猛然停下脚步,愤怒地看着特雷斯,“他这么轻易就*给*了你一个名字,并且如实招供了一切?他*开口*了?”
杰斯帕不理解汗为什么要质疑他朋友的调查能力:“呃,毕竟你用问题击溃他了,对吗?以格拉德的方式。”他赞许地看着特雷斯,然后继续向前走。“所以迪雷克?谁来着?特伦特莫勒?”
“正是,我核实过了。都匹配得上。他们十八年前共用一间牢房。在迪雷克服刑的最后一年。他被提前释放了。这还有个转折点,待会记得提醒我。话说回来。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各自的故事激怒了对方,之后,有一天,赫德讲了个*非常*诱人的故事。迪雷克感觉自己支配了他。总之,他开始喋喋不休。他认出了一个人…等等别急!来自普里奥焦尔斯克圈。”
“得了吧!一派胡言!”汗不为所动。特雷斯不以为意。“这个男人来自那个圈——让我们先暂时假设有这样一个圈,好吧——而他算是…一个领导。真正的恶人。而且很危险。在女孩们消失的几年后,这个领导找到迪雷克,开始讲述他和朋友们是如何劫持女孩们的。顺便说一句,他们是情人,领导和迪雷克。”
“很好。”
“迪雷克不能告诉任何人任何事,不然他们就会杀了他。所以。现在迪雷克告诉了赫德,而你们无法想象这件事是多么,以赫德和迪雷克的交流方式,多么…呃…可笑的。我甚至有点高估迪雷克。以我能在喀琅施塔得的文件中找到的内容来说。一个恋童癖。调戏他姐姐的孩子,主要是在家庭内部。没什么严重的。那个女人最终把他送了进去。迪雷克是个懦夫。他告诉牧师他是多么后悔,以及某样东西是如何诱导他的。”
特雷斯讲这些的时候怀疑地甩着手,他继续道:“…而其它一切的恶魔行径都因它而起。”
树下就是养老院的后方。游廊木制边缘涂了白漆,一条石阶通向后门。年代合适的红色墙体,以及脆弱的木结构建筑,正如瓦萨过去的房屋一样,使这里的居民们回忆起青春年华。栗子树上,最后几片叶子飘落在“黄昏”的屋顶。
“现在,当然了,迪雷克已经70岁了。或者75岁,你自己可以算算。而且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被提前放走了吗?”
汗和杰斯帕并不知道为什么迪雷克·特伦特莫勒,普里奥焦尔斯克恋童癖圆环的领导者的同性情人,会从监狱里提前释放。
“他变成老糊涂了。”
“什么?就是说,在他六十岁之类的年龄?”杰斯帕了解可能罹患的并发症。
“差不多就是那样,是的。”
“完全痴呆了?”
“我不知道。那上面没写他怎么痴呆的。总之,情况恶化了。走快点,我们会看到的。”
汗跟在其他人后面,拖着脚步登上养老院的楼梯。三人站在木制拱门前。特雷斯按响了门铃。
“画…”汗手扶在膝盖上,喘着气,“赫德从哪弄到的画?”
“有点像那边的圣物。手手相传,如果咱们能找到拥有原版的男人,就能举办我们的葬礼派对了。我向你保证。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生活了。”特雷斯再次按下门铃,这次带着点怒气。“只有赫德把它公开了。普里奥焦尔斯克的领导者…”在汗的注视下,特雷斯纠正了自己,“假定存在的普里奥焦尔斯克圈的领导者把它传给了迪雷克,迪雷克向赫德展示它。在我看来赫德只是有点好奇。你知道的,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特雷斯露出邪恶的笑容。
--------------------------------------------
瓦萨在50年代和平的幸福中酣睡。冬季结束了。屋檐上的冰柱落到人行道上,在冰层上留下一个洞。白天变得越来越长,而在遥远的某处,中央学校的院子里,斯文·冯·菲尔逊在刁难一个超重的移民。是什么让他觉得,玛琳会喜欢这样伤人的谈话?哈?真的是这样吗?特雷斯站在远处院子的尽头,不敢干预。他希望杰斯帕会从看到的景象中感受到过多的痛苦。有所反应。
油毡推销员走在郊区的人行道上,他的靴子沾上了融化积雪中的盐。他一整晚都没睡,明亮的阳光和冰面上的太阳倒影刺痛着他的眼睛。他的手因咖啡而颤抖,大脑突突地跳动。紧绷的,脉动的红色神经元中继器。他们在夜间交谈的上千幅图像,如漩涡般涌入油毡推销员的脑海。他把手放进底部被剪刀裁开了一个孔的口袋。他乘坐有轨马车兜圈,每次都在法鲁下车,溜到桥下,看着柳树丛,之后在路的对面回到电车上。油毡推销员把头靠在车窗上休息。有时他会睡着,但即便那时他的想象力仍在工作,他摆出越来越奇怪的姿势,在他面前张开腿。即便在他睡着时,他也想要。但油毡推销员训练过他的神经。窗外车站的时钟敲响两次,学校放学了。油毡推销员的下巴抖动着,他苏醒了。孩子们从电车车厢涌出,在他家的车库里,排列着一卷又一卷的油毡。他现在住在这里。住在瓦萨,普里奥焦尔斯克。他走过洛韦萨郊区的街道。油毡推销员吊在扶手上。他想要蠕动。一个老妇人奇怪地看着他。和之前是同一位老妇人。前天她也在电车上。还有昨天。他再也无法承受,他得做出选择。法鲁站到了,油毡推销员下了车。他溜到桥下,憧憬地看着他的柳树丛。他再也不能忍受。水滴从柳枝上的小冰墩上滴下,油毡销售员的呼吸加热了它们。滴,滴。太阳在水坑中闪耀着,视野在柳树丛的另一端消失了。四个一排。最小的那个喋喋不休地说着话。哒,哒,哒。这是油毡推销员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他想要她们。在那之后,就结束了。他会杀死自己,把世界从油毡推销员的身下解放出来。但首先,她们。
--------------------------------------------
心脏病药的气味令人恶心。杰斯帕擦了擦脖子,焦虑地调整着毛衣领上的领带。似乎这些关节软膏以某种方式沾到了他的皮肤上。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如此拼命地延续生命。白色蕾丝窗帘系在窗户两侧,某些东西从迪雷克·特伦特莫勒房间的墙壁上爬过,把它变成一个临时病房。树枝的阴影投射在花卉墙纸上。偶尔,当机动汽车伴着嘶鸣声经过时,影子从车前灯中复生,在昏暗的灯光里滑行。桌灯是黄色的。层层叠叠的花朵和树枝彼此交错划过。死亡——极少出现在男孩谈话里的词汇,似乎根本不存在。一切只是消失和消散了。
当时机来临,杰斯帕走出门外,进入十一月的空气里。立方体房屋的灯光被留在身后,滑雪道通往城郊。积雪下,是一望无际的荒芜平原,杰斯帕越过原野,去往树墙耸立的阴暗之地。*Zigzag dröm*[81],云杉树的枝条拂过他的白色大衣。阴暗的森林,黑暗的绿色眼睛。在寒冷的空气中,女孩们的声音如银铃般响起,她们在等待…在永恒的冰川下,在百万年未有涉足的原始环境里;深入格拉德的肺部,人类禁止前往的地方。杰斯帕没把这些告诉过任何人。
迪雷克的房间,或者说,病房,杂乱地堆放着许多管子。在一个小书架上,相框里是家庭照片。发光的草坪。杰斯帕不敢去看那些照片。孩子们,侄女吗?看护人某天也会清扫这些东西吗?床的上方摆着德洛丽丝·黛的银制圣像,而迪雷克·特伦特莫勒就坐在她的下面。他双手交叉放在大腿上,肩上披着一条格子床单。脖子上的小巧银链闪耀着。挂输液袋的架子高竖在床头上。
“孩子们,我的记忆力已经衰退了…明天我就认不出你们了。这是我身上发生的最好的事。它就像一个祝福,让一些人能喜欢我。有些早上我醒来后,甚至忘了我自己的名字。我记不起我是谁了。更不用说那些事…”
特雷斯站在那里,手放到窗帘后,检查着窗框。“你看起来状态很好。”他转过身。“你从谁那得到的*画*?安妮艾琳·伦德背部的那张。谁?”
“哦亲爱的…”特伦特莫勒先生长着肝斑的脸颤抖着,看起来疲惫不堪。“我不再记得这些事了。我想要记住的那些事,我记不住。我记不得我的儿子,所以,那些事…”
“别耍我,迪雷克。”特雷斯在老人面前蹲下,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马切耶克探员刺穿了迪雷克浑浊的双眼,汗在一旁恐惧地看着。“现在听好了,你跟你的狱友聊过,*维德孔·赫德*——你怎么不说你记不得赫德?谁又能忘掉呢?你讲了…”特雷斯把手放在老人的下巴下,重新把他的脸转向自己,“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我知道你在监狱里告诉维-德-孔-赫-德你认识的某个人,二十年前从夏洛茨扎尔海滩绑架了伦德家的四个女孩。而你画了其中一个女孩的胎记草图当作证据。迪雷克,草图是吻合的!”
泪水顺着特伦特莫勒松弛的脸颊流下。
“迪雷克!嘿!草图是吻合的!”
“我画了…我去了同性恋公园。我记不清了,我不想…”德里克发出他老人的呜咽声,而特雷斯变得越来越愤怒。他的上嘴唇蜷缩在他被烟草染色的牙齿旁。迪雷克像看到鬼一样向后靠着,但特雷斯的手就放在紧急按钮上。“如果你因为记忆疾病不愿意配合,那就听好了!如今我们有一种机器。它就像冰淇淋勺,迪雷克。我会把所有我需要的从你脑子里舀出来,然后…”
“特雷斯!”汗从椅子上起身,抓住他的肩膀。
“…然后祝福就会降临!”
“特雷斯,别提那个!”杰斯帕不明白。他疑惑地看着探员威胁迪雷克,他的手放在警报按钮上。汗愤怒地推着他的肩膀。“你知道这会如何摧毁你,特雷斯,你知道的。我们需要你留在联警里,你不能被开除。我也有个想法,我们不用…”
特雷斯冷静下来。“好的,杰斯帕,关上门。”杰斯帕向外看着空荡荡的走廊,下午的养老院如此安静,就像被废弃了一样。他把门拉上。心脏在胸腔里激烈跳动,男人背靠门把手平复着,紧张地揉捏他的金发。房间里的空气沉重,杰斯帕看见床上的老人在瑟瑟发抖。他用手捂住脸,躲避着特雷斯。
“油毡推销员。”联合警探蹦出一个词。
男人抬起眉毛,布满皱纹的悲伤眼睛睁大了:“谁?”
“油毡推销员,你的男朋友。他画的画。是他告诉你男孩的事。他是谁?谁,迪雷克!?”
“他只是…他那时只是。”迪雷克不再哭泣了。泪水在他的脸颊上风干,老人如同被闪电击中般瘫倒在阳光下“只是个油毡推销员。他们都是。那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很专业。”一声疲惫的叹息从他的嘴里飘出,“哦主啊,帮帮我…”
房间里很安静。孤独的摩托车轰鸣声从窗外传来,树影掠过杰斯帕,落在门对面。汗悄悄把特雷斯推到一旁。“做的很棒,迪雷克。现在这样多好。”他用杏仁眼眸看着毯子下的老人,“你会帮我们找到这些女孩,不是吗。”
“两个地方。”特雷斯对汗耳语。
“两个地方。迪雷克。告诉我们这个男人去过的两个地方。他住在哪儿,哪个地区,你知道吗?”
“普里奥焦尔斯克。他们都住在普里奥焦尔斯克。”
“很好,棒极了。现在说另一个。想想,迪雷克,想想油毡推销员刻下的其他地方。帮我们找到女孩们。他还去过哪儿?”
“他那时在看着她们…在沙滩上,从一个酒店里。”
“海天使?”特雷斯焦急地在窗下踱着步。
“我记不清了,求求你…”
“有了。”特雷斯点点头,向门口踏出两步,“海天使,我们出发!”

--------------------------------------------
十八年前。维德孔·赫德坐在隔间角落的自制书桌前,老派背头上的一缕头发贴在前额上——现在你仍可称之为“经典”。维德孔这时还年轻。相对的。前额还没布满皱纹,脸颊塌陷为北陆斗牛犬样子的进程才刚开始。桌子上放着成堆的手稿。未来主义哲学,历史学家,优生学家的通用理论。它解释了世间的一切,这是他留给人类的遗产。
“维德孔·赫德:‘维德孔·赫德’”的粗体字写在纸板封面上,两张改装床靠在墙边,日光从小窗户里渗进天花板。
迪雷克·特伦特莫勒躺在床上。老态龙钟。不知为何心烦意乱。他拿起脖子上的银色项链,看了一会儿,随后爆发出大笑。“哦,你会喜欢它的!我认为它其中甚至有确凿的超人性。有时是冒险和科学,而那些的所有,毫无疑问,超越了善恶。”
多么美好的灵魂蜜月!迪雷克讲述而维德孔记录。会意地点着头。请求暂停一会儿,然后更换墨池。窗口的光束爬过地板,蔓延至铁门。天色渐晚,维德孔打开了台灯。他把一张纸举到空中对着它吹气。
美好的时光,美好的时光。
迪雷克在房间里伸了个懒腰,俯身靠近维德孔:“你知道他接下来说了什么吗?油毡推销员。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她们做了‘出色的手术’。他‘把她们拼接在一起’。最小的那个死了,其他的存活了下来。你明白吗,差不多是这样。”
--------------------------------------------
油毡推销员。油毡推销员。油毡推销员伸手去拿厕纸。海边咸湿的空气从海天使的阳台渗进房间里。芦苇席上摆放着一个望远镜。一个特殊的相机连接着望远镜。之后,他在外面四处游荡。
他在候车亭阅读时刻表,但最后一班列车已经启程前往市区。女孩们在车上。夏天的傍晚气温宜人,男人的心也因此变得柔软。他脱下凉鞋。他光着脚走在温暖的沥青路上。沥青路轻薄易碎,列车轨道冰凉。夏洛茨扎尔沉在傍晚中。他深爱着它。他深爱着女孩们。他深爱着海滩,那个抹除所有意义的地方。他恋爱了。“它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极光在极地冰盖上扭曲时,他这样想。绿色房檐下有一对情侣。窗外下着雪。它从没发生在油毡推销员的身上。但他爱着沙滩。还有女孩们。尤其是那一个。特别是那一个。其他的也爱。
赤脚下是沙子,脚趾间也是。白天很温暖。之后则变得潮湿。花园里传来音乐声,房屋的灯光在远方的松树间闪耀。更远处,岩石悬崖下,在没人能看见的地方。他赤脚下的冰凉岩石因为水流变得湿滑。他的鞋去哪了?他记不清了。他走在岩崖下,石头间,海浪拍打在他的裤子上。轻柔的黑暗。他跪在地上大笑起来。松树沙沙作响。游泳!他走进岩石间的海水里,没有人看到他是多么得快乐。裤子打湿了,他滑倒撞伤了膝盖。那又如何!海水漆黑而温暖,天空中星光璀璨。
--------------------------------------------
“去德律风根!”杰斯帕打了个响指。“我认识那儿的人。离这儿不远。在那儿你想打多少个电话都行,特雷斯。尽情施展你的魔法。”他举起手,三人想要在洛韦萨郊区唯一的主干道上叫出租车。汽车呼啸而过。马路的另一端升起一堵树墙,傍晚的车流稀疏。“现在是九点半,我们还来得及。”
汗跟在后面。“我不知道…火急火燎有什么意义。我们来谈谈吧。”
“没什么好谈的,我们要打几个电话,今晚我们就要自由飞翔了。”杰斯帕身旁,特雷斯同样焦急,即使在未亮起黄灯的出租车经过时,他也高举着手。“我们还在等什么?你还没厌倦等待吗?”
“没错,而且我不在乎。”杰斯帕单脚跳着说。经过的车辆溅脏他的衣服。“如果你认为我拼命地想知道那是多么糟糕,多么*毁灭性*——太情绪化了,汗——机器,你,特雷斯,用的,我其实不感兴趣。你去完成你的工作,而且没时间了。三天内是找到某人的好时机,尤其是孩子,活的,机率每天都会减半。百分百,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二十五,汗。你会怎么做?”
“那不重要!去他的!”头顶的雨慢慢转为晚秋的雨夹雪。车轮下的水花扫过汗。“你和你的出租车,停止就在眼前!你不明白,杰斯帕,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它会给我们造成什么影响!该死的麦斯卡林…麦角酸…”
“来了!停车!”杰斯帕向停靠在路边的出租车跑去,回头喊道:“所以你会用好警察策略的,对吧?”
“说实话,已经够了…”特雷斯在出租车里靠窗的位置抱怨。
汗侧身滑进客厢,喘着气。“你看,杰斯帕…你不明白这个东西其实是…*违法*的。在所有签署了声明的国家都是…顺便提醒一句,这里就是属于联合刑警的国家[82]…呃…”
“管辖权。”前排的特雷斯终结了汗的语句,对司机说:“去德律风根。”
一段时间里,车里很安静。引擎发动了。冰雨在轮胎下唰唰作响。杰斯帕想寻找一个论点,但特雷斯击败了他。“是的,我在赫德身上用了那个机器。我的决定。他永远—*永远*—不会告诉我们任何事。他只会坐在那里,得意地大笑。他会跟我讲两个小时混血吉卜赛人和黑人。这就是原因。”
“但是特雷斯。”汗的语气带着哭腔,“他们会炒了你!”
“在我的掌控中。你猜怎么着?我不想再谈论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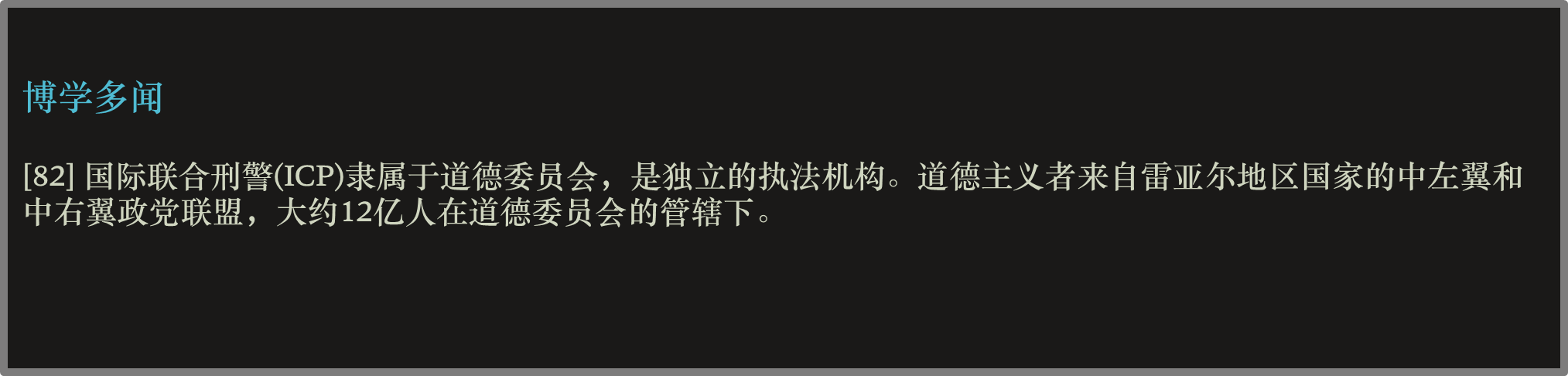
--------------------------------------------
第二天,油毡推销员的长远的目光在夏季温暖的大雨中闪耀。在他调试三脚架时画面随之抖动,然后静止——锐利,干净。油毡推销员耳边的雨沙沙作响。云层被太阳照亮,雨水落在酒店阳台上。潮湿的海滩边缘一半以上被芦苇覆盖,延申至远方。下方的沙滩也雨声大作,但在他脑海里,他听到的是雨滴落在阳伞上的轻快鼓点。望远镜的眼睛里,是一个小小的红色花朵图案的遮阳伞。它立在悬崖上,几乎在千米之外,但油毡推销员的手伸到雨中,触碰着它。“走开,小胖子。”他说道。油毡推销员从城里买了一本女性杂志。封面上是穿着时髦的安-玛格丽特·伦德,一个从政的女人。杂志里还有一些照片。在她的漂亮公寓里的安-玛格丽特。她与她的四个女儿坐在咖啡色沙发上。照片下方是一排名字和年龄。
安妮-艾琳…
他第一次见到她们的那天想出了怎样的故事。恐怖的东西。他将如何安置她们。油毡推销员是一名医生,他是医生。油毡推销员医生。他会像这样将她们启动。她们向他走来。而他对此仍不满足。他的神经是如何低哼着,无比饥饿,那些神经想把她们生吞下去。随后一切又是如何消退的。当他来到这里时。多好的地方!她们在两个面对面的列车座椅上聊天。他在她们后面。油毡推销员闻到了她们纯洁,纯洁的头发的味道。马匹小跑着,列车驶下山坡。是沙滩来找他,而不是相反的方式。而她们四个带领他去往那里。沥青路面上扬起尘土,芦苇摇曳,蓝天上,太阳放射出苍白的光。它不像那些其他的沙滩,阿尔达或是瓦萨周边,奥斯特姆的,它们让油毡销售员大汗淋漓。他在令人作呕的松弛身体间蜿蜒前行,目光追随着一只皱巴巴的小狗。这里不是耶林卡游泳池,那里的氯让油毡推销员的眼睛发红,他不得不等待两个小时才能离开泳池。
清风撩起着他的头发。浩瀚广袤的存在!世界都能容纳在其中。微风吹拂;他订下了最高的旅馆房间,这样风才能吹进,让油毡推销员冷静下来。他不敢走下沙滩,只是温柔地注视着她们。在她们身边。仅仅是触碰她们,他也会化为灰烬。他拍摄照片。光子跃迁,晒伤女孩后背的那束光从她细小的胎记上弹跳开,蚀刻在漆黑的负片上。白色的光点如同夜晚的明星。记忆的快门速度。他做了一根亚麻绳,一个绳套,然后自慰。这是最后一次。他的呼吸颤动床单,油毡推销员随着精液一起,从他身体里出来了。不见了。
油毡推销员的记忆和他看见的一切,都在一天天消退。雨滴在雨伞上敲打出鼓点,安妮艾琳把小手伸到雨中叮当作响的钢琴上。今天,当他醒来时,他忘记了油毡推销员。照相馆里,在她们拍摄家庭照片的时候,只有一丝的油毡推销员来到了他的脑海里。安妮在雨中摇晃着她白色的头,小辫子垂在背上。只有他透过望远镜温柔地注视着她。
--------------------------------------------
二十年零两个月之前,几千公里之外,在冬季轨道的另一边,“罗季奥诺夫”号气象调查船被困在了浮冰里。现在是极夜的十二点半。聚光灯在北海海峡上分散开,船员面前是一幅冰冷的景象。穿着皮大衣的人们聚集在甲板上,毛皮帽子旁是竖起的银灰色衣领。船员处于恐慌中。在黑暗似乎略微变厚,距离无限延伸到远方,却毫无地平线的迹象之处,就是灰域开始的地方。船员们感知到且恐惧着,尽管没人能在夜晚看到百米之外的地方。调查船的天线单元发射着绝望的求救信号和科研读数。这个无线电信号传输到卡特拉大陆,格拉德州的中继站,就像在曲面镜里一样,被诡异地扭曲了:“*区域-轨道-区域,区域-轨道-区域*…”
冰面的边缘弯折到灰域下的天空,咔嚓声传来。抹除一切的狂风像倒放且慢放十倍的音乐。灰域迫近着——一场世界记忆的崩溃——以鲁莽的速度埋葬着物质。浩瀚无垠的星空中,星星一个接一个被它的滚刷抹除。
在轨道上,通讯卫星“圣像”见证了灰域是如何一挥手,就消除了整个卡特拉洲北海海峡的。它还吞没了覆盖在萨马拉南部的岩漠萨马斯特,以及蒙迪大陆苏帕穆迪斯的二分之一。灰域在循环,弯曲,聚集,对抗着物质。黑洞吞噬了循环的眼睛。“方位角”在平流层边缘校准了测量工具。现在熵灾直接影响的区域包括列敏凯宁[83],萨马拉针叶林东北部的奈德-乌麦生态区,格拉德的叶科卡塔[84],北地群岛[85]的高原灌溉网络区。遥远的,抛弃了生命的物质世界角落。现在是70年代初,9月29日,两天前的晚上是同学聚会。现在则是世界末日。
两小时前,在德律风根的全景餐厅里,马切耶克把电话放在餐桌上,指示海天使酒店的秘书朗读52年6月到7月间*全部*的客人名单。桌子上摆满了食物。半个美味的蟹钳靠在电话上。汗喜欢美味的螃蟹,杰斯帕在向他说明如何从蟹腿中吸出蟹肉和汤汁。
“吸,吸。”杰斯帕说,指了指侍者示意收走盘子。今晚,晚餐是杰斯帕的风格。杰斯帕请客。而杰斯帕热爱美食。米饭和通心粉可满足不了他。
汗吮吸着。“呃,我不知道,它当然更好,但如果你把*饺子*放进米饭和通心粉里…”
杰斯帕啜饮着冰水。“特雷斯,听我说,我可以自己去普里奥焦尔斯克。我在那儿为一个儿科医生设计过住宅,认识了一个开发商。我觉得他应该有渠道联系他曾经…”
“人口登记簿。”特雷斯说。他的肩膀因为痛苦而颤抖。但这里的南格拉德红酒极好,他很想来一口。随后他必须把电话放回肩膀上。酒店秘书已经挂了一次电话。但随后特雷斯打给了行政部门,要求告知对方:“四个小女孩的生命由你的良知决定。”这句话起作用了。
汗从酒杯旁端起一个笔记本,打开,纸上写着超过两千个人名。
“已经一半了,夫人。就剩两千多个了。”他的头晃动着,拉尔、伯格、阿克在他眼中如列车灯般闪过。
“那好吧。”杰斯帕骄傲地展开餐巾,擦了擦嘴。“已经十一点半了。再过一个半小时,餐厅就该关门了。我可以协商一下再延两个半小时。所以,我们开始吧,我来负责人口登记簿。”
侍者将另一个电话放在桌子上。其他客人带着克制的兴趣看着三人组的饭菜。一个瘦削的克吉克已经持续两个小时单调地朗读人名,还把它们写在笔记本里。一个黄棕混血,穿着珀修斯·布莱克双层折领衬衫的人举着眼镜,敲碎蟹钳,然后向对桌的一个阿姨挥手致意。特雷斯的笔记被此举搞得乱七八糟。“汗,嗯,你的任务可不是最难的。所以请把它做好!”
“特雷斯,听着,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用这个记事本。”
“不行,它必须记在笔记本里。”
“为什么非要用笔记本?”
“迪雷克·特伦特莫勒。”特雷斯以一贯的机械嗓音朗读道,随后睁大眼睛看向汗,“迪雷克·特伦特莫勒?哈喽!你确定吗?他那栏备注什么了吗?”
“度假。”
“还有呢?”
“油毡推销员。”线路的另一端,酒店秘书用疲惫的嗓音说道。“迪雷克他妈的特伦特莫勒,6月17日-24日,油毡推销员。”
杰斯帕的重拳砸在他五年前设计的餐桌上。
汗把蟹钳放到盘子里。“现在轮到ZA/UM出场了。”
迪雷克·特伦特莫勒梦到了一个油毡推销员。油毡推销员所见的一切在他眼前旋转,像一团均匀的血肉和黑暗。有时他会醒来。他无法入睡。之后旋转的血肉和黑暗回去了,迪雷克睡着了。在他的梦里,他和油毡推销员是情人。他是另一个人。一声咔嚓,从上升着的无形记忆中穿过。木窗裂开了。玻璃在窗框里嘎嘎作响。然后是一声闷响,迪雷克醒了。
死神。这一定是死神。华丽的墙纸上装点着深棕色的花朵。树影摇曳,窗帘在风中飘荡。没错,这和迪雷克一直设想的场景一模一样。一个穿着鱼尾大衣,高大瘦削的身形,在敞开的窗户前出现。他们还有更多!肥胖的死神砰地一声从窗台上落下,低声道:“好,进来了。保持警戒。”
高个死神来到床边切断了警报按钮的连接。胖死神打开台灯走到特雷斯身旁,温柔地把手放在他的头发上。他大大的深棕色眼睛看起来似曾相识。“迪雷克,别反抗。我们现在需要你身上的一些东西。我们需要你去回忆,因此我们要给你稍微注射一下。不会痛苦的,它就像一场梦。”
迪雷克听到手提箱的咔哒声,随后高个死神带着手套的手捂在了他的嘴上。奇怪的味道,一切都消退了,温柔的深棕色眼睛注视着他。
“但万一他真的记不起来了呢?那时它怎么工作?”
“我们拭目以待。”
迪雷克·特伦特莫勒在特雷斯面前敞开。现在水边的人变成了特雷斯。涉水而过的老虎。他一直在那里,潜伏着。无论迪雷克停在哪里,老虎都会在附近徘徊,嗅闻并搜寻油毡推销员。在北雪平,在阿尔达峡湾镇,在磁悬浮列车上,在耶林卡极地定居点,他紧随其后,在油毡推销员所到之处的黑暗角落里,他的眼睛闪烁着磷光。他在一个天花板低矮的混凝土墙地下室里, 油毡推销员正对着他的侄女做鬼脸。当他终于到达瓦萨后,老虎就在车站等待,坐在月台的尽头舔舐着它的爪子;就在灯笼的光芒无法触及的地方。他在公园的桤木林中窸窣作响,让油毡销售员大吃一惊。在春天的早晨,他走在洛韦萨的街上,口袋里有个剪刀剪的洞,人们可以短暂地一窥老虎的内心。学校的操场进入视线,而一场争斗,正发生在两个男孩之间。

Hotel Havsänglar- Aleksander Rostov
当油毡推销员来到夏洛茨扎尔,特雷斯在那里御风而行,他是一只猛禽,持续监视着。他拥有鹰的眼睛,一切尽收眼底。直到一天下午,他发现油毡推销员消失在海天使酒店的顶层。一半的人离开了。一天又一天,油毡推销员的存在早已被忘却。直到最后,那里只剩下衰老腐朽的迪雷克·特伦特莫勒。
“油毡,油毡,油毡…”他喃喃低语,“真的存在‘油毡’这个词吗?”一种奇怪的,诡异的失去感。但他思念的并不是油毡。油毡推销员哀悼着自己,有时会想起自己,设想他从未消失的生活。他嘴里吐出恶心的语句,阅读维德孔·赫德的回忆录。他独自幻想。而迪雷克·特伦特莫勒思念着截然不同的事物。
这是二十年前,8月29日,他感觉很糟糕。出事了,他整晚睡不着。晨报躺在浴室地板上。教育部长的四个女儿失踪了。迪雷克·特伦特莫勒感到无法呼吸,世界每况愈下,时间在失控脱节。在红色灯泡的红光下,业余摄影师在阳台上展览他的照片。他双手颤抖着,他确信她们就在那儿。确信。但在晾衣绳上,晾衣夹下的照片排成一行,它们全都充斥着*真空恐惧*。虚无。
漂浮在显影盘中的光面纸上出现岩石峭壁的轮廓。苍白的夏日天空。但不是她们。
汗和杰斯帕搀着几乎无意识的特雷斯坐进出租车里。他的鞋拖在地板上,不停颤抖着。杰斯帕的声音从凸面镜中传来。杰斯帕…杰斯帕还是个酷哥们。
“特雷斯,特雷斯!保持清醒。我们该拿你怎么办?”
“不是他做的。不是他做的。”
“好,但是我们现在该拿你怎么办?带你去医院?特雷斯!”
特雷斯的声音细不可闻:“我们现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我们应该把你送到医院还是让你睡过去?”
特雷斯尝试撑起身。“不,你不明白。死局。我很抱歉…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
他们把他塞进出租车里,汗按低特雷斯的头。“先等等,老虎。你要先睡过去。之后就是我的回合。我有个计划。”
特雷斯晕了过去。一切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