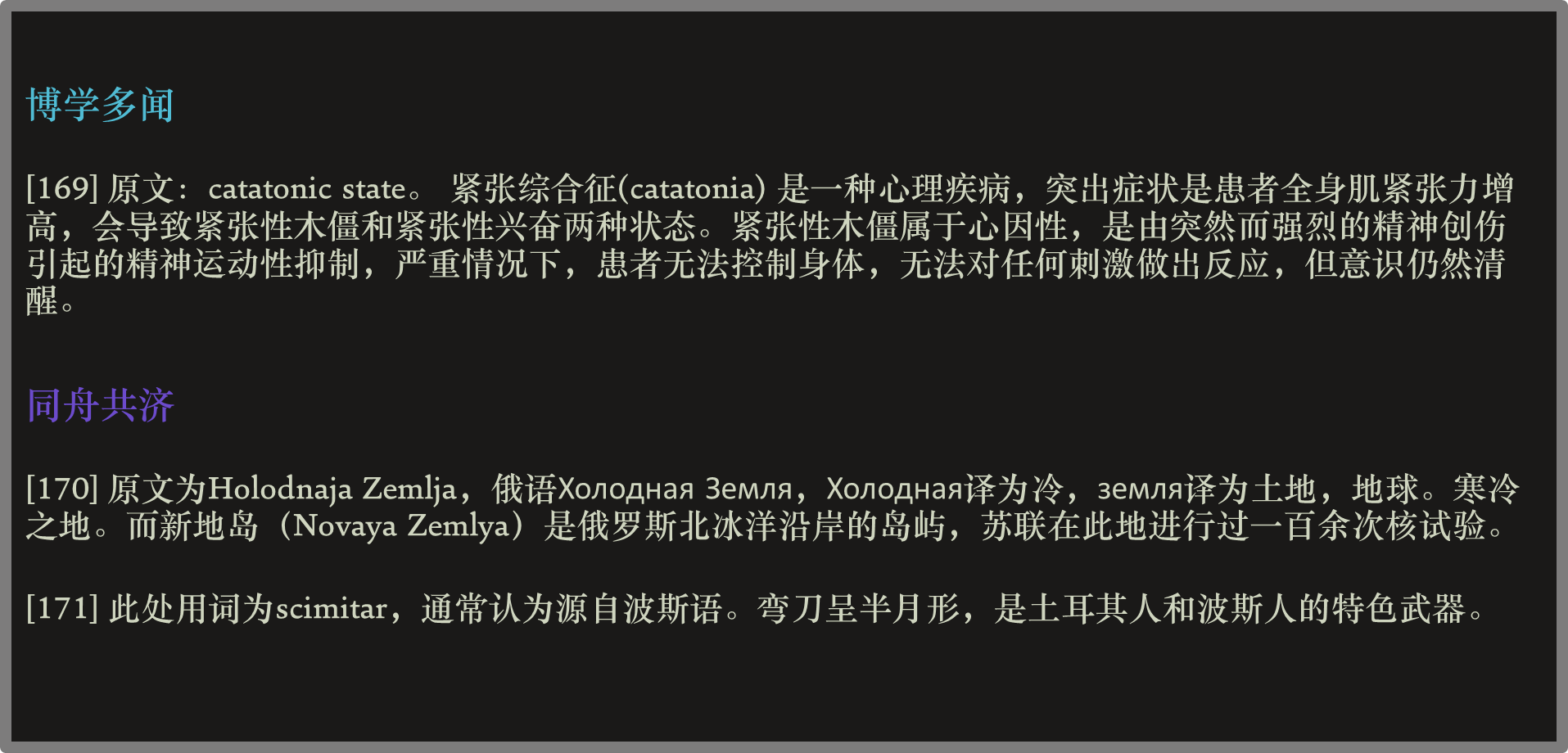迪雷克·特伦特默勒躺在床上,正处于紧张性木僵状态[169]。他周围的养老院都被静音了。他记不得任何事物的名字,也没有任何一个联系对他有意义。一切都被遗忘。他带着孩童般幸福的印记看着整个世界。两个月后,一名看护师来到他的房间,在门口解脱地长舒一口气。他从老人的手腕上拆下插管。外面,一辆载客车从积雪覆盖的街道上飞驰而过,树干上的蕾丝在墙壁上滑动。
车轮在雪地上嘎嘎作响,在建筑内温暖的沙龙里,一位著名的极简主义者兼聋人音乐评论家,杰斯帕工作室时期的同事,奥勒·阿克伦德,在四处游荡。他的前途似乎并不光明。如果没有新专辑问世,继续复制西方的专辑评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奥勒·阿克伦德吸食了大量的可卡因,而据我们所知,那会让人变得异常聪慧。如今的社交天象不同于往日,但这类消费却保留了下来。这意味着仍然存在打广告的空间。奥勒·阿克伦德为瓦萨一家举世闻名的创意实验室的前身奠定了基础,一家生产广告*创意*,而非真正广告的广告公司。之后别人会把它们做出来的。几个月后,一个末日广告宣传的杰作会从创意实验室诞生。北陆诸国的境况相同,运输业巨头ZAMM发起了一场以“逃吧!现在还不晚。”为口号的洲际竞赛。
在那段时间里,或是稍晚一些,冬至前后,康拉德·盖斯勒的新纪录片将在更广泛的公众中沉寂下去。冬季来临,漫长而黑暗,惊慌失措的群众需要更轻松的娱乐。导演是八次奥斯卡·佐恩候选人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但随后,梅斯克联合侵略者把它的舰队带出了灰域,越过北方高原驶向更远的北方。在在格拉德的冷地岛[170],舰艇的黑烟升到天空中,飘荡在极光下。阿尔达,瓦萨和苏鲁加入了两个月前向梅斯克宣战的格拉德阵营。于是,卡特拉,世界的边疆之地,被包夹在离心机中。
电影《维德孔·赫德:“维德孔·赫德”》的观众数量正在增加。然而,令康拉德·盖斯勒倍感失望的是,当他在电影院播放他那富有争议的项目时,看到的正是他最害怕的那群观众。糟糕的日子为不满的情绪赋予民族主义色彩,那里坐着与年迈的纳粹祖父一同前来的,聚精会神的青年军人。他们中没有一个理解盖斯勒微妙的隐喻,他的讽刺,他的荒谬感。愚蠢的战士们认真地欣赏着赫德黑衬衫的姿态,不含一丝讽刺的意味。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那位伟人最终崩塌在他自己的超级人类格言下。他在最后一次采访时的胡说八道似乎对他们来说很有诗意。牢房里的镜头,像菜叶一样的赫德感动得他们潸然泪下。最终,电影证明了即使是他,和他的传奇英雄想法也无法在古老的真相中存活。它们过于诚恳,过于真实了。作为一个战士,赫德将自己推到了极限,不向稀释文化影响屈服。那是他的胜利、狂妄和垮台:真理——它实在太强大了。
这不过是无数世界末日的荒谬之一,但这个让斯文·冯·菲尔逊思考,是时候出柜了。斯文正在逐步淘汰诙谐的管理学文章,取而代之的是“支持政府和武装部队的声明”。之后,当格拉德和它的北方盟友发现,它们站在了世界大战失败的一边时,只有在伊尔玛组织起了真正的交锋。斯文·冯·菲尔逊不想要骆驼屎伸出的援手:“在你发觉之前,他们会在你背后用弯刀[171]捅你一刀。”
但最终,法西斯主义在社会的边缘留存了下来,那是它一直存在的地方,在神秘动物学和灵能学之间。公共生活的主要群众与斯文·冯·菲尔逊不同。他们的北方风情太明确了,而极端无法获得共鸣。编辑用精细的手法从这些著作中剔除了种族敏感词汇。他们不能不让它们出版——那将违背言论自由。因此,灰域中的这片土地与剩下的世界一起,进入了地缘政治的末日阶段,不过并非崩溃,仅仅是疏远。仍然是社会民主主义。他们仍在慷慨地援助那些什么都没做的人。巡洋舰在北海的炮火中消亡,但是,失业的艺术家仍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其领域的再培训机会。格拉德北方的北部平原失守了,杰林卡在持续三个月的极夜里燃烧,无人生还,但是失业的普通人乔纳斯仍在对他写的那本书夸夸其谈。格拉德放弃了微不足道的卡特拉战区,集中力量保卫他们家乡的大陆,通往阿尔达的大路已向侵略者敞开,战线一天比一天接近,但仍然没有关于普通人乔纳斯的书的讨论。因此,尽管极端分子极力反对,瓦萨连同它的三年带薪陪产假,以及无可挑剔的公共交通,还是隐退到了历史的幕帘后。
似乎也没有什么能阻止那里富有生态良知的未来项目。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当灰域朝着瓦萨的方向爬过大洋时,反光污染游说团体的美梦成真了。工业和金融建筑在最后一个工作日关闭了它们的人工照明,路灯装配了特殊的过滤器。瓦萨,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大都市,完全消除了光污染。这不仅是应对空袭的措施,还挽救了可能会迷失在城市灯光迷宫中的鸟类,以及因白天太长而被打乱交配节奏的海豹。你或许会因此发笑,但在夜晚,远方广阔的世界成为血泊漩涡时,瓦萨的家庭们走出家门来到街上,不以为然。只有远处的爆炸惊扰了冬夜深深的平静和它完美的星空。所有人都仰着头,看向上空。
在塞勒姆,汗年迈的母亲也在观看。她的眼睛涂抹了彩虹色的漆黑,就像他们在伊尔玛做的那样。一条金色的头巾遮住了她的头发。天气很寒冷,女人呼出的蒸汽穿过木制城市的街道。距阿莉雅·汗最后见到她儿子的那个晚上,已过了四年。没过多久——不超过一个月——他打电话跟他的母亲道别。家庭们在附近散步,其中包括服役年龄的男性。伊纳亚特说他不会回来了,而来自北方战线的他们,却一直在返回。士兵们。不知为何,战争也被忽视了。这全都是一种停滞,一种投降,但它反映出的异常却也与道德主义精确关联,一场同样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子细胞的运动。它听起来就像:“在一段时间里,人类似乎还有希望。”
之后,当头顶的星星在降下的毁灭中扭曲时,很多人将不再能严肃地对待“世界末日”的口号。恐慌被平息了。在疏散的怪异冷漠中,整个家庭都留在了后方的瓦萨。在那里,在私人住宅中,在宽敞的公寓里,他们玩着桌游。他们喜欢富含维他命的食物。之后,只剩几天灰域就要到来时,那里一直在举办纪念这个时刻的美妙活动。水果发霉了。霉菌在水果里病态地肆意生长。孩子们听到桌子上的橘子在咔咔作响。孢子在果肉中发芽,苹果因它们而长毛。如果你尝试触碰它们,它们就会咔嚓一声裂开。没人知道它们为什么会这样。但只有少数人因此对那个时代感到害怕,而这就是我说它美丽的原因。
汗的母亲就是决定在灰域降临时留在瓦萨后方的众人之一。也有很多人逃走了。他们逃向阿尔达,靠近前线,远离灰域的地方。在冬季轨道内,安妮塔·伦德奎斯特带着她那双精致的手,前往弹药厂打磨弹药筒。在最后的几年里,尤其是疏散之后,内衣模特似乎极为强大。所有那些让女孩在正常运转的世界中成为模特的轻松乐趣和生活之乐,在世界末日时完全转化成另一种东西。这是领导力,而安妮塔·伦德奎斯特是难民营的女王。当奥勒·阿克伦德在那里遇到她时,他完全没有认出来。这位女武神是谁?但随后安妮塔来到他面前,叫出他的名字,并带来一些药物缓解阿克伦德的戒断症状。世界著名的极简主义者兼失聪的音乐评论家十分感激。他向她讲述了一个不再运作的国际药物生意。以及关于黑色钞票IIR[172]——洲际雷亚尔——是如何贬值的,还有世界经济的崩溃。最后,阿克伦德告诉她*反世界*的事情——他来难民营的旅途中经历的一切。他是步行来到阿尔达的。男人错过了疏散,花了两个月穿越冰冻的峡湾。他孤身一人穿过遗弃的鬼镇,灰域就跟在他身后。他艰难地走过永冻土,周围是沉入沙堆下,被击落的飞艇残骸。阿克伦德还说起那匹为他拉雪橇,最终被他吃掉的马。而安妮塔告诉他杰斯帕的事。她只讲了好的那些。
安妮塔工作的工厂是一处战略资源。尽管它深藏在峡湾里,近期发射的梅斯克侦察卫星“马赛克”还是在那里找到了它。联合侵略者用炸弹雨抹平了军工厂,而内衣模特消失在战争的风雨飘摇中。这是汗,杰斯帕和特雷斯驾车离开的那个暴风雪之夜后的第六年。
在卡特拉的东海岸,物质的敌人,伟大的转变埋葬了曾经的大陆。那里曾经是瓦萨和夏洛茨扎尔海滩。如今,没人离开那里,尽管那些留在后面的人——朋友和家庭成员——在营地里不断期待着。那里的某处,安-玛格丽特·伦德坐在她的厨房里,在灰域中,她的房间安静而整洁。前教师穿着米色的夹克和及膝短裙,看着杏子上的霉菌。如果说她在此期间从未惊慌过,可能太过了。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她不知道在这个对当下的感知正慢慢飘走的长期滞留之地该做些什么。但当其他人溶解在他们的记忆中时,她只是消失了。她的生命似乎从未存在过。过往并没在等她回归。她在房间里闲逛,调整奶奶的蕾丝花边和床罩,重新把窗帘按到轨道上。就这样,优雅地,她拒绝屈服于随着世界解体而造访人类灵魂的狂喜。没有什么能从她的掌控中离开,什么都没有返回。当卡特拉大陆最终沉入灰域时,安-玛格丽特·伦德变成了一团不含一丝欢愉的蛋白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