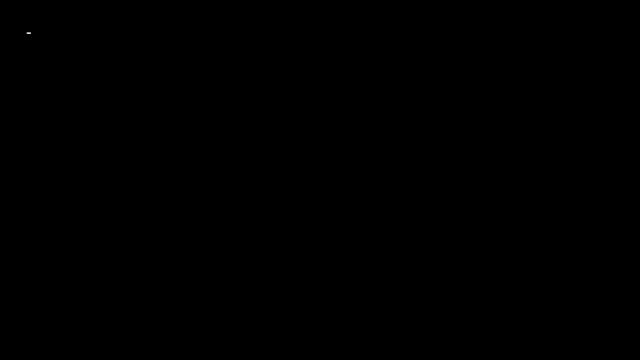
各位旅行者,請檢查飛船後視鏡和核動閥門,調整電臺音樂頻率。前方即將降落於土星野餐旅館:全息玫瑰碎片HologramRo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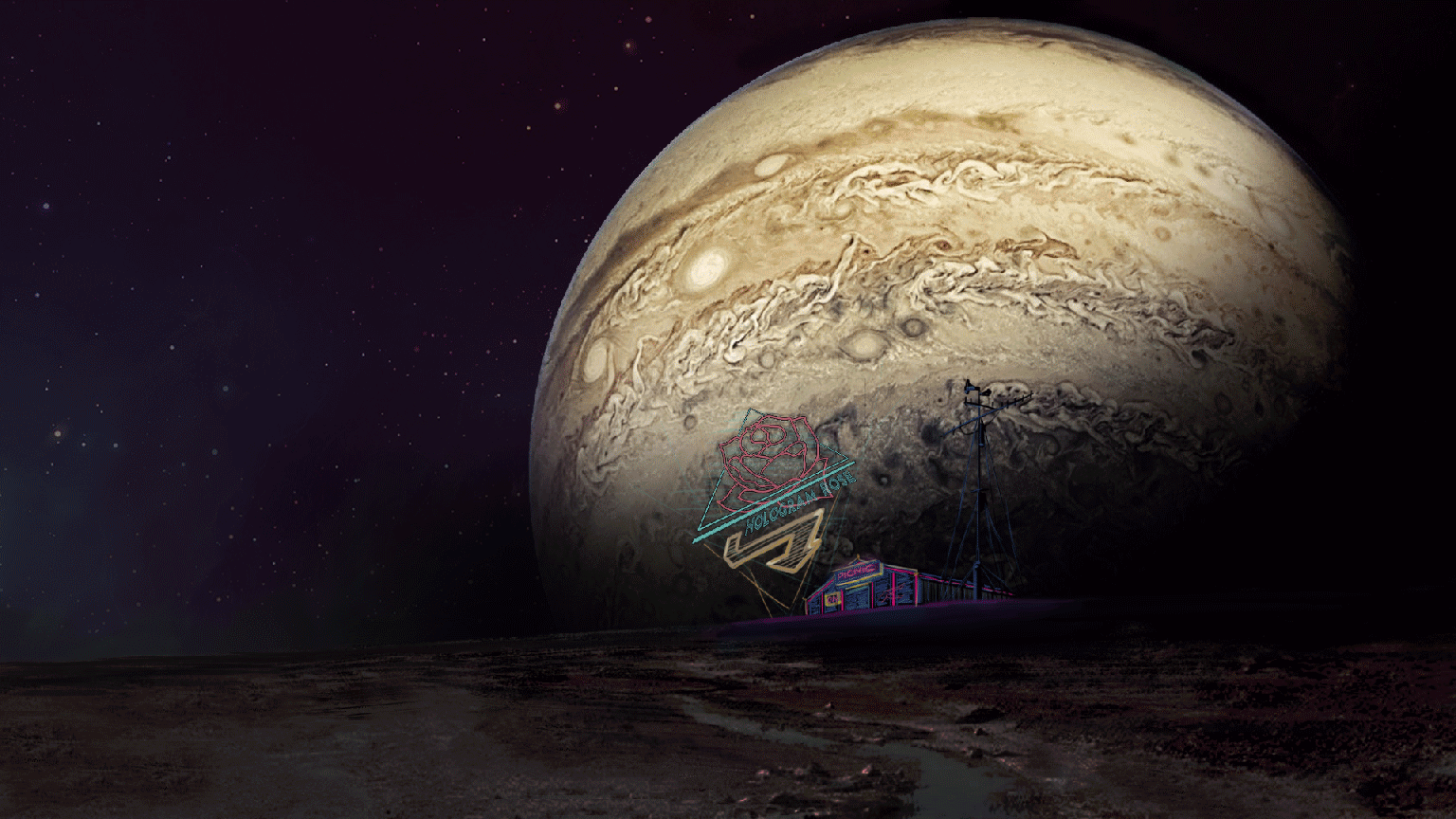
「全息玫瑰碎片HologramRose」:一個寫作團體,由一些玩家和遊戲作者共同成立。我們希望一起做一些硬核又有趣的事兒。在瘋狂的宇宙裡,希望有片刻能打動你——每一位旅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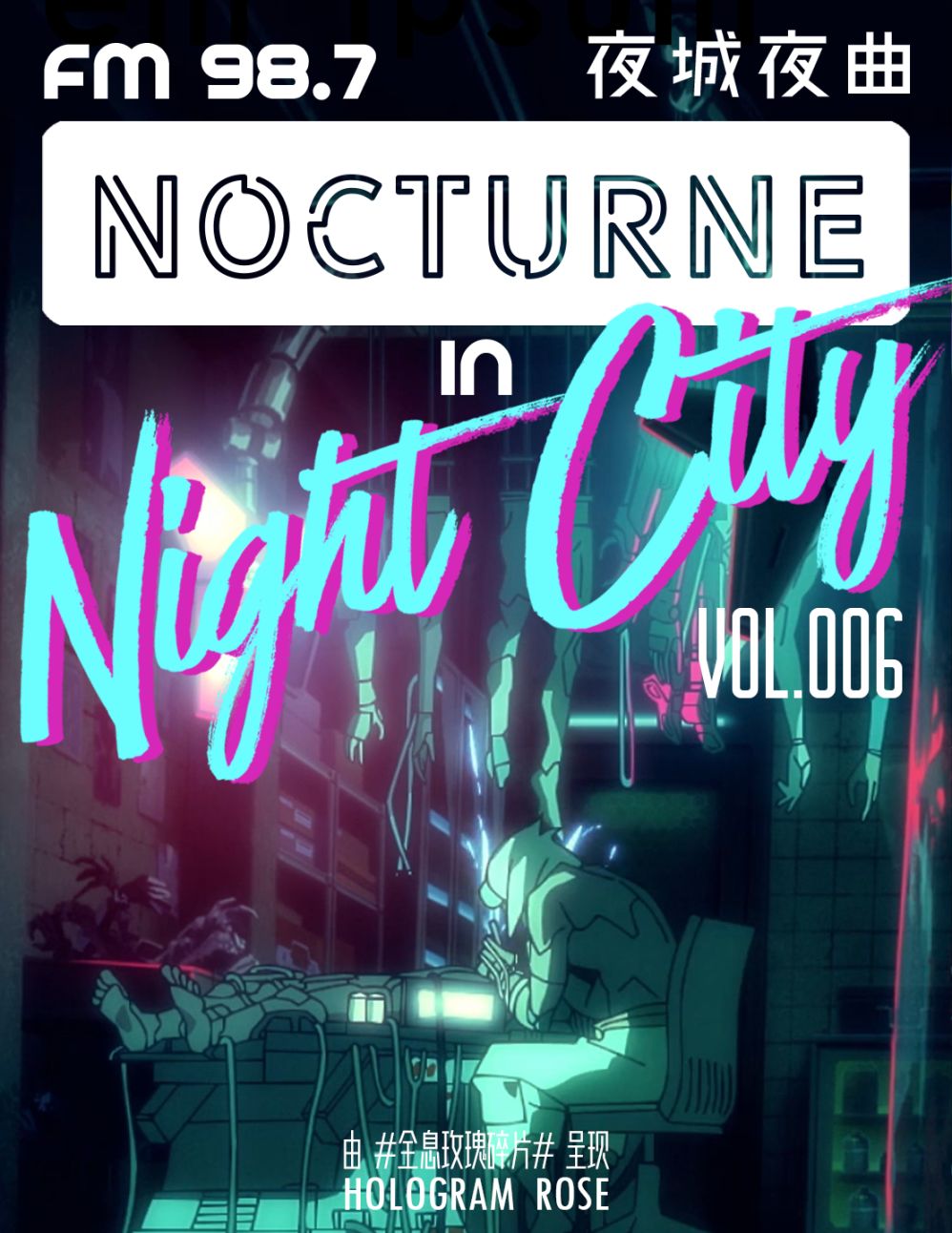

安盯著這片鏡像看得出了神。握持在他戴著白色橡膠手套手中的熱熔手術刀,刀面映照出他戴著醫用口罩、眼神暗淡的模樣。
“安...安......”一聲聲關於他名字的呼喚聲彷彿從遠處傳來,那種感覺...由遠至近,由慢到快,由模糊到清晰。好像你剛聽到它們時,還在遙遠的某處,而有意識去嘗試捕捉它的來源與方向時,那個聲音瞬間就會打到你腦門上,然後才突然反應過來,自己剛才在發呆。
安抬起頭看著在他對面同樣戴著醫用口罩的菲利普·門羅。
“你又在發呆了。”菲利普用極具疲憊感的眼睛盯著安,沒有一絲情感地說出這句話。
安望向四周。
熒光燈在菲利普身後的牆壁上發出微弱的亮光,飛蛾、蚊蟲們還在瘋狂朝著燈管上衝撞、拍打,發出一下又一下叮嚀似的“叮叮”聲。電流由電線通向燈管內發出的聲音,彷彿一具滿是病痛的軀體仍在孱弱地呼吸,使整個“手術室”充盈著偏淡藍的光色。
他突然意識到,自己一直不知道這淡藍的光色,究竟是燈光本身的顏色,還是室內牆壁或物品反射出來的顏色。彷彿這一切都是假的,從來沒有真實過。
安重新聚焦目光,看向菲利普。
“我需要你專心,好嗎?”菲利普仍然用那雙充滿疲憊感的眼睛盯著安。
“我知道,開始吧。”安也毫無感情地回答著。
菲利普隨即俯下身去,穿在身上的手術服摩擦發出風吹似的窸窣聲音,然後用白色橡膠手套包裹著的手指撫摸過被無影燈聚焦的一具人類軀體的背部,低垂著雙眼說:“那麼,還是老樣子,一人一邊。”
安也跟著俯下身去,手術衣發出窸窣聲,用手指慢慢撫摸眼前這具人類軀體的背部,然後仔細端詳附著在其背部的義體脊柱。
“荒坂K-303型金屬義柱。”安在腦中默唸著,“中端產品,市價三十萬美金。”
“莫莉帶來的。估計又是一個剛還完義體貸款的年輕公司狗。”菲利普彷彿讀到了安剛才在腦中默唸的話一樣,像接著他話說出來似的。
安知道怎麼回事,他們這套成熟且骯髒的地下產業鏈。莫莉只是依附、徘徊在酒吧裡千萬個“歸棲者”的其中一個。“歸棲者”,只是那些有神秘主義傾向的普通人對莫莉這類人的“蔑稱”而已,行業內的黑話通常把它們稱作“鉤子”。“鉤子”沒有性別...或者說性別隨獵物的取向而變化,外貌大概率也是隨意變化的,裝載最先進的感情模塊與情緒監視程式。這一切讓人眼花繚亂,神迷心醉的設備都能通過錢來獲得。並且裝載這些東西的目的也只有一個——鉤住更多的獵物,送到“屠宰場”,得到更多錢。它們挑選的獵物通常都是些邊緣人或者底層的公司職員,因為這類人一般都裝著市面上較好的義體,但又沒錢或是揹負貸款,買不起“創傷小組”的保險,是實施綁架和謀殺再好不過的對象。
不過這些情況誰也保不準,所以在“鉤子”用酒精或藥物將獵物麻痺,運到“屠宰場”的“屠夫”手裡進行手術的一整個過程,都會用最好的手段維持他們的生命體徵——比如泡冰水,同時讓他們持續不斷地吸入低濃度的麻醉氣體——直至那坨血淋淋的義體設備從他們的原生骨肉上分離開來。
安握著手術刀在空中輕揮一下,鋒利的刀刃劃開冰冷的空氣聲短暫而急促,這種鋒利感彷彿快到連死亡也來不及嘆息,然後便將刀刃抵壓在金屬義柱與皮膚粘合的地方。在經過與菲利普重複過無數次的眼神交流之後,安俯下身去,將注意力集中在即將切割的皮膚上……
“三,二,一……”安在心中默唸,然後輕輕一使力,便聽到了普通人難以察覺到的皮肉撕裂開來的“呲啦”聲,刀子嵌進了皮下深處。幾秒鐘之後,鮮血便會從看似已與刀刃緊緊閉合在一起的傷口出緩緩湧出,轉瞬之間,鮮血與生豬肉混雜在一起的腥味就會散開來,瀰漫在整個房間——這味道與安記憶中屠宰場的味道別無二致,每一次進行“切割作業”的時候他都會想起,只是從沒和任何人提起過。
隨著安慢慢拉動手術刀,比蚊子扇動薄羽更輕微,更讓人難以察覺的皮開肉綻的聲音由點連成了線,好像拉開衣服上的拉鍊一樣。這些聲音在專注力的處理下,變得更大聲了,彷彿在在耳道中迴盪,在大腦柔軟的皮層上飛馳。
“義體與肉體連接得不算緊緻,而且傷口還很新,估計剛裝上去沒多久,不會是全款買的吧?”菲利普開口打破了凝滯的氛圍,但安沒應聲。
菲利普抓住那條與皮肉剝離開來,但首位仍與頸部、尾巴骨粘連著的金屬義柱,往上提了提,肉體與粘液閉合分離擠出空氣發出“滋滋”的響聲,鮮紅溫熱的血液便順著“滴答”往下淌。安抬起頭,看到菲利普眼中正散發出一股陷入狂熱且病態的光芒,而眼前的這具人類軀體與金屬義柱在菲利普的擺弄下,形如手提箱又或是了無生氣的提線木偶一般,任他把玩。
“你他媽別玩了,快把銜接處分離,我今天有事,急著‘下班’。”安出聲制止他,而他眼中狂熱且病態的光芒彷彿氣泡被戳破一樣,瞬間停止消散了。
菲利普放下手中的東西,轉頭去撥開這具軀體後腦勺上凌亂頭髮,一陣窸窣後,他摸到了腦機接口,揮揮手示意安把“黑線”遞給他,然後便把“黑線”插到腦機藉口上。身旁的全息屏上顯示著入侵器與鏈接者大腦建立數據通道的進度條,在到達百分之百之前,入侵器會不斷釋放出脈衝電信號刺激鏈接者的大腦,這會導致鏈接者的身體短暫抽搐或是心率瞬間升高——這一過程就如同舊時代的撬鎖人,用一根鐵絲或髮卡插入鎖眼,不斷抖動刺激機械內部精妙且敏感的構造,直到一聲又一聲清脆的“咔噠”聲過後,緊閉的大門被打開了。
安在全息屏上熟練地操作,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到了義柱的分區並黑進它的BIOS,選擇解除鎖定狀態。義柱上的呼吸燈迅速閃爍了三下紅色之後,頭尾與人體鏈接著的接口處發出彷彿在太空船出艙口洩壓的“噗呲”聲,就完成了義柱與人體的分離。
菲利普把義柱取下來用酒精浸泡清洗乾淨,又把它裝到塑料袋裡,抽空裡邊的空氣,最後裝進一個銀灰色的金屬手提箱裡,貼上封條後,就和開始脫掉手上的膠手套。
通常來說,他們這項搗鼓義體販賣的灰產分工非常嚴密,各個環節之間的工作人員都被精確分工,幾乎不存在交流。比如從鉤子把獵物帶回來到弄到麻醉後,就與這個“項目”脫開“關係了,只需要通過他們這個產業的內部網絡通知轉運人員將獵物就近分配給最近的”屠宰場“,這些”屠宰場“通常隱藏在某間公寓之中或是隱蔽的下水道里,收到任務分配的”屠夫“就在規定時間自行前往”屠宰場“。在手術完成之後,”屠夫“們只需要把拆卸下來的義體封包裝好,就可以離開”屠宰場“了,後續的善後工作則交給”清道夫“們處理。在這一套流程中,各個環節之間的人員幾乎不存在交流,交流的內容也僅限於線上推進工作項目進度的彙報。效率確實相當高效。
至於獵物?沒人在乎他們的死活,在被”清道夫“運走之後,他們將會在潮溼陰暗的後巷裡醒來,醒來的時候不是躺在地面的積水上,就是在灌滿垃圾的垃圾桶裡,或者有些人不會再醒過來,通常就是政府收屍人員來處理了。
“你急著去哪呢?”菲利普邊脫著膠手套,邊和安搭話。
”不關你的事!“安有些惱怒地回答,仍將注意力置於獵物背部傷口的縫合——手持熱能癒合儀在背部傷口上慢慢移動,儀器時不時發出類似於電擊的”噠噠“聲,就好像在塗玻璃窗口邊上的收邊膠一樣。
菲利普也並不繼續和他搭話,把膠手套脫下來扔進垃桶之後,就打開房門出去了。待傷口處理完畢,安朝菲利普離開的房門凝望了一會兒,然後走過去用手踝打開房門,露出一條縫隙伸出頭,朝空曠的走廊四下張望,走廊裡安靜得可怕,一個人也沒有,只有塵埃在走廊燈的光照下輕飄飄地飛舞。
在確認周圍沒人之後,安趕緊把頭縮了回去,將房門從裡鎖死,走到昏迷的獵物旁邊,稍稍猶豫停頓了一會,便嘗試用雙手將其翻過身來。費了好大一番力量,安氣喘吁吁地望著眼前這具軀殼,全身上下的皮膚光滑細膩,看起來吹彈可破,但不知道在這下面還隱藏著多少粗糲沉重的機械體,以至於他的重量遠超表面看上去的那樣沉重。
安迅速拿起手電筒,俯下身去翻開獵物緊閉的眼皮,去尋找那隻剛剛在入侵系統時發現的”蔡思-6R“義眼。但拿著手電筒照射了半天,發現兩隻眼睛都是自然眼,安開始變得疑惑起來,他把手掌置於獵物被頭髮覆蓋的額頭上,用手指右到左使勁地又摳又摸。終於,他在獵物眉心左邊的眉毛那,摸到了一條極為隱秘的縫隙,再用力一撥開,在這片狹小縫隙的血汙中,機械義眼閃耀著淡藍色的光輝。
這竄光束猶如興奮劑一般,讓安內心振奮不已,但表面還是毫無感情,充滿疲憊感——這是一個人被這座城市異化的”標誌“。
安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死死地捏住這顆義眼,擔心自己像《伊索寓言》裡的烏鴉;右手則在操控著全息屏,嘗試把這顆義眼的”鎖頭“打掉。
沒用多久,這顆義眼就被摘下來了,”鎖頭“比他想象中的要簡單。他把義眼洗乾淨,揣進兜裡,也脫下膠手套扔進垃圾桶,隨後便離開了”屠宰場“。

安走出”屠宰場“所在的公寓,快步向地鐵站走去。雖一直是撲克臉,但急促的腳步早就暴露了他激動的心情,即使是搭上地鐵之後,也時不時低頭朝兜裡偷瞄一眼那個奇蹟的淡藍色。
在回到安自己的廉租蜂窩之前,總會經過一條狹長逼仄的後巷。這條後巷陰冷又潮溼,每當夜幕完全沉沒下來之後,沒有一絲照明光線能觸探到這裡,只有在入口和出口處能看得到閃爍的霓虹光源,即使頭頂上還不是完全封閉,卻也仍然看不到任何自然光亮。高聳的大樓是這顆星球的蜂巢,看上去像工業巨獸的眼睛,散熱孔,鱗片,以及……花灑樣的屁眼子。
因此,每當安踏入這條後巷之時,總感覺像行走在無盡的虛無之中——這是一種非常奇妙的感覺,就像身處在一片吞噬所有光亮的封閉空間中,只能看得到前後頭自己頭頂令人感到不自在的光,然後也只能朝著前面微弱的光源前進,但同時你又能感覺到冷颼颼的風從四面八方吹來,輕觸在自己臉龐,這股冷風中間還夾雜著一絲怪異的溫熱,彷彿是工業巨獸休憩後呼吸的餘溫。如果不是因為熟悉這條後巷的氣味,許多人或許還沒走到一半就會被這繁雜的感覺迷惑了心智,好像這裡無限狹小,又無限廣闊,迷失方向感之後只想往回走。
只是這一切對於安來說,反而讓他想起了一些溫馨的事情。
安打開自己蜂窩的大門,在走進去關上門之後,瞬間感到渾身都放鬆了下來,然後長舒一口氣,對坐在窗邊眺望夜景的凱茜說:“你今天沒出去嗎?”
凱茜仍舊用右手撐在桌上,託著下巴望著窗外,沒有回應安的問話。
安無奈地嘆了一口氣,然後脫掉自己的外套,換了一個情緒更興奮的聲調繼續說:“寶貝,我今天又弄到了好東西。”
“別再安裝這些沒意義的東西了……”她的雙眼仍朝向窗外,側著臉打斷了安關於這份喜悅的分享。
“你……說什麼?”安感到有些震驚。
“我說,別再安裝這些沒意義的東西了!”凱茜的語氣變得有些憤怒起來,但其中還是有些脆弱與無力感。
安放下衣服,轉過身去注視凱茜,才發現此時的她正盯著他,眼中噙著淚水,聲音在憤怒中變得有些顫抖與嗚咽了。
安變得有些迷惑不解,問到:“為什麼?!”
“安……”凱茜顫抖著聲音,緩緩起身離開窗邊,腳步一步慢一步快,踉蹌地走向安,然後一整個人無力地趴在他身上,望著他的雙眼,伸手撫過他因機械改造而變得僵硬的臉龐,繼續哀求到:“我求求你了……”
安看著她那佈滿淚痕的臉頰,緊閉雙唇用鼻息嘆了口氣,低下頭,用陰鬱的聲音說:“為什麼……為什麼你還是不理解我?”
“我當然理解你!”凱茜提高音調說著“可它們——這些破銅爛鐵正在摧毀你的主體意識,你沒感覺到嗎?”
“摧毀我?不…!你歸根結底還是不明白,不理解我!它們,不是在摧毀我,而是...正在和我融為一體。”
“安,你還不知道嗎?你的狀態以及開始變得不穩定了,你答應過我去看心理醫生的!”凱茜用她那淚眼婆娑的臉看著他,期望他能有那麼一刻能軟下心來。
“心理醫生?!”安的語氣突然變得尖銳起來,然後用渾厚低沉並逐步變大聲的聲音說:“我!說!過!別再和我提什麼他媽的心理醫生!這幫傢伙簡直比蛆蟲還可恨!和你扯七扯八,時間一到就從你手中騙取血汗錢,最後堂而皇之地以高價賣給你從黑市上200塊就能搞到的Neuropozyne(排斥抑制劑)或是什麼鬼藥物,並讓你持續治療。當你走出他們裝潢豪華的公寓大門之後,竟然開始心安理得地數錢!但問題根本沒解決過,他們只不過是在用藥物掩蓋問題!放屁!就連我都比他們高尚,我都比他們有夢想!他們是臭蟲!豬狗不如!賽博精神病從來都不是什麼義體精神問題,從來都不是!是什麼他們自己明白!”
凱茜的一句話已完全點燃了安的怒火,在安自己也不明白的一通胡亂的大吼大叫之後,他把凱茜一把推開,自己坐到房間角落的床上,只留下凱茜癱坐在地上滴落淚水,無聲地哭泣。
在這片令人窒息的空間僵持了幾分鐘之後,安的怒氣有些許退散,默默地從自己右側的衣服口袋中拿出那枚“蔡思-R6”。在房間昏暗的燈光下,那枚義眼的淡藍色光亮顯得唯美又動人。
安起身打開公寓的房門走出去,來到天台。他抬起頭,仰望這虛無的深空以及高層建築散發出的光芒,他感到無比痛苦。
他記起了自己孩童時的快樂,記起在外祖母建在山中的小木屋的房頂上躺著仰望星空的小時候。一到晚上,四周高聳的小山就變成了黑黢黢的遮蔽物,把一切外來光線擋住,只是它們再如何高聳,都無法將頭頂的星空遮蔽起來。從山谷深處吹來的山風總是夾雜著淡淡的桂花香氣,清爽宜人。每當這時,他總會臆想這股風原來可能並不好聞,它們原本有可能是工業排出的熱氣,或是鯨魚擱淺屍體腫脹爆炸後吹出的氣體......之類的,只是經過他們所在的山間才變得好聞起來;
他記起了自己的夢想,記起與父母關於科技醫學的約定。當時整個世界都振奮於義體的出現,它的出現不僅僅只是能讓殘疾人迴歸正常社會,並且能讓人體變得更強,超越以往的世界。而隨之而來的就是自然人對自身的殘害,把自己的自然體切掉只為了換取更強大的能力。之後一紙禁令限制世界各地對於義體無節制的安裝,只有這座城市,以“進步、自由、平等”之名,從聯邦中獨立了出來,開闢一個專屬於“超人”們的城市。於是,安的父母也前往了這座城市實現自己的夢想。而安,也緊隨著他父母的步伐通往夢想;
他記起了自己的愛情,記起剛與凱茜墜入愛河的瞬間。每個來到這座城市的人都會喪失掉以往一切的身份,變成一個徹徹底底的孤兒。凱西是他喪失身份之後認識的第一個人——在來生酒吧迷亂、籌光交錯閃爍的霓虹燈光下,獨自一人坐在吧檯邊上與一杯“龍舌蘭日落”相伴。一頭火紅的頭髮似閃電,迷亂的燈光也遮掩不住的閃亮,讓他那顆自然心感受到一股強烈且長久的震顫在胸腔深處迴盪。
“我對舊世界沒有任何留戀,我會將生命的所有貢獻給偉大的新世界。”安在煙霧繚繞的廉價汽車旅館床上對凱茜說到。
這些記憶只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特定的物品,特定的氣味中才會顯現。

安撫摸自己曾經能感受到凱茜溫度的雙唇,然後意志堅定地走下樓梯,回到蜂巢裡,環顧了一下四周,並沒有發現凱茜的身影。
默默嘆了口氣,把藏在口袋裡的義眼拿出來,低頭凝視著它,一股熱辣的思維脈衝流經他的大腦,衝擊每一根感官神經。
“你不懂,你不懂,你還是不懂。”安邊輕輕搖著腦袋自言自語,邊翻開床下儲物箱拿出一張簡便的摺疊躺椅,然後將躺椅置於照明燈正底下打開放好,再把全息電腦的數據線插入自己腦後的腦機接口,最後回到躺椅上躺了下來。
安深呼吸了幾下,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天花板上的燈光看。這束光猶如天堂之扉向他打開,偏金的光色從內部射出直插他眼睛深處,傳達到大腦彷彿也被聖光包裹,一片空白。
安打開通訊系統想要聯繫凱茜,但卻顯示對方已離線。收件箱裡有一條凱茜前天就發給他的未讀信息:
“安,我並不想和你爭吵。可是你現在精神狀態已經非常不穩定了,你時常無法意識到自己在說什麼,做什麼,你的變化讓我感到害怕——我很害怕你也變成”賽博精神病“。這讓我怎麼獨自在這座城市活下去?我請求你不要再繼續安裝這些義體了,它們只會加重你的精神失常,現在這樣就很好了!我求求你,我真的很害怕那樣,情願我與你一起死掉,也不要獨自一個人在這裡生存。”
安讀完,咧開嘴笑了。然後開始輸入回覆內容:
“你不懂,你不懂,你還是不懂。即使我已經告訴你千百遍,義體並不是引起賽博精神病的元兇,我也不會得賽博精神病,你還是不懂。真正引起賽博精神病的是這座城市的謊言。義體能帶給人超越自身的錯覺,每當他們獲得一個新義體的時候,這種錯覺總是會帶來一段持續且不可逆的興奮感。他們認為自己能凌駕一切權威之上,但現實將會狠狠打他們的臉!義體始終無法讓他們超越自己的階級,只能讓他們被禁錮在自己階級的自由牢籠裡,像一條發狂的野獸肆意妄為。現實的落差讓他們的思想隕滅,以為安裝越多的義體就能越接近超凡。無數懷揣著夢想的氣泡飄到這片枯萎的土壤之上破裂,再多的氣泡化成的水分也無法滿足這片枯萎腐敗的土壤。你不明白,而我明白這一點,就不會變瘋。
我對舊世界沒有任何留戀,我會將生命的所有貢獻給偉大的新世界。
別了,凱茜。”
寫完,安便看著眼前的燈光在視線中變得越來越大,直至完全覆蓋他的整個視覺範圍。
安的口中輕輕吟唱著上個世紀的歌謠:
獻給那些曾經離開的人,
你覺得它刺耳,非常刺耳,
陽光下的群山,
歌聲點綴著小雨下的冷杉林,
這些經歷裝進了我的揹包
記憶中摻雜著悲傷還有那黑暗的過去
我還是追逐著朦朧的霧和氣息
朦朧的霧和針葉林的味道
然後...慢慢地,將食指與大拇指伸向左眼球,再一用力......“噗呲!”

三天後,因為房租到期,一具滿臉鮮血的男性屍體與一具高度腐爛的女性屍體被從這間公寓中搬出來。
只是安不明白,在這座城市裡,即使是真正的革命者,在他人眼裡也不過是另一種刻奇行為。

感謝您的閱讀,此篇內容是本人基於《電馭叛客2077》所創作的獨立短篇。
主要是出於對《邊緣行者》動畫中對“賽博精神病”標籤化的展現“不滿”而進行創作,當然筆者本人並非否定這部動畫的優秀,而更多是可惜沒對這一主題進行探討。不過筆者本人的文筆與思想深度似乎也還未能完全撐起這一主題,只是希望能讓各位能在此篇想表達的角度下,去對這一主題進行思考,並一同探討。希望你能喜歡本篇內容!
最後,本篇封面與首圖均出自另一位“全息玫瑰碎片HologramRose”成員之手:JackieMishka
「夜城夜曲」由#HologramRose#全息玫瑰碎片呈現,是以不同的視角和主題進行的《電馭叛客2077》相關內容企劃。往期內容:
從2077到2021,一段通關感想&一點年度總結
「夜城夜曲Vol 01」黑夜無眠,人偶爾需要貼近一顆心
「夜城夜曲Vol 02」偽裝成獨白的愛情:強尼銀手的最後一次死亡
「夜城夜曲Vol 03」激情、前衛和迷幻,電馭叛客2077的電子音樂
「夜城夜曲Vol 04」在黃昏,我回憶起夜城的一生所愛
「夜城夜曲Vol 05」《賽博浪客》-“對不起,我們不能一起去月球了”

“想想看,有時做共犯比告密者更好。”——猶如萍水相逢的人最終成為一段歌謠,我們是遊戲玩家,努力做一些硬核又有趣的事情,我們是全息玫瑰碎片HologramRose。
#全息玫瑰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