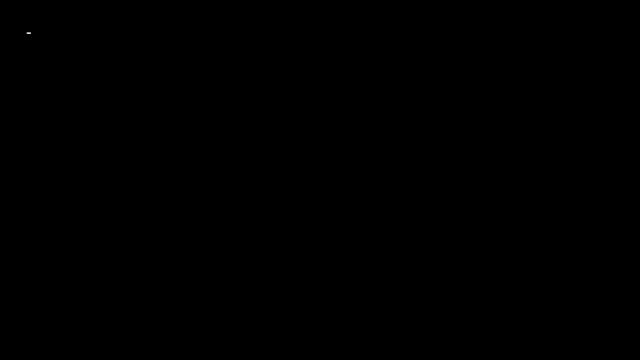
各位旅行者,请检查飞船后视镜和核动阀门,调整电台音乐频率。前方即将降落于土星野餐旅馆:全息玫瑰碎片HologramRo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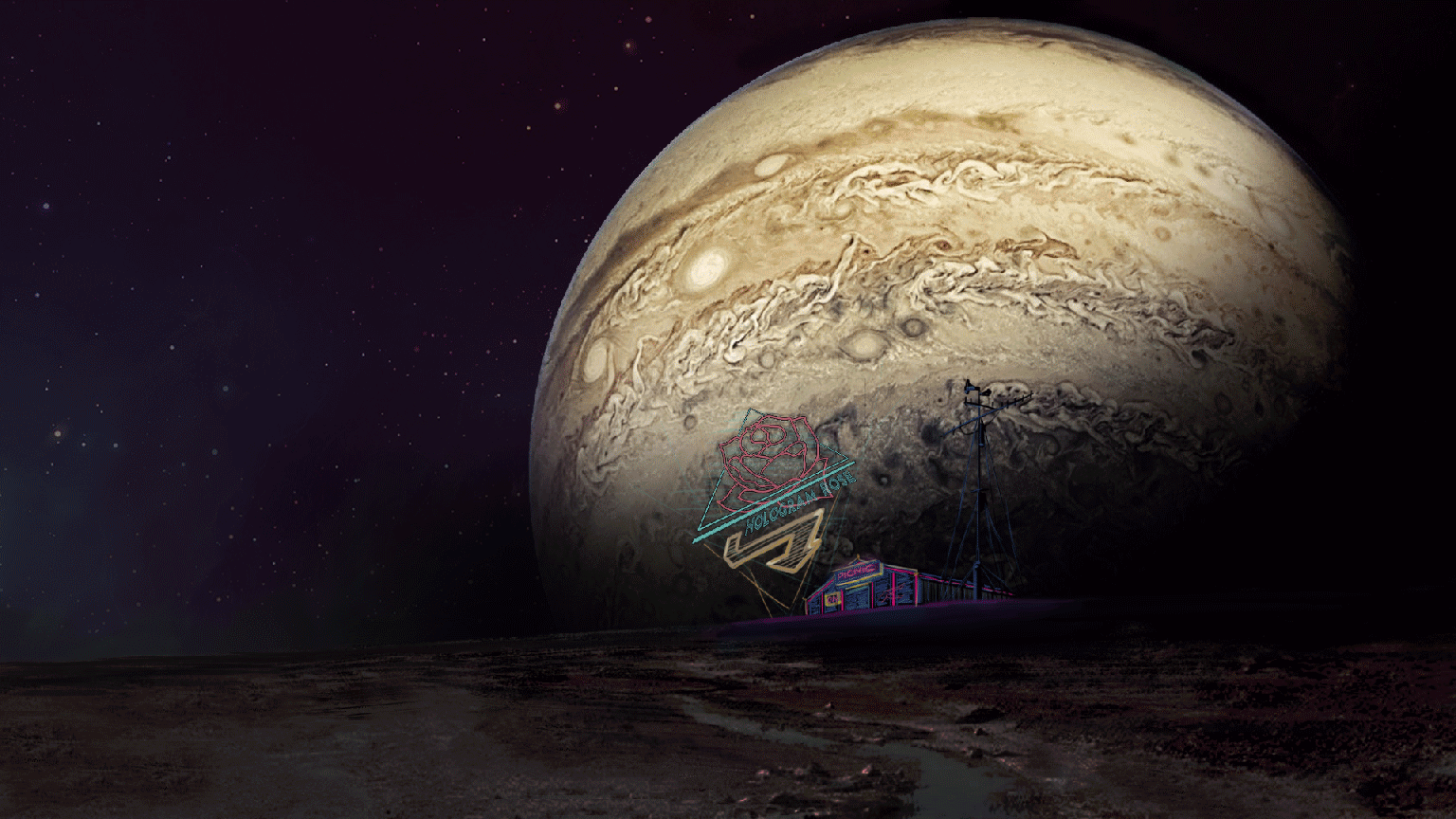
「全息玫瑰碎片HologramRose」:一个写作团体,由一些玩家和游戏作者共同成立。我们希望一起做一些硬核又有趣的事儿。在疯狂的宇宙里,希望有片刻能打动你——每一位旅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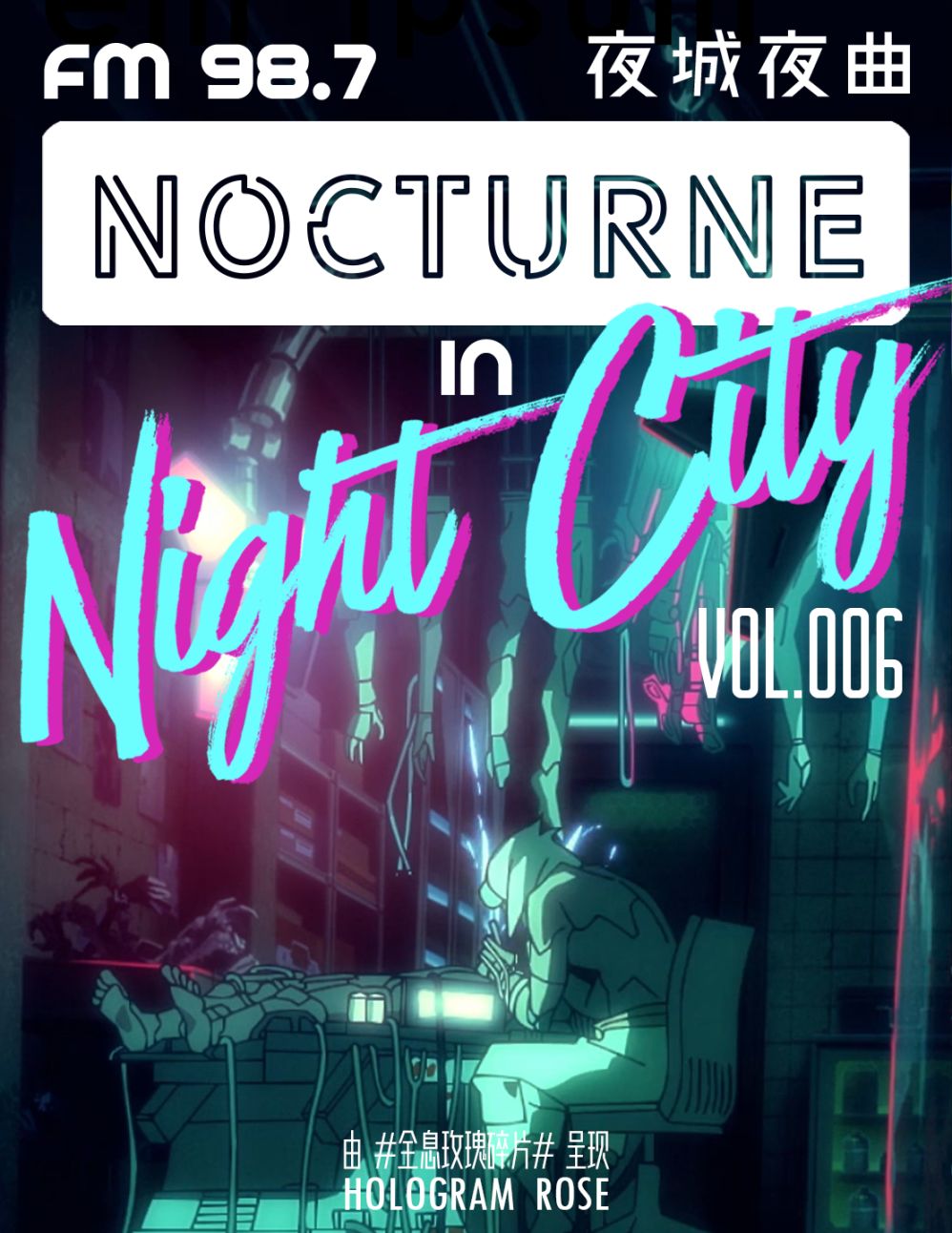

安盯着这片镜像看得出了神。握持在他戴着白色橡胶手套手中的热熔手术刀,刀面映照出他戴着医用口罩、眼神暗淡的模样。
“安...安......”一声声关于他名字的呼唤声仿佛从远处传来,那种感觉...由远至近,由慢到快,由模糊到清晰。好像你刚听到它们时,还在遥远的某处,而有意识去尝试捕捉它的来源与方向时,那个声音瞬间就会打到你脑门上,然后才突然反应过来,自己刚才在发呆。
安抬起头看着在他对面同样戴着医用口罩的菲利普·门罗。
“你又在发呆了。”菲利普用极具疲惫感的眼睛盯着安,没有一丝情感地说出这句话。
安望向四周。
荧光灯在菲利普身后的墙壁上发出微弱的亮光,飞蛾、蚊虫们还在疯狂朝着灯管上冲撞、拍打,发出一下又一下叮咛似的“叮叮”声。电流由电线通向灯管内发出的声音,仿佛一具满是病痛的躯体仍在孱弱地呼吸,使整个“手术室”充盈着偏淡蓝的光色。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不知道这淡蓝的光色,究竟是灯光本身的颜色,还是室内墙壁或物品反射出来的颜色。仿佛这一切都是假的,从来没有真实过。
安重新聚焦目光,看向菲利普。
“我需要你专心,好吗?”菲利普仍然用那双充满疲惫感的眼睛盯着安。
“我知道,开始吧。”安也毫无感情地回答着。
菲利普随即俯下身去,穿在身上的手术服摩擦发出风吹似的窸窣声音,然后用白色橡胶手套包裹着的手指抚摸过被无影灯聚焦的一具人类躯体的背部,低垂着双眼说:“那么,还是老样子,一人一边。”
安也跟着俯下身去,手术衣发出窸窣声,用手指慢慢抚摸眼前这具人类躯体的背部,然后仔细端详附着在其背部的义体脊柱。
“荒坂K-303型金属义柱。”安在脑中默念着,“中端产品,市价三十万美金。”
“莫莉带来的。估计又是一个刚还完义体贷款的年轻公司狗。”菲利普仿佛读到了安刚才在脑中默念的话一样,像接着他话说出来似的。
安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这套成熟且肮脏的地下产业链。莫莉只是依附、徘徊在酒吧里千万个“归栖者”的其中一个。“归栖者”,只是那些有神秘主义倾向的普通人对莫莉这类人的“蔑称”而已,行业内的黑话通常把它们称作“钩子”。“钩子”没有性别...或者说性别随猎物的取向而变化,外貌大概率也是随意变化的,装载最先进的感情模块与情绪监视程式。这一切让人眼花缭乱,神迷心醉的设备都能通过钱来获得。并且装载这些东西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钩住更多的猎物,送到“屠宰场”,得到更多钱。它们挑选的猎物通常都是些边缘人或者底层的公司职员,因为这类人一般都装着市面上较好的义体,但又没钱或是背负贷款,买不起“创伤小组”的保险,是实施绑架和谋杀再好不过的对象。
不过这些情况谁也保不准,所以在“钩子”用酒精或药物将猎物麻痹,运到“屠宰场”的“屠夫”手里进行手术的一整个过程,都会用最好的手段维持他们的生命体征——比如泡冰水,同时让他们持续不断地吸入低浓度的麻醉气体——直至那坨血淋淋的义体设备从他们的原生骨肉上分离开来。
安握着手术刀在空中轻挥一下,锋利的刀刃划开冰冷的空气声短暂而急促,这种锋利感仿佛快到连死亡也来不及叹息,然后便将刀刃抵压在金属义柱与皮肤粘合的地方。在经过与菲利普重复过无数次的眼神交流之后,安俯下身去,将注意力集中在即将切割的皮肤上……
“三,二,一……”安在心中默念,然后轻轻一使力,便听到了普通人难以察觉到的皮肉撕裂开来的“呲啦”声,刀子嵌进了皮下深处。几秒钟之后,鲜血便会从看似已与刀刃紧紧闭合在一起的伤口出缓缓涌出,转瞬之间,鲜血与生猪肉混杂在一起的腥味就会散开来,弥漫在整个房间——这味道与安记忆中屠宰场的味道别无二致,每一次进行“切割作业”的时候他都会想起,只是从没和任何人提起过。
随着安慢慢拉动手术刀,比蚊子扇动薄羽更轻微,更让人难以察觉的皮开肉绽的声音由点连成了线,好像拉开衣服上的拉链一样。这些声音在专注力的处理下,变得更大声了,仿佛在在耳道中回荡,在大脑柔软的皮层上飞驰。
“义体与肉体连接得不算紧致,而且伤口还很新,估计刚装上去没多久,不会是全款买的吧?”菲利普开口打破了凝滞的氛围,但安没应声。
菲利普抓住那条与皮肉剥离开来,但首位仍与颈部、尾巴骨粘连着的金属义柱,往上提了提,肉体与粘液闭合分离挤出空气发出“滋滋”的响声,鲜红温热的血液便顺着“滴答”往下淌。安抬起头,看到菲利普眼中正散发出一股陷入狂热且病态的光芒,而眼前的这具人类躯体与金属义柱在菲利普的摆弄下,形如手提箱又或是了无生气的提线木偶一般,任他把玩。
“你他妈别玩了,快把衔接处分离,我今天有事,急着‘下班’。”安出声制止他,而他眼中狂热且病态的光芒仿佛气泡被戳破一样,瞬间停止消散了。
菲利普放下手中的东西,转头去拨开这具躯体后脑勺上凌乱头发,一阵窸窣后,他摸到了脑机接口,挥挥手示意安把“黑线”递给他,然后便把“黑线”插到脑机借口上。身旁的全息屏上显示着入侵器与链接者大脑建立数据通道的进度条,在到达百分之百之前,入侵器会不断释放出脉冲电信号刺激链接者的大脑,这会导致链接者的身体短暂抽搐或是心率瞬间升高——这一过程就如同旧时代的撬锁人,用一根铁丝或发卡插入锁眼,不断抖动刺激机械内部精妙且敏感的构造,直到一声又一声清脆的“咔哒”声过后,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
安在全息屏上熟练地操作,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义柱的分区并黑进它的BIOS,选择解除锁定状态。义柱上的呼吸灯迅速闪烁了三下红色之后,头尾与人体链接着的接口处发出仿佛在太空船出舱口泄压的“噗呲”声,就完成了义柱与人体的分离。
菲利普把义柱取下来用酒精浸泡清洗干净,又把它装到塑料袋里,抽空里边的空气,最后装进一个银灰色的金属手提箱里,贴上封条后,就和开始脱掉手上的胶手套。
通常来说,他们这项捣鼓义体贩卖的灰产分工非常严密,各个环节之间的工作人员都被精确分工,几乎不存在交流。比如从钩子把猎物带回来到弄到麻醉后,就与这个“项目”脱开“关系了,只需要通过他们这个产业的内部网络通知转运人员将猎物就近分配给最近的”屠宰场“,这些”屠宰场“通常隐藏在某间公寓之中或是隐蔽的下水道里,收到任务分配的”屠夫“就在规定时间自行前往”屠宰场“。在手术完成之后,”屠夫“们只需要把拆卸下来的义体封包装好,就可以离开”屠宰场“了,后续的善后工作则交给”清道夫“们处理。在这一套流程中,各个环节之间的人员几乎不存在交流,交流的内容也仅限于线上推进工作项目进度的汇报。效率确实相当高效。
至于猎物?没人在乎他们的死活,在被”清道夫“运走之后,他们将会在潮湿阴暗的后巷里醒来,醒来的时候不是躺在地面的积水上,就是在灌满垃圾的垃圾桶里,或者有些人不会再醒过来,通常就是政府收尸人员来处理了。
“你急着去哪呢?”菲利普边脱着胶手套,边和安搭话。
”不关你的事!“安有些恼怒地回答,仍将注意力置于猎物背部伤口的缝合——手持热能愈合仪在背部伤口上慢慢移动,仪器时不时发出类似于电击的”哒哒“声,就好像在涂玻璃窗口边上的收边胶一样。
菲利普也并不继续和他搭话,把胶手套脱下来扔进垃桶之后,就打开房门出去了。待伤口处理完毕,安朝菲利普离开的房门凝望了一会儿,然后走过去用手踝打开房门,露出一条缝隙伸出头,朝空旷的走廊四下张望,走廊里安静得可怕,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尘埃在走廊灯的光照下轻飘飘地飞舞。
在确认周围没人之后,安赶紧把头缩了回去,将房门从里锁死,走到昏迷的猎物旁边,稍稍犹豫停顿了一会,便尝试用双手将其翻过身来。费了好大一番力量,安气喘吁吁地望着眼前这具躯壳,全身上下的皮肤光滑细腻,看起来吹弹可破,但不知道在这下面还隐藏着多少粗粝沉重的机械体,以至于他的重量远超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沉重。
安迅速拿起手电筒,俯下身去翻开猎物紧闭的眼皮,去寻找那只刚刚在入侵系统时发现的”蔡思-6R“义眼。但拿着手电筒照射了半天,发现两只眼睛都是自然眼,安开始变得疑惑起来,他把手掌置于猎物被头发覆盖的额头上,用手指右到左使劲地又抠又摸。终于,他在猎物眉心左边的眉毛那,摸到了一条极为隐秘的缝隙,再用力一拨开,在这片狭小缝隙的血污中,机械义眼闪耀着淡蓝色的光辉。
这窜光束犹如兴奋剂一般,让安内心振奋不已,但表面还是毫无感情,充满疲惫感——这是一个人被这座城市异化的”标志“。
安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死死地捏住这颗义眼,担心自己像《伊索寓言》里的乌鸦;右手则在操控着全息屏,尝试把这颗义眼的”锁头“打掉。
没用多久,这颗义眼就被摘下来了,”锁头“比他想象中的要简单。他把义眼洗干净,揣进兜里,也脱下胶手套扔进垃圾桶,随后便离开了”屠宰场“。

安走出”屠宰场“所在的公寓,快步向地铁站走去。虽一直是扑克脸,但急促的脚步早就暴露了他激动的心情,即使是搭上地铁之后,也时不时低头朝兜里偷瞄一眼那个奇迹的淡蓝色。
在回到安自己的廉租蜂窝之前,总会经过一条狭长逼仄的后巷。这条后巷阴冷又潮湿,每当夜幕完全沉没下来之后,没有一丝照明光线能触探到这里,只有在入口和出口处能看得到闪烁的霓虹光源,即使头顶上还不是完全封闭,却也仍然看不到任何自然光亮。高耸的大楼是这颗星球的蜂巢,看上去像工业巨兽的眼睛,散热孔,鳞片,以及……花洒样的屁眼子。
因此,每当安踏入这条后巷之时,总感觉像行走在无尽的虚无之中——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就像身处在一片吞噬所有光亮的封闭空间中,只能看得到前后头自己头顶令人感到不自在的光,然后也只能朝着前面微弱的光源前进,但同时你又能感觉到冷飕飕的风从四面八方吹来,轻触在自己脸庞,这股冷风中间还夹杂着一丝怪异的温热,仿佛是工业巨兽休憩后呼吸的余温。如果不是因为熟悉这条后巷的气味,许多人或许还没走到一半就会被这繁杂的感觉迷惑了心智,好像这里无限狭小,又无限广阔,迷失方向感之后只想往回走。
只是这一切对于安来说,反而让他想起了一些温馨的事情。
安打开自己蜂窝的大门,在走进去关上门之后,瞬间感到浑身都放松了下来,然后长舒一口气,对坐在窗边眺望夜景的凯茜说:“你今天没出去吗?”
凯茜仍旧用右手撑在桌上,托着下巴望着窗外,没有回应安的问话。
安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脱掉自己的外套,换了一个情绪更兴奋的声调继续说:“宝贝,我今天又弄到了好东西。”
“别再安装这些没意义的东西了……”她的双眼仍朝向窗外,侧着脸打断了安关于这份喜悦的分享。
“你……说什么?”安感到有些震惊。
“我说,别再安装这些没意义的东西了!”凯茜的语气变得有些愤怒起来,但其中还是有些脆弱与无力感。
安放下衣服,转过身去注视凯茜,才发现此时的她正盯着他,眼中噙着泪水,声音在愤怒中变得有些颤抖与呜咽了。
安变得有些迷惑不解,问到:“为什么?!”
“安……”凯茜颤抖着声音,缓缓起身离开窗边,脚步一步慢一步快,踉跄地走向安,然后一整个人无力地趴在他身上,望着他的双眼,伸手抚过他因机械改造而变得僵硬的脸庞,继续哀求到:“我求求你了……”
安看着她那布满泪痕的脸颊,紧闭双唇用鼻息叹了口气,低下头,用阴郁的声音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还是不理解我?”
“我当然理解你!”凯茜提高音调说着“可它们——这些破铜烂铁正在摧毁你的主体意识,你没感觉到吗?”
“摧毁我?不…!你归根结底还是不明白,不理解我!它们,不是在摧毁我,而是...正在和我融为一体。”
“安,你还不知道吗?你的状态以及开始变得不稳定了,你答应过我去看心理医生的!”凯茜用她那泪眼婆娑的脸看着他,期望他能有那么一刻能软下心来。
“心理医生?!”安的语气突然变得尖锐起来,然后用浑厚低沉并逐步变大声的声音说:“我!说!过!别再和我提什么他妈的心理医生!这帮家伙简直比蛆虫还可恨!和你扯七扯八,时间一到就从你手中骗取血汗钱,最后堂而皇之地以高价卖给你从黑市上200块就能搞到的Neuropozyne(排斥抑制剂)或是什么鬼药物,并让你持续治疗。当你走出他们装潢豪华的公寓大门之后,竟然开始心安理得地数钱!但问题根本没解决过,他们只不过是在用药物掩盖问题!放屁!就连我都比他们高尚,我都比他们有梦想!他们是臭虫!猪狗不如!赛博精神病从来都不是什么义体精神问题,从来都不是!是什么他们自己明白!”
凯茜的一句话已完全点燃了安的怒火,在安自己也不明白的一通胡乱的大吼大叫之后,他把凯茜一把推开,自己坐到房间角落的床上,只留下凯茜瘫坐在地上滴落泪水,无声地哭泣。
在这片令人窒息的空间僵持了几分钟之后,安的怒气有些许退散,默默地从自己右侧的衣服口袋中拿出那枚“蔡思-R6”。在房间昏暗的灯光下,那枚义眼的淡蓝色光亮显得唯美又动人。
安起身打开公寓的房门走出去,来到天台。他抬起头,仰望这虚无的深空以及高层建筑散发出的光芒,他感到无比痛苦。
他记起了自己孩童时的快乐,记起在外祖母建在山中的小木屋的房顶上躺着仰望星空的小时候。一到晚上,四周高耸的小山就变成了黑黢黢的遮蔽物,把一切外来光线挡住,只是它们再如何高耸,都无法将头顶的星空遮蔽起来。从山谷深处吹来的山风总是夹杂着淡淡的桂花香气,清爽宜人。每当这时,他总会臆想这股风原来可能并不好闻,它们原本有可能是工业排出的热气,或是鲸鱼搁浅尸体肿胀爆炸后吹出的气体......之类的,只是经过他们所在的山间才变得好闻起来;
他记起了自己的梦想,记起与父母关于科技医学的约定。当时整个世界都振奋于义体的出现,它的出现不仅仅只是能让残疾人回归正常社会,并且能让人体变得更强,超越以往的世界。而随之而来的就是自然人对自身的残害,把自己的自然体切掉只为了换取更强大的能力。之后一纸禁令限制世界各地对于义体无节制的安装,只有这座城市,以“进步、自由、平等”之名,从联邦中独立了出来,开辟一个专属于“超人”们的城市。于是,安的父母也前往了这座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安,也紧随着他父母的步伐通往梦想;
他记起了自己的爱情,记起刚与凯茜坠入爱河的瞬间。每个来到这座城市的人都会丧失掉以往一切的身份,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孤儿。凯西是他丧失身份之后认识的第一个人——在来生酒吧迷乱、筹光交错闪烁的霓虹灯光下,独自一人坐在吧台边上与一杯“龙舌兰日落”相伴。一头火红的头发似闪电,迷乱的灯光也遮掩不住的闪亮,让他那颗自然心感受到一股强烈且长久的震颤在胸腔深处回荡。
“我对旧世界没有任何留恋,我会将生命的所有贡献给伟大的新世界。”安在烟雾缭绕的廉价汽车旅馆床上对凯茜说到。
这些记忆只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物品,特定的气味中才会显现。

安抚摸自己曾经能感受到凯茜温度的双唇,然后意志坚定地走下楼梯,回到蜂巢里,环顾了一下四周,并没有发现凯茜的身影。
默默叹了口气,把藏在口袋里的义眼拿出来,低头凝视着它,一股热辣的思维脉冲流经他的大脑,冲击每一根感官神经。
“你不懂,你不懂,你还是不懂。”安边轻轻摇着脑袋自言自语,边翻开床下储物箱拿出一张简便的折叠躺椅,然后将躺椅置于照明灯正底下打开放好,再把全息电脑的数据线插入自己脑后的脑机接口,最后回到躺椅上躺了下来。
安深呼吸了几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的灯光看。这束光犹如天堂之扉向他打开,偏金的光色从内部射出直插他眼睛深处,传达到大脑仿佛也被圣光包裹,一片空白。
安打开通讯系统想要联系凯茜,但却显示对方已离线。收件箱里有一条凯茜前天就发给他的未读信息:
“安,我并不想和你争吵。可是你现在精神状态已经非常不稳定了,你时常无法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你的变化让我感到害怕——我很害怕你也变成”赛博精神病“。这让我怎么独自在这座城市活下去?我请求你不要再继续安装这些义体了,它们只会加重你的精神失常,现在这样就很好了!我求求你,我真的很害怕那样,情愿我与你一起死掉,也不要独自一个人在这里生存。”
安读完,咧开嘴笑了。然后开始输入回复内容:
“你不懂,你不懂,你还是不懂。即使我已经告诉你千百遍,义体并不是引起赛博精神病的元凶,我也不会得赛博精神病,你还是不懂。真正引起赛博精神病的是这座城市的谎言。义体能带给人超越自身的错觉,每当他们获得一个新义体的时候,这种错觉总是会带来一段持续且不可逆的兴奋感。他们认为自己能凌驾一切权威之上,但现实将会狠狠打他们的脸!义体始终无法让他们超越自己的阶级,只能让他们被禁锢在自己阶级的自由牢笼里,像一条发狂的野兽肆意妄为。现实的落差让他们的思想陨灭,以为安装越多的义体就能越接近超凡。无数怀揣着梦想的气泡飘到这片枯萎的土壤之上破裂,再多的气泡化成的水分也无法满足这片枯萎腐败的土壤。你不明白,而我明白这一点,就不会变疯。
我对旧世界没有任何留恋,我会将生命的所有贡献给伟大的新世界。
别了,凯茜。”
写完,安便看着眼前的灯光在视线中变得越来越大,直至完全覆盖他的整个视觉范围。
安的口中轻轻吟唱着上个世纪的歌谣:
献给那些曾经离开的人,
你觉得它刺耳,非常刺耳,
阳光下的群山,
歌声点缀着小雨下的冷杉林,
这些经历装进了我的背包
记忆中掺杂着悲伤还有那黑暗的过去
我还是追逐着朦胧的雾和气息
朦胧的雾和针叶林的味道
然后...慢慢地,将食指与大拇指伸向左眼球,再一用力......“噗呲!”

三天后,因为房租到期,一具满脸鲜血的男性尸体与一具高度腐烂的女性尸体被从这间公寓中搬出来。
只是安不明白,在这座城市里,即使是真正的革命者,在他人眼里也不过是另一种刻奇行为。

感谢您的阅读,此篇内容是本人基于《赛博朋克2077》所创作的独立短篇。
主要是出于对《边缘行者》动画中对“赛博精神病”标签化的展现“不满”而进行创作,当然笔者本人并非否定这部动画的优秀,而更多是可惜没对这一主题进行探讨。不过笔者本人的文笔与思想深度似乎也还未能完全撑起这一主题,只是希望能让各位能在此篇想表达的角度下,去对这一主题进行思考,并一同探讨。希望你能喜欢本篇内容!
最后,本篇封面与首图均出自另一位“全息玫瑰碎片HologramRose”成员之手:JackieMishka
「夜城夜曲」由#HologramRose#全息玫瑰碎片呈现,是以不同的视角和主题进行的《赛博朋克2077》相关内容企划。往期内容:
从2077到2021,一段通关感想&一点年度总结
「夜城夜曲Vol 01」黑夜无眠,人偶尔需要贴近一颗心
「夜城夜曲Vol 02」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强尼银手的最后一次死亡
「夜城夜曲Vol 03」激情、前卫和迷幻,赛博朋克2077的电子音乐
「夜城夜曲Vol 04」在黄昏,我回忆起夜城的一生所爱
「夜城夜曲Vol 05」《赛博浪客》-“对不起,我们不能一起去月球了”

“想想看,有时做共犯比告密者更好。”——犹如萍水相逢的人最终成为一段歌谣,我们是游戏玩家,努力做一些硬核又有趣的事情,我们是全息玫瑰碎片HologramRose。
#全息玫瑰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