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琳德的傳說任務《夜色無聲》是我入坑以來玩到的最好的原神故事,玩兒的時候基本上一句臺詞也沒跳過。心血來潮寫一篇文字,劇透警告。
編劇的巧思
故事開始於克洛琳德和娜維婭四處找人參加一個新推出的“桌上劇團”(也就是跑團)試玩版,名字叫《逐影獵人:審判之時》。我、林尼、芙寧娜加入了這個遊戲。這個戲中戲的設定並不新鮮,但是由於編劇做對了很多事情,發揮了這個結構獨有的長處。
克洛琳德作為冷靜寡言的楓丹『決鬥代理人』,也是一個硬核跑團愛好者,擔任這個劇本的主持人。作為二次元刻畫人物的常規的反差設計本身並不足為奇,但在劇本推進過程中,她不顧一切地保護這個遊戲本身不中斷、不出戲、不超遊,不得不做出一些臨場發揮的安排。比如佯裝劇情要求,讓全體玩家閉眼,自己好進行真實的戰鬥等等,玩家一邊消化“這個跑團到現在弄假成真了”的翻轉而必須開始動腦筋理解和猜測的同時,還要控制角色進行戰鬥。就這樣,跑團劇本、真實世界的逐影獵人的歷史、克洛琳德的成長史、克洛琳德與娜維婭之間一個長期隔閡的消融,四重敘事得以同時推進,信息量滿載。

克洛琳德對跑團本身秩序的堅決維護,形成了多個假戲真做、戲裡戲外一語雙關的,巧妙的機會。典型例子是,她需要一邊戰鬥,一邊杜撰跑團裡的劇情說給四位扮演者聽,如同前鋒一邊帶球一邊帶著耳麥給中央五臺解說,非常高難度,同時也非常搞笑。『守護人們的幻想,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克洛琳德對亡羊補牢的逐影獵人後代說。這裡面有一點the show must go on的浪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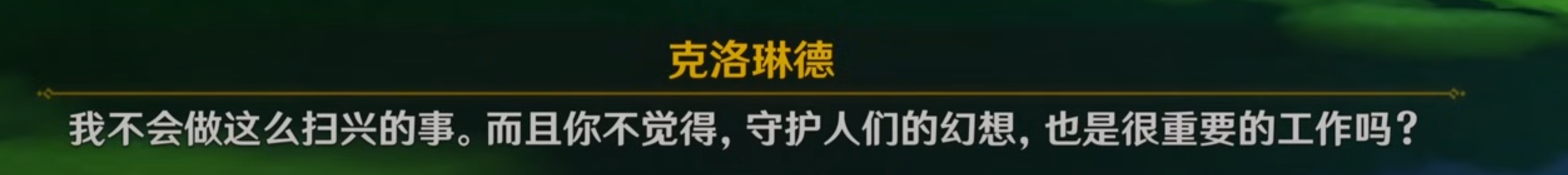
故事的結尾,遊戲散場之後,主角問了一個關於人生意義的問題,克洛琳德不願作答,她躲回到GM的敘述模式中,說了一句旁白,cue自己體面的退場,『關於這個問題,那個逐影獵人沒在說什麼,就交給這無聲的夜色來替她回答吧』,也就是傳說任務的標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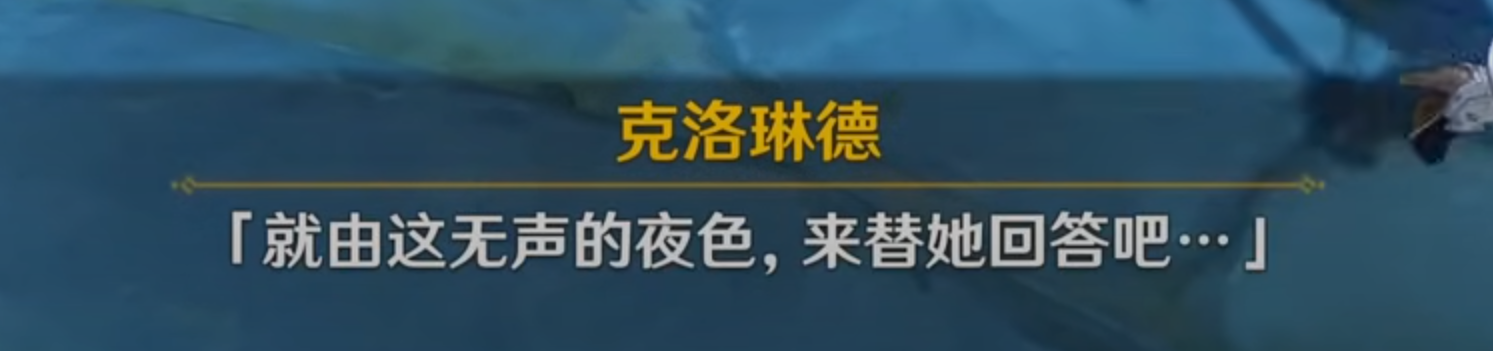
娜維婭和芙寧娜則構成了很有趣的meta反差:跑團玩家的兩種心態。娜維婭認為跑團最大的樂趣在於隨機數帶來的不確定性,她非常享受挑戰劇本邊界,讓主持人壓力很大的胡鬧嘗試。

而芙寧娜則完全相反。一方面,芙寧娜是第一次跑團,這個跑團新手的內心OS跟我自己現實生活第一次跑團的經驗一毛一樣,比如非常擔心隨機數不給面子,讓故事變得很尷尬(其實這是一種完全不必要的擔心);再比如,在自我身份的芙寧娜,和自己扮演的逐影獵人芙寧娜之間反覆橫跳,確認自己現在在以什麼身份說話,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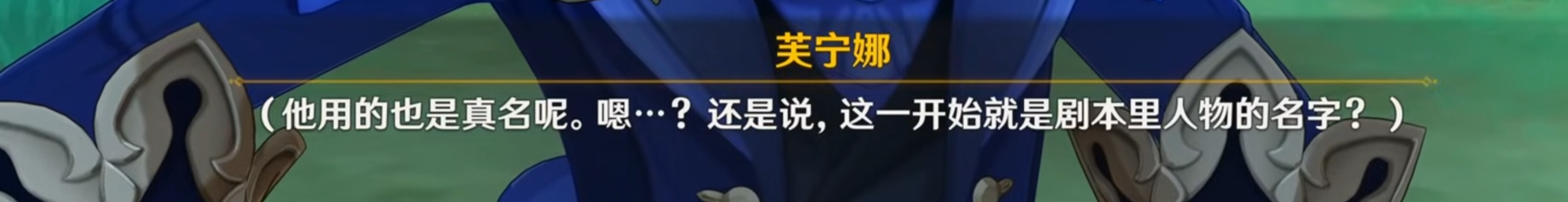
另一方面,芙寧娜對跑團的理解和興趣都側重於表演而非博弈,她認為骰子檢定不通過會擾亂故事,畢竟故事走向本身是應該有其合理性的,所以她選擇了輕鬆體驗(骰子檢定一律默認通過),並把注意力放在表演和觀看別人表演本身上。這也體現在她全程都很在意這個遊戲的製作水平,比如誇讚道具會發光,演員過於投入地配合氣氛和故事,都暈倒了……而且別人在推理的時候,她會直接進入鑑賞品評模式:哦這是什麼什麼轉折,什麼什麼套路,嗯嗯寫的不錯啊!這些都是一個戲劇發燒友合情合理會有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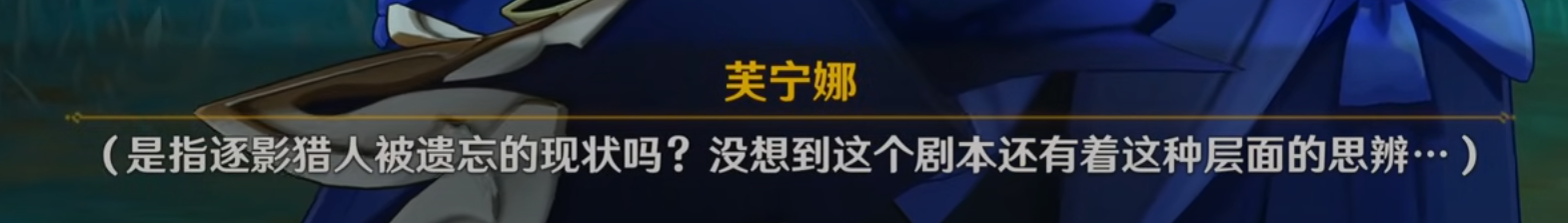
任務過程中很少的幾個供玩家選擇的分支,也都落在娜維婭-芙寧娜的上述區別中,玩家在選擇的時候,其實是在潛臺詞地認同其中一方——如何從市民獲取情報?你可以對隱瞞的NPC使用讀心術,對受傷的NPC進行治療等技能來獲取好感;也可以選擇明顯離譜的給對方唱歌、表演魔術,當然若如此做,克洛琳德以及隊友們都會血壓很高。
關於跑團,我想最後再補充一個觀察,就是跑團這個場合(巧合地)抹平了故事中很多注意力無處安放的無聊時刻(『尿點』是指這個意思吧?)獲得信息——砍怪並且得到寶箱——國王沒收財富把我們抓進大牢,玩家的注意力完全不會糾纏於情節的合理性——跑團嘛!——而是集中在四位逐影獵人對每一個情況的反應(在意什麼)和策略(擅長什麼),一個多小時裡面我沒怎麼遇到『這也太弱智了,跳過吧』的我的原神日常。
故事的延伸
克洛琳德的傳說任務和逐影獵人有關。逐影獵人是一個古老王國傳下來的職業,他們憑藉肉體凡胎和磨練的劍技,在黑暗中對抗魔物,保衛人間,推翻殘暴統治。隨著故事的深入,玩家瞭解到這個跑團是一個陷阱。一個繼承父親逐影獵人身份的,心懷恨意的年輕人設計了這個遊戲,以奪取克洛琳德手中的鑰匙碎片,打開逐影獵人團體共同的藏寶庫大門。是逐影獵人的一個傳統,澆灌了他的恨意——逐影獵人必須自願放棄任何金錢和名譽的回報,匿名行事。
曾經奉獻和犧牲過的人,得不到名譽和認同。我們都在銀幕上看過同一個故事的變種,一名老兵窮其一生想要確認犧牲的戰友們的稱號,卻發現連自己連隊的番號都找不到,自己甚至無法證明他們的存在……旅遊的時候,美國賓州一個衰敗的無名小鎮裡,一個老爺爺無限驕傲地對我說,自己的爺爺和父親工作過的阿特拉斯水泥廠曾經遠銷全球,紐約帝國大廈的水泥就有他祖輩的功勞。人們熱衷於談論黑暗騎士結尾蝙蝠俠深沉帥氣的決斷,卻不會好奇,那樣的傳統如果永遠堅持下去,被時代遺忘的舊日英雄,是否會受到陰影的侵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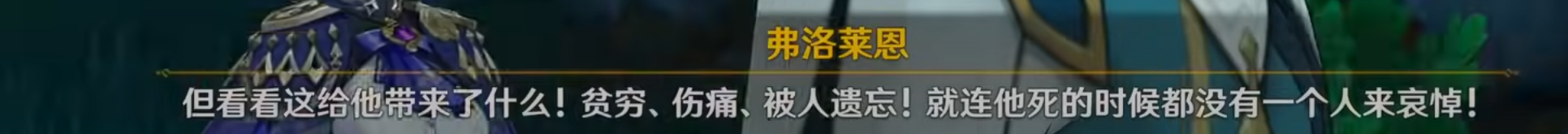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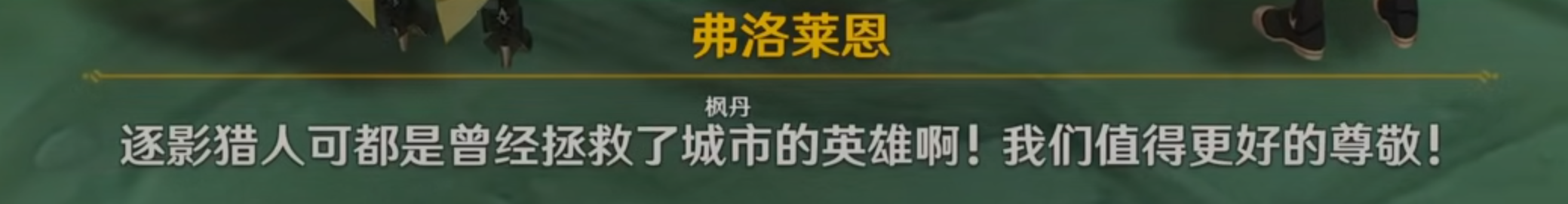
自身的存在被拒絕,被無視,有時會釀成深深的怨恨。經濟上的爭奪,成了名譽得不到公正時的代償。J.D. Vance成為這一屆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之後,他的自傳《鄉巴佬的哀歌》一時間洛陽紙貴。對於其中滲出的恨意,單一經濟視角的解讀會錯過真正重要的東西:那個以外婆為化身的,山區走出來貧窮的蘇格蘭威爾士白人移民後裔的宗教信仰、家族關係與社會文化,比城裡的進步人士(“你們為什麼就不能離開那裡??”)以為的要堅硬。
逐影獵人這個看似幼稚的傳說故事裡做對了的一點在於,失意階層的一名憤世嫉俗的後代想要撬開許諾的獵人財寶,得到的卻只是前輩的兵器與一方碑刻。沒有財寶,只有記錄,而且這記錄從來不是為了公諸於世而籌備的自我表彰,而是給遺忘了傳統的繼承者們留下的提醒。寶藏就是逐影獵人的理念,和名字。

大多數的平凡人就像戲中的人一樣,安心地扮演著自己的角色,渾然不覺第四堵牆已經坍塌,自己正在被誰保護(其實也就芙寧娜不知道哈)。芙寧娜、娜維婭、林尼和玩家按照跑團劇情的要求,舉起先輩的兵器(其中娜維婭的那一把署名是克洛琳德的師父),喚醒古老的逐影獵人,與同樣古老的魔物戰鬥——用舊日的武器,斬斷今日的積怨——這個場景令人心碎地提醒著,這只是一個幻想,一場童話而已。它也還是要用“和同伴們共度的時光或許就是意義”這樣萬能的庸俗結尾作為總結。但絲毫不妨礙它成為一個精彩的故事。

一些聯想
商業二次元遊戲的絕大部分故事,對我來說都非常呆滯。不堪推敲的翻轉,缺少分量的苦難,都只是售賣人物時華麗麗的背景布罷了。而角色性格和內心的塑造,似乎也總是膽怯於走出它的標籤和設定,似乎讓一個角色不停地確認這些點,就足夠了。比如一個人喜歡打牌,喜歡諧音梗,就不停地讓他提議打牌或者講冷笑話;再比如一個人很刻薄,他就不停地對所有情境裡的所有人刻薄,很魔性沒錯,但原地打轉讓人完全動不起腦子。確認只是原地踏步的重複強調。我說的膽怯,就是不敢、或者懶得去構建一個稍微複雜點的情境,讓角色多一點反應和不那麼直給,邏輯不那麼短的人設強化。然而,觀眾如果可以靠自己置身於情境之中,把微妙之處串聯起一個理解,其深入人心的程度往往遠大於重複強調,不是麼?
這又讓我想到之前看到玩家在議論自己的“同擔”們最近“伙食不好”的討論。克洛琳德的傳說任務很有意思的一點在於,它似乎沒有像其他角色的一樣把筆墨全部用在克洛琳德本人身上,旅途終點,我對林尼、芙寧娜、娜維婭和克洛琳德的認知都有差不多均等的推進。我在想如果我也這樣消費金庸古龍的小說,喬峰和遊坦之的筆墨要不要配平呢,阿朱和阿紫的可愛和可恨要如何評價呢。我還在想,遊戲內容,或者說今天所有廣義的娛樂產品的消費,在多大程度上等同於吃和嗑,還有多少餘地留給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故事呢?
想得更遠一點,以售賣角色為目標的內容創作這件事,有沒有可能在技術升級,模式充分驗證,天花板不再升高,地板也不會太低的穩定週期裡,得到一些鬆綁,和更有企圖心的嘗試呢?
以及,一個年近四十的非二次元的誤入原神的非目標玩家的胡思亂想有任何參考價值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