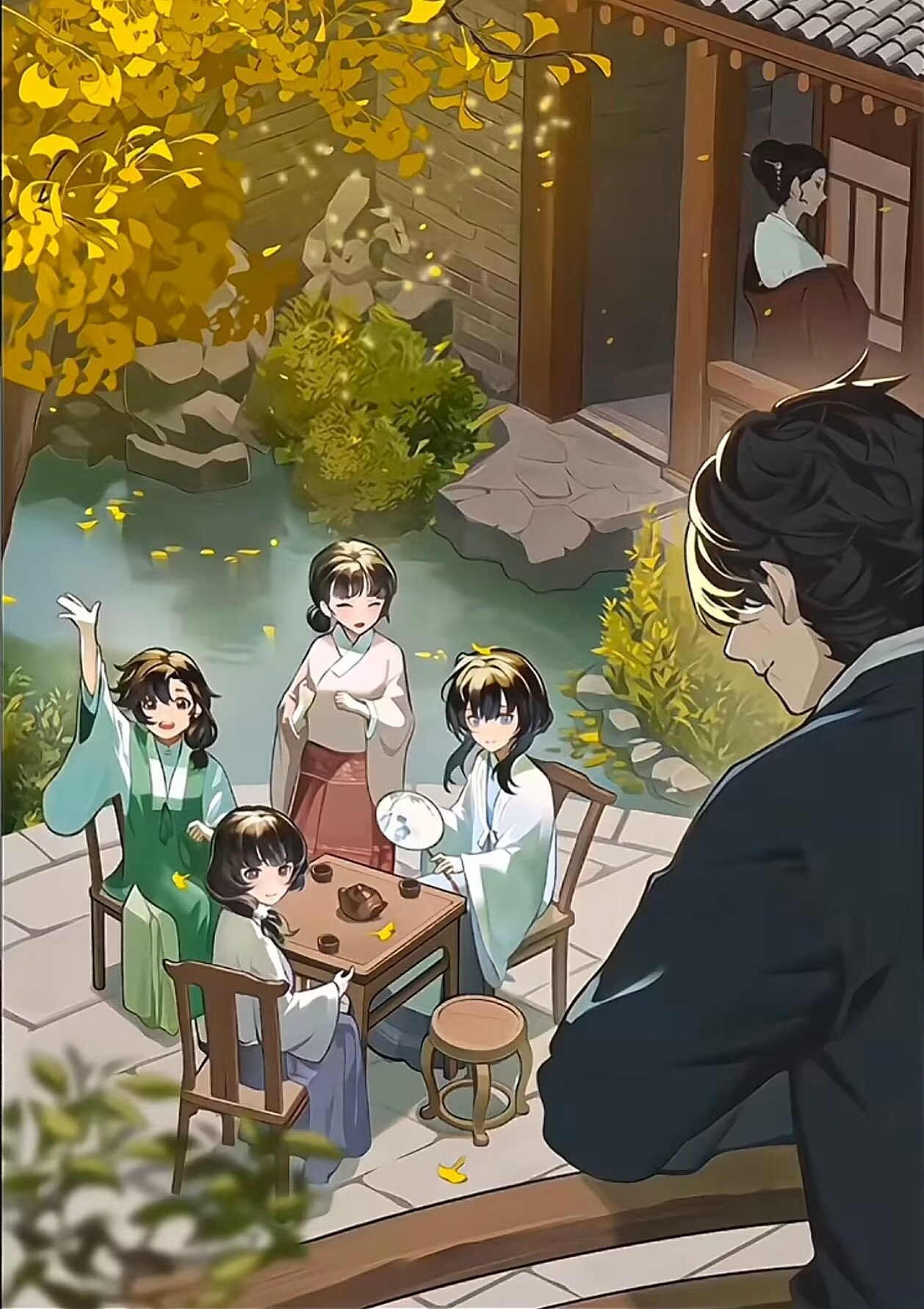
1662.6.11
“良爷,可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记得,当然记得啊。”
今天是她的诞辰,是我与她洛水重逢的日子,是我重获新生的日子。
我怎会忘呢?年年都和她一起过呢...
去年居然真叫这郑式打跑了洋人,夺回了东番,我们也顺理成章的从南方乘船渡来这岛上了。
今后也更安稳了,生活质量也渐渐的好起来了。
鸡鸭牛羊,米面粮油都不会再缺了。
凝儿今年也已十二了,让我和穗儿能省心了,经常会帮他娘做些事情。
而我...
我今年,已是几龄了?
...
这脑子,居然开始不好使了。
是真的,去年起,我便出现了一些记忆丢失的病况。
我很担忧,我怕忘记,我害怕着忘却某人。
我甚至于对此而产生恐惧。
是啊,不能忘掉她。
你是我今与夕的挥影,
我是你一个人的泪迹。
茫茫人海中你与我相遇。妳却是一滴水,经不起风霜雪雨。
会从白菜上滴落而下,
会从体肤上滴落而下,
会从茶杯上滴落而下,
落入泥土中,
落入床绸中,
落入茶盘中。
但是妳却无视险阻,从无数次跌倒中拼尽全力走到我的面前。用愤怒与仇恨的滔天巨浪淹没我。
可我,
“并不是狼,我是...良。”
...
......
“良爷?良爷?”
满穗伸出小手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把我从思索中唤起。
“噗,良爷真成良爷了啊?果然是老咯。”
她苦笑一声,随后调侃起我来。
我有什么病症,自然是瞒不过这小妮子的。但我也认了,这样子也好。
自从发现了我的记忆出现问题后,她经常会指着一些东西,让我说出它的作用和名字。这种交流,仿佛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小崽子。
但我也认了,这样子也好。
“今日是你的诞辰,你想吃些什么呢?”
“还是老样子吧,红薯。”
从很多年以前,她的诞辰就一直是买几颗红薯回来吃了。
我一开始觉得这样子有些不妥,毕竟诞辰总要吃些好的。而这东西,虽说并不难吃,但总归是要吃些正经东西的。
直到后来她和我说了这其中的缘由。
那晚,我沉思了很久,很久很久。
直到突然上下眼皮一阵打架,便睡了过去。
那晚的梦里,我梦见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我当然知道是谁,戴着个草帽,一副陕地农民的模样。
他是穗儿的父亲。
他的心脏位置上有个血淋淋的刀口,那是我捅出来的,是我拼尽全身的力量,将父亲给予我的长刀捅进他的胸膛,所捅出来的。
他看了我许久,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走到我的面前,伸出了右手。
他的右手手指内侧关节上都是划开的血肉,是他最后时刻试图掰开我插在他胸膛上的刀时所致的。
他将这可怖的手搭上我的肩膀,我低着头,不敢看向他。
我知道,这是我犯下的罪。
我本以为我会在梦中,接受她父亲的罪责与怒罚。
“陪着她吧。”
一阵慈祥却又平静到几乎是亲朋好友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
“把你的命,陪给她。”
“我知道了。”
梦境在这一瞬分崩离析,面前的画面犹如一张画布失去了支撑架一样瞬间倒塌。
画布倒塌褶皱前的最后一刻,我看到了那男人嘴角的一丝微笑。
眼前一阵大亮。
她的父亲不在了
不在我的眼前了
不在她的眼前了
不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不会出现在她的眼前了
梆梆梆。
一阵听起来就很有礼貌的敲门声传入我的耳朵。我自然是第一个醒过来的,缓缓推开房门。
原来是店小二,他看我还睡眼朦胧的样子,一阵致歉,随后也问了我们是否需要送上些吃食来。
“一个时辰后做好就行。”
小二说了声好便就下楼去了。
关上房门,推上门插,转头看向满穗
她此时已然醒了,被我吵醒了。三千青丝如瀑布般顺着耳朵柳下,眼角微微颤动,两条如玉般白洁的手臂支着床榻,淡粉色的嘴唇微微曲着,窗外刚刚升起的暖光照着睡眼朦胧的她。
(此段衔接于《泰岳游行,身病惊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