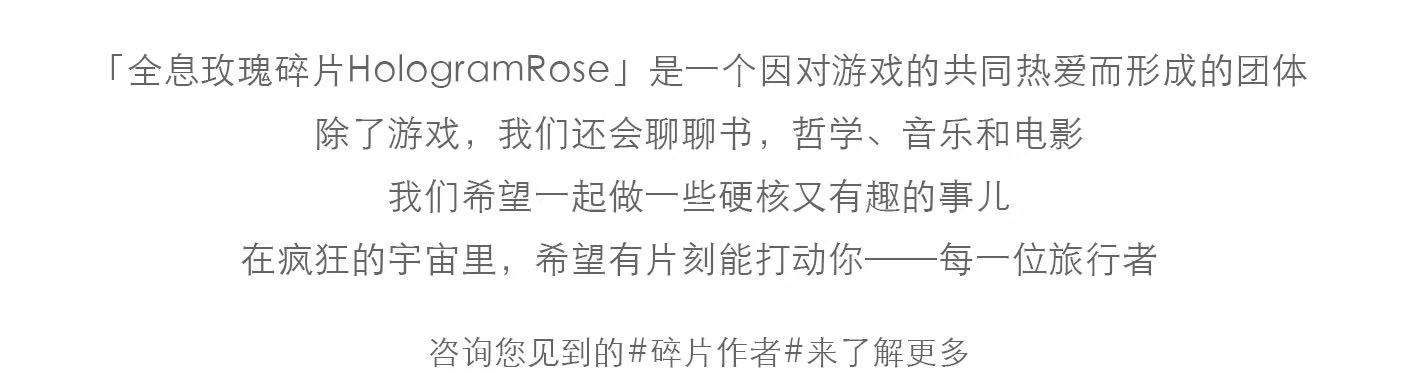前言
傳媒之神啊,取了這樣標題哄騙讀者進來的我有罪。請懲罰我雲頂之弈老八一整天,只因我早已發誓不再碰那傻杯遊戲;或者讓網易雲把我收藏中James Blunt的歌全部變灰,那將是對我莫大的折磨。
本文基於對《明日方舟》“長夜臨光”活動劇情的討論和聯想,預設讀者對於活動劇情有所瞭解;但會對於《帕西法爾》有基礎的介紹,不需要提前瞭解也能理解表達內容。
“長夜臨光”活動結束了!快去把那些精彩的壁紙都截圖保存下來!!

大概是bug。作戰結束封鎖關卡後就顯示內容無法查看了,仍在提示通關對應關卡。
場間休息片段是純粹看個樂呵,標題中出現的都是很普通的特殊疑問句,都不是設問。純粹為讀者場間休息以及圖一樂。
那麼我們開始。

目錄:文章不怕長,暴論搶先看(笑)
0.房子實際上沒有那麼大。
1.耀騎士與聖盃騎士的救贖
“如果瑕光、臨光和瑪恩納是同一個人。”
場間休息:家族血統在這次變革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2.《帕西法爾》:瓦格納和宗教劇變革
“‘只有純潔的愚者能拯救,他因同理心而得大智慧。’”
場間休息:舟遊本次活動的配樂演出有什麼講究?
3.被利用並被救贖的女性:昆得麗與白金
“與其理解成開後宮,不如看作是反叛信仰之後得到救贖。”
場間休息:《頭號玩家》的主角為什麼要叫帕西法爾?
4.卡西米爾的城市概念:宗教的缺失與信仰的泛濫
“‘上帝已死,是我們殺了祂。’現在,我們都是上帝了。”
場間休息:只存在於瓦格納書信中的哲學家
5.尼采與瓦格納的糾葛,以及怯薛的角色意圖
“很多人都知道尼采提到‘上帝已死。’但很少人知道它的下一句是什麼。”
場間休息:有趣的傳聞-莎樂美與尼采
6.結語
“我是傻杯”

房子實際上沒有那麼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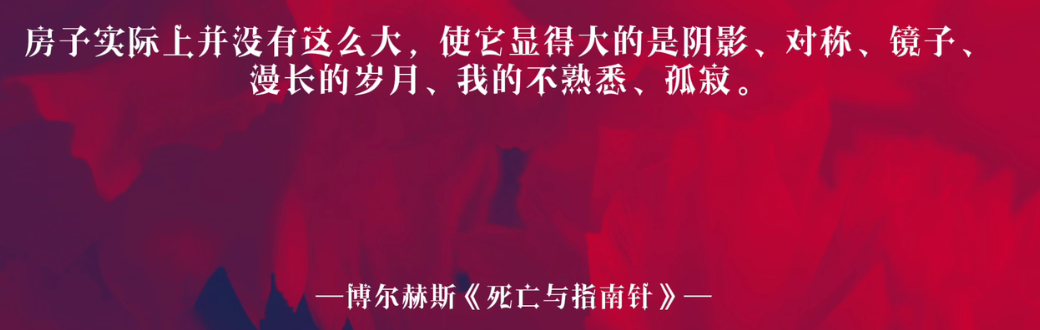
文章在我第一次看到“卡西米爾”這個詞的時候就在構思了,因為和“帕西法爾”念起來特別像,他們也都是騎士故事,人物都在各種意義上的發光。所以我當然曾猶豫過,“這是我過度解讀嗎?我是在掉書袋子嗎?”
使我解脫的是博爾赫斯的這句話。我會質疑自己過度解讀是因為我自己本看到了許多精彩的、有趣的內容,卻無人分享、無人談論;只是借這次活動的劇情和“卡西米爾”這個詞彙和發音讓這種缺失感不斷的、不斷的浮現,催使我寫下了這篇文章。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會選擇“劇情聯想”作為標題,而不是往常的“考據”——我心中一定是相信《明日方舟》的活動編劇根本沒有參考《帕西法爾》的。但我仍然迫不及待的想要和大家分享這兩部我喜歡的作品,分享一些理解劇情的視角。以及很普通的,如果你喜歡《帕西法爾》,你或許也會喜歡“長夜臨光”這次活動;反之亦然。

耀騎士與聖盃騎士的救贖
“只有純潔的愚者能拯救,他因同理心而得大智慧。”
提到這句話,我第一個想到的是瑕光。她並不理解騎士競技的運作機制和自己家族歷史的真相,但純潔而懵懂的她所展現出對於競技騎士中的感染者群體的同理心慢慢建立起了與感染者的鏈接,邁出了試圖拯救的第一步。
這句話是出自《帕西法爾》中,聖盃顯示的神諭。當時的情況是國王安佛塔斯(下稱老安子)因為美色被奪走了自己本當守護的、曾被用作刺穿耶穌基督的聖矛並被其刺傷,祈禱聖盃指引他脫離苦痛時,聖盃回覆的答案。
不言而喻,這句神諭指示的是全劇主角帕西法爾。他因為在森林中射殺天鵝被聖盃騎士一行人發現,在老騎士古內曼茲(下稱老古子)的訓斥下,連自己名字都記不清的蠢蛋帕西法爾竟對著天鵝屍體痛哭流涕,折斷了自己的弓並答應從此不再射殺天鵝。老古子見他竟有如此悟性與同情心,並想起了神諭,將帕西法爾帶到聖盃儀式,才有了後來機械降神拯救老安子的橋段。
如果要說瑕光是在愧疚和教導中剛剛獲得同情心的少年帕西法爾,臨光則像是已然開悟並通過考驗成為“純全的騎士”的成年帕西法爾。除開兩者的強大都是寫在設定集裡的之外,兩人默然用行動和力量追求正義之事的凌然形象也讓我覺得他們身影慢慢重合了。
事實上耀騎士臨光所手持光芒四射的長槍也與帕西法爾的聖矛非常匹配,會不會是某種巧合呢?

保存在霍夫堡皇宮的命運之矛,photograph by René Hanke (GFDL) - Edited en:Image:Heilige Lanze 01.JPG (maybe the same as File:Heilige Lanze 01.JPG),CC BY-SA 3.0,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741801

人物立繪手中的、除開光芒特效的實體形狀和聖矛出奇的相似。圖片出處右上水印,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沙雕UP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瑕光和臨光可以是同一個人嗎?如果我們暫且不將時間認定為線性,作為姐妹,我們能看到的是不同時期的同一個人,或許包含“瑪莉婭·臨光”這一系列的活動劇情安排就是在用瑕光講臨光從前的故事。
以這樣的視角去看家族作為一個整體也是很有趣的。懵懂天真的瑕光、不信任的瑪恩納叔叔、得到救贖直面黑暗的臨光、暫時還活在傳言中的引領變革的老頭子們。他們同時存在於當下,但又體現出了家族在通篇歷史中對於家鄉卡西米爾的情感聯結與相對關係。
我不想直接聯繫到尼采的無限輪迴,但我們會談到尼采。畢竟這篇文章的主場是瓦格納,而劇評家達爾豪斯在談及瓦格納時提到過:

“Time is a flat circle. We’re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出處《真探》第一季,我每看一次都像從前死過一次的懸疑劇。
場間休息
家族血統在這次激動人心的變革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換句話說,如果不是天馬一族的家族積澱和先天超能力,以及小天馬們祖上的社會關係,我們真的能看到如此振奮人心的變革嗎?還是隻會是另一個像“覆潮之下”裡一般、仰首企盼羅德島幹員機械降神,然後在劇情裡稍微成長一下的無力角色呢?

《帕西法爾》:瓦格納和宗教劇變革
我一直相信不瞭解作者是無法完整了解一部作品的。我並不瞭解鷹角編劇組,但萬幸我能分享一些關於歌劇作家瓦格納和這部作品的故事。
19世紀有個經典笑話:我跟愛人說話的時候說法語,跟情人說西語,跟騾子說德語。當時哪怕是德國人也認為德語不夠高雅,盛行的歌劇皆為意大利語或者法語作品,輕情節而重音樂創作;瓦格納相信音樂與戲劇應當並重,引領在歌劇變革期間以德語創作的諸多歌劇都具有集中的情節和清晰遍佈全劇的主導動機(喊話《雙城之戰》編劇,學著點(笑))。
瓦格納作為基督教徒,創作《帕西法爾》所參考的素材最主要來自中世紀德語詩人沃夫朗的傳奇作品,敘述男主角帕西法爾通過考驗成為“純全的騎士”的過程。瓦格納的歌劇則將帕西法爾的傳說,改寫成一個人通過考驗成聖的過程。
但角色動機和情節更多體現了佛教思維對於同理心的理解,是瓦格納在以生平最後一部作品第一次質疑基督教。作品表現出了他自己的和解,而劇本內容中卻處處體現著矛盾。

這並不是初演劇照,但可以想象初演演員在唱這句詞的時候可能會很迷茫
初稿的創作背景是在1849年參與資產階級革命、五月起義失敗之後通緝流亡過程中,但直到1877年才完稿劇本。這段時間對於瓦格納本人來說是人生和現實社會的動盪時期,機緣巧合下從晚年叔本華那裡接收到了佛學相關思想;這其實標誌著他不僅僅對於既定的歌劇結構和調性產生了勇敢的質疑,也同樣開始反思社會思想和宗教秩序。
這樣的質疑吸引到了我們的老超人尼采先生。用達爾豪斯的話說,尼采覺得瓦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是眾神覆滅的反神學神話,但又在《帕西法爾》中“崩潰在十字架前”。可達爾豪斯給出了有理有據的反駁,我們馬上會聊到怒號“上帝已死”的老超人和歌劇革命家的糾葛。
順帶一提,香草社早期的PS4作品《奧丁領域》,就改編自瓦格納基於北歐神話創作的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其敘事結構就已然能看出《十三機兵防衛圈》的雛形,精彩的敘事手法和演出都是值得一雲的好作品。

對我而言這種畫風是種折磨,但瑕不掩瑜。

場間休息
很多朋友聽聞或者學到瓦格納是他獨特的配樂理論,尤其是關於各類動機的搭配;
但我根本不喜歡歌劇,我也聽不懂歌劇。我絲毫不會德語,在學了,但是根本學不懂。
我在聯繫我認識的學習電影配樂的朋友們分析一下舟遊本次活動的配樂演出有什麼講究;但他們都太菜了,“NL-噁心-6關”的突襲都打不過去,怕是指望不上他們。
如果讀者裡有了解配樂理論的朋友可以試著去分析一下!
寫成文章了請戳我一下,我很少有在手遊中感受到深深打動我的配樂了。

被利用並被救贖的女性:昆得麗與白金
另一個充滿戲劇性和詼諧經歷的主要角色:可憐的白金,被無胄盟玩弄於股掌之間。其實在《帕西法爾》中也有非常相似的角色。
故事中大反派克林索爾手下的女奴昆得麗就是一個因為嘲笑揹負十字架的耶穌基督而遭到不死詛咒的女性。故事的背景裡,克林索爾本是聖盃騎士,由於自己無法剋制淫慾自宮,卻因為傷害自己的身體而被聖盃永遠的拋棄,一怒之下遁入魔道並致力於利用花妖勾引年輕的聖盃騎士來報復。
之前提到老安子是由於被一位陌生女性勾引、摔下馬而被克林索爾奪走聖矛並刺傷的,這位陌生女性就是被克林索爾玩弄於股掌之間的昆得麗。她在全劇開篇就體現為瘋瘋癲癲的女傳信人,試著為受傷的老安子帶來一點藥物,也能在此看出她的悔過之心,讓她後期跳反克林索爾毫不生硬。看完通篇才會理解,昆得麗對於國王的痛苦的同情正如即將上演的帕西法爾對於射殺天鵝的同情如出一轍,這也是瓦格納編劇的功力所在。
結局的故事是昆得麗被帕西法爾所拯救,最終也因投向聖盃騎士懺悔而得到救贖。不僅作為全劇劇情推動的關鍵角色,同樣是一條交代背景的完整人物暗線。

來買兇報仇了屬於是
以這樣的故事回看《明日方舟》中白金刺殺博士的橋段,或許直到被礫格擋之時白金都始終對於自己必將被鳥盡弓藏的結局躺平了。她為自己準備的最後的保命手段,也只是趁亂碰碰運氣,看看能不能從人流中逃走。走後去哪,負傷怎辦,全然不知。
只是在自己劍指博士的同時,大量需要玩家手點的對話以實際內容側面體現了白金眼中一具說話的屍體竟然能夠緊抓各方勢力的矛盾和分裂,以發展的視角看待一場死局,這個從小攥劍張弓長大的憨憨才第一次接觸到經濟學視角,自己眼中的“上帝”分崩離析,被拆解的大型神像皮下是一個個“人”的運動和慾望流動。
在她與她眼裡同處死局的博士共情後,她摒棄了自己視若神明的無胄盟,最終選擇了羅德島完成自己的救贖。若是如此理解白金的劇情線,博士跳脫出平凡角色神化資本的視角而抓住與強大勢力博弈的時機,恰似瓦格納意識到宗教的人工之處。
白金在那一刻意識到了無論是主辦騎士競技、還是玫瑰報業的文化霸權企圖,都不過是“想要當真去相信和認識的事物,根據其象徵的價值加以理解領會,並以此通過理想的方式對它們予以呈現,讓其中隱藏著的深層的真理得以為人認識。(《宗教與藝術》,瓦格納)”從此發覺了反叛無胄盟的可能性。
雖說我們早知道白金最終安然無恙的上島,編劇也必定不會把白金人寫沒了。最終遍體鱗傷的她機緣巧合遇到了羅德島並終究得到一個溫馨的歸屬,與其在讀者角度理解成博士開後宮,不如在角色角度看作是白金在反叛信仰之後得到救贖,更能多幾分獨特的趣味。

場間休息:《頭號玩家》的主角為什麼要叫帕西法爾?
《頭號玩家》的主角為什麼要叫帕西法爾?我不懂啊,你以為為什麼這個問題會是場間休息(攤手笑)。我唯一的想法是,如果只是說《頭號玩家》的主角在與現實生活中的底層人民交往後產生了同情,從而得到救贖成為聖人,那隻能說這個名字取得中規中矩,算不上很驚豔。

宗教的缺失和新神登基
“長夜臨光”劇情發生在卡西米爾,一個東歐國家為原型的城市,但在通篇劇情中沒有渲染任何與宗教信仰直接相關的行為和角色。僅有一個格格不入的怯薛,但他的行為也更像是一種社會文化信仰,而不是流行宗教。
宗教的缺席到底是有意為之,還是商業聯合會成為了新的宗教機構?如果以宗教機構的運營模式來分析,當商業運作和流量偶像成為了新神,競技騎士則替代征戰騎士成為了教會象徵,騎士競技則是可讓“聖盃騎士”們無需進食不眠不休也能保持神力的聖餐儀式。
哪怕是無胄盟的小弓們的行為和敬畏更像是指向一種觀念,相信商業聯合全知全能、手眼通天。隨時隨地一通電話,萬里開外一根玄鐵,於是兩位青金試圖與之抗衡的意圖才格外富有戲劇性——一反圍繞感染者展開的爭奪,而是在他們的宗教體系中弒神的過程。
弒神之後?人人都想成為新神。作為媒體崛起的新神,作為商業盤踞的強神,還有武力至上的戰神。
賽事結束後,玫瑰新聞聯合報業董事的一通電話屬實營造了某種不可抗衡的邪惡力量形象,同時也以非常現代化的視角營造國與國的博弈,一反早期主線兵刃相交的現實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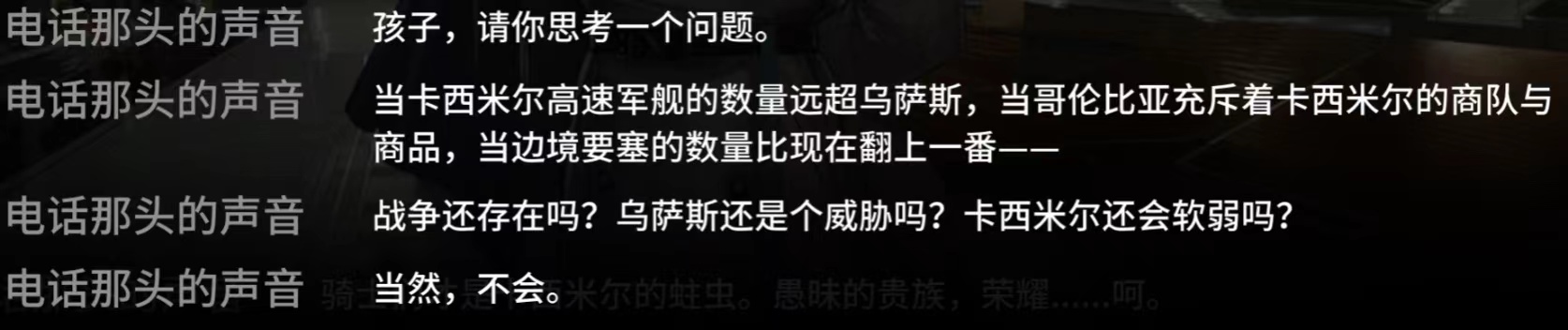
事實上媒體控制論並沒有那麼的完美無缺;也能看到編劇的創作是基於“不可能發生現世戰爭”結論的反推。
至於征戰騎士,退居監正會的身份而不是讓卡西米爾陷於兵變的火海確實讓人認同其為正派角色,但畢竟他們的爭端在於“什麼才算真正的騎士”,而不是在於用證券指數賭博試著賺幾天飯錢的底層人民過著怎樣的生活。

所以他們大概只是高高在上的騎士,而不是改變世界的同志。
場間休息
瓦格納在創作《帕西法爾》的過程中不斷的提到對於一位哲學家Samuel Lehrs的友誼和感激,但網上很難找到這位哲學家的相關資料,也沒聽說過有什麼知名的理論。可能那位友人屬於當時的“哲學學者”,而“哲學家”那時還算是一種普遍職業。

宗教的缺席:尼采和瓦格納的糾葛,以及怯薛的角色意圖
我第一眼見到怯薛這個角色的第一感覺就是,人家亮閃閃騎士打架呢關你啥事。
與當地環境格格不入的怯薛存在,很鮮明的襯托出了“宗教”和“信仰”概念之間的區別:天途比起宗教更像是一種文化,或是達爾豪斯評論中提到,也是尼采抨擊的,藝術化的宗教。不存在的可汗讓怯薛此時的信仰沒有了一個指向,淪為一種失去實質的儀式行為;他強迫著自己將旅行機械地重複下去,直至在沉默中爆發或是變態,也不願直面自己內心深處信仰缺失帶來的痛苦。
小怯薛衝著天馬們一而再地叫囂宣戰,此時在我眼中更像是一種求救:救命,請給我的行為賦予一些意義,我痛苦得快要死去了。
而聽聞他求救的人們的回應也如出一轍得很精妙:我幫不了你。
也就好像瓦格納在《宗教與藝術》中表露的,他認為宗教是在變換的歷史形象中不斷發展的真理。人們過去字字當真的神話故事,在如今變化成了一種隱喻的約定俗成。它轉移到藝術中,方可作為象徵保留其意義與合法性。
小怯薛最後也完美融入了騎士競技的舞臺,用自身的威壓和氣勢而通過藝術性的畫面,放棄了字字當真的“天途”的傳說,而是用盡情戰鬥展現出“天途”最原始也是最本真的意圖——勇氣與成長。
沒辦法,在“天途”這個故事中的至高之人“可汗”已經不存在了。小怯薛終於在得到新的可能的答案之後具備了直面缺失感的勇氣,選擇成為自己的可汗,引領自己征戰。比起單純的存在主義解讀,我個人認為理解為質疑和超越宗教行為會使得這個角色更加具有魅力。

在黑幕後給出一副藝術化的表達確實是很好的表現。而且這次用的是破折號!不是省略號了!(笑)
提到存在主義,尼采常被認為是完善其理論的重要哲學家之一;只可惜在達爾豪斯的劇評中,讀不出《帕西法爾》帶有源自叔本華的佛教相關思想、也無法對時代下宗教變革精準把握的尼采是“對基督教的教條式、實證式的認識,以及對戲劇藝術的鄙視”。
很多人都知道尼采寫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時提到上帝已死,但相對的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後幾句是什麼,也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話題在當時風行已久——尼采自己的《快樂的科學》,法國作家維克托·雨果,德國作家讓·保羅,甚至可以追溯到黑格爾的藝術終結論。真正存在進步關係的是這種藝術性表達背後蘊含的理念,也就是他們為什麼要這麼說。
尼采借“上帝已死”這一表達指出當時時代人們開始摒棄基督教所塑造的“客觀而普適的道德法律”,而失去絕對道德觀就將導向虛無主義,引起人們對於非有神論的價值觀體系的警惕。
但同時這個潘多拉魔盒也為人們留下了新的可能性:人們大可以放棄向超自然力量諂媚的尋求幫助、試著認識這個世界的新一套價值——放下過去的包袱,自由、創新的活在當下。或許是由於師出叔本華,尼采這樣的表達與佛教思想不謀而合,也引到了後來提出的超人理論。
但若是要說小怯薛成為了尼采意義上的超人,我倒是覺得目前表現出的內容來看差距很大。小怯薛剛剛展露出自己決絕的新信念就被錘爆了(不是)就脫離了劇情的敘事中心,我們並不得而知其是否會陷入接受失去可汗後的虛無狀態,再駕馭自己的虛無主義成為傳奇人物。只能說,祝他好運。

場間休息
一個有趣的傳聞是,莎樂美在初見尼采的演講上質疑尼采為什麼要說“上帝已死”而不是“上帝從未存在過”。
這是尼采的原文“God is dead. God remains dead. And we have killed him.”和1797年讓·保羅在《西本凱斯》中提到的“There is no God”形成的很有趣的對比。
而莎樂美本身出走作為沙皇將軍的顯赫家庭而去遊歷歐洲的一大動機就是對傳統宗教的厭倦和懷疑,與尼采一拍即合也是情理之中。只是他倆的故事再次證明了婚姻不適合所有交心的情人。

結語
之前和一位海外神學專業的朋友聊天,問及神學是什麼。他說神學就是教你跳大神,然後看你信不信;重要的從來不是跳大神,而是信不信。
宗教和信仰從來都是兩回事。很多人常將信仰和盲從劃等號,卻在提到大眾流行的科學觀念或者經驗常識的時候狂熱擁護,以對待宗教偶像的態度對待科學。
很喜歡DOTA解說DC老師直播時說的一段話:以前(指貼吧時代)在網上對噴的時候還會和整個寢室說我在噴人,大家一起引經據典、看看這個說法到底有什麼漏洞;現在網上的對噴都是喊口號和情緒宣洩了。
忽略信息繭房和壟斷資本的形成過程與發展狀態,一味將其塑造成不可戰勝的邪惡力量,與迷信宗教沒有什麼本質區別;身體力行地與被壓迫者共情,以實踐引領變革與反抗,可能才更貼近我們試圖批判宗教時本自以為佔據的辯證唯物主義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