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某些神秘的原因,當我在初中結束的暑假決定開始寫一個故事後,我開始了大約一年半的故事學習——通過閱讀羅伯特麥基(Robert McKee)的《故事》。麥基的“虛構藝術三部曲”(Robert McKee’s trilogy on the art of fiction)中的最後一部——《人物》——是我最近在書店中無疑發現的,而我和《故事》一起買的《對白》卻在一次選修課回來後不見了蹤影。在利用了較長的時間研讀了《故事》後,我相信麥基的這三部書旨在構建一個純粹的故事模型——用於寫作故事的模型,而非對現存的各種樣式的故事的分析(儘管這種模型可以被推廣)——一個所有行動都是為了故事寫作的方法,包括場景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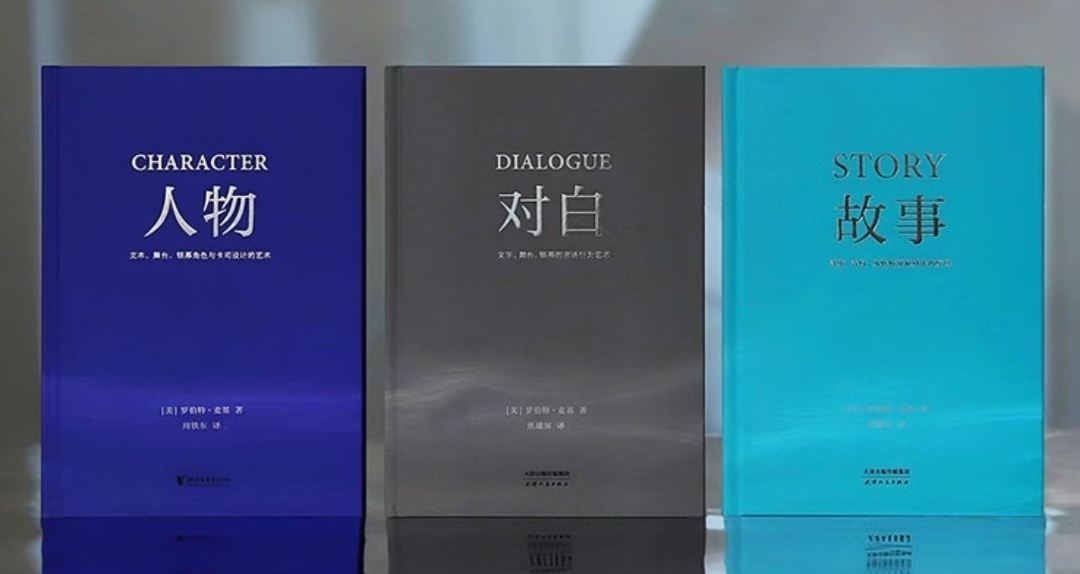
麥基在《故事》第一部分的開場後立刻開始了徹底地對故事的解構,而結論也很有趣——故事是一個有機的整合體,人物(塑造)和情節(結構)是故事的一體兩面,而背景和類型是限制結構以及提供或然性的法則。第三部分則是根據一些已經確定的故事事實來提出零碎卻有用的建議——必須存在的打破主人公平衡生活的“激勵事件”;主次情節間合適的關係;主人公需要具備的特性等等。而最後一個部分是爭對常規化的故事概念的設計的原理——對於反面人物,解說信息,人物以及(劇本)文本以及最終的“作家創造方法”。
事實上,從零開始闡述這麼一個歷經過許多思維工作的故事模型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從基礎的邏輯學工作(如皮亞諾對算數原理的解釋)就可以看出,而我在此也只是簡單呈現一些我認為最為重要的方法以及想法——耦合於我的故事學中羅伯特麥基的《故事》。
麥基書中第一個令我感到振奮的概念是鴻溝——故事的材質和能量。作者將故事描繪為“產生於主管領域和客觀領域的交接之地”之物,而鴻溝則是滿足這個條件的最小單位。若觀眾移情於主人公並有著同樣的慾望對象,這些基本的位於期望和結果之間的鴻溝就會給觀眾帶來驚奇、好奇與見解,並將觀眾帶入故事的新方向,直至人物求索的盡頭。無盡的鴻溝與鴻溝的迭代以一種十分清晰的方式解構了故事並構成了它的脊椎——人物在(生活的平衡被打破後)追求其慾望對象時進行的風險逐步遞增的與世界的對抗之旅。鴻溝的優秀之處在於它不僅十分清晰的鏈接了諸多範式的故事要素——人物、世界和情節,還能在其迭代的形式下體現結構,人物塑造以及主控思想(故事提供的“最大”見解,後文也將提及)的一體性。

故事由衝突構成,而我們人的生活也是。人和人物的基因中都刻著奧卡姆的剃刀,風險高低永遠和行動意義成正比。通過考察故事中人物在高潮時面臨的巨大風險做出的何等意義的行動,我們得以瞭解作家筆下的故事以及他到底相信什麼。麥基在《人物》中寫道,“我常常希望我能夠像我瞭解沃爾特·懷特和《絕命毒師》一樣瞭解我自己和美國”。生活不會像故事一樣給我們自己或其他的人提供故事高潮式的大風險,這似乎也是社交與政治如此令人費解的一大原因。
麥基強調主次與核心。在《故事》中你可以看到它的許多理論都是以故事為核心,而其他任何的非故事要素在創作時都應為故事服務。於是,為了進一步明確故事的本質,麥基在 “作為修飾的結構”一節中寫道,“故事講述是對真理的創造性論證”。顯而易見,故事結構上的本質和故事藝術上的本質不同,前者和生活類似,由矛盾和鴻溝組成;而後者是一個意義,是一個作者相信且願意花費數月甚至數年去闡釋的“真理”。這個真理和這種思想在書中也體現得很深刻。事實上,“作為修飾的結構”的下一節就是“主控思想”——這個名字“指出了故事的根本或中心思想,同時還暗含了其功能:主控思想確立了作者的關鍵性選擇”,這些大到高潮,小到任意鴻溝的關鍵性選擇都必須在主控思想的限制下,如果你想要創造一個極佳的對真理的創造性論證。主控思想和鴻溝在概念上都十分令人愉悅,抑或說主控思想的強大的統領性功能進一步指出了鴻溝時未明確闡明的人物塑造和結構此二者和見解(主控思想)的關係——一個好的論證應該處處自洽。

倘若你手邊有一本果麥版的《故事》或《對白》,你可以翻到它扉頁的後一頁。在一張黑白的作者照片下,有著他手寫體的“write the truth”。我認為這並不只是他自己的信仰,也更是他對每一個作家乃至藝術創作者的要求。這個“truth”也遠遠不止是真相,而是一個人相信的東西,一個基於人的相信和見解而存在的觀點,而非其不是什麼。麥基在《故事》的序言中幾個對《故事》描述完美地描繪了他的“truth”:
“《故事》講述的是原理,而不是規則。
《故事》講述的是永恆、普遍的形式,而不是公式。
《故事》講述的是原始模型(Archetype),而不是陳規俗套。
《故事》講述的是一絲不苟,而不是旁門擇徑。
《故事》講述的是寫作的現實,而不是寫作的秘訣。
《故事》講述的是如何精通這門藝術,而不是如何揣摩市場行情。
《故事》講述的是對觀眾的尊重,不是對觀眾的鄙薄。
《故事》講述的是獨創,而不是複製。”
故事應在主控思想的統領下逐步成形,對於鴻溝來說如此,對於任何其他的故事以及非故事要素也應如此。這是麥基在創造《故事》的準則,也是數學家或控制論學者闡述龐大模型的方式,它們都有著較高的完備性,也因此令人感到愉悅。從這一觀念出發,麥基將許多的建議貫穿在了他的書本之中。
較為淺顯的,是麥基對邏輯與合理性的強調。第五章“結構與人物”中的“結構和人物的功能”一節中,作者強調了塑造人物的表面形象的原則,“簡言之,一個人物必須可信:以適當的比例,足夠年輕或年老,強壯或虛弱,事故或天真,學識淵博或目不識丁,慷慨大方或自私自利,聰穎機智或頑固不化。每一種搭配都必須給故事帶來合理的素質組合,以令觀眾相信,這個人物能夠做到而且很可能做他要做的事”。在一個動作冒險電影中,主角通常是經典的肌肉猛男,很少是白髮蒼蒼的老人或者擁有過人的智慧,除非這個故事會對類型進行重建並解釋其意義——這種合理性就是許多優秀作品的主人公無可挑剔的原因。
更為深沉的,有麥基對解說信息的建議——“把解說轉化為彈藥”。將解說戲劇化的這一目的就是為了故事結構上的統一,即解說信息的揭露需要構成鴻溝,推進直接衝突,而其本身只能作為次要的目的。在幾乎最後的篇幅中,麥基又把這種追求完備的(形象系統)創作原則稱為詩化影片——強化電影的表現力。“就像所有的藝術品原因,一部電影是一個綜合體,其中的每一個物體和其他的所有形象或者物體具有關聯”,而這種關聯越多越深沉,這部電影的結構就會更加緊湊,更加靠近主控思想——非故事要素會詩化故事,增強其表現力;而故事的結構也會使主控思想獨特地呈現出來,以高潮的形式給觀眾提供最生動現實的見解,詩化這非凡的意義。
在這本書的最後,最核心的作家寫作方法也嚴格地貫穿著這一法則。麥基稱自己的寫作方法為“從裡到外的寫作”,作家將日復一日地在一張張卡片上寫作——或幕中高潮,或人物設計,抑或是簡簡單單的設定。隨著創造出的“卡”的數目逐漸增多,作家邊愈發能辨別什麼滿足於這個單一故事的或然性法則,即使其中一些“卡”具有著不俗的美感,他也因明白至少它不會出現於這個故事中。循環以往,一疊疊的卡片不僅構成了作者的故事,更讓他在對自己“卡”的反覆取捨和創造中收穫了類似鴻溝中湧出的見解——他會找到這個故事的高潮,及其對應的主控思想。於是乎,作家需要做的最後的工作便是使這個故事“自洽”,按照主控思想對其進行從尾到頭的改寫。至此,一個珠圓玉潤的故事便新鮮出爐了。
這個工作方法實在令人愉悅。重要的是,這種“寫卡”的方法不只在故事學中有所應用,因為很少有人能真正地把一些事物確定下來,也基於常常是負梯度起著完善結構的作用。法國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對宏大敘事的見解就有如此的體現——宏大敘事應該讓位於小敘事,或者更為溫和的“本地化”敘事,這些敘事可以通過引入單一時間來“甩掉”宏大敘事——基於進步主義,啟蒙解放和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永遠的真相。換句話來說,人的理性更多地體現在應用模型上,而非建立模型——即使我們能以群論為工具,哥德爾任會擋在人類進化的最後一步。然而,想要在控制論中尋求“寫卡”的共態物並不是這篇文章的重點。讓我們迴歸到故事學。
最後,讓我們來更加根本地探討一下故事成立的又一基本問題——為什麼讀者會從中收穫見解?為什麼讀者會收穫藝術的體驗?抑或為什麼讀者會相信作者相信的觀念並隨主人公一同走到了求索的最終點?不難得出,讀者對人物的移情就是答案。就像最後一個問題本質上就是答案一樣,麥基從讀者對故事的相信這一現象進行分析並創造了移情這一個概念,同時也對它的方方面面進行了擴展。在第三部分的故事設計原理的第一章“故事材質”中,麥基在“觀眾紐帶”這一節中些許地闡釋了移情——“主人公是人,觀眾也是人。當觀眾昂首仰望銀幕時,他能看出人物的人性,感覺自己也共享這一人性,對主人公產生一種認同感,並一同扎進故事裡”。
相較於純粹的音樂和繪畫藝術,故事的觀眾紐帶似乎是最為明顯的,這一點也使其變成了許多藝術的基礎——我們可以看到連環畫,或是一首寫羅密歐和朱麗葉的歌曲,抑或是現在最為出名的時間藝術——遊戲。事實上,移情指的就是人對物體或藝術及其自身關聯的意識(藝術是原始模型的延伸,自然則是原始模型的本源),相較於共情,這種在藝術體驗的情感共鳴更有一份目的性,也多多少少參與了“移”這個字的構成。
至此,我的模型中耦合的麥基的故事學已盡數呈現。當然,故事學這門複雜的藝術的極限遠非如此,但這一套基本的理論確實給我提供了更廣地進行藝術探索的思路,就像麥基的故事學給我的啟示遠非故事藝術本身一樣。
也正如麥基所強調的,故事的力量在於它的真實性和能夠引起共鳴的能力。一個故事,無論其結構多麼複雜,情節多麼曲折,如果不能觸及人心,那麼它就失去了作為藝術的意義。我們作為故事的創造者,不僅是在編織一個個情節,更是在構建一個能夠讓讀者產生共鳴的世界。這個世界可能充滿了衝突和矛盾,但正是這些衝突和矛盾,構成了故事的魂魄。
因此,當我們坐下來寫作時,我們不僅是在記錄,我們是在創造。我們是在用文字構建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有著自己規則和邏輯的世界,並創造出一種能夠超越紙張和屏幕,直達人心的體驗。
當故事最終完成時。它可能不完美,可能有瑕疵,但它是真實的,是有生命的。它是我們的創造,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和感受的體現。它是“truth”,是最純粹的故事學,也是最純粹的藝術。
這就是故事的力量,也是為什麼要有作家的原因——對我們內心深處的主控思想的熱愛。這就是故事學的終極目標,也是每一個故事創造者的追求。讓我們繼續在這條道路上前行,不斷探索,不斷創造,不斷寫作,直到我們的故事能夠觸及每一個人的心靈。
分割線~~~
這個文章本來不會這麼快完成。
我某天突發奇想,建立了近十個word文檔,每一個都以一些我感興趣或有所探討的概念命名,而這一篇最初的立項有三個詞——故事學,時間藝術和遊戲學。但出於申請香港學校的迫切需要,這個三分之一文章幾乎原封不動地變成了一個完整的文章。這似乎也指出了我文章各部分關聯性不強的缺點。但這個情景也給我了將它發表的機會,到也不是個壞事。
再整理申請香港學校的材料的同時,我也讓“重做”了新建word文檔這件事——那些原先作為標題的概念被我轉化到了一個思維導圖裡。儘管沒有新寫寫什麼,卻也十分賞心悅目。
我想我會在高考結束後完善這個三分之一文章,填充一下數不清的新建文件夾,同時開始做一些項目,各式各樣的,誰知道呢。
再回到我的文章,基於我個人的水平和精力有限,裡面不免會存在錯誤或不恰當的解釋,也請各位多加包容與理解,也敬請批評和指正,我也希望我的這個最長的暑假能見到一些更多且更有趣的人,去做一個更振奮人心的沒人知道會是什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