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很適合用來說明機核和重輕老師的牛逼
編者按
夸克、哈利-波特、主題演講、單一麥芽威士忌、路虎、荔枝果實、愛情事務、脫引指針、齊澤克、玻色子、園藝師、莫桑比克、超級馬里奧兄弟,都是公平的遊戲。
這不是一篇掉書袋和充滿文化資本的惡意文章。相反,Bogost 試圖通過「掉書袋」來最終將掉書袋的智力/學術崇拜消除。
這應該是一篇可能到 2009 年為止討論「遊戲是什麼?」這個本體論問題最全面也最時髦的回應。讀起來像 Bogost 嘗試站在哲學史的高度上來試圖描述總結遊戲研究中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時髦在於他結合了正在發生的哲學思潮,物導向本體論,而試圖為遊戲研究給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框架。
在他的討論的意義上我被說服了。雖然在某種層面上,他「什麼都沒有說」,但至少他以一個外在的視角釐清了糾纏不清的「遊戲學 vs 敘事學」的陳詞濫調,並且展現了在那之後的學者的部分討論,而我也期待中文世界的遊戲討論能早日跨過這個坑。
我不知道當時的臺下有多少人聽明白了,但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基底。
更重要的是,倘若我們能接受這種「平面的本體論」哲學視角作為背景開展對遊戲具體的討論,那至少不會出現所謂的學科和視角之間相互欺壓的鄙視,或者對商業、設計、硬件、玩家的忽略,或對學術黑話的高揚。
玩家、哲學家、工程師、設計師、人類學者,大家或許都可以其樂融融地相處。
這是一個放蕩的本體論(slutty ontology)
值得一提的是,Ian Bogost 的興趣點在於某種物質性,這或許很接近於「媒介考古」的視角,而其提倡的軟件研究,遊戲「數字性」,以及更底層的「平臺研究」毫無疑問是今天毫無技術力與創造性的人文環境所匱乏的。
而 Ian Bogost 可能是距離哲學家和學術傳統最近的一位遊戲設計師。或者說,他的遊戲研究的思考得益於西方哲學學術傳統,並目前來看有得以相接的傾向,你能夠在與遊戲無關的「物導向本體論(OOO)」的維基詞條中看到他的名字,而這或許也變相地導致了似乎近年來他更多是作為哲學家,以及泛文化寫作者來行事,附帶一系列學術雜誌、刊物的主編活動。
這是很少見的,他把自己作為信使而從遊戲研究的地下室中走了出來。
不過有些惋惜的是似乎很難看到他的新作,早年開創 Persuasive Games 公司、製作《Cow Clicker》、還有雅達利主機上的詩歌遊戲的創作行為似乎也看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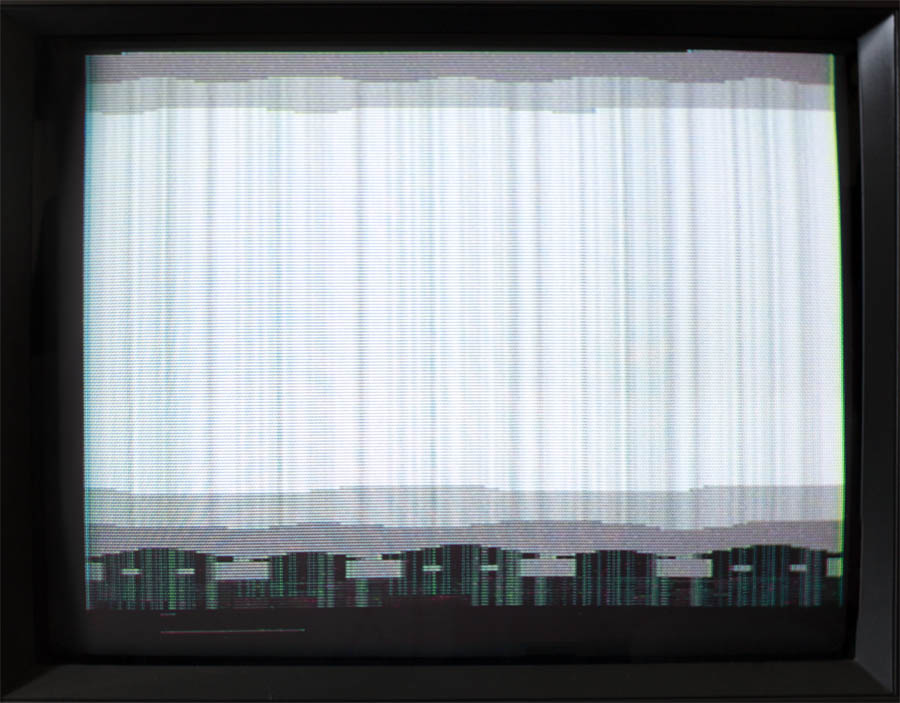
Ian Bogost: A Slow Year, Spring, Atari VCS
或許有人會問,這是否回答了落日間「何為遊戲」的困惑?
在操作層面上,是的,畢竟我想做的就是以各種創作、形態、討論來擴大對電子遊戲的定義,讓更多的力相互交織混雜。
但本體論層面呢,則還沒有,因為好的概念不僅要包容,更重要的是通過概念去創造,去引向新的認識,理解與可能性。
Ian Bogost

Ian Bogost 是一位作家和遊戲設計師,他是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電影與媒體研究項目的教授和主任及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的教授,Bogost 還是獨立遊戲工作室Persuasive Games LLC 的創始合夥人,以及 The Atlantic的特約編輯,著有《Persuasive Games》《Play Anything》《Alien Phenomenology》等。他是MIT 平臺研究相關出版系列叢書的共同編輯,還負責 Object Lessons 叢書和論文。
他的獨立遊戲包括《Cow Clicker》,這是一款《Facebook》遊戲,以及 A Slow Year,是 Atari VCS、Windows 和 Mac 的電子遊戲詩集,贏得了 Vanguard 和2010 年 IndieCade 音樂節上的 Virtuoso 獎。
電子遊戲是一團糟
Videogames are a Mess(2009)
原文鏈接:點擊跳轉
翻譯:葉梓濤
以下是我在2009年數字遊戲研究協會(DiGRA)會議上的主題演講,該會議於2009年9月1日至4日在英國的 Uxbridge 舉行。這些文字相當準確地符合於我在會議上的發言。在少數情況下,我添加了一些澄清,其中有額外相關的背景或評論。
如此多的電子遊戲研究都被一個單一問題所標記:「什麼是遊戲?」
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社區已經把這個「標記」理解為一種詛咒或瘟疫——一種形式主義的禍害,它吸引了,或者說仍然吸引著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遠離了意義、接收和使用等更重要的事。
今天我想回到這個問題,「什麼是遊戲」?希望提醒我們它到底是什麼:不是一個戰略、修辭或政治問題,至少主要不是這樣。相反,它是一個本體論問題。它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問題,而不是領域建設的問題。也許是時候這樣對待它了。
在更直接地回到本體論問題之前,讓我們簡要地回顧一下我們作為一個領域的歷史中的幾個關鍵時刻。
很久以前,吸引我們集體想象力(和憤怒)的問題是這個:
電子遊戲是一個規則的系統,或者是一種敘事?
我們非常喜歡這個問題,以至於我們甚至為它起了一個綽號:
遊戲學 vs. 敘事學
像你們中的許多人一樣,我以前也對這件事發表過一些看法。最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應該記住,是所謂的遊戲學家選擇了這些術語,而且他們做得非常優雅。
首先,看看這個詞!Ludology。遊戲學。在其所有的拉丁文的榮耀中,它給這種當時極不體面的以研究電子遊戲為生的行為賦予了一種嚴肅性。
它也是歷史性的,從 Huizinga 和 Callois 對 ludus 這個詞的使用中汲取了靈感。感覺幾乎就像你可以想象在畢業證書或名片上看到的東西。(譯註:指的是 Huizinga《遊戲的人》使用的 homo ludus 的古典遊戲的詞源作為「遊戲學」的構詞)
正如 Gonzalo Frasca 在六年前的第一屆 DiGRA 會議上試圖提醒我們的那樣,但也正如我們可以從他1998年的 DAC 論文《遊戲學遇上敘事學》(Ludology meets Narratology )中得知的那樣,這兩個概念從未打算以像「Ludology vs. Narratology 」這樣值得在拉斯維加斯的侯爵標籤中暗示的方式成為對手。相較於遊戲學的「小麥可」,敘事學與其說是 「本田活塞」,不如說是 「路易斯醫生」,它騎著自行車在前面行駛,慫恿遊戲研究這個虛弱而不發達的英雄。
(譯註:這裡都是《拳無虛發 Punch-Out !!》的角色,小麥克(Little Mac)是作品中年紀最小的選手,本田活塞(Piston Honda)是對手,而路易斯醫生(Doc Louis)是小麥克的教練,這裡的意思大概就是敘事學與遊戲學並不是旗鼓相當的對手的關係,而更像是敘事學被創造出去幫助遊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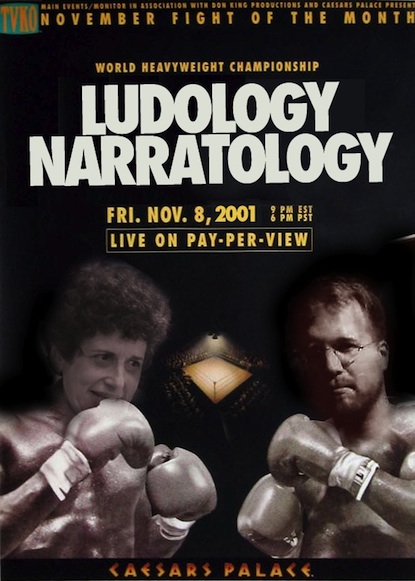
正如 Frasca 所觀察到的,遊戲是弱勢的。他正確地提出:「傳統遊戲的學術地位一直不如其他對象,如敘事學。」遊戲學的提議並不涉及與敘事學進行一場重量級的較量,而是要向它學習,把它作為一種「研究對象如何變得合法」以及「研究本身如何變得成熟」的樣本。正如敘事學的發展是設法解決敘事問題,也應發展某些新事物來設法解決遊戲問題。
問題是,整個舉動都只是一個伎倆。Frasca 認為,「必須發明*敘事學這個術語,以統一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們關於敘事的工作」。遊戲學應該為遊戲做同樣的事情。他認為,這一舉措應該解決遊戲研究中的一個 「主要問題」:「缺乏明確的定義和理論;更多的是功能主義的方法,而不是形式主義;不同學科的分析支離破碎」。
但是 Frasca 把敘事學搞錯了。它從來都不是一個統一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的術語;事實上,敘事學仍然是研究敘事的一種非常特殊的結構主義方法——注意這裡不是故事(story),而是故事和它們講述之間的差異。Frasca 最好說:「傳統遊戲的學術地位一直不如其他物品,比如海貝」。這樣的說法可能會產生較少的誤解。
然而,「敘事學」 框架的轉移掩蓋了真正的議程:朝著研究遊戲的形式主義而非功能主義的方向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弗拉斯卡的標題「遊戲學與敘事學的相遇」提供了被蒙在我們集體眼睛上的第一道陰影:這樣的 「相遇」根本就不應該令人驚訝。一種形式主義的分析方法與另一種形式主義的分析方法相遇的想法,與其說是啞劇演員轉變為泌尿科醫生,不如說是律師重塑自己為立法者。一個小心翼翼的轉折有效地重構了一個話語,發明了一個它永遠不會輸的衝突。這就像《藍調兄弟》中的一幕,艾爾伍德在 Bob's Country Bunker 問酒保克萊爾:「你這裡通常有什麼樣的音樂?」而她愉快地回答:「哦,我們有兩種。鄉村和西部。」
(譯註:意思是當時西部和鄉村音樂融合,其實這並不是兩種音樂而是一種“The country music scene of the 1940s until the 1970s was largely dominated by Western music influences, so much so that the genre began to be called "Country and Western"”,用於說明其實敘事學和遊戲學這個對偶其實本質上都是形式主義,並不真正有對立)

我強調這一點是為了讓大家注意所謂的遊戲學與敘事學辯論背後的真正目標。通過將一種形式主義與另一種形式主義對立起來,結果成為一個必然的結論:形式主義獲勝。實際上,哪一種都不重要,因為基本假設是如此相似。遊戲學/敘事學問題可能看起來是這樣的。
但實際上,它更像是這樣的問題。
遊戲是否是一個規則系統,就像故事是一個敘事系統?
分歧已經消失,答案已經隱含(是)。大衛可以放下他的吊索,把石頭扔回小河裡。這第一種遊戲的本體論實際上是一種修辭(rhetoric),根本不是一種本體論。它讓我想起了齊澤克把伊拉克戰爭比作弗洛伊德的水壺軼事。
(譯註:齊澤克用了一個笑話來諷刺伊拉克戰爭有著太多的理由從而顯得這場戰爭是牽強的:弗洛伊德講述了一個男人的故事,這個男人被鄰居指責說他把水壺燒壞了,他反對並提出了三個論點(1):我從來沒有向你借過水壺 (2):我還你水壺的時候它沒有破 (3):我從你拿到這水壺的時候,它已經破了。比喻使用彼此矛盾的論點來捍衛一個核心論點,這些矛盾的論點彼此並列。它們被呈現為矛盾本身不存在。logique du chaudron[1] ,具體可參考齊澤克《伊拉克:借來的壺[2]》,大意就是 Bogost 認為遊戲學和敘事學之爭就如同是強行尋找藉口而發起的一種修辭手法,讓我想到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杜撰王敬軒來掀起虛構的論戰而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力)
在這裡,讓我們注意到電子遊戲本體論的第一步:暗示遊戲本體論是一種形式的本體論:研究支撐遊戲整體的結構和系統,遊戲的類型或形式,整體意義上的及具體遊戲的特殊案例。
正如 Espen Aarseth、Michael Mateas 和其他人所觀察到的,對 「敘事學」(narratology)角色更好的描述是類似於 「敘事主義」(narrativism),Aarseth 描述為「這樣一種觀念,即一切皆為故事,講故事是我們主要的,也許是唯一的理解模式,是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視角」。敘事學是一種正式的分析方法,是實際的批評家在研究實際的故事系統和人工製品時使用的方法;敘事主義是一種從未被使用過的意識形態,但像所有的意識形態一樣,在背景中驅動選擇,被其干擾的主體甚至無法看到。
與遊戲學的進步同時進行,但也延伸到遊戲學之外的另一個思路是承認遊戲似乎與故事敘述(storytelling)有很多共同之處。弗拉斯卡以遊戲與故事共享的「許多元素」開始了他早期關於遊戲學的文章,包括「角色、連鎖行動(chained actions)、結局、背景設置」。在 3D Realms 開始開發《永遠的毀滅公爵》的同年,Aarseth 寫道:「聲稱遊戲和敘事之間沒有區別是忽略了這兩個類別的基本性質。......區別並不明顯,二者之間有很大的重疊」。
這一思想最值得注意的延續來自於 Jesper Juul,他從作為借來的水壺的遊戲學中退了出來,認為遊戲是由規則和虛構(rules and fiction)組成的。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重要的轉折,即遠離作為形式主義的敘事學和作為意識形態的敘事主義,而擁抱一種更加務實(pragmatic)的方法。正如 Juul 在《Half-Real》中所說。
.....電子遊戲同時是兩種相當不同的東西:電子遊戲是真實的,因為它是由玩家實際互動的真實規則組成的;遊戲的輸贏是一個真實事件。然而,當通過殺死一條龍贏得遊戲時,這條龍並不是一條真正的龍,而是一條虛構的龍。因此,玩電子遊戲就是在想象一個虛構的世界時與真實的規則互動,電子遊戲是一套規則,也是一個虛構的世界。
這裡有兩個進展。首先,有一個新的折衷論(syncretism)的接納,一個由 Frasca、Aarseth 和其他人在言辭上提出但從未認真執行的接納。Juul 認為,遊戲可以同時是可玩的(ludic),也可以是虛構的(fictive),而不必放棄其系統性或虛構性的本質。
第二,出現了一絲漸變性。對於 Aarseth 和 Frasca 來說,敘述、角色和其他源自故事的元素存在於遊戲中,但事物的天穹是形式的:它們背後的一個規則系統。Aarseth 說,當所有其他的東西都從遊戲中剝離出來時,「規則仍然存在」。對尤爾來說,這個問題稍微有點細微的差異,但儘管如此,我們看到本體論的次序在地平線上出現。
Aarseth 溫和的謾罵式敘事主義立場和 Juul 關於規則和虛構世界的更真誠的折衷立場都做出了一個共同的舉動。
Whatever a game is, some part of it is more real than another. 無論一個遊戲是什麼,它的某些部分都比另一個更真實。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遊戲本體論的一個新轉折,也就是似乎沒有人談論的那個轉折:觀念論與實在論的衝突。我們可以對這在形而上學中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的疑難,而它仍然是流行的且胡攪蠻纏的這一事實感到些許高興。它提出了以下問題:現實的本質是基於我們頭腦中的觀念,還是獨立於知識和意識單獨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與當代思想相悖,Aarseth 和 Juul 對遊戲採取了一種隱含的實在論立場,但卻是一種麻煩的立場。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固定的獨立概念,而是哲學家 Lee Braver 所說的對應性(correspondence)(A Thing of This World, pp.15-16):真理涉及思想與真實事物之間的某種對應關係。在 Juul 和 Aarseth 的立場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分層的區分。規則的形式結構是真實的,而像虛構和故事及這些規則的整體經驗是在遊玩及玩家的頭腦中的副產品。
在這裡,我們也發現了對觀念論更熟悉的反應的痕跡,那就是康德式的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當然,心智汙染了我們對現實的經驗,但這沒關係:我們對於世界的知識並不反映事物本身,而是反映我們的感知與心靈中已經存在的原則的對應性。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讀 Aarseth 和 Juul 的立場:要麼作為實在論的直接對應性理論,要麼作為超驗的觀念主義,其中像故事這樣的東西是由對已經存在的規則的觀念的推理感知而產生的。在任何情況下,有一點是肯定的:遊戲的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基本,而有些部分僅僅是主體的(subjects)偶發現象。
我們發現在遊戲設計的文獻中也有類似的運動。在 Hunicke、LeBlanc 和 Zubek 的遊戲設計的機制動力學美學(MDA)模型中,遊戲的「美學(aesthetics)」或體驗是由玩家與 「動力學(dynamics)」的互動產生的,而「動力學」又是由設計師對機制(或規則)的構建產生的,其湧現行為產生了這些動態。在這裡,我們發現了相同的對應性和超越性的怪異融合:遊戲的現實是玩家感知的構建,但這種構建更根本地存在於與機制相對應的某個深層。
順便說一句:在我們明天將聽到的另一個進展中[也就是在會議的背景下,Michael Mateas 和 Noah Wardrip-Fruin 主張一個比機制更高序列的概念。他們把這個想法稱為 「操作邏輯(operational logics)」,我把它描述為首先使特定的機制得以實現的結構。
總之,讓我們把這稱為電子遊戲本體論的第二步:暗示遊戲存在於多個層面,但有些比其他層面更真實。至少其中一些層次是心理的建構,而另一些則是物質的天穹,遊戲在其形式層次上是真實的,但這種真實比它真正的真實更具有超驗性。
最近,Juul 對遊戲學術的現狀提出了另一種看法。他認為,遊戲學和敘事學的老問題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問題,他稱之為“遊戲/玩家問題”,簡而言之,Juul 問道,研究的對象應該是玩家還是遊戲?區別很簡單:以遊戲為中心的觀點認為,遊戲玩法驅動著玩家能做什麼,而以玩家為中心的觀點則認為,遊戲玩法中發生的一切都由玩家驅動。
Juul 的觀察也強調了社會科學的興起,研究的重點是遊戲玩家的社會實踐,例如在美國的休息室和韓國的電腦房(PC Baang is a type of LAN gaming center in South Korea)中的遊戲差異。因為這種方法對玩家的興趣超過了遊戲,所以他們也出現了幫助解釋像大型多人在線遊戲(MMOG)這樣的多人體驗。我們也可以把關於遊戲作為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更少見的觀點捆綁到遊戲/玩家的難題中。我特別想到了 Alex Galloway 和 McKenzie Wark 的工作。
就 Juul 而言,他在這個問題上確定了兩種立場,稱一種為「隔離主義(segregationist)」(「遊戲是獨立於玩家的結構」),另一種為「整合主義(integrationist)」(「遊戲是由玩家選擇和維護的」)。在這裡,各種其他因素都在發揮作用,可以說,這些因素通常不會在早期的形式主義或遊戲的敘述中得到解釋。Juul 提供了一些例子,從一個玩家通過《動物森友會》與她垂死的母親關係的迷人而悲傷的生動故事,到一個人購買什麼遊戲機以及有什麼遊戲可以使用的根本選擇。在這裡,我們還發現了其他的混合型的工作,比如 Michael Nitsche 的遊戲空間理論,其中游戲空間(也就是像沙發、地毯和電視櫃這樣的東西)的作用和遊戲中的空間渲染同等,甚至更加重要。

正如「隔離主義者」這個含糊的貶義和歷史性的標籤所暗示的那樣,我認為 Juul 的意思是認為遊戲最好被認為是玩家和遊戲的交融,但很難不看到這種思路中隱含的趨向:遊戲實際上只是的軟弱的皮膚,可能存在,但只以較弱的形式,直到它們被玩家填充和激活。
讓我們把這稱為電子遊戲本體論的第三步:認為遊戲在玩家佔據了它們,並根據他們自己特定的個人和遊戲背景來重新分配其形式的屬性而賦予它們生命時存在。
我認為,此舉是是對「康德式哥白尼革命」之於形而上學的一種相當直接的改編,在這種情況下,事物主要或專門為人類而存在,事物可能存在,但卻無法脫離了它們的被思來思考這些事物。玩家群體中的背景、傳播和差異的想法發揮了強大的作用,就像它在過去幾十年的文化研究中一樣。
我想分享的關於電子遊戲本體論的最後一個說法來自我自己最近與 Nick Montfort 關於平臺研究[3](platform studies)的工作。用這個會議和組織為自己選擇的名字來說,數位遊戲研究的一個諷刺是,「數字」的東西在我們的談話中是多麼的缺席(譯註:Bogost 所參加的這個會議名字為 DiGRA 數位遊戲研究協會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例如,遊戲學一直為自己接近「一般」的遊戲而自豪。一些關於遊戲設計的流行說法也是如此,包括Katie Salen 和 Eric Zimmerman 和 Tracy Fullerton。
(譯註:前者指 NYU 教材《Rules of Play》,後者指 USC 的《Gamedesign Workshop》中文為《遊戲數字夢工廠》)
Nick Montfort 和我想得出一個區別:電子遊戲是計算性的人造物(computational artifacts),對它的理解至少需要部分地掌握計算機的架構。更強烈的是,每個電子遊戲都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點,在一個特定的計算機硬件上創建和運行的一個特定軟件。這些軟件和硬件系統單獨或共同對彼此施加壓力,向後延伸至靈感和影響,向前延伸至慣例和流派。我們希望這樣的方法可以幫助支持社會的、批評的、物質的和政治經濟的考量,而在此基礎上去理解電子遊戲等軟件製品。簡而言之,我們建議,計算媒體的一個主要的,甚至可能是首要的特徵來自硬件和軟件設計的限制。
在《Racing the Beam》(我們對 Atari VCS 的平臺研究)的後記中,Nick 和我提出了一個關於計算性創造力(computational creativity)的研究模型。我們認為,它可以採取一些重點,我們區分了五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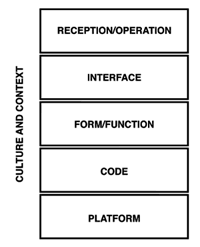
- 接受和操作(Reception / Operation)側重於用戶的體驗,包括讀者反應理論、精神分析和媒體效果研究等方法。
- 界面(Interface)側重於用戶與計算機系統的可見、可操作部分的關係,包括人機交互學科、視覺、電影和藝術史方法,以及像 Jay Bolter 和 Richard Grusin 的 「再媒介化(Remediation)」的概念。
- 形式和功能(Form and Function)著重於程序的運作和行為。在這裡我們可以找到關於程序運行的方法。順帶一說,這裡是遊戲學和敘事學的所在地。
- 代碼(Code)側重於程序員的理解與編程工作方式,包括軟件研究和代碼美學,以及軟件工程和其他用於理解代碼如何工作和構建的計算機科學方法。
- 平臺(Platform)則專注於代碼下的抽象層。如果說代碼研究是新媒體之於軟件工程和計算機編程的類比,那麼平臺研究就是之於計算系統和計算機架構的(代碼研究的)版本。
我們認為,對新媒體的有效研究往往會從這一模式的多個層次中汲取營養。但更強烈的是,我們認為我們稱之為平臺的分析層次既是有希望的,也是新媒體學術研究中未被充分探索的方面。
Nick 和我把這五個層次放在文化和背景的湯裡,而它們中的每一個都位於與人類文化和經驗的複雜關係中。例如,我們對雅達利的硬件設計的大部分討論涉及到1970年代計算機的商業和社會實踐的背景。同樣地,我們對特定遊戲的討論的重要方面涉及到工作和創造的背景和文化,包括像《Adventure》和《Pitfall!》這樣的遊戲的開發者在表達目標、文化影響和硬件平臺本身的物質性限制之間的妥協。
對這種模式有一種可能的反對意見,我們當然不止一次地聽到過。有人稱其為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但更細微的抱怨可能會指責我們是科學自然主義(scientific naturalism)。對於自然主義者來說,世界相當於由更基本、更小的事物和部分組成的集合,而真正真實的事物相當於最基本的事物。物引向部分,部分引向元素,元素引向原子,原子引向質子,質子引向夸克,等等。科學旨在探究事物的底部,並繼續挖掘,直到找到一個底部。
但是,我們的模型的目的並不是論證平臺是遊戲的根本,對硬件的仔細研究,直到金屬,將為所有現存的遊戲帶來某些粒子雨的解釋。相反,它的目的是表明平臺是遊戲中無可爭議的一部分,假裝它們不是,充其量不過是排外主義,最糟糕的是純粹的瘋狂。
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我想在遊戲的本體論中提出第四步,包含並回應所有變化,我希望它能讓我們所有人都滿意並有所幫助。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必要在當代形而上學中快速迂迴一下。

近年來,一小部分但越來越有發言權的哲學家一直在集合對後康德傳統的反實在論(anti-realism)的批判。由於它與我的興趣相關,這種批判涉及兩個相關的進展:第一,對觀念論的拒絕和對實在論的重申。第二,對存在的關注擴大到人類之外。
讓我們從普遍持有的觀點開始,也就是我們在上個世紀一直伴隨著的觀點,我們可以追溯到康德的超驗觀念論。這一立場認為,存在(Being)只為了主體而存在。對貝克萊(Berkeley)來說,它以主觀觀念論的形式出現,或者說,物體只是感知它們的人頭腦中的一捆感官數據。對黑格爾來說,它以絕對觀念論的形式出現,或者說,世界的最佳特徵是它在自我意識的頭腦中出現的方式。對海德格爾來說,物存在人類意識之外的,但它們的存在只存在於人類的領會之中。對德里達來說,事物永遠不會完全呈現在我們面前,而只是在特定的背景下,無休止地對於個體進行區分和延遲。二十世紀中期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延續了現象學開創的對意識的偏愛,但將這種自負過渡到語言。
所有這些舉動都把存在看作是一個訪問(access)的問題,而且是人類的訪問。甘丹·梅亞蘇(Quentin Meillassoux)創造了一個術語相關主義,來描述這種觀點,即相關主義認為存在只是作為心靈和世界之間的某種相關物而存在。雖然對於一些相關論者來說,事物可以存在,但在梅拉蘇的觀點中,它們只是為我們而存在。梅拉蘇在他2006年的書《有限性之後》中提供的主要例子是:相關論者不能接受「事件Y發生在人類出現之前的xx年」這樣的論述。
「不,他將簡單地添加,也許只是對他自己而言,但他會添加類似於一個簡單的附註,總是同一個附註,他將謹慎地附加在這句話的末尾:事件Y發生在人類出現之前的X年,對人類而言(甚至,對人類科學家而言)。」 (p 13)
雖然這個概念可能是可理解的,但它只是通過重印在人類過去的認知過程而變得如此。在相關主義論者看來,人類和世界都是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一個永遠不會離開另一個而存在。我們在這裡發現了與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的現代性批判類似的東西:它試圖將世界分成人類和自然兩部分。人類文化被允許是多種多樣的和複雜的,但自然或物質世界只被允許是單一的。
梅亞蘇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以「思辨實在論」為標準,試圖拒絕相關主義,重新承認存在的多重複雜性,並將存在從人類的唯一權限中解放出來,讓其迴歸到所有的對象,包括人類。現實被重新確認,人類被允許與海膽、野葛、玉米餅、類星體和特斯拉線圈一起生活在其中。
這項任務有許多方法,但我最喜歡的,也是我認為對澄清遊戲本體論最有用的,是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的方法。從海德格爾的工具分析開始,哈曼構建成他所謂的「物導向的哲學(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
非常快:海德格爾提出,物(objects)是不可能被這樣理解的。相反,它們與目的相關,這種情況使得將錘子或玉米餅作為物來談論是有問題的;這樣的物體在被背景化(語境化)時是「上手」(或 zuhanden)。海德格爾進一步認為,當物不再將自己隱藏在這些背景中時,它們最能顯現。他稱這種狀態為「在手」(或 vorhanden)。他最喜歡的例子是錘子,它提供了打釘子的活動,我們在追求一個更大的項目時,比如說建造房子時,會忽略它——除非它壞了,變得抽象了。

哈曼認為,這種「工具存在(tool-being)」是所有物體的真理,而不僅僅是「此在」Dasein 的真理:錘子、人、俳句和熱狗都是隨時隨地的,都是「上手」和「在手」的。他建議,物體不僅僅是通過「人的使用」來聯繫,而是通過任何使用,包括一個物體和任何其他物體之間的所有關係。在這裡,我們也找到了對科學自然主義的回應:事物被允許平等存在,無論其大小、規模或秩序如何。
關於這一切,還有很多話要說,但現在沒時間了。你可能會注意到與我們共同的學科更熟悉的其他傳統的相似之處,如懷特海在過程哲學中的 occasions 概念,或者拉圖爾在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中的行動者概念。但是,也許總結哈曼立場的最簡單的方式是引用他對 Lee Braver 的實在論概念的非正式補充:「人類/世界關係只是任何兩個實體之間關係的一個特例」。我想澄清的是,在這種情況下,「特例」只是指一個特定的,而不是例外。
在把我們從形而上學的水池的清爽浸泡跳出晾乾之前,我還需要遊一圈,它通過 Levi Bryant 對哈曼的面向對象的哲學的改編,變成前者所說的平面本體論(flat ontology)。這是一個首次出現在曼努埃爾-德蘭達(Manuel DeLanda)作品中的術語,他用它來指代完全由個體組成的本體論(而不是例如物種或屬)。Bryant 對這個短語的使用有些不同:一個扁平的本體論允許所有物體具有相同的本體論地位。此外,就拉圖爾而言,「對象」可以指有形的或無形的實體,包括意圖的對象(objects of intention):夸克、哈利-波特、主題演講、單一麥芽威士忌、路虎、荔枝果實、愛情事務、脫引指針、齊澤克、玻色子、園藝師、莫桑比克、超級馬里奧兄弟,都是公平的遊戲。如果稱這些東西為「物(objects)」讓你感到困擾,你可以用我的術語「單位(unit)」來代替它,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好了,終於回到遊戲上來了。在我與你分享的所有關於遊戲本體論的觀點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共同的屬性:所有這些觀點都陳述或暗示了電子遊戲對象的本體論等級。在某些情況下,這種等級是科學主義的一種,比如對新媒體層次的(錯誤)解讀,或者操作邏輯、機械學、動力學和美學之間的關係。在其他情況下,這種等級制度是一種反實在論的自然/世界之分,如 Juul 的想象世界和真實規則,或玩家對遊戲的應用和遊戲本身。

如果我們接受哈曼和布萊恩特的邀請,使本體論領域扁平化,使所有對象處於平等地位,那麼結果就是一個無差別的平面,在這個平面上,遊戲存在的所有方面都有同樣的可能性。然後我們可以提出的問題是,對於一個特定環境下的特定遊戲,哪些單位是重要的?這樣的策略使我們免於尋求何種遊戲對象無可爭議的依據,防止我們對計算機硬件或人類經驗(或兩者之間的任何東西)提出短視的本質主義,並迫使我們對特定的分析情況提出更具體的問題。對於「什麼是遊戲」這個問題,尋求一個答案應不再令人滿意。
這不僅僅是號召我們大家和睦相處,也不僅僅是呼籲一個不明確的德勒茲式的內在性或集群(assemblage)的平面。這不是魔術,也不是空洞的理論。它是一種思考遊戲的存在(existence
)的實際方法。
舉個例子是有必要的。我想,鑑於其中一些材料的深奧特性,最好選擇一個大家熟悉的電子遊戲,一個每個人都能立即意識到其重要性和品質的遊戲。

什麼是 Atari VCS 上的《E.T》?有很多方法可以回答。
《E.T.》是8千字節的6502操作碼和操作數,你可以在 ROM 本身的十六進制轉儲中看到。每個值都與一個處理器的操作相對應,其中一些操作也需要操作數。例如,十六進制$69是增加一個值的操作碼。
裝配好的 ROM 實際上只是遊戲彙編代碼的重格式化版本,而《E.T. 》也是它的源代碼,是一系列人類可讀的(或者說是稍微可讀的)機器操作代碼的助記符,用於運行該遊戲。
《E.T.》是一束射頻調製流(RF modulations),它是由用戶輸入和程序流改變了被稱為 TIA 的定製圖形和聲音芯片上的內存映射寄存器中的數據而產生的,它又被轉化為無線電頻率,與電視的電子束和揚聲器一起運作。
《E.T.》是一個掩膜 ROM ,一個集成電路,其上的存儲器(在這種情況下價值8k)被硬接到一個蝕刻的晶圓上。這類 ROM的光罩(photomask )設置成本很高,但好處是量產非常便宜,量產當然是電子遊戲 E.T. 的主要特點之一。
《E.T.》是一個用螺絲釘固定的成型塑料盒,上面貼著一個膠粘標籤,依次印有膠印標籤。
《E.T.》是一種消費品,是一種包裝在盒子裡的產品,零售時有印刷的說明書和包裝紙板,掛在鉤子或放在架子上。
《E.T.》是一個產生某種體驗的規則或機制系統,這種體驗在某些方面與一個虛構的外星植物學家滯留在地球上的故事相對應,他的名字叫 E.T.,一群孩子試圖保護他不受政府和科學暴力的仇外心理的影響。
《E.T.》是一個可以擁有、保護、許可、銷售和侵犯的知識產權單位。
《E.T.》是一種收藏品,是一種絕版或「稀缺」的物品,可以進行交易或展示。
《E.T.》是一個標誌,描繪了1983年崩潰的情況。在這個意義上,《E.T.》這個標誌不僅僅是一個虛構的外星植物人,而是一個極端失敗的概念,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遊戲」:它是的貪婪文化情結和設計約束導致了在阿拉莫戈多垃圾場的著名的遊戲墳場,是隨後被過度簡化的替罪羊過程——換句話說,「E.T.」是 Atari 的 「滑鐵盧」。
所有這些單位同時存在,但又彼此獨立。沒有一個「真正的」《E.T.》,無論是敘事的結構、特徵和事件,還是產生它的代碼,或者兩者之間的任何東西。拉圖爾稱其為不可還原(irreduction)。「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被還原成其他東西」,即使一個事物的某些方面可被認為是對其他事物的改造。
事實上,有一些工作是從這些視角中來看待遊戲的,例如 TL Taylor 對《無盡的任務》,Seth Giddings 對技術文化,Bart Simon 對 Wii 的工作等等,我在這次演講中的興趣在於提出本體論的主張,而不是社會/政治的主張,這一點的進一步澄清需要行為者網絡理論的突破。更多的內容可以在我2008年的《計算機遊戲哲學》主題演講中找到,更多的內容可見我即將發表的(2009年11月)SLSA 主題演講。
拉圖爾通過網絡的概念來處理變換的過程,網絡由行為者(可以是人或非人)的相互行為,進入和退出關係組成。我的「單位操作概念」提供了另一種模式,一個單位由一組其他單位(同樣是人或非人)組成,不考慮規模,由一種類似於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的「計數為一」(compté comme un)的姿態構成。單位操作與拉圖式的網絡和行動者有著重要的區別,但我必須把這個澄清留待他日。
總之,這些進展使我們能夠在相關主義(媒體研究和遊戲的社會科學分析中常見的問題)和還原論的兩難(對遊戲的形式和材料分析的常見批評之一)之間行走。讓我們考慮兩個簡單的例子。
關於相關主義,昨天我們聽到 Graeme Kirkpatrick 爭論說,遊戲不能參與意義,因為它們的結構本身就與意義相悖(這發生在前一天的美學討論小組中)。同樣地,就在我去參加會議之前,遊戲設計師 Frank Lantz 發表了他的論點:《遊戲不是媒體 Games Are Not Media (2009)》。這樣的觀點拒絕了一些人(包括我自己)關於遊戲確實能夠建構意義和進行論證的主張。然而,平面本體論的好處是,我們不需要認為遊戲只能表意,Graeme 、Frank 和我可以繼續像迪斯科舞廳裡的啞劇演員和泌尿科醫生一樣相處。

此圖由譯者補充
關於還原論,當 Jesper Juul 一年前[發現了《吃豆人》投幣遊戲的拆解程序 ROM 時,他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就是Pac-Man 的真實面貌嗎?」 答案是肯定的,在某種意義上。《吃豆人》的代碼在很大程度上是真正的《吃豆人》。但是,從另一種意義上說,它並不是《吃豆人》事物的全部。
同樣,《E.T.》也從來不是剛剛提到的事物之一,它也不僅僅是所有這些事物的集合。矛盾的是,一個扁平化的本體論允許它既是又不是。我們可以區分「遊戲即代碼」和 「遊戲即遊玩過程」的本體論地位,而不必求助於某種作為形式、類型或超驗的遊戲的高階概念。用 Levi Bryant 的一個玩笑的術語來說,這是一個放蕩的本體論( slutty ontology),在這個本體論中,任何東西都足以讓人玩得開心。

同樣地,關聯主義的批判的一種解讀方式不是拒絕關聯,而是拒絕唯一的關聯(對梅拉蘇來說,存在-思想;對哈曼來說,存在-人類),接受多種關聯,只要我們願意或需要,就可以。當哈曼聲稱人與世界的關係只是任何兩個實體之間關係的一個特例時,這當然是他的立場。如果我們認真對待放蕩的本體論的誘惑,我們可能會預見一個本體論增殖的新時代。
這樣的視角帶來了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遊戲研究不僅意味著對遊戲的研究,或作為遊戲規則的研究,還意味著作為計算機的規則,或作為計算機的操作邏輯,或作為硅片的彈殼,或作為寄存器的指令,或作為無線電頻率的電子槍的研究。而遊戲不僅是為人類的遊戲,也是為處理器、為塑料盒外殼、為盒式總線、為消費者、為記憶載體等等的遊戲。這是一個完全沒有探索過的領域,也是我最有興趣探索的方向。
最後一件事:我們可以把這種雜亂無章的東西稱為什麼,它取代了我們以前對「什麼是遊戲」這個問題的過於簡化的、等級制的和相關主義的答案?
儘管我想抵制拉圖爾的存在只通過關係而存在的概念,以及他相關的網絡的概念,我認為這些概念過於規範化了,但我們倒是可以採用他「亂局」imbroglio 的概念,一種「永遠不清楚誰和什麼在行動」的混亂(Reassembling the Social, p. 46),拉圖爾最初的例子是與人類知識有關的,例如閱讀報紙的方式使我們捲入了不同領域的糾結中,它們相互聯繫但又相互混合。拉圖爾這樣寫道:
混合[報紙]文章勾勒出科學、政治、經濟、法律、宗教、技術、虛構等方面錯綜複雜的局面。...... 所有的文化和自然每天都在被攪動,...... 但似乎沒有人為此困擾。 ——《我們從未現代過》,第2頁
但是拉圖的「亂局」感覺太正式了,對我來說太有條理了。亂局是一種智力上的困境,這肯定如一團亂麻,但這團亂麻是戴著領帶的。
也許我們可以採用演員網絡理論家約翰-勞(John Law)的說法來代替。Law 講述了一個故事,他與一位合作者進行了一個研究項目,兩人調查了一家醫院信託基金處理酒精導致的肝病患者的方式。正如在許多官僚主義的情形下,他們很快發現了其巨大的邏輯複雜性。在某些情況,而不是其他情況下,來自市中心諮詢中心的病人被建議去治療項目,但他們必須預約。然而,許多人並不這樣認為,而認為它是一個隨到隨治的地方。Law 實事求是地總結說,這種情況是一團「混亂(mess)」。
Law 反思了作為方法論關注的混亂概念,這個概念抵制創造整齊的小堆的一致的分析。相反,有必要追求「非一致性(non-coherence)」。Law 說:「這就是談論'混亂'的問題:它是那些痴迷於使事物整潔的人所使用的一種貶義詞。相反,我更傾向於放鬆邊界控制,允許非連貫性的東西表現出來。或者更確切地說,開始思考我們可能採取的方式。」

請注意 Law 的混亂和結構主義方法的形式主義之間的區別:它不是一些說明所有事情的總體系統操作,一套文化道德或一套在光亮的樺木地板上舉行的特別精心安排的狂歡的規定,而是一個鬆散並快速的單位的結構化——為了——什麼任何事,不僅僅是為了事件牽涉的人類演員。
混亂不是一堆東西,即使位於難以落腳的地方,也能整齊地組織起來。混亂不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優雅事物。它不是一個由穿著馬甲的保險商評估和管理風險的智力項目。一團混亂是一堆不方便的、有時令人厭惡的東西。
它不像在波洛克或畢加索的畫作中發現的那種混亂,而更像在凱因霍爾茨(Keinholz)的雕塑中發現的混亂。
混亂是意外(accident)。混亂是一種你在你不想要的地方發現的東西。混亂是當你錯過了鬧鐘,抓住了水杯時,地板上一串串的碎玻璃。混亂是凳子上的一堆熱乎乎的、看不見的狗屎,然後是凳子上和靴子底的。混亂是不優雅的,是雜亂的,是凌亂的,是恐怖的。我們對它感到畏懼,但它就在那裡,我們必須處理它。
電子遊戲是一團亂。
一團我們並不需要一直試圖清理的混亂,如果有可能的話。
References
[1] logique du chaudron
[2] 伊拉克:借來的壺
[3] 平臺研究

Keinholz的雕塑,譯者補充
封面:選自《The Policeman's Beard Is Half Constructed》中 Joan Hall 所繪製的插圖,在插圖邊上的詩歌是這樣寫的:
許多被激怒的精神病學家正在煽動一個疲憊的屠夫。屠夫疲憊不堪,因為他已經切了幾個小時和幾個星期的肉、牛排和羊肉。他不希望與狂暴的精神病學家一起吟唱任何東西,但他唱起了他的琴絃切除師,他夢見了一位宇宙學家,他想到了他的狗。那條狗叫赫伯特。 —— 計算機詩人 RACTER .1984
落日間是一個探索「何為遊戲」與「遊戲何為」的媒體實驗室。
日 | 落譯介計劃是媒體實驗室落日間對一些有助於思考遊戲/電子遊戲的外文文本翻譯和推薦/索引計劃。(鏈接有點多了,做了一個網站來索引)
感謝朋友們:@小雨 @阿偉 @11 @昕仔 @某小熊貓貓 @少楠 @Bob傅豐元 @小河shan @希辰Xichen @小樂 @DC @Bynn @webber @紳士凱布雷克 @侯晨鐘 @Minke @Roam @兜&敏 @KIDD @菲茲 @喵嗚 @李喆 @特特 @Skellig @阿和 @某大王akak1dD @solsticestone @魚片與花捲 @Stoney @樹袋熊 @MrNewton @鴨脖拉罕 @松果 @五香丸子@紀華裕 @李朵拉 的贊助及所有關注者的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