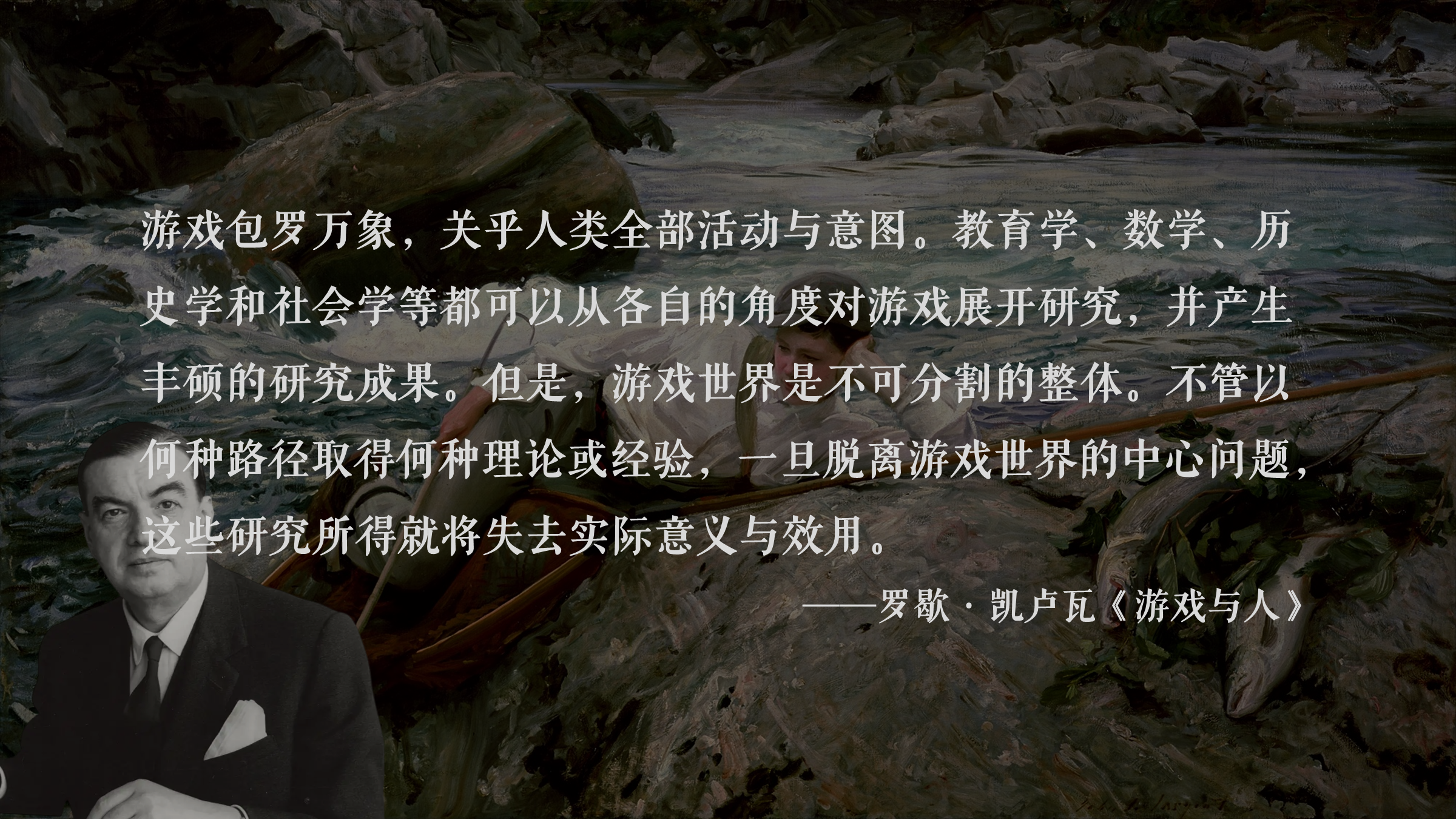
0.寫在前面
關於作者
羅歇·凱盧瓦(Roger Caillois,1913—1978),法國作家、哲學家、學者,研究領域橫跨人類學、社會學、哲學、文學理論,專注於遊戲理論和原始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神話與人》(Le Mythe et l’Homme,1938),《人與神聖》(L’Homme et le Sacré,1939),《遊戲與人》(Les Jeux et les Hommes,1958),《石之書》(L’écriture des pierres,1970)。
關於本書
《遊戲與人》(1958,原書在1961年由Meyer Barash譯成英文)是凱盧瓦對赫伊津哈的遊戲理論經典著作《遊戲的人》(Homo Ludens,1938)的直接回應。在本書中,凱盧瓦吸收了大量來自兒童教育學、動物行為研究、數學等其他領域的研究成果,通過明晰的類型學剖析拓展了赫伊津哈基於人文主義的遊戲理論。
凱盧瓦和赫伊津哈都將遊戲視為一種基礎性的人類活動,並在一定程度上對“遊戲是文化產生的必要條件”這一觀點達成了共識。但凱盧瓦並不認同“人即遊戲,遊戲即人”的人類本質價值規定,恰恰相反,在《遊戲與人》中,凱盧瓦暗示作為人類活動的遊戲和從事遊戲的人必須區分並分別得到充分的研究。儘管兩者之間存在著大量複雜的互動,但對兩者的混為一談是有害且缺乏意義的。
正是在這樣的方法論自覺下,凱盧瓦實際上建立了一種新的遊戲本體論。他指出赫伊津哈對人類尊嚴——競爭精神的強調使其忽視了賭博等機運類遊戲的存在。與此同時,他對遊戲類型(競爭-機運-模仿-眩暈)和遊戲方式(戲耍-技遊)兩種範疇的分類也建立在其對“遊戲”與“人”的區分之上。
在他對遊戲本質的著名概括(自由性、抽離性、不確定性、非生產性、規則性、虛構性)中,凱盧瓦尤其強調虛構性和規則性。他認為,遊戲通過遊戲規則嚴格地抽離於日常活動,是人類的原始衝動(動因)而非遊戲本身導致了遊戲類型(而非遊戲方式)的變質(腐化),遊戲也並非文化演進的初級或退行階段產物,而是兩種作用領域不同但相互補充的人類運轉機制,它們共同表現著人類的基本動因。
誠然,和絕大多數遊戲理論經典一樣,凱盧瓦的《遊戲與人》在發表後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但這部“赫伊津哈之後遊戲本體論新的宣言”實際上鼓勵著人們從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數學等學科的夾縫中跳脫出來,而把注意力直接放在(作為一個整體的)遊戲世界的中心問題上來。
從某種程度上說,凱盧瓦預言了電子遊戲興起後遊戲理論的美好可能進路:遊戲的人學與人的遊戲學相互尊重、共享成果、相互促進。到那時,赫伊津哈所倡導的人文精神將得到更充分的實現。
(札記只寫到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凱盧瓦基於廣義遊戲論的文化史研究)
1.遊戲作為一種特定的人類活動:遊戲的本質
凱盧瓦開篇就把矛頭指向了赫伊津哈對遊戲的定義。他直言《遊戲的人》研究的不是遊戲本身,而是“遊戲精神的文化效用”
,也因此,赫伊津哈淡化了遊戲本身的描述和分類,把理想化的、僅限於競爭類遊戲規則的遊戲精神反過來嫁接到所 有遊戲上,同時也就導致了忽視能夠產生物質利益的賭博和機運遊戲的偏頗。不過,他也肯定了赫伊津哈對遊戲自由性、規則性、虛構性和日常獨立性的深刻洞見。
在赫伊津哈的基礎上,凱盧瓦提出了全書最為著名的遊戲本質六大特點:一、自由性,玩家不能被迫參與遊戲;二、抽離性,遊戲發生在一個特定的時空限制範圍之內;三、不確定性,遊戲的進程和結果不能完全確定,玩家在遊戲過程中掌握了一定的主動權;四、非生產性,遊戲至多隻能轉移資產而不能創造資產,或者說遊戲至多隻能是經濟交易的方式而非經濟生產的實質;五、規則性,遊戲需要暫時擱置慣常的規則而採取專屬於遊戲的規則。六、虛構性:遊戲過程是對次現實,而非日常生活的認識。
凱盧瓦強調,遊戲的非生產性並不意味著遊戲不涉及經濟利益,而是指遊戲所牽涉的經濟行為僅由玩家產生,並對玩家產生影響。這一針對赫伊津哈的觀點成功地把機運類遊戲引入了遊戲的分類範圍之中。
另一方面,凱盧瓦也強調遊戲規則對遊戲空間本身的優先性和與日常生活的分離性。他指出,遊戲規則的嚴肅性對於任何參與到遊戲當中來的玩家是必須的,即便這些規則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可能是荒謬的、奇怪的。於是,看似沒有規則的角色扮演(模仿類遊戲)也被納入到了遊戲範疇之中。
實際上,在引言中,凱盧瓦已經通過對法語的“遊戲”(jeu,動詞形式為jouer)一詞的語義學分析,指出了遊戲對文化發展的貢獻:競技類遊戲將發展為體育運動、模仿或幻想遊戲是戲劇表演的前身、機運類遊戲則是概率論等數學理論的起源。凱盧瓦的野心在於進一步拓展遊戲的可能類型,從而擴充遊戲研究的範圍。那麼,為了容納特定的遊戲類型而考慮進來的某些本質特點定義,即使是相互矛盾的,也不應該輕易拋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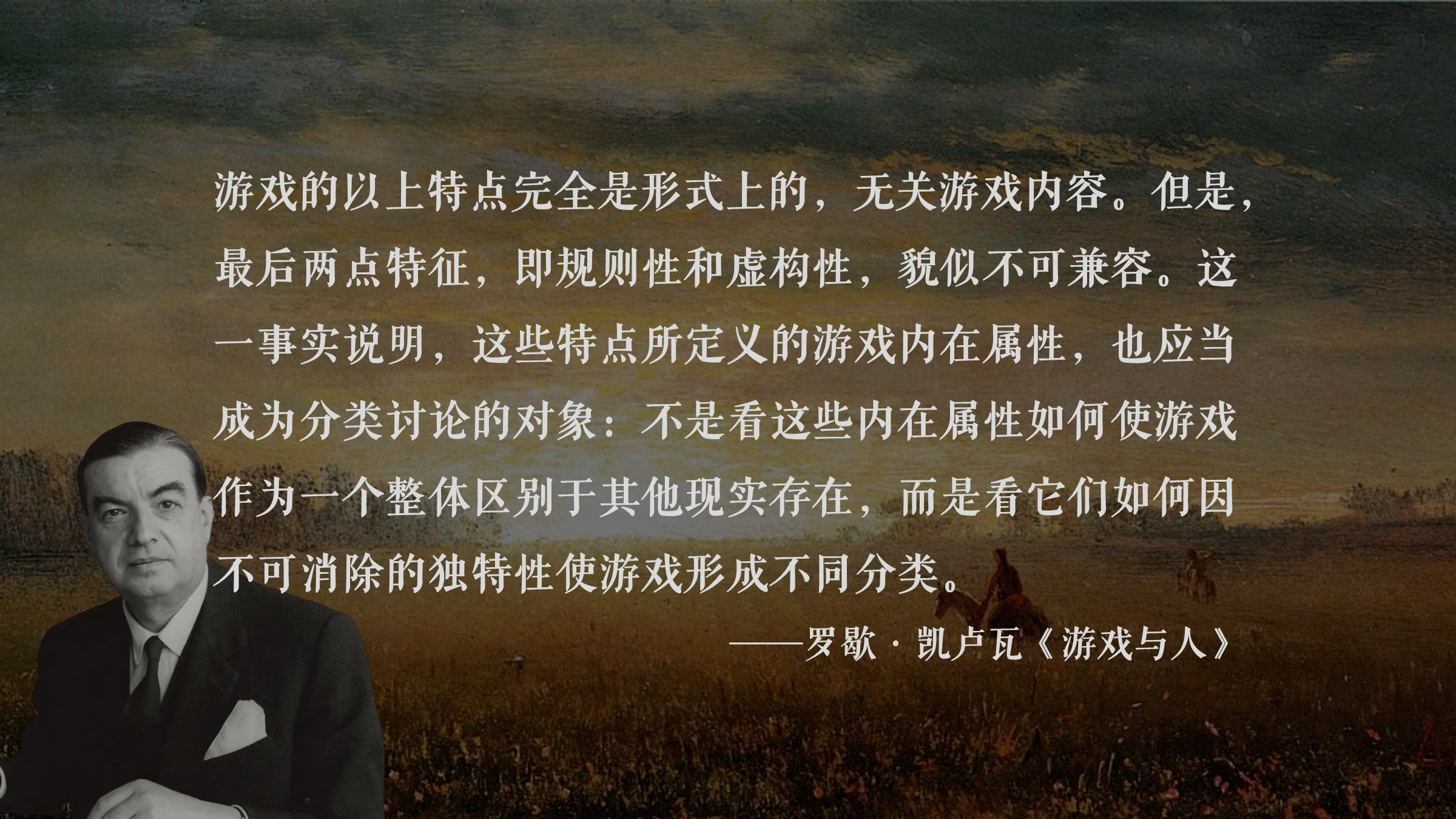
凱盧瓦認為,遊戲的規則性和虛構性之間可能存在衝突,即玩家在次現實的世界中為什麼還要嚴肅地對待某些規則;反之,遊戲規則的限制也會削弱遊戲的幻想性嗎?不管怎樣,這些疑惑不應該是遊戲研究(放棄)的終點,而恰恰應該是起點:對遊戲本質的探討並不是為了建立一種抽象的遊戲大一統理論,從而囊括歷史上所有形式的遊戲,而是為遊戲類型學的探究指明方向——特點的模糊之處正是類型分歧的可能之處。
2.遊戲的類型學與玩家的類型學:兩種類型學的分離與結合
在第二章中,凱盧瓦根據不同遊戲對根本特徵的反映,將遊戲劃分為四大類別:一、競爭類遊戲(agôn),二、機運類遊戲(alea),三、模仿類遊戲(mimicry),四、眩暈類遊戲(ilinx)。
競爭類遊戲強調遊戲規則對每位玩家的絕對公平性,即使參與者的實力懸殊,遊戲也會通過玩家讓步的形式構建平衡。機運類遊戲與競爭類遊戲相反,玩家面對的是命運,遊戲的公平建立在機運對所有參與者的一視同仁,消除任何非命運的因素。模仿類遊戲要求玩家暫時接受一種幻象、一種虛構世界的協約,暫時成為他者或被認作他者。眩暈類遊戲追求眩暈感,以帶有快感的迷亂刺激取代清晰意識。
這四種分類是凱盧瓦深思熟慮之後的得意之作,亦是後續章節的基礎。但在此之外,凱盧瓦還引入了另外一個類型學的維度,稱之為遊戲的層級(在後面則稱之為遊戲方式)。遊戲方式,從根本上說是指玩家參與到遊戲中來的方式和態度,任何類型遊戲的實際發生都是以一定的遊戲方式為前提的。在“遊戲方式”這個連續函數的內部,一極是戲耍(paidia),另一極則是技遊(ludus)。戲耍的玩家是無準備、無規則地遊玩的,他們追求躁動、喧鬧、輕鬆、自由,並不在意遊戲的混亂。技遊的玩家則刻苦、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遊戲中,把遊玩視為一種專門化、規範化的技術。凱盧瓦也指出,技遊的另一個特徵還在於追求潮流,即玩家對展現技術的熱忱超越了特定的遊戲種類,不斷與時俱進、推陳出新。
凱盧瓦認為,遊戲方式體現著玩家對遊戲規則的理解,正是它使得遊戲成為具有孕育力的文化工具。凱盧瓦在遊戲理論方面的洞見性也在於此。他意識到了,遊戲活動中的遊戲與人,分別承擔著不同的功能和作用。遊戲是人所從事的活動,不是遊戲本身,而是遊戲著的人利用遊戲創造了文化。那麼,一種合理的、真正關切到了遊戲世界中心問題的類型學,首先要承認兩種研究對象的獨立存在。就此而言,凱盧瓦使兩種類型學分離了,這也使得遊戲理論獲得了自省的規範:將遊戲與人混為一談只能是範疇錯誤的謬見。
只有遊戲的人與人的遊戲事先分離了,兩者的結合才是有意義的。凱盧瓦認為,遊戲方式可以和各種遊戲類型結合,但某些結合情況在事實上並不可能,如戲耍與機運類遊戲、技遊和眩暈類遊戲。
此外,凱盧瓦還特別指出了中文中的“玩”字囊括了從戲耍到技遊的全部價值追求(玩弄、玩耍、把玩、玩攝影等)。特定的文化傾向於以某種遊戲方式(態度)接受著某些類型的遊戲,文化的密碼一部分就藏匿在人們對遊戲的偏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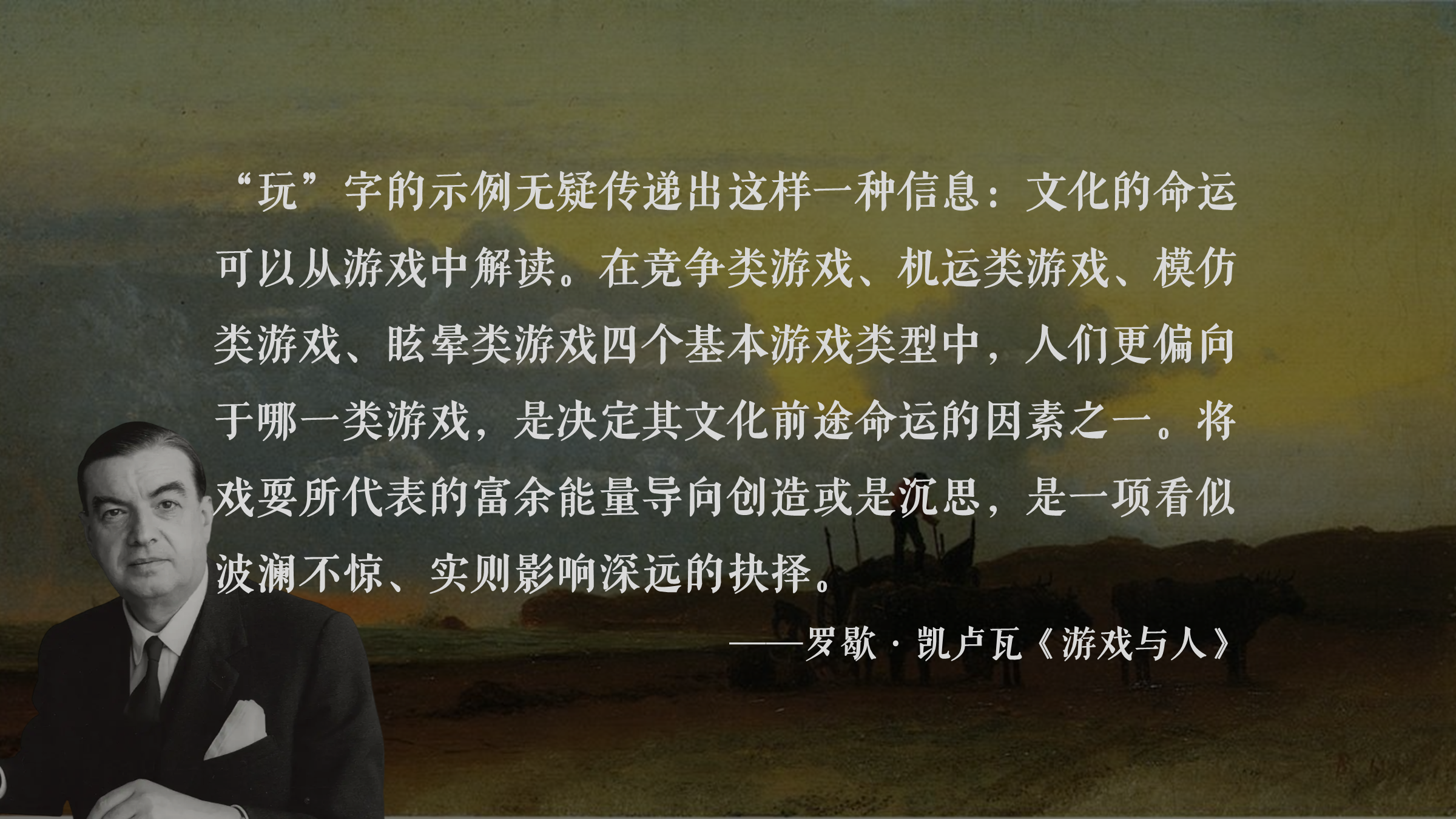
3.人害遊戲,而非遊戲害人:遊戲的變質
基於對兩種類型學的區隔,凱盧瓦在第四章探討了遊戲的“變質”(corruption,在法(英)語中既可以指詞語的變體形式,也可以指使“人”道德敗壞的行為,凱盧瓦反用其義,旨在倒轉人們對遊戲的價值觀察角度)。
凱盧瓦強調,遊戲的本質特徵將遊戲與現實(日常生活)嚴格地分割了開來。遊戲著的人如果取消了這一界線,就會腐化遊戲。遊戲所受到的這種變質在不同的遊戲類型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主導各種遊戲的心理因素(在後面也稱之為原始衝動或動因)保持著相對的穩定。它們主要是憑藉個人才幹脫穎而出的勝負欲(競爭類遊戲)、被動等待裁決的命運感(機運類遊戲)、扮演另一種身份的熱忱(模仿類遊戲)和對眩暈的追求(眩暈類遊戲)。
當遊戲發生變質時,界線的取消沒有使遊戲世界發生崩塌,而是使原本由遊戲規則框限的、作用在特定時空內的原始衝動擴散到了日常生活中,把日常生活一起吸納進了遊戲世界。人的無限衝動引發了遊戲的變質,進而造成了人的變質(腐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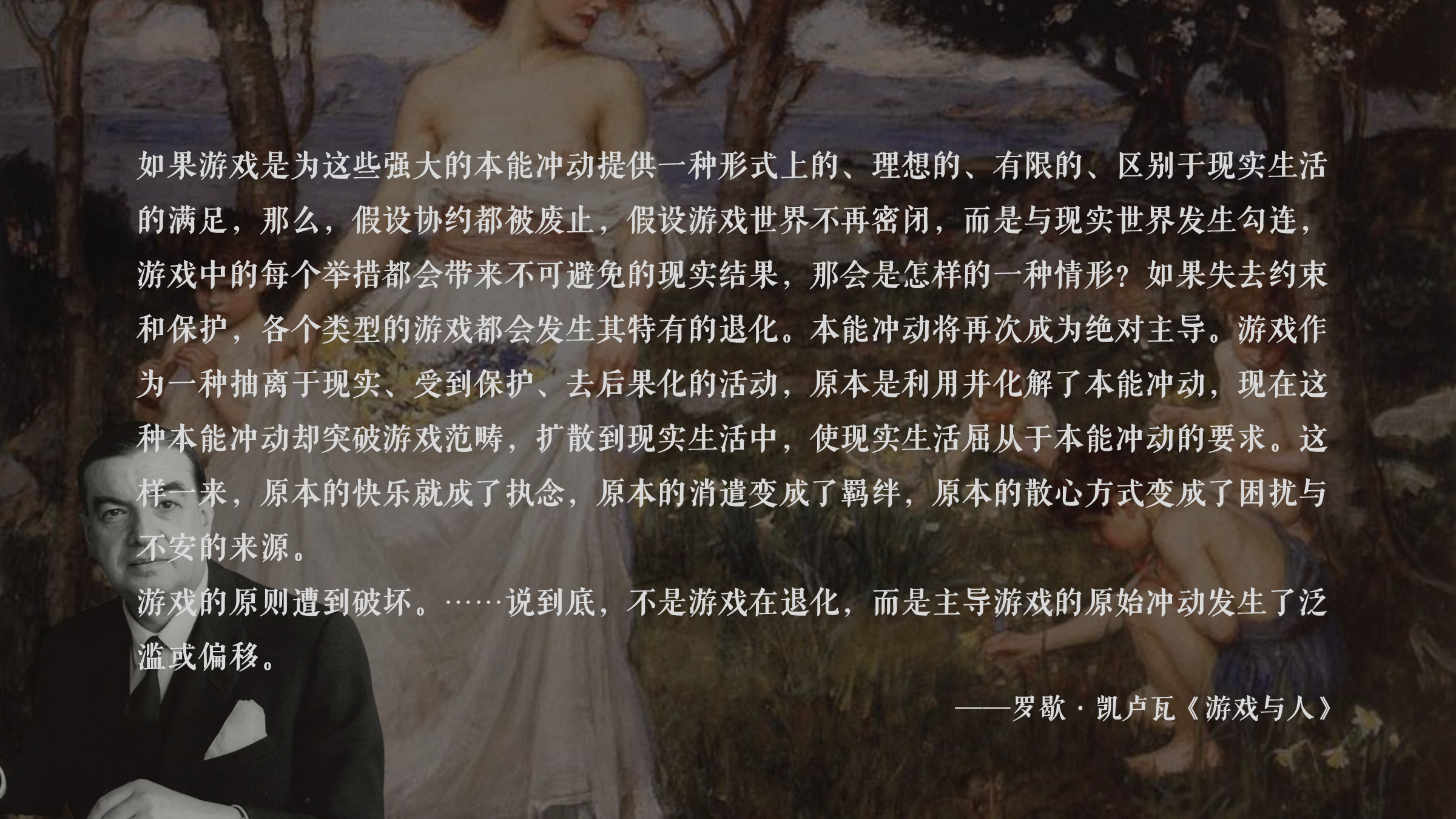
凱盧瓦進一步分析道,遊戲違規者(作弊者)逃避遊戲規則,但又恰恰利用了其他玩家對規則的遵守,他們並沒有改變遊戲世界本身,而是影響了其他玩家對遊戲的參與;遊戲的職業選手也不會改變遊戲的性質,他們只是有特殊化的遊戲目的,並由此影響著自身的遊戲方式。
在這裡,我們再次看到了凱盧瓦對遊戲與人區分研究的方法論自覺。在他看來,遊戲的變質歸根到底是玩家層面的議題。基本動因在於遊戲者而非遊戲,也只有遊戲類型而不是遊戲方式才可能受其影響發生變質(腐化),而遊戲對人類文化的作用(不論有益無益),嚴格來說應該是遊戲對人的反作用。
隨後,凱盧瓦概括了不同類型中游戲變質的表現。
在競爭類遊戲中,主導的遊戲規則要求參與者信任裁決的公正性,在公平競爭之中,付出了巨大努力即使遭遇慘敗,也能落落大方接受結果。這一規則限制了人的貪婪本性,保證了玩家的有效參與。但在變質的競爭類遊戲中,現實世界殘酷、不完美、充滿漏洞的道德、法律、社會約束體系破壞了遊戲者對競爭原則的支持,使其懷疑乃至否決裁判的公正,玩不起、也輸不起遊戲。
在機運類遊戲中,對命運的絕對信任被嚴格地限制在抽離的、無生產性的遊戲世界之中。但經過變質,遊戲者產生了對日常生活的怯懦而將自己寄託於外部力量和天賜良機,在紙牌、星象、占卜等活動中謀求機遇,這就是迷信。
在模仿類遊戲中,模仿的角色、裝束或面具至多是惟妙惟肖的擬真。但在變質的模仿中,遊戲者不再是扮演另一個人,而是直接成為另一個人。他忘記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完全異化為了他者。
對眩暈類遊戲來說,眩暈感和在日常生活中一樣受到了嚴格的、儘可能安全的限制。變質的眩暈遊戲為了製造持久的眩暈感,從即時的物理效應轉向混雜的化學反應。只有中毒
和隨之的自我摧殘才能帶來平常化的刺激感受。
簡而言之,暴力、陰謀、迷信、異化、多重人格、成癮都是遊戲變質的表現。遊戲的失序同樣也會腐化人,而遊戲的守序則是文明進步的標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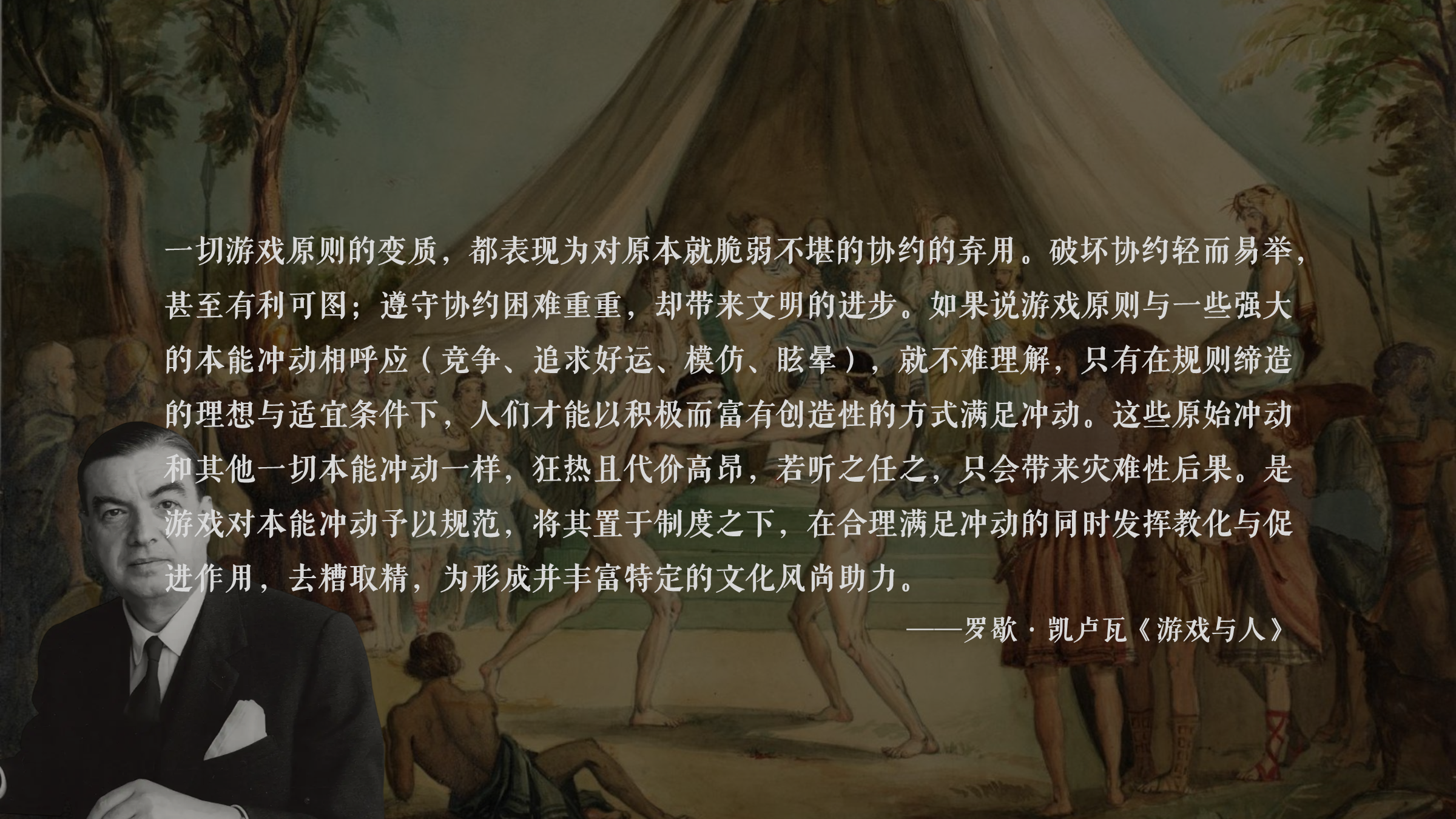
4.從文化中解放遊戲
在凱盧瓦看來,人們對遊戲的選擇是文化取向的側面表現,那麼,遊戲與文化的關係如何?在本書第一部分的最後,凱盧瓦再一次回應了赫伊津哈在《遊戲的人》中的觀點。
凱盧瓦總結道,赫伊津哈認為遊戲先於文明存在,遊戲是文明的藍本,文明規則的建立以遊戲規則為基礎。另一種爭鋒相對的觀點則把遊戲(這裡主要指兒童遊戲)視為嚴肅的人類文明衰落之後的終極淪落。
凱盧瓦對上述兩種觀點均不同意。他認為,遊戲隨著時過境遷成為歷史的殘留,是因為失去了社會容納的土壤,與當下社會格格不入,發生改變的是遊戲的社會功能,而不是它們的性質。遊戲是一項與日常現實平行、獨立的活動,社會功能的改變或部分意義的喪失恰恰證明了這些活動蘊含著遊戲的架構。
由於強調遊戲與文化制度的相互獨立性,凱盧瓦認為,遊戲年代史的重點不應該是尋找遊戲的本質,或是爭論遊戲與嚴肅活動的架構孰先孰後,而應該是發現兩個獨立領域之間的互動關聯。作為人類活動的形式,遊戲與現實共享著各種動因與原始衝動,但分別作用於不同的領域,有著不同的主導因素。它們之前的互通性與差異性本應該首先得到充分的研究,但因為長期的混淆遭到了忽視。
也正因為遊戲與現實的作用域獨立,文化制度對遊戲的取向,才是一個有意義的社會學問題,人類構建的遊戲制度,畢竟是人類自身的寫照,將遊戲奉為萬物起源或貶為歷史殘渣,不過是特定文化制度的價值取向。遊戲彷彿一個無處不在的幽靈,可能會扭曲、腐化、變質,但永遠地作用在那裡,等待著與文化制度的互補、溝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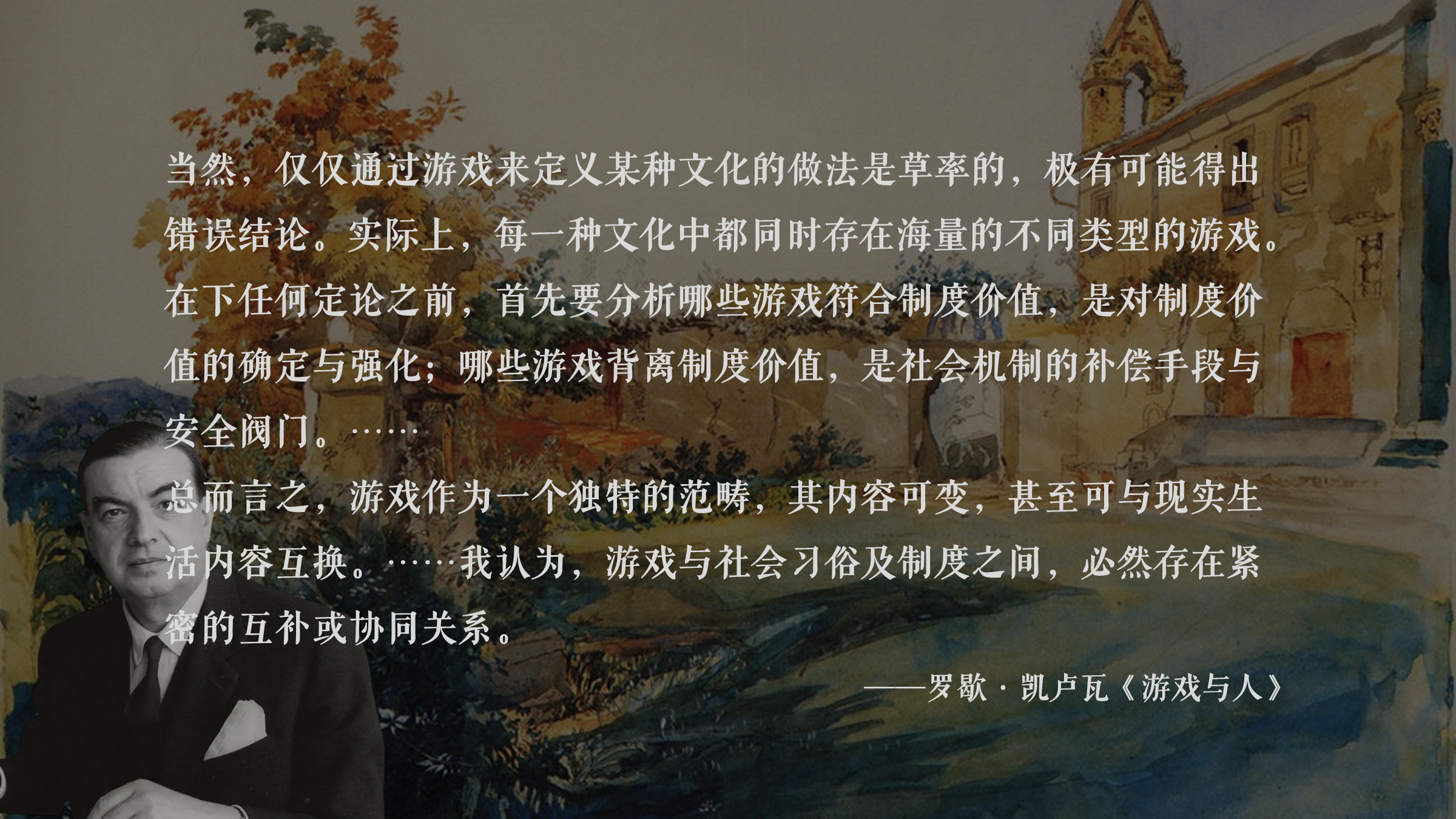
顯而易見,直到《遊戲與人》第一部分的結尾,凱盧瓦已經勾勒出了自己對遊戲理論的期待:人的遊戲與遊戲的人分離並不是為了爭出誰高誰低,外部也不意味著邊緣,兩種形式的研究都是為了在現代世界中恢復大寫的人。於是他在第二部分順理成章地轉向了文化史的研究……(未完不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