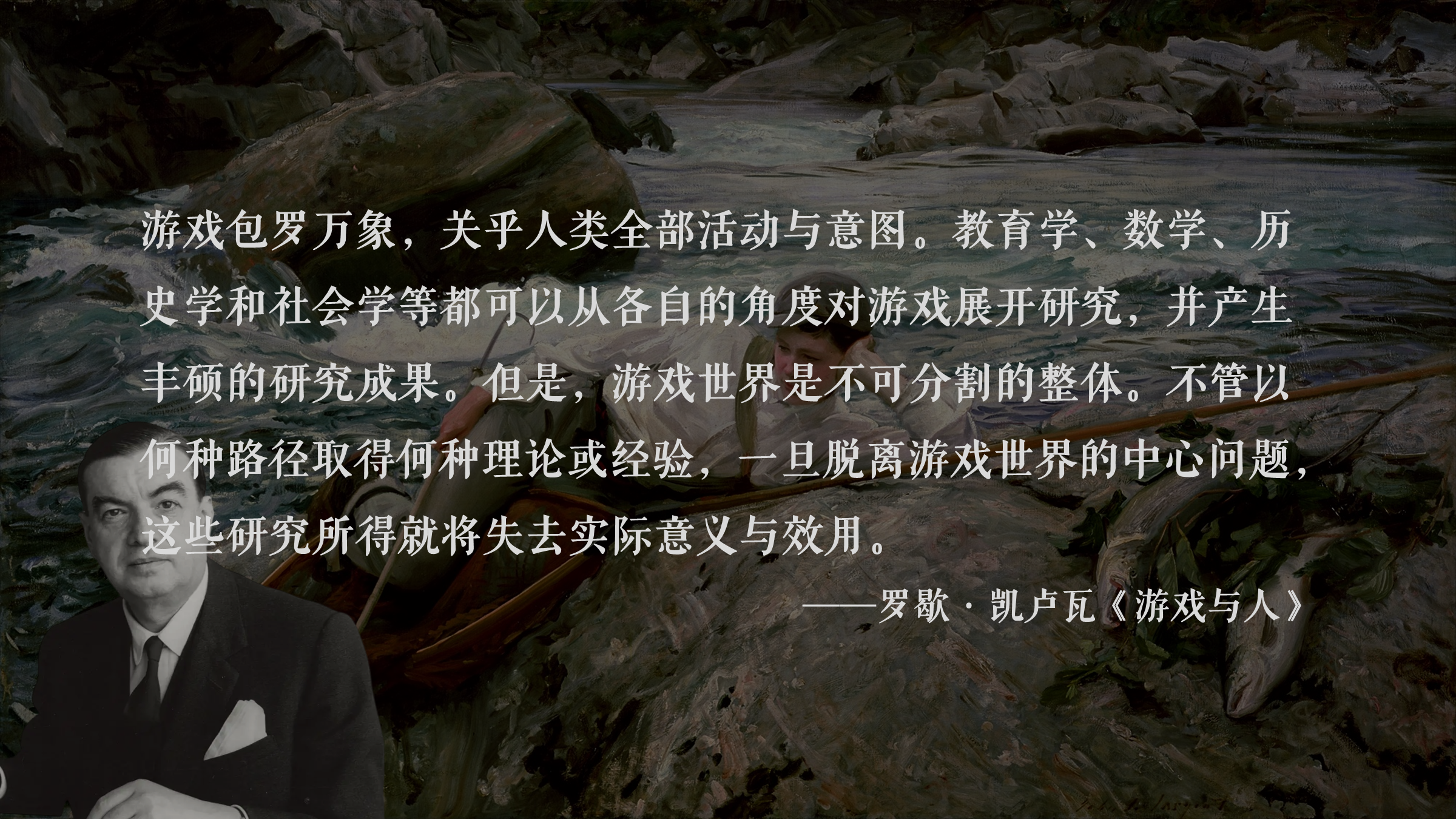
0.写在前面
关于作者
罗歇·凯卢瓦(Roger Caillois,1913—1978),法国作家、哲学家、学者,研究领域横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文学理论,专注于游戏理论和原始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神话与人》(Le Mythe et l’Homme,1938),《人与神圣》(L’Homme et le Sacré,1939),《游戏与人》(Les Jeux et les Hommes,1958),《石之书》(L’écriture des pierres,1970)。
关于本书
《游戏与人》(1958,原书在1961年由Meyer Barash译成英文)是凯卢瓦对赫伊津哈的游戏理论经典著作《游戏的人》(Homo Ludens,1938)的直接回应。在本书中,凯卢瓦吸收了大量来自儿童教育学、动物行为研究、数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通过明晰的类型学剖析拓展了赫伊津哈基于人文主义的游戏理论。
凯卢瓦和赫伊津哈都将游戏视为一种基础性的人类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游戏是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这一观点达成了共识。但凯卢瓦并不认同“人即游戏,游戏即人”的人类本质价值规定,恰恰相反,在《游戏与人》中,凯卢瓦暗示作为人类活动的游戏和从事游戏的人必须区分并分别得到充分的研究。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大量复杂的互动,但对两者的混为一谈是有害且缺乏意义的。
正是在这样的方法论自觉下,凯卢瓦实际上建立了一种新的游戏本体论。他指出赫伊津哈对人类尊严——竞争精神的强调使其忽视了赌博等机运类游戏的存在。与此同时,他对游戏类型(竞争-机运-模仿-眩晕)和游戏方式(戏耍-技游)两种范畴的分类也建立在其对“游戏”与“人”的区分之上。
在他对游戏本质的著名概括(自由性、抽离性、不确定性、非生产性、规则性、虚构性)中,凯卢瓦尤其强调虚构性和规则性。他认为,游戏通过游戏规则严格地抽离于日常活动,是人类的原始冲动(动因)而非游戏本身导致了游戏类型(而非游戏方式)的变质(腐化),游戏也并非文化演进的初级或退行阶段产物,而是两种作用领域不同但相互补充的人类运转机制,它们共同表现着人类的基本动因。
诚然,和绝大多数游戏理论经典一样,凯卢瓦的《游戏与人》在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这部“赫伊津哈之后游戏本体论新的宣言”实际上鼓励着人们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数学等学科的夹缝中跳脱出来,而把注意力直接放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游戏世界的中心问题上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凯卢瓦预言了电子游戏兴起后游戏理论的美好可能进路:游戏的人学与人的游戏学相互尊重、共享成果、相互促进。到那时,赫伊津哈所倡导的人文精神将得到更充分的实现。
(札记只写到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凯卢瓦基于广义游戏论的文化史研究)
1.游戏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类活动:游戏的本质
凯卢瓦开篇就把矛头指向了赫伊津哈对游戏的定义。他直言《游戏的人》研究的不是游戏本身,而是“游戏精神的文化效用”
,也因此,赫伊津哈淡化了游戏本身的描述和分类,把理想化的、仅限于竞争类游戏规则的游戏精神反过来嫁接到所 有游戏上,同时也就导致了忽视能够产生物质利益的赌博和机运游戏的偏颇。不过,他也肯定了赫伊津哈对游戏自由性、规则性、虚构性和日常独立性的深刻洞见。
在赫伊津哈的基础上,凯卢瓦提出了全书最为著名的游戏本质六大特点:一、自由性,玩家不能被迫参与游戏;二、抽离性,游戏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限制范围之内;三、不确定性,游戏的进程和结果不能完全确定,玩家在游戏过程中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四、非生产性,游戏至多只能转移资产而不能创造资产,或者说游戏至多只能是经济交易的方式而非经济生产的实质;五、规则性,游戏需要暂时搁置惯常的规则而采取专属于游戏的规则。六、虚构性:游戏过程是对次现实,而非日常生活的认识。
凯卢瓦强调,游戏的非生产性并不意味着游戏不涉及经济利益,而是指游戏所牵涉的经济行为仅由玩家产生,并对玩家产生影响。这一针对赫伊津哈的观点成功地把机运类游戏引入了游戏的分类范围之中。
另一方面,凯卢瓦也强调游戏规则对游戏空间本身的优先性和与日常生活的分离性。他指出,游戏规则的严肃性对于任何参与到游戏当中来的玩家是必须的,即便这些规则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可能是荒谬的、奇怪的。于是,看似没有规则的角色扮演(模仿类游戏)也被纳入到了游戏范畴之中。
实际上,在引言中,凯卢瓦已经通过对法语的“游戏”(jeu,动词形式为jouer)一词的语义学分析,指出了游戏对文化发展的贡献:竞技类游戏将发展为体育运动、模仿或幻想游戏是戏剧表演的前身、机运类游戏则是概率论等数学理论的起源。凯卢瓦的野心在于进一步拓展游戏的可能类型,从而扩充游戏研究的范围。那么,为了容纳特定的游戏类型而考虑进来的某些本质特点定义,即使是相互矛盾的,也不应该轻易抛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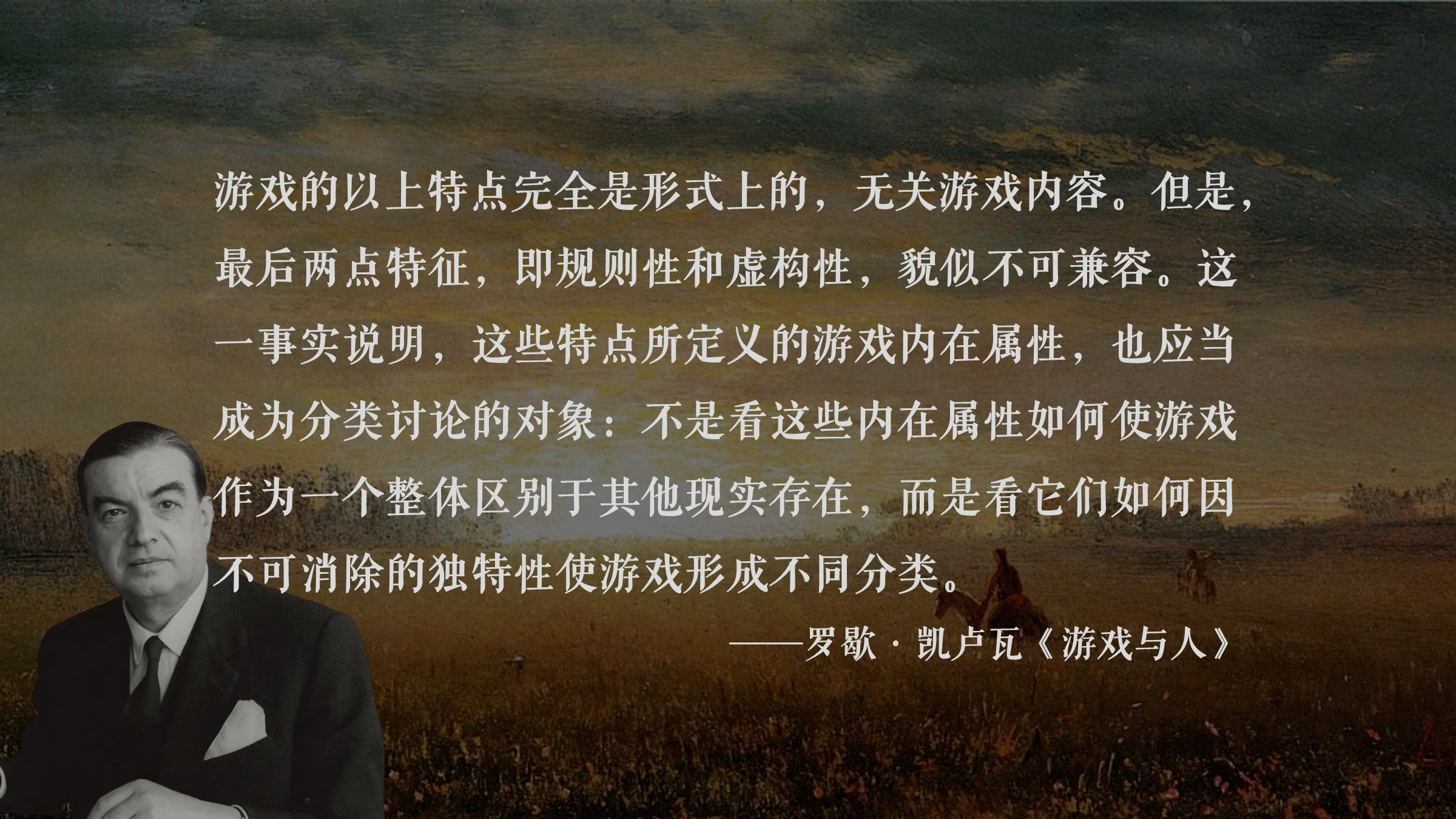
凯卢瓦认为,游戏的规则性和虚构性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即玩家在次现实的世界中为什么还要严肃地对待某些规则;反之,游戏规则的限制也会削弱游戏的幻想性吗?不管怎样,这些疑惑不应该是游戏研究(放弃)的终点,而恰恰应该是起点:对游戏本质的探讨并不是为了建立一种抽象的游戏大一统理论,从而囊括历史上所有形式的游戏,而是为游戏类型学的探究指明方向——特点的模糊之处正是类型分歧的可能之处。
2.游戏的类型学与玩家的类型学:两种类型学的分离与结合
在第二章中,凯卢瓦根据不同游戏对根本特征的反映,将游戏划分为四大类别:一、竞争类游戏(agôn),二、机运类游戏(alea),三、模仿类游戏(mimicry),四、眩晕类游戏(ilinx)。
竞争类游戏强调游戏规则对每位玩家的绝对公平性,即使参与者的实力悬殊,游戏也会通过玩家让步的形式构建平衡。机运类游戏与竞争类游戏相反,玩家面对的是命运,游戏的公平建立在机运对所有参与者的一视同仁,消除任何非命运的因素。模仿类游戏要求玩家暂时接受一种幻象、一种虚构世界的协约,暂时成为他者或被认作他者。眩晕类游戏追求眩晕感,以带有快感的迷乱刺激取代清晰意识。
这四种分类是凯卢瓦深思熟虑之后的得意之作,亦是后续章节的基础。但在此之外,凯卢瓦还引入了另外一个类型学的维度,称之为游戏的层级(在后面则称之为游戏方式)。游戏方式,从根本上说是指玩家参与到游戏中来的方式和态度,任何类型游戏的实际发生都是以一定的游戏方式为前提的。在“游戏方式”这个连续函数的内部,一极是戏耍(paidia),另一极则是技游(ludus)。戏耍的玩家是无准备、无规则地游玩的,他们追求躁动、喧闹、轻松、自由,并不在意游戏的混乱。技游的玩家则刻苦、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游戏中,把游玩视为一种专门化、规范化的技术。凯卢瓦也指出,技游的另一个特征还在于追求潮流,即玩家对展现技术的热忱超越了特定的游戏种类,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凯卢瓦认为,游戏方式体现着玩家对游戏规则的理解,正是它使得游戏成为具有孕育力的文化工具。凯卢瓦在游戏理论方面的洞见性也在于此。他意识到了,游戏活动中的游戏与人,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游戏是人所从事的活动,不是游戏本身,而是游戏着的人利用游戏创造了文化。那么,一种合理的、真正关切到了游戏世界中心问题的类型学,首先要承认两种研究对象的独立存在。就此而言,凯卢瓦使两种类型学分离了,这也使得游戏理论获得了自省的规范:将游戏与人混为一谈只能是范畴错误的谬见。
只有游戏的人与人的游戏事先分离了,两者的结合才是有意义的。凯卢瓦认为,游戏方式可以和各种游戏类型结合,但某些结合情况在事实上并不可能,如戏耍与机运类游戏、技游和眩晕类游戏。
此外,凯卢瓦还特别指出了中文中的“玩”字囊括了从戏耍到技游的全部价值追求(玩弄、玩耍、把玩、玩摄影等)。特定的文化倾向于以某种游戏方式(态度)接受着某些类型的游戏,文化的密码一部分就藏匿在人们对游戏的偏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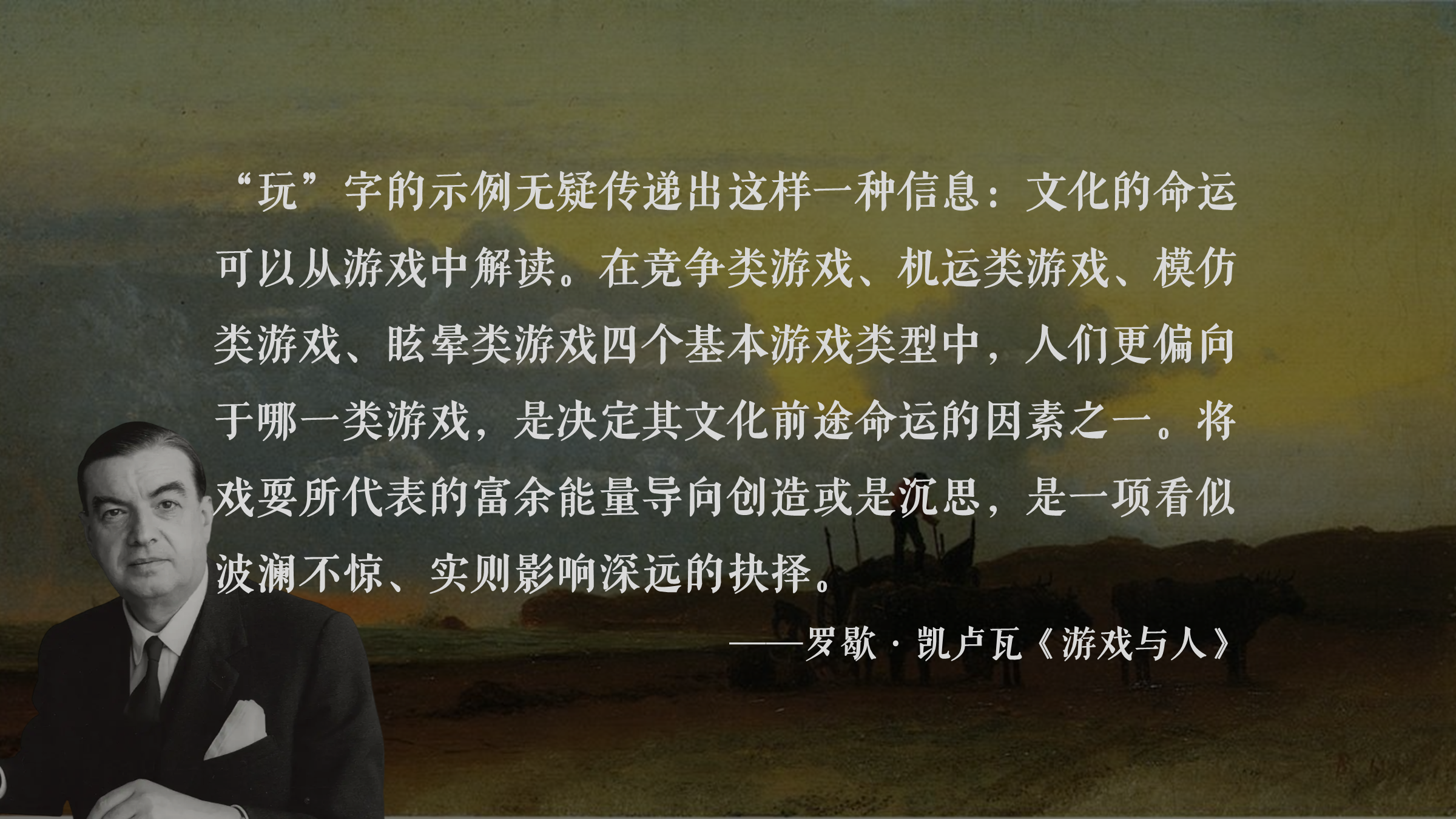
3.人害游戏,而非游戏害人:游戏的变质
基于对两种类型学的区隔,凯卢瓦在第四章探讨了游戏的“变质”(corruption,在法(英)语中既可以指词语的变体形式,也可以指使“人”道德败坏的行为,凯卢瓦反用其义,旨在倒转人们对游戏的价值观察角度)。
凯卢瓦强调,游戏的本质特征将游戏与现实(日常生活)严格地分割了开来。游戏着的人如果取消了这一界线,就会腐化游戏。游戏所受到的这种变质在不同的游戏类型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主导各种游戏的心理因素(在后面也称之为原始冲动或动因)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它们主要是凭借个人才干脱颖而出的胜负欲(竞争类游戏)、被动等待裁决的命运感(机运类游戏)、扮演另一种身份的热忱(模仿类游戏)和对眩晕的追求(眩晕类游戏)。
当游戏发生变质时,界线的取消没有使游戏世界发生崩塌,而是使原本由游戏规则框限的、作用在特定时空内的原始冲动扩散到了日常生活中,把日常生活一起吸纳进了游戏世界。人的无限冲动引发了游戏的变质,进而造成了人的变质(腐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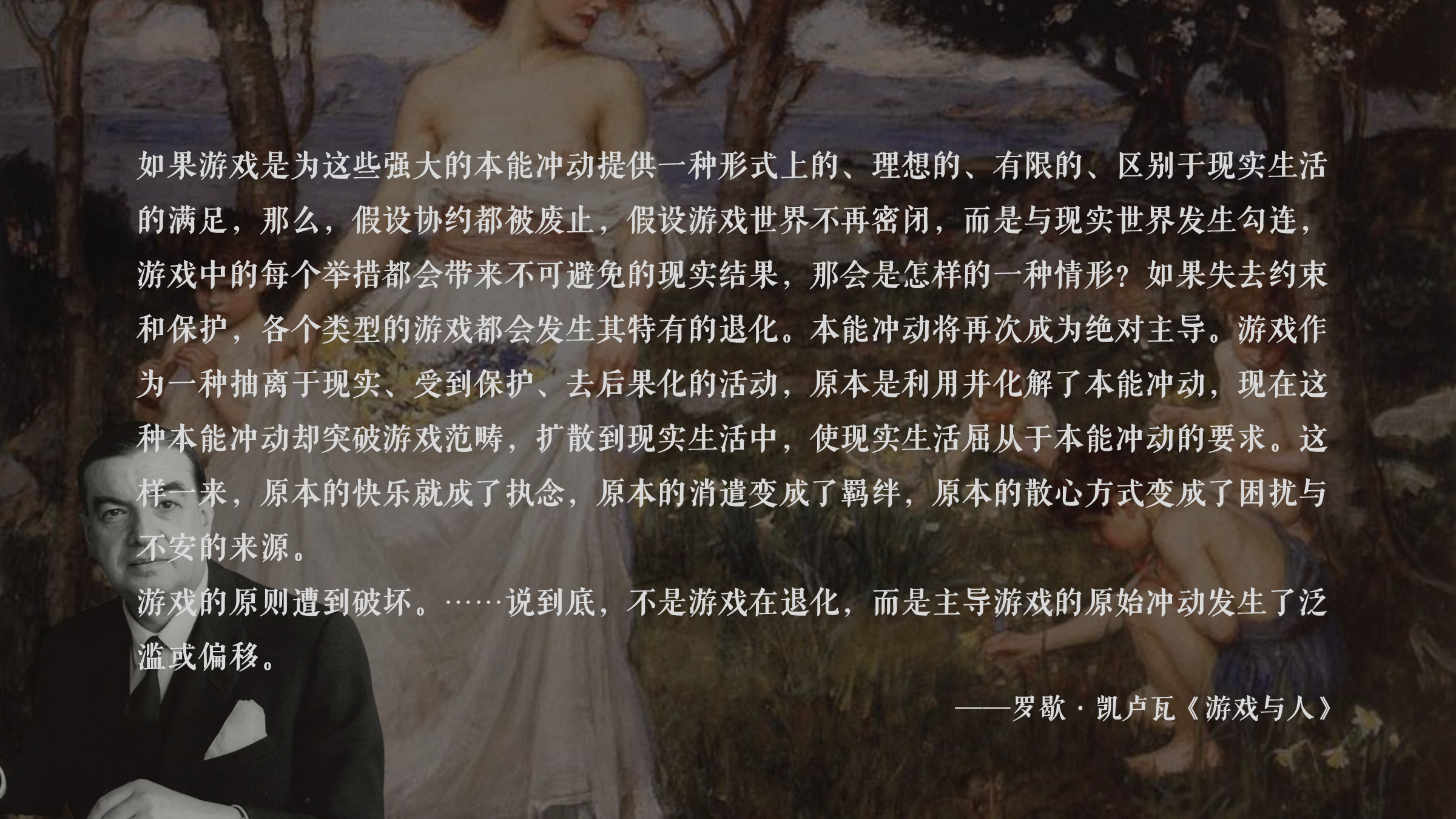
凯卢瓦进一步分析道,游戏违规者(作弊者)逃避游戏规则,但又恰恰利用了其他玩家对规则的遵守,他们并没有改变游戏世界本身,而是影响了其他玩家对游戏的参与;游戏的职业选手也不会改变游戏的性质,他们只是有特殊化的游戏目的,并由此影响着自身的游戏方式。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凯卢瓦对游戏与人区分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在他看来,游戏的变质归根到底是玩家层面的议题。基本动因在于游戏者而非游戏,也只有游戏类型而不是游戏方式才可能受其影响发生变质(腐化),而游戏对人类文化的作用(不论有益无益),严格来说应该是游戏对人的反作用。
随后,凯卢瓦概括了不同类型中游戏变质的表现。
在竞争类游戏中,主导的游戏规则要求参与者信任裁决的公正性,在公平竞争之中,付出了巨大努力即使遭遇惨败,也能落落大方接受结果。这一规则限制了人的贪婪本性,保证了玩家的有效参与。但在变质的竞争类游戏中,现实世界残酷、不完美、充满漏洞的道德、法律、社会约束体系破坏了游戏者对竞争原则的支持,使其怀疑乃至否决裁判的公正,玩不起、也输不起游戏。
在机运类游戏中,对命运的绝对信任被严格地限制在抽离的、无生产性的游戏世界之中。但经过变质,游戏者产生了对日常生活的怯懦而将自己寄托于外部力量和天赐良机,在纸牌、星象、占卜等活动中谋求机遇,这就是迷信。
在模仿类游戏中,模仿的角色、装束或面具至多是惟妙惟肖的拟真。但在变质的模仿中,游戏者不再是扮演另一个人,而是直接成为另一个人。他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完全异化为了他者。
对眩晕类游戏来说,眩晕感和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受到了严格的、尽可能安全的限制。变质的眩晕游戏为了制造持久的眩晕感,从即时的物理效应转向混杂的化学反应。只有中毒
和随之的自我摧残才能带来平常化的刺激感受。
简而言之,暴力、阴谋、迷信、异化、多重人格、成瘾都是游戏变质的表现。游戏的失序同样也会腐化人,而游戏的守序则是文明进步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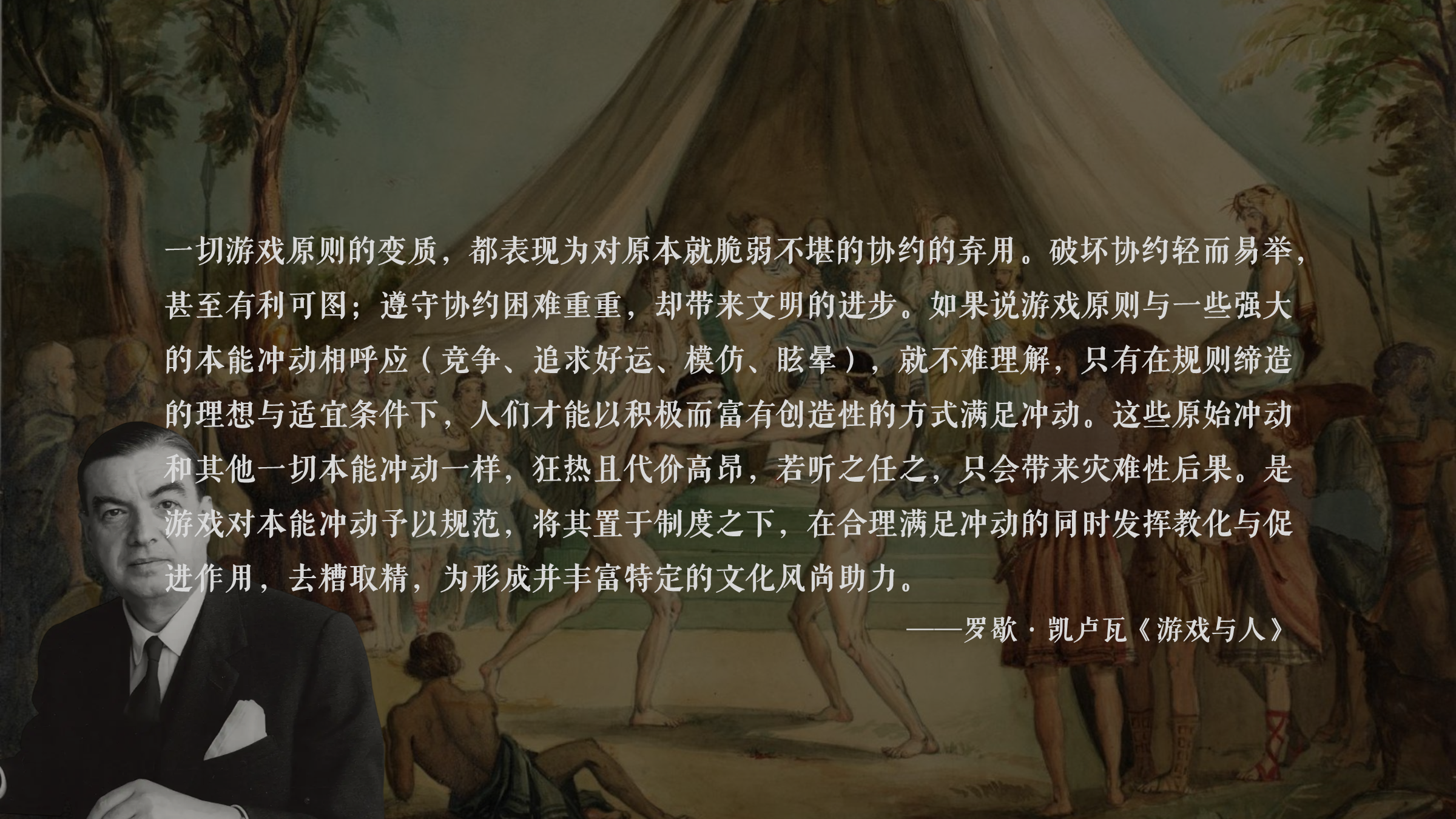
4.从文化中解放游戏
在凯卢瓦看来,人们对游戏的选择是文化取向的侧面表现,那么,游戏与文化的关系如何?在本书第一部分的最后,凯卢瓦再一次回应了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的观点。
凯卢瓦总结道,赫伊津哈认为游戏先于文明存在,游戏是文明的蓝本,文明规则的建立以游戏规则为基础。另一种争锋相对的观点则把游戏(这里主要指儿童游戏)视为严肃的人类文明衰落之后的终极沦落。
凯卢瓦对上述两种观点均不同意。他认为,游戏随着时过境迁成为历史的残留,是因为失去了社会容纳的土壤,与当下社会格格不入,发生改变的是游戏的社会功能,而不是它们的性质。游戏是一项与日常现实平行、独立的活动,社会功能的改变或部分意义的丧失恰恰证明了这些活动蕴含着游戏的架构。
由于强调游戏与文化制度的相互独立性,凯卢瓦认为,游戏年代史的重点不应该是寻找游戏的本质,或是争论游戏与严肃活动的架构孰先孰后,而应该是发现两个独立领域之间的互动关联。作为人类活动的形式,游戏与现实共享着各种动因与原始冲动,但分别作用于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主导因素。它们之前的互通性与差异性本应该首先得到充分的研究,但因为长期的混淆遭到了忽视。
也正因为游戏与现实的作用域独立,文化制度对游戏的取向,才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学问题,人类构建的游戏制度,毕竟是人类自身的写照,将游戏奉为万物起源或贬为历史残渣,不过是特定文化制度的价值取向。游戏仿佛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可能会扭曲、腐化、变质,但永远地作用在那里,等待着与文化制度的互补、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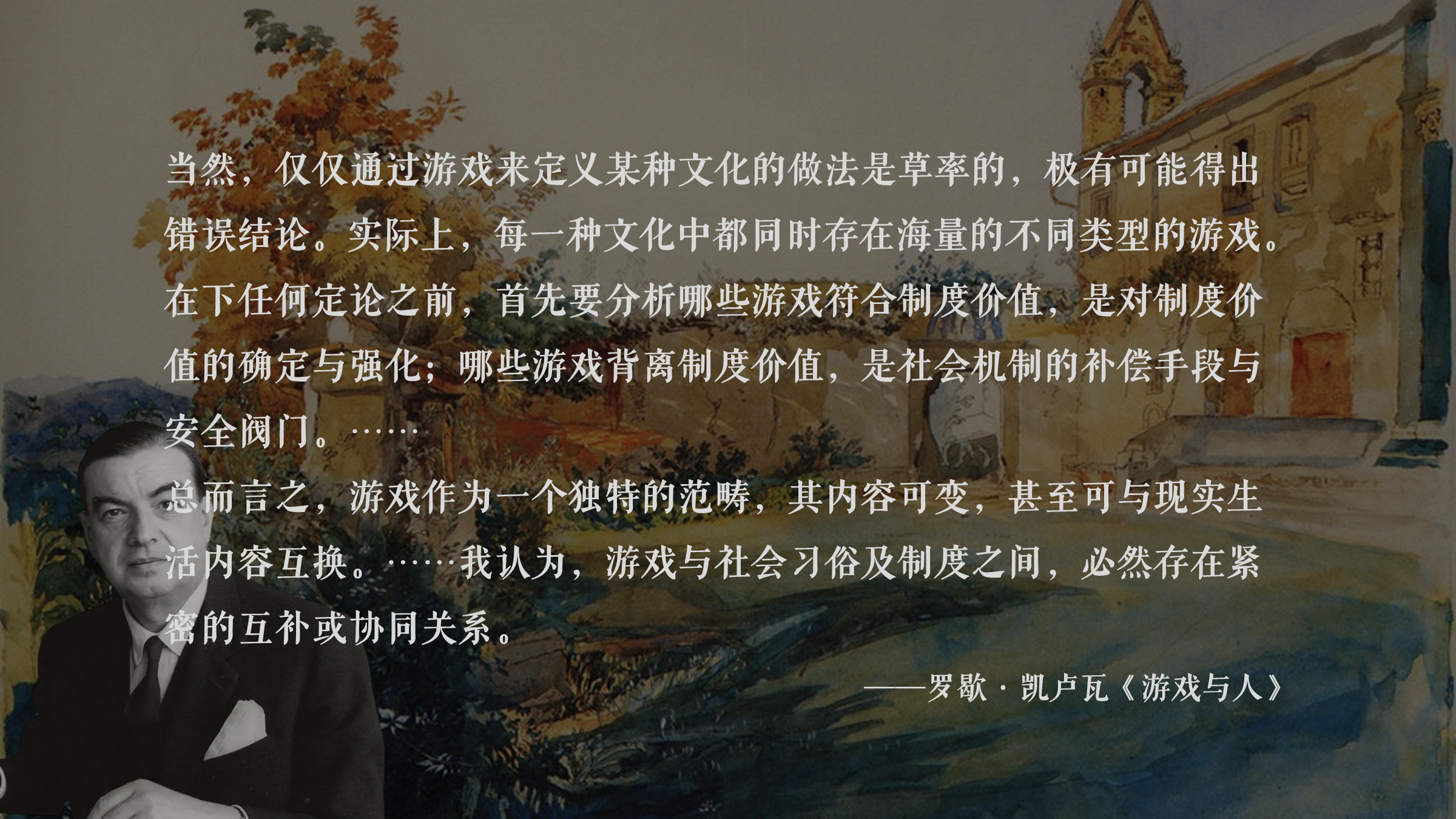
显而易见,直到《游戏与人》第一部分的结尾,凯卢瓦已经勾勒出了自己对游戏理论的期待:人的游戏与游戏的人分离并不是为了争出谁高谁低,外部也不意味着边缘,两种形式的研究都是为了在现代世界中恢复大写的人。于是他在第二部分顺理成章地转向了文化史的研究……(未完不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