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常常與哲學家們糾纏—個神秘的永恆輪迴觀:想想我們經歷過的事情吧,想想它們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無休無止地重演下去!這癲狂的幻念意味著什麼?
從反面說“永劫迴歸”的幻念表明,曾經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樣沒有分量,也就永遠消失不復迴歸了。無論它是否恐依,是否美麗,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麗都預先已經死去,沒有任何意義。”
坐者用一段對尼采“永恆輪迴”的論述為開頭,引出本書的內容,如果生命中的每一個時刻會無數次重複,那麼我們就能不斷地選擇不同的結果,直到選出最好的結果。但同時,每一件事都會因為它的無數次重複而變得平庸:“如果十四世紀的兩個非洲部密的戰爭一次又一次重演,戰爭本身會有所改變嗎?會的,它將變成一個永遠隆起的硬塊,再也無法歸復自己原有的虛空。
如果法國大革命永無休止地重演,法國歷史學家們就不會對羅伯斯庇爾感到那麼自豪了。正因為他們涉及的那些事不復迴歸,於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過變成了文字、理論和研討而已,變得比鴻毛還輕,嚇不了誰。這個在歷史上只出現一次的羅伯斯庇爾與那個永劫迴歸的羅伯斯庇爾絕不相同,後者還會砍下法蘭西萬顆頭顱。
於是,讓我們承認吧,這種永劫迴歸觀隱含有一種視角,它使我們所知的事物看起來是另一回事,看起來失去了事物瞬時性所帶來的緩解環境,而這種緩解環境能使我們難於定論。我們怎麼能去譴責那些轉瞬即逝的事物呢?昭示洞察它們的太陽沉落了,人們只能憑藉回想的依稀微光來辯釋一切,包括斷頭臺。”
正是因為只有一次,沒有所謂的如果,當下的決定才顯得艱難與充滿力量,也因為只有一次,人才獲得了自由,不被受困於"最好的選擇“。也正是這份自由,昆德拉給出了第一種對立,那就是生命的輕與重:
“最沉重的負擔壓得我們崩塌了,沉沒了,將我們釘在地上。可是在每一個時代的愛情詩篇裡,女人總渴望壓在男人的身軀之下。也許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最為充實的象徵,負擔越沉,我們的生活也就越貼近大地,越趨近真切和實在。 相反,完全沒有負擔,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運動自由而毫無意義。”
生命的重,是對命運的肯定,是對責任的承擔,是一種“Mussessen”(非如此不可)。特麗莎左手握著右手睡覺,渴望她心中值得一生與她相守的人。弗蘭茨熱衷於革命,參加各式各樣的遊行,希望參與在歷史的第一線。
與之相反,生命的輕是承認生命都虛無和無意義。托馬斯同兩百多個女人睡覺,執意發表文章使自己丟失工作……薩賓娜不斷地“背叛”既有的價值,她既不親近蘇聯,也不親近西方。她的畫作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她同特麗莎一樣四處同自己喜歡的人做愛。
這種對立是故事的明線,故事在明面上就展示了不同人對輕和重之間徘徊。
托馬斯是個英俊且德高望重的外科醫生,他擁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在外人看來他是“成功”的男人,但是他卻深感婚姻中責任的束縛,他離婚後一邊渴望著女人的身體,一邊厭惡著同女人的責任,托馬斯從不留女人在家過夜,也不在別的女人家裡過夜,他絕不與女人過於親近,但卻在一個偶然的下午一切都改變了。托馬斯因為一個偶然的換班,他遇到到了改變他生命的人:特麗莎。托馬斯與特麗莎互相一見鍾情,他們很快就相愛,但特麗莎很快就發現了托馬斯與不同的女人睡覺。堅信著肉體與靈魂是一體的她忍受不了托馬斯的肉體不屬於她,她一邊為此痛苦,而又無法失去托馬斯的愛。托馬斯更是如此,他也為此痛苦,他一邊像是同情般地對特麗莎愧疚,一邊又不能失去別的女人,肉慾和愛慾就像他的重獲光明的眼睛和早已習慣的耳朵一樣都無法失去。托馬斯不知道如何去選擇:“如果我能活兩次,一次我會讓她住下,一次我會把她趕走,然後我會得出最佳選擇,可是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是如此之輕。就像一個輪廓,我們無法填充,或者修正,讓它變得更好”當下在時間的就是當中凝結為名作過去的永恆,正是因為生命只是在不斷地生成和凝結,無法在無數次迴歸中找到答案,不知道如何選擇是最好的選擇,人才為此感受到了自由,這種自由毫無方向,向上漂浮,這是生命無法承受的輕……這種自由是托馬斯的幸福也是托馬斯的痛苦的源泉,這種自由讓托馬斯擺脫婚姻的苦海也讓他陷入深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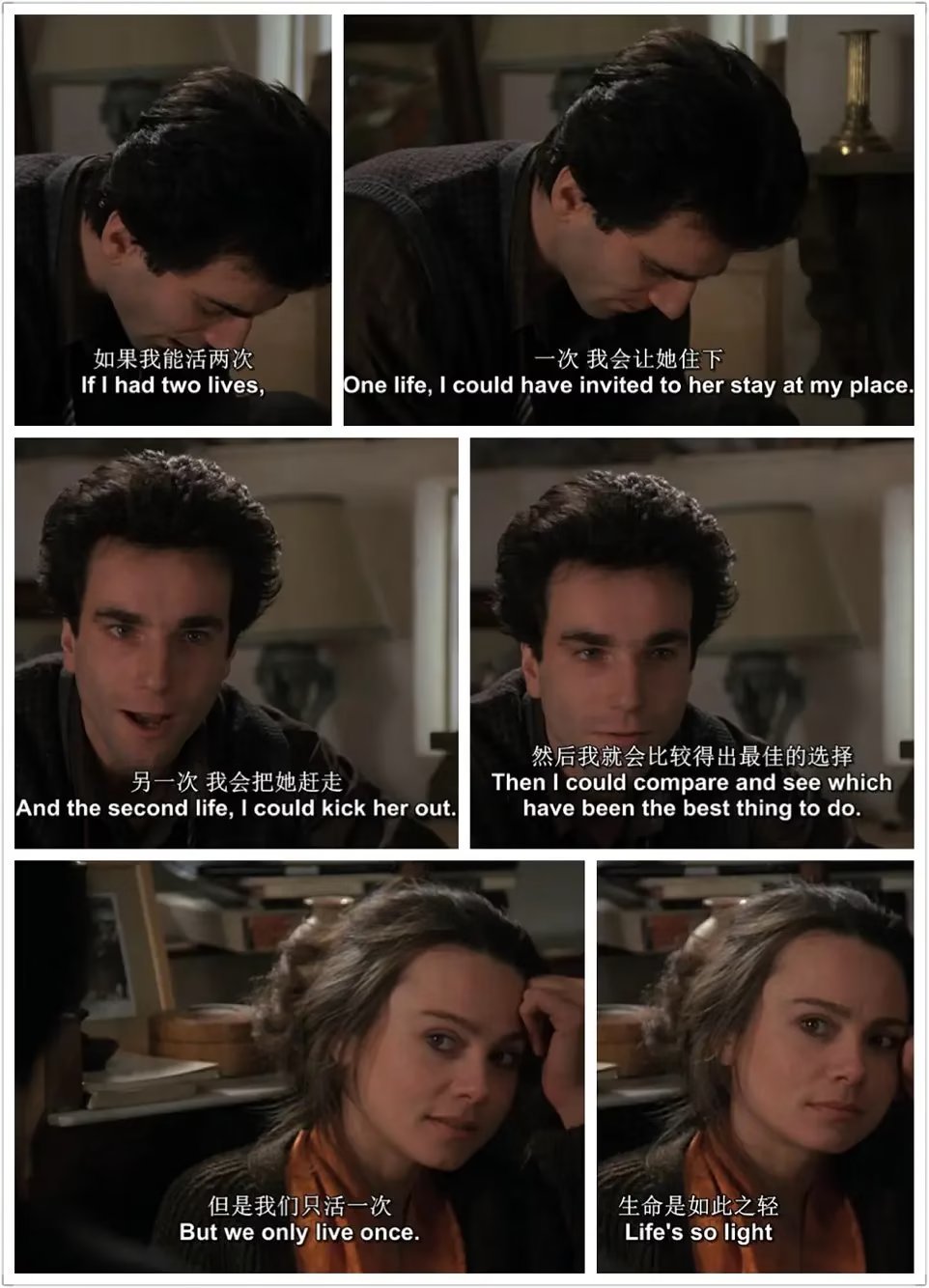
布拉格之春在托馬斯與特麗莎的糾纏當衝悄然發生。特麗莎無法忍受蘇聯的行徑拍下照片,報社和政府的麻木讓特麗莎不甘,蘇聯的行動讓特麗莎害怕,他們離開了布拉格來到了日內瓦。而早就離開布拉格的薩賓娜帶來了本作真正的對立:媚俗。媚俗的根源就是對生命的絕對認同。政客們慷慨激昂地演講,捍衛著某種價值:捷克的政客信誓旦旦地要保衛祖國,卻離遠遠地觀望戰場;蘇聯的政客一邊高呼著“社會主義”萬歲的美好一邊下令抓捕不同意他們話的人……他們有什麼區別嗎?他們或許都不明白其中的含義只是確信著自己踐行並代表著這種價值。這種自以為是對自己的生命的肯定就是媚俗,但是堅定地反對著這種自我為是也何嘗不是一種自我為是?薩賓娜也為弗蘭茨變得如她所鄙夷的人一樣,弗蘭茨與薩賓娜的相遇就在薩賓娜對媚俗的反對當中。弗蘭茨熱衷於革命,他對妻子談不上愛只是出於一種同情,他的妻子不斷地表達出一種沒有他就活不下去的情感,但他對薩賓娜一見鍾情並願意為他拋棄他所固有的價值,而薩賓娜也為他心動。薩賓娜厭惡那種溫情但是又渴望著這種愛。她在弗蘭茨與托馬斯之間徘徊,托馬斯也在薩賓娜和特麗莎之間徘徊。特麗莎在瑞士並沒有多受待見,她的照片也沒有引起多少的轟動,而托馬斯不斷尋找別的女人讓特麗莎痛苦不堪。生命對特麗莎來說太沉重了,而對於托馬斯又太輕了,他無法接受托馬斯的價值。托馬斯終於擺脫了特麗莎,終於回到了原來自由而又快樂的生活,但是他對特麗莎或許是愛又或許是同情,讓他回去了布拉格,他知道,回去了就再也無法離開了。非如此不可嗎?“貝多芬視沉重為一種積極的東西。既然德語中sChwer的意思既是“困難”,又是“沉重”,貝多芬“難下的決心”也可以解釋為“沉重的”或“有分量的決心”。這種有分量的決心與他的“命運”交響樂曲主題是一致的(“非如此不可!”);必然,沉重,價值,這三個概念連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價值。”托馬斯一直反對著這種必然,在托馬斯眼裡他們是自由的,他厭惡著所謂的普世價值,他厭惡所謂的家庭幸福美滿和每天把信仰掛在嘴上的人,厭惡著隨便把共產主義萬歲掛在嘴上的人,他惱火的或許不是“非如此不可”,而是薩賓娜口中的媚俗。他討厭的是在一種價值裡沉淪而放棄了自己的自由,他們的“非如此不可”只是自我的不加思考地沉浸於意識形態當中。而此時的他自由地選擇了不自由,“非如此不可”是最沉重的負擔,也是對自己最不負責最任性的輕浮。當托馬斯意識到這點,他或許明白了輕本身也是一種沉重,自由和無意義意味著在黑暗當中探索,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他同薩賓娜一樣,反對著蘇聯和媚俗的反抗者,他拒絕撤銷看上去不利於蘇聯的文章也拒絕在反對蘇聯的提議上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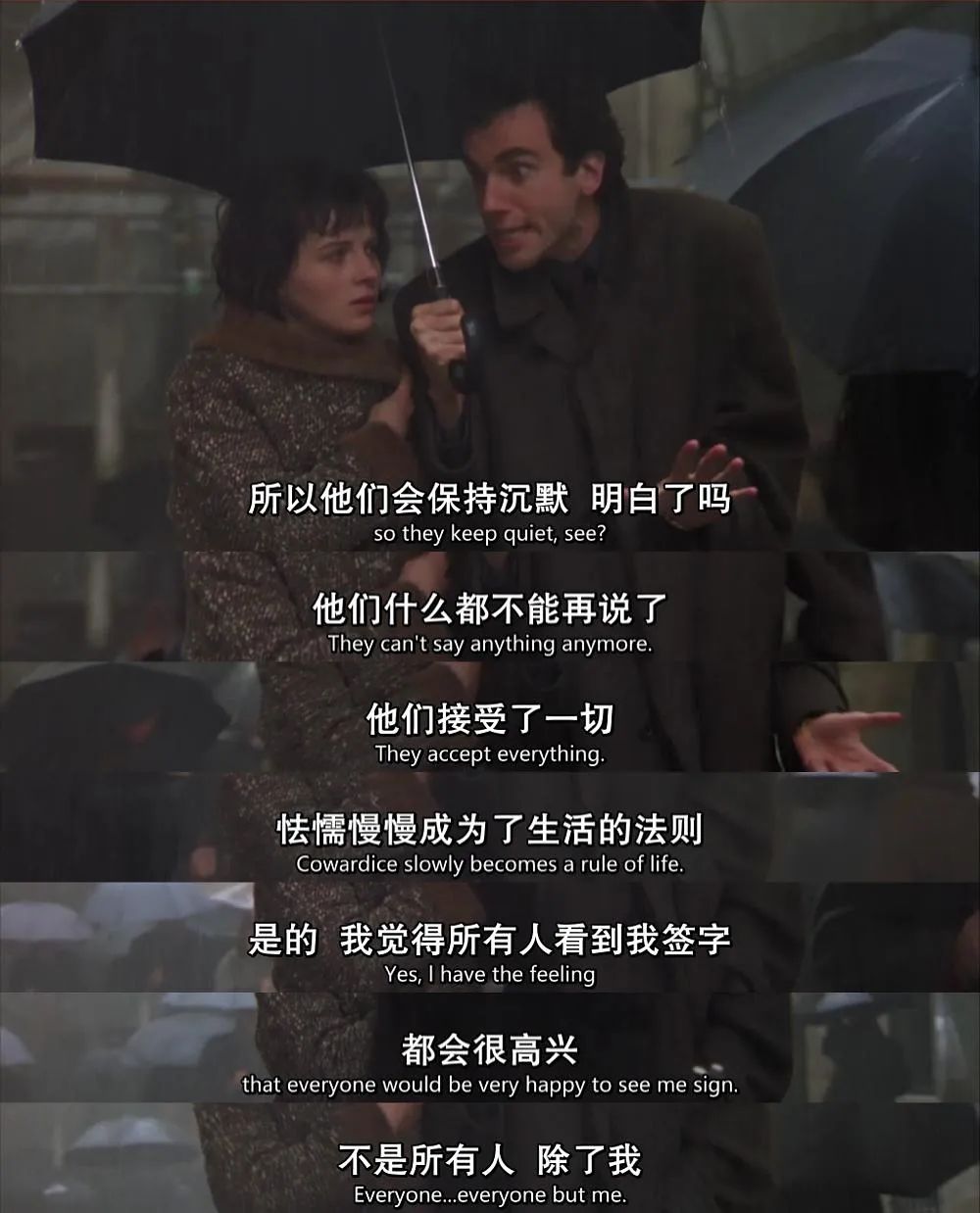
薩賓娜最後離開了弗朗茨,她明白弗朗茨對他似乎只是崇拜,她也明白自己不想要那種生活,弗朗茨幻想著她與生活在光芒之下,這份重量是薩賓娜承受不起的重量,也是弗朗茨對革命的幻想在薩賓娜身上的呈現。最後弗朗茨死在一次在越南的反戰宣言的路上被土匪所殺,一生追隨著沉重的人輕浮地隨意地死去,他的妻子也再也不能留住他的愛。斯大林的兒子被德軍俘虜,在集中營裡別人忍受不了他把廁所弄得又臭又髒的惡習不讓他上廁所,最後一頭撞死在電網上。“斯大林的兒子為大便獻出了生命。但是為大便而死並非無謂犧牲。那些為了向東方擴充領土而獻身的德國人,那些為了向西方擴展權勢而喪命的俄國人——是的,他們為某種愚昧的東西而死,死得既無意義,也不正當。在這次戰爭總的愚蠢中,斯大林兒子的死是唯一傑出的形而上之死。”斯大林兒子的死是無意義的,但又是最偉大的,他為了自己的信念而死,而不明不白死去的人雖然死於某種偉大但卻只是死於某種被賦予的價值裡。
重與輕究竟有什麼區別呢,其實並沒有,最沉重的負擔讓人不用忍受自由的痛苦,不用去選擇,只要活在既定的價值裡,這何嘗不是一種輕浮?而無意義的自由不也正是說明著承擔著自由選擇的重擔和責任?媚俗是對一種價值的不加反思地確信,而反對媚俗的確信也只是另一種媚俗,人不過只是在這之中徘徊,而選擇重與輕,媚俗與否是深藏於虛無中最最不可去闡明的自由……
#米蘭昆德拉# #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動漫紅黑榜# #存在主義# #布拉格之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