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常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个神秘的永恒轮回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
从反面说“永劫回归”的幻念表明,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依,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
坐者用一段对尼采“永恒轮回”的论述为开头,引出本书的内容,如果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会无数次重复,那么我们就能不断地选择不同的结果,直到选出最好的结果。但同时,每一件事都会因为它的无数次重复而变得平庸:“如果十四世纪的两个非洲部密的战争一次又一次重演,战争本身会有所改变吗?会的,它将变成一个永远隆起的硬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原有的虚空。
如果法国大革命永无休止地重演,法国历史学家们就不会对罗伯斯庇尔感到那么自豪了。正因为他们涉及的那些事不复回归,于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过变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而已,变得比鸿毛还轻,吓不了谁。这个在历史上只出现一次的罗伯斯庇尔与那个永劫回归的罗伯斯庇尔绝不相同,后者还会砍下法兰西万颗头颅。
于是,让我们承认吧,这种永劫回归观隐含有一种视角,它使我们所知的事物看起来是另一回事,看起来失去了事物瞬时性所带来的缓解环境,而这种缓解环境能使我们难于定论。我们怎么能去谴责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呢?昭示洞察它们的太阳沉落了,人们只能凭借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辩释一切,包括断头台。”
正是因为只有一次,没有所谓的如果,当下的决定才显得艰难与充满力量,也因为只有一次,人才获得了自由,不被受困于"最好的选择“。也正是这份自由,昆德拉给出了第一种对立,那就是生命的轻与重:
“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崩塌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可是在每一个时代的爱情诗篇里,女人总渴望压在男人的身躯之下。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 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生命的重,是对命运的肯定,是对责任的承担,是一种“Mussessen”(非如此不可)。特丽莎左手握着右手睡觉,渴望她心中值得一生与她相守的人。弗兰茨热衷于革命,参加各式各样的游行,希望参与在历史的第一线。
与之相反,生命的轻是承认生命都虚无和无意义。托马斯同两百多个女人睡觉,执意发表文章使自己丢失工作……萨宾娜不断地“背叛”既有的价值,她既不亲近苏联,也不亲近西方。她的画作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她同特丽莎一样四处同自己喜欢的人做爱。
这种对立是故事的明线,故事在明面上就展示了不同人对轻和重之间徘徊。
托马斯是个英俊且德高望重的外科医生,他拥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在外人看来他是“成功”的男人,但是他却深感婚姻中责任的束缚,他离婚后一边渴望着女人的身体,一边厌恶着同女人的责任,托马斯从不留女人在家过夜,也不在别的女人家里过夜,他绝不与女人过于亲近,但却在一个偶然的下午一切都改变了。托马斯因为一个偶然的换班,他遇到到了改变他生命的人:特丽莎。托马斯与特丽莎互相一见钟情,他们很快就相爱,但特丽莎很快就发现了托马斯与不同的女人睡觉。坚信着肉体与灵魂是一体的她忍受不了托马斯的肉体不属于她,她一边为此痛苦,而又无法失去托马斯的爱。托马斯更是如此,他也为此痛苦,他一边像是同情般地对特丽莎愧疚,一边又不能失去别的女人,肉欲和爱欲就像他的重获光明的眼睛和早已习惯的耳朵一样都无法失去。托马斯不知道如何去选择:“如果我能活两次,一次我会让她住下,一次我会把她赶走,然后我会得出最佳选择,可是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是如此之轻。就像一个轮廓,我们无法填充,或者修正,让它变得更好”当下在时间的就是当中凝结为名作过去的永恒,正是因为生命只是在不断地生成和凝结,无法在无数次回归中找到答案,不知道如何选择是最好的选择,人才为此感受到了自由,这种自由毫无方向,向上漂浮,这是生命无法承受的轻……这种自由是托马斯的幸福也是托马斯的痛苦的源泉,这种自由让托马斯摆脱婚姻的苦海也让他陷入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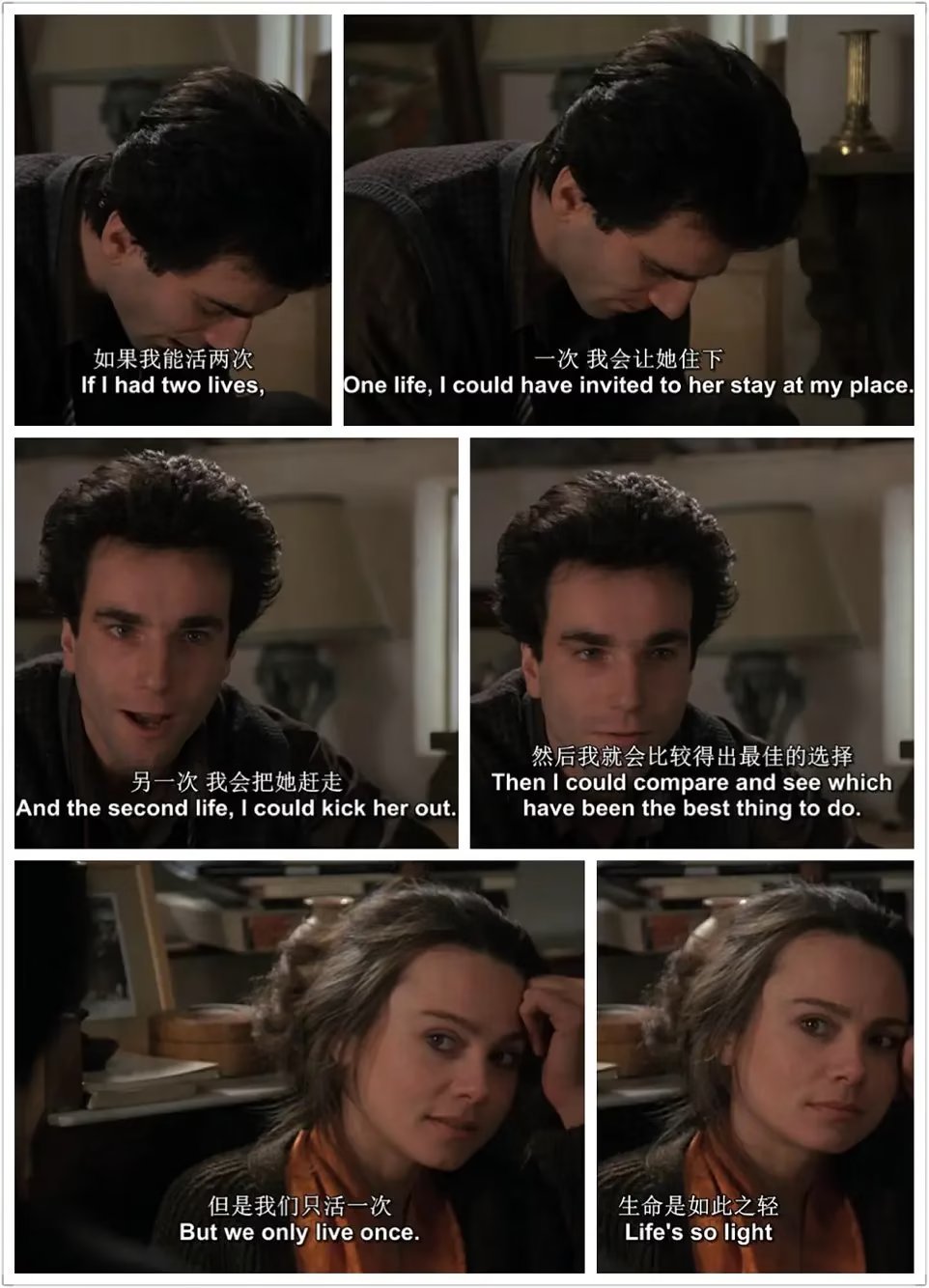
布拉格之春在托马斯与特丽莎的纠缠当冲悄然发生。特丽莎无法忍受苏联的行径拍下照片,报社和政府的麻木让特丽莎不甘,苏联的行动让特丽莎害怕,他们离开了布拉格来到了日内瓦。而早就离开布拉格的萨宾娜带来了本作真正的对立:媚俗。媚俗的根源就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政客们慷慨激昂地演讲,捍卫着某种价值:捷克的政客信誓旦旦地要保卫祖国,却离远远地观望战场;苏联的政客一边高呼着“社会主义”万岁的美好一边下令抓捕不同意他们话的人……他们有什么区别吗?他们或许都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只是确信着自己践行并代表着这种价值。这种自以为是对自己的生命的肯定就是媚俗,但是坚定地反对着这种自我为是也何尝不是一种自我为是?萨宾娜也为弗兰茨变得如她所鄙夷的人一样,弗兰茨与萨宾娜的相遇就在萨宾娜对媚俗的反对当中。弗兰茨热衷于革命,他对妻子谈不上爱只是出于一种同情,他的妻子不断地表达出一种没有他就活不下去的情感,但他对萨宾娜一见钟情并愿意为他抛弃他所固有的价值,而萨宾娜也为他心动。萨宾娜厌恶那种温情但是又渴望着这种爱。她在弗兰茨与托马斯之间徘徊,托马斯也在萨宾娜和特丽莎之间徘徊。特丽莎在瑞士并没有多受待见,她的照片也没有引起多少的轰动,而托马斯不断寻找别的女人让特丽莎痛苦不堪。生命对特丽莎来说太沉重了,而对于托马斯又太轻了,他无法接受托马斯的价值。托马斯终于摆脱了特丽莎,终于回到了原来自由而又快乐的生活,但是他对特丽莎或许是爱又或许是同情,让他回去了布拉格,他知道,回去了就再也无法离开了。非如此不可吗?“贝多芬视沉重为一种积极的东西。既然德语中sChwer的意思既是“困难”,又是“沉重”,贝多芬“难下的决心”也可以解释为“沉重的”或“有分量的决心”。这种有分量的决心与他的“命运”交响乐曲主题是一致的(“非如此不可!”);必然,沉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价值。”托马斯一直反对着这种必然,在托马斯眼里他们是自由的,他厌恶着所谓的普世价值,他厌恶所谓的家庭幸福美满和每天把信仰挂在嘴上的人,厌恶着随便把共产主义万岁挂在嘴上的人,他恼火的或许不是“非如此不可”,而是萨宾娜口中的媚俗。他讨厌的是在一种价值里沉沦而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他们的“非如此不可”只是自我的不加思考地沉浸于意识形态当中。而此时的他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非如此不可”是最沉重的负担,也是对自己最不负责最任性的轻浮。当托马斯意识到这点,他或许明白了轻本身也是一种沉重,自由和无意义意味着在黑暗当中探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他同萨宾娜一样,反对着苏联和媚俗的反抗者,他拒绝撤销看上去不利于苏联的文章也拒绝在反对苏联的提议上签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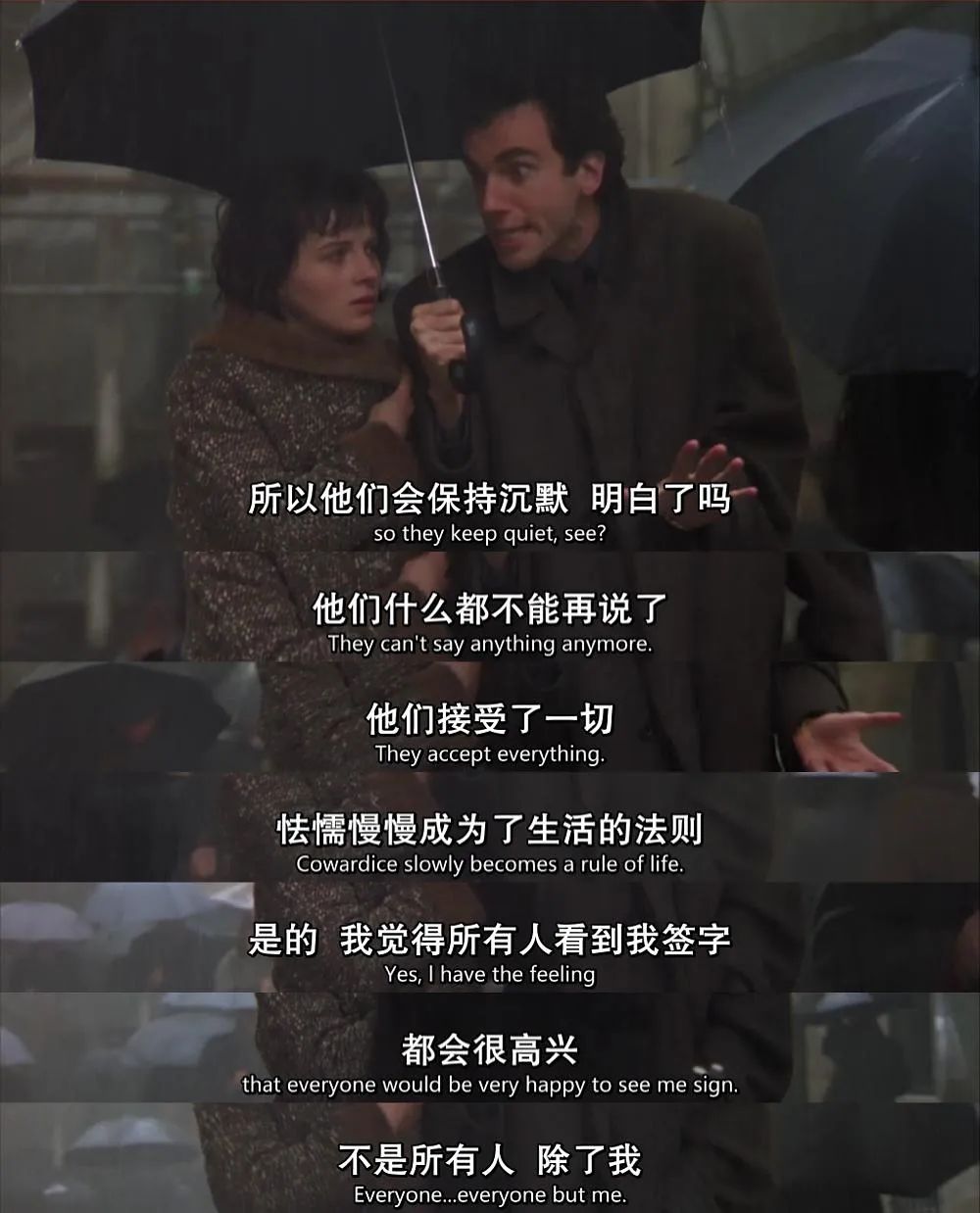
萨宾娜最后离开了弗朗茨,她明白弗朗茨对他似乎只是崇拜,她也明白自己不想要那种生活,弗朗茨幻想着她与生活在光芒之下,这份重量是萨宾娜承受不起的重量,也是弗朗茨对革命的幻想在萨宾娜身上的呈现。最后弗朗茨死在一次在越南的反战宣言的路上被土匪所杀,一生追随着沉重的人轻浮地随意地死去,他的妻子也再也不能留住他的爱。斯大林的儿子被德军俘虏,在集中营里别人忍受不了他把厕所弄得又臭又脏的恶习不让他上厕所,最后一头撞死在电网上。“斯大林的儿子为大便献出了生命。但是为大便而死并非无谓牺牲。那些为了向东方扩充领土而献身的德国人,那些为了向西方扩展权势而丧命的俄国人——是的,他们为某种愚昧的东西而死,死得既无意义,也不正当。在这次战争总的愚蠢中,斯大林儿子的死是唯一杰出的形而上之死。”斯大林儿子的死是无意义的,但又是最伟大的,他为了自己的信念而死,而不明不白死去的人虽然死于某种伟大但却只是死于某种被赋予的价值里。
重与轻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并没有,最沉重的负担让人不用忍受自由的痛苦,不用去选择,只要活在既定的价值里,这何尝不是一种轻浮?而无意义的自由不也正是说明着承担着自由选择的重担和责任?媚俗是对一种价值的不加反思地确信,而反对媚俗的确信也只是另一种媚俗,人不过只是在这之中徘徊,而选择重与轻,媚俗与否是深藏于虚无中最最不可去阐明的自由……
#米兰昆德拉#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动漫红黑榜# #存在主义# #布拉格之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