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最近和同學健身減脂,需要吃的乾淨一點。就又回到了學校食堂吃飯,這樣吃比點外賣輕食便宜不少。這兩天吃著大學食堂就不得不感嘆,還是大學食堂好,一樓套餐自選餐,二樓品牌餐。一想到高中食堂的泔水飯,就讓我作嘔。在某次閒聊時就突然提起來以前食堂是個什麼樣子,於是就有了這篇文章。
文章旨在分享歷史事件與知識,所有內容均基於公開可用的資料和學術研究。我們盡力確保信息的準確性和客觀性,但由於歷史資料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可能存在部分細節的不完全準確或解讀上的差異。本推文不構成任何專業建議或歷史事件的最終定論,僅供參考和啟發思考之用。對於因使用本推文內容而產生的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失,我們概不負責。如讀者發現推文中有任何錯誤或遺漏,歡迎指正,我們將盡力核實並修正。請尊重歷史事實,理性討論,共同營造一個健康、積極的歷史知識交流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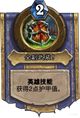
疊甲,過
在我們討論之前,需要確定“食堂”這個概念本身。“食堂”設於機關、學校、廠礦、集體用餐等企事業單位,為供應內部職工、學生等就餐的場所,統稱為食堂。古時叫伙房、膳房,仍有機關單位叫膳食科,也叫飯堂,常見於學校、公司、工廠和軍營,是大量人群集體用餐的地方,同時它通常設有固定的用餐區域和廚房設施,由專業的廚師或餐飲服務人員負責烹飪和供應餐食,以滿足該群體成員的飲食需求。
我們能從上述提取到什麼信息,一般出自於機關、公司、學校、工廠等地,這些說明食堂只是這些場地的附屬品,而非其根本目的。同時還具有大量人群集體用餐的條件,在這個前提下還需要設有固定的用餐區和廚房設施。

從這些要求出發,我們就可以大概框定一個範圍,來看看以前人的食堂是個什麼樣的狀態。在《國語·楚語》中的《子常問蓄貨聚馬鬥且論其必亡》中“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秩之。”翻譯:楚成王聽說子文吃了早飯連晚飯都沒有,每逢朝見時就準備一些肉乾和糧食,送給子文。一直到現在都成了對待令尹的慣例。這個算是給“令尹”的工作餐,但是遠遠還沒有到達我們要求的大量人群集體用餐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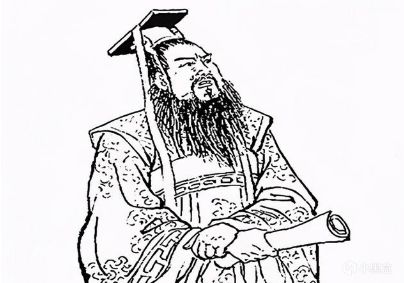
楚成王(但是手裡拿紙是不是有歷史錯誤)
在唐代就有了一種初具雛形的制度“公廚”而這個制度大概就是公廚主要指因政務工作需要由政府提供的免費公務廚食猶如今日的機關食堂。公廚屬於官吏的基本待遇享受公廚待遇的標準因官員品級的不同而不同。所以這樣看下來就和我們當今的食堂差不多了,但是這個制度的重點屬性還不是在乾飯上,能在於“ 凡政事者,因於會食,遂以議政,比其同異,齊其疾徐會斯有堂矣。則堂之作不專在飲食亦有政教之大端焉”。其 目的不專在飲食,實有益於提高官府的行政效率。故公廚成為非正式的議政場所官員同僚在同桌共食之際集思廣益 使施政更公正客觀,有利於營造和諧的議政氛圍。所以這樣一來就感覺是唐代人把會議桌搬到了飯桌上,屬於是換個地方開會。
在飲食內容也是有著非常強的等級制度,各官員按照等級食用相對應的食料。相應的,供給對象一般是宰相,知制浩的中書舍人,宰相的家人。據聖歷三年四月 初三 日武后救文規定 “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例。”唐代宰相多是兼官只有加了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銜才可知政事在堂廚會食。這麼高的標準則是讓我們這樣的平頭百姓難以企及,在民間出現的食堂往往一直到了宋代這個商品經濟高度繁榮的時代才緩緩出現在人們的眼中。
邊吃便開會,吃個飯還要接受拷打
宋代的開封可以說是在同一時間內,世界上最繁榮的城市,不然也不會有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而飲食方面更是遙遙領先。在《馬行街鋪席》中講到過“其餘坊巷院落,縱橫萬數,莫知紀極。處處擁門,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飲食。市井經紀之家,往往只於市店旋買飲食,不置家蔬”就是說“每個區域都是門庭熙攘,茶坊、酒館隨處可見,賣藝、小吃,所在皆是。生活在這裡的生意人,往往習慣在這條街上買東西吃,從不買菜回家做飯。”但是這個有點像我們常說的小吃街,這一點小吃街很難構成我們常說的食堂。
所以小吃街、夜市不夠,酒樓、麵食館、茶肆來湊。那個時候的大一點吃飯的地方都稱之為“分茶”那個時候的酒樓“近里門面窗戶,皆朱綠裝飾,謂之“歡門”。每店各有廳院東西廊,稱呼坐次。客坐則一人執箸紙,遍問坐客”翻譯:酒店靠近大街一邊的門窗,都會用紅綠彩絹等來裝飾,叫作“歡門”。一般規模大一點的酒店,進門就能看到一個大院子,兩邊是走廊,客人一般就在廊中用餐。跑堂會招呼客人落座。客人坐好後,會有跑堂拿出紙筆,仔細詢問客人們都要吃些什麼。這樣的地方硬要說可能還算不上食堂,但在那個時候,平頭百姓也算是有了一個大規模聚餐的場所。
清明上河圖中的聚餐場所之一
在明清時期的食堂,較為出名且代表的就是光祿寺。剛剛我們在唐之後並沒有涉及到官方的食堂。光祿寺則是從被北齊至兩宋不斷發展的機構,其職能就是主要負責備辦筵宴,皇室與宮中辦事人員的日常膳食,及祭品的備辦等。《明史·職官志》記載:“卿掌祭享、宴勞、酒醴、膳饈之事,率少卿、寺丞官屬,辨其名數,會其出入,量其豐約,以聽於禮部。”
我們這次就先不講籌備宴席、祭祀等等,就單說日常飲食這一塊,由於光祿寺的籌備範圍過於驚人,它基本承包了整個皇宮加行政機關的飲食。
光祿寺提供膳食的對象大致包括皇帝,“光祿寺卿職奉御膳”,皇室,“光祿寺隨處預備皇上、兩宮皇太后、后妃御膳及酒飯供具”,及宮中辦差人員,“凡內外衙門官吏、監生、人匠等,供應酒飯者,俱本寺支給”。————《明代光祿寺研究》
相應的,其廚師規模也會達到一個恐怖的量級,根據張鳴老師的調查,光祿寺在北京能查到上來的人口就有4000個,後續有增加了100個。天子所食之物,不僅限於表面上的酒飯,更是皇權的一種延伸,具有不可褻瀆的神聖性。光祿寺卿作為這一機構的首長,對御膳的辦理可謂謹小慎微、不敢怠慢。但是對於皇帝來說,這樣的規模當然是多多益善。
別看光祿寺為皇上的規模如此驚人,但是其中的宮內太監、宮女及其他工作人員的酒飯菜色最為單一,每餐大概只有一到兩種菜。即便是準備如此簡單的伙食,卻需要光祿寺大量的廚料和廚役。
如此眾多的人數,這裡面也會包含相當多的冗餘浪費腐敗等等一些列問題
隨後到了民國時期,我們能蒐集到的資料相當之少,個人認為“食堂”這個東西出現的前提是社會穩定及糧食富足。而在民國時期,這個條件相對苛刻,我們就選用大學食堂來進行介紹,但是其並不能代表當時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所以各位就當笑談看待吧。
據潘光旦先生回憶,在清華的食堂飲食是相當之好的。在那個年代下,學生們可以吃到八菜一湯,四盤五碗,還能在十一月一日吃上火鍋。而在飲食質量上,大米飯、白麵饅頭、小米稀飯、拌上香油的各種醬鹹菜。光是這些東西,都足夠展現了清華在那個時代的待遇。
潘光旦先生
而接下來就是一些比較有意思的文人趣事,不管在哪個年代,年輕的學生尤其的能吃,現在也一樣,我們天天想著乾飯。而在那個時候,清華食堂裡也會有著大胃王比賽,那會還叫“賭東道”像是梁實秋先生就創造過“12個白麵饅頭和三大碗炸醬麵”的記錄。而梁實秋先生能吃那麼多的原因之一,他最早還是一名體育生,那個時候對待體育生也會有著優待,會給他們提供相對於其他桌學生更多的蛋白質,有趣的是體育生那一桌則被其他學生稱之為“雅座”。
光看照片很難相信梁實秋先生會如此能吃
而作為那會國內最頂尖的學府,其食品種類也是多種多樣,不僅有著小館小炒,還有西餐食堂,而吳宓教授就是那裡的常客,還會常常請學生們去那裡吃飯。除去種類多樣的食堂,餐館外,還有著各種小吃零食,其中不少記錄都是梁實秋先生給我們留下的。
讓筆者在查資料時,有著意外之喜得則是在在清華園大門前右方、南院對面的小河邊開起一家飯館,名為“小橋食社”。這家飯店是由趙元任的妻子楊步偉和其他幾位太太一同請了“五芳齋”的廚師來擔任主廚,食社供應以南方菜點為多,食社一開便名聲遠播,學生們知道後,跑來要求搭夥,老師們則來訂酒席。吳公之先生還送來一副對子:“小橋流水一間屋,食社春風滿座人。”
而正巧的是筆者所在的大學食堂正好也有著一家五芳齋,雖然裡面的東西都開始工業化,便捷化,口味則是更加複合,沒想到我這個不學無術的混子也能和小一個世紀前的各位清華偉人能有這樣的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