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鈴芽之旅上映一個月,反超日本本土票房的成績也會有漸漸褪去熱度的未來,兩極分化的口碑、爭吵與謾罵成為新海誠後311三部曲中頗為戲劇的記憶點。隨著正主熱度的流逝,那些爭吵也因流逝而擱置在一旁,並未吵出個結果,只是擱置久了,正主與背景板錯位,抵不住時間的背景板也流逝後,就不知被擱置的爭吵處在什麼樣的虛無中了。(本文成文於2023.4.27)
一:地震、國家、民族的共同體
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作者安德森認為民族是隨著近現代人類社會步入工業化才出現的產物,看似有理,但換言之在此之前“民族“概念必然是尚未發現的風景,而處在維繫社會作用位置上的“未知的共同體”是區別於民族概念的。
問題隨之而來,未知的共同體是什麼?
無論安德森的理念正確與否,我們能確定的是未知的共同體一定存在,在此前提下我們需要回看過去,回到風景被發現的那一刻。
伴隨工業化的到來,產業資本蓬勃發展。沒有砰然墜地,自然經濟理所應當的燃盡,小農們走出自給自足的田地,成為社會大分工的一部分。
在窺探歷史的部分後,尚可粗淺的下一個結論,起碼在英國是自然經濟,也即農業共同體維持著民族共同體出現前的社會。
但若將安德森的理論粗暴的搬進日本社會,搬進文藝作品,甚至與地震扯上關係,那便自然而言因手段的粗暴而出現理論的瑕疵。

圖片中這套“地震民族主義“理論依託自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由某位知乎用戶提出,這個優秀的反例不但能幫我們證明地震與民族沒有太大的關聯性,更能幫助我們找到安德森理論體系中的錯誤。
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認為,“人類社會是交換的聯合體,生產過程中的一切分工都由交換引起,人們之間的產品交換形成了分工。”
而馬克思在對交換理論的進一步批判與解釋中將分工與交換細分為自然分工與社會分工,社會分工的形成乃是依賴於不同生產領域之間的交換。
現代民族概念正是基於這種交換關係而產生的,但並不表示民族概念進一步推動了交換關係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後現代主義可以是依附於現代主義的附庸而存在一般,現代民族概念與之相似的作為交換關係的附屬品存在。
在確立了現代民族概念之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剖析為何地震與現代民族概念沒有正向關聯性了。
不論是離人們記憶稍近的311大地震,還是發生於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人們的失望態度可以說是一如既往。在1995阪神大地震的前幾年,日本進入了知名的泡沫經濟破碎時期,也即失去的二十年。非常巧合的是,在2008金融危機的三年之後,日本迎來的又一次地震,2011東日本大地震。人們的失望態度也不難理解了,既有對政府失誤決策的瀆職使國民生命無謂流逝的失望,也有長久經濟停滯甚至衰退那份對未來無力感的失望。
在失望情緒籠罩的社會里,原有的社會交換與分工體系遭到了摧毀,這令苦難只有消解民族主義的作用不言自明瞭,只有優秀的救災行動才會讓災難本身被歸入多難的分類中,而更多的被忽視的苦難只會隨時間流失被漸漸掩蓋而已。同時,體系建構所需的時間與摧毀它相比,實在是長了太多太多,在重新建構的過程中,原先早已被摧毀的“農業共同體”在想象的層面中從地震廢墟里建構起來拾起了維繫社會,也即維繫苦難的大旗,這是一個接受現代民族概念的群體所不得不作出的選擇,這種特殊、扭曲、甚至虛假的 “民族概念”並不是現代民族。如果某天,關於地震的治理像曾經所解決的天災一般得以解決,所謂地震民族主義這個想象的共同體得以消解後,現代日本民族的概念也會一同消解嗎?
二:家庭、自我、精神寄託何處
精神分析法的再建構者拉康認為自我之所以是分裂的,因為自我在本質上就是他人。如果我們認同拉康的理念,進而採用精神分析法去分析鈴芽鈴芽戶締,那麼我們至少需要一個主體,一面鏡子,一個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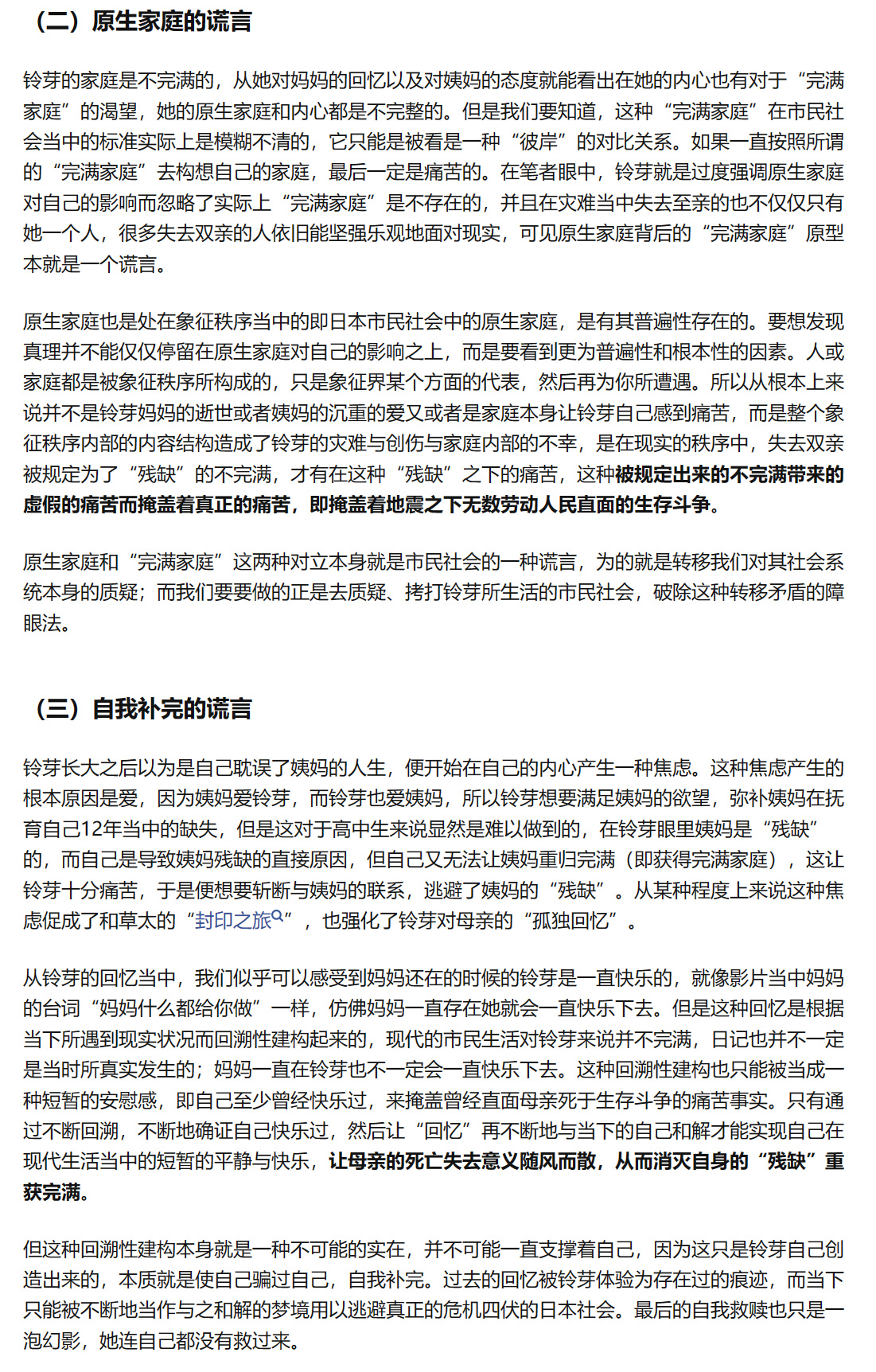
門。從空間關係來看,門起到分割與聯繫地理單元要素的作用,給空間賦予了相對位置屬性,創造了“裡面”與“外面”兩個概念。但鈴芽戶締中的門,也是如此嗎?
往門,通往常世(tokoyo),在日語中有永恆的含義。加入時間概念後,門的作用從連接地理單元轉變為連續時間要素,門完成了從門到鏡子的轉換。此時關門的行為與過程相較以往,多了審視的含義。其一、審視過去;其二、審視自我。我們得到了一面鏡子與關門的主體,先把他者擱置在一旁。
拉康由鏡像理論建構出的想象界是一個“由感知覺、認同與統一性錯覺”所構成的前語言領域,嬰兒在此時期通過鏡像對自我與周遭事物進行模糊而抽象的感知,嬰兒在鏡像中所看到的完整的自我被叫做理想自我。
這個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套用到鈴芽之旅上對巖戶鈴芽進行分析,甚至於可以套用進絕大部分文藝作品,在私小說氾濫的當代日本更是大放光彩。
如果使用拉康的定義,可以得知的是,東日本大地震前的那個在常世中的4歲的巖戶鈴芽已經初步完成了對理想自我的建構,但拉康認為主體永遠無法成為理想自我的存在,甚至於當理想自我出現時,自我就不復存在了。也正因此17歲的巖戶鈴芽,作為主體在常世(鏡像)中看到的4歲的巖戶鈴芽無法作為理想自我存在,此時的鏡像已經不再具有審視作用了,因此而進入了迷失的狀態。
跨越性批判的作者柄谷行人為這種迷失狀態找尋了一種的建構邏輯,即自白制度,根據柄谷行人所說:這是一個和單純的所謂‘自白’根本不同的形式,正是這個形式創造出了必須自白的‘內面’,自白制度的含義不僅僅包含“自白”的行為,它對自白這個行為的實施者和內容都有現代性的要求:它的實施者必須是具有現代性主體的人;它的內容必須在作品中構築“與作者的‘我’相異而獨立的世界”,要反映人的“內面”,而不是告白什麼罪過,更不是簡單的自敘傳。更重要的,現代性的主體和內面都是被這個制度生產出來的。
一旦將4歲的巖戶鈴芽作為內面去看待,很多概念就不言自明的出現了。往門不再是具象的鏡子,而是成為類似於上帝或耶穌但又與之不同的抽象的聆聽者。17歲的鈴芽在關門與前往常世的過程中將自己作為往門的附屬品存在,也即自白行為的實施者能動的放棄了自我本身。因為迷茫的實指是對自我概念的懷疑,所以巖戶鈴芽轉而凝視自身的主體性,將自我與自身的主體性分割開來,往門可以說是起到了連續的作用,同時對精神進行解放,還是主體精神本身。
那巖戶環呢?
毫無疑問的是,本片中的母性大他者從一而終的是鈴芽的生母,而父親的形象與男性形象在本片中或多或少有著殘缺。
拉康對父親形象的不在場視作為主體邊界界限失敗的象徵,這同樣是許多文藝作品中迷失狀態的重要來源,但我們已知巖戶鈴芽的迷失不來源於此。換言之父性大他者的形象在本片中以一種非常隱晦的方式,甚至於可能是新海誠自身都未能發現的方式出現了。這個形象的承受者就是環姨媽。
例如,在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後4歲的巖戶鈴芽跑入雪地中尋找母親,被巖戶環發現,與巖戶環發生摩擦,最終被巖戶環帶了回去,這段劇情沒有展現出的但理所應當的內容是,巖戶鈴芽在與巖戶環的摩擦中一定完成了從尋找母親到放棄尋找母親的轉變。這個轉變象徵著巖戶鈴芽內心接受了母親逝世的事實,也即巖戶環不自覺的推動巖戶鈴芽殺死了她的母性大他者。
拉康認為只有比母性大他者更強大的父性大他者才能殺死母性大他者,也因此說明巖戶環作為女性承擔起了父性大他者的部分屬性。雖說父性大他者是虛指,不是實指,不代表一定由男性承擔,但現實世界中的視差一定會使得主體認識偏差,所以巖戶環不單繼承了這殘缺的父性大他者,也必然的繼承了部分的母性大他者屬性。如果用通俗的話作不恰當的比方便是:又當爹又當媽。
這份殘缺性使得主體對主體邊界認知的殘缺,不具有彈性。在現實生活中的表象則會愈來愈趨向於兩個極端,不是徹底拒絕,便是讓渡自我。在本片中這種徹底拒絕的行為則表現為了雨天收費站時的情感爆發。
三:創傷,和解,故土的溫柔鄉
家庭作為最小的社會單元仍包含了眾多人際關係,如親子、夫妻、兄弟關係等,同時受父權、家庭暴力等權力關係塑造,最終體現為自我的衝突與慾望、自我與他人的衝突以及社會倫理道德等矛盾衝突。因此,社會的面貌往往被家庭反映出現。

家庭對人的影響與塑造之深遠,使得個體性的創傷往往來源於此,但為何在作為群體性事件創傷的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後,日本文藝界普遍選擇了迴歸對個體性創傷的關注,或是依託個體性創傷的認同感轉化為群體性創傷呢?
這個世界衚衕小巷無處不在。
任誰都知道日本當代作家的代表中,作為國民作家的村上春樹佔據了重要一席,宇田常寬在看完鈴芽之旅後帶著三分戲謔的表示:新海誠接過村上春樹國民作家的接力棒走向了空洞。
有關東京中心主義這個概念的源頭我無法考據,但這個概念非常恰當的切中了國民作家的空洞性,福岡、新宮、熊野,這些日本的後發地區如同南北戰爭後的南方州一般,是被遺忘的風景與被遺忘的人們,對於生活在東京都23區中的現代都市人而言,在城市化與工業化中落下來的那些地方已經不再是日本的一部分了。新海誠把其作為日本的全部、全部的日本推向世界時,便操起了這份空洞性。在後311三部曲中,主人公總是生活在鄉下就可見這一斑空洞性,這份故土的溫柔鄉是給商業電影的受眾現代都市人們看的。
千禧年時,日本社會從泡沫經濟、阪神大地震與奧姆真理教的陰霾中漸漸站起來,國民GDP總值恢復到了相對高位,人們開始重新思考現代化、都市化中的家庭關係,許多舊有關係被打破,在轉型中個人的創傷被群體所關注,並期望通過直視創傷等方式來找尋治癒創傷的辦法,因此日本迎來了21世紀前十年創傷敘事的發展時期。
同時,千禧年後東京都都市圈的城市集聚效應使東京都與日本其他各縣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拉大,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使如四方田犬彥等一批日本創作家們有意識的批判東京中心主義,那些無人在意的風景仍是日本的一部分。
再之後,311地震打斷了這一切。再一次的巨大創傷直接性的撕裂的日本社會,沒人有精力再去關注那些本就沒人關注的風景了,直接受災縣所需的災後重建時間又更進一步、變本加厲的撕裂了人們的精神世界,同時脆弱的社會結構已經經受不起也沒有興趣再經歷解構與反叛,由於群體的分化,使得群體性創傷的直接建構也不復存在了。
在這樣的時代中,新海誠所選擇的和解敘事是被迫的和解,我曾說:新海誠就出生在後現代生活裡談何保衛呢,只不過是大多數中的哪一個,與時代一同面對新自由帝國主義心安理得的接受並躺平了。
在這般時代背景下,能夠做到站起來向前走,解放災害對社會與自我的禁錮,在我看來已屬不易。個體所尋求的解放並非批倒過去所經歷的一切,對當下生活方式的再思考亦是一種解放,對其所謂批判人物命運陷入原有秩序中,無非是吹毛求疵,無數人在中失序的迷失中夾縫生存,可曾想過在旁人眼中不值一提的這般固有秩序,正是一個群體,一個時代,一個國家所傾力追求的。
四:空洞、掩蓋、失去的世界系
世界系的涵義是廣泛且抽象的,在此我採用東浩紀、岡田鬥司夫等人的定義:主人公之間友情與愛情的小問題與世界存亡的大問題成為密不可分的。
藤津亮太認為喪失感是商業化程度較高的後311三部曲與曾經新海誠範式的小清新文藝片的一個重要分界元素。無論是星之聲、言葉之庭或秒速五釐米,由於這些作品中的戀愛關係總是不確立的,但影片又熱衷於以男性自戀視角為前提的,使得男主角總在失去那些不存在的關係與事物。換言之在失去不存在事物的影片之外,在觀眾看不到的地方男性自戀的視角將得到消解。
與這份視角一同消解的,是新海誠所堅持的世界系敘事,當失去了自戀的幻想,愛情隨之消散時,為愛情所存在的世界系這層外殼便也一同失去價值了。從某種角度上來說,這與新世紀福音戰士·終的走入現實類似。(庵野秀明上樓梯)
在21世紀二十年代,世界系作品已經不再像過去一般是被社會所接受甚至理解的亞文化,以至於在亞文化社區內部世界系都不算是熱門的話題。這源於世界系所帶來的新鮮感已經不再能抵消內核所蘊涵的空洞,由於這種空洞的存在,在世界系外殼中的喪失感所喪失的是空洞本身,所以新海誠在言葉之庭及之前的影片爭議反而不算大。
正因如此,如果期望通過世界系敘事來展現一個相對宏大的社會話題,那麼作品必然得是不能促成戀愛關係的,也即在個人層面上不能達到HE結局。或許秉持原教旨純愛觀點的人們會認為在戀愛關係建立前的互動與成長才是最好的,但這終究是少數。
顯而易見的是,從你的名字到鈴芽之旅,戀愛關係的確立變得愈發放肆起來,在你的名字中,男女主角直到最後才以模糊記憶的樣子相見;天氣之子則是在最重要的世界or愛情選擇中確立關係,也即電影的中後段;而鈴芽之旅則是在一開始就確立起了這份關係。喪失感的喪失使得觀眾們認為三部曲比較起來一部比一部乏味,一部比一部空洞,但新海誠真的是在世界系敘事的道路上狂奔,並且沒回過頭嗎?
天氣之子中的東京被淹沒時,須賀對帆高說:別以為你們改變了世界,“反正世界本來就是瘋狂的”。婆婆富美也說:如今被淹沒的東京只是“回到了幾百年前本來的樣子”。這兩句話實則道出了在二十年代世界系敘事的迷失,世界系敘事在二十多年的創作實踐中幾乎沒能推動任何一項公共議題的發展,創作者可以說放棄了其屬性,當世界系僅有的“被消解的空洞”也成為無意義的空洞時,世界系就被失去了。如今的世界系敘事只不過因為能抽離掉不必要的社會元素,便於創作者進行創造,轉變為為展開劇情而搭建的大大的戲臺罷了。
將後311三部曲進行對比,鈴芽之旅從天氣之子的倫理問題迴轉到了你的名字中的掩蓋問題,但掩蓋的手法與立意又高於你的名字,畢竟再怎麼說鈴芽之旅也是選擇了正面回應與對抗東日本大地震中的某些公共議題,這種不在主觀上將惡意與壞人形象賦予地震的做法,總比村上春樹來的強些,迴避核議題的後311文藝作品也不止新海誠一家,諸如:神啊2011、核洩漏事故後的世界、床邊的謀殺案等文藝作品同樣迴避了核議題,估計新海誠本人寫企劃書時也是抱著面對新自由主義的態度一般,擺了吧。
在本片中巖戶家還有一層難民的身份是新海誠沒有強調出的,幾乎被掩蓋的事物,起碼對於大多數中國觀眾是如此,新海誠採用的演出形式與色彩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對觀眾產生了誤導,向觀眾展現出的是一個雖有痛苦,但總體美好,帶著回憶濾鏡的故鄉。而回避了福島一千平方公里、數萬民眾們至今無法回去的鬼城故鄉。
需要指出的是,這裡的掩蓋是民眾自身的掩蓋,在本片中的展現是自然的,新海誠如果對其作強調處理可以看作是放大了難民的苦難。因為在失去家人、住所和工作後,部分災民會產生作為人的尊嚴和個人的主體性已經全部喪失的屈辱感,形成類似“難民”的心理,而並非實質他們是難民。這便是我反對將巖戶家視作需要社會看護的特殊者,完全是站在了高位對受難者進行俯視的廉價同情與憐憫,而絲毫不理解對方也是有著獨立人格的人。
這些迴避在一定程度上無疑會對公共性生活在看不見的陰影中被反覆撕裂,但站在客觀理性人的視角去看,這種迴避實則是為了避免更大的撕裂。如果想追求絕對的公共生活,那還是選擇用絕對的解構主義消解掉公共生活本身吧。
參考文獻
著作類:
[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增訂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日)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3](日)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跨越性批判——康德與馬克思[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期刊類:
[4]劉文.拉康的鏡像理論與自我的建構[J]學術交流,2006(7)
[5]洪小兵.略論馬克思的交換理論及其現實意義[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3(2)
[6]徐小棠.從反叛到和解——21世紀初日本家庭片的創傷敘事研究[J]當代電影,2018(11)
[7]熊淑娥.從災難文學透視當代日本社會困境——以第61屆群像新人文學獎作品《美顏》為視角[J]東北亞刊,2019(6)
[8]王欽.社會的“強倫理”與“世界”的“弱倫理”——論新海誠《天氣之子》[J]中國圖書評論,2020(4):29-36
[9]崔健,舒練.拉康“三界學說”對意識形態理論的啟示及其侷限[J]世界哲學,2021(1)
[10]羅詩琳.虛構的存在之真——以拉康“鏡像理論”分析《霸王別姬》中程蝶衣的心理機制[J]今古文創,2023(14)
學位論文類:
[11]尹茸葦.後3·11時代日本新生代導演的症候表達和創傷敘事[D]北京:中國傳媒大學,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