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信睿週報》第56期,經授權發表。
文_蘇婉(北京大學人類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後)
傳統遊戲與儀式的邊界非常模糊。如果說儀式是人類學研究偏愛的正統代言人,那麼遊戲就是那個被忽視的孿生兄弟。無論是莫斯的誇富宴、馬林諾夫斯基的庫拉圈還是葛蘭言的節慶與歌謠,人類學的經典範式都是以儀式的名義建構的。雖然大師們都提到了這些儀式的遊戲屬性,但僅僅將遊戲是作為儀式的一個次級範疇,並沒有重點研究。人類學者蒂裡·溫德林(Thierry Wendling)統計了1888年至2000年間《美國人類學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這是一本由對遊戲充滿興趣的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參與創辦的人類學雜誌)以遊戲(play)為主題的文章,他發現,人類學家對遊戲的興趣自1930年就開始降低,以至於1949年以後,這一主題的文章幾乎完全消失了。
在《Why We Play: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我們為什麼要玩》)這本書中,法國人類學家羅伯特·胡瑪雍(Roberte Hamayon)追溯了遊戲的“次要性”歷史。遊戲是一種跨文化的民俗形式,其由於被看作一種不太嚴肅的儀式形式而受到忽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對羅馬馬戲團遊戲和相關遊戲形式的貶損和打壓。這是因為一神教中的神是一個在社會生活中不容被模仿和玩弄的絕對存在,而這與泛靈或多神的宗教形態恰好相反——在萬物有靈信仰中,神靈是可以通過遊戲來互動和邀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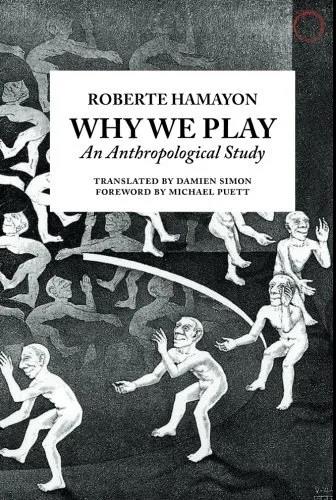
Why We Play: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Roberte Hamayon,HAU 2016
上帝不喜歡遊戲,而神靈喜歡遊戲。在胡瑪雍考察的蒙古和西伯利亞地區集體儀式的框架中,遊戲(playing)意味著人類與掌握其生活來源的非物質實體具有同源性,這種同源性框架將雙方置於夥伴或敵對的平等關係當中。但平等關係卻是等級體系所厭惡的。因此,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裡,長期存在著教會與教父對一切遊戲和玩耍的譴責,這種壓制後來在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治中也得到了轉述。過了大約一千年,軍事藝術、體育競技之類的“嚴肅遊戲”才以高度專門化的形式從整體的遊戲類別中分離出來,而餘下的那些沒有顯著政治與經濟功用的“不嚴肅遊戲”,則被降級為輕佻和無用的東西。
如果說對遊戲的排斥性教化反映在包括人類學在內的西方社會科學研究視角當中,那麼如胡瑪雍所言,以跨文化和比較研究的視角關注遊戲可以克服西方中心主義的認識模式。遊戲不是祈禱、祭祀、交換等儀式的“不嚴肅的”版本,而是在根本上有著不同“設計”、隱含著不同類型關係的人類活動,它應當被作為與儀式相當的“另一個範疇”來討論。
然而,遊戲作為“另一個範疇”的獨立性又該如何界定?對於不玩遊戲或對遊戲不感興趣的人來說,這個問題反而更容易回答。遊戲的某種“無聊”正是在於它獨特的非現實性,在於它是對現實生活的“打斷”。歷史學家赫伊津哈在《遊戲的人:文化中游戲成分的研究》中將這種“不平常”“不真實”界定為遊戲的核心特徵之一:在遊戲的過程中,相信與假裝之間的區別消失了,遊戲者既知情又“受騙”,且甘願“受騙”。從赫伊津哈所考察的神聖儀式、詩歌藝術的古典意義上來看,遊戲相對於現實而言是有邊界的,這一邊界劃定了特定的時空與規則範圍,而且常常與現實利益無關。這一點似乎也得到過弗洛伊德的贊同,他認為“遊戲的對立面不是嚴肅,而是真實”。
數字遊戲出現之後,遊戲研究者將這種“分離性判斷”濃縮在“魔圈”(magic circle)隱喻之中。自21世紀初開始,“魔圈”隱喻就成了遊戲研究中被反覆討論的對象。在第一次出現“魔圈”的文本中,赫伊津哈這樣寫道:
所有遊戲都是在遊戲場所中進行和存在的。……競技場、牌桌、魔圈、廟宇、舞臺、銀幕、網球場、法庭……在形式上、功能上都是遊戲場所,即隔開、圍住、奉若神明的禁地,特殊規則通行其間。所有這些場所都是平常世界裡的臨時世界,用於進行與外界隔絕的活動。遊戲場所內,無條件、特有的秩序主宰一切。
通過劃定空間並在其中創造秩序,遊戲把暫時的、受約束的完美帶進殘缺的世界和混亂的生活,讓遊戲者得以進入嚴肅的神聖狀態。
數字遊戲誕生之後,遊戲與現實相分離的規範性假設受到了挑戰。在數字世界民族誌的“深描”之下,抽象的遊戲概念越是被還原為具體的遊戲,遊戲與現實的邊界似乎越是呈現出模糊的狀態。首先,真實社交在數字遊戲中不斷髮生,這些關係延伸到線下,發展成社群與社團,甚至演變為更為親密的摯友或戀人關係。也就是說,數字世界雖是虛擬的,但社會關係卻是真實的,無論人們接受與否,這些關係都可以跨越虛實之間的不嚴格邊界。
“魔圈”內的特定規則也可以被人為地改變。按照社會學家T.L.泰勒(T. L. Taylor)的看法,在互動關係更加密集的大型多人在線遊戲(MMOG)中,人們可以通過創建“模組”(mod)的方式來改變遊戲的內容和規則。由此,“魔圈”原先的秩序也就被打破了,遊戲不再是僅遵循既定規則的烏托邦。
所以,遊戲肯定不是完全封閉的,用人類學家托馬斯·馬拉比(Thomas Malaby)較為保守的措辭來說—至少是“半封閉”的。遊戲邊界之所以“脆弱”,關鍵在於遊戲根本上是由人類實踐構成的,因此始終處於“成為”(becoming)的開放過程中。規則不再是遊戲的根本,偶然性才是。“魔圈”製造的秩序恐怕只是一個鬆散的框架,遊戲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在開放的偶然性與可重複的行動條件之間達到了一種生成性的平衡。
泰勒和馬拉比的結論帶有實踐理論和過程理論的印記,二者都強調社會行動是被文化性地塑造著的實踐,而不是對任何超驗結構的表述。實踐論者都喜歡遊戲,因為實踐意味著在對規則與模式的不斷操演中反過來重塑它們,意味著情境性、自主性和創造的潛能。
不過,也有遊戲學者認為,對“魔圈”的指控根本是子虛烏有。遊戲學者傑斯珀·尤爾(Jesper Juul)認為,“魔圈”本質上並不是泰勒和馬拉比敘述中那種由外部主體制造並強加的封閉秩序,而是與玩家合意創造、協商和維護的心理及社會空間。這一觀點與人類學家格雷戈裡·貝特森(Gregory Bateson)提出的“遊戲是一種交流框架”的說法相似。貝特森提出了遊戲的元交流(metacommunication)理論,即遊戲是關於交流的交流,“這是個遊戲”的共同意願在遊戲起始時創造出一個悖論性的框架,在這個框架中的遊戲行為都包含或指向非遊戲(non-play)的行為,但又並不代表這些行為通常所代表的意義——所有的遊戲參與者必須在主觀上提醒自己“這只是個遊戲”,否則遊戲的框架就會頃刻消失。
因此,所有參與者的自願是達成遊戲的第一步,如果真的存在一個所謂的“魔圈”,也是參與者可以隨時退出和顛覆的邊界。遊戲的過程就是維護這個空間與世界其他部分之間不完美的“分離”。因此,遊戲的好玩之處,正是在於玩家可以選擇創造和否認“魔圈”。尤爾繼而提出用“拼圖”隱喻來代替可能造成誤解的“魔圈”:一塊拼圖的特性在於要融入其他拼圖共同構成的整體版圖,遊戲的特性也在於要與具體的遊戲背景相契合,“遊戲必須被整合到一個環境中,以便被體驗為與該環境的分離。”
“魔圈”爭論逐漸落下帷幕的同時,遊戲封閉性的邊界“被打開”,似乎也是一種順應理論大潮的宿命。從人類學古老的族群研究開始,邊界就具有悖論性的含義:其既意味著區分和隔離的狀態,也蘊含著跨越和連接不同領域的可能。對信息技術的科學哲學和社會學研究,正在賦予遊戲研究中的“邊界”近乎革命性的新意義。
正如尤爾所說,“魔圈”爭論的混亂來自傳統理論關注點在數字研究中的錯置——傳統研究中的遊戲像是儀式的開放或簡單版本,而數字遊戲則是複雜的人造之物(artifact)。在這種轉變中,有一個問題凸顯出來,即遊戲生產者的出現。傳統遊戲中的規則制定者要麼無法追溯,要麼並沒有在遊戲現場進行的“儀式過程”那麼重要。遊戲儀式屬性的“祛魅”也與遊戲生產者本身的出現緊密相關:每個電子遊戲都有明確的開發者、設計師、營銷部門、發行商、法律團隊,他們與玩家以互動實踐、共同建構的行動創造出遊戲組合體。遊戲在多方參與的“交叉”意義上成為了一種“邊界物”(boundary objects)。
“邊界物”是蘇珊·利·斯塔(Susan Leigh Star)和詹姆斯·R.格瑞史莫(James R. Griesemer)在1989年提出的概念:“邊界物具有足以適應各方的需求和限制的可塑性,同時又強大到可以在不同節點處保持不變的身份……它們在不同的社會世界裡有不同的意義,但它們的結構對一個以上的世界來說是共同的,足以使它們可以被識別、被作為一種翻譯的手段。”在原文中,“邊界物”是業餘收藏家和博物館專業人士兩個社會群體之間共享的信息,例如標本、田野筆記和地圖,他們對這些對象的解釋不同、用法不同,但這些對象在內容上可以保持極高的完整性,並且始終能夠讓雙方保持有效的溝通和協作。
遊戲之所以能夠被視作一種“邊界物”,正是因為它也是一種橫跨多個社區、能夠組織不同認知的人造物。正如泰勒所說,遊戲被一系列行動者——從設計者、營銷商到玩家——共同參與、拓展和改變,已超出了遊戲生產者的意圖,被捲入到個人意義製造、社會過程及技術結構的多重邏輯當中。所有參與者都可以為邊界物貢獻知識,修改它或以某種方式使用它。
“玩工”(playbour)的概念特別能展現遊戲產業中因多方參與而產生的工作與娛樂的混合狀態。遊戲理論學者尤里安·庫克裡奇(Julian Kucklich)將創建遊戲“模組”的玩家稱為“玩工”。“模組”是玩家為遊戲創建新的內容來增強遊戲體驗的數字創作,著名的模組包括由《半條命》發展而來的模組《反恐精英》,由《魔獸爭霸III》發展而來的《DOTA》。這種共同創作使得創建和維護“模組”成為“產消合一”的行為:創建“模組”的工作可以被視為有趣和愉快的“娛樂”,但它同時又是為遊戲公司的資本積累提供無償勞動、不享有最終版權的“工作”。正如庫克裡奇所說,遊戲“模組”的自願性和非營利性使資本對遊戲“模組”愛好者的剝削變得更為隱匿,而這種隱性剝削受到忽視,與把數字遊戲有關的一切都當做玩家單向操作的休閒娛樂活動的長期觀念有關。因此,“邊界物”也有助於我們理解遊戲行動及體驗上的複雜性,尤其能夠修正關於遊戲與工作的習慣性區分。
在數字遊戲幾乎成為公眾在談論game時的唯一所指之前,play才是理論研究中最常出現的範疇。玩樂(play)作為文化行動的非功利性和非生產性,特別受到法國學者的頌揚。20世紀最著名的遊戲理論家羅傑·卡約瓦(Roger Caillois)曾在《Man,Play and Games》(《人、玩與遊戲》)中提出,“遊戲是一種純粹的浪費活動”,並強調遊戲作為經濟生產領域之外的有趣活動的作用,“在比賽結束時,所有人都可以而且必須在同一點重新開始。沒有收穫或製造任何東西,沒有創造出傑作,沒有積累任何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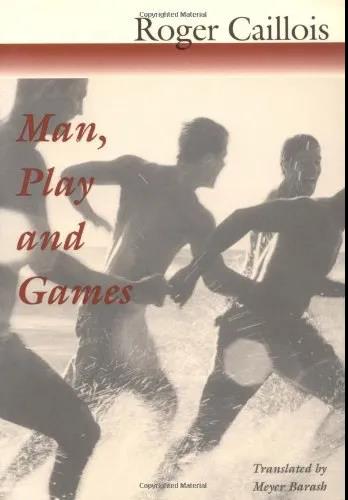
Man, play, and games ,Roger Caill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1.
大衛·格雷伯明確區分過play與game。他把兜轉在臃腫科層制中填寫大量表格的工作定義為一種game,並認為game的明確規則是人們怨恨繁雜的行政程序但又“痴迷”於此的原因。他認為,玩樂(play)不可預測,而遊戲(game)則是有明確規則的——“每個人都知道規則是什麼,不僅如此,人們還真的遵循規則。只要遵循規則,人們甚至真的能夠成為贏家!這一點,以及人們無須像在真實生活裡一般、而是完全自願遵守規則,正是遊戲的樂趣所在”。
大部分時候,game和play常被替換使用,但是一些數字遊戲的研究者卻對這種關聯“耿耿於懷”,因為play自帶的好玩的意涵削弱了數字遊戲中行動者體驗的複雜性,消解了數字遊戲可能產生的外部效應。其實,沒有必要因為這個原因讓數字遊戲與play劃清邊界。人類學一直在為當代人被異化的社會生命尋找新的可能,探尋著人是否能夠在生產者或消費者之外,作為一個思考者、體驗者和創造者來生活。在“要成為有用之人、做有用之事”的規訓之外,好玩或有趣本身也具有不可否認的正當性。“好玩”這件事本身便是對成為“單向度的人”的抵抗,而抵抗本身就是有意義的。
政治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持續關注各種形態的支配與抵抗關係。他在《六論自發性》中,用“建築工地”式的遊樂場和沒有按照字母順序排列的越戰陣亡者紀念碑,來強調開放和自主的遊戲之於社會生活的嚴肅意義。和所有哺乳動物一樣,人的社會性、適應性、歸屬感和創造力都仰賴看似無序又毫無實際目的的遊戲。他引用有反社會人格的人與其缺乏玩耍經歷的童年之間具有相關性的例子,證明遊戲對個人和社會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
![六論自發性: 自主、尊嚴, 以及有意義的工作和遊戲,[美] 詹姆斯·C.斯科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https://image.gcores.com/82442163-4102-49b0-b51d-0759d386dfc7.jpg)
六論自發性: 自主、尊嚴, 以及有意義的工作和遊戲,[美] 詹姆斯·C.斯科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
席勒有句被廣為引用的老話:“只有當人在充分意義上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只要我們還在探索如何擁有更值得一過的人生和更平等良善的社會,那麼對於遊戲、遊戲邊界的討論,就將永遠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