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龐蒂有句經典的論述:“我擁有一個身體,我擁有一個世界。”這句簡潔明瞭的口號宣揚了現代哲學以身體本位而非以意識本位的特徵,同時這裡主體“我”暗含的前提是擁有肉身現實的自然人。然而,隨著技術媒介發展到了當今的地步,此處“我”的內涵也得到了更豐富的擴展,它不再單單指涉現實的自然人,同時包括了更多的“虛擬”
[1]意味。例如,電子遊戲中的第一人稱角色便也在一般意義上成為了一個新的主體。
此時問題變成了,在電子遊戲的語境下,角色主體也適用於梅洛-龐蒂哲學意義上的“我”嗎,角色主體也擁有一個身體、同時擁有世界嗎?換句話說,梅洛-龐蒂的這種身體理論是否還適用於當今多元語境下的主體呢?本文試圖從梅洛-龐蒂的深度空間概念出發,分析在《艾迪芬奇的記憶》中的角色是如何感知世界的。
本文將分為以下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梅洛-龐蒂從空間的深度維度對“我擁有一個身體,我擁有一個世界”的論證,以及此種空間深度呈現出“動機-情境-決定”的交互關係;第二部分將借用第一部分的模型分析《艾迪芬奇的記憶》中的角色主體,考察遊戲中的角色是否與梅洛-龐蒂語境下的論述享有相同意向性結構;第三部分將具體以《艾迪芬奇的記憶》中的三個不同角色為例,考察不同角色是如何以具體的方式感知世界的。
一、梅洛-龐蒂的深度空間
梅洛-龐蒂的深度空間是他的身體現象學的一個重要側面,而他從存在論出發關於身體的主要態度可以被表述為:身體-主體作為一個在世界中存在的主體,同時也是一個介入的、實踐的主體。[2]可以看到,梅洛-龐蒂在這裡凸顯出了身體主體曖昧的二重性:一方面在世存在的身體主體是事先被給出的,它永遠首先被拋入進一個情境之中存在;另一方面只有通過身體主體能動的運動,世界才得以展開。在這樣的語境下,梅洛-龐蒂才提出了“我擁有一個身體”也即“我是我的身體”,以及“我擁有一個世界”。
可以看到,身體主體與世界呈現出相互交互的關係,這種交互通過身體的知覺得以可能。而二者進行互動的場域則被稱之為“現象場”或“知覺場”,身體與世界通過知覺活動產生的現象場而得到連接,現象場同時反映出外部空間與身體空間的雙重界域。因而,梅洛-龐蒂關於空間的描述也由此得到展開。這樣一種空間絕非單一的客觀空間或主觀空間,而是外部空間與身體空間的辯證統一,可以說,身體空間是外部空間顯現的基礎,而空間正是由身體開拓出來的。
在這樣的空間觀中,梅洛-龐蒂尤為強調空間中的深度維度(depth),他認為“深度比其他空間維度更直接地要求我們摒棄關於世界的偏見和重新發現世界得以顯現的最初體驗;可以說,深度最具有‘存在的’特徵。”[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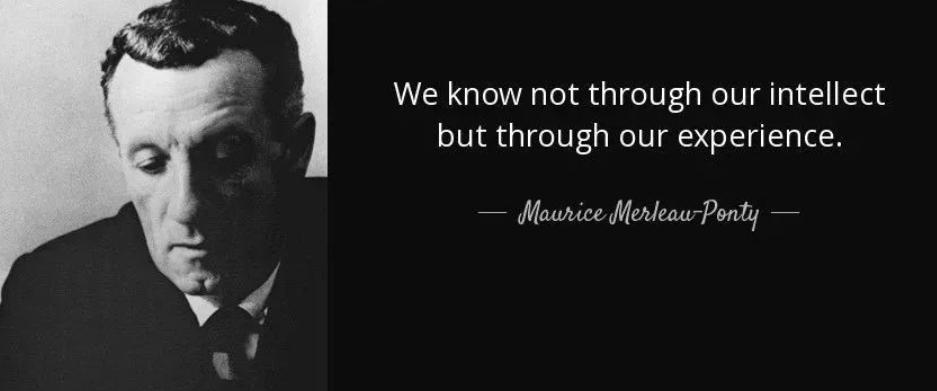
應該如何理解空間之深度?首先,梅洛-龐蒂批判傳統經驗論與觀念論共享的關於“深度是不可見的”的觀點,這種觀點把空間當成了對象性的存在,“對象性”預設了主體與客體分離以及相對而立的情形,物體作為一種平面圖形被得到理解,而在這樣一種存在觀中自然也不存在深度的位置了,而這顯然與從身體視角出發的境域化存在相悖。其次,從知覺的角度切入,空間之深度恰恰變成了可見的,空間之深度正顯現出身體主體與世界之間“不可消解的連接”關係。
在梅洛-龐蒂看來,深度既不屬於物與物的關係,也不是思維主體的非具身性構造,而是一種“動機-情境-決定”的動態、有機的相互關係。藉助Stratton和Wertheimer的實驗[6]他發現,行為或現象的驅動不能被簡單還原為某種獨立的第三人稱因果關係和意識構造出的理性決定。它們的動因根植於以過去、身體和世界相互交織,並作為推進和重塑各種可能性的關係背景之中。
[7] 而動機與決定的關係實際上是“一個處境的兩個元素:前者是作為事實的處境,後者是被承擔的處境。”[8]可以說,這是意義與意義之生效的關係。
此種“意義”並非狹隘意義上的價值,更合理地說,它指向更為廣泛的意向性。身體是意向性的身體,梅洛-龐蒂也將其稱之為“虛擬的身體”:“對於景象之定位有意義的不是我實際存在的身體,不是作為客觀空間中一物的身體,而是一個由各種可能行動構成的系統,一個虛擬的身體,它的現象‘位置’由其任務和處境規定。哪裡有事要做,哪裡就有我的身體。”[9] 因而也可以說,這種從肉身化軀體化的真實身體到意向性的虛擬身體的轉變,正是通過空間之深度體現出的一種關係。
通過意向性的身體在空間中深度的展開,“我擁有一個身體”也正式得到了賦義。所謂“擁有”身體,就是讓身體成為作為我一切行動之根據的背景,就是讓身體進入曖昧的身體空間。而只有當意向性的身體在存在論的意義上被齧合進世界之中,主體才得以“在世界中存在”。[10]這種意向性關係的內涵非常豐富,它包含牛頓物理學式的空間維度[11],同時也包含歷史文化價值的維度,小到個人日常的經歷、大到民族的興衰,任何身體主體在世界中進行的行動都建基於最源初的意向性之上,而此種意向性關係在空間中正具體化為“動機-情境-決定”的動態關係。當身體通過運動捕捉作為情境出現的深度線索時,這些線索已經將“含混的”(Implicit)意義(動機)給予了身體,而視知覺的目光(決定)才使得這些意義清晰化(Explicit),構成深度表現出來。[12]
梅洛-龐蒂關於深度的討論不止於此。在1953年法蘭西學院講課稿《感覺的世界和表達的世界》中,他進一步將深度關係溯源為身體表達與生成的慾望。他明確指出此種“動機-情境-決定”中包含著慾望與快樂的訴求。這裡的快樂是表達的快樂,而我們的身體就是被給予的表達,知覺主體和被知覺的空間事物通過知覺進程共同實現了表達的慾望。[13]而在後期著作《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中,梅洛-龐蒂更是試圖將空間深度提升到本體論的地步:“沒有深度就沒有一個世界或存在……深度使事物有一個肉身(Flesh),也就是說它使事物抵制我對各種障礙的探究,它是一種抵抗,但這種抵抗恰恰是事物的實在、事物的開放、事物的當下現實…在被我的純粹觀看當作現在之持留的東西中,深度就是源始。”[14]
可以看到,空間深度在梅洛-龐蒂中後期進一步從身體主體出發的“動機-情境-決定”關係被拓展為了事物之間可見與不可見的張力。但總得來說,空間深度是“我擁有一個世界”的可能性標誌。正是事物與世界之中存在深度的可能,正是身體主體能夠自發地建立與開拓此中的深度關係,整個世界才得以通過知覺向主體呈現。
二、《艾迪芬奇的記憶》中的角色主體是如何感知世界的?
通過第一部分對梅洛-龐蒂的空間深度的分析,可以看到身體主體感知世界的其一重要方式就是建立與開拓深度,而這種深度關係可以被描述為“動機-情境-決定”關係,身體首先意向性地與事物與世界建立勾連,其次又通過行動開拓出空間場域。這樣一種建立-開拓關係實際上就是動機-決定的體現,它們一同作為情境中兩個相互依存的要素而出現。
那麼,當這樣一種身體與空間的關係移置到遊戲角色主體中時,是否還依舊奏效?遊戲角色主體是否依舊是通過建立與開拓空間深度的方式感知世界的?
在開展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對本文中的遊戲“角色主體”進行說明與限定。與一般從“玩家主體”視角出發的論述不同[15],本文以角色為中心而展開“角色主體”出發的論述,這種視角並非棄絕了現實玩家層面,而是強調“玩家進入角色、併成為角色”這樣一種狀態。這種視角出發的“角色主體”實則具有角色-玩家二重性。
角色-玩家這二重性體現了電子遊戲操控與被操控的媒介性質。電子遊戲的特殊性在於,它通過操控與交互的方式使角色與玩家形成連接,遊戲中的主體也因而獲得了雙重身份——這是角色與玩家的相互映照。以此方式構成的角色主體,一方面以被拋的方式完全浸入遊戲世界中,另一方面又在遊戲之外操控與交互遊戲世界中的行動。這二者的關係可以被描述為,遊戲中的角色以敞開的方式面向玩家,並藉助玩家之身體體驗著遊戲世界。在這樣的遊戲過程中,角色身體與玩家身體也實現了合一,正是在“玩家扮演角色”的遊戲狀態中,角色主體才達到了擁有身體以及擁有世界的可能。
因而,遊戲中的角色主體在身體方面也具備了角色身體-玩家身體的二重性,當後文提及角色主體時皆包含這兩個方面。

《艾迪芬奇的記憶》是一款第一人稱視角出發的遊戲,玩家將通過扮演一個家族中不同的成員而體驗各自的死亡。下文將通過兩個方面對遊戲中的角色主體感知世界進行分析:首先,本部分是從空間深度出發探討角色主體知覺世界的可能性;其次,下一部分將探討不同角色主體是如何呈現出各自知覺世界的。
首先,針對第一個問題,角色主體以簡化的意向性探索並開拓著遊戲世界。
《艾迪芬奇的記憶》以第一人稱視角的設定就讓角色主體與真實玩家主體享有共同的觀看方式——遊戲屏幕恰呈現出眼睛看到的視野。視線所及也隨著角色主體的行動而得到擴展,角色主體的行動設計也非常簡單:通過操縱上下左右的控制鍵,角色得以實現行走;而通過其他特殊形式的操縱方式,角色得以實現與遊戲世界內不同物品的交互動作。通過以上兩種方式,遊戲角色得以在遊戲世界中展開探索。
表面上看,這樣一種以步行模擬器[16]呈現的簡單玩法似乎並無深意。但其實,視野的呈現與簡單的行動設計已經呈現出身體意向性的重要方面。如上文中所述,身體並不僅僅指涉實在的肉體,而更強調意向性的“虛擬身體”方面,身體的意向往往與所置身的處境與任務規定相關,而角色身體恰恰突出了這一意向指向的層面。
在遊戲中,角色主體的行動往往帶有強烈的非主題的目的性,例如遊戲中的諸多行動都可以通過“我需要找到一個可以交互的特殊物品,從而探尋下一步可能的行動”來描述。這樣一種簡潔明快、直切正題的玩法設計使玩家脫離了現實生活中可能性過於豐富的意義場,從而以明確的意向指向遊戲世界中固定的現象場[17]。這樣一種意向性性貫穿遊戲始終,指引著角色進行遊戲。當然此處需要澄清的是,“意向性”並不能被理解為具有明確主題的目的性,意向性的意義實際上是非主題性的,它在目的性之前存在並給予目的性以支持。角色在遊戲中總是將遊戲世界看成充滿可能性的意義場,而非僅一物理空間,因為角色的目的就是為了通過與遊戲世界多層次的互動而掌握此遊戲世界的意義。因而,貫穿於角色的意向性身體在世界中不斷搜尋可能的意義物,並在一次次互動中完成對遊戲世界的意義勾勒。
在如此一個意向性身體裡,角色開啟了對遊戲空間的深度開拓。上文中已提到,深度關係實際上指的是“動機-情境-決定”的一種動態、有機的相互關係。而在遊戲中,動機指向的就是角色的目光投向包含含混的意義的遊戲世界,而決定則指向角色的實際行動。與遊戲世界中任何一個物品的交互行為都有可能開啟一段新的空間與新的意義,這樣一種意向得以使玩家從遊戲開始便不斷開拓空間[18]並與空間緊密交織。角色也正式以如此意向的方式知覺世界的。
三、三個案例:《艾迪芬奇的記憶》中多元角色主體的感知復現
在《艾迪芬奇的記憶》中,“角色主體”並不僅僅是一個。玩家將化身芬奇家族中不同的成員,通過閱讀家宅中的筆記本,經歷每個成員的離奇死亡,從而揭開芬奇家族所經受的詛咒。因而,針對上一部分的第二個問題,本部分將通過遊戲中的三個案例呈現多元角色主體拓展出各自多元的“動機-情境-決定”的交互關係,從而達到對世界的感知。
不同的角色儘管享有相同的意向結構,然而由於各自所處的情境不同,其“動機-決定”的體現方式也各不相同。遊戲中圍繞著芬奇家族展開的多視角死亡經歷設計,使得角色主體的體驗變得豐富多元,不同角色身體出發的意向的定向各不相同,因而所經歷的空間深度的處境與意蘊也各不相同。由此,儘管遊戲中的角色都處於同一個客觀的遊戲空間,然而每一個“我”都通過各自的知覺、擁有各自的“世界”,而正是得益於這些各異的身體空間,一個擁有豐富意蘊的遊戲世界才真正得以塑成。
以下將通過具體分析遊戲中其中三位家族成員的死亡經歷,而探究多元角色主體是如何呈現多元的情境體驗、以及挖掘各自的空間深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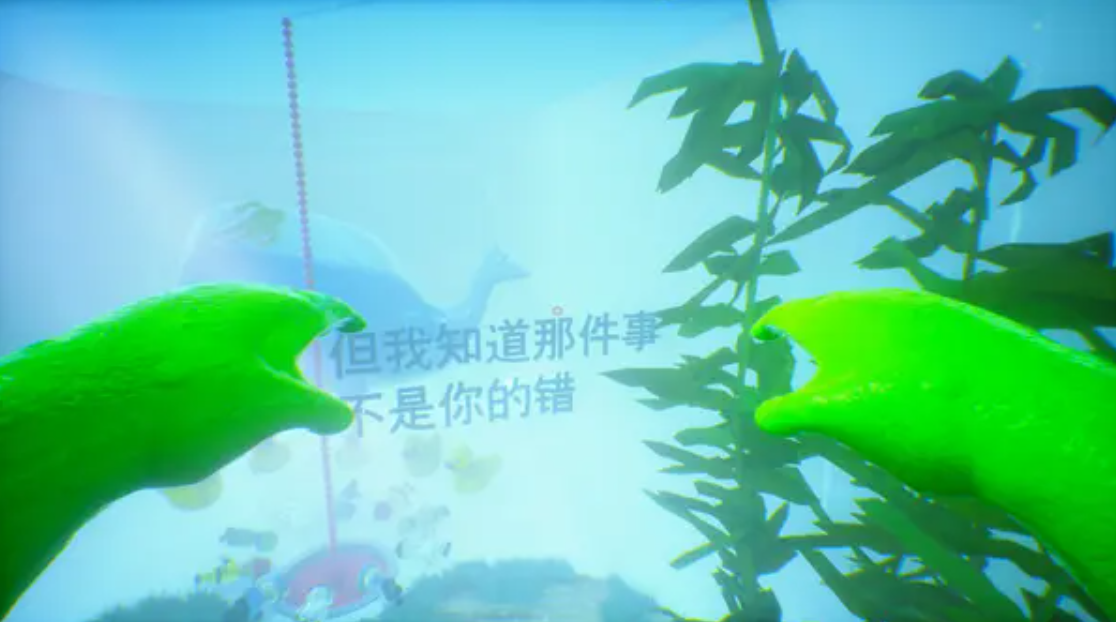
第一位是Gregory,他的死因是在浴缸中溺亡。從客觀描述出發的遊戲敘事如下:只有一歲大的Gregory在浴缸中邊洗澡邊玩著各種充氣橡膠玩具,他的母親將浴缸中的水放完了之後接到了丈夫打來的電話便離開了。然而Gregory自己卻打開了水龍頭,碰巧他的玩具正堵住了出水口,因而不幸溺亡。
可是,當這樣一種情形移位到Gregory的第一視角時卻發生了變化。與母親關注水位的高低以及孩子的安全不同,Gregory作為一個喜愛嬉戲、沒有自我保護意識的一歲嬰孩,他的全部意向性實則拋向的是浴缸中各種有趣的玩具。以“動機-情境-決定”進行分析,角色此時置身的“情境”並非充滿水的浴缸,而是充滿與自身作伴的動物玩具的小型水上樂園;角色“動機”並非洗乾淨身體,而是與樂園中各種動物相互玩耍的慾望;角色的“決定”也並非洗澡,而是與動物的互動,比如攪動水面使各種動物活動起來。
所以,在這一部分遊戲的伊始,角色被引導的交互行為就是與浴缸中的玩具鴨子、玩具鯨魚、玩具青蛙等各種玩具進行互動,並且這樣一種玩耍的意向持續到溺亡的那一刻。而遊戲中對於角色溺亡的誇張化視覺表現更是突出了此種意向性,在Gregory被淹沒在水中而尚有意識的時候,畫面轉而從浴缸變為了海底世界,而Gregory則化身先前他無比喜愛的青蛙玩具,不停朝著前方遊動,前方的鯨魚、鴨子等等動物共同圍繞著一箇中心跳舞旋轉[19],彷彿在舉行盛大的狂歡,而當Gregory最終加入它們時,眼前也隨之出現一片黑暗——Gregory終於失去了意識。


第二位是Lewis
,他的死因是濫用藥物產生幻象而被工廠的機器所傷而死。從客觀描述出發的遊戲敘事如下:Lewis在一家魚罐頭廠工作,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切魚頭、並將剩下的魚肉放上流水線的重複勞作。然而,痴迷幻想的Lewis並不滿足這樣乏味的工作,他開始在工作時幻想自己偉大而激動的冒險之旅,但是隨著藥物的濫用,他逐漸沉迷於自己的冒險幻想而無法自拔,最終當幻想世界完全侵佔現實世界時,他被切魚頭的機器所傷而亡。
同樣,在Lewis的視角中,他的意向並非單純指向完成切魚頭的工作,實際上可以說他在兩種處境中徘徊,一方面他置身於必須完成工作的處境,而另一方面他卻希望超越上述處境而創造一個嶄新的境域——也就是對冒險世界幻想的再現。因而,角色的“動機”也由逃離切魚頭的工作與進入冒險世界構成;相應地,角色的“決定”實際上體現為一邊切魚頭、一邊構思冒險世界的具體旅程。
遊戲對於如此相互交織而矛盾的意向性身體做出了非常富有表現力的設計。此時玩家扮演的角色Lewis需要通過兩種不同的操作行為而推動遊戲進展。一方面,玩家需要用右手點擊鼠標而完成現實層面切魚頭的工作;另一方面,玩家同時還需要用左手操控上下左右的行動方向鍵而展開幻想層面的冒險活動。兩種相互鬥爭的意向通過左右手的操控活動而得到展現,角色試圖平衡幻想與現實的活動正表現為玩家對左右手操控的協調努力。然而,隨著Lewis對藥物的濫用,遊戲起初的鬥爭性被幻想慢慢削弱,角色的幻想空間逐步吞噬了現實空間。直到了最後的關頭,玩家不再需要執行切魚頭的操作,而是將整個魚罐頭工廠幻視成他冒險終點抵達的勝利城堡,此時他正走上階梯準備接受王冠的授予,而當他彎下腰等待王冠的降臨時,降落的卻是切魚頭的機器——Lewis的生命因而在幻想的最高潮部分終結。


第三位是Barbara,她的死因是在家中被潛入的殺人魔所殺害。從客觀描述出發的遊戲敘事如下:Barbara小時候曾是恐怖電影的童星,以尖叫而出名,然而隨著長大後聲音的變化而過氣。在她16歲的生日當天由於父母外出,當地的殺人魔潛入家中,Barbara與其搏鬥而被殺害。
從Barbara出發的視角與上述二位不同,她具備清醒的自我防衛的意圖。她所處的緊張、恐怖的危險情境使她的動機與決定都圍繞著與殺人魔搏鬥展開,這看上去是一種常人在應對危及時共有的反應模式。然而,Barbara的童年經歷卻為這樣一個情境增添了更豐富的意蘊。在Barbara的敘述中,她唯一的願望就是被銘記——如同她童星時期因尖叫而聞名被別人銘記那樣,可是長大後的她再也發不出那樣驚恐的尖叫聲了。在這樣的背景下,Barbara此刻在現實中經歷恐怖殺人魔的場景與小時候參演恐怖電影的場景相交融,Barbara在與殺人魔搏鬥的過程中是否會回想起小時候出演恐怖電影的經歷呢?Barbara在因看到殺人魔而尖叫的那一刻是否會想起自己的願望呢?當Barbara完成了生命中最後一次出色的尖叫時,她又是否會為自己而感到驕傲呢?
童年時期的經歷以背景的方式盪漾在角色主體現身情境的周圍,角色以一種既驚悚恐怖又戲劇滑稽的怪誕情感經歷著死亡。一方面角色因為自己絕佳的尖叫而欣喜,另一方面這尖叫卻是來源於現實中的驚恐而非表演。此刻,也許連角色自身都不清楚自身的意向到底指向何處。
通過上述對Gregory、Lewis和Barbara三位家族成員的死亡經歷的復現,我們發現不同家庭成員的身體意向以及所置身的現象場各不相同,因而,他們從各自身體出發展開的遊戲空間也各有差異。這些空間在客觀描述中並無意義,可以說三者都是由於偶然原因而死亡的。然而,當我們把目光轉向不同角色自身經歷時,卻發現這死亡中帶有豐富的意蘊,經歷與死亡的關係並不是偶然與必然的範疇,而是相互包含的關係——死亡與角色的過去、身體和世界相互交織從而形成一個整體。而遊戲畫面將此種角色身體意向的連貫性與整體性很好地描繪了出來。喜歡玩玩具的嬰孩Gregory在溺亡時進入了水下樂園,熱衷於幻想冒險的切魚工Lewis將切魚機器幻視為授予王冠的桌臺而死,渴望得到銘記的過氣童星Barbara在被殺人魔殺害的時候也完成了自己的心願。
動機與決定、意義與意義的生效在不同角色面對死亡的處境時相互作用,而角色關於遊戲空間的深度感知也隨著意義的深入而得到開墾,深度就是這樣一種將含混的生活世界經驗彼此區分開來的手段。Gregory戲水、Lewis切魚以及Barbara尖叫,三種角色主體在當下某刻作出行動的同時,也將三個角色所置身的現象場勾連了出來。由此,角色並不與世界相對而是生活在世界之中。因而,遊戲角色也如此以各自的方式知覺世界。
綜上來看,梅洛-龐蒂關於“我擁有一個身體,我擁有一個世界”的表述依舊在遊戲中得以成立,這是因為梅洛-龐蒂的身體是意向性的身體,這樣的身體處於前認識的現象場與知覺場中,它勾連著客觀的空間認識以及意義化的空間。身體一方面在世界之中、被豐富的事物與歷史所圍繞,另一方面通過主動對空間進行開拓而使豐富卻又含混的意義變得明晰了起來。這樣二重性的身體在遊戲中則體現為遊戲角色身處的意義世界,以及遊戲角色在意義世界中的行動,這相互關係通過“動機-情境-決定”而得到顯露,而遊戲空間的深度也在此意義上得到挖掘。因而,儘管遊戲中的角色身體並不等同於現實的肉體身體,然而二者仍在意向性的層面享有相同的構造,遊戲世界中的角色主體依然通過意向的方式感受世界,而玩家進行遊戲的目的實際上也是完成對遊戲意義世界的填充。
[1] 這裡並不是想要把“現實”與“虛擬”對立,“虛擬”的用意是對應非自然生成意義上的人類主體。
[2] 張堯均. 《隱喻的身體—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研究》. 博士, 浙江大學, 2004.
[3] 張堯均. 《隱喻的身體—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研究》. 博士, 浙江大學, 2004.
[4] 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姜志輝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5] 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姜志輝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頁326
[6] 這兩位的實驗探究的都是身體“有能力”迅速將倒置和傾斜的視像擺正的問題。
[7] 李貫峰. 《深度視覺理論演進及梅洛-龐蒂的本體論讀解》. 社會科學論壇, 期 5 (2017年): 98–110.
[8] 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楊大春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頁357
[9] 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楊大春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
[10] 馬元龍.《身體空間與生活空間——梅洛-龐蒂論身體與空間》.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33, 期1 (2019年): 141–52.
[11] 或者說牛頓代表的這種自然科學式的空間是建基在此種意向性的身體空間之上的。
[12] 李貫峰. 《深度視覺理論演進及梅洛-龐蒂的本體論讀解》. 社會科學論壇, 期 5 (2017年): 98–110.
[13] 吳娛.《“從我到事物”的現象學距離——梅洛—龐蒂早期現象學中的空間進深問題》. 外國哲學, 期1 (2022年): 171–94.
[14] 莫里斯·梅洛-龐蒂.《可見的與不可見的》,羅國翔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頁277
[15] 例如藍江老師在論文《寧芙化身體與異託邦: 電子遊戲世代的存在哲學》中就採用以玩家主體為中心的視角,在這種視角下他將角色主體描述為寧芙化身體,而以玩家主體出發的世界也轉變為“多個”世界而非梅洛-龐蒂的“一個世界”。與此相反,本文從角色主體出發的論述依然遵循“一個世界”的原則。
[16] 《艾迪芬奇的記憶》的核心玩法可以被稱作步行模擬器,玩家通過操控第一人稱角色自由移動,通過接觸物體、與對象進行交互或是到達位置來解鎖劇情。然而因其缺乏遊戲性而受到詬病,這裡的遊戲性與故事性相對,指向偏操控交互方面的技術性,二者共屬於傳統電子遊戲研究的一個基本範疇。
[17] 遊戲中事件的主要發生地都集中在一棟四層的家宅中,因而現象場實際上主要體現在家宅中。
[18] 遊戲中的關卡設置良好體現了這一點,玩家隨著關卡的深入而能探索越來越多的空間,其中很多空間在此前都是被禁止物理進入的。
[19] 這裡其實是對玩具堵住浴缸的出水口的戲劇化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