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为“信睿电台”播客节目,经授权发布。
前言
如果说元宇宙的最终形态还飘渺无依,游戏却是一个我们能用来想象元宇宙的有效参照。在本期节目中,华东师范大学张笑宇老师和北京师范大学刘梦霏老师正是从游戏与游戏的发展历史切入,探讨了真实与虚拟、娱乐与创造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试图回答一个关于元宇宙最根本的问题:在资本的狂欢之外,每个“普通人”最有可能借由元宇宙实现何种价值?
共同想象与共同创造
刘梦霏:元宇宙这个概念,当然是最近资方炒的很热的一个概念,里面不可避免地充满了水分。“元宇宙”这个词,我一直感觉给人的印象非常不好,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唯一的霸权。它的“元”字是基本的“元”,然后又和起源的“源”同音,所以就让你觉得它是唯一的一个重要的宇宙。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看《雪崩》那本小说,它里面提到metaverse的时候,它并没有翻译成“元宇宙”。在里面metaverse是作为“超元域”提出来的,我觉得“超元域”这概念挺好,它既符合“meta”又符合“verse”。
![雪崩 [美] 尼尔·斯蒂芬森 / 著 郭泽 / 译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https://image.gcores.com/7599da48-a210-4af4-91ac-dd37ea898d1b.jpg)
雪崩 [美] 尼尔·斯蒂芬森 / 著 郭泽 / 译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雪崩》这本小说,它的核心其实是语言,它在说的其实是语言和信息的魔力。因为“verse”单独的含义,本身就是“诗句”,所以“metaverse”从一开始“超元域”的定义,其实就和语言有关。它里面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讨论各种不同的语言,包括巴别塔会出现,是因为它是最初人类语言开始分歧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
如果元宇宙的核心是语言和信息的魔力的话,所有这些文学作品、神话传说,它们创造的平行世界可能就很重要。这种语言创造的平行空间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切入点,这样的平行空间本身在文学里面存在,在电影里也存在,在游戏里理所当然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能够让我们可能看到元宇宙的一些更具创造性的、更具文化性的方向。
张笑宇:对,因为“meta”这个词在希腊语里最早的意思就是“在后边”,我们翻译“metaphysics”为“形而上学”,其实是说“在physics后边的那篇文章的讲义”。亚里士多德在写metaphysics的时候,其实想说“这课是放在物理学后边上的”。“meta”原意是这样子,结果我们把它翻译成了一个“元”,但是“元”的东西真的是“verse”这个空间吗?
不一定。“元”的东西其实是规则,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则。比如说所有写创造小说、想象小说、穿越小说之类的,把我放在另外一个世界,世界可以不一样,但是语言必须相通。语言相通的背后藏着对人类的一种预设:比如说我作为人,我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我还是有一些不变的人性——我会爱上某个人,我会因为某件事勇敢,我会坚持某种理念。这种事情既可以在地球上发生,也可以在外太空发生,也可以在古代,也可以在一个不同的宇宙发生。这才是多重世界特别有魔力的一种东西,每次讨论元宇宙我都很难控制地想到一句话,这句话是其实咱们也会涉及到的话题,就是《龙与地下城》。
刘梦霏:《龙与地下城》是一个我觉得在中国一直有点被低估的、非常小众的“元游戏”。《龙与地下城》其实特别独特,就它的性质来说,它算一个桌面游戏。大概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西方出版了一整套“规则书”,是为了方便玩家组成小队,在桌面玩的。这整套“规则书”叫做《龙与地下城》,它其实就是一个异世界的构建规则。在整套的规则里,会有一个人扮演地下城主,ta来写剧本,ta来安排地下城的各种情况,另外还会有很多玩家,ta们需要按照“规则书”来制作自己的人物卡,并且通过掷骰子、说服地下城主,来推进地下城主写的剧情。有意思的是,玩家在这里面不是一个被动的,比如说看小说、看电影的这种角色,玩家是一个特别主动的、有机的角色,它要和地下城主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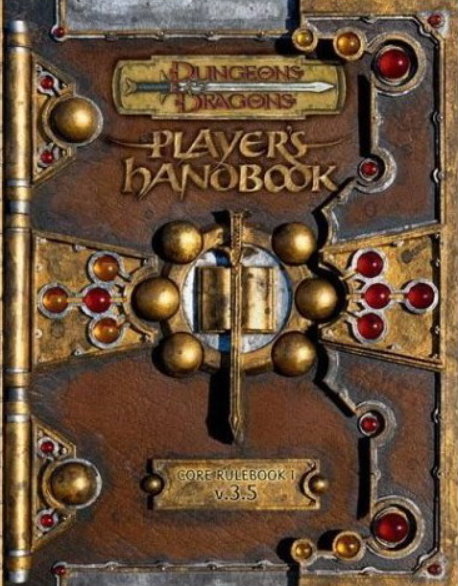
龙与地下城玩家手册 Wizards of the Coast / 著 奇幻修士会 / 译 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 2002
张笑宇:是共同创造,共同去想象,彼此对这个想象世界有认可。
刘梦霏:而且这里有角色扮演的快乐和释放自我的快乐,就是你扮演和现实生活中不同的自己,这其实是一种和狂欢节有点类似的快乐。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空间,所以我们在这个空间里既可以自由释放天性,也可以破坏。这有点像中世纪的狂欢节,大家戴上面具,狂呼乱叫,做一点正常生活里可能不会去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它的魅力之一。我前面说它很独特,而且它是“元游戏”,还有一个原因是它是有生成性的那类游戏,就是玩D&D的过程,我们管它叫“跑团”。有一些故事,有一些非常好的奇幻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桌面游戏里诞生的。
张笑宇:是的。在《头号玩家》那个世界,你是一个全盘接受的规则的,但是真正的元宇宙,你是在书写自己的故事,你是在主动参与到一个一个新的现象,这就要回到我刚才想说崔斯特那句话——我特别喜欢的那句话——“我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龙的世界”。因为一个没有龙的世界,没有魔法世界,就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世界,一个没有让你激动的东西,让你兴奋得让你觉得可以为它去放弃现实中很多东西的世界。
我不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所以元宇宙的核心在于想象力,而《龙与地下城》这个规则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它给你创造一条基本的逻辑,你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生发出无限的想象力。
游戏的社会功能
张笑宇:既然聊到了咱们这个时代怎么看待游戏,实际上我认为游戏在今天已经成为技术进步、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驱动力。我在《技术与文明》里总结了一个东西,到我第二本书里会明确突出。就是咱们仔细想一下:历史上的技术进步,真的是科学家发明的那个东西最重要吗?

技术与文明 张笑宇 / 著 一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不一定的,可能很多大科学家的发明都被人遗忘掉了。他在那个时代发明出来了,却根本没有起到作用——99%的发明可能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所有实验室里的发明和技术,都需要经过一个“漏斗”的考验,“漏斗”的名字叫做商业化或者产业化。而商业化的前提是什么?是需求。实际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这样的,先有需求,然后找到了技术,技术通过了“漏斗”的考验之后,它就是一个“喇叭”效应,它会迸发出我们原先压根想象不到的巨大的影响力和震撼力。
到了今天刘老师讲的时间节点,不论是《龙与地下城》的规则也好,电子游戏的兴起也好,是20世纪70年代。为什么是20世纪70年代?其实这跟另外一个现象有关系,就是技术进一步的自动化。技术越自动化,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从机器制造业抛弃,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之后,他会去干什么?其实他的消费娱乐,尤其是娱乐本身,会变成新的需求。
就像我们看到奥运会、足球这些产业有这么大发展,游戏也是在其中的。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处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之间的年代。我们过去对社会前进的理解是你不断地去工作,不断地创造新商品。但是今天其实是你不断地发掘新需求,这个需求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前进。
我可以在游戏行业里直接找到例子,我们都很熟悉一个公司叫NVIDIA。NVIDIA是做显卡的,它一开始就是为了游戏做显卡。到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叫吴恩达。吴恩达发现用NVIDIA生产的GPU,可以把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算法效率提升100倍,然后才有了人工智能大爆炸。如果没有游戏行业的巨大需求,NVIDIA就做不出来这么好的GPU,就不会有今天的人工智能进步。
刘梦霏:好多时候,我觉得确实有一些底层的基础的事情是被忽略了。刚才张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其实也一直在反思。游戏行业,我们哪怕不说它创造的技术进步,就说现在中国玩家已经6个多亿了。像Switch其实很多普通家庭都有,因为它有《健身环大冒险》之类的这样的“出圈”的游戏。我觉得游戏在人口当中的流行,和它的文化地位是不成正比的。我以前一直觉得游戏是大众文化,但是实际的文化地位上,它是个亚文化。
要让游戏从亚文化变成大众文化,首先肯定是需要知识阶级持续的努力和关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录这样的播客。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像社会实验也是必要的,因为它会有一个展示的场所(showcase),它会让你看到,游戏是可以和更严肃、甚至没有想到可以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的。
张笑宇:其实这种结合已经发生很多了,比如说像我们都知道一款特别有名的游戏叫《魔兽世界》,《魔兽世界》之前爆发过一个事件,就是游戏里边有一个怪物的技能是会释放毒,这个毒是会传染的,有一次毒就被一个玩家带到城市里边,然后城市里边就大量死人。这个事情被传染病学家知道了,发现它跟现实中的传染病模型是非常相近的,所以他们就去管暴雪要到了模型,然后就发了好多关于传染病研究的文章。
还有一个游戏我自己很喜欢,叫《都市:天际线》。它是模拟一个城市进行管理,它已经可以模拟到这个城市里面几十万的居民,沿着自己居住、工作、消费的路线前进。很多城市规划设计师已经在通过这个游戏来训练自己现实中的技能。

《都市:天际线》游戏图景,图源Steam官网
我们未来很可能对很多重大议题的处理,是要从游戏中找借鉴的。我们很多方案进入现实之前,我们可能在游戏里边先试一遍,这样做比较人道。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游戏作为当今时代的“漏斗”的意义,我觉得真是越来越凸显、越来越重要。
刘梦霏:坦白地说,其实所有的游戏体系都是教育体系,它一定要教你上手对吧?然后你要逐步精进,再在游戏里主动地做一些别的创造。
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游戏应当是一种通用语言(universal language)——我们觉得每一个人应该都可以是玩家——不管他以前接没接触过电子游戏。那么是不是每个人也都可以是游戏的创造者?它其实又扣回了我们最开始在说元宇宙:它不是一个消费性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带着你走的东西,它是一个需要你来主动行动的一套行动的规则。
张笑宇:刚才谈及游戏和教育的问题,仔细想一想,教育是什么?很多人一想到教育,觉得是一个“爹味”很重的概念,就是我必须教你怎么干,孩子才能怎么干。但是本质上教育不是这个样子的,教育是让一个人的灵魂得到提升的过程。那么游戏的过程中提升的是啥呢?这个是值得我们业界去讨论的问题。监管永远只能从负面角度去走的,因为他不知道所谓的正向是怎么走,而一个真正的正向的路怎么走,永远只能从这个行业里边诞生。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后边咱们游戏产业,包括对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就又回到我之前聊过的一个比较大的视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技术进步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代,自动化机器人这些东西都是大规模展开的。
其实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经历了一波了,而我们是正在经历。中国现在是机器人技术普及最快的一个国家。这个状况下,社会本身就是会受到重大冲击的,一定会有大量的人从第二产业移到第三产业。所以我们会看到比如说现在直播特别流行,有大量的青年是在短视频这个行业里去就业。我们说的“泛娱乐”行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虚拟世界的需求、超越现实世界的需求,成为主导推动力的第一步。
短视频本质上还是一个被动接受的东西,他给你拍什么东西你就看,那么有没有可能第二步是你开始主动创造,通过游戏的方式主动创造。你自己做一个游戏,经济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你做出了游戏给别人提供了快乐,快乐是值得为此付钱的,就像我们喜欢看喜剧,然后花钱花钱买电影票一样,那么你从中得到了回报,然后你再反过去回报别人,这是一个可以持续运作的经济系统,从中可能生发出未来社会前进的很多可能性,硬件的、软件的、算法的、系统的,这都是有可能的。
何为“游戏素养”?
刘梦霏:我之前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按照付费模式来区分了一下现在的游戏。一次性付费,没有后续消费的这种,不管它是在什么平台上的,我管它叫作品游戏,其实也可以叫作者游戏。
它更接近一个作者创作的逻辑,就是我游戏拿出来卖,然后你们玩家买了,我创作者能收到钱,我就有更多的动力去改善后续。像《刺客信条》、《勇者斗恶龙》,他们才能形成一个系列。但是这种逻辑在国内并不是最赚钱或者最流行的。游戏产业每年2000多个亿的产值,作品游戏的贡献微乎其微。这2000多个亿的产值主要来自于被我定义的另外两类游戏。

《刺客信条》游戏海报,图源网络
另一类叫做消费游戏,其实就是那种就是免费下载、道具付费的游戏。为什么叫消费游戏?因为它的核心的经济体系是一套消费系统,游戏主题没有那么重要。当然消费游戏做得好的话,它至少还有一些公平性,它允许你靠技巧取胜,但是这仍然不能改变你下载游戏、你玩游戏开发者收不到钱,只有你开始消费的时候开发者才能收到钱这个事实。
所以我们要从马克思的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游戏的核心就是他的那套消费体系,就是那种给你创造痛苦和不便,然后你花钱来消除痛苦和不便的这种这种思路。这种游戏它肯定是赚钱的,而且我也不觉得它邪恶,我觉得只要你维持好这个功能性,对它的商业它是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但是你不能只有这种游戏。
第三类游戏被我定义成赌博游戏,我觉得这一类游戏它真的是暴利,因为这种游戏的核心它其实算是消费游戏的一个子类,因为对它一定是免费下载的,但是它的游戏的核心它是不允许你靠技巧取胜的,它的核心体系就是是围绕着抽卡、氪金的开箱的机制来的。
赌博类的游戏我觉得仍然是行业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毒瘤,因为它真的是瞄着人性的弱点来的。你如果说像《王者荣耀》这样的游戏,它至少是公平的,它也许你靠技巧取胜的话,赌博游戏的核心是天意,是几率(chance)。我后来甚至认为玩这种游戏的可能都不完全是玩家,我后来开始说完消费游戏的是消费者,玩赌博游戏的是赌徒。
我们同样讨论青少年保护的问题,很多青少年他不知道游戏分作品游戏、消费游戏和赌博游戏,他看起来这是一个无害的手游,手游可能有也宣称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开放世界,然后在里面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游戏世界的核心其实是围绕着这个孩子所不能控制的几率来的。而且在游戏里面消费的货币往往不是现实中的人民币。你看你去赌场,赌场也要你换筹码,因为在心理学上,你花筹码和你花真钱,你的心理状态就是不一样的,他就是要创造一个中介物,你花筹码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
在青少年在没有形成对于钱的认识的时候,就开始这样花这种虚拟货币,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我们知道就可能有一些围绕着游戏的负面的、让我们自己也觉得很痛心的社会新闻,孩子在游戏里面里面充值太多,就跳楼了之类的这种这些新闻,后来我去细看他们那里面的游戏,全是赌博游戏,所以这是我觉得真的应该重拳出击的。
张笑宇:在今天这个年代,最大的阶层固化就是认知固化。实际上游戏是一个必然客观存在的,存在于本性和文明需求中的一个东西,你不可能把它抹消掉。当你不可能把它抹消的情况下,你从认知上怎么跟它共存,甚至怎么对待它,就成了最重要的问题。就像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移动智能的时代,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你不会手机你是跟世界无法交流的,所以在未来元宇宙这个时代,如果你不懂游戏逻辑是怎样的,你可能是跟这个世界完全无法融入的。因为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你如果从小没有玩过游戏,你反而会被赌博类游戏和消费的游戏去俘虏。
刘梦霏:我觉得重要的,其实真的是有非常多游戏研究的成果是能够帮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游戏研究其实不是关于怎么设计游戏的研究,游戏研究是关于“游戏的人”的研究,关注的其实是游戏的本质是什么,玩家到底是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在游戏里行动的。
特别是针对这些可能将来会受困于游戏素养过低,由于游戏素养过低而变成一个阶层壁垒,这个事是我们特别不愿意看到的。我们都可以回看一下《头号玩家》里的世界,《头号玩家》的男主角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游戏的。他游戏的时候用VR头盔包住双眼,这样他就不用看到他周围窄小的环境——一个典型的贫民窟;101的那些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游戏的,他们那些真的游戏创造者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下游戏的?
它展现了最坏的现实。如果我们不加强游戏素养的教育,如果我们不让新一代最需要了解游戏是什么的人,去了解游戏真正是什么,我们得到的就是《头号玩家》。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绝对没有任何可能竞争过大资本控制下的101公司,这肯定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未来,就是这种人完全被游戏消费的未来,我觉得是非常糟糕的,也是我们不应该让它发生的。
更多内容会发布在“信睿周报”公众号,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