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啼书
悠游居,纷杂市井间的一处游戏旅店,欢迎入榻。
本贴为《地铁:离去》前作《地铁:2033重置版》Steam版游骑兵模式游玩下的延伸思考与评测,不含剧透,请放心食用。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提起远据北方的那个民族,我的脑中都会下意识地响起《红色警戒三》中的那首《苏维埃进行曲(Soviet March)》,仿佛身着红色大衣的动员兵正在我耳旁大声呐喊着:
Наш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карает
我们的苏维埃将惩戒全世界
Весь мир от Европы к Неве на восто-ок
从欧洲直抵涅瓦河向东
Над землей везде будут петь:
大地上随处都将唱响:
Сто****, водка, Советский медведь наш!
首都,伏特加,我们的苏维埃巨熊!

当那时的我很容易忽视一个事实:这首歌的填词和作曲,都是美国人——而《苏维埃进行曲》与其说是一首颂歌,不如说是刻板印象的夸大与输出。
但在逐渐走入这个民族的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我开始改观与思索:当我们谈起斯拉夫民族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地铁:2033》,算是种种作品中,最让人印象深刻且震撼的一位。
当我们谈起“废土美学”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地铁》系列的故事,发生在架空的近未来世界:人类文明被战争投下的核弹摧毁殆尽,只留极少部分人逃入地铁之中苟延残喘。
这种题材,在科幻之中被称之为“废土”,虽在相当程度由《辐射》系列为人所知。但事实上,早在1968年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甚至更早之前,对核战后世界的构建就已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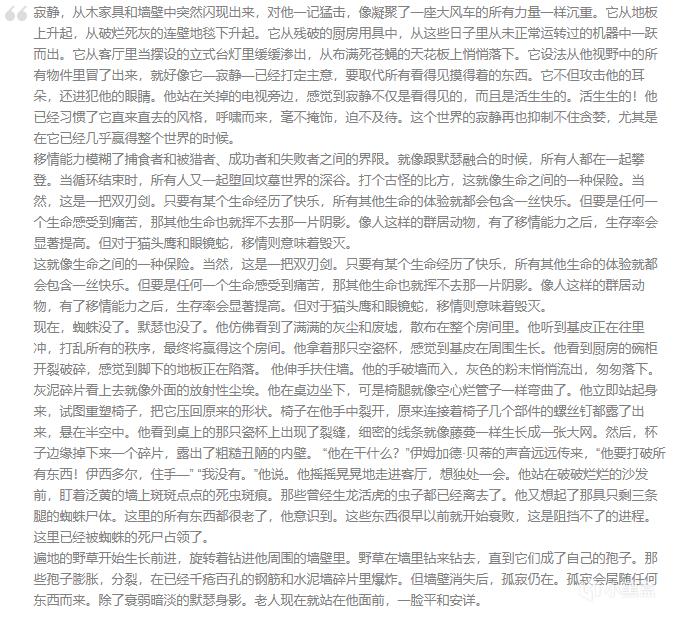
大家可以通过摘抄的文字感受一下《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对于废土题材的理解。
而《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还有一个更为大众所熟知的名字:1982年的电影《银翼杀手》,是近年来大热概念“赛博朋克”各种意义上的鼻祖。而导演老雷之所以没有选择改编原作小说的废土部分,我认为是出于视觉风格上的考量:彼时1988年的
 在取舍之下,老雷奠定了赛博朋克的美学。幸运的是,你可以在《银翼杀手2049》中看到对原作废土部分的视觉呈现。
在取舍之下,老雷奠定了赛博朋克的美学。幸运的是,你可以在《银翼杀手2049》中看到对原作废土部分的视觉呈现。
为什么《辐射》将废土概念发扬光大?为什么老雷要割舍原作的废土部分?
这两个问题都导向了一个答案:因为废土题材作品的视觉呈现太重要了,它几乎直接左右了这一题材作品对受众的吸引力。
 私以为,这也是《辐射》系列为何能将废土概念推广开来的原因。
私以为,这也是《辐射》系列为何能将废土概念推广开来的原因。
在这种语境下,影视和游戏,成了废土大展手脚的头号阵地。
《地铁:2033》对于废土世界的美学构架,是其最让人惊叹的部分。
游戏开场,你以主角阿尔乔姆的双目看到的这个世界的第一眼,便是地铁中的房间。
 地铁中极为有限的“私人空间”。
地铁中极为有限的“私人空间”。
拥挤,阴暗,浮尘携着辨认不出的怪味在吝啬的光线中起舞,人在尊严在有限的地铁空间内被挤压到最小以至于变形——在第一人称中中,沉浸感与画面细节被放到了最大。
有限的光线和泛黄的色调,构成了玩家双眼之中,对地铁世界的初印象。

但这只是4A对于废土构架的第一步——第一人称下破败文明的苟延残喘,极尽难堪与衰败。
4A的下一步,就是对之前构建世界的打破与逆反,让玩家亲眼见证地铁外的世界。
当玩家戴上防毒面罩,走入那个无法再接纳人类的地面世界时,他们最先看到的......
 大街上的雪不再有专人扫除开来,肆意堆积着。
大街上的雪不再有专人扫除开来,肆意堆积着。
是扎眼的光和洁白的雪,填满了眼。
玩家对于地铁世界的直观印象,在相对立世界的视觉对撞中,被构建起来了。

玩家可能读不懂晦涩的对白,可能无法理解高深的表达,但他们定然看得懂:这断壁残垣上覆盖的厚厚白雪下,是藏污纳垢的拥挤地铁。
对于核后废土的视觉呈现,便是《地铁:2033》的窗户,在带来震撼的同时,将玩家带入游戏背后的思索与表达。
当我们谈起“选择取向”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谈起《地铁》系列到底有怎样的表达和思索,就难以绕过其三部曲一脉相承的核心机制:道德点。
当你在游戏的流程中作出选择时,游戏会根据其正负向进行判定,从而左右你的结局——这与同样大名鼎鼎的第一人称类型游戏《耻辱》的“混乱值”相似,被称之为选择取向。
 你永远不知道游戏接下来会记录你的哪个决定。
你永远不知道游戏接下来会记录你的哪个决定。
但与“混沌值”不同的是,“道德点”更具不确定性,除了击倒和击杀外,你的每个选择可能都会引发眼前的闪过白光或是失去色彩:路边小孩的乞讨,队友的生死,甚至于路边的对话。
“一路圣母便可以抵达好结局”——这是相当一部分玩家对于道德点设计的评价。但仅仅“圣母”二字便可以囊括这个机制的设计和表达?
我不这样认为。
在国内的科幻界,有一场“吃人对话”常常被提起,对话的其中一方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之首任系主任的江晓原,另一方是曾写出“圣母程心”的刘慈欣。
2007年,在成都的白夜酒吧,刘慈欣和上海交大的“科学史”教授江晓原有过一场关于“吃人”的辩论。当时刘慈欣假设,如果世界末日,只剩下他、江晓原和现场一位主持人美女,“我们三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我们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吃吗?”
江晓原说他肯定不会吃。
刘慈欣强调,可是全部文明都集中在我们手上。“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不吃的话,这些文明就要随着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举动完全湮灭了。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们都消失了,一片黑暗,这当中没有人性不人性。只有现在选择不人性,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
江晓原说:“如果我们吃了她,就丢失了人性,一个丢失了人性的人类,就已经自绝于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
很显然,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刘慈欣后来说,之所以自己的作品受欢迎,“正因为我表现出一种冷酷但又是冷静的理性。而这种理性是合理的。你选择的是人性,我选择的是生存,而读者认同了我的这种选择。”他套用康德的一句话: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
在玩家作出选择之前,游戏就已经奠下了地铁世界的语境:一场人类的自我毁灭,附加着对环境的破坏而主角阿尔乔姆作为在被毁灭的地铁文明中成长的人类中坚力量,他是人类的希望还是赎罪者?
在道德点机制下,这个问题被具象化的同时,这两个身份被逐渐模糊了。

随着游戏逐渐深入,玩家看到的越来越多,地铁世界的全貌被逐渐揭开:赤军和纳粹在铁路上疯狂地交火,断壁残垣中变异生物成群地迁徙,不可见的黑怪张开双臂......
于此相对的,是越发沉默寡言的阿尔乔姆,他的步履越发缓慢,肩上的担子越发沉重——那是两个世界的命运。

在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我们是否要将最后象征着文明的人性丢弃于地?
科幻的本质是反思,道德点将这番表达烙印在了机制和游戏性之上,在“地铁”的暗处凝视着玩家的言行举止。
如此一来,当我们在“地铁”漫步时,便知道该谨言慎行,轻声讨论了。
当我们谈起民族性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当我们在“地铁”漫步时,我们在轻声讨论什么?我很难给出答案,但我想能从可汗的话语中窥见一二:
“我们创造的核弹,摧毁了天堂,摧毁了人间,甚至摧毁了炼狱,那些无处可去的灵魂,只能游荡在地铁里了。”
我从可汗和他的话语中看见的,是整个民族的剪影——他们英勇的脊梁里,多少藏着些多愁善感,如同地铁中随处可见的,露管枪旁的旧吉他。
 几乎每个地铁站都能看到的吉他。
几乎每个地铁站都能看到的吉他。
这种混合着信仰与忧伤的科技反思,被具象化成了游戏中的黑怪,串起了整个游戏的故事走向。它混杂着未知与畏惧,催促着阿尔乔姆和玩家趟入混乱的地铁世界。
 “游骑兵”在地面上的最后据点是一座教堂。
“游骑兵”在地面上的最后据点是一座教堂。
这种掺着哀愁的反思不止于《地铁》系列,也不局限于科技层面。
“我们创造的核弹,摧毁了天堂,摧毁了人间,甚至摧毁了炼狱,那些无处可去的灵魂,只能游荡在地铁里了。”
在游戏之后,我寻觅了很久游戏中错过的这句对话。最后,在命运石之门的选择下,我居然在贴吧对于《秘密战争》的讨论里看到了别人的引用。
这部《爱,死亡与机器人》中的剧集,同样将镜头对准这个民族,讲述了一个赎罪的故事:
为了战争和政治触犯神秘学的禁忌而被惩罚的土地上,揭示真相的士兵英勇赴死。
 不止于科技,还有对历史,社会和政治的反思。
不止于科技,还有对历史,社会和政治的反思。
而在绝望的重压之下,他们也同样选择拿起乐器,在微弱的灯火前弹奏起来——曲调并不欣然,也不至于哀婉,只是为重伤的弥留者而奏。

在波波沙和伏特加的刻板印象之下,他们是复杂而多面的。面对未知的敌人会畏惧,会在生死的闲暇之间以音乐排忧,会在战前于教堂间徘徊,会在抉择之前矛盾而痛苦......
而《地铁:2033》所做的,就是以沉浸感的第一人称将玩家代入其中,让玩家与阿尔乔姆在面罩下一齐呼吸的同时,一齐看遍夹缝中民族与人类的喜怒哀乐。
这是《地铁:2033》最为珍贵的部分,也是它不可替代的原因:它用游戏工业与特性呈现了自己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