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後的感受
北京時間6月23日凌晨0點,我終於結束了跨時差參加的、本週正在西班牙塞爾維亞舉辦的DiGRA2023年會中我的演講部分。DiGRA的全稱是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遊戲研究協會),是遊戲科研屆極具權威的會議之一,集結了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其總會每年舉辦一,於是今年的年會,也被稱作是DiGRA23。
雖然我遇到了遠程參加必不可少的網絡技術問題,但所幸的是,一切都在慌亂之中順利解決。我也按照自己計劃的那樣,沉著自信地完成了演講。我已經把我準備的東西演示地很好了,所以我要給自己鼓掌!之後的extended abstract(拓展版大綱)在網絡端 ACM Digital Library 也會有發佈,有版權保護,所以我想,在中文社群上提到這一內容,問題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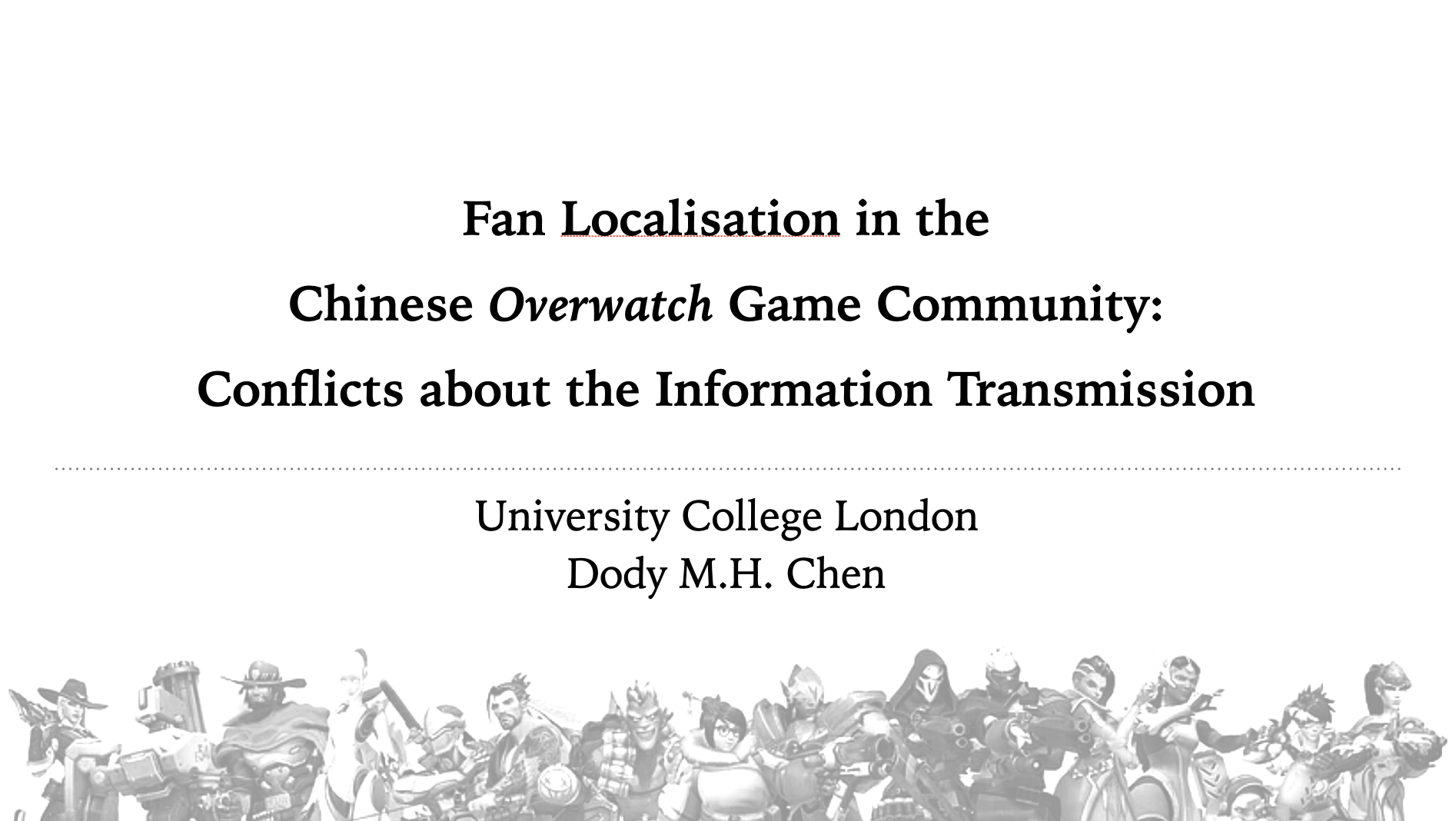
粉絲本地化:中國鬥陣特攻社群中與社群矛盾相關的信息傳遞
一晃眼,已經2023年了,誰知道鬥陣特攻2023年國服都沒了,成都獵人隊也下線了,很多我喜歡的選手也都退役了。從2020年和老師說,“我想要把鬥陣特攻作為我的碩士畢業論文課題”,一路走到今日。在夜深人靜時,我幼稚著想著這些“如果”,和我科研中一條條人跡罕至的路。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黃色的樹林裡分出兩條路,可惜我不能同時去涉足。
有時候我真的好像一個反覆咀嚼別人剩下的美食的小孩,還一直在“殘羹冷炙”中回味著什麼。當然,我也有在吃其它一些“菜”。只不過,這些境遇的反差和我參加會議時的片段,一直在腦海裡來回穿梭,有點亂。我的性格又讓我不斷反思自己,總覺得自己表現得不夠好:
一方面,是因為,我面對的是各個國家的學者,大概沒有人比我更瞭解這個課題了——我想努力展示出來。
另一方面,又因為,這是《鬥陣特攻》啊。
DiGRA23: 參會流程
DiGRA23的主題是“Limits and Margins of Games”,遊戲的限制與邊界。會議於2023年6月19日至23日在西班牙塞爾維亞舉行。會議採用了線上線下結合的模式。會前徵稿啟示與相關時間節點,在官方推特和官網都可以查詢到。
參加DiGRA的進程非常直觀,每一步我記錄在此。如果想要以presenter(演講者)的身份參加,需要投稿自己的proposal並被審核。之後進行官網註冊,選擇參會方式,並得到確認信息。收到會議大綱之後,可以查看分區選擇。同期,課題的內容可以進行修改。需要在給出的期限前準備好camera-ready version(預發表版)的文件,以及演講PPT。
所投稿的proposal,並不僅僅與full paper(論文全文),或者是extended abstract(拓展大綱)有關。會議除了對於論文或者拓展大綱分出的talk(演講),還有給成熟研究者、或者遊戲行業相關人士分享內容的panel(講座),進行培訓的workshop(工坊),又或者是給PhD在讀生們提供聯繫和分享機會的PhD Consortium(博士生研討會)。可以說,各種門類,都是給與遊戲相關的不同研究門類的一個極好的交流平臺。
這些申請的步驟對於老練的研究者來說,也許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但對於我這種early-stage researcher(早期研究者)來說,每一步,都是一個未知且充滿挑戰的狀態。在此之前,我並沒有很多國際大會的參與經驗,所以去嘗試,以及記錄下這些信息,也是一種有益的反思。
一直以來我都想要去參加和遊戲相關的會議,而不僅僅是和翻譯相關的翻譯。誠然,這兩個話題在我心中的地位是沒有先後之分的。但跳脫出我較為熟悉且更為安全牌的翻譯類別會議,我對遊戲會議的期盼,大概從我去年所寫的 遊戲研究會議之FDG聽會小結 中大概也可以映射一二。去年的FDG會議我並沒有作品參加,只是作為旁聽者跟了大部分喜好的演講,心中對展示課題這件事十分羨慕。今年我帶著題目考慮參加會議,因為時間安排、參會限制以及23年初轉學事項帶來的影響,我放棄了今年已經入選的翻譯與媒體研究頂會之一Media4All23,決定還是全力準備允許網絡參與的DiGRA23。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雖然在這兩條小路上,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跡。 雖然那天清晨落葉滿地,兩條路都未經腳印汙染。
我的博二感悟:致早期研究者生涯
很多像我一樣的早期研究者無法擺脫的困境之一,即為不知道如何去獲得前人的經驗;即便獲得了,也不知道該去利用、去實踐這些經驗。可以說,我在博士生階段的前兩年,乃至於如今的第三年初,也一直陷在這種困境裡。
人不是一直能保持衝勁。每每我看到網絡上的call for paper(各類會議、期刊的徵稿啟事),我都有一種頗為窒息的錯覺。這種腎上腺素的飆升,從打開徵稿頁面,閱讀相關信息開始,會一直蔓延,直到認清現實的那一刻。
——“我可以的,去試試。”
與此同時,一種我不配的態度也會同時佔據的我腦海。“我是誰”,“我只是一個‘學生’”,“我寫的東西真的有價值嗎?”。尤其當我翻看某些會議,徵稿往年的參與者的各類稱號時,或者當我看到自己的社交媒體底下一些不和諧的聲音時,這種不配感會隨著具象化而愈發嚴重。
但去逃避這種想要擁有的狀態,去糾結,去掙扎,實則並不會有什麼良性的收益。最近有一則很火的致非母語海外研究生的post,在推特上熱傳。
“每天我都對國際學生充滿敬畏。在你的祖國以母語攻讀博士學位很難。用非母語在不同的國家及文化中攻讀博士學位,要困難得多。”

有趣的是,很多時候,鼓勵到我的力量,似乎都來自於我自己而不是外界。這是一種和自己和解的方法。所以,我大概記錄下至今為止的有用的思路。這些曾經是、將來也會繼續是,我一直反覆考慮且糾結的話題。這些信念的堅定與否,大概會一直伴隨著我走過的道路。
- 不要自怨自艾,相信自己是最瞭解課題的人,更要相信自己擁有科研之外的閃光點。 有時候人很容易陷入一個自己懷疑的境地,適當停下來放空或者放慢思考,可以幫助理清問題的思路。不同學科之間的差異很大,不要因為網絡上的人對自己學科的不瞭解,甚至是沒有來由的攻擊,而陷入自責和沮喪。我做我的,別人愛咋咋地。 在我之前一篇 論文發表 的最初階段,我收到了一鬨而入的評價,有好有壞。其中令我的難過的評價,莫不是將這篇東西的價值與自己本科所“糊弄的水文”混為一談,且把因“工作”與我的交談,當作NGA社群中的談資。這種困惑的行為,讓我意識到,即便是在自己所熱愛的研究領域,仍需要對自己進行充分的保護。 但人的一生並不僅僅是為了科研/學習而生的,如果一直把自己禁錮在一個角色之中,就會在其它的場合無所適從。所以,對我幫助很大的解壓方式,就是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或是打遊戲,或是寫文章,或是出去喝咖啡看看風景。在這種療愈的狀態裡,生活也在給予我更多養分,而這些養分,或許也會積極帶動周圍的人。 比如我最近在餵養流浪貓,看到能給它們飽腹,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去公園裡玩的時候,茶館老闆養的小狗就會開心地來給我帶路,這也能讓我很有成就感——因為我願意花時間溜一溜我的小狗朋友,而我的小狗朋友也會熱情地回應我。相比起漫長而暫時無法回報的科研,這種短暫而真實的快樂,更加寬慰人心。 在社交媒體上寫這些“看似沒用的話”,實際上也是種發洩。只要最後有一個人能給到我積極的反饋,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事實上,我真的經常在延遲中收到喜悅。這些大概是生活中的某個幕後推手看我不自覺洩了氣,於是給我恰到好處推一把。比如即便我長久沒有更新b站,仍能收到一些溫暖的私信,告訴我她們看了我的視頻也選擇了某所大學攻讀翻譯,又或者畢業之後從事了“遊戲本地化",一點小小的啟發,戰線之長,足可以橫跨三四年,倍感溫暖。又比如,某遊戲的譯者,給我分享了他們新出的本地化推送……每每收到這些消息,都讓我覺得,我還是有點用的,謝謝你們。值得!
- 避免過度的研究社交乃至於對他人的研究窺視,專注好自己的,每一步走紮實。 我之所以會提到這一點,是因為我曾經也有一段時間周旋在研究社交中備受煎熬。我並不是熱愛社交的人,社交對我並非必需品,甚至是朋友的朋友要推我微信都會讓我產生不自在。但是每每在各種社交場合,總讓我有一種“如果你不社交你就輸了”的錯覺。所幸的是,後來我的一些經歷,再次證實了,萍水相逢並不代表雙方可以直接產生“互利的”聯繫,淺淺認識也並不是什麼值得誇耀的事情。得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去糾結人際關係,問題才會迎刃而解的。 與此類似,所謂的科研的“風口”,也曾經讓我有類似的慌張感。當所有人都在追風口,我得是堅定的相信,自己一定是追不上的。我從小就不是爭著去回答問題的人,電影首映、遊戲首玩,又於我何加焉?去順應自己的性格和節奏,有什麼碗吃什麼飯。風口的存在並不代表著某個話題就是唯一,大家都會填飽肚子的。 博士二年級的後期,在布里斯托的博士生分享中,我接收到一些影響我至今的觀點。那次我聽到了一位遊戲研究博士生分享的,關於牙買加遊戲的課題。同時,在這次的DiGRA23中,我看到了關於土耳其本地化《暗黑3》的課題。這些課題和分享者的生活背景、個人經歷息息相關。他們是風口嗎?他們是討喜的嗎?別人去做這些可以嗎?別人有興趣去做嗎? 那一瞬間我發現,每個人都是不可替代的,這種性格和背景中的吸引力會引導一個人一直向前,每個人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個性,這些個性也許共同組成了所謂“研究價值”的共性,共同塑造了多彩的領域。這多好啊。 所以,我走過的路,只有我走過,我也一定是不可替代的。
- 珍惜挫折和情緒,以後這都不算啥,是可愛的過往。 當我在網絡上分享一些關於我科研和生活的細節時,說明我一定斟酌過其對我所謂“形象”是否會產生一些偏差。但我每每又想到自己沒有所謂人設和形象,於是那些在廁所裡因為反思爆哭,半夜收到好消息狂笑的片段,又成為了心底不願掩藏的過往。也許很多年後,當我翻看這些每年的總結,我會疑惑,“難道當時我真的這樣做了嗎?太扯了吧”,但我說,我就說,假設很多很多年後我的學生翻到我所寫的內容,在蛛絲馬跡中感慨:“哦,原來老師也這樣啊——” ok,你最好不要太懂中文,如果你來問我,我會不承認並且3秒後暴走。 但說句實話,以七情六慾來真實面世界(e.g. 科研道路),讓反饋與情緒自然流淌,又有什麼不好的呢?我最近喜愛看的幾個不同領域的PhD在讀生的社媒,允許任何事情發生,包括挫折。比如 成溪的試驗田,就分享了她作為農學博士種土豆失敗,研究出了更不抗病的土豆和不結果的番茄,把屏幕前我的給笑暈。 允許任何事情發生,才能讓這些成為以後的經驗。
寫了三點,差不多就是我博二的感慨。其實也可能是因為我累了,寫到這裡的時候我朋友喊我打遊戲去,我說“1”。再回頭來看這些話的時候,我突然在腦海裡閃過了很多早期研究者的名字以及方向:人機交互,遊戲/電影無障礙,遊戲本地化,遊戲文化,遊戲法……在某一瞬間,我覺得大家也許都是相似的。每個人都在荒草悽悽、十分幽寂的路上獨自行走著。大概率我會把這篇文章分享給你,又或者你們通過其它途徑看到。希望你們可以會心一笑。
最後的最後,博士二年級的末期,我也迎來了科研道路上很重要的轉變。經過九九八十一個連環事件,我最終不捨但又果決地從布里斯托大學轉到了倫敦大學學院。每一個決定都是當時能做的最合適的選擇,這是一個很好的新的開始:新的視野,新的師資,新的感悟。把我放到三年前,五年前,我大概從來都沒有思考過這個轉折點,也沒有膽量去思考。畢竟當年,“我向著一條路極目望去”,“它”就這麼“消失在叢林深處”。
只是我沒有真的想到,2020年的某一天,布里斯托大學伍德蘭路上的某間小房子,裡面的木頭樓梯老舊了,咯吱咯吱發出聲音,我帶著電腦包,去老師那兒要office hour。更確切來說,那次我終於意識到:我對電影的興趣根本不足以戰勝我對遊戲的興趣,所以這個小小的分叉路口(電影老師的office在樓梯左,遊戲老師的office在樓梯右),還真就決定了我的道路……
如今,我又選擇了人跡更為罕至的一條,一眼沒有盡頭。說實話,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到哪裡去。但我的過去,又成為我未來的經驗。所以在文章的最後,我也想借助此時迸發的情感,在公開的社媒,再次對陪伴我走過一段路程的 布大 Carol O'Sullivan 教授 表示感謝。正如我們的約定:雖然就此揮別,來日定會再見!同時,我也非常感謝 UCL 兩位老師對我的認可與期待。
林中路,無憾路。步履不停,keep walking。
拓展閱讀
DiGRA23 的視頻版反思 與本文內容互為補充 我發在b站 歡迎三連
DiGRA23: Limits and Margins of Games 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