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洛韋薩的操場上,一位年輕的母親正看著她四歲的兒子沃爾夫。正值仲夏,烈日當空,灰色的薄片從楊樹上落下,母親卻在焦慮。其他的孩子們在圍著玩具房子奔跑,男孩們尖叫著,拉扯女孩們的頭髮。幼童們在玩具房子的檯面上奔跑時,上面的吊橋震動著。下方,男孩女孩們在一個巨大沙坑的木板邊緣建造了一座城鎮。一個女孩繞著塔樓旋轉著小飛艇模型,兩個男孩在挖掘隧道,一個從這邊,一個從山丘的那邊。隧道在中間交匯,男孩們洋洋得意地大笑起來。那個女孩感到無聊,哭了起來,另一個女孩走過來詢問發生了什麼事。
只有小沃爾夫獨自一人,遠遠地坐在沙坑的另一邊。當有人詢問沃爾夫,他用那一大片布建造的孤零零的房子是什麼時,他什麼也沒有說。男孩只是茫然地望向遠方,露出神秘的稚氣微笑。不知為何他似乎…對此表現得太*酷*了。過於酷而不跟其他搗蛋鬼講他的房子。其他人很快對沃爾夫傲慢的舉止感到厭煩,讓他一個人待著了。這位年輕的母親無法理解,她的孩子為什麼不在乎是否有他人作伴。即使是與自己的父母,沃爾夫也不會有超過十個詞的交流。他會講話,但只在他一個人的時候。有時母親在另一個房間聽到他在說話,她不明白她的小男孩出了什麼問題。
遠方的街道傳來遊行的聲音,低音鼓砰砰作響:咚-咚…沃爾夫孤傲地坐在沙坑一角,隨著音樂的節奏來回搖晃著他長著捲髮的頭。看起來他幾乎是在… *自我愉悅*。
--------------------------------------------
星期三的下午,離傑斯帕住宅不遠的森林裡。這會兒汗在帶路,其他人盡力跟上他的腳步。他攝入了大量的咖啡因,一整晚都沒睡。在早晨到來之前,他按下“哈南庫爾”的按鈕,煮了咖啡,打了一個長途電話,聽悲傷的音樂,直到他的母親讓他調低音量。汗說話時揮舞著雙手,他橙色的外套敞開,綠松石-橘-淺紫的伊爾瑪配色的條紋圍巾在空中飛舞。這是他母親冬至織給他的,蓬蓬球帽子則是之前的生日禮物,也是伊爾瑪配色。它們組成了一個系列。
林間小徑在丘陵間蜿蜒,兩側是高大的松樹。三個人並排——傑斯帕走在右側的輪胎印記上,特雷斯在左邊,而汗徑直走在中間的草叢裡——走下山坡,來到積雪覆蓋的沙路上。灰色裝點著乾草,在腳下沙沙作響。一片孤單的雪花在空中飛舞,晚秋乾燥的大自然閃閃發光。
汗深吸一口新鮮的空氣。苔蘚腐爛了。兩隻手套被繩子掛在他的背上,他將它們拍在一起。“我從來不相信違法的解決方案,你是知道的。向前的每一步都有意義,因此,追捕油氈推銷員固然很好,但是特雷斯,有時我覺得你收集那些人就像我收集紀念物一樣,你懂我的意思嗎?當然了,我沒有貶義。”
特雷斯吐出一個大大的銀灰色菸圈,讓“阿斯特拉”從中間套過,隨後消散在安靜的微風中。“我不介意,你也說對了。你收集那些東西是因為你認為在其中能發現關於女孩們的某些線索。我因為同樣的理由收集我的怪物。”
“那你收集什麼呢,傑斯帕?”汗問道。
“我什麼也不收集,你這個怪胎。但有個愛好總歸是好的。嘿,下一步幹什麼?”
“嗯,我們去搜尋特倫特默勒的財產,採訪他的親戚。”特雷斯戴著皮革手套的手指列出清單。
“但是你看到了他沒做那件事,對嗎?”林中小徑拐彎了,淺灰色乾草像是某個人的頭髮拂過軌道,在傑斯帕的腳下沙沙作響。“還是說你不確定?”
“在佩皮·波皮卡納西斯[100]船長的迷幻儲藏櫃中,你什麼都無法確定。”亢奮的汗轉過身來插嘴道。他往回走了幾步,對特雷斯解釋道:“這就是為什麼ZA/UM在法庭上無法算為證據。這是迷幻之境,你看,僅憑它自己可不夠。現實要與之*對應*。必須有證人和證物。總之它毫無意義!”
“呃,我不會說它毫無意義。”特雷斯把菸頭扔到樹下,濺射出橙色的火花。“但是你對佩皮·波皮卡納西斯的觀點是正確的,他的測試對象把幻想和現實混在了一起。對我來說它更像是他的…一個層面。中斷存在的一面或是…如果我有時間的話,我會讓當地的機構調查一下這些東西。”
“但現在,如你所說,它*Bastaa*[101]?”
“現在,它*Bastaa*,是的。”
“好極了,因為讓我們說實話吧!你們哪個想在某個下水道里找到她們?說真的。它本身並不是目的,它無法了結任何事!”汗傻笑著等待回答,他看見特雷斯舉起了手。
“我想,它本身就是目的。你聽說過閉合[102]嗎?一個概念。”
傑斯帕仍然把佩皮·波皮卡納西斯的合成器視為被高估的未來主義者的自我滿足。“你能提供什麼更好的東西嗎?*Tempus rev*[103]?我們這次做對了嗎?”
“不失為一個想法。真的,我不否認。”
“得了吧,汗,講點道理。”特雷斯又點了一支菸,寒冷的空氣中有股硫磺的味道。“時間在流逝,我們失去了瑞瓦肖和奧西登的聯繫。半個世界都危如累卵,如果戰爭爆發,所有的調查都會被叫停,檔案,文件,還有人們都可能失蹤。我們得手腳麻利點,在為時已晚之前綁緊鬆散的結局。”
三個小剪影穿過雜草叢生的田野,一邊爭吵,一邊在一根原木柵欄上保持平衡,緩慢地移動。冰塊順著腳邊的小溪漂流而下,在昏暗的森林隧道里,他們躍過橫倒的樹木,排成一列走在白色的草地上。汗從中間鑽過鐵絲網,傑斯帕像特雷斯基[104]一樣從上方躍過。空地落在身後,森林樹影稀疏,沙路像小運河一樣橫躺在樹根之下。海風在樹頂上沙沙作響,已經能在空氣中感受到廣闊無垠的大海。
“這麼久以來我們一直在做你的事情,但從中卻一無所獲。現在給我一個機會。”汗用於表達的手勢比語言更多。
“好吧,你說的對,這是個死局。”特雷斯承認。“但起碼告訴我們計劃是什麼,讓我們考慮一下。如果我認為其中能有所發現,那沒問題,我們去做,如果不能,我們就必須去休息。”
“你不明白。”汗聳肩道。“如果你說不,那我們就永遠不會知道了。再也不會有其他的選項。我不能冒著被你否決的風險。在此之前我們先來一次短途旅行,哈?我們去找一位專家聊聊。我們很早之前就該聯繫他們了;現在情況非常緊急。”
“你說再也沒有其他選項是什麼意思?”傑斯帕不明白。“而且瑪琳的信怎麼說?一定是某個人投遞的,筆跡吻合,但在那個年紀,應該有一些進步才對。如果一個人十三歲時寫下字,那她們的筆跡不會與十五歲的100%相同,95%是非常可信的;我讀到過這些東西,對嗎,特雷斯?”
“是是,沒錯。”汗插嘴。“但你知道嗎?對於如何理順這些事,我有個主意。而*現在*我們不該再繼續等待了。我們要行動起來,立刻馬上!”
“什麼主意?”
“嗯,我在報紙上登了個廣告。”
特雷斯穿著50年代風格的魚尾服走著路,看起來就像一個真正的克吉克,他的嘴巴因為思考而微張。“這個主意也許不算太壞。你什麼時候登的廣告?”
“我前天投遞的。今天應該就發出來了。我把你的號碼也放上去了,傑斯帕,以防我不在家。”
“那你在上面是怎麼寫的?”
“如果有任何人有任何信息,請直接來告訴我們,不會有任何壞事發生,幫助我們,你知道的!”
“這種東西可能比你以為的更有效些。”特雷斯對傑斯帕解釋道。“尤其是像這樣的陳年舊賬。不過你還是得月復一月地在不同欄目上釣魚。你刊登在哪了?”
“在《達根斯》[105]和《資本家》上。我沒更多的錢了。順便,你們每人欠我五十。還有我推薦的顧問,找他也要錢。還有旅行的費用。你最少要帶一千塊,他要價不菲,級別非常高。我為此已經等待了很久,讀了很多關於他的…”
傑斯帕失去了耐心。首先,他現在絕對哪也不想去,其次,他已經意識到是誰的錢正處於危險之中。汗依靠他死在油井裡的父親的賠償金生活,而特雷斯如果不開展任何調查,他就不會有任何工資。“聽著,說清楚,我們在聊的顧問到底是哪位?”
三個人影來到懸崖邊緣。他們越過乾涸的草原,與廣闊的海洋相遇。乾草上點綴著白色的雪,一組松樹在風中孤單地顫抖。男人們接近懸崖邊緣時,天色變暗了。傑斯帕拉起外套的衣領,耳中的水聲更響了。他經常獨自在這裡走上六公里。在這個地點,他們能看見朝思慕想的事物——海灣另一邊,積雪覆蓋的遠方,夏洛茨扎爾閃亮的藍色沙灘帶。
汗靠在木柵欄上向下看去。海浪擊打巖牆發出巨響。海水捲曲著,白色的浪尖破碎成百萬個泡沫群,落在男人的眼鏡上,模糊了他的視線。傑斯帕欣賞著一年一度的秋季浪潮,他現在有一個清晰的計劃。我們出發。他會告訴女孩他也要出發了,他會為男孩們想些其他的東西。他在測量著風。
“自-我-愉-悅-者。”汗說道,“這是跟他講女孩的事情的最後機會。”
傑斯帕開始大笑,但特雷斯很嚴肅。
“等等,等等!他能把阿巴達納茲和多佈雷娃骨骼的位置鎖定在一公里的範圍內。”汗解釋道。“還有呢?兩年前,他們跟隨他的線索去蒙迪之軀尋找科尼利厄斯·古爾迪[106]。他帶走的項鍊如今已沉沒在灰域裡,但他們在那附近發現了古爾迪的剩菜和露營地。那可是一百年後的參照!那位自我愉悅者,傑斯帕,住在列敏凱寧鄉下的一間木屋裡,而我們就要去那裡。”
雪落在鉛灰色的海面上,氣溫接近零度;海灣裡的風速不到十米每秒,接下來的兩週在卡圖的西邊,就在灰域的邊緣,將會看到讓海洋波濤洶湧的風暴。一個兩週的窗口期,完美的情況。傑斯帕已經能感受到在十公里外的夏洛茨扎爾海灘,海水將會如何翻滾肆虐,在波浪中破碎。海浪在他面前移動,廣闊而平穩,就像美麗的思緒。
“好吧。”傑斯帕說。“但我有個會議。設計的事情。從週四到週六。順便提醒一句:現在去列敏凱寧可不是個好主意。還是說你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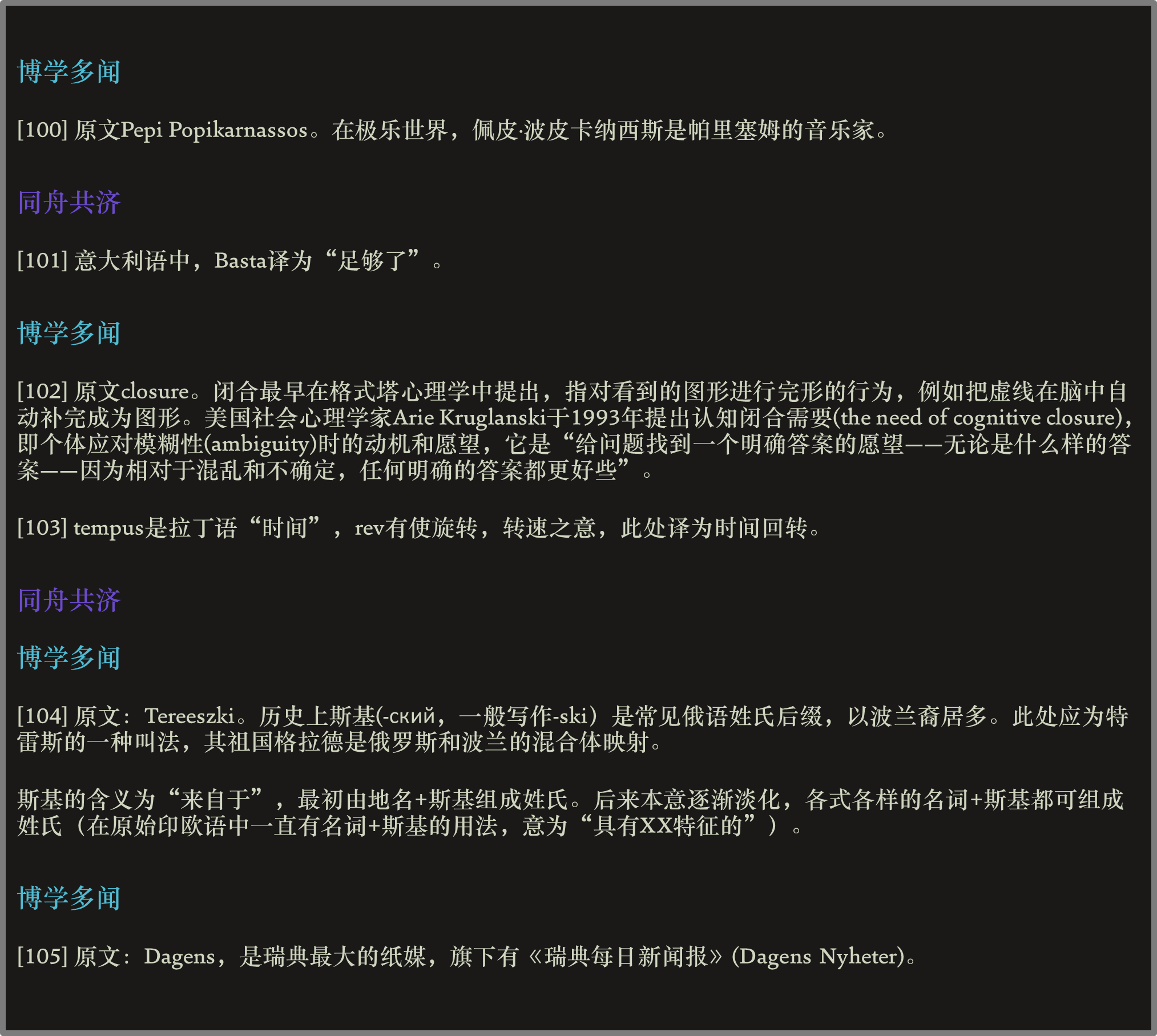
--------------------------------------------
現代舞曲在奧蘭治誕生時,小沃爾夫九歲。約翰·豪爾,裡特維爾德[107]和阿諾·凡·艾克[108]在禮堂裡轉動唱片;在維斯帕的維德倫德,世界上第一家迪斯科舞廳,“Das Baum[109]”開業了;在一個夏天的夜晚,梅西納的拱廊廣場上,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史詩的*場景*後,狂熱的民眾將西奧·凡·科克加冕為無罪者。沃爾夫揹著雙肩包從學校回家。他上四年級,因為沃爾夫不在乎老師在說什麼,所以他獨自一人坐在班級的後面。數學和科學不能引起沃爾夫的興趣;愚蠢的女孩也不能引起沃爾夫的興趣;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能引起他的興趣。在維斯特姆[110]回家的路上,他張著嘴,站在Fonopoe[111]的門口,樂迷在其中進進出出。一臺老舊的機器播放著西奧·凡·科克的昏迷混音專輯,樂迷們看著小沃爾夫像著魔一樣搖擺和舞蹈。淚水順著沃爾夫的臉頰流下,整個世界消失了。所有人都在大笑,敬畏地看著小男孩蹦跳,甩動,搖擺,喘息,揮舞和咆哮。“哇,這難道不驚人嗎?!”他的手腳在半空中橫衝直撞,用手掌拍打汽車引擎蓋,他就是不明白:“這為什麼能如-此美妙?!它不可能這-麼美妙!!!”一個穿著時髦運動衫的推銷員從店裡走了出來;沃爾夫從舊日之物的灰域裡,從跨越人類歷史的昏迷回聲裡走到這位年輕人面前;而他交給沃爾夫一個八聲道磁帶。封面上寫著“西奧·凡·科克/”,“普魯斯-米特雷西伯爵”。這是沃爾夫生命裡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認為某個活人對他有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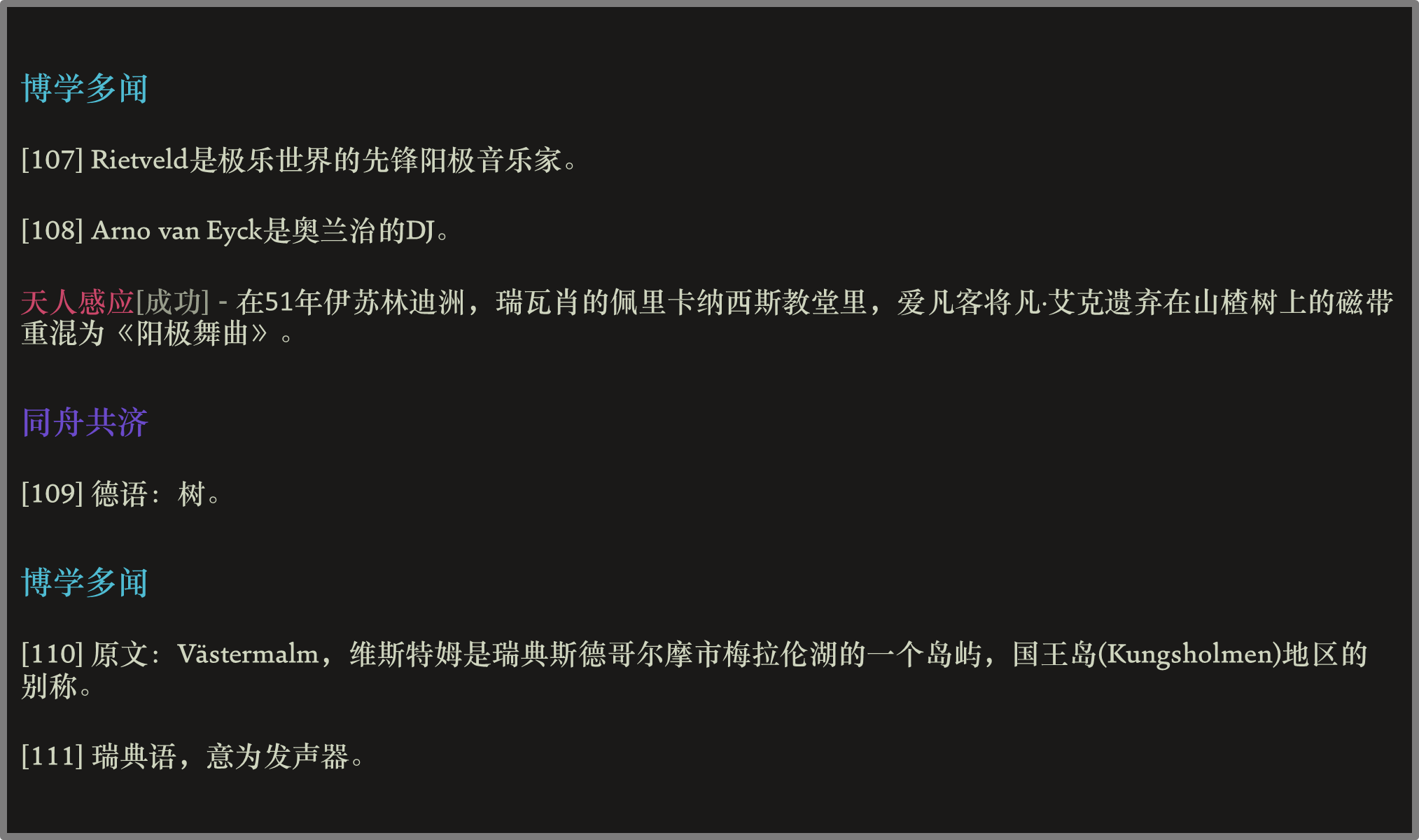
--------------------------------------------
機動車帶有溝槽的輪胎旋轉著,積雪在車輪下沙沙作響,但伊納亞特·汗不在那裡。十三歲的他,邁出特雷斯父親鄉間別墅的門廊,進入蘋果園。天色昏暗,蟋蟀在鳴叫。自我愉悅者把一個八聲道磁帶放入播放器,兩個塑料碟片開始轉動。*試音*正在進行中,而九月的夜晚靜謐無聲,音樂不會傳太遠。這是二十年後,距離汗十分遙遠的地方。空氣中充滿了香味,他如幽靈般從樹下接近男孩,環繞在他的膝蓋周圍,散發著早熟蘋果的味道。汗光著腳走在沾有露水的草地上。男孩們在二樓的屋裡睡覺,但他睡不著。他們早上七點半一起去打工了。汗的身體因為建造工程而筋疲力盡,但他內心卻無法休息。錢不夠。經銷商齊吉在電話裡拋出了天文數字。300雷亞爾。在經歷一番勸說後,傑斯珀把他收藏的系列冒險小說《來自赫姆達爾的男人》帶去了二手書店。汗變賣了他的雙筒望遠鏡。
機器心臟的十六沖程燃燒室中發生著劇烈的撞擊;在遙遠的列敏凱寧,農場窗戶上的一扇玻璃在貝斯節奏中顫抖著。*檢索*,*檢索*…但伊納亞特不在那裡。一顆蘋果落到在他面前的地上。小伊納亞特用袖子把蘋果擦乾淨,坐到花園長椅上。他咬下水果,感受著甜蜜的痛苦在心中橫衝直撞,讓他呼吸困難。失足的可能性日漸增長,到了今晚終於足夠被察覺了。“說吧…你總是能說出很酷的言論。在歷史和自然科學…”深綠色的眼睛,難以置信的溫柔且興致勃勃。你確定嗎,汗?現在嘗試理性思考一下;沒有任何理由把自己貶低得一無是處。
發動機蓋冒著蒸汽,引擎傳動帶在運轉,磁帶貼著放音磁頭滑動。但果園中仍然十分安靜。伊納亞特·汗不相信上帝,完全不。上帝是三千多年前,在伊爾瑪,一個叫皮烏斯的人發明的。或許。但現在汗把蘋果核扔進樹叢裡,雙手合十,祈禱著。
“請讓我討瑪琳的喜歡。上帝,請讓我非常討她喜歡,而不僅是…你知道的,畢竟你是上帝。我向你保證我之後不會再認為是某個男人——來自佩裡卡納西斯的皮烏斯——發明的你。我向你保證,我會相信在時間原點時你就已經存在,用你的…呃…金色羅盤之類的東西,畫出了天空和大地。對不起,上帝,不該這樣開你的玩笑。但是你看,如果我不能討瑪琳喜歡的話,我真的很難相信你的存在。”
汗抬頭望向天空。在他內心的黑暗之處,愛像星辰一樣旋轉和蔓延。愛,像一隻毛色亮麗的貓,蜷縮在他的胃裡。對他來說,愛亦是對失去的恐懼。
尾燈的紅光在雪地上留下血跡,引擎消音器噼啪作響。綁著鏈條的輪胎在雪地上發出嗖嗖聲,引擎轟鳴了一陣。換擋。音調上升。加速度將莽撞的司機壓入座椅中。這個年輕的男人戴著賽車護目鏡和駕駛頭盔,手指被凍結在操縱桿上。無光的山路從他護目鏡堅硬的表面反射出來,消失在車輪之下。
大氣層盤旋在列敏凱寧灰域理論災難區的上空。黑暗的山脈上,被積雪覆蓋的山峰切開了地平線。它們的牙齒像油氈推銷員的一樣裸露在外。在山谷底,空地和雲杉林綿延不絕,一輛黑色汽車在蜿蜒的道路上以每小時一百五十公里的速度飛馳。
“靠,這簡直有-病!”汗尖叫。特雷斯點頭,引擎冒出的酸性工業煙霧充斥在車廂裡冷空氣中。探員看向窗外,注視著被積雪覆蓋的路樁從暴雪中飛過。在山谷底,空地點綴中的一團白色物質若隱若現。汗彈到對面特雷斯身旁的位子上,喝掉酒瓶裡的最後一點酒。烈酒刺激著他的感官,他砰的一聲撞在車廂的牆壁上。
“沒了。”他向特雷斯展示空空的瓶子。另一瓶風味漿果酒出現在汗的手中。旋擰式瓶蓋砰的一聲彈起。“甜度:25%”。他在齒間磨著糖塊。遠方,對面的山坡上,若隱若現的燈光在黑暗中閃耀。從星期三晚上開始,所有其他的車輛都在反向行駛,遠離灰域理論災難區。那也是汗,探員馬切耶克和瘋狂的拉力賽車手肯尼——就叫肯尼——從瓦薩出發的時間:
“你叫什麼名字?”
“Kenni.”
“Kenni kuka?”
“Vain Kenni.”
“Kattoo, entroponeetisen romahduksen vyöhyke! Ei voi olla, kuusetkin rupee taivaasen ajautumaan, saa-ta-na, ihan kuin ne sanoi, sen kyllä täytyy nähdää! Ja talot myös!” [112]肯尼在駕駛座上大喊。
“你還好嗎?”汗喊了回去。與特雷斯不同,當機器在黑暗中搖晃時,他依然略感擔憂,在車速表的淡黃色光芒中,他看到指針指向一百七十邁。
“Hienosti menee, ihan hienosti, en huolehdi ollenkaan!”[113]
“那路呢?路怎麼樣?”
“Että mikä, tiekö? Ei, hyvin on, en huolehdi ollenkaan.”[114]
肯尼並無huolehdi ollenkaan[115]。相反,他還想要風味漿果酒,而當汗認為肯尼不應該酒駕時,肯尼說:“Äla huolehdi, 好嗎? Mä oon puolet tiet juonu jo, muuten mä nukahtaisin. Se autta mua keskitymään, kato!”[116]
道路繼續沿著山坡蜿蜒前行,兩邊是雲杉樹。肯尼身體前傾,在彎道上維持行進的路線。只有在汽車深陷林中,沿著鄉間小路行駛時,汗才獲得些許的安全感。車輪下的積雪吱嘎作響,發動機艱難運轉著,車窗上佈滿一圈圈的雪花。深色的樹牆在照明燈後顫動。突然間,肯尼拐到路的左側,汗跳回了他自己的座位上。汽車飛速超過一輛紅色的格拉德通訊麵包車。在他們被積雪覆蓋的照明燈下,新聞團隊向他們揮手致意,汗也向他們揮手。
在過去的兩天裡,汗和特雷斯一直在車廂裡喝酒。司機拒絕停車休息。肯尼想要打破一個記錄。他的手裡拿著一個秒錶。這段時間裡他們見到的所有汽車都是對向行駛的。此時已經距瓦薩兩千公里遠,而馬路對面的大堵車依然在龜速爬行。郊區的人們前往市區投奔親戚。他們從汽車收音機裡得知,同樣的恐慌遍佈整個卡特拉洲。因為位於北雪平的磁懸浮列車站,阿爾達變成了每個人都想去的地方。甚至在崩塌的北方高速公路附近的耶林卡,也已經賣光了接下來兩個月的車票。無路可出,可能還不如步行穿過北方高原[117]。
漸漸地,一側的窗外變成穹頂景觀,朦朧的山脊從地平線上滑過,雲杉樹林低伏。深夜,汽車駛入了高速公路,但對向的車流並沒有減少;只有在積雪變厚的原野中央,道路才從支柱上降下,那裡的田野也因此閃閃發光。汗進入了深度睡眠,他的頭靠在一側的玻璃上休息,而在他們前方的黑暗裡,路的一側是車前燈組成的鑽石海洋,而在另一側,只有寒冷的,空蕩蕩的高速公路。只有一對紅色尾燈加速前往列敏凱寧。他們唯一的陪伴只有軍車隊,和車頂插有通訊天線單元的國外通訊社汽車。
早上,他睜開眼睛,看見一個被遺棄的村莊從窗邊掠過。電線杆間的電線飛舞著,在空曠的郊區街道上,一個鄉下女孩騎著自行車。她穿著長裙和夾克。鄉下女孩直視汗的眼睛,自行車輪轂上的反光條閃著光。他們已經離開瓦薩邊境一千五百公里,前方還有第二段一千五百公里的路程。肯尼開得很慢,你能在車廂裡聽見車輪下的水坑裡,冰塊碎裂的聲音。女孩揮揮手,拐進居民區郊外的一條小路上。森林中的黑暗將她吞噬,自行車尾燈隨著發電機的節奏而閃爍。前方,樹木組成的隧道里已經大雪紛飛。於是他們出發了——伊納亞特·汗和特雷斯·馬切耶克,還有肯尼,就叫肯尼,出租車停車場裡最硬漢的男人。在經過蘇魯的幾個小時,男孩們安靜地坐在昏暗的燈光裡,觀察著。路燈組成的寒冷星光在遠方亮起,房子屋頂的瓦楞鐵皮塌縮進永恆。隨著夜幕將至,雪也越下越大。山脈的黑色鋸齒從地平線上升起,村莊愈發稀少,特雷斯提議打開一瓶風味漿果酒。
“不然會變得太壓抑了。”
他們經常能在前方逐漸變暗的山脈上空,看到軍隊的飛艇。有一次,一隻鐵鳥在橋上嘶嘶鳴叫,嘗試用它的聚光燈抓住他們;氣墊威脅要把汽車翻個底朝天。但之後那隻鳥不見了。只有它的探照燈從黑暗的森林上滑過。這被稱為一次疏散。
被遺棄的檢查站立在路邊,上面的文字“列敏凱寧”發著光。一個混凝土塊澆築的軍事路障從馬路對面掠過。肯尼把雪鏈纏繞在輪胎上,然後開車繞過屏障,掀起了一半的土地。從那時起就一直下著雪的冬季軌道,和檢察站一起被留在了後面。瀝青路漸漸消失,於是一個個家庭乘坐著雪橇,沿著積雪的碎石小路向他們的方向駛來。自童年起,親眼看著灰域在身後升起,就是他們尊貴的特權。馬匹拉著雪橇,帶著全部財產的家庭向深黃色皮膚,戴著厚鏡片的滑稽矮胖男人揮手致意。
“真奇怪,他們一直在揮手。”汗說,格拉德通訊麵包車已經遠在身後,壓在了肯尼汽車輪底的一團雪雲下。不再有車前燈或是雪橇燈籠在黑暗的森林中閃爍。只有那些願意留下的人被留在了農場中,私人混合車道上,以及停業的鄉村商店裡。而在黑暗中,灰域悄然逼近。
“Kuuletko sen?”肯尼問道,“Harmaa… se on nyt varmasti harmaa! Mua vähän huolestutta.”[118]
特雷斯和汗聆聽著。確實,在風聲之下萌發出一種新的聲音,轟隆轟隆,一陣令人作嘔的,低沉的爆裂噪音。像一道波浪碎裂開來,慢慢地,慢慢地…汗聽起來就像是一首歌的開頭。他在一場夢裡聽過它。
“我不在聯警工作了。他們讓我滾。”特雷斯大叫,手放在嘴巴前比出喇叭狀,他醉醺醺的。
“什麼?”汗一開始沒聽清,噪音攝人心魄。他感到身體上的毛髮豎了起來,寒意順著脊柱流淌,就好像他剛剛在一個寒冷的房間裡脫下毛衣一樣。
“他們讓我滾出聯合刑警局!”
“我知道!”汗大喊,遞給特雷斯一瓶風味漿果酒。“你一直在展示一個叫薩默塞特·烏爾裡希的人的警徽!”
“你怎麼知道的?”一股酒精味從特雷斯嘴裡升起,飄蕩在車廂裡的冷空氣中。
“因為檢查點的所有警衛都叫你烏爾裡希先生,還有警探烏爾裡希,或是薩默塞特·烏爾裡希。”
“我拿的證明是一個失蹤探員的。我有一大堆。”特雷斯啜飲一口酒,他的嘴唇發紅,粘稠的液體從瓶頸溢出,滴落在他的襯衫上。“證明,我是說。失蹤的探員也是。在喀琅施塔得,我出示了‘馬切耶克’,否則,他們沒法發現我的行蹤。我想我要帶薩默塞特·烏爾裡希的去列敏凱寧,並留下痕跡,如果有能力的話就來抓我吧!”
“你是個通緝犯,還是…”
“是,是,我沒跟你說嗎,哈?有個人因為那檔事還犯了心臟病!”
“ZA/UM,還是…”
“是的,就是它。”特雷斯說,他看到了前方的拉力賽之王肯尼,一團黑雪緩慢地飄向天空。在雲杉樹被自己的樹根撕裂時,大地咔咔作響。樹木在尖叫,礦石浸泡在其中,就像在牙醫的椅子裡一樣。巨型石灰岩飛向空中,而在這之上更遙遠的地方,黑暗裡,第一批樹被灰域包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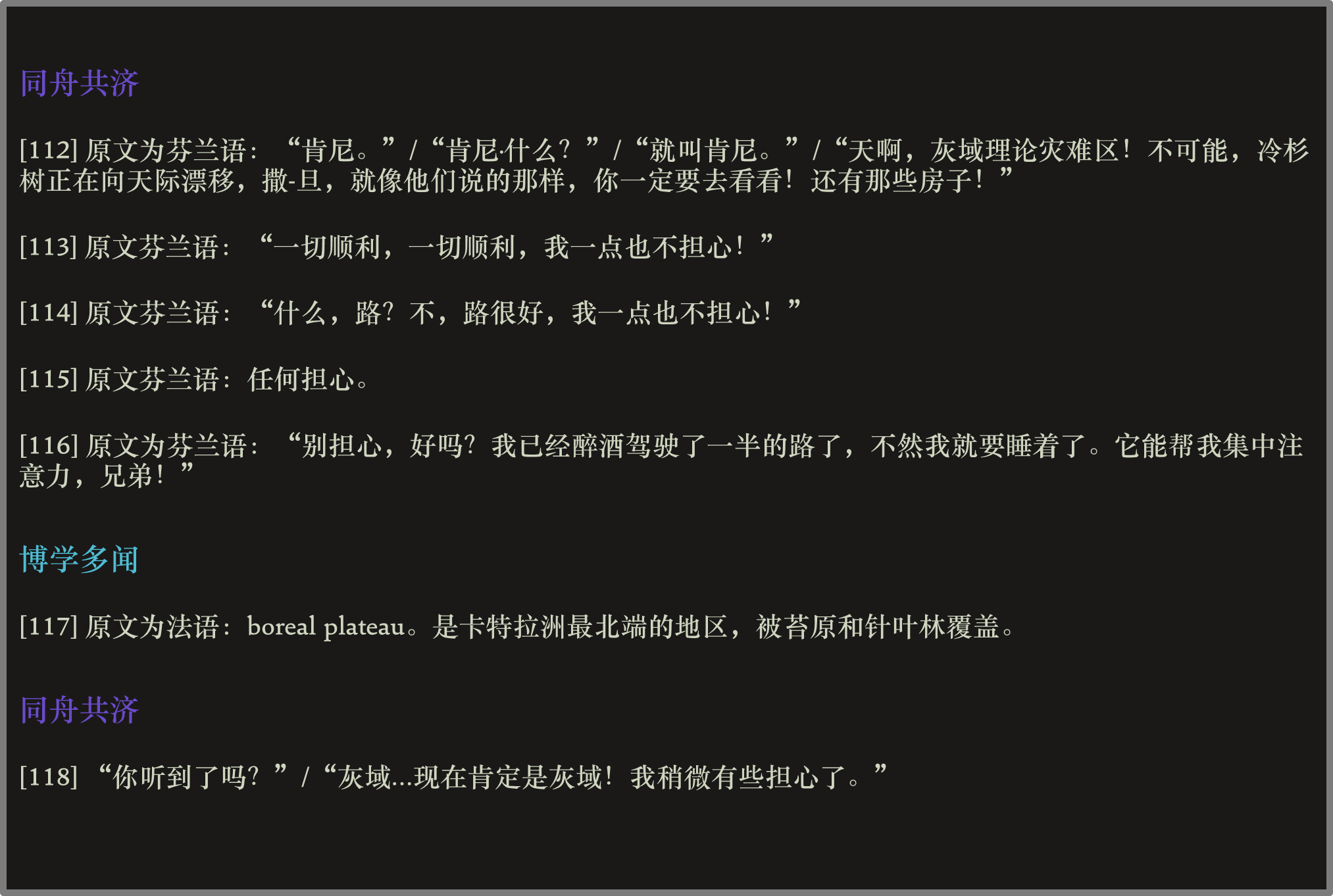
--------------------------------------------
兩年前。
汗在睡夢中聽到了電話鈴聲。這是一個冰冷而陌生的聲音,一次假醒。他在母親的地下室裡睜開雙眼,只穿著睡褲和拖鞋從床上起身。他感覺到某些異樣,但還是走了過去。在夢裡,周圍的地下室變得很奇怪,物品擺放在錯誤的地方。娜佳·哈南庫爾在他的掛墜盒裡露出可怕的微笑,貢子手中的並非羅盤,而是一個永生桃子,它發黴了。
房間的中央,一個空的玻璃展示櫃擺在檯面上。汗不敢看向那個方向,在它的虛無裡有個他無法忘卻的東西。不對勁。鈴聲聽起來也是——它從樓上的走廊發出,穿過公寓的黑暗。
他走上樓,走廊在他周圍沉睡,牆上的電話響著鈴。他畏懼地伸出手。他拿著塑料聽筒的手滲出汗液,有些東西禁止他接起電話。但他必須接,這很重要,每一通電話都有意義。於是他從固定鉤上拿起電話,隨後走廊裡充滿了灰域的靜電干擾。它弄疼了他放在聽筒旁的耳朵。
“你好?”汗試探道。
但沒人回答。
“你好,你是誰?請告訴我你是誰!”他重複著,男人的聲音愈加懇切,靜電干擾就愈發嚴重。直到他被它擊潰,耳腔內的壓力消失了,只剩下它的核心中起源未知的震顫。靜默像波浪一樣流經血肉。它寒冷刺骨。
“求你了,”滾滾的淚珠從汗的眼中落下,“告訴我你是誰…”
“你知道我是誰。”振動發出孩童的聲音,訴說著可怕的事情。汗開始顫抖,猛縮到走廊的角落,聽筒還在他的手裡。
“這不是你!這不是你!”他哭了。男人的現實身體隨著精神抖動。他在床上醒來,痛哭流涕。他的耳朵嗡嗡作響,而夢境還在清醒世界裡持續著,只是飛艇模型回到了展示櫃裡,娜佳不再微笑,貢子拿著羅盤。
展示櫃的頂部是他母親做的幹掉的奶酪三明治,和冰涼的咖啡。還有一個信封——一封來自格拉德的晨間磁報。寄信人一欄寫著“薩爾揚·安巴蘇姆揚”,裡面只有一把鑰匙,純金打造,紛繁複雜。
他還有兩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