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洛韦萨的操场上,一位年轻的母亲正看着她四岁的儿子沃尔夫。正值仲夏,烈日当空,灰色的薄片从杨树上落下,母亲却在焦虑。其他的孩子们在围着玩具房子奔跑,男孩们尖叫着,拉扯女孩们的头发。幼童们在玩具房子的台面上奔跑时,上面的吊桥震动着。下方,男孩女孩们在一个巨大沙坑的木板边缘建造了一座城镇。一个女孩绕着塔楼旋转着小飞艇模型,两个男孩在挖掘隧道,一个从这边,一个从山丘的那边。隧道在中间交汇,男孩们洋洋得意地大笑起来。那个女孩感到无聊,哭了起来,另一个女孩走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只有小沃尔夫独自一人,远远地坐在沙坑的另一边。当有人询问沃尔夫,他用那一大片布建造的孤零零的房子是什么时,他什么也没有说。男孩只是茫然地望向远方,露出神秘的稚气微笑。不知为何他似乎…对此表现得太*酷*了。过于酷而不跟其他捣蛋鬼讲他的房子。其他人很快对沃尔夫傲慢的举止感到厌烦,让他一个人呆着了。这位年轻的母亲无法理解,她的孩子为什么不在乎是否有他人作伴。即使是与自己的父母,沃尔夫也不会有超过十个词的交流。他会讲话,但只在他一个人的时候。有时母亲在另一个房间听到他在说话,她不明白她的小男孩出了什么问题。
远方的街道传来游行的声音,低音鼓砰砰作响:咚-咚…沃尔夫孤傲地坐在沙坑一角,随着音乐的节奏来回摇晃着他长着卷发的头。看起来他几乎是在… *自我愉悦*。
--------------------------------------------
星期三的下午,离杰斯帕住宅不远的森林里。这会儿汗在带路,其他人尽力跟上他的脚步。他摄入了大量的咖啡因,一整晚都没睡。在早晨到来之前,他按下“哈南库尔”的按钮,煮了咖啡,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听悲伤的音乐,直到他的母亲让他调低音量。汗说话时挥舞着双手,他橙色的外套敞开,绿松石-橘-浅紫的伊尔玛配色的条纹围巾在空中飞舞。这是他母亲冬至织给他的,蓬蓬球帽子则是之前的生日礼物,也是伊尔玛配色。它们组成了一个系列。
林间小径在丘陵间蜿蜒,两侧是高大的松树。三个人并排——杰斯帕走在右侧的轮胎印记上,特雷斯在左边,而汗径直走在中间的草丛里——走下山坡,来到积雪覆盖的沙路上。灰色装点着干草,在脚下沙沙作响。一片孤单的雪花在空中飞舞,晚秋干燥的大自然闪闪发光。
汗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苔藓腐烂了。两只手套被绳子挂在他的背上,他将它们拍在一起。“我从来不相信违法的解决方案,你是知道的。向前的每一步都有意义,因此,追捕油毡推销员固然很好,但是特雷斯,有时我觉得你收集那些人就像我收集纪念物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当然了,我没有贬义。”
特雷斯吐出一个大大的银灰色烟圈,让“阿斯特拉”从中间套过,随后消散在安静的微风中。“我不介意,你也说对了。你收集那些东西是因为你认为在其中能发现关于女孩们的某些线索。我因为同样的理由收集我的怪物。”
“那你收集什么呢,杰斯帕?”汗问道。
“我什么也不收集,你这个怪胎。但有个爱好总归是好的。嘿,下一步干什么?”
“嗯,我们去搜寻特伦特默勒的财产,采访他的亲戚。”特雷斯戴着皮革手套的手指列出清单。
“但是你看到了他没做那件事,对吗?”林中小径拐弯了,浅灰色干草像是某个人的头发拂过轨道,在杰斯帕的脚下沙沙作响。“还是说你不确定?”
“在佩皮·波皮卡纳西斯[100]船长的迷幻储藏柜中,你什么都无法确定。”亢奋的汗转过身来插嘴道。他往回走了几步,对特雷斯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ZA/UM在法庭上无法算为证据。这是迷幻之境,你看,仅凭它自己可不够。现实要与之*对应*。必须有证人和证物。总之它毫无意义!”
“呃,我不会说它毫无意义。”特雷斯把烟头扔到树下,溅射出橙色的火花。“但是你对佩皮·波皮卡纳西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的测试对象把幻想和现实混在了一起。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他的…一个层面。中断存在的一面或是…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会让当地的机构调查一下这些东西。”
“但现在,如你所说,它*Bastaa*[101]?”
“现在,它*Bastaa*,是的。”
“好极了,因为让我们说实话吧!你们哪个想在某个下水道里找到她们?说真的。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无法了结任何事!”汗傻笑着等待回答,他看见特雷斯举起了手。
“我想,它本身就是目的。你听说过闭合[102]吗?一个概念。”
杰斯帕仍然把佩皮·波皮卡纳西斯的合成器视为被高估的未来主义者的自我满足。“你能提供什么更好的东西吗?*Tempus rev*[103]?我们这次做对了吗?”
“不失为一个想法。真的,我不否认。”
“得了吧,汗,讲点道理。”特雷斯又点了一支烟,寒冷的空气中有股硫磺的味道。“时间在流逝,我们失去了瑞瓦肖和奥西登的联系。半个世界都危如累卵,如果战争爆发,所有的调查都会被叫停,档案,文件,还有人们都可能失踪。我们得手脚麻利点,在为时已晚之前绑紧松散的结局。”
三个小剪影穿过杂草丛生的田野,一边争吵,一边在一根原木栅栏上保持平衡,缓慢地移动。冰块顺着脚边的小溪漂流而下,在昏暗的森林隧道里,他们跃过横倒的树木,排成一列走在白色的草地上。汗从中间钻过铁丝网,杰斯帕像特雷斯基[104]一样从上方跃过。空地落在身后,森林树影稀疏,沙路像小运河一样横躺在树根之下。海风在树顶上沙沙作响,已经能在空气中感受到广阔无垠的大海。
“这么久以来我们一直在做你的事情,但从中却一无所获。现在给我一个机会。”汗用于表达的手势比语言更多。
“好吧,你说的对,这是个死局。”特雷斯承认。“但起码告诉我们计划是什么,让我们考虑一下。如果我认为其中能有所发现,那没问题,我们去做,如果不能,我们就必须去休息。”
“你不明白。”汗耸肩道。“如果你说不,那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了。再也不会有其他的选项。我不能冒着被你否决的风险。在此之前我们先来一次短途旅行,哈?我们去找一位专家聊聊。我们很早之前就该联系他们了;现在情况非常紧急。”
“你说再也没有其他选项是什么意思?”杰斯帕不明白。“而且玛琳的信怎么说?一定是某个人投递的,笔迹吻合,但在那个年纪,应该有一些进步才对。如果一个人十三岁时写下字,那她们的笔迹不会与十五岁的100%相同,95%是非常可信的;我读到过这些东西,对吗,特雷斯?”
“是是,没错。”汗插嘴。“但你知道吗?对于如何理顺这些事,我有个主意。而*现在*我们不该再继续等待了。我们要行动起来,立刻马上!”
“什么主意?”
“嗯,我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
特雷斯穿着50年代风格的鱼尾服走着路,看起来就像一个真正的克吉克,他的嘴巴因为思考而微张。“这个主意也许不算太坏。你什么时候登的广告?”
“我前天投递的。今天应该就发出来了。我把你的号码也放上去了,杰斯帕,以防我不在家。”
“那你在上面是怎么写的?”
“如果有任何人有任何信息,请直接来告诉我们,不会有任何坏事发生,帮助我们,你知道的!”
“这种东西可能比你以为的更有效些。”特雷斯对杰斯帕解释道。“尤其是像这样的陈年旧账。不过你还是得月复一月地在不同栏目上钓鱼。你刊登在哪了?”
“在《达根斯》[105]和《资本家》上。我没更多的钱了。顺便,你们每人欠我五十。还有我推荐的顾问,找他也要钱。还有旅行的费用。你最少要带一千块,他要价不菲,级别非常高。我为此已经等待了很久,读了很多关于他的…”
杰斯帕失去了耐心。首先,他现在绝对哪也不想去,其次,他已经意识到是谁的钱正处于危险之中。汗依靠他死在油井里的父亲的赔偿金生活,而特雷斯如果不开展任何调查,他就不会有任何工资。“听着,说清楚,我们在聊的顾问到底是哪位?”
三个人影来到悬崖边缘。他们越过干涸的草原,与广阔的海洋相遇。干草上点缀着白色的雪,一组松树在风中孤单地颤抖。男人们接近悬崖边缘时,天色变暗了。杰斯帕拉起外套的衣领,耳中的水声更响了。他经常独自在这里走上六公里。在这个地点,他们能看见朝思慕想的事物——海湾另一边,积雪覆盖的远方,夏洛茨扎尔闪亮的蓝色沙滩带。
汗靠在木栅栏上向下看去。海浪击打岩墙发出巨响。海水卷曲着,白色的浪尖破碎成百万个泡沫群,落在男人的眼镜上,模糊了他的视线。杰斯帕欣赏着一年一度的秋季浪潮,他现在有一个清晰的计划。我们出发。他会告诉女孩他也要出发了,他会为男孩们想些其他的东西。他在测量着风。
“自-我-愉-悦-者。”汗说道,“这是跟他讲女孩的事情的最后机会。”
杰斯帕开始大笑,但特雷斯很严肃。
“等等,等等!他能把阿巴达纳兹和多布雷娃骨骼的位置锁定在一公里的范围内。”汗解释道。“还有呢?两年前,他们跟随他的线索去蒙迪之躯寻找科尼利厄斯·古尔迪[106]。他带走的项链如今已沉没在灰域里,但他们在那附近发现了古尔迪的剩菜和露营地。那可是一百年后的参照!那位自我愉悦者,杰斯帕,住在列敏凯宁乡下的一间木屋里,而我们就要去那里。”
雪落在铅灰色的海面上,气温接近零度;海湾里的风速不到十米每秒,接下来的两周在卡图的西边,就在灰域的边缘,将会看到让海洋波涛汹涌的风暴。一个两周的窗口期,完美的情况。杰斯帕已经能感受到在十公里外的夏洛茨扎尔海滩,海水将会如何翻滚肆虐,在波浪中破碎。海浪在他面前移动,广阔而平稳,就像美丽的思绪。
“好吧。”杰斯帕说。“但我有个会议。设计的事情。从周四到周六。顺便提醒一句:现在去列敏凯宁可不是个好主意。还是说你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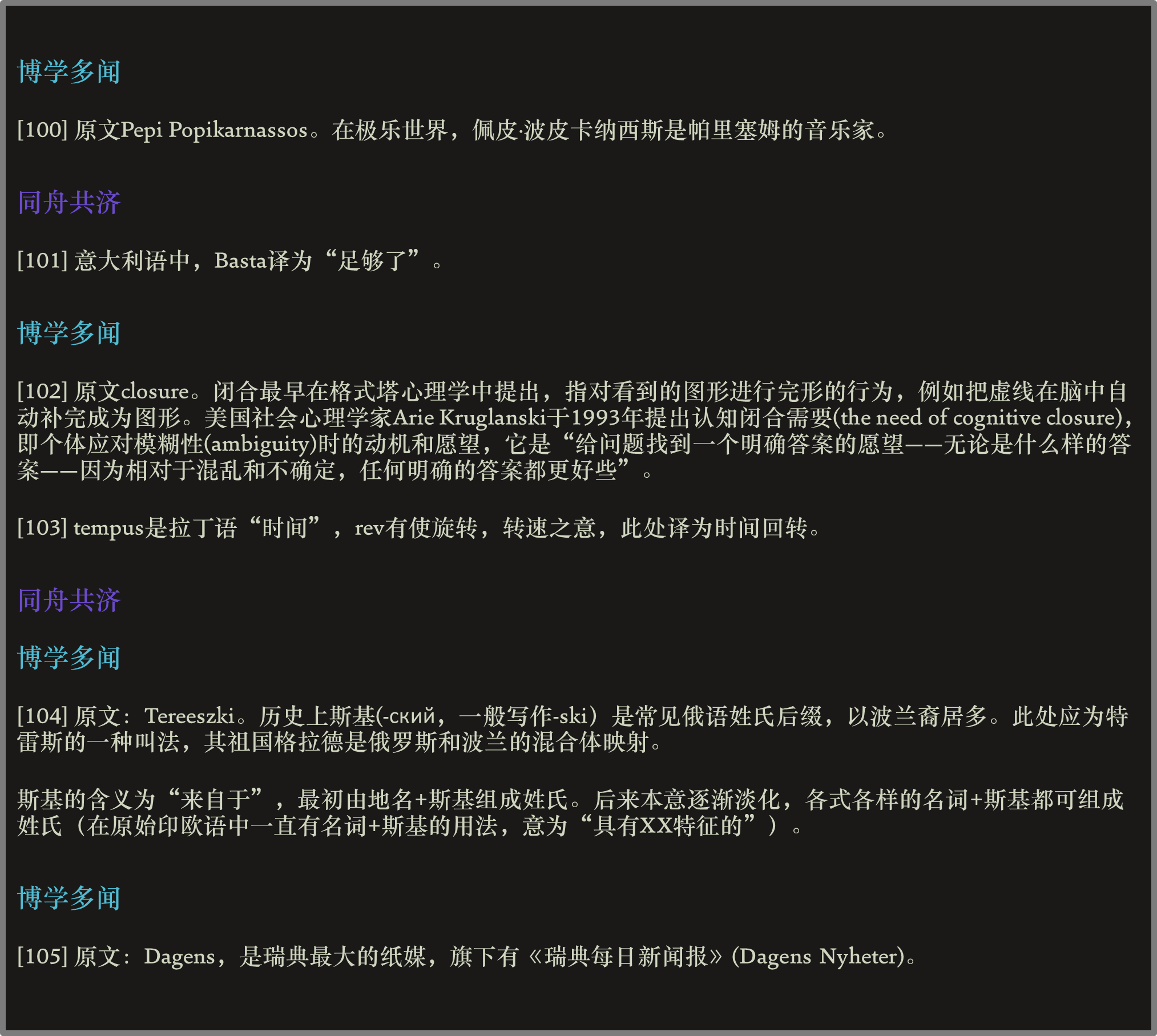
--------------------------------------------
现代舞曲在奥兰治诞生时,小沃尔夫九岁。约翰·豪尔,里特维尔德[107]和阿诺·凡·艾克[108]在礼堂里转动唱片;在维斯帕的维德伦德,世界上第一家迪斯科舞厅,“Das Baum[109]”开业了;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梅西纳的拱廊广场上,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史诗的*场景*后,狂热的民众将西奥·凡·科克加冕为无罪者。沃尔夫背着双肩包从学校回家。他上四年级,因为沃尔夫不在乎老师在说什么,所以他独自一人坐在班级的后面。数学和科学不能引起沃尔夫的兴趣;愚蠢的女孩也不能引起沃尔夫的兴趣;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能引起他的兴趣。在维斯特姆[110]回家的路上,他张着嘴,站在Fonopoe[111]的门口,乐迷在其中进进出出。一台老旧的机器播放着西奥·凡·科克的昏迷混音专辑,乐迷们看着小沃尔夫像着魔一样摇摆和舞蹈。泪水顺着沃尔夫的脸颊流下,整个世界消失了。所有人都在大笑,敬畏地看着小男孩蹦跳,甩动,摇摆,喘息,挥舞和咆哮。“哇,这难道不惊人吗?!”他的手脚在半空中横冲直撞,用手掌拍打汽车引擎盖,他就是不明白:“这为什么能如-此美妙?!它不可能这-么美妙!!!”一个穿着时髦运动衫的推销员从店里走了出来;沃尔夫从旧日之物的灰域里,从跨越人类历史的昏迷回声里走到这位年轻人面前;而他交给沃尔夫一个八声道磁带。封面上写着“西奥·凡·科克/”,“普鲁斯-米特雷西伯爵”。这是沃尔夫生命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认为某个活人对他有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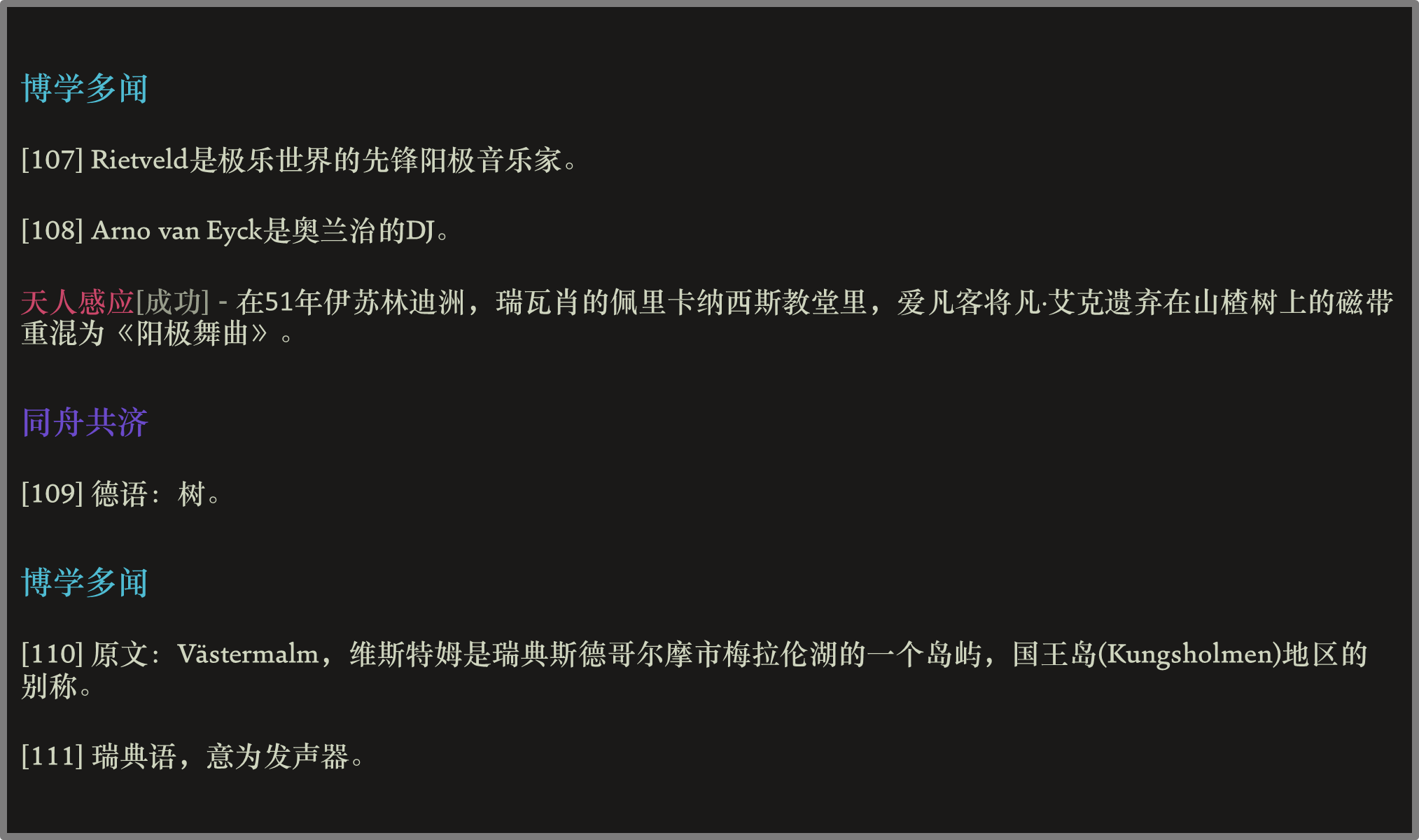
--------------------------------------------
机动车带有沟槽的轮胎旋转着,积雪在车轮下沙沙作响,但伊纳亚特·汗不在那里。十三岁的他,迈出特雷斯父亲乡间别墅的门廊,进入苹果园。天色昏暗,蟋蟀在鸣叫。自我愉悦者把一个八声道磁带放入播放器,两个塑料碟片开始转动。*试音*正在进行中,而九月的夜晚静谧无声,音乐不会传太远。这是二十年后,距离汗十分遥远的地方。空气中充满了香味,他如幽灵般从树下接近男孩,环绕在他的膝盖周围,散发着早熟苹果的味道。汗光着脚走在沾有露水的草地上。男孩们在二楼的屋里睡觉,但他睡不着。他们早上七点半一起去打工了。汗的身体因为建造工程而筋疲力尽,但他内心却无法休息。钱不够。经销商齐吉在电话里抛出了天文数字。300雷亚尔。在经历一番劝说后,杰斯珀把他收藏的系列冒险小说《来自赫姆达尔的男人》带去了二手书店。汗变卖了他的双筒望远镜。
机器心脏的十六冲程燃烧室中发生着剧烈的撞击;在遥远的列敏凯宁,农场窗户上的一扇玻璃在贝斯节奏中颤抖着。*检索*,*检索*…但伊纳亚特不在那里。一颗苹果落到在他面前的地上。小伊纳亚特用袖子把苹果擦干净,坐到花园长椅上。他咬下水果,感受着甜蜜的痛苦在心中横冲直撞,让他呼吸困难。失足的可能性日渐增长,到了今晚终于足够被察觉了。“说吧…你总是能说出很酷的言论。在历史和自然科学…”深绿色的眼睛,难以置信的温柔且兴致勃勃。你确定吗,汗?现在尝试理性思考一下;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贬低得一无是处。
发动机盖冒着蒸汽,引擎传动带在运转,磁带贴着放音磁头滑动。但果园中仍然十分安静。伊纳亚特·汗不相信上帝,完全不。上帝是三千多年前,在伊尔玛,一个叫皮乌斯的人发明的。或许。但现在汗把苹果核扔进树丛里,双手合十,祈祷着。
“请让我讨玛琳的喜欢。上帝,请让我非常讨她喜欢,而不仅是…你知道的,毕竟你是上帝。我向你保证我之后不会再认为是某个男人——来自佩里卡纳西斯的皮乌斯——发明的你。我向你保证,我会相信在时间原点时你就已经存在,用你的…呃…金色罗盘之类的东西,画出了天空和大地。对不起,上帝,不该这样开你的玩笑。但是你看,如果我不能讨玛琳喜欢的话,我真的很难相信你的存在。”
汗抬头望向天空。在他内心的黑暗之处,爱像星辰一样旋转和蔓延。爱,像一只毛色亮丽的猫,蜷缩在他的胃里。对他来说,爱亦是对失去的恐惧。
尾灯的红光在雪地上留下血迹,引擎消音器噼啪作响。绑着链条的轮胎在雪地上发出嗖嗖声,引擎轰鸣了一阵。换挡。音调上升。加速度将莽撞的司机压入座椅中。这个年轻的男人戴着赛车护目镜和驾驶头盔,手指被冻结在操纵杆上。无光的山路从他护目镜坚硬的表面反射出来,消失在车轮之下。
大气层盘旋在列敏凯宁灰域理论灾难区的上空。黑暗的山脉上,被积雪覆盖的山峰切开了地平线。它们的牙齿像油毡推销员的一样裸露在外。在山谷底,空地和云杉林绵延不绝,一辆黑色汽车在蜿蜒的道路上以每小时一百五十公里的速度飞驰。
“靠,这简直有-病!”汗尖叫。特雷斯点头,引擎冒出的酸性工业烟雾充斥在车厢里冷空气中。探员看向窗外,注视着被积雪覆盖的路桩从暴雪中飞过。在山谷底,空地点缀中的一团白色物质若隐若现。汗弹到对面特雷斯身旁的位子上,喝掉酒瓶里的最后一点酒。烈酒刺激着他的感官,他砰的一声撞在车厢的墙壁上。
“没了。”他向特雷斯展示空空的瓶子。另一瓶风味浆果酒出现在汗的手中。旋拧式瓶盖砰的一声弹起。“甜度:25%”。他在齿间磨着糖块。远方,对面的山坡上,若隐若现的灯光在黑暗中闪耀。从星期三晚上开始,所有其他的车辆都在反向行驶,远离灰域理论灾难区。那也是汗,探员马切耶克和疯狂的拉力赛车手肯尼——就叫肯尼——从瓦萨出发的时间:
“你叫什么名字?”
“Kenni.”
“Kenni kuka?”
“Vain Kenni.”
“Kattoo, entroponeetisen romahduksen vyöhyke! Ei voi olla, kuusetkin rupee taivaasen ajautumaan, saa-ta-na, ihan kuin ne sanoi, sen kyllä täytyy nähdää! Ja talot myös!” [112]肯尼在驾驶座上大喊。
“你还好吗?”汗喊了回去。与特雷斯不同,当机器在黑暗中摇晃时,他依然略感担忧,在车速表的淡黄色光芒中,他看到指针指向一百七十迈。
“Hienosti menee, ihan hienosti, en huolehdi ollenkaan!”[113]
“那路呢?路怎么样?”
“Että mikä, tiekö? Ei, hyvin on, en huolehdi ollenkaan.”[114]
肯尼并无huolehdi ollenkaan[115]。相反,他还想要风味浆果酒,而当汗认为肯尼不应该酒驾时,肯尼说:“Äla huolehdi, 好吗? Mä oon puolet tiet juonu jo, muuten mä nukahtaisin. Se autta mua keskitymään, kato!”[116]
道路继续沿着山坡蜿蜒前行,两边是云杉树。肯尼身体前倾,在弯道上维持行进的路线。只有在汽车深陷林中,沿着乡间小路行驶时,汗才获得些许的安全感。车轮下的积雪吱嘎作响,发动机艰难运转着,车窗上布满一圈圈的雪花。深色的树墙在照明灯后颤动。突然间,肯尼拐到路的左侧,汗跳回了他自己的座位上。汽车飞速超过一辆红色的格拉德通讯面包车。在他们被积雪覆盖的照明灯下,新闻团队向他们挥手致意,汗也向他们挥手。
在过去的两天里,汗和特雷斯一直在车厢里喝酒。司机拒绝停车休息。肯尼想要打破一个记录。他的手里拿着一个秒表。这段时间里他们见到的所有汽车都是对向行驶的。此时已经距瓦萨两千公里远,而马路对面的大堵车依然在龟速爬行。郊区的人们前往市区投奔亲戚。他们从汽车收音机里得知,同样的恐慌遍布整个卡特拉洲。因为位于北雪平的磁悬浮列车站,阿尔达变成了每个人都想去的地方。甚至在崩塌的北方高速公路附近的耶林卡,也已经卖光了接下来两个月的车票。无路可出,可能还不如步行穿过北方高原[117]。
渐渐地,一侧的窗外变成穹顶景观,朦胧的山脊从地平线上滑过,云杉树林低伏。深夜,汽车驶入了高速公路,但对向的车流并没有减少;只有在积雪变厚的原野中央,道路才从支柱上降下,那里的田野也因此闪闪发光。汗进入了深度睡眠,他的头靠在一侧的玻璃上休息,而在他们前方的黑暗里,路的一侧是车前灯组成的钻石海洋,而在另一侧,只有寒冷的,空荡荡的高速公路。只有一对红色尾灯加速前往列敏凯宁。他们唯一的陪伴只有军车队,和车顶插有通讯天线单元的国外通讯社汽车。
早上,他睁开眼睛,看见一个被遗弃的村庄从窗边掠过。电线杆间的电线飞舞着,在空旷的郊区街道上,一个乡下女孩骑着自行车。她穿着长裙和夹克。乡下女孩直视汗的眼睛,自行车轮毂上的反光条闪着光。他们已经离开瓦萨边境一千五百公里,前方还有第二段一千五百公里的路程。肯尼开得很慢,你能在车厢里听见车轮下的水坑里,冰块碎裂的声音。女孩挥挥手,拐进居民区郊外的一条小路上。森林中的黑暗将她吞噬,自行车尾灯随着发电机的节奏而闪烁。前方,树木组成的隧道里已经大雪纷飞。于是他们出发了——伊纳亚特·汗和特雷斯·马切耶克,还有肯尼,就叫肯尼,出租车停车场里最硬汉的男人。在经过苏鲁的几个小时,男孩们安静地坐在昏暗的灯光里,观察着。路灯组成的寒冷星光在远方亮起,房子屋顶的瓦楞铁皮塌缩进永恒。随着夜幕将至,雪也越下越大。山脉的黑色锯齿从地平线上升起,村庄愈发稀少,特雷斯提议打开一瓶风味浆果酒。
“不然会变得太压抑了。”
他们经常能在前方逐渐变暗的山脉上空,看到军队的飞艇。有一次,一只铁鸟在桥上嘶嘶鸣叫,尝试用它的聚光灯抓住他们;气垫威胁要把汽车翻个底朝天。但之后那只鸟不见了。只有它的探照灯从黑暗的森林上滑过。这被称为一次疏散。
被遗弃的检查站立在路边,上面的文字“列敏凯宁”发着光。一个混凝土块浇筑的军事路障从马路对面掠过。肯尼把雪链缠绕在轮胎上,然后开车绕过屏障,掀起了一半的土地。从那时起就一直下着雪的冬季轨道,和检察站一起被留在了后面。沥青路渐渐消失,于是一个个家庭乘坐着雪橇,沿着积雪的碎石小路向他们的方向驶来。自童年起,亲眼看着灰域在身后升起,就是他们尊贵的特权。马匹拉着雪橇,带着全部财产的家庭向深黄色皮肤,戴着厚镜片的滑稽矮胖男人挥手致意。
“真奇怪,他们一直在挥手。”汗说,格拉德通讯面包车已经远在身后,压在了肯尼汽车轮底的一团雪云下。不再有车前灯或是雪橇灯笼在黑暗的森林中闪烁。只有那些愿意留下的人被留在了农场中,私人混合车道上,以及停业的乡村商店里。而在黑暗中,灰域悄然逼近。
“Kuuletko sen?”肯尼问道,“Harmaa… se on nyt varmasti harmaa! Mua vähän huolestutta.”[118]
特雷斯和汗聆听着。确实,在风声之下萌发出一种新的声音,轰隆轰隆,一阵令人作呕的,低沉的爆裂噪音。像一道波浪碎裂开来,慢慢地,慢慢地…汗听起来就像是一首歌的开头。他在一场梦里听过它。
“我不在联警工作了。他们让我滚。”特雷斯大叫,手放在嘴巴前比出喇叭状,他醉醺醺的。
“什么?”汗一开始没听清,噪音摄人心魄。他感到身体上的毛发竖了起来,寒意顺着脊柱流淌,就好像他刚刚在一个寒冷的房间里脱下毛衣一样。
“他们让我滚出联合刑警局!”
“我知道!”汗大喊,递给特雷斯一瓶风味浆果酒。“你一直在展示一个叫萨默塞特·乌尔里希的人的警徽!”
“你怎么知道的?”一股酒精味从特雷斯嘴里升起,飘荡在车厢里的冷空气中。
“因为检查点的所有警卫都叫你乌尔里希先生,还有警探乌尔里希,或是萨默塞特·乌尔里希。”
“我拿的证明是一个失踪探员的。我有一大堆。”特雷斯啜饮一口酒,他的嘴唇发红,粘稠的液体从瓶颈溢出,滴落在他的衬衫上。“证明,我是说。失踪的探员也是。在喀琅施塔得,我出示了‘马切耶克’,否则,他们没法发现我的行踪。我想我要带萨默塞特·乌尔里希的去列敏凯宁,并留下痕迹,如果有能力的话就来抓我吧!”
“你是个通缉犯,还是…”
“是,是,我没跟你说吗,哈?有个人因为那档事还犯了心脏病!”
“ZA/UM,还是…”
“是的,就是它。”特雷斯说,他看到了前方的拉力赛之王肯尼,一团黑雪缓慢地飘向天空。在云杉树被自己的树根撕裂时,大地咔咔作响。树木在尖叫,矿石浸泡在其中,就像在牙医的椅子里一样。巨型石灰岩飞向空中,而在这之上更遥远的地方,黑暗里,第一批树被灰域包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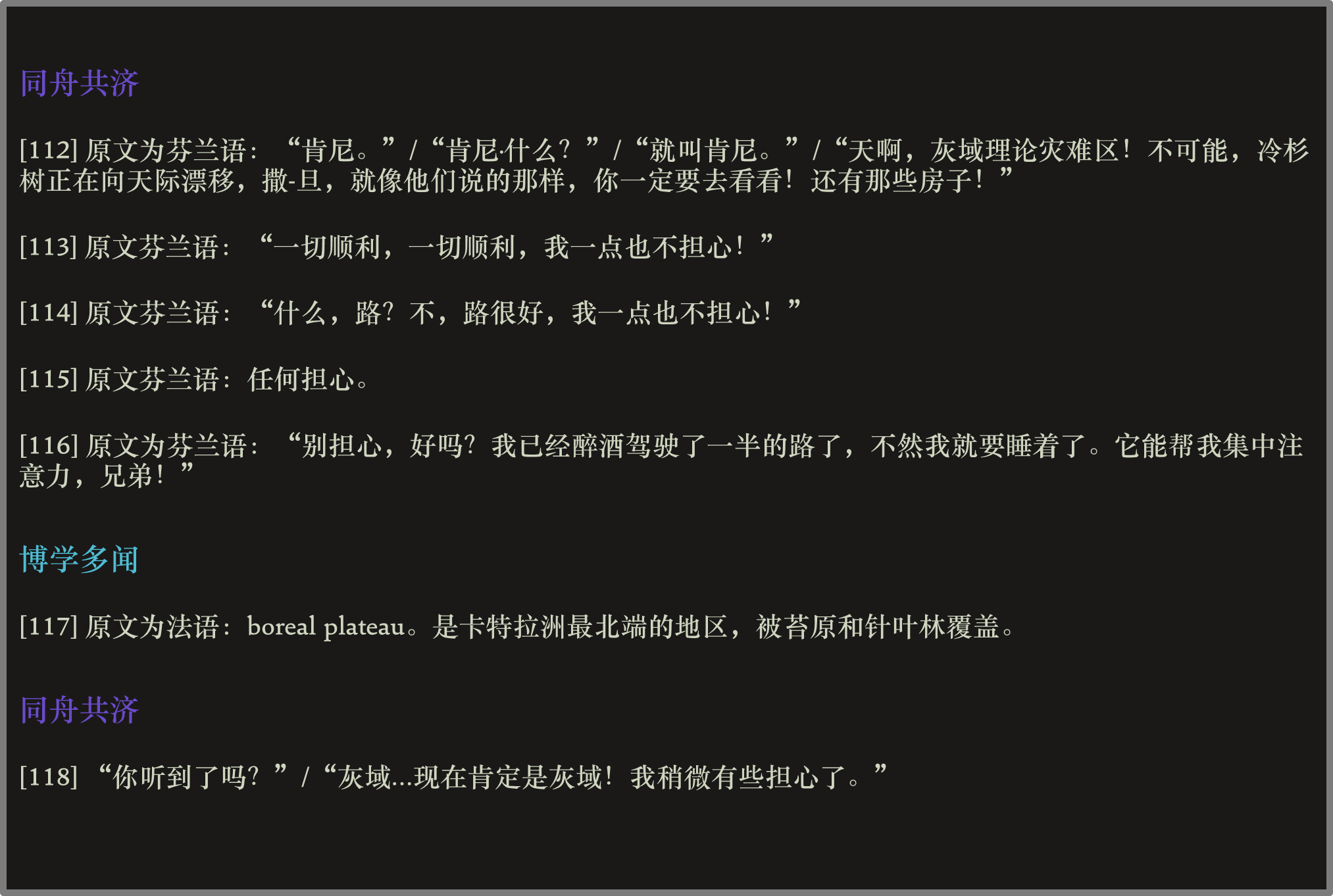
--------------------------------------------
两年前。
汗在睡梦中听到了电话铃声。这是一个冰冷而陌生的声音,一次假醒。他在母亲的地下室里睁开双眼,只穿着睡裤和拖鞋从床上起身。他感觉到某些异样,但还是走了过去。在梦里,周围的地下室变得很奇怪,物品摆放在错误的地方。娜佳·哈南库尔在他的挂坠盒里露出可怕的微笑,贡子手中的并非罗盘,而是一个永生桃子,它发霉了。
房间的中央,一个空的玻璃展示柜摆在台面上。汗不敢看向那个方向,在它的虚无里有个他无法忘却的东西。不对劲。铃声听起来也是——它从楼上的走廊发出,穿过公寓的黑暗。
他走上楼,走廊在他周围沉睡,墙上的电话响着铃。他畏惧地伸出手。他拿着塑料听筒的手渗出汗液,有些东西禁止他接起电话。但他必须接,这很重要,每一通电话都有意义。于是他从固定钩上拿起电话,随后走廊里充满了灰域的静电干扰。它弄疼了他放在听筒旁的耳朵。
“你好?”汗试探道。
但没人回答。
“你好,你是谁?请告诉我你是谁!”他重复着,男人的声音愈加恳切,静电干扰就愈发严重。直到他被它击溃,耳腔内的压力消失了,只剩下它的核心中起源未知的震颤。静默像波浪一样流经血肉。它寒冷刺骨。
“求你了,”滚滚的泪珠从汗的眼中落下,“告诉我你是谁…”
“你知道我是谁。”振动发出孩童的声音,诉说着可怕的事情。汗开始颤抖,猛缩到走廊的角落,听筒还在他的手里。
“这不是你!这不是你!”他哭了。男人的现实身体随着精神抖动。他在床上醒来,痛哭流涕。他的耳朵嗡嗡作响,而梦境还在清醒世界里持续着,只是飞艇模型回到了展示柜里,娜佳不再微笑,贡子拿着罗盘。
展示柜的顶部是他母亲做的干掉的奶酪三明治,和冰凉的咖啡。还有一个信封——一封来自格拉德的晨间磁报。寄信人一栏写着“萨尔扬·安巴苏姆扬”,里面只有一把钥匙,纯金打造,纷繁复杂。
他还有两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