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想說,我和你就像是簡·愛和羅切斯特。我是落魄的簡·愛,你是憂鬱的羅切斯特。”
“可事實上,我並不是簡·愛,沒有意外之財,也沒有堅定的信念。”

前言
1920年,是有史以來中國春節到來最晚的一年。
那年一月,國際聯盟第一次召開會議,簽署了歷史上著名的《凡爾賽條約》,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正式塵埃落定。

那年的法國,是戰勝國,那年的花都巴黎,是自由、平等、博愛之都。
那年的中國,仍處於新思潮與舊觀念的矛盾與衝擊之中,一眾有志之士篤信,唯有去往那些有先進思想的國家深造學習,才能救得了彼時的中國——彼時,一陣赴法勤工儉學之風在中國掀起。
在如此這般的迷茫時期中,一位名為“廉豐”的青年被自己所屬的封建家族送往法國留學,而又在那所謂最是自由平等博愛的花都,一場名為浪漫與華麗,實則矛盾而骯髒的戲劇正緩緩拉開歷史的幕布——
不為人知的故事,即將開始。

《花都之戀》宣傳圖
唯美而又富有質感的花都百景與人生各態
當初第一眼看到《花都之戀》的宣傳視頻時,我便覺其美術風格特別鮮明——大概是緣於看起來有一種油畫般的感覺?

這種感覺在遊戲的女主角愛麗絲身著勒肉的拉丁舞裝時尤為強烈,裸露的肌膚與光滑的人體質感相襯之下,雖然角色的服飾並不繁綴,卻有一種別樣而醒目的視覺衝擊,或者說,是一種非常鮮明的肉感。
當然,並不是說《花都之戀》的美術非常驚豔或精細,只是在當下看遍了遊戲中服飾繁冗而掩蓋了大部分肌膚的女性角色後,兀地見到一片還頗有質感的雪白,的確讓人眼前一亮罷了。

除此之外,《花都之戀》的背景畫也別有一番趣味——有不少取自法國真實地理位置與建築,如塞納河、路易中學等——雖然限於製作組經費原因遊戲場景並沒有畫的較為精細,但仍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玩家巧妙的真實與虛擬交融的體驗感。

遊戲場景“路易中學”
帶有哲思,而滿載歷史韻味的浪漫故事
歷史,對於我們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麼?也許所謂“歷史”與大多數人的生活軌跡少有交集線,又或許因為學業不少人也不得不與“歷史”產生交匯,但換個角度來想,我們所經歷、所生活過的每一分一秒,大概同樣也能稱之為“歷史”吧。
話題拉回來,筆者個人認為《花都之戀》雖然僅僅是新人制作組的出廬之作,不過其文本,乃至於整個故事,卻意外地經得起推敲,並且含有一種獨特的韻味在其內——這種韻味,名為歷史。

猜猜出自哪款遊戲?
那時的中國,名義上迎來了新思潮——1919年恰爆發了五四運動,此後,又有一大批有志之士倡導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如果看過《覺醒年代》的朋友,估計通過陳延年與陳喬年兩位青年便不會對勤工儉學運動感到陌生),可實際上呢?彼時之中華,仍處於軍閥混戰,封建未散的年代,直皖戰爭、兩廣戰爭,一場場軍閥之爭仍禍害著百姓。而赴法的學子,在那時卻也不是那麼好受的——德國是戰敗國,但法國彼時便真的可以稱得上是戰勝國了嗎?物價飛漲,工人失業,剛建立起的社會保障彈指間灰飛煙滅,那些原本便處在社會邊緣的人呢?又有誰,會去在意他們的死活呢。
1920年,對於法國來說,也並非是個好年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法兩強衰落,俄國內戰仍在持續,德國處於一片混亂。巴黎的光鮮亮麗不過是歐洲最後的餘暉罷了。”那時被認為觀念先進的西方尚且處於這般景況,要動搖千年根基的中國又何嘗容易,幾多前賢為中國的前途絞盡了腦汁,而我們的主人公,處於封建大家族的廉豐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我的懷疑:救國,到底要走怎樣的一條路?
這是故事的其中一個矛盾,也是那個時代的矛盾,關乎信仰與懷疑——不曾活在那個時代的我,並不能感受彼時之人的迷茫,但也許笛卡爾說的沒錯,“我思故我在。”沒有懷疑,又如何更堅定地確立自己的信仰?那個時代的他們,處在萬千懷疑當中,他們或許沒有選擇出最正確的那條,但毫無疑問地——他們踏向了能拯救民族的那條路。

此外,遊戲中的末尾,即攔截諸會長與王秘書攜帶贓款逃離一段,解讀起來也饒有趣味——作為所謂“正義”一方,褚會長被廉豐義正言辭地批為“惡鬼”,但卻不知諸會長的家人正是被廉氏家族剝削的一份子,兄弟姐妹被餓死,父母拼死拼活在廉氏家族的工廠手底下做工,才勉強養活褚會長一根獨苗。
“你說我是敲骨吸髓的惡鬼,”
“那你呢?來到巴黎上著最好的中學,談著浪漫愛情的——大少爺?”諸會長眉頭舒展開來,而廉豐的心頭卻被重重地錘擊了一番。
底層、工人、剝削乃至壓迫;少爺、無憂無慮的生活與——我。
難道,“我”也是惡鬼的一份子嗎?不可能,不可能,我明明是為了救亡圖存的事業而來到這裡的……不可能,我明明是在與敲骨吸髓的惡鬼做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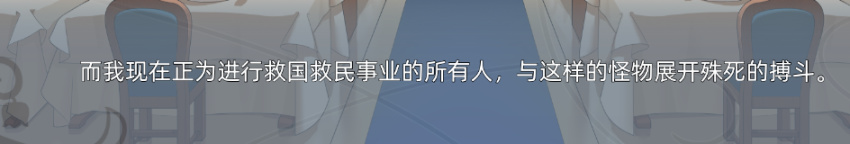
這一段劇情又引出了另一個矛盾——個人與環境,這在1920那個年代並不稱得上是普遍的矛盾,可對於廉豐這類人而言,卻是一套無法避開的枷鎖,一方面,他們擁有著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意識,是思想先進之輩,另一方面,他們卻因階級之差,未曾知曉自己生活的優渥是建立於剝削之上,這是環境之悲,也是命運之悲。他們間接地剝削著底層的人們,他們能稱得上是惡鬼嗎?難講,他們為國而繼命的責任同樣也盡到位了,正如恩格斯出生在一個富有家庭,但他仍為無產階級的大眾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只不過,對於這類前賢本身而言,也許倒要作一番自我的思想鬥爭,崇高之於精神,汙濁之於時代,這是他們最令自己痛苦的詛咒——活在那個骯髒的社會,自己雖為最艱難的使命而前行,身下卻早已踩滿了自己所欲拯救者的屍骨。

法國蒙達爾尼會議留影
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在攔截諸會長和王秘書逃離這一段劇情之後,並未直接進入審判終章,這之間還穿插了一段有關女主角父親皮卡爾的故事——皮卡爾是一位法國軍官,在他年輕時,他擁有著幸福美滿的家庭,漂亮的妻子,在軍中不低的威望,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撫慰民心,又或者說,為了一個所謂的虛偽“交待”,政府上頭頒佈下來一個任務,處分一位猶太籍的下層軍官,靠著一些不確鑿的資料,要求皮卡爾作為審判員親自為這位下層軍官打上間諜的罪名。那時的皮卡爾十分年輕,又意氣用事,因為對方是猶太人,憑著先入為主的觀念,他輕易地處分了對方——在大庭廣眾之下,取下了對方所有的榮耀,無論是勳章,還是軍服。
可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在皮卡爾升職之後,他再一次翻看往昔的案件,那時的他再看到自己親手處理的這一案件,背後其實是政治的把戲——或許早在審判時他也已經猜到,只不過,他還沒有勇氣去面對這份骯髒。
他決定著手再次重新處理這一冤案,他想為那位猶太籍的軍官再次奪回公正。
“如果,我是說如果,”皮卡爾不禁喃喃道。
“如果連審判的觀察員都保持著沉默,那麼還有誰,能為那位無辜的人,挺身而出呢?”

在此後十年,皮卡爾專注於為那位猶太人平冤,因此,他也成了政府眼中的一根刺,他的申訴信多次上投,卻都石沉大海,甚至於,他還莫名其妙地被派往了前線,經歷了九死一生的生活,即使這樣,回來後,皮卡爾還仍在堅持為那位猶太人發聲,而逐漸地,他也在社會上得到了些許支持——可為此,他回家的頻率也越來越低,他能感受到,家中妻子那種幽怨的眼光,年少孩子陌生與頗有隔閡的舉止。
這一切,又是否值得呢?
終於,他的聲音得到了回應,上頭徹查了此事,還了那位猶太人一個清白,但當他時隔多年再次推開家中的門,僅剩目光冷冰冰的僕人——
在此期間,他的妻子終於耐不住寂寞,跟一位英國人離開了美麗的花都巴黎,他的女兒也不知所蹤。

皮卡爾疲憊地坐在自己的房間,日復一日,只是望向窗外,望向這片自由、平等、博愛的土地,十年的努力,十年對理想與正義的追求——換來的不過是滿目瘡痍。
時間不知道過去了多久,皮卡爾如同雕像一般坐在那裡——至少他在留下的信中是那麼寫著的,直到門鈴響聲將他從恍惚中拉回,他麻木地走向門口,麻木地開門,麻木地向一位猶太人問好——
那是,自己為之伸冤的猶太人?是數十年未見一日自己卻始終為了這之而奔波的猶太人,
那位猶太人看著皮卡爾的臉,眼神真摯,說出了一句簡單地不能再簡單的話——
“謝謝你。”
……
坐在桌旁的皮卡爾手執著筆,他思考了許久,寫下了這樣的話:
“愛麗絲,當你看到這句話時,我大概已經不在人世了,”
“我有預感,這次被派往前線,也許是我此生最後一次了。”
“我有些對不起你,在你年幼時,沒能給予你一位孩子應該體驗到的,父親的關愛,”
“但我想讓你明白,你的父親這輩子沒有辜負理想,沒有辜負正義。”
“最後,我想獻給你,或者你遇到困難的朋友幾句話,也許這能夠幫到你們。”
“理想並不只是空洞的,它從對現實的不滿中而來,向著在現實中實現而去。”
“也許理想永遠不會有徹底實現的一天,但是在這永恆的追求當中,千千萬萬個人,會因追求理想的人,而從枷鎖中掙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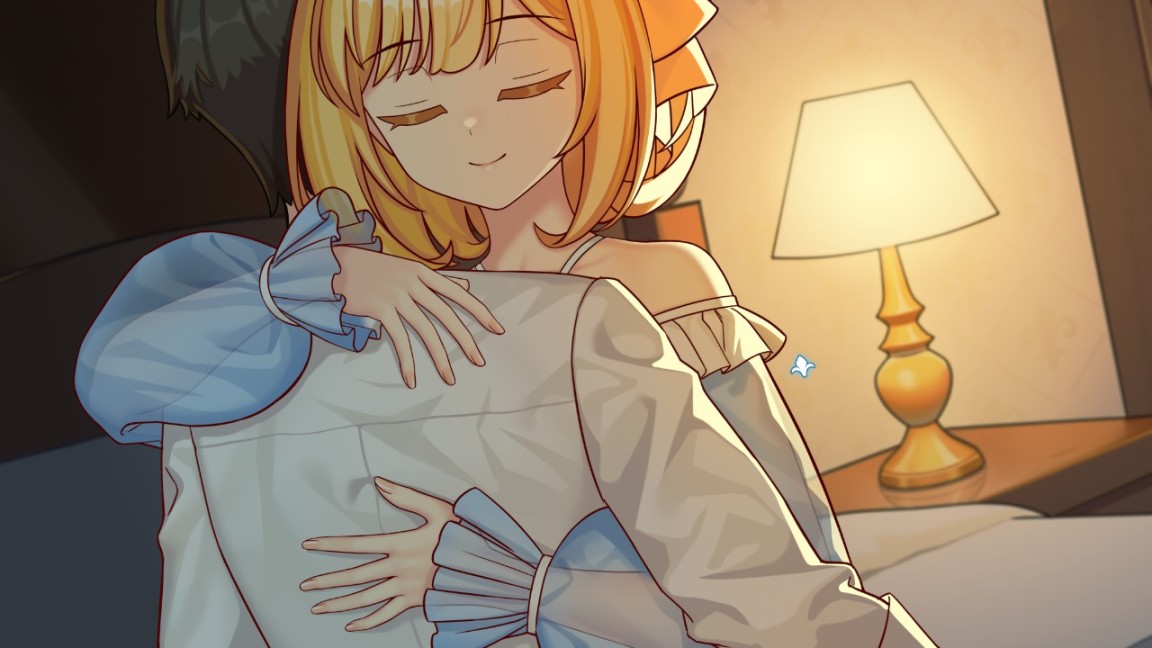
最後,我還想說說關乎遊戲內文本與文學作品的結合——《花都之戀》的劇情始終與兩本書串聯著:《娜娜》與《簡·愛》。興許有沒看過這兩本書或其中一本書不曾涉及的朋友,那麼在這裡,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兩本書的大致劇情:
《娜娜》講述了主人公娜娜因一次充當戲劇主演的成功,讓當時巴黎上流社會的男士紛紛拜倒在其石榴裙下,繼而成為花都紅極一時的交際花,把追求她的男士的錢財一口口吃掉,使他們破產甚至於命喪黃泉。但諷刺的是,娜娜最後也因天花病而死,她一生的興衰,便是第二帝國墮落奢靡社會的真實寫照;
至於《簡·愛》這篇流傳度較高的文學作品,講的則是女主人公簡·愛在生活中自立自強,逐漸認識憂鬱而富有的羅切斯特,與之墜入愛河,卻又遇到一系列曲折,但最終仍與失明的羅切斯特廝守終生的故事。
兩本書其實是一個絕妙的對照——墮落而臃腫,任憑錢如小河般從自己大腿流入的娜娜,與自立自強自愛的新時代形象女性簡·愛。放在《花都之戀》的故事裡,娜娜是什麼?是戰後的法國社會,上層社會驕奢淫逸、腐朽墮落,住在金碧輝煌的富人區,過著朝不慮夕的寄生生活,那些亞非裔,卻只能寄居在骯髒的小巷裡,遭受警察不公平的對待,吃了上頓而沒有下頓;大批失業的工人,坐在破舊的酒吧喝得面紅耳赤,面對著隨時可能被解僱的處境,只能苦笑了之——他們,是巴黎光鮮的白衣之下,不能被人揭開的,骯髒的塵灰。
1920年的巴黎,是自由平等博愛之都,但如果你嘗試透過塞納河畔的倒影,相信你也能看到,這背後,藏著的是一個多麼骯髒糜爛而又令人紙醉金迷的慾望怪物。

《娜娜》
而《簡·愛》在《花都之戀》的故事裡充當的角色也頗有意思,從某個角度來看,書中女主人公簡·愛實際上便是《花都之戀》中幾位主要女性角色的剪影,無論是愛麗絲或是林琴,她們都是獨立自主而知書達理的新時代女性;但從整體來看,我們卻能意外發現,廉豐與愛麗絲的愛情實際上便是一場“簡愛”式的故事——當落魄的芭蕾舞者遇上封建家族的少爺,當自立自主、不忠於慾望的新時代女性愛麗絲遇上夾雜於封建與理想之中央的赴法留學生廉豐,這或許是一場有些淒涼,但總歸是美滿的愛情故事,為了自己的理想,他們最終手捧鳶尾花,一起踏上了前往救亡圖存的道路,此處,在我遊玩時可以說算是觸動了我幾分,不僅是因為這種崇高的愛戀,而更是因為這種,在命定的歷史前,義無反顧與之反抗的精神令人而感動,這讓我想到無數前賢在那時的大義凜然——
因為他們,歷史的齒輪得以轉動,中華民族的命運得以改變,如若有機會,我也願意扭動反方向的鈡,回到那時,回到那個為理想與正義而奮鬥的時代,為國家,為民族出我的一份力,灑我的一身血。
說起來,似乎引言看的有些莫名其妙,在尾聲,我便分享一下引言的出處以及我自己一些亂來的情感抒發吧——
“我本想說,我和你就像簡·愛和羅切斯特。我是落魄的簡·愛,你是憂鬱的羅切斯特。”
“可事實上,我並不是簡·愛,沒有意外之財,也沒有堅定的信念。”

1920年的巴黎,經濟蕭條的戰後巴黎,或者說,看似是戰勝國的巴黎,真的沒有下一個簡·愛與羅切斯特了嗎?夢終會醒來,但當遠洋而來的中國留學生碰上了落魄的芭蕾舞者,當他明白那個最講求自由平等博愛的巴黎並非只有盧浮宮、先賢祠與埃菲爾鐵塔,當他看到落魄悲傷的戰後軍人,看到為生活奔波勞碌的非洲裔,看到酒館裡的所謂新銳藝術家與那群善意的酒鬼,又是否會為自己的到來而感到後悔?
1920年的巴黎,是自由平等博愛之都,是骯髒醜陋罪惡之都。
致謝
感謝看到最後的你,感謝你能聽我一長段的絮絮叨叨直到此刻,
這並不是一篇為了誰而作的文章,這僅僅是一篇,因為電子遊戲而產生觸動,繼而衝動寫下的有關浪漫,更關乎歷史的雜文罷了。
歷史輪轉,時至今日,我們仍在為自己的理想與正義而奮鬥著——希望每個人都能成為在最後關頭清醒的廉豐,都能成為自立自強的簡·愛,能成為人世清醒的皮卡爾。
在理想與正義的路上,懷疑不可避免,慾望長存世間,而我們能做的,就是清醒地活在這人間。為了那個千萬人心中的夢而奮鬥,為了不回到那個迷茫的1920,堅定地手捧聖潔的鳶尾花,踏向充滿鏽跡的道路,正確地走下去。
此致諸位:再次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