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心灵的激流冲破宇宙的绝对控制时,游戏才是可能的、可以想象的、可以理解的。” —— 赫伊津哈 《游戏的人》
二十一世纪初期之前,“游戏”这一概念不像今天有些时候那样,是意涵丰富的大熔炉,无论是文学、艺术、哲学,还是历史、数字人文、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者都忍不住尝试将游戏纳入到自身领域中玩弄一番,进行一些意义阐释、理论导向……那时候的游戏仍处在“理论之前”——它既没有清晰的定义,也没有被收拢到人文学科或教育体系中。它是一个高度重视规则却十分无序的产物,人类对欲望、历史、宇宙和自身无论最深刻还是最肤浅的想象,都可以作为“游戏”而出场。它可以是感人的、狂暴的、史诗的、纯爱的、色欲的、浪漫的、竞技的、恐惧且战栗的……它甚至可以是反游戏的、不好玩的。
游戏的概念泛指了自古以来一切类型的游戏,有时候它往往指向一种游戏或者游玩精神。前者是具有实体的,在漫长的历史中起起伏伏了许多种游戏类型,如各种棋牌类、竞技、小孩子的玩具等等;后者则涵盖更广,指向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与倾向,这样一种游戏精神使得所有人类活动都可以变成游戏(人生如戏啊),这一点在现代以前尤为常见。它符合人类对高级生活的一种想象(才子佳人、英雄相惜、骑士浪漫),现代以前,这样一种想象长期被贵族、英雄、名士等掌握。想象通过文字、故事的形式流传下来,好的词与上层人士挂钩……(对这样一段历史演绎感兴趣可以看维柯的《新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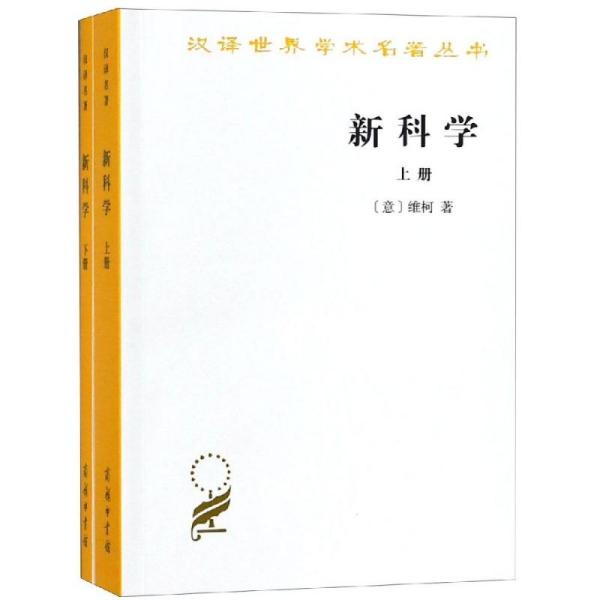
本书旨在谈历史上的“诗性政治”,文学/语言是如何塑造人的政治意识的
但随着现代的到来,工业化、民族认同、人道主义、平等等概念使得人变得“同质化”,英雄和骑士消亡了。旧的人及其文化,尤其是文化中的游戏属性被终结了……“游戏精神”也被现代社会警惕、摈弃。在今天,一个人如果宣称自己秉持着游戏精神去工作,那他同时否定了一种价值趋向,会被主流社会警惕甚至摈弃。游戏与游戏精神被捆绑在一起,游玩的心态应该只有人在进行特定游戏的时候才可以合理拥有。这种文明状况引起了一些怀旧者的哀叹,其中便有“游戏”概念的奠基者。
当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ha,1872-1945)在其名作《游戏的人》(Homo Ludens)中将人类文化历史反转成了一场依靠人类(其中的佼佼者)的游戏精神而推动的游戏历史时,他似乎不愿多想现代之前的“游戏人”仅仅占有多么小的一部分——当英雄们在大战过后惺惺相惜的时候,更多的无名者却成了高贵者游戏的代价。因此在赫伊津哈的游戏论点诞生伊始便有批判者批评其“旧文人”式高雅假想和对现代文明的偏执怨恨。然而随着战争将现代文明破产重洗,文化趋向后现代的多元与重构,游戏精神也自然抬头……一个更特别的技术产物——电子游戏——出现了。
电子游戏是游戏吗?它被游戏包含,还是游戏是它的一部分?赫伊津哈曾给出游戏的四个特征:
- 自愿性(游戏是玩家自愿自发参与的)
- 超现实性(它尽管在摹仿现实,但它超越甚至远离了现实时空)
- 限制/隔离性(“游戏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范围内“进行”的。游戏自有其进程和意义。”)
- 规则性(游戏创造了规则,游戏就是规则)。
电子游戏的确符合这些特征:它是玩家自愿参与的、遵守一定规则展开的、在计算机程序中的、脱离现实的精神活动。然而其他人类精神活动似乎也未违背这些特征——以读小说为例,读者自愿参与其中,接受一个与他现实生活无关的虚构故事,故事自有其时间线和进程,同时它有一些潜在的规则束缚读者(语言语法规则、叙事规则、联想、比喻等文化符号规则等等)。读小说是不是一场游戏?赫伊津哈一定会给出肯定答案,事实上他在《游戏的人》中也专门谈了诗歌、哲学、艺术的游戏属性。
那么究竟什么是游戏?电子游戏又与游戏有怎样的关系?赫伊津哈已经提出了一个十分“怀旧”的观点:文明就是游戏,在游戏中人类建立了文明,没有游戏,文明也不存在。在他看来,人类文明的数千年历史可以被视作人类的游戏历史,可惜文明在步入现代后变得严肃、变得拒斥游戏……游戏的精神没落了。
而现代文明留给游戏的是一种业余的、休闲的、被压缩和局限的短暂生活,这种狭隘的业余游戏远远无法满足一个人的游戏精神。对英雄、骑士、君主的身份想象,对战争、爱情、权谋的渴望,对未知体验的期待……尽管文学与电影填喂着渴望的心灵,然而人们想要的更多,直到在电子游戏这一载体上,想象的欲望得到了满足的可能。

muses,艺术之神
电子游戏依赖信息技术而诞生,且技术至今仍在拓宽它的可能。它吸收了传统的八大艺术,与图像、音乐、文字深度联结,在电影这一它不久远的前辈之上,它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摹仿领域——交互性(interactivity),电子游戏的魔力正是其对交互的摹仿。
人无时不刻与世界发生交互,这个交互可能是物理的、精神的,可能是与他人的、自我的,可能是现实的、虚构的……当玩家第一次操控游戏角色行走或跳跃时,他获得狂喜是对交互模拟的狂喜:无论行走还是跳跃,在物理规则下它的进行呈现为我们所熟悉的形态,我们在游戏中品尝了这一交互。直到今天电子游戏行业仍在不断拓宽交互的可能,无论是物理的还是精神的,这些都被玩家所期待。
随着它越来越逼真,它对交互的模拟越来越混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它开始在交互上突破真实,它强调第二自然、第二宇宙、人工智能体。正是因为它属于现代文明中业余的、娱乐的游戏领域,它无需对严肃负责,也不需要对文明负责。
在游戏中,想象拥有了最大的活力。
今天的电子游戏既遭受了巨大的污名化,同时被认为包含巨大的变革潜力(游戏戴上了“个人性”的最大桂冠,而曾经摘享桂冠的“诗、小说、电影”缪斯们则递次冷清)。像历史上众多被污名的文化载体一样,游戏被视为一种远离现实的精神闭环活动,对游戏的发问有:它既然对现实(物的)世界没有什么用,那它又能有什么用呢?难道它会让人更好吗?如果不能,那么我们要禁止、至少也要节制它。更多有识之士觉得游戏只是“游戏”而已,适当“玩物”无伤大雅,但游戏给游戏者的巨大诱惑或“上瘾性”则令人警惕。人们厌恶低级趣味的、败坏道德的、坏的游戏(文学、电影、视频……),小说曾被指摘与批评了数百年,如今则被许多人担忧其消亡是否会导致文化的堕落与品味的下降。
时代似乎变了,在今天与可预见的未来,当游戏成为更加本体的“学科”,游戏附着上民族意识、现代性、人文的乃至政治的诸多筹码,一扇巍然耸立学科大门终于冠上了“游戏”二字。其中有诸多游戏知识分子谈笑执笔,又有野生的大师散发惊人的慧思。游戏逐渐被细分为众多品类:古典游戏、严肃游戏、通俗游戏、民族游戏、批判现实的游戏、元游戏、表现主义游戏……今天的游戏设计者已经有意识地涉猎与制作这样的作品,或许将来提供给游戏学科研究的,是一份并不野生的系统性遗产。
以上事件尚未完全发生,今天游戏的状况也暂未到达可以被人文学科完全接管的时候。如果对标“书籍”,属于游戏的“印刷术”还未到来。但游戏制作门槛仍被降低到了可供个人作者发挥一席之地,足够表现思考的时候。
然而,也正是因为游戏的技术正在发展(尚不成熟),游戏这一媒介仍处在分娩的阵痛与狂喜的时刻——如果说几十年前玩家发现自己的一个按钮可以让马力欧“跳起来”而因此进入一种狂喜阶段,那么直到今天,曾因游戏技术的发明而狂喜的游戏人仍不愿放弃对分娩狂喜的期待,这种期待类似于第一次看到印刷文字、电灯、汽车、飞机的喜悦,这正是文明对新生儿的期待——它即肩负着传统,又被期待着变革。在步履蹒跚中,它必将成长、成熟、年老,当它过时后,文明将会抛弃它,转而关注另一个被选中的孩子。

视觉小说《The Life and Suffering of Sir Bran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