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碎骨者的困境
统一尤克本身并没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很多兽人以前就这样做过,还有各种各样关于战争军阀们在某个时间点声称这个小世界属于自己的歌谣。但任何一名老迈的猛汉都能整个吞下一只钻孔史古革。真正的壮举是干掉一个。或者至少阻止它自己乱闯。
碎骨者想要群星。但是为了得到它们,需要所有那些他刚刚聚在一起的部落友好相处,并且通力合作。他想灌输给它们的想法是斯莫克-安哈-斯尼亥克-纳克哈。这是句屁精话:意思是“现在藏起来,明天再捅他们”。比如,倘若你想要别人的东西,但偷取它会使你受伤,你就会藏起来制造武器,直到你发现有机会伤害另一个人,并把那东西拿走。
它之所以是一句屁精话,那是因为其对兽人来讲毫无意义,或许除了血斧。看看那个“咬住-咬人者-的脸”;他恨你们入骨,但他知道如果对你们好,他会变得更富有,下次就会有更多的东西用来杀掉你们。咬仔的怪异出自于此。

敲黑板,这里在前文有所提及,是咬仔的兽人语名字
但大多数兽人都不是咬仔。如果一个兽人看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会一直努力直到得到它,或者直到他死在战斗中。而且兽人想要的通常只是一场战斗,所以他们看不到等待的意义。于是先知为自己安排了活儿干。
有一段时间,他找到了其他战斗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离群者、叛乱分子、以及那些声称创造了他们自己、废料、氏族的兽人们。当他们耗尽后,就轮到了太空。尤克轨道上的东西很少——大部分是古旧的人类空间站,但很久以前就被兽人们占领了,长久以来他们在那里过着自己奇怪的生活,从地表无法到达。直到现在。斯纳茨哒咔,事实证明,他一直在建造巨型炸药运载火箭,因为他总是幻想着一场核战争。不过随着弹头被装有椅子的大金属板条箱所取代,它们被证明是相当不错的突击运输舰,很快,尤克的轨道也归于了碎骨者所有。
在那之后甚至尤克的孪生卫星也落在了他的手里,连同居住在上面的那些奇怪、瘦弱、没有氏族的兽人们。舰船也一样——这个星系中没什么可回收的东西,但仍有一些笨重的战舰,它们已经空置着漂流了许多许多年。舰队让碎骨者充满希望,他可以通过发动入侵该星系的外围世界来延长他的太空战争。但后来外部的世界找上了碎骨者。
有几百艘舰船。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当它们开始靠近时,其等离子体喷流让尤克天空中的星星看似数量增加了一倍。斯纳茨哒咔的那些火箭刚刚又被改装回炸弹用作将它们变成灰烬,就在这时,卫星外的一个血斧间谍站传来消息:这些船悬挂着碎骨者的旗帜。当俺看到投影在王座厅墙上那些“让-东西-更大”机器的照片时,俺的血液仿佛发出了绿色的光芒:是俺之前用先知的血画的那幅画,涂在半英里高的战舰撞击颌上。

兽人的太空船
那些外部世界又小又冷,破烂甚至比尤克还多。但它们之间有一大群兽人,在碎骨者征伐期间,他们开始收听到从尤克发出的电码信号,他们想来分得一杯羹。所以他们来了,人数之多,俺简直不敢相信,这预示着一个问题:“然后俺们杀谁?”
那时先知已没有办法回避他的问题:他已经没有战争了。这意味着很快他的各支军团将发动自己的战争,除非他能说服他们接受那个怪诞的“斯莫克-安哈-斯尼亥克-纳克哈”想法——现在藏起来,明天再捅他们。这是他面对过的最艰难的一场较量。
“搞哥没有给俺做这件事的工具。”先知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对俺说道。他在头目大厅露台旁的房间里踱步,就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史古革巨兽,他想思考的时候就会去那里,除了俺,别人都不允许跟着他。
外面,锈钉那持续不断的氏族街头大战仍在激烈进行着。但是那天晚上,从战斗中传来的咆哮声、枪炮声和刀锋的碰撞声让人毛骨悚然。自从统一以来,它听起来一天比一天不快乐,一天比一天愤怒。尽管碎骨者曾用自己的几次殴打巩固了那条大规矩,但它每天都在经受考验。
当晚,那场争吵就像一整池的液态史古革燃气在等待明火。并且头目知道,如果他用拳头蹚进去,就可能成为点燃一切的导火索;一股如兽人狂怒般迅速蔓延的火焰,将他那羽翼未丰的帝国夷为平地。所以他是对的;搞哥给予的天赋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但俺不想被踢飞穿透墙壁,所以俺闭上了嘴,躲在一个角落里,就像俺命中注定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俺和碎骨者的谈话方式 - 俺躲在那里,啥也不说 - 并且它成功了。
“俺知道,俺知道,”头目不耐烦地说道,愤怒地用爪子戳俺,就好像俺说了什么似的。“毛哥会有答案。而俺会找到的。俺只需要想……想……想想想西西西昂昂昂……”
就像有什么东西突然扑向他。或者直接刺进他的脑袋里。碎骨者那巨大的身体扭成了一个弯曲、僵硬的弧形,足以举起一辆卡车的肌肉群同时猛烈地各自收缩,他那只完好的眼睛也凸了出来。然后他开始颤抖。
“呃啊啊啊啊啊啊。”先知说道,试图通过紧闭的下巴来咆哮。之后,随着破裂的一声,他的一颗尖牙粉碎成了一团黄色的碎片。
那头痛无疑越来越严重了。开始于他在计划征服这颗星球的时候。但当时只是短暂的抽搐,现在变成了每次能影响他好几分钟的癫痫发作。当然,那看着很有趣,但除此之外的俺就不太喜欢了。看到碎骨者虚弱是不对的。这就像看到太阳熄灭,或看到一个屁精帮助另一个屁精。这是……亵渎的。虽然俺知道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当你的大脑被剁碎又长出来的时候,俺确信格鲁斯尼克也与此有关。
或者更像是里面有把手术刀。
随着碎骨者变得越来越大,他的那块金属护板并没有随他一起变大,脑袋里的其他新部件也没有跟着长大。由于格鲁斯尼克是唯一一个知道头目颅骨内的所有东西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人,碎骨者不断地回去找那兽医重新组装他的脑袋。格鲁斯尼克则因突然成名而变得富有,他放弃了自己的旧帐篷,接管了碎骨者的头目堡垒旁那间高耸的酿酒小屋。他在楼下的门口有一群看守,还有几十个屁精来帮他干脏活。
但他还是那个老格鲁斯尼克。他甚至可以给搞哥动刀子,而除了他自己那肮脏的幻想,他什么也不在乎。俺不否认,他确实有让碎骨者的脑袋保持在一起。但俺注视着他。俺紧盯着他。俺看着他往先知那裸露的大脑上撒下蛰刺讨厌鬼。俺看着他用肮脏的爪子戳了几下,只为了瞅瞅先知的哪一部分在跟着抽搐。俺看着他再次封上先知的头骨前,将一把扳手留在了里面,之后自言自语地笑了起来。这很公平,因为这很经典。但这是不对的。
他看到俺在观察所有这些,可他并不在乎。然而他为什么要在意呢?俺可能已经是头目的屁精了。但这只意味着俺可以跑去拿头目早上的史古革肝脏,而不会承受比轻踢更糟糕的痛苦。到最后俺还是个屁精,如果俺告诉碎骨者不要相信格鲁斯尼克,俺就会像任何尝试同样事情的真菌嫩芽一样被踩扁。
因此,当碎骨者翻来覆去扭动着身子的时候,俺甚至不能说俺已经告诉过他了。俺所能做的就是看着他表演,他盲目地盯着天花板,把自己的尖牙磨成碎片。
不过最终还是完事了。碎骨者挺直了身子,脖子发出的声响像是一辆战争摩托上掉下来的悬架,并且愤怒地呕吐了好长时间。接着他又吐了一些,呕出一大块被咬掉的舌头,还用他的巨爪将断牙的残根撬了出来。
“一次头脑-的-跳动,”他最后伴着一次颤抖的呼吸说道。“这就是俺要给他们的。”他说这话的时候,好像刚刚他只是灵机一动,而非癫痫发作似得。但这就是碎骨者头痛的原因。因其阻止了他的身体移动,让他不能仅仅靠踢家具来赶走烦人的问题。他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当他的眼睛看不到真实世界时,俺幻想他看到的是伟大绿潮。在那里,那个被损坏的壳子里,被诸神触碰的心灵洞穴里,那是他最靠近神性的地方。
“哼嗯,”他扭头看了看,就好像刚刚发现俺,然后接着说道。“就像……那是什么东西,你喊的……地方,让你的暴徒们杀得更猛。”
俺只是继续潜伏,但先知对俺咆哮,愤怒地用巨爪做着手势。
“来吧!俺的脑伤。找到那个词给俺。”
“一次演讲?”俺抽泣着说道,感觉就像踩在泥浆沟里的薄冰上。
“一次演讲,”他嘟囔着,转身面向露台,俯瞰着那场战斗。“只是……像一种反向的演讲。那种让你的暴徒们想要更少的……杀戮。”
如果再回答头目的话,那就是在考验俺的运气,所以这次俺只是带着一种钦佩的样子在嗤笑。
“去找子弹,”头目吩咐道。“让他召集其他的头目。然后去非常-冷的-洞,和所有你可以欺负的屁精们,把肉从里面都拿出来。俺要唤醒俺们曾经的那个东西,而它会饿的。”
兽人们不记录历史,同理他们也不建造坟墓。因为过去已经死了。就像死掉的兽人一样,他们认为最好还是让其烂掉,而不是用石头堆在上面将这个地方塞满。看,时间对兽人们来说是狭窄的。现在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但它只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用已经做过的事来填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本可以做些别的事情。此外,就像死者腐烂然后成长出新的兽人,过去也会腐烂成为故事,仅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真实。
注意,屁精是不同的。俺们想知道在俺们之前的人恨什么,以防那些是俺们从未想过要恨的东西。并且这给了俺们一些小小的乐趣,以俺们永远不会挨揍的方式侮辱俺们的主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尝试和理解它。所以俺们就在秘密的地方为俺们的不幸而挣扎:在瀑布下的隧道里,在俺们要修补的靴子底,还有卡车底下。俺曾畏缩在战斗堡垒下面,那就像你们的藏书台 - 车轴、传动系统和燃油泵被几个世纪以来的怨恨所刻满。
但关于尤克历史的所有可知信息也都被这些子弹尾部留下的刻痕记录了下来。兽人们为了垃圾互相打架。有时候人们入侵,遭到痛扁,并留下新的垃圾让他们去争夺。帝国发展又崩溃。兽人们为了垃圾彼此干架。你们明白了吧。
但那天晚上,在头目堡垒的露台上,首次发生了一些不同的事情。
“所以你们想要一场战斗,是吗?”
那是他曾经叫德格梅克时用的声音。不是吼叫、不是咆哮、也不是呼喊,但声音大得像是一艘恶月运输飞艇在头顶巡航,穿透所有东西的内部,把松动的螺丝弄得嘎嘎作响。即使处于争吵的喧闹声中,那些兽人们也全都听到了,一片被火把照亮的尖牙森林齐齐转向那声音的源头。当最后一拳落下时,伴随着像暴雨的最后一滴那样逐渐减弱的肉质撞击声,人群看起来很困惑,然后是愤怒。这算什么问题?但碎骨者没有给他们回答的时间。
“你们想要一场最激烈的战斗吗?”他用巨爪指着他们以示挑战地问道。“你们会杀掉无以计数的神祇,并将城市淹没在你们的鞋印里吗?你们会在一个大到让整个世界变绿的暴徒团伙中奔跑吗?”
“你们会吗?”他奚落道,这是自从勘探者支起帐篷以来,锈钉第一次陷入寂静。
那答案就像一声爆炸,一半是嚎叫,而另一半是对邻人的拳打脚踢。碎骨者斜靠在露台上,怒目而视地扫过街道,沉浸在暴徒们压抑已久的愤怒之中。然后他做出回答 - 并且这次他吼了起来。
“你们在这里是得不到的!”
当你在跟兽人们说话时,不需要太多就能引起骚乱。当最前面的人群已经开始攀登头目堡垒时,先知的声音仍然回荡在整个城市之中,但碎骨者已经做好了准备。站在他后面的其他头目们拿着铁棒走上前来,开始砸烂露台栏杆上出现的每一根绿色手指。每当有一个兽人成功爬上露台边缘时,就会听到一阵尖锐的咕噜声从格鲁斯尼克住所顶部的大桶传来,詹朗·斯塔拉特迦姆在那里架设了一把远-距离-枪,而一具尸体就会应声滚落回兽潮之中。

兽人所谓的“狙击枪”
碎骨者任由他们来。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了。
“你们在这里是得不到的,”他说道,那声音就像一架经过的轰炸机发出的压力波一样压制住了人群的愤怒,“因为它在上面!”他将巨爪指向城市上空透着暗淡光线的烟雾云,街道上的愤怒稍稍减弱了一点,然后又摇摇晃晃地重新陷入混乱。
“俺们不能跟云战斗,”在短暂的沉寂之后,一个声音大嚷道。但就在赞同的呼吼声开始高涨之际,刮起了大风,云层开始移动。“看呐,”当更广泛的情绪转回暴行时,又一个声音传来。“大湿玩意跑了。”
“看远一点,”先知命令道。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一团烟雾在风的吹拂下消散,露出了下面的星星。“你们一辈子都在跟乌云作战!将自己扔在战争中改变不了什么。这是一场让诸神厌恶的战斗。但在上面,群星所在的地方,有比你们最残酷的梦想更大的战斗。那里有……战争。”他说这个词就像灌了糖浆一样。“或者可能有,如果你有与他们战斗的渴望。”
“那就弄些太空船,”声音出自一个戴着发光彩饰的恶月,霓虹黄色的骷髅和骸骨 - 俺猜是一个从其他星系来的 - 赞成地吼道。“俺们今晚就离开!”
“用什么燃料?”碎骨者咆哮道。“还有用什么引擎?你以为你了解太空,是吗?俺才了解太空。诸神展示给俺看了。它是巨大的。你的舰队都不够装俺们的八分之一,走八分之一的路程就会报废。然后呢?你要出去推吗?”
“是的,”那穿着华而不实盔甲的海盗说道,但他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

兽人海盗在装束上通常都极度爱炫
“俺可以带你们去。诸神已经告诉俺怎么做了。等俺们到了那里,俺向你们保证 - 会有比你们现在知道的还要多的杀戮。在你们的余生里,你们只会感觉到鲁克-拉兹哈,最纯粹的战争狂喜。然后,等你死了,搞毛二哥会让你变得更强壮,得到更多。”
“但有一件关于战斗的事情。”随后,碎骨者停顿下来,眯起他那只完好的眼睛,仰望着那些散落在外的星星,而在他刚刚平息下来的沉默中,没有一个声音敢发出来。“它们越大,伤害就越大。你们付出的痛苦越多,得到的也越多。不过,兽人是怎么看待痛苦的?”此时,头目低头看着人山人海的面孔,带着挑战的目光,他的胃里升腾起一股残忍而骄傲的感觉。
“没什么!”答案一下子从许多许多许多许多人的喉咙里传来,头目的脸顿时绽放出一副得意洋洋、龇牙咧嘴的狞笑。
“没什么!”他吼了一声,并用巨爪猛击露台的栏杆以示强调。“这场战斗的痛苦是前所未有的——这场战争!有些会在它之前到来。那将不是战斗的痛苦。等待的痛苦。你们害怕那种痛苦吗,兽人?你们是否太过软弱,无法承受?”
人群想了想。他们努力思考。当他们脑袋里正翻腾的时候,风将面前高耸的屠宰场周围散落的护板碎片吹得嘎嘎直响。他们看着领导各自氏族的战争军阀们,正手持血淋淋的棍棒站在碎骨者旁边。
“俺可以接受!”一个小山般高大的高夫咆哮着,从他被斯塔拉特迦姆射中胸口后倒下的地方说道。
“俺要接受两次,”他旁边站着的一个死颅夸耀道,不想被其氏族蔑视的对手比下去。
“简单!”一个干瘪的老邪日咯咯笑道,挥舞着一柄用旧摩托零件焊接而成的红色锤子。随后整个人群都开始了,每个兽人都在取笑这项任务,希望自己能比旁边的兽人做得更好。并且没有谁揍任何人。
“那么接受这痛苦吧!”碎骨者吼道,他那只完好的眼睛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而未来正展现在他面前的街道上。“让它在你们的血液中燃烧。让它令你们饥饿,这样你们的尖牙在盛宴到来之前就会更加锋利。”
那是俺的信号。俺向露台上的其他屁精们发出嘶嘶声,随后俺将侧边的史古革肉举到栏杆上翻下去,然后他们也都做了同样的事。
“在那之前,俺会让你们的斧臂继续有活儿干,”头目承诺道,此时大块的肉开始像雨点般落进人群中,发出一阵湿漉漉的砰砰声。“那里还有群山要被击碎,有油湖要从深岩中被汲取。那里还有锻炉要被喂养。刀片要造得锋利。需要从敌人梦魇中拖出来的战争机器。在俺拥有诸神力量的手下,你们将把自己打造成一支能使群星变绿的大军。”
随后他把自己那巨大的金属脑壳向后仰起,发出最古老的战争嗥叫,那是每一个兽人在其生命中第一次呼吸,通常也会在最后一次呼吸时所发出的。每个氏族的每一个兽人都咆哮着回应,直到那些吼声汇聚成一个伟大的声音。
WAAAGH!
它就像一个巨人从城市下面的生长洞里爬了出来,有那么一瞬间,在那惊天动地的吼声环绕之下,俺仿佛又回到了那伟大绿潮中。
俺甚至发现自己也加入了进去,这令俺很是震惊,因为那不是屁精们会做的事情。但当俺开始的时候,露台上其他的屁精也一起这么做了。而当他们开始的时候,城里的每一个屁精也都跟着一起,直到第二次嗥叫 - 更高、更难听 - 潜伏在兽人的吼声里钻入天空。俺只能说,在那一刻,俺不是一个屁精。俺仅仅是某个巨大、绿色、可怕东西的一小部分,被灌进了一具屁精形状的身体。
也许那天晚上碎骨者没有长得比平常更大。不过在锈钉的每一个兽人,俺发誓,在那场嗥叫结束时都长高了半个头。当他们脱离它的影响时,他们看到上空的云层已经全部消失了 - 就好像其真的害怕被打得遍体鳞伤一样 - 在尤克上北极光发出的噼里啪啦的绿光后面,只剩下了群星。
当然,那极光是一种预兆。但不是俺,或是锈钉里的任何其他生物所认为的那个。当俺们屁精对这一胜利的征兆咯咯直笑,兽人们用塞满礼物般肉块的嘴得意地吠叫时,碎骨者只是低吼了一声,然后大步走回了他的堡垒中。因为他知道真相 - 这绿光不仅仅是在太空中等待他的命运的象征。那是来自搞毛二哥的警告,告诉他不要浪费任何抓住那命运的时间。
你看,诸神已经厌倦了。现在,终于有什么东西再次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渴望碎骨者去执行他们的意愿。你还记得俺是怎么说兽人的吗?如果看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会一直努力直到得到它,或者直到他死在战斗中。好吧,兽人的神祇也是如此。只是他们还有别的东西要搞死。而在这个事例中,是尤克。
审讯六
尽管她正全神贯注于玛卡伊的故事,法尔克斯还是听到了亨德里克森平静的喘息声——总是在愤怒的打断之前发出的那种——就在她向其投去了一个冰冷的眼神时,令人担忧的是,她开始认为自己是这间牢房里“它们”那一边的。
+ 这比黎明前醉鬼的故事还要荒谬, + 他向她的意念发送道,+ 那个腐烂的野兽索塔尔在哪里? +
正在准备运送。其目前的样子是不合时宜的。但它会来。在那之前,我们让它们继续。
那位老萨满屈就地露出牙齿以示回应,不过他还是让咬仔继续下去。
当然,她知道亨德里克森的问题是什么:玛卡伊那失踪的烧伤疤痕完全没有解释,尽管之前被保证很快就会做出解释。诚然,考虑到那屁精表面上是在为其自己的性命辩护,她自己也有点惊讶于那解释还没出现。但她对这一事实的担忧远比她的死亡守望同伴要来得少。事实上,如果她对自己完全诚实的话,法尔克斯越来越不确定这个玛卡伊的真实性问题对她到底有多重要了。
亨德里克森处理的是绝对问题。毕竟他是阿斯塔特。超然于人类。而且是芬里斯风格的。在他的世界里,塑造银河系命运的乃是强大英雄之间伟大而关键性的对抗,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因此,如果这个玛卡伊不是真品,那么它对符文牧师来说就毫无价值。即便它是真的,如果其不提供一些能改变游戏规则的战略信息,那么它的整个叙述对亨德里克森来说也没有什么价值;部分重要、脉动性的资料可以用来建立一些戏剧性的关键对抗。
但法尔克斯是人类,她对帝国为生存而斗争的理解也是。毫无疑问,他们那痛苦、永无休止的战争会不时被英雄们的行为所打断。而且是的,这种行为确实可以拯救整个世界。但拯救一个世界有什么价值呢?在浩瀚银河的斗争中,即便个人能力最大限度的运用也只能是一个微小的山峰,几乎无法从缓慢的消耗海洋中凸现出来。在阿斯塔特修会那小巧、闪闪发光的矛尖后面,人类的战争机器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它的质量几乎完全是由数量来定义的,其最微小的命运变化是用数百万人的生命来衡量的。有时能挽救生命,但更多的是失去生命。
因为在它那冰川般疯狂的崩溃中,帝国心甘情愿地蒙蔽了自己,不去了解它的仇敌们。甚至她自己的命令——她痛苦地提醒自己,这是最高级别的防御非人类威胁的命令——将任何超出对对手最基本理解的事情都列为禁忌。他们认为仇恨就足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了。
“你暗示尤克要死了。”在一段关于传送事故,一个兽人和一群鼻涕精融合在一起的故事中间,法尔克斯突然说道。
“它的恒星正在消亡,”咬仔自鸣得意地纠正道。“但玛卡伊说,只有碎骨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大多数兽人只觉得这是一个很长的冬天,直到进入了第二年。”
在那名翻译不知情的情况下,法尔克斯已经知晓了关于尤克恒星的一切。为了核实事实,在审讯开始时,她曾默示船上的档案管理员查阅这个曾经被称为尤洛克莱斯的世界的所有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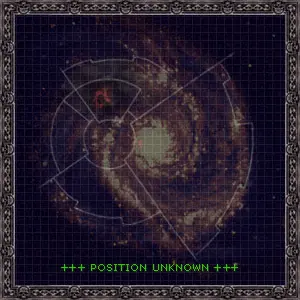
尤洛克莱斯是人类对这颗星球的称呼,自M32“野兽战争”后永久落入绿皮的控制之下
当碎骨者崛起的时候,那颗恒星已经到了它衰亡的终点,被烧成一团稠密的、有放射性的重金属熔渣。玛卡伊所描述的绿色极光便是它的死亡摇铃:在其核心完全消失并爆炸成灾难性的新星之前,辐射发出了短暂的最后一声咳嗽。
这是野蛮物理学的杰作,而非任何所谓的诸神。当然,碎骨者不可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然而,就像某些显赫的兽人经常出现的令人发狂的情况一样,他表现得就像他已经意识到了似得。
“让玛卡伊告诉我们有关尤克最后的那段日子,以及碎骨者是如何打发时间的。然后,”当亨德里克森伸出双臂,好像在抗议一场摔跤比赛的不公裁决时,法尔克斯补充道,“你要提醒它解释那失踪的烧伤疤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