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涉及劇透。
《傳世不朽(Immortality)》以三部電影的臺前幕後片段講述了一位神秘女演員在電影拍攝期間的過往。“互文性”視角幫助我們感知作品,也提示了敘事主題和機制設計的特點。這一視角下的整部作品迴響著一種一致的精神,非常獨特。

1、從“互文性”進入作品
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或譯作文本間性)一般認為是法國符號學家、女性主義批評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提出,最常見的定義是:“任何文本的構成都彷彿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轉換”。在克里斯蒂娃那裡,“文本”首先是整個社會歷史。“文本”可以指一部作品媒介,但也指一種意義生產過程;“另一個文本”可以指先前的作品,但更是指一切社會歷史的實踐。任何發生互動關係符號系統、文化現象都可以看作是“文本”。
下面以遊戲中第一部電影的拍攝時點“1968年”為例。由此出發,我們關於這一歷史時期的理解和感受開始甦醒,特定語境的社會歷史文本如引文一般被接入,遊戲文本所指向的意義開始顯現。
1968年法國暴發五月風暴,一般認為是女性主義理論第三階段的開始。克里斯蒂娃本人也是女性主義的研究者,她認為五月風暴與精神分析法共同開啟了女性主義的一條新的道路:尋找兩性的差異。
《傳世不朽》始終或明或暗地講述著女性的生存與命運。在第一部電影《安布羅休》中,當牧師忽然意識到眼前的女子竟然就是聖母畫像的模特,這是兩人的關係即將從禁忌走向欲情的關鍵時刻。在這段影片的隱藏片段中,永生女性以聖母瑪麗亞的形象出現,她看著畫像說到:“瑪麗亞當時並非處子。”這是什麼意思?

“她當時並未身著藍衣,也並非處子”
克里斯蒂娃曾在1999年的一次研討會上作了題為《從聖母像到裸體:女性美的再現》的發言,在第二章“童貞瑪利亞”中如此說到:“她的童貞構成了最大的醜聞……它把女性從性中排除,懲罰性的貞潔彷彿是把女性接納入神聖——並接納入再現——的代價!”,“(瑪麗亞)被縮減為耳朵和眼淚的身體;苦難和疼痛的神聖化,以及只有在此之後才有的對一個無可匹敵力量的承認……她的永生甚至被暗示出來,她是福音書傳說中唯一的不死者;她通過‘聖母永眠’的媒介來度過從生到死的過程……苦難是留給瑪麗亞的,微笑是留給畫家的!”
接下來,在第三章中,克里斯蒂娃即以文藝復興時期畫家喬凡尼·貝利尼的作品為例,詳細說明了西方藝術再現中“女性特質”如何從聖母向裸體滑移,從早年拜占庭式的、靜謐的母性形象,直到貝利尼晚年時期如維納斯般的《鏡前的裸女》。
同時,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在遊戲的這段隱藏片段中,相比於其他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聖母畫像,永生女性的聖母形象更接近貝利尼的晚年作品中的聖母形象。

白色頭巾包裹著頭部
1968年的另一個社會歷史“文本”,是夏皮羅當年發表的一篇著名的藝術批評文章《塞尚的蘋果:靜物的意義研究》。彼時夏皮羅認為形式主義批評存在侷限,他根據大量歷史資料對塞尚的蘋果逐層挖掘,分析出塞尚的情感問題、童年壓抑、無意識投射等結論。在這篇文章中,夏皮羅結合兩希文明傳統象徵以及中世紀以來的文學意象,指出了塞尚的蘋果和水果背後的色情意義。
同時,在遊戲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關於水果的成就:Fruit means temptation, knowledge and sex。基於這些文本的拼接和吸收,遊戲影片中不斷出現的水果作為一種文本符號就出現了新的結構與意義;當我們在影片中跟著水果不斷點擊跳轉時,對這些文本的所指會有新的感知。比如海瑟曾經以蘋果為理由拖延時間向瑪麗亞求援,在前後兩個場景中,蘋果處於鏡頭的中心位置;當瑪麗亞來到後曾高舉蘋果又放下,隨後說到女性權力、應對產業等話題。於是這些能指又與整個作品中關於女性主義的討論相互關聯起來。

我們在社會歷史話語中找回不同的形象、文本、話語,在作品中將之轉換為新的結構、指向新的意義,由此看到整部作品的文本符號逐漸交織起來。這是互文性作用的結果,也是我們理解和進入作品的一條可能的路徑。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克里斯蒂娃所在的法國“Tel Quel”小組推出了論文集《整體理論》,論文集中,德里達、福柯、羅蘭·巴特等人從哲學、語言學等不同的領域批判了“結構”、“符號”、“主體”等“神學範疇”。也正是同一時期,克里斯蒂娃先後在《巴赫金,詞語、對話和小說》等三篇論文中使用了拼合的法文新詞:互文性。
《傳世不朽》中還有許多互文性要素,但這裡無力詳盡,只能略舉例子說明互文性概念如何將我們的想象和感知在閱讀和遊玩空間中展開。在電影史、女性主義、精神分析等視角下的《傳世不朽》可能會呈現更豐富的意義和趣味。
2、以“二重性”反抗“同一性”
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論離不開“Tel Quel”小組的符號批判與主體批判思想的理論語境。這也提示了我們如何看待作品主題的一種可能。
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論發展自俄國文藝批評家巴赫金的對話理論。“二重性(ambivalence)”是兩人理論中使用最多的概念,涉及到“對話”、“話語的雙重指向”、人格二重性、“狂歡節”等相關內涵。“‘二重性’意味著社會歷史被寫入文本,文本又被寫入歷史”。在克里斯蒂娃那裡“二重性”與“互文性”幾乎可以換用。

在《傳世不朽》中,我們很容易注意到各人物形象的“雙重”身份。比如:三部電影女主角,上帝的僕役與撒旦的化身,芙蘭妮與法蘭基,明星與替身;生澀內斂的馬賽爾,飾演情慾誘人的瑪蒂爾達,而性感熱情的索菲亞,則出演單純乖巧的安東妮婭;當芙蘭妮對古德曼完成“雕刻”後說“現在有兩個古德曼了”;變裝人群、跨性別者內在同時存在的兩種“性別特質”;作為公眾人物的“肯尼迪”海森伯格和“真實自我”海森伯格;客串的編劇巴里·吉福德說:“兩位殺人犯,成雙成對,充滿聖經寓意”……

極有代表性的場景還有(以場景排序)最後一段影片:1999年的瑪麗亞唱了一首電影同名歌曲:《Two of everything》;此時的瑪麗亞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將以海瑟的生命繼續生活;而作為海瑟,又化名為克里斯蒂娜。在這段影片的隱藏片段中,永生女性也唱了一首歌:《Candy Says》。這首歌以上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活躍的跨性別明星Candy Darling為原型,她可能是最早出現在聚光燈的跨性別者,也是當時著名藝術家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身邊“變裝男性”群體中最知名的一位。30年前拍攝第二部電影《明斯基》時安迪·沃霍爾曾來訪片場;彼時的永生女性還只是瑪麗莎,而此時同時成為了約翰,既是女性又是男性。此時的永生女性還剛剛發現了永生男性的到來,在這30年後的重逢中兩人達成了和解,試圖重新實現兩人的共存。“Two”所指向的意義交織而複雜。

“你和我”
這些人物形象身具多種特徵。一個個場景、臺詞、片段中,不同的話語、符號和意指系統交疊著同時存在,迴響著各異的價值與觀念。巴赫金用“狂歡節”來形容這種複雜行為的綜合。克里斯蒂娃在《詞語、對話、小說》中寫道:
狂歡節的參與者既是演員,也是觀眾;他失去了他的個體意識,穿過狂歡話語行為的臨界點,分裂為表演的主體和遊戲的客體。狂歡節上,主體退化為虛無,而作者的結構浮現,以匿名的形式創造著並看著自己被創造,他既是自己又是他者,既是人又是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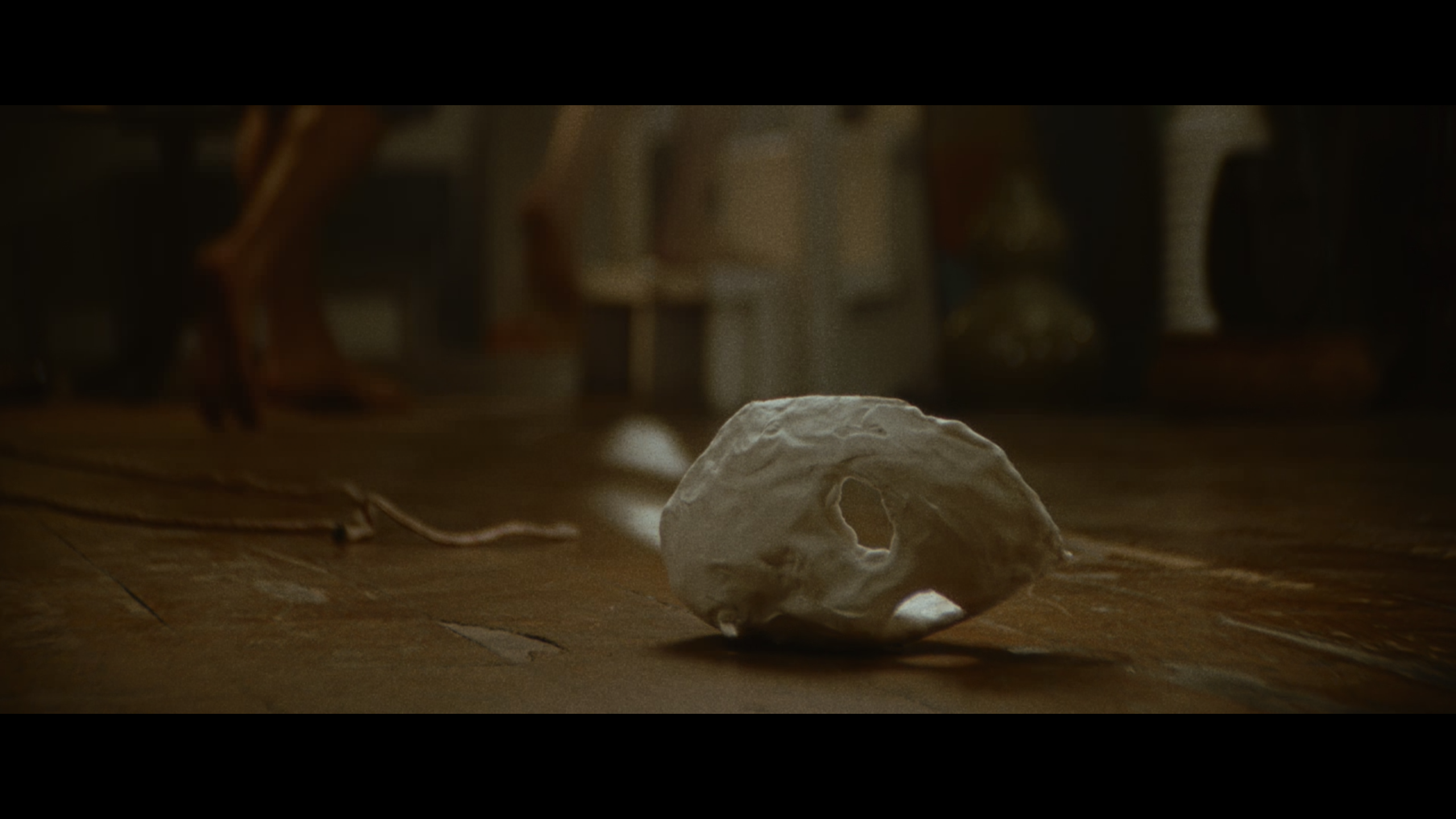
面具代表著身份的不確定性
20世紀下半葉西方一些學者開始反思現代性,排斥“整體”“絕對”“普遍”等真理概念,懷疑傳統形而上學的理性大廈,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惡果使得學者們越發意識到將“同一性”的單一概念置於總體框架下是否能讓我們把握生活的世界。克里斯蒂娃試圖用“二重性”概念突破由因果關係確定的同一實體的思維框架,反抗二元對立的僵化模式,挑戰上帝、權威和陳規。
克里斯蒂娃質疑基於0-1區間的語言規則,1表示同一律、法則、上帝、定義、意義、真理等等;而0-2區間的“二重性”(互文性)詩性語言能打破1的禁忌,2表示詩性語言的“二重性”,一個“文本”同時也是兩個“文本”。
狂歡節的“二重性”正是反基督教和反理性主義的,狂歡化的語言重複、不連貫、(非排他地)對立,分離了所指又將能指組織起來,用插科打渾、粗鄙對話等影射權威的消失、等級的破碎、邊緣的逆轉……“狂歡節的場面……既是舞臺也是人生,既是遊戲也是夢境,既是言語也是表演。”

永生女性在審訊室的三重隱藏片段或許可以視作整部作品“中心思想”的自白(當我寫到“中心思想”,剛好發現這段影片處在所有片段最中心的位置,全作共計202個片段,這一片段處在電影排序的第101位),她如此說到:
你可以把人類文明分為兩股勢力。其中一個,是控制和破壞的衝動,被恐懼所驅使,我們可以稱之為法則;另一個是創造、治癒的衝動,受愛驅使,藝術家。歷史上每一次衝突都是法則對上藝術家。

“就算你自認為是藝術家也一樣”
由此,雖然整部作品探討的話題牽涉甚廣、涉及的社會歷史背景複雜,但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一個“核心語(Hypogram)”(來自裡法泰爾:詩的詞彙圍繞核心詞相互聯繫並且從不同方面鞏固核心詞):反抗同一性。
在女性主義那裡,是女性模特反抗試圖雕塑她們的男性藝術家,是女演員反抗資本權力的侵佔;在電影史那裡,是電影作者反抗製片廠,是新好萊塢反抗類型電影;在跨性別者那裡,是多元性別特質反抗性別刻板,是男性對內心女性特質的接納與自我認同;在兩位永生者那裡,是代表普通人、個體、異質性的女性永生者反抗代表上帝、威權、理性和同一性的男性永生者……

二元特質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而可以同時存在、互不排斥。互文性理論繼承的是20世紀以來後結構主義的文化理論批判精神。這一精神也同樣閃現在整部《傳世不朽》的敘事中。
3、迴響的精神
作者Sam Barlow的前兩部作品從《她的故事(Her Story)》到《說謊(Telling Lies)》,遊戲機制和玩法變化不大:通過臺詞來索引片段。但《傳世不朽》在機制上出現了兩個變化,從互文性的視角來看別有意味。
第一,取消了關鍵詞搜索,改為在點擊畫面中物實現穿梭跳轉。互文性概念顯示了符號意指系統之間的轉換移植。我們在遊戲中沿著物件、畫面、人物等符號來回穿梭轉移,不斷對正題重新定位;因為作為意指系統的‘位置’和‘對象’從來就不是單一的、完整的、同一的,而總是多樣的、破碎的。我們看到一個人從中世紀到好萊塢,一個水果被修士剝開又被演員舉起。從一個不同物到另一個不同物的位移和搖擺,提醒我們重新注視所有的二重對立。
第二,所有已知片段全部呈現排列在一起,而不是如同前作般只顯示按時間排序的前5個結果。後結構主義反對線性的時間範式,因為線性意味著文本圍繞意義的凝固、穩定和不可逆,意味著源流、權威和因果。將縱向的歷時關係轉化為橫向的共時關係,能夠將當前文本與先前文本的關係視作為“對話”和“互動”而不是“因果”,視作“交匯”和“中和”而不是“影響”。

我們通常將遊戲機制、畫面、語言等符號和文本視作意義的表達。但在德里達那裡,符號是延異(différance)的在場,延擱了我們遭遇、擁有、消費事物的瞬間。德里達用“交織物”(interweaving)或“紡織品”(textile)來形容我們眼前的這些能指文本的不斷變化、互相交錯的動態過程;而所指概念絕不會自我出場。一個作品文本中的要素若要有所表徵、傳達意義,該如何實現?

“我試著不去視覺化”
克里斯蒂娃在1968年對德里達的訪談中提出“什麼是作為‘延異’的文字”、 “何種實踐能夠超越語言(所謂的)‘表達’和終結”等問題。德里達的回答中提到:
每個要素作為符號起作用,就必須具備指涉另一個自身並非簡單在場的要素,這一交織的結果就導致了每一個‘要素’語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號鏈或系統的其他要素的蹤跡上。這一交織和織物僅僅是在另一個文本的變化中產生出來的文本。
德里達所稱的“延異”包含兩種不同的意義:既是“延宕(temporization)”,“在暫時性和延宕性的迂迴中介中有意無意地追索,推遲‘慾望’或‘意志’的滿足和實現”;又是非同一性、他者性、可辨識性的,空隙、距離、間隔都在兩個他者元素間產生。
在所謂的(‘所表達的’)意義已經完全由差異組織構成的程度上,在已經存在著文本之間的相互參照的文本網絡的程度上,文本變化中的每個‘單個術語’都是由另一術語的蹤跡來標識的,所假定的意義內在性也已經受到它的外在性的影響。

交織品
在前兩部作品中,玩家始終關注、尋找關鍵詞,我不斷地問道:“正確答案(關鍵詞)是什麼?”在《傳世不朽》中,似乎無法如此提問。“我在尋找的是什麼?”對於接下來作出回答的每一個作為能指的文本,都已經在我的面前,比如蘋果、面具、場記……但其所指向的意義在哪裡,我卻無從追索。互文性重視語義的流動超過對答案的確信。作為玩家,唯一能做的——僅僅在做的——是在影片要素的“交織品”和“文本網落”中流竄,在延宕中抵達非同一的另一個能指,直到某個所指終於被映射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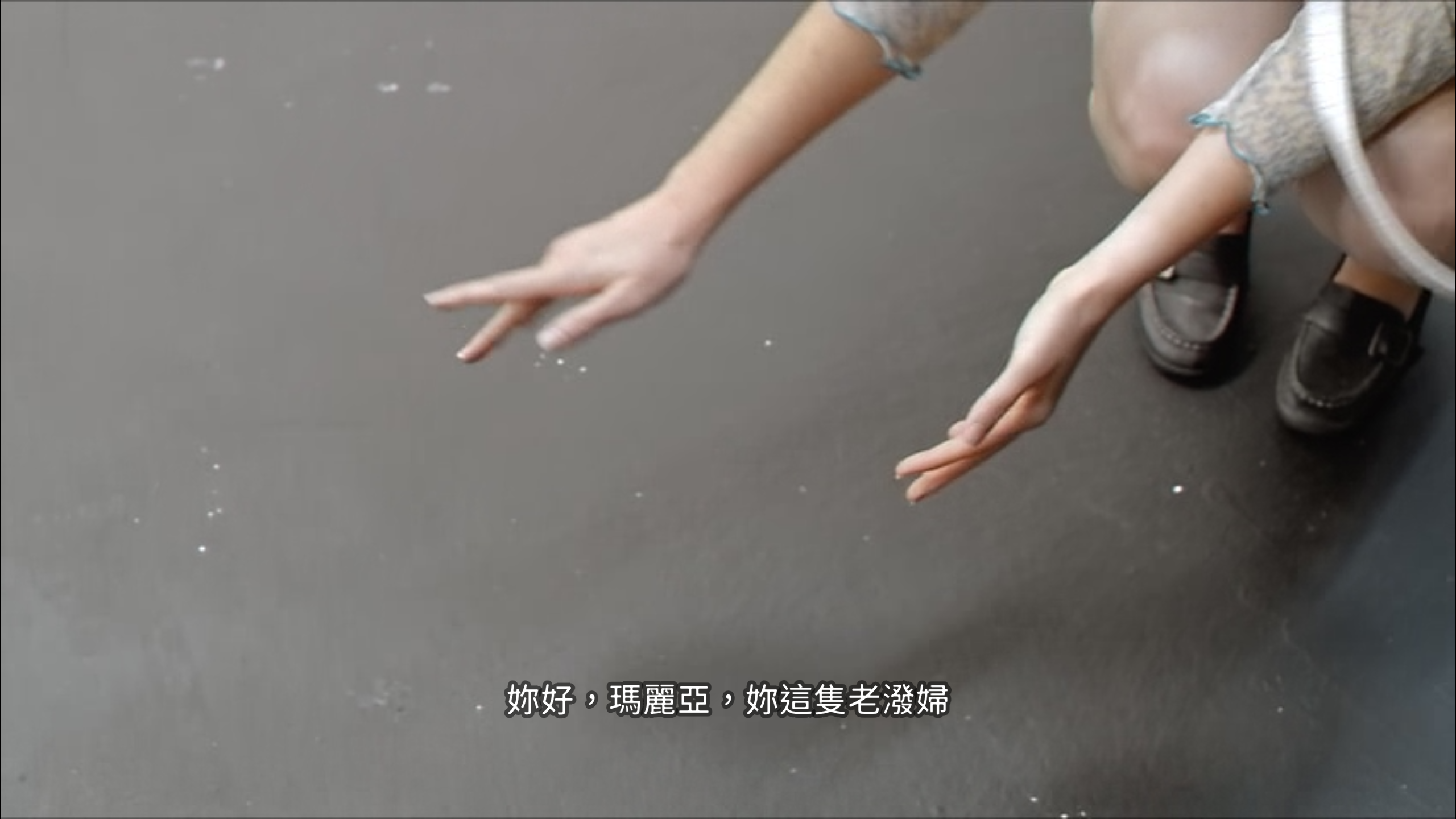
即使什麼也沒有,也有所指向
《傳世不朽》中,充滿既視感又不復雜的播片機制,在互文性視角下有著令人驚訝的解構意味,玩家的實踐與“反抗同一性”的主題迴響合唱,反抗邏各斯中心。機制玩法和故事情節顯現了一種形而上的相通。核心玩法上看似變化不大,但配合著整個社會歷史語境下的敘事,是否恰恰說明製作團隊非常清楚所需要的機制是怎樣的以及為何需要,並做出了非常精確的調整?

每部電影都需要一把鑰匙打開母本
綜上所述,從互文性的視角出發,我們看到整部《傳世不朽》從劇情和敘事的創作中的二重性,到作為主題的對同一性的反抗,再到玩法機制中顯現的解構意味。
也因此,我擔心“機制幫助敘事(或反之)”等遊戲設計視角是否能合適地解釋作品帶來的感受;從“機制/敘事”的二分是否就已經錯失了整個作品背後一致性的指向。這種一致性,樸素地說,大概就是遊玩結束時的百感交集;一股茫然龐大的氣氛壓迫而來,推動著我們湧向作品預謀的所在。
從互文性(及其解構)視角中,整部作品(包括寬泛意義上的機制和敘事)共同迴響著某種精神。這是如此難能可貴。反應時代精神的理論容易找到,沿著精神創作劇本或許也不難,但是作為電子遊戲媒介,要將之與一種恰好的機制迴響在一起,該要怎麼做才好?還是反過來,從機制向著一種精神探索前進?都不容易。這些使得這部作品非常獨特。
4、最後說到“不朽”
最後說回到遊戲的名字“不朽”。
在收集資料的時候看到一則趣聞:年旬70的蘇珊·桑塔格在一次公共演講中回憶了一段年輕往事,她曾在意大利機緣巧合地認識了一位野心勃勃、“盲目自大”的青年學者:他說自己正在準備一本絕對的暢銷小說,並因此正在學習大仲馬;他說這事關人的“不朽(immortality)”,他設想兩百年後還會有人繼續閱讀他的小說。

“數以百萬的人觀看?”
此青年便是翁貝託·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意大利符號學家、文學批評家、小說作家,1980年出版了《玫瑰的名字》——一本充滿互文性的後現代小說。艾柯曾在《符號學理論》中說到:“持續不斷地將其直接意指轉化為新的含蓄意指,其中沒有哪一項目終止於第一闡釋成份上”。這麼看來,我們似乎永遠無法到達對審美的最終答案。
克里斯蒂娃曾說起互文性概念如何繼續發展了結構主義所忽略的兩個方向:其一是對社會歷史文本的開拓,這也是本文至此一直討論的部分;其二是對話語主體、主體性的研究。
作為言說主體,我們的主體性不會一勞永逸地鑄就。意義的產生需要符號鏈的動態生成,並不是直截了當的現成事實。
在《傳世不朽》中,“拉片”(即反覆倒帶觀看電影)作為最基本的單元,將片段、畫面、道具、角色等文本與玩家連接,也將文本與歷史鏈接。我們不僅面對的作品本身,還同時被拋來了作者“意圖”、玩家接受、語境歷史。誰在觀看這些遊戲中的影片資料?這些資料被Barlow保存,提供給馬賽爾的粉絲;鏡頭拍攝給三部電影的觀眾,但是約翰正是大多數鏡頭背後的注視者;兩位永生者一邊談論卡爾、約翰和大多數人,同時一邊看向鏡頭,似乎又在與誰交談。他在看自己,導演在看她,我們也在注視,這些目光的漩渦有怎樣的關聯?

德里達在1968年那篇訪談中說:“首先是有意識的和說話的主體取決於差異系統和延異活動,主體唯有在與自身相區分中,在生成空間中、在拖延中、在推遲中才被構成。”
所以當永生女性看著鏡頭對我們說“我已經成為了你的一部分”,她的意思可能是:當我們遊玩、觀看、尋找時,我們從文本進入感知,在持續不斷地讀解中也進入文本;由此,我們作為玩家的主體性也被建構,然後成為了“文本”的一部分。“不朽Immortality”指的可能不僅是她,也是作品,也是玩家。

I am part of you now
文中提到的文獻:
-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 克里斯蒂娃自選集[M].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祝克懿,宋姝錦. 詞語、對話和小說[J]. 當代修辭學,2012年.
- 雅克·德里達. 一種瘋狂守護者思想[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