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有核心劇透。如果您對遊戲感興趣,請暫緩閱讀。
這篇短文簡要分析《三相奇談》中的兩點:時間敘詭對玩家視角的利用,以及對小遊戲這一類型傳統的一些改進。這兩處巧思不僅關乎本作的體驗,也涉及了所屬類型的條件或界限。
這裡的討論將《三相奇談》視作一款標準的類型遊戲:懸疑解謎方向的冒險遊戲。在這個類型中,故事情節主導了遊戲進程。玩家一邊蒐集線索一邊揭開謎團,不時進行一些推理和抉擇,與角色一同還原事件全貌。這類遊戲通常還會在多個環節設置一些小遊戲,比如開鎖、破解機關等。至於本作,站內站外已有諸多評測,就不多贅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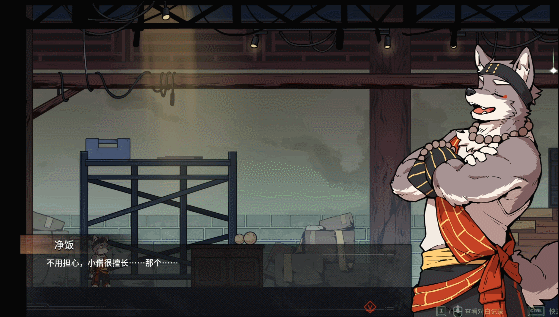
一個發生在東方幻想世界的故事
1、時間敘詭:玩家的單一視角
遊戲第四章包含一個與時間線相關的敘事詭計。敘事詭計利用玩家的信息盲點,在故事前期欺騙玩家,以求在揭秘時刻帶來最大程度的信息差。儘管敘事方面的鋪墊也十分重要,但這裡主要關注機制方面,特別是對玩家視角的利用。
故事層面,三寶、淨飯、皮月羞三位主角分頭混入山寨,試圖盜取密碼箱中的鑰匙。經歷了一番調查後,三寶和淨飯兩人雖然成功匯合,但行動失敗以至逃亡,未曾想還被山寨頭領埋伏——正當此時,劇情反轉,眼前的頭領竟是由夥伴月羞假扮。藉助影像的閃回,玩家這時才得知,原來早先月羞利用了兩人的行動,略施小計,成功獲取鑰匙,結果皆大歡喜。
交互層面,本章玩家分別操控三位角色進行活動,大多數時候可任意切換。雖然三位角色位於山寨內不同區域,但各自行動的結果會幫助其他兩位同伴解除困境。直到反轉來臨,玩家才知曉,原來此前操控的皮月羞與其餘兩人不在同一時間線,之前的相互影響只是煙霧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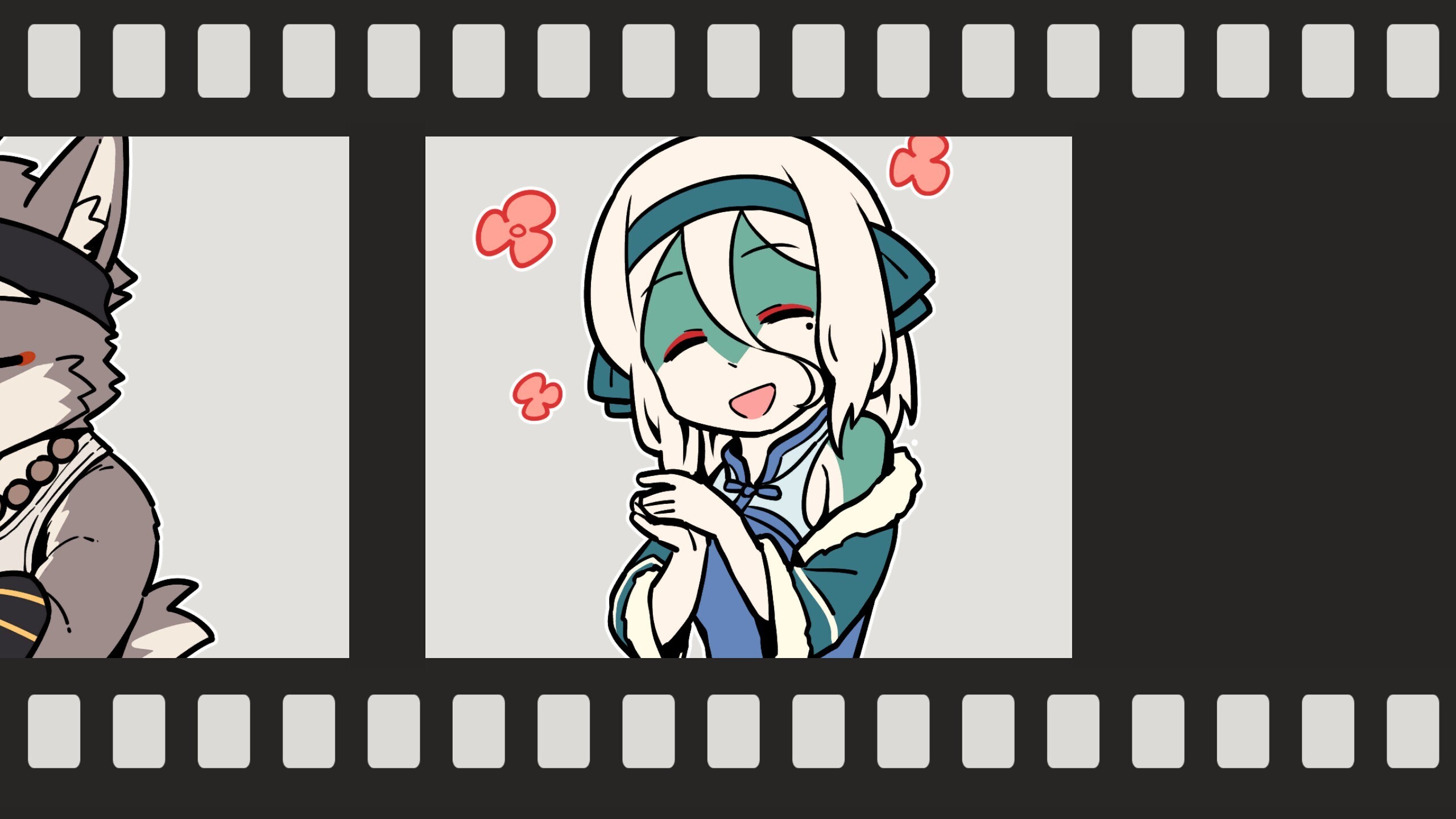
切換角色的界面,皮月羞與其他兩人並無差別
在本作所屬的遊戲類型中,似乎存在一項慣例:玩家視角的一致和持續。這一設計可以上溯到角色扮演類型。通常來說,玩家操控單個角色,並儘可能保持連續操控。即便存在多角色切換的機制,被拋下的角色也會在原地等待,直到切換回來,玩家會接續之前的行動和故事。
從敘事效果來看,這一設計有利於塑造沉浸感。玩家在遊戲世界裡獲取的信息始終與角色同步,無論是情感表達,還是信息整合,玩家都與角色共同經歷。即使反過來想,操控的斷裂似乎也是沒有必要的,除了省略,有什麼理由需要讓角色不受控地(甚至在玩家的視線之外)行動呢。
但如果參考電影鏡頭語言對觀看方式的掌控,或者小說敘述者在直接和間接話語之間的轉換,那麼作為一種類型慣例,玩家對角色的操控,以及由此建立的敘事視角,就顯得有些單一。特別是在一種越發追求自由構築、個人故事和開放世界的創作氛圍中,玩家與角色的這組關係會變得越發牢固。設計慣例和思維慣性,彼此強化。
在此,《三相奇談》發現了信息斷裂的作用,利用了玩家視角的思維慣性。
首先,作為敘事詭計的參與人數,三人剛剛好。三寶和淨飯兩位角色的匯合,強化了玩家對信息和時間的預設,開闢了第三人行動的錯位空間。哪怕改為雙角色也會削弱戲劇效果。
其次,玩家認為自己與角色的信息始終同步,但月羞在某個時間段的行動和故事發生在玩家的視野之外。玩家因為信息的缺失而掉入詭計。
最後,按照遊戲機制,當月羞使用自己的能力假扮NPC時,通常來說會以重影顯示,但當月羞偽裝的山寨頭領出現在玩家面前時,並沒有按照玩家以為的樣子來顯現。甚至角色本身都已脫離了玩家的操控。遊戲機制欺騙了玩家。
趁便一提,利用玩家視角的設計可能自然地需求一個meta層面的解釋。時間敘詭利用遊戲機制展開詭計,也既是說,玩家作為詭計的實施對象,已經預先被當作遊戲設計的運作目標。在時間敘詭中,meta已經發生。

敘事詭計常常利用那些作為慣例的敘事方式,而在《三相奇談》所屬的遊戲類型中,角色視角這一設計正是敘事方式中一個不易重視的環節。或者說,類型傳統中作為敘事技巧的遊戲機制,被作者有意識地利用和改造,藉此創造了新的敘事效果。
2、小遊戲:轉場與表意
作者顯然對小遊戲這個“祖宗之法”抱有懷疑。在第五章中,玩家剛剛完成了2個小遊戲,角色便吐槽這小遊戲到底有啥用?然後果然發現,機關之所以被開啟,只是因為夥伴恰好在遠處擺弄系統。而緊接在這個吐槽之後,作者又拋出了本作最大體量的小遊戲,並略顯諷刺地附上了跳關選項。《三相奇談》如何處理食之無味、棄之不能的小遊戲大禮包?

好吧,變換房間的小遊戲物理上連通了出口,至少邏輯上是直觀的
“魚缸套圈”遊戲是特別精彩的一例,作者在這裡置入了一個轉場。三寶為了結交山賊,準備試玩魚缸遊戲機。玩家進入遊戲界面,獲得分數。但當退出結算時,玩家操控的角色已從三寶變成了淨飯。旁邊的山賊透露,淨飯是第三個體驗的人。於是玩家知道,這裡發生了轉場,三寶開啟遊戲後這位山賊也玩過了,再之後淨飯來到此處。

這也是本章中淨飯第一次進入玩家的操控
一方面,此處借用了電影語言,但又有所不同。鏡頭先是轉向某處,轉回時場景已經發生變化,電影利用觀眾的視覺慣性和心理預期隱藏剪輯點,自然地實現時空跳躍。不同之處在於,電影觀眾要麼代入角色,要麼旁觀場景,只要轉場前後保持一致,鏡頭所用的視角可以選擇是主觀的或客觀的,但遊戲媒介要求玩家將自我意識投入到小遊戲裡,也即必須以主觀視角進入。玩家先扮演三寶(主觀視角),退出後玩家發現時空變換(客觀視角;從兩位角色的視角時空是一致的,變換隻發生在玩家這裡),然後開始扮演淨飯(主觀)。僅從試聽語言來說,“主-客-主”這樣的變換可能會不夠自然。
另一方面,這裡也對類型常見用法有所改進。傳統小遊戲通常意在模擬行為、進而再現情感。比如因為角色在開鎖,所以玩家也進行一個開鎖小遊戲,玩家用自己的行為補充敘述了角色的行為和情感。但“魚缸套圈”中玩家成為被敘事的對象(而不是敘事者或敘事手段),玩家“沉浸在小遊戲中”這件事本身(而不是其產生的再現效果)被作者利用了。利用的結果是玩家成為兩名角色的中介(而不再僅僅模擬兩名角色的行為),而這又隱晦地表現了:玩家意識在不同角色之間是同一的——故事最後的meta敘事進一步闡釋並補完了這一點。回頭來看,“意識同一”的設定緩和了“主-客-主”變換的不協,或者說,這轉場中的不自然,變成了敘事的一部分。
如果說“魚缸套圈”的轉場設計需要多角色、meta敘事等作為先決條件,僅算增添趣味和風格的神來之筆,那麼其他小遊戲則多少貫徹了一項實用(如果不那麼創造性)的設計原則:小遊戲(至少得)幫助表意,或融入敘事。
以貫穿始終的“切斷因緣”遊戲來說,且不論繩結作為緣結的具象,遊戲機制不斷升級,並總是伴隨了敘事上的進展。在NPC楊鬱的身上,淨飯第一次見到了變幻詭異的緣結,於是淨飯(和玩家)很自然地意識到事態變得複雜。後期三寶加入,玩家能力得到明顯提升,對兩人的情誼和信任有清晰的表意作用。其他例子包括第三章時“推方塊”標註了師兄弟的名字;“魚缸套圈”附註了暴君的故事,並在結尾重新講述。
無論如何,在小遊戲這個類型傳統上,作者在明確地做出改進,至少嘗試利用,如果不是徹底改變。

小遊戲這東西…是有點謎,常常突兀地打斷情緒和故事,不知所云,“沒活了就來一個”
綜上,作品對一些常見的類型要素進行了雜技般的創造。從設計維度來說,(挪用東浩紀的評論)這部作品是“作為使文本類型中隱藏的事物走向前臺的通道來發揮作用的”。作者在明確的意識下將類型化的條件和界限充分利用,創作全新體驗的同時,也展現了這一遊戲類型的可能性。
————————————————

一點零碎的個人感受,一併寫在後面
meta的引入有不少好處,不僅機制方面,而且敘事方面meta一站式地補全了邏輯鏈條,還緩和了亂入的現代語言所帶來的違和感。但除這些外,我還感到一個似有似無的作用:meta使作者能更直接地與玩家交流。與其字面意義“元遊戲”(超出遊戲)相反,從設計角度看,meta反而是將玩家置入遊戲之中;而與此同時,作者自己也進入了遊戲裡。
我確實感到作者的交流慾望非常強烈。除了精彩的主線段落和人物群像,諸多小故事也可堪回味,臺詞和文本充滿機鋒,各種(諧音)梗手到擒來。令狐兩千的俠客行、螞蟻驅動背後的族群記憶、畫妖們的身份認同、詩經和聊齋的引典、諸般方術的存在……幾近炫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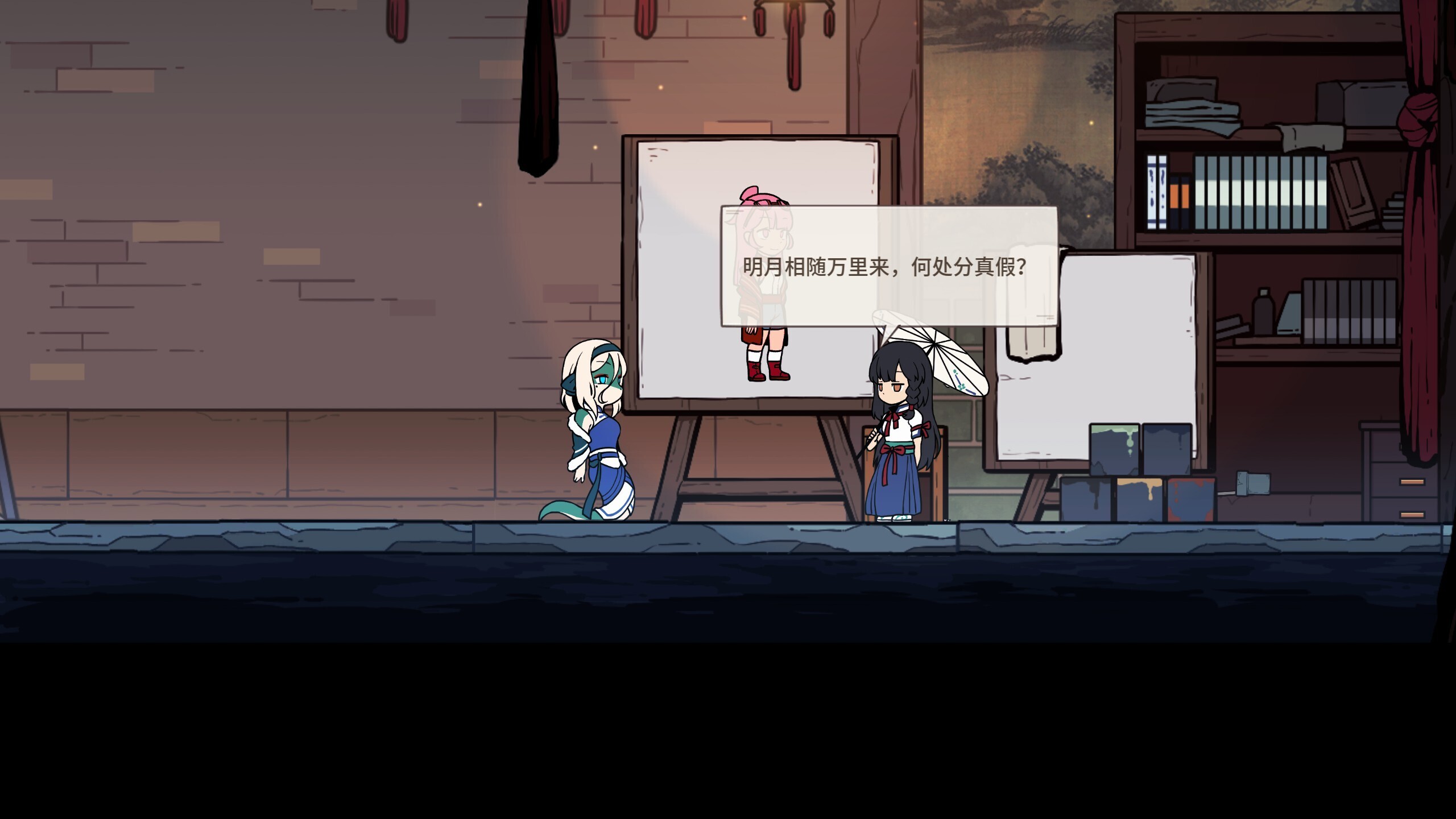
只是……那麼多慧念一閃,竟沒有一個深入下去。各種閃光小點子羅列堆砌,像是小孩子急於展示自己收藏的寶貝。精心挑選,絕無冒犯,保證娛樂。然後到了某個時候,展覽結束,燈光熄滅。所有可能的激情到此為止。既不留下什麼,也不向往什麼,就像是在一條風景宜人的小路上散了會兒步。
完全沒有責難的意思。參照類型也好,利用類型也罷。遊戲呈現了出色的故事,考慮到與遊戲交互內容的配合,其中多少打磨和巧思,難能可貴。只是當玩到中途時,我一度很想知道,畫妖們對自我的彷徨、對生命的渴望將會如何安置。

畫妖無有來處,不知歸途;就像創作時突然誕生的諸多創作激情,渴望交流,渴望被看見,渴望身份。故事的最後畫妖們獲得了戶籍,成為了青龍城的一員;就像靈感匯聚,在一個傳統類型中找到了安身之所。畫妖也是要吃飯的嘛。遊戲已完成眾籌,自然要給付費者一個交代。類型化亦是妥帖的商業決策,青龍城會給誠懇的勞動者應有的價碼。
所以真誠地祝大賣。當畫妖們都安家樂業,希望身份焦慮能被緩解。只是這青龍城本非盛世,而且畫妖們又有這麼些可能性,那麼在這個行將就木的混沌年代,或許就能期待一點新的故事,一點不同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