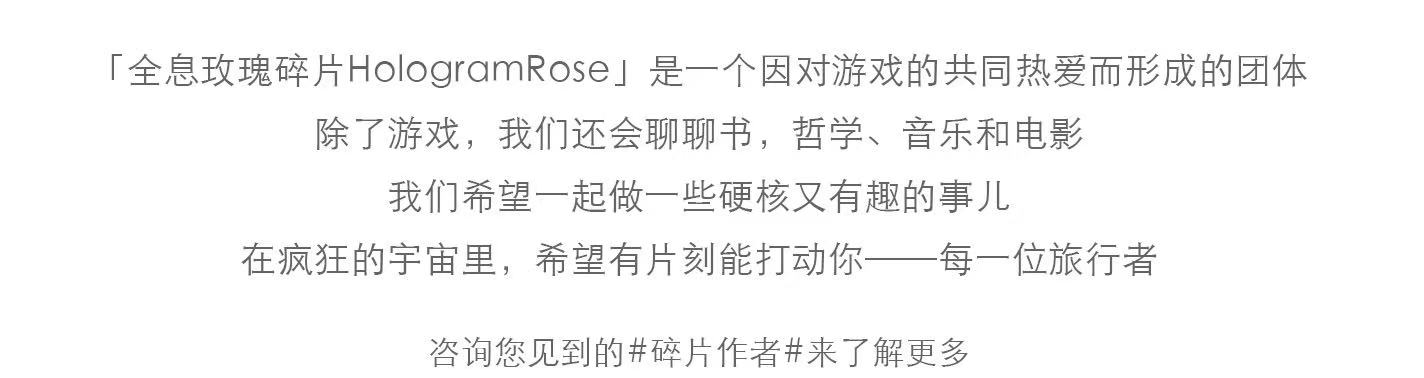前言
說來慚愧,我最早玩《史丹利的寓言》是高中時期的綠色免安裝學習版。當時民間漢化補丁非常的接地氣,字幕讓我很好的體驗了一把和旁白鬥智鬥勇。
近來聽聞《史丹利的寓言》推出了豪華版,裡面增加了許多新內容,我又正好在研究“間離戲劇”的代表人物布萊希特,一位擅長於打破第四面牆、且強調戲劇故事應當具備現實意義的戲劇革命家。兩者理念和帶給我的體驗讓他們的身影慢慢重合。
布萊希特同樣要求自己的每一部劇具有現實意義,“作為講述工人們生活的寓言”,以“與觀眾保持距離,將故事陌生化”的方式提醒每一位觀眾時刻保持思考;這又和《史丹利的寓言》不謀而合,開場的各種信息讓我們以為故事發生在再普通不過的“現實世界中”的辦公室,可不斷地反轉致使這款遊戲的真實世界觀變成了我們難以想象的模樣。Davey Wreden在製作這款遊戲的時候想讓我思考什麼?我們的現實世界思維方式上被破除後,被如何引導著反思現實問題?
我希望能夠展開講述從戲劇視角重新解讀這款遊戲和作為meta game的元素本身。由於布萊希特和間離戲劇稍稍有點晦澀,在此先以一些基礎概念作為鋪墊。
容我把我發現新鮮事物的激動情緒和語無倫次的炫技衝動按捺一下,再出長文慢慢和大家講清楚,為什麼我在重溫《史丹利的寓言》之後開始質疑我們常見的出於“第四面牆”的、meta game的普遍定義,以及在沒有遊戲的那部分歷史,戲劇界的天才創作者們在用什麼樣的作品給人類似於遊玩《史丹利的寓言》的體驗。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安利這款遊戲的時候收到了“這遊戲怎麼沒中文”的反饋。除了漢化補丁,大家也可以關注一下《史丹利的寓言》其中一位製作人、也是作為創始策劃的Davey Wreden的創作故事。我推測他在獲獎後的遭遇和精神狀態很難讓他與發行商合作,推進各語言的本地化工作。這也是為什麼在我看到豪華版推出後非常意外!製作者是其中一位原作者分道揚鑣後成立的CrowsCrowsCrows,而編劇是Davey Wreden,他們又開始合作了!
那麼我們開始。

電影空間與戲劇空間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會在電影結束之後鼓掌,好像本就應該那樣。哪怕在電影院,我也很珍惜全場觀眾默契的笑聲;只是絕大部分時候坐在一起的觀眾們似乎都沉浸在私人的體驗當中,影院數十排座位像是獨立的隔間。
無論是搶首映坐在電影院裡,還是自己在被窩裡看一部經典老片,電影與我的關係總是私密的。我可以安全的縮在角落為自己獨有的想法和體驗竊竊歡喜,但想要與人共享我的想法,就必須付出額外的努力:小到發朋友圈,大到把贅肉減掉去談個戀愛。哪怕是想看的電影碰上了檔期,我也很難自然的在電影放映室與身邊人分享,更不要說和活生生的演員建立聯繫。
如果是在劇場,觀眾很快就和陌生人融入共同的經歷,為同樣的笑話發笑,同情同樣的人物,瞭解同樣的秘密。電影要如何造成這種廣義的共同反響?觀眾在電影前單個的與熒幕建立直接關係,極少會做出集體性的強烈反應(我們總覺得大笑或者出聲會“打擾”其他觀眾的體驗,但其實不盡然),尤其不會一起鼓掌(大概因為我們覺得製作人員不會聽到)。
相比之下,戲劇在歷史上給人的始終是一種社交性體驗。要看一部現場戲劇,就必須在差不多的時間和演員到達同一個場地,在幕間休息時或許會想和身邊的觀眾攀談,結束後又一起離開。很多時候不止可以笑出聲和大力鼓掌,聽到周圍觀眾在做同樣的事情我們又會更加激烈的鼓掌、放肆的大笑。這不只是為了向演員和製作組表達敬意,同樣也包含了一種集體體驗——我們感受到了周圍人的共同體驗,這種踏實的感覺電影很難給到。
沒必要提西方戲劇,哪怕是嚴格來說屬於中國曲藝的京劇和相聲,我都會覺得如果沒有觀眾的掌聲、叫好和笑聲就少了什麼,像是演出不完整了。這也是種現場戲劇的獨特體驗。而京劇和相聲又正好是我們更熟悉的表演中,分別能夠幫助理解兩種戲劇表演的演出形式。那就是——

表現和再現
如果說戲劇是一種表演,如何定義表演這一行為本身呢?比較流行的理論是,如果一種行為最終為引起別人的注意,目的在於吸引關注、引人發笑或是發人深省,我們則稱其為表演。就拿相聲舉例:如果只有郭德綱和于謙兩人私下對話,就屬於溝通;但如果他倆故意為了讓其他人聽到、注意到而對話,“溝通”就變成了“表演”,“其他人”就成為了“觀眾”。
既然瞭解了表演,我們來籠統的區分一下戲劇表演的兩種形式:表現和再現。表現,基本就是相聲、脫口秀等的表演形式。臺上演員和在場的觀眾能“不停的”感受到彼此的存在,演員往往明確的為了觀眾而說學逗唱,甚至是唱跳rap籃球,且——這是最重要的——公開的、即時的對於觀眾的掌聲、要求、笑聲等做出反應。以這樣的定義,很多常見的手法,例如旁白、獨白、以至於謝幕都屬於表現的一種。

這爺倆演到一半看你一眼,你總不能覺得驚嚇吧
這種表演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羅馬的戲劇。我們都知道古羅馬以角鬥和鬥獸而不是戲劇聞名,可想而知當時的戲劇多難吸引觀眾——角鬥場比話劇刺激多了!也因此產生了很多根據現場情況或者在場觀眾即興的表演內容,以此和角鬥表演搶觀眾。儘管如此,古羅馬的知名劇作和劇作家也遠比不上古希臘,不過這是後話了。
反觀再現,我們印象裡絕大部分的正劇都屬於再現。在這種觀看體驗當中,觀眾往往會覺得演員和他們無關,於是他們更願意關注臺上正在發生的事件,而不是表現方式本身。無論是《戀愛的犀牛》中用跑步機(還是俯臥撐?我忘了)代表行房事,還是《暗戀桃花源》裡“老陶”在地板上蹭蹭代表划船,觀眾樂於忽視這種“拙劣的模仿”而趨於相信演員就是角色本身、臺上的戲就是正在發生的故事。“自願擱置懷疑”,是英國評論家科爾律治用於描述這種關係的名言。一部好劇不只是引人深思,更加能夠打開觀眾的感官,讓觀眾擁有感情,感到超脫,甚至自發的想要改變。

《夜半鼓聲》布萊希特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是否意識到觀眾”的表現形式和我們常見的籠統意義上的“第四面牆”並無關係。事實上如果你有機會試一試劇場舞臺演出,就會發現無論你再怎樣試圖隔絕觀眾的影響,他們的一聲輕嘆或一抹微笑都會成為對於演員強烈的刺激。如果對於戲劇中“第四面牆”的演變和被認知感興趣,我會推薦《西方舞臺設計史》。
“演員演出就像是在舞臺上吊。觀眾做出反應了,演員就活了。觀眾沒有反應,他就吊死在那裡了。”
這也是為什麼頻頻有知名電影明星寧可推掉電影檔期,也時不時要回到戲劇舞臺上:
“拍電影的過程是如此零散,挑戰性在於如何使表演自成一體。而在舞臺上,你可以遇到追波澈浪的絕對喜悅。那是一種更有張力的體驗” ——凱特·布蘭切特
對這一類演員而言,戲劇表演像一種極限運動。

遊戲中的戲劇空間
回想遊戲經歷,大部分時間都像是獨自享受電影般的體驗。先不提單機遊戲,哪怕是多人在線遊戲,現實世界中玩家坐在我左右的時刻不算多見。似乎在電腦普及到每家每戶之後,哪怕是熟人開黑大都也直接在遊戲內見面了,更不太會有陌生人坐在一起開黑的情況。或許這就是線下開黑獨特魅力的來源——一種真實的、人與人之間的體驗共享。
我們會為遊戲世界中發生的事件感到相似的情緒,並且不遠萬里來到網絡世界和素未謀面的人一同分享我們的感受;不為別的,只為“我們都喜歡同一款遊戲,並體驗了同一個事件”。《魔獸世界》首映當晚和《頭號玩家》裡高達出場時,全場的歡呼和笑聲都讓我感覺自己身處劇場。
“我認為(遊戲類)娛樂最大的一個好處,是可以創造出一種彼此共享的方式。這也就是為何在線遊戲如此吸引我們。” ——麥克·莫漢(前暴雪CEO),央視紀錄片《互聯網時代》第六集

《魔獸世界》的故事曾經真的很令人難以忘懷
我們在為一件並不真實發生的故事付出生命的一部分,為了角色的開心而微笑,為了角色的難過而哭泣。遊戲內容有能力深深的穿透屏幕,成為了我們生命裡的一部分,輕鬆到似乎遊戲本就應該具備這樣的威力。
可布萊希特偏偏不這麼想,他總是不喜歡觀眾跟著開心的角色笑或者看到傷心的角色就哭,似乎更希望觀眾看到角色笑就難受或者看到角色哭就開始;因為這至少不代表觀眾純粹的在跟隨感性,而是注入了自己的思考,得到了自己的答案。
他的一部代表作《四川好人》至今被收錄於德國高校教材課本。故事本身其實和我們熟悉的四川沒有任何關係,他就是會取一箇中國地名,僅僅是為了讓觀眾對故事保持敬畏和清醒;同樣這部劇的結尾也沒有給出任何答案,觀眾需要自己產出自己的理解。

遊戲中的表現與再現
儘管大部分遊戲內容在完成後是不變的,對於每一位玩家而言又是相同的;但隨著我們處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情緒的不同狀態,遊玩同樣的遊戲總會有不同的感受:或許我們在同一款遊戲時,我正巧讀過題材相關的書、你遇到過和角色相似的人、甚至哪怕是他的櫃子剛好動了一下,產生的體驗都是完全不同且不可復刻的。從這種角度而言,遊戲又具有戲劇的即時性。
“戲劇令人神往的原因之一在於它無法保存。你不能再次看到同樣的演出,因為它是活的…電影是死的。你可以對著銀幕笑啊、哭啊、叫啊,電影照演不誤。但是劇場裡的觀眾對演出是有影響的,不管他們自己是否知道。……那是最棒的生命之流,不是嗎?” ——伊恩·邁凱倫
戲劇史上對於表現和再現的極端人類都曾嘗試過。曾有“自然主義”流派的戲劇製作人為力求“讓演員像真實生活一樣表演”,不止會要求演員像日常對話一樣口齒不清、磕磕絆絆,更曾將一座公寓房間完全搬到舞臺上——所有的傢俱,甚至是每一片牆紙,都是真實的公寓房間裡搬出來的。
打破這種趨勢的一位名作家叫做布萊希特,著名的《罵觀眾》就創作於極端“再現”的潮流之後。這位導演利用標語、獨白、燈光等方式讓演員在舞臺上對著觀眾交流,就好像是演員在不斷試圖和觀眾直接對話一樣,並以此間接的和觀眾在演出的過程中探討社會問題。

長著一張天才的臉(不是
以此我想類推到最近更新新篇章的《史丹利的寓言》——一部常被稱為Meta遊戲的代表作,但它到底是如何打破第四面牆的?我們又是否該認定為Meta遊戲?

再看《史丹利的寓言》
像我所說,絕大部分遊戲傾向於“再現”:在近未來城市生活的仿生人產生了情緒和意識,十三位高中生年齡的少年少女駕駛機械對抗怪物,白眉拳傳人殺入幫派為報殺父之仇,甚至是試圖努力重連美國的送貨員。觀眾與遊戲之間有明顯的界限,我們可以用自己的行為推進故事,但我們本身不在故事之中。
這也就襯托出《史丹利的寓言》與眾不同之處:我們的行為在故事中有了意義,像是在和遊戲中的角色直接的交流。這樣的直接表達打破了我們在大部分遊戲中感受到的“再現”故事,而直接給到了我們單純的“表現”的體驗。

就好像劇場牆上的標語。肯定是給觀眾看的,但同時也屬於劇作的一部分。
我們“自願擱置懷疑”,不去想象控制史丹利的龐大企業到底是怎樣建立的,旁白是否有一個可供我們對抗的實體、又或是單純的程序指令,我們需要對抗的另有人在。
這一切的一切的巧合讓我無法控制自己發問的衝動:既然我們從戲劇概念借來了“第四面牆”,我們又怎麼解釋元戲劇之於傳統戲劇和元遊戲之於傳統遊戲的差異的不同?在戲劇中與觀眾交流如此普遍,為什麼我們不會像meta game那樣感到反轉?入侵現實是決定meta的門檻嗎?反轉又是meta元素的必要設計嗎?
《史丹利的寓言》是作者在《半條命》《軍團要塞》那個遊戲時代下完成的,那這個時代需要《史丹利的寓言》嗎?這個時代需要布萊希特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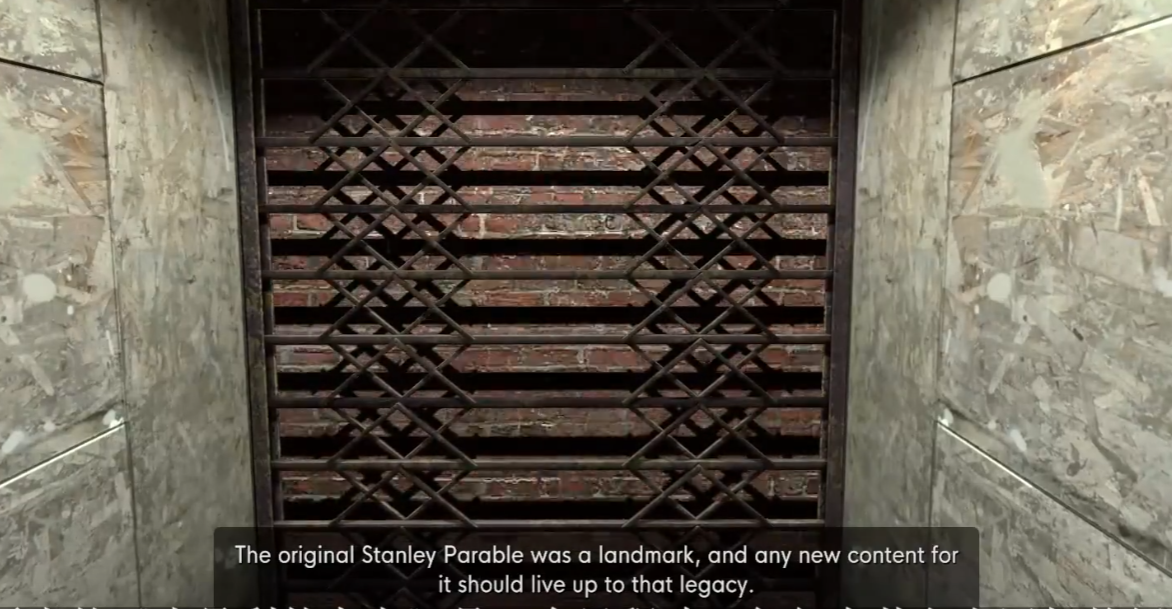
豪華版更新中的一句話,要有第二部了!!
於是我邀請了以先鋒戲劇作為畢業設計的導演專業碩士,應屆實習遊戲策劃,大學在北美做了四年華語戲劇的學生製作人,初入行的遊戲媒體工作者,電影研究碩士,產品戰略工作者……我能接觸到的各種各樣的人,在這週一起討論這個很酷但沒有什麼用處的話題!我會將參與方式或者直播鏈接儘可能的給到你,因為製作戲劇的經歷告訴我,想要探索真相,我們真的需要儘可能多樣的人!(我想表達All kinds of people哈哈哈)
來吧!

結語
我一直相信戲劇不是高大上的東西,而是生活化的、你和我每個人都能理解的。讀過這篇文章後你具備了與我一同思考的所有前置條件。現在如果你想一起研究這個很酷但沒有什麼用處的話題,可以試著看看布萊希特的劇,瞭解一下契訶夫開啟的現實主義戲劇時代是怎樣結束的、人們又開始研究什麼了。
同樣,《Undertale》,《心跳文學社》,《Inscryption》,無數你能找到的meta game;《Severance人生切割術》《黑鏡:潘達斯奈基》等等帶有meta感的電視劇或者電影;甚至是元宇宙…?
即便你沒能趕上直播,我也會整理成文章緊接著發在我的賬號,你同樣可以通過評論區穿越時空逮住我,我們一起來把這個龐大的話題說清楚!
那麼先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