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如今依旧朗朗上口的《闲情记趣》,在这趟去往山西的旅途归来之时,将我的思绪拉向十年前的一个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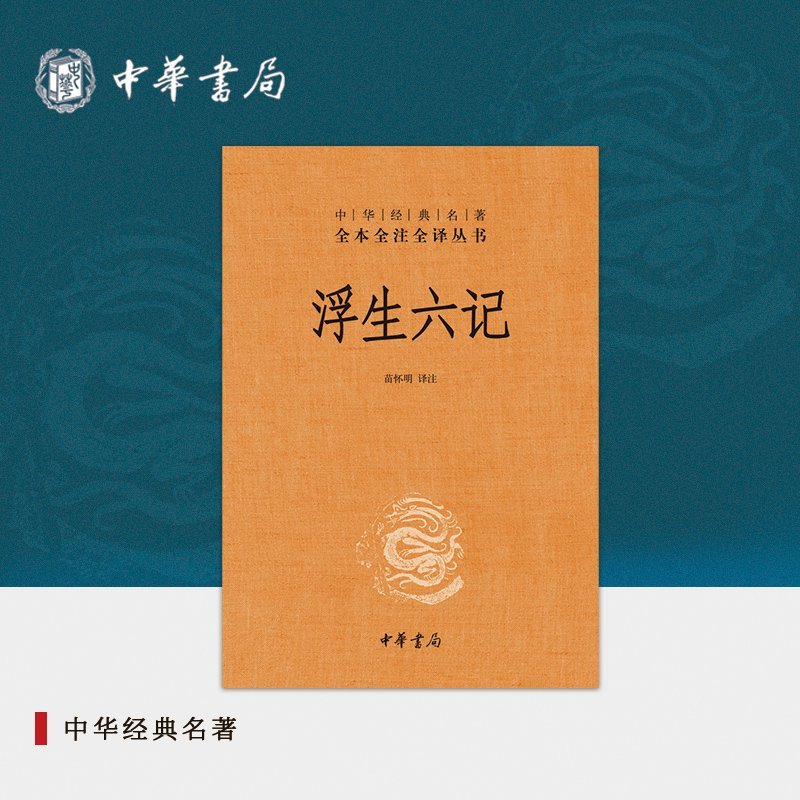
人生十年,不过尔耳。
彼时我正就读于高中,未曾恋爱,没有幻想,在枯燥的学习生活中,只知道读书所能带来的乐趣,因此周边的朋友大多在生日时会送我一本书作为礼物,《浮生六记》——这本选入初中课本的小品文集,便是这样的一本书。
即使是现在,依旧能够回想起“私拟作群鹤舞于空中”“神游其中,怡然自得”“盖一癞虾蟆”这些精彩名句,童年时期的乐趣大抵与此无异,谁幼时不曾攀树捉虫、观蚁运食,无忧无虑的时光总是掩藏于成年人的某一个奇妙时刻。
沈复,一个能够在清贫生活中发现乐趣、创造乐趣的清代文人,很难让人想到他如此的命途多舛,遇人不淑、妻子早亡、家人反目,好在在短短的夫妻恩爱廿三年中,以及在游历大好河山的旅途中,他依旧还是我们记忆中的沈复,热情积极、乐于助人,在枯燥的生活中发现奇妙的乐趣。
芸娘去世,排除自身旧疾之外,固然有封建礼教的束缚影响,但是从沈复在文中的描述,可以看出另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沟通不畅,解决问题的根源在于沟通,芸娘以“得罪公公不好再得罪婆婆”为由断绝了沟通的可能,从而导致了这场家族悲剧的开始,由“三娘”的称呼转为“三太太”,从西人索债到“谗害小叔”,大概便是从书信代写得罪公公、姚氏侍女得罪婆婆,落得全家鄙夷,恰好父母又偏爱其弟启堂,写到这里倒是想嗤笑一番,沈复前期看似养尊处优,其实从启堂娶亲搬离沧浪亭、启堂欠债诬陷芸娘,再到父亲身死启堂不曾告知、沈复流落在外启堂借钱葬父,不争夺三千两家产的沈复落得家破人亡,弟弟启堂难逃其咎。
好在诗三百关雎为首,《闺房记乐》十分出彩,读完全书,一篇《吃粥记》的小说故事已经跃然于心,“藏此专侍汝婿”,夫妻之情始于此终于此,吃酒煮茶、桂花佛手、打理庭院、对诗歌曲,二十三年夫妻恩爱,相互搀扶,还是难以忘记那句“姊何心舂乃尔耶”。二人意趣相投,彼此欣赏,双双契合,相敬如宾,男画女织,射覆对酒,非如是,焉得白头偕老哉?
恶友虽有,良友亦多,鸿干、云客、曹公等,还有承载了太多的鲁半舫家的萧爽楼。沈复一生,沧浪亭、萧爽楼,二者乃其人生乐趣的大多数,四忌、四取,喝酒五斤,着实令人吃惊。
全书亮点无疑是《闺房记乐》与《坎坷记愁》,前者写乐,后者写愁,其实二者皆为情,爱情为主,友情为辅,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
推荐大家阅读中华书局版本的,校注和翻译要好于果麦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