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了很久,該如何把遊戲的內容和我自己一些粗淺的理解呈現給屏幕前的各位朋友。每個人的遊戲進度、對遊戲的理解可能都各有不同,極樂迪斯科這個遊戲的內容又太過豐富,如果太糾纏於細節,也許會讓這個系列過於長,又非常難讀。所以我最終決定,乾脆更加自我一點,大致上按照時間順序,講一講那些觸動我的點。
我非常希望能通過我的敘述,讓這個遊戲“去標籤化”。如果可以的話,還請不要因為“深沉”、“歷史”、“哲學”這樣的標籤就接受或者拒絕它。極樂迪斯科終歸只是個要被拿來玩的遊戲,遊戲能給人帶來共鳴和快樂,這就足夠了。
一切故事,自襤褸飛旋開始
·Day 1哈里房間·鏡子
鏡子是什麼?在心理諮詢這一行,人們常常說好的諮詢師應當成為一面鏡子,讓來訪者看到真實的自己。從某種角度上,哈里房間的鏡子行使了差不多的職能:讓哈里看到了自己,把左下角模糊不清的肖像框變成了“巨星笑容”。這也是玩家第一次看到哈里的臉。
鏡子 -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你想表達什麼樣的情緒?”
你 – 這是痛苦的表現。
經驗+5:獲得經驗
鏡子 – 你是對的

這是在哈里的房間裡最觸動我的一段對話。“沒辦法消退的笑容”會是痛苦的表現,並且得到了超越性的認可(獲得經驗),這本身就是帶有諷刺性的設計。換言之,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被迫擺出某種表情的時候。學生時代被老師或者父母罵“你還委屈了是吧,我批評你批評錯了?”時被迫賠上的笑臉,到成人時代“請問還有什麼能幫助您?”的營業性微笑,大概與後迪斯科時代搖滾巨星紀堯姆·列米利翁的標誌性微笑在根本上具有某些相似之處。
救命!這是我的臉自己掛上的表情,跟我沒有關係!
到了這個時代,表情都成了社會化的對象,我們甚至不能用自己的臉公然地表達屬於自己的表情,難道這件事情不夠可笑嗎,這樣的笑容,難道不痛苦嗎?
我猜創作者的本意應該不是這樣,這部分東西非常具有“地方特色”。但是沒辦法,我自顧自地這樣理解了。我已經快三十歲了,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被批評了露出不開心的表情是不對的。
·Day 1 二樓走廊·卡拉潔
“Hello, officer.”

這溫柔的煙嗓,來自奧蘭治小姐,迪斯科舞者卡拉潔。至少在初次見面的時間點,這句問候毫無疑問的向我傳遞出一種我還屬於這個世界的感覺。卡拉潔的出現甚至早於金曷城,是整個遊戲我們遇見的第一個人。
所以,為什麼是卡拉潔呢?對於已經多周目的朋友,會知道這個角色貫穿遊戲始終,是不折不扣的主線人物。對於一週目的朋友,卡拉潔則是頗為致命的初見殺。明明哈里是位警察,至少他自己說,他是來處理“警方事務”的。可是從卡拉潔的敘述中,哈里自從來了這裡之後就躲在房間喝酒,昨天夜裡還放了招搖樂團的“喧鬧的迪斯科音樂”,後來開始放《聖桑小教堂》,一首“世界上最小,最悲傷的教堂”之歌。整夜的噪音並沒有讓卡拉潔有什麼不快,甚至沒有抱怨一句。當哈里反覆確認自己身份的時候,卡拉潔還會說:“
是的,沒有任務。玩家在遊戲裡遇到的第一位NPC,沒有你給任何任務。如果你點了“那個”判定,就會驚訝的發現,無論判定成功或者失敗,最後的結局都是卡拉潔走向自己的房間,進入,關門。無論如何敲門,敲多少次門,結果都是一樣的。
沒有任務、沒有繾綣、沒有一見鍾情,在這個場景,我們不過是與卡拉潔擦身而過的警探罷了。我們可以拼命嘗試向她證明什麼,或者展示什麼……不過,這最終都只是一次普通的晨間對談而已。這是極樂迪斯科這個遊戲與其他遊戲一個非常大的與眾不同之處:遊戲設計的目的是為了展示製作組的所思所感,而不是為了讓玩家玩下去。
我倒不是說那些以吸引玩家繼續遊戲為目的的設計就是“不好的設計”,只是極樂迪斯科這種並不完全以玩家為中心的設計,在我眼中還挺黑色幽默的:
寫這文章的我和屏幕前的朋友們,恐怕都從未有機會成為世界中心吧。 我不是哈里,也不是金曷城,我甚至不是餐廳老闆加爾特。我自己覺得,我大概是睡著的港口工人吧。大約配得上三行臺詞。 別對自己太苛刻,朋友們。差不多什麼樣的人都能躺得平。
·Day 1 一樓大廳 金·曷城
啊,金!

同舟共濟【中等:成功】 - 如果現在這棟建築遭到襲擊……如果窗戶粉碎掉落,全世界都壓在你的身上……這個男人會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來拯救你。這一點你非常肯定……但是為什麼呢?
我不相信會有人玩了這個遊戲,卻沒有被金·曷城所打動。他很溫柔,他很敬業,他與我們同舟共濟,他還有自己的道德標準,他心甘情願給我們打下手,不會搶風頭,也不會喋喋不休。他甚至做到了無條件的積極關注,沒有指責,沒有抱怨,接受了目前一團糟的事實,把目光放在應該做而沒有做的事情上。甚至可以說,這個角色是稍顯有點超越的。我認為金·曷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製作組眼中理想人格的存在,而非單純的遊戲角色。
金·曷城是在遊戲裡第一個給予我們明確的目標與指導的人,是對我們投入最多關注的人,是陪我們玩耍的人,是會在危急關頭保護我們的人。甚至他在某種意義上還部分承擔了一個“大他者”的形象,監督與評價我們的行為:如果要錢太多,喝酒太多,嗑藥太多,等待玩家的就是來自金的無情吐槽。但是金並不會嘗試矯正我們的行為,或者說,製作者沒有賦予金“教玩家玩遊戲”的職能。

我覺得這從一個側面體現出兩種文化的差異。我們的文化更傾向於大家長主義,被監護人需要接受來自家長的指導與矯正,家長需要為被監護人的行為負相當程度的責任。但是在其他一些文化中,家長對被監護人的義務就要弱很多。這在極樂迪斯科中就體現為,金並不會為我們“作”出來的事情買單。如果哈里花光了身上的每一分錢用來買酒之類的,到最後旅店老闆會說“那你不如去垃圾桶裡睡覺吧”。如果哈里真的去了,金就只會看著哈里爬進垃圾桶,落得個精神失常的下場。
哈里和金是“搭檔”,金並不是哈里的監護人。這是一種清晰的,不可逾越的邊界。我認為理想人格非常重要的屬性之一,就是與他人建立清晰明確的邊界感。有了邊界,社交網絡中的每個人就會各居其位,形成健康的關係。所以說“金媽媽”這個梗,沒準是玩家們期待中的母親形象:指導者、幫助者、關注者,而不是關於掌控與被掌控的大家長形象。
我無意比較這兩種文化。但我想說的是,在我們身邊,的的確確存在一種現象:
絕不會為你負責的實體竊取了家長的立場,嘗試指導和矯正你的行為。
比如說,前一陣子沸沸揚揚的“某公司監控員工流量使用情況”或者“上班時間行為管理軟件”。它的本質是公司追求更高的績效嗎?肯定不是。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不會認為被監控有助於工作效率的提升。它更接近於,公司在試圖超越僱傭關係,向員工植入一種“需要接受全程指導與行為矯正”的思想。一旦這樣的思想形成,僱傭關係甚至會轉向某種意義上的“人身依附”。如果終身僱傭製成立的話,興許這種做派還能顯得文雅一點。但是我相信屏幕前的讀者一定明白一個道理:沒有任何公司會為員工負責。同理可得,一樣會有實體試圖超越“戀愛關係”、“師生關係”、“合作關係”。
簡單點說,我們管這個叫“PUA”。每當懷疑自己是不是在被PUA時,不如想想金·曷城會怎麼做。
·Day 1 一樓大廳 莉娜,神秘動物學家的妻子
又是一個貫穿全遊戲的角色。哈里第一次下樓碰見的,還真就都是貫穿全遊戲的角色。

同舟共濟【容易:成功】 - 這個莉娜足夠古怪,和你們這支半吊子探案隊畫風完全一致。趕緊聘用她!
我早都忘了這位溫柔女士向我講述的神秘動物故事,但是我還記得她給我的善良綠猿人筆和紀念別針。在走出旅店大門面對吊人、工會主席、失槍等等一系列糟糕的事情之前,這位女士為我們帶來了關於世界的基本信息,也與其他人一起構建了一個情緒的錨定點——很糟糕,但是還沒有那麼糟糕。莉娜和金差不多可以算是第一批向主角釋放出善意的人,對於孤立無援的哈里來說,是在陌生世界的莫大安慰。
如果通過了檢定,得到了莉娜贈予的紀念別針,請記得贖回來之後還給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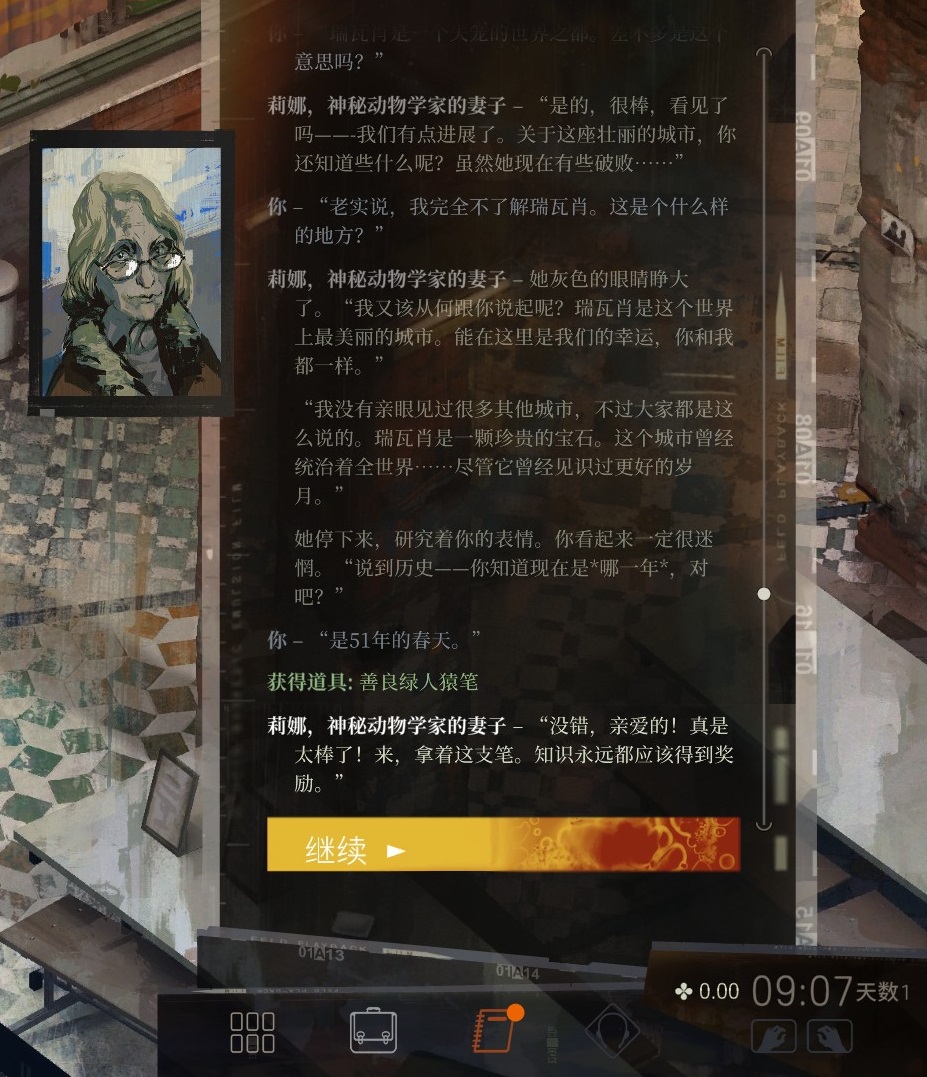
得到善良綠人猿筆的時候,看到莉娜說的話,突然就非常難過。
在我長大的過程中,很少因為“學會知識”而獲得獎勵。大多數時候,都是“通過考試”。但是這兩者顯然不能等同起來。時至今日,好像所有的知識都可以*速成*,幾個小時學會這個,多少天學會那個。我不是一個聰明的學習者,迄今為止,我也沒速成過什麼。每一項微不足道的技能,都是花費好多好多時間慢慢練習得到的成果。
我也知道很多人,明明付出了好多努力,但是也沒有取得很好的結果。當然了,能找到好多好多理由去指責一個人為什麼沒有取得好的結果。不過,那些付出過的人們,至少值得得到一支善良綠人猿筆。
“親愛的,知識永遠都應該得到獎勵。”
此外,她講神秘動物故事的時候我一頭霧水。這種東西聽起來非常玄乎,總讓人感覺到有點神神叨叨的。但是她的講述如此堅定,她的聲音如此慈祥,不由得讓人產生一種感覺:她所講述的就是事實真相。莉娜的形象會讓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我們一般稱之為“理想主義者”的人。
隨著時間流逝,“理想主義者”這個詞竟然毫無疑問地帶上一絲負面意味。屬於一般人的宏大敘事已經結束了,革命失敗了,公社覆滅了,沒有人再去質疑來自資本的“崇高力量”。人和人彷彿生來就是不平等的,高淨值人士像地痞拿走雙目失明的乞丐面前用以乞討的碗一樣,拿走本應屬於勞動者的財富。小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年輕人居無定所,商業街一片蕭條,酒精和違禁藥品暢通無阻。每個人心中都充滿了疑慮,不知道未來該去向何方。
這就是*瑞瓦肖*的現實。但是襤褸飛旋酒店裡,在世界將你遺忘的第一天,還能遇見莉娜這位並不完美的理想主義者,這很難理解成一種巧合。可無論如何,莉娜還是將竹節蟲埋在了主角心裡,或許也埋在了玩家心裡。我們都在懷疑*那個*是不是真的存在,但是一邊懷疑,卻又一邊尋找。
我想,總有一天,這顆種子會抽枝發芽,成長為足以支撐起一個人全部信仰的參天大樹。繼續奮鬥吧,我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