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導演BK離開了從事十多年的電競行業開始創業,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做了一個遊戲紀錄片公司,並採訪拍攝了幾百位頂尖的遊戲從業者。
直到現在他依然是全球華人中,唯一一個只做遊戲紀錄片的公司。
他為什麼要做這麼小眾的事情?他是怎麼活下來的?他的錢從哪來?
——————————————————————
一、上海的大食堂
我在上海的時候,印象最深的不只是這座城市的繁華,還有大食堂。
如果我盯著一種食物點,飲食相對單調,導致我手上經常長倒刺,甚至開裂,嘴裡頭還容易長潰瘍。
奇妙的是,一旦我改去食堂吃上兩天,這些症狀就會竟然緩解、消失。
我至今都覺得有點神奇,大概是因為食堂的菜餚豐富、營養均衡。

當然,除了飲食均衡,我現在還要關注血糖和胰島素。
因為血糖不穩,我時常需要在採訪或節目正式開始前補一針,生怕聊著聊著就會出現不適。
這樣的生活節奏,既讓我對身體有更深的自覺,也讓我對“珍惜當下”有了新的理解。
二、“BK”的由來
“BK”這個名字聽起來有些簡短,卻來源已久。
它最早可以追溯到98年我玩CS的時候,需要一個英文名字。
我那會兒在自學吉他,而知道藍調吉他大師B.B.King,就覺得得用個類似的名字,不僅致敬一下大神,也簡潔好記。
後來創業要註冊商標時,發現“B.B.King”這名字註冊不了,就縮寫成“BK”一直用到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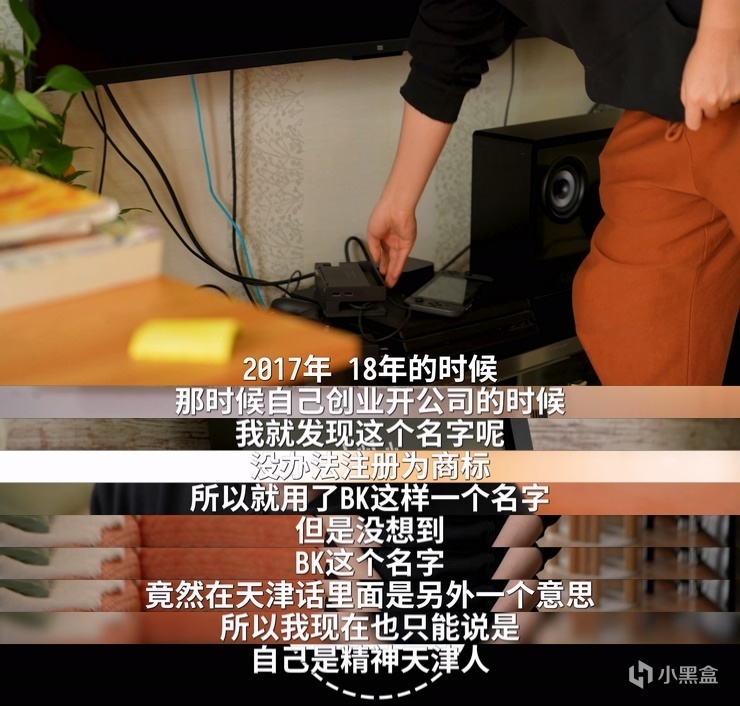
雖然我家裡囤了各種遊戲機和掌機,但一直沒培養出用手柄操作的習慣。
小時候在偏遠地區,其實見不到什麼主機遊戲,再加上我從小就對自己“其實沒那麼擅長玩遊戲”有清晰認知。
我直到大學才在別人宿舍裡第一次見到PS2,非常好奇:那黑盒子是啥?
於是大多數時間,我還是喜歡用電腦玩遊戲。
三、電競啟蒙
在我那會兒,大家並沒有“電子競技”這個概念,只說“打比賽”。
記得高中時我們年級組了個“color”戰隊,每個人都取上自己喜歡的顏色。
我們喜歡和別的年級甚至別的學校“約戰”打CS,過癮又帶著些年輕的“中二”氣息。
團隊作戰感十足,對我吸引力很大,我也很喜歡用狙擊槍。

後來我考到西安,學的是計算機。
其實那並非我所熱愛的專業,我更偏愛寫作和採訪。
不過因為堂哥選了文科,家裡人就讓我選理科,一來“家裡孩子總得有個理科的嘛”,二來也覺得我的數學成績湊合。
雖說如此,我進入西安後,意外地接觸到極其濃厚的電競文化。
當時國際賽事也陸續把西安納入賽區範圍,我在那一時期裡做過賽事籌備、活動報道,逐漸在電競圈子裡站穩了腳跟。
四、初入上海
2005年我大學畢業,正趕上WE戰隊要在上海成立,需要一個能搞商務的人。
我就揣著我媽偷偷給我的2000塊路費,坐上去上海的車,正式開始了在這座城市的電競打拼生涯。
公司給出的薪水是4000多塊,對一個年學費只有5000、只帶2000塊啟動金的人而言,簡直像做夢一樣。
第一次拿到工資時,我把現金取出來攤在床上,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地數,樂呵得停不下來。
那段日子雖然物質上並不奢侈,但我有幹勁、有激情。
2006年,我們用“草臺班子”的方式租下了長寧國際體操中心,想做一場現場4000人的電競賽事。
錢是東拼西湊來的,人手也就那麼幾位,但我們依舊成功地讓觀眾坐滿了場館,用P2P技術把比賽轉播給二十多萬人,硬是扛下了暖氣費、網費等各種開銷。
五、轉戰電視臺
到了07年,我發現一年只辦一次比賽的模式學不到新東西,就轉去了“遊戲風雲”電視臺。
當時我想試試更專業的影片製作,也想提升自己。
可惜到了08年金融危機爆發,贊助商倒閉,很多人失業。
遊戲風雲多個月發不出工資,我也被迫花光所有積蓄,還只能靠三把掛麵和一瓶醋度日,撐了一個多月。
那會兒又掙扎又興奮,因為我已能獨立剪片、策劃內容,內心裡仍對遊戲與節目充滿希望。
並且,當時的整個大環境裡面是沒有的類似節目。
所以很快我的片子就到了頻道的收視率第一,每天都能收到很多正反饋。
等到10年,技嘉科技這家曾給我們贊助的公司,重新把散落各地的老同事召集起來,說經濟危機過去了,把過去的遊戲推廣和活動運營接著幹。
我們於是再次重振旗鼓,成立了新的電競公司。
彼時優酷、直播平臺和網吧的環境也都變得更成熟,有些主播通過頁遊的聯運廣告賺到“電競行業的第一桶金”。
那份熱鬧讓我對電競的未來更有信心。
六、撞上風口,但我退場了
2015、16年堪稱電競資本的高峰,有錢人、富二代、資本大佬紛紛湧入,想要打造所謂“電競綜合體”,從直播到俱樂部再到經紀公司一條龍。
當時幾乎每天都有人來問我:“要不要再創個直播平臺?要多少錢?幾千萬還是幾個億都行,我們一起幹!”
也有人打算用電競圈熱度來炒地皮、搞地產投資。
熱衷於“風口概念”的人,花式操作層出不窮,可很少有人真的想靜下心來做內容或賽事體系。
我看著這些熱錢狂舞,心裡卻覺得不踏實。
因為我的經驗告訴我,資本是要看回報的,如果行業基本面還不成熟,只靠投資吹泡沫可能很危險。
最後我選擇在17年退出了一線電競圈,去了心動做投放,親身從乙方轉成甲方,感受另一種角色的壓力。
在當時的環境下,找UP主做插入廣告非常便宜,導致很多時候預算花不完。
而且當時的up主也非常願意配合投放,他們會想盡辦法的去在他的片子裡邊把這種植入性的廣告做得非常的有意思。
這個是跟我們那個個年代的人是完全不一樣的。
七、開始紀錄片創作
我其實一直比較擅長寫人物專訪、人物傳記,也喜歡記錄幕後故事。
2018年,我決定創業做一檔專門關注遊戲與電競人物、幕後製作的紀錄片自媒體。
決定的當下,就發了一條朋友圈,便很快就拿到了融資。
在我看來,電競或遊戲行業的真相不應只停留在賽場上,還有太多封塵的故事值得被挖掘。
然而事實是,當我真的投入其中,高製作成本與平臺流量分成之間的矛盾立刻凸顯。
平臺方一若發現視頻裡包含商業植入,輕則不推薦,重則限流。
看起來理所當然的廣告收入,往往很難真正落到我們頭上,播放量也無法覆蓋團隊開支。
為了維持生計,我們嘗試拍一些人們更好奇的話題或網紅,從而快速漲粉、獲取流量。
雖然後來數據確實大漲,但我內心依舊對“幕後大佬和行業深度”這一塊兒念念不忘,總覺得那才是我想要長期堅持的東西。
八、“心動”再拉我一把
2020年的YQ來得猝不及防,團隊成員大多是外地人,春節回家後無法返滬。
我被迫解散辦公室,暫時停止不少拍攝項目。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我進退兩難之時,心動“老甲方”又一次出現在我生命裡——他們要做一款平臺跳躍類格鬥遊戲,名叫“Flash Party”,希望我跟拍一年研發全過程,做成11期的紀錄片。
對我而言,這既是機會,也是一種“救贖”。
我喜歡深入團隊去拍他們如何設計角色、如何測試打擊感,還有團隊內部的小爭吵、小糾結。“有人願意出錢拍攝幕後”,還讓我“聽故事”,我當然興奮。
儘管這片子在大眾平臺的播放量一般,但團隊內部和玩家社群反響很好。
心動也覺得這是一個可以留下測評、研究與傳播價值的內容。
對我來說,這些幕後點滴讓我看到更真實的遊戲行業,也真正讓我在艱難環境裡找到了一絲空間。
九、錢從哪來
在“Flash Party”之外,我又逐漸展開“錢從哪來”這一系列,繼續聚焦遊戲與電競行業中的不同主體:有強資本背景的大廠,也有寥寥數人的獨立團隊。
尤其是做獨立遊戲的這群人,讓我深受觸動。
他們常常不被外界看好,資金薄弱、技術也許並不頂尖,可就是因為熱愛,咬牙堅持了下來。
我想起自己當年在一個沒人認可的時代搞電競,也是一種“草臺班子”,卻能迸發出巨大生命力。
這些獨立開發者在項目反覆跳票、經費嚴重透支時,也常常被質疑“跑路了”。
可當我近距離拍攝時,看到他們依舊會為了一個設計不睡覺,翻書、學程序、挑戰架構。
我能理解那份“偏執”,正是因為曾在另一條路上同樣頗有共鳴。
十、不放棄記錄的理由
我在家裡養了四隻貓,全是流浪貓,一年撿回一隻。
起初我並不擅長照顧小動物,可是隨著時間推移,它們對我的信任、依賴讓我對生活多了一份牽掛,似乎也軟化了我的性格——因為我得保證它們按時吃飯、打疫苗、體檢。
有些貓平時對人很高冷,可一旦覺得我情緒不對,居然會跳到我懷裡蹭臉,傳達一種“你別難過,還有我”的信任感。
這種奇妙體驗與我拍紀錄片的心態也互相呼應。
就算外界再風雲變幻、平臺政策再迭代更新,我都還有這一群小傢伙默默陪伴,還有我的團隊和觀眾在背後支持。
我始終覺得,熱愛與堅持本身就值得被記錄,不論它能否得到主流資本的青睞,不論數字流量是否能跑贏成本,它依舊是我想做且會一直做下去的事。
導演BK
專注遊戲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