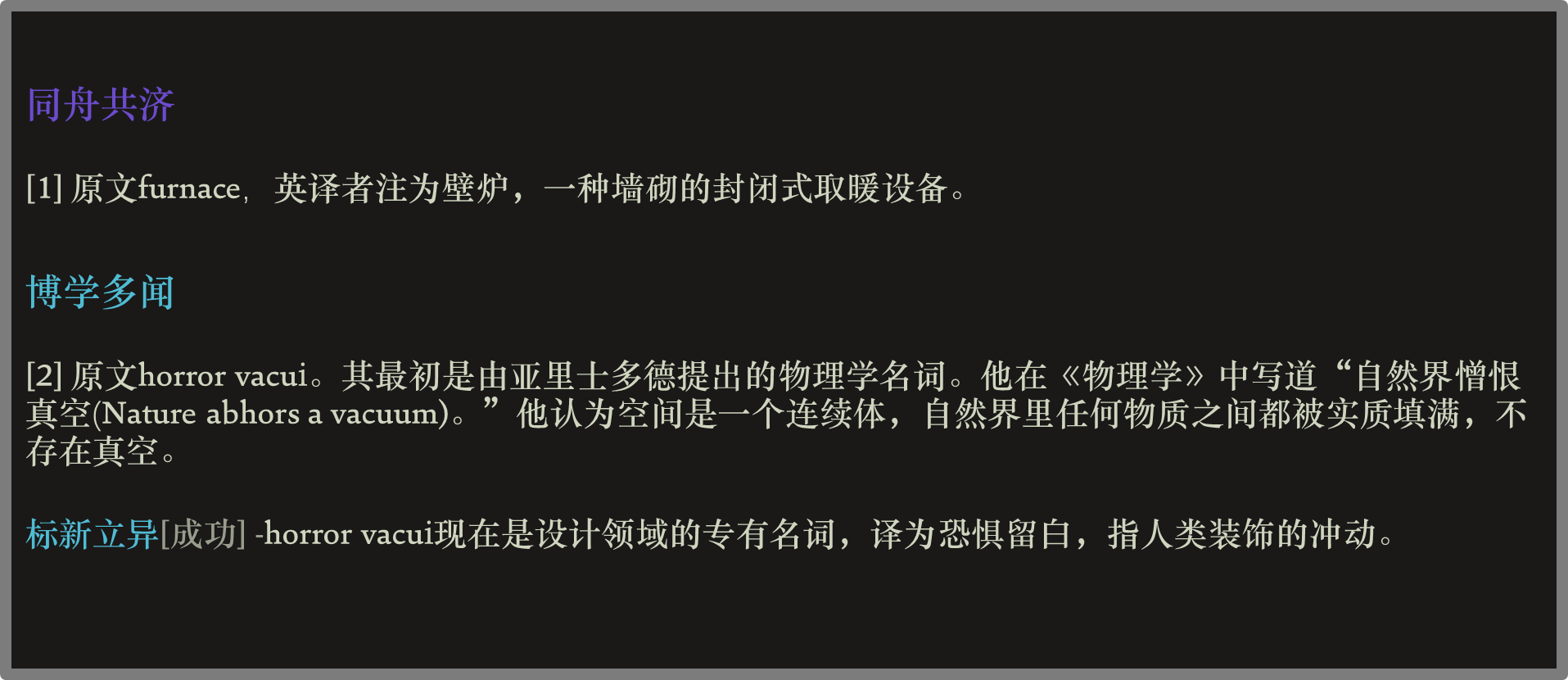瓦薩附近的夏季度假村吞噬了倫德家的四個女孩。連同她們嬌小骨骼和曬得黝黑的皮膚一同消逝的,是整個時代。六千米長綿延曲折的海岸線,在50年代是盛極一時的游泳勝地;換衣間鱗次櫛比,茂盛的蘆葦在風中沙沙作響。你能在那裡找到一個保守黨哀悼的時代。回到那時,父母往孩子們夏季短褲的口袋裡塞2雷亞爾,用來買冰淇淋和公交車票,讓他們在無人看管下去海灘。家長們擔憂地搖著頭,隱瞞從梅西納、格拉德和格特瓦爾德傳來的消息,那裡——對他們來說——每週都能發現小型骨架被投進了誰家的烤爐[1]裡。似乎每週都有被囚禁在地下室三十年的某人的女兒逃脫,跑到街上哭喊著求救。
但不是在這裡。
這裡,有社會民主主義,以及嬌嫩的社會民主之桃花,溫和的社會項目。在這些進步的事物裡,人類破損的靈魂開始感到慰藉。那種詭異的,想要建造秘密地下室的技術衝動永遠不會抵達市郊。這裡我們有開口在花園草坪,外表裝扮成微型陶土風車的通風系統。
那些腦海裡陰暗的狂熱,在郊外的清冽霧氣中冷卻;人們頭腦中病態的想法,在遙遠藍色冰川的吐息中凍結。瓦薩。你最好住在那裡。
說回到一個晴空萬里,白雲朵朵的星期二早晨,四個姐妹——瑪姬(5歲)、安妮艾琳(12歲)、瑪琳(13歲)和夏洛特·倫德(14歲)——一起去海灘游泳。她們帶了2雷亞爾現金,四身泳衣,一些食物和飲料,以及裝在兩個沙灘包裡的兩條大毛巾。早上9:30,她們從瓦薩的一個郊區,洛韋薩,登上了有軌馬車。列車司機仍然清楚地記得她們。二十年後的今天,對於住在療養院,尚能談論此事的羅蘭來說,那天還記憶猶新:“年紀最大的那個給每個人都買了票,去夏洛茨扎爾。40分。每張10分錢。如果她們再多坐一站,那每張票就要20分錢了。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國道的起始地,關稅要高一倍。但我的天吶,多麼漂亮的女孩!還那麼有禮貌!那個年紀最大的,夏-洛-特!”老人有節奏地滔滔不絕。“我當時不知道,後來在報紙上讀到的。然後我就直奔警察局了,毫不遲疑,一秒也不敢耽誤。”
上午10:25,女孩們在夏洛茨扎爾海灘下車。正如好孩子那樣,她們一個接一個對列車司機道謝。那天早上沙灘非常炎熱,人影稀疏。
女孩們隨後遇見了冰淇淋店的售貨員阿妮莎。二十年前阿妮莎還是學生,冰淇淋店的工作是她暑假的兼職。瑪琳和安妮艾琳買了四支冰淇淋:兩支香草味,一支檸檬味和一支巧克力味。沒有看到剩下的女孩們。百葉窗都被拉下來阻擋陽光,櫃檯旁邊,唯一沒被遮擋的窗戶展示著商品陳設。這是工作日的早上,客流稀疏,年輕的阿妮莎記得女孩們以及她們固定的口味偏好。那天,瑪琳最愛的胡椒薄荷口味已經賣完了,因此出了點小狀況。出乎意料的是,除了冰淇淋,女孩們還買了三個油麵糊炸的肉餅,這使賬單達到了1雷亞爾50分。女孩們離開了店鋪,阿妮莎注意到,有一個男人在櫃檯旁未被遮擋的窗戶裡陪著她們。阿妮莎記不得其他任何關於那個男人的信息了。年齡、身高、衣著,那裡是否不只一個男人——或者,阿妮莎之後將思考的——那真有個男人嗎?
這是女孩們最後一次出現。
兩天前才宣誓就職教育部長的安·瑪格麗特,和造紙商卡爾·倫德的四個女兒,失蹤了。媒體開始了對本案長達數年的密切關注,所有細節都被刊登在報紙欄目中,而倫德家的四個女孩則被裹挾至民族記憶的深處。失蹤故事本身成為了雷亞爾區最著名的懸案之一。
大約12:40,距離女孩們應該到家的時間——六點——前的五小時二十分鐘,以及她們出現在冰淇淋店的三十分鐘前,三個男孩坐在客廳裡。陽光穿過條形窗簾灑進房間,一片金黃。這些男孩是其中兩個姐妹的同學。高個子的雀斑男孩正把電話舉在耳旁。
“快點!都打電話了,撥過去!”金髮男孩在後面催促道。
“嗯,如果比我們約好的時間早三小時打過去,可不會留下什麼好印象…”
胖胖的伊爾瑪移民扯著高個男孩的袖子:“認真的,特雷斯,打過去。不太對勁!”
“我知道,我知道。”特雷斯說,鐵質撥環在他手指下叮叮作響。
可怕的時間噪音接近了,那是世界上最暴力的聲音。不再有金色的陽光射入房間,取而代之的是深不可測的灰域。在那裡,任何距離都不可逾越,*真空恐懼[2] *充斥在每個物體之間。

HORROR VACUI - Aleksander Rost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