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間鏈接:Harun Farocki 平行I-IV Parallel I-IV (2014)
譯按
本文適合於配合日 | 落 譯介計劃網站收錄 Adam Jesper 的 哈倫·法羅基最後的項目 文章一同觀看。就像在文章中所描述的,「作為對電腦生成圖像歷史的思考,《平行》可被視為法羅基對電影命運畢生探索的延伸,同時亦可視作與該項工作的大膽斷裂——一件反思性的脫離之作」。
而我則是在與徐露試圖取道於 Video Essay 與 Latour 的傳統來嘗試切近電子遊戲,作為可玩的,或者是「過程式」媒介的某些潛能時,不可避免的再度遭遇了法羅基。而這也是哈倫·法羅基研究所的首位駐地藝術家,視頻論文製作者李起萬(Kevin B. Lee)《視頻論文十週年》的演講上觀眾所指出的那樣:「在視頻論文領域,法羅基就是那個大他者。」
某種意義上,法羅基是我們要處理無論是視頻論文-可玩論文、視頻論文與遊戲、遊戲與電影(運動影像)的某個中間點。法羅基在《平行》四部影像中對遊戲中「樹,水」「邊界」「佈景」「人」的考察就充分展現了某種視頻論文的豐富面向,他不僅僅是要傳達出某個觀點,更像是詩意的陳述,策展與連接評論,對電子遊戲進行了片段的選取重組,找尋並呈現虛擬和構造的模式。
這種虛構與現實的齟齬,到達虛構世界的邊界「出戏」和崩塌的瞬間對玩家,遊戲開發者,技術人員來說絲毫不稀奇,在網上你可以找到大量玩家以此為樂,津津樂道的話題,(甚至有大量在現實中模仿遊戲中的bug,做作的行走姿態,cosplay,重演,重拍第一人稱射擊鏡頭,穿模笑話等等),但這卻似乎很容易吸引學術和藝術界在對此批判而大驚小怪,但哈倫·法羅基可以說避開了這一姿態,我們絕不應僅僅將其看作對於某種電子遊戲虛擬性,或空洞性的批判,而應將其看作對於這種新影像令人激動的觀察與沉思:
就像法羅基在2011年夏天寫給拉賈曼的信中所說,「新項目令人興奮,那些膠片先驅和數字餘像。我想象著大海如何閃光,樹葉如何在風中飛舞,沙子如何漂移。」
在《平行》中,他也構想計算機生成影像的出現之於電影是否能夠如同「攝影的出現之於繪畫」那般也許「讓電影在其他方面得到解放」。
《平行》中有段話這樣描述:「讓人想起了一個孩子,他把一個洋娃娃切開,以探索再現的奧秘」,而巧妙即是在於法羅基沒有陷入這種解構化的還原,而對素材進行了漂亮呈現和組織,呈現出了電子遊戲圖像的邊界,以及其運作的方式(How it works)。我認為重點不是這些數碼物的「空無一物」,而是其僅僅通過表象和某種數據進行再現就能夠創造世界的運動的這一事實。
落日間
葉梓濤
校按
這個作品可以看作是法羅基的操作圖像理論下的一種實踐。他將遊戲放在更長的視覺歷史中,將計算圖形的圖像史與藝術史並接,以媒介考古學的研究方式追蹤技術圖像的不同形式。其實,有關數字圖像或者視覺論文的研究已經有很多,但我們更感興趣的是圖像作為一個關鍵領域,感知和行動如何在這裡相遇,圖像如何成為動員我們身體與影響我們認知世界的實踐方式。不論是翻譯Latour的可視化,還是介紹Farocki的研究,都是為我們以後探索可玩論文做準備。這些作為模式、測量、說明和非再現性圖像的視覺形式不同於以往與現實保持著索引聯繫的影像,它們重演世界時不僅邀請觀看者仔細觀察和聆聽圖像的變形,也促使觀看者思考 X/Y 軸可視化以外的Z軸——一種推想的時間,而這種時間又將與當代空間成像實踐產生共鳴。
徐露
Harun Farocki

哈倫·法羅基(Harun Farocki, 1944-2014)出生於與德佔時期的捷克斯洛伐克。從1966年到1968年,他在柏林德國電影與電視學院(DFFB)學習。除了在柏林、杜塞爾多夫、漢堡、馬尼拉、慕尼黑和斯圖加特擔任教職外,他還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訪問教授。法羅基為電視和電影製作了近120部短片和長片,大多數是分析社會現實的紀錄片和論文電影(essay films),他精確地使用運動影像,並關注圖像創作中涉及的政治和社會學背景。他還作為編劇、演員和製片人與其他電影人合作。
1976年,他與 Hanns Zischler 一起在瑞士巴塞爾上演了 Heiner Müller 的戲劇《戰鬥》和《拖拉機》。1974年至1984年,他是《Filmkritik》雜誌(慕尼黑)的編輯和撰稿人。他的作品曾在世界各地的畫廊和博物館的許多展覽中展出。從2000年到2004年,法羅基在柏林他以前的學校DFFB和藝術大學任教。2004年,法羅基首先成為維也納美術學院的客座教授,然後在2006年成為正式教授。作為一名教師,哈倫·法羅基對備受讚譽的柏林學派電影運動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電影和思想影響。於2014年7月30日死於柏林附近。
而我們也不能忽略了其工作的長期合作者馬提亞·拉賈曼(Matthias Rajmann),據說他們共同為了這個項目收集了近千段影像素材,並且法羅基僱用了拉賈曼十幾歲的兒子連續幾個小時地玩遊戲(從檔案來看,應該有幾百次這種連續幾個小時的活動),以此來獲取完成作品所需的原始素材。
Parallel I-IV
電腦動畫目前正在成為一種普遍的模式(general model),超過了電影。在電影中,有吹來的風和由風力機產生的風。而計算機圖像沒有兩種風。
在2012年至2014年期間,《平行I-IV》深入研究了當代運動圖像(moving images)製作中涉及的技藝和技術。通過電子遊戲、工業電影和軍事影像記錄計算機動畫的發展,法羅基拋棄了「真實」的電影概念,揭示了不可見的勞動如何被無形地呈現在屏幕上的數字世界中。
法羅基的四部曲《平行》(Parallel)涉及計算機動畫(Computer Animation,或動態的數字生成圖像CGI)的圖像類別。該系列的重點是計算機動畫世界(computer-animated worlds)的構建、視覺景觀和內在規則。
「一百多年來,攝影和電影是領先的媒體。從一開始,它們不僅起到了信息和娛樂的作用,而且也是科學研究和記錄的媒體。這也是為什麼這些複製技術與客觀性和當代性的概念聯繫在一起,而通過繪畫創造的圖像則指向主觀性和超理性的(transrational)。 顯然,今天的計算機動畫正處於領先地位。我們的主題是數字動畫的發展和創作。例如,如果一個森林必須被樹葉所覆蓋,基本的遺傳生長程序將被應用,這樣就可以創造出「有新鮮樹葉的樹木」,「一個森林中一些樹木長著大概新生四周的樹葉,另一些長著新生六週的樹葉」。生成算法(generative algorithms)用得越多,圖像就越能脫離發現的表面現象,而成為一個理念典型(ideal-typical,譯註,柏拉圖的視角下,在評論文章中描述那些與實際物體共享特性,但並不忠於或呼應於某特定實例的模型)。 通過使用樹木和灌木叢、水、火和雲的例子,我們比較了過去30年計算機動畫圖像中表面和色彩的發展。我們想記錄現實效果,如反射、雲和煙的演變歷史。」 ——哈倫-法羅基
《平行 I》(15:53分鐘,2012)開啟了計算機圖形的風格史。20世紀80年代的第一批遊戲僅由水平和垂直線組成。這種抽象被視為一種失敗,而今天的表現形式則以照片寫實主義為導向。
《平行 II》(8:38分鐘,2014)探索了遊戲世界的邊界和界線。該作品講述了人物通過任何手段逃離他們的動畫世界的邊緣的嘗試,並試圖揭示這些被定義的空間和數字邊界之外的東西。
《平行 III》(7:21分鐘,2014)尋求遊戲世界的背景佈景及其數碼物的本質。它揭示了數字世界的形式是漂浮在宇宙中的圓盤,讓人想起前希臘化時期(pre-Hellenistic)的宇宙概念。這些動畫世界就像單面的戲劇舞臺,只有通過全知全能的攝影機的運動才能看到其平坦的佈景。世界中的物體往往對「自然力量」沒有反應。它們的每一個屬性都必須被單獨構建併為它們指定。
《平行 IV》(11:20分鐘,2014)探討了電子遊戲世界中的主人公(hero)和主角的行動。這些主人公沒有父母或老師;他們必須測試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並自行決定要遵循的規則。法羅基指出,這些角色是「人體模型(homunculi),擬人化的存在,由人類創造。誰和他們一起玩,誰就能分享創造者的驕傲。」
(校注:homunculi 這個詞來自拉丁語,是 homunculus 的複數,指「人工製造的小人」,也就是緣於鍊金術的人造人。因為ho-(human)和cul(小)的組合,所以也有侏儒和矮人的意思,但仍然和源於鍊金術的人造人有關(在玻璃瓶中培育出的拇指大的小人)。)
本片源為油管尋找到的網友版本,還請對此有興趣的朋友前往藝術館進行觀看(昊美術館曾策劃了法羅基的許多展覽 HOW皮膚之下,機器之間 | 哈倫·法羅基:深度遊戲)。
《平行》
翻譯視頻鏈接:【日 | 落譯介】哈倫·法羅基(Harun Farocki)平行 Parallel I-IV (2014)

以下為字幕
《平行 I》
哈倫·法羅基(Harun Farocki)
翻譯:葉梓濤 校對:徐露
1980年的《謎之屋》 第一個有圖形的電腦遊戲,房子能進入,但邊上的樹則沒有遊戲功能(no game function)
計算機遊戲歷史上對樹進行再現的歷史。

這些樹在遊戲中有一定的功能,當它們擰入泥土時,周圍的方塊變成紅色,並不再能夠被訪問。
現在樹葉在風中輕輕搖擺,鳥兒飛過圖像(images),有些只是影子。
計算機遊戲的世界現在可以被分別地探索,你可以檢視背景或其他細節。
三十年間,從線條畫到一種難以與真實的電影拍攝區分開的寫實圖像(photographic images) 。在1980年,只有垂直線和水平線可以使用,而回到1986年,每一個形狀都得用方塊(像素)組成。
樹葉與枝幹幾乎都學會了移動,問題已經變成了,它們是否運動得太呆板了。或許一根細枝應該彎曲得比一根粗枝更多。
在電影中,有吹來(blurs)的風,也有由風力機產生的風,計算機圖像中,只有一種風。
一種新的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
這是一個由方塊構成的火焰,他們說那時候他們只能用方塊構成事物。
有人用同樣的方式說: 埃及人只能通過側面輪廓繪製人像。
你可以在水鼓裡重演一場海戰。同樣,一種形式的圖像歷史,可以作為另一種類型圖像發展的模型,繪畫,膠片,計算機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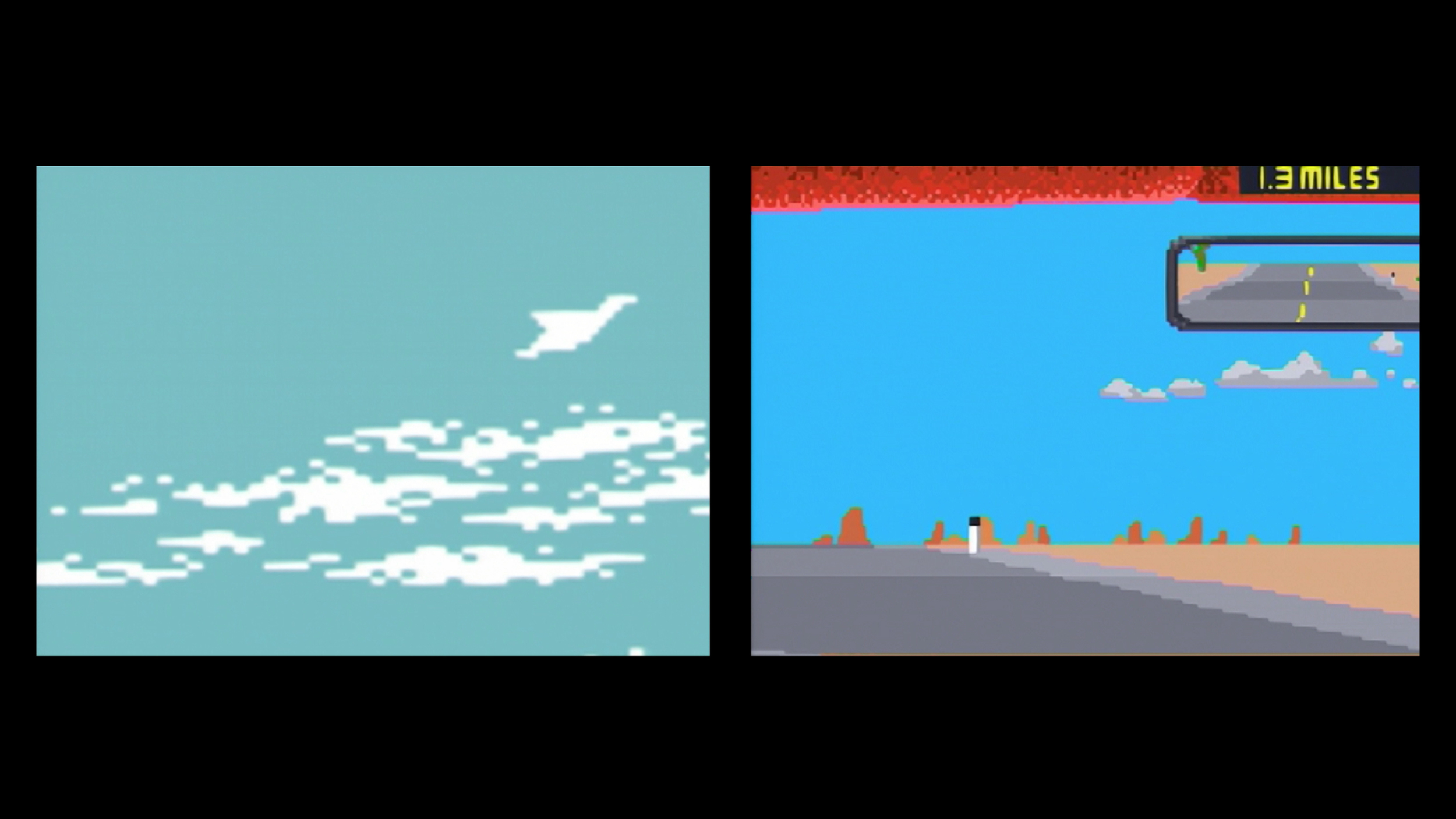
「戰爭的消息迫近」,「厄運已經襲擊了南方的燈塔」。
大多數現代畫家拒絕承認官方的藝術史。其中認為,早期再現的藝術是侷限的,在攝影出現後經歷了一些挫折之後,才有所進步。
在這裡,水被表示為帶有綠色斑點的藍色表面,用虛線和點構成的運動著的水(water in motion)。

計算機圖像的創造者不必等待數千年才等到文藝復興。從一開始,他們的圖像就與技術人員和科學家的工作密切相關。
這些圖像也顯示了從象徵性的形式到電影寫實主義的發展,從抽象到具體主義(concretism)。
在這裡,泡沫隨著每一個波浪向上徑直飛濺,顯然表面之下有什麼東西直接擋住了水流。
在(用計算機生成的)虛擬畫面(fiction film)中,我們會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種效果。如果飛濺的泡沫被認為是某些事物的線索,例如沉船,或是水泥棺材。
虛擬攝像機可以潛入水下,但是並不能看到海底。岩石浮在水面上。
讓人想起了一個孩子,他把一個洋娃娃切開,以探索再現的奧秘。
埃及人能造金字塔,中世紀的人則創造大教堂,但它們都不能用透視的方式來進行再現。
這是我們在學校所學到的,這是用小方塊構成的雲。
根據神話,希臘人宙克西斯(Zeuxis)能把水果畫得如此之逼真,引得鳥兒去啄食。
由計算機創造的雲,以及由鏡頭所拍攝下的雲。右邊閃爍的圖像表明它來自相機。
也許計算機圖像將承擔先前電影所具有的功能,也許這會讓電影在其他方面得到解放。
計算機圖像試圖達到電影圖像的效果,它想要超越它們,將它們遠遠甩在身後。
計算機圖像的創造者不想吸引成群的希臘鳥兒,他們的天堂應該由他們自己設計的造物所居住。
《平行 II》
如果我不看它,這個世界還存在嗎?一個乘火車或汽車長途旅行時孩子的視點,
掠過的一切都是為我而設的,從空無(emptiness)中出現,然後又消失在空無之中。
飛快地衝出大門,騎手能騎多遠,這個世界的盡頭在哪,這個世界似乎是無盡的。

一個由凝視落於其上而產生的世界。
這片蠻荒的西部世界有著天然的邊界。
這些人物被包裹在一個隱形的膠囊裡,就像一個安全氣囊,它保護和支持著橫向移動。

這個洛杉磯也有著不可見的、幾乎無法逾越的邊界。
「你瞎了嗎!」 「抱歉,這裡是警察,我需要你的車」 「當心點,警察」 「這是來自你的工資,不是我的」
噴氣式戰鬥機收到了一條警告,被許可的空域用藍色表示。而橘色的此處則是禁飛區,最終警告,消失在無形的邊界上。
這個遊戲世界是一個平面,就像古希臘時代之前的地球。
這個程序是為了保護遊戲中的人物不從世界的邊緣掉下來。
在這個遊戲中,你可以在某個特殊模式下突破安全屏障,掉出而落入太空中,就像宇航員從飛船裡彈射了出來一樣。

在這種模式下,通常不可見的邊界變得可見,就像從背後無法看見的大門或畫影線(hatching),這裡又是橫向移動(sideways movement)。
一個由鋼鐵和玻璃構成的圓頂包圍著這個搖搖欲墜的地區,像一個奶酪圓頂或蒼穹。
《平行 III》
我們可以直接切入事件的正中心。
而只需一個簡單的命令,我們就可以輕鬆地離開這個地方,
不久就會達到遊戲表面的極限。
表面之外是一個佈景,就像在劇院裡一樣。
世界以如同一場棋盤遊戲一樣結束。
那兩個人從樹籬中穿過,而沒有一片葉子被擾動。
這些物除了自身之外,沒有別的存在 而它們自身就是無(nothing),它們的每一特性都必須被特定地構造(constructed)。
這是遊戲角色的移動讓樹枝運動的構造。
在這裡,鏡頭試圖穿透一個公共雕塑的基座,基座的主體被構造成如同一塊石頭,子彈會打出彈坑。
在這個特殊的劇場模式下,攝像機可以穿透基座,就像故事片中的攝像機,移動攝影車穿透牆壁,以此來建立敘述者的全知全能。
很明顯,這個方塊是中空的,從內部看不到牆體。
在這裡,攝像機試圖穿透地面,它的目光就像鐵鍬在敲打堅硬的土地。
從下方看不見大地的表面,它缺少能被從兩面都能被看到的特性。
攝像機可以輕易地穿透岩石峭壁,這些岩石並不結實,它下方是海。
水的表面僅僅只是表面,它下面沒有水,它在空無中漂浮。
這個世界漂浮著,就像原始海洋中的島嶼。

《平行 IV》
主人公被拋(thrown)到了他的世界中。
主人公沒有父母,也沒有老師,他必須自己學習哪些規則是有效的,他接近其他人。
「停」 「你真是個混蛋,你知道嗎?」
這位探索著他的世界的主人公。在這兒遇到了他無法推搡或衝撞的人,他打不到他們,射不到他們,他們就像黃昏的生靈,某種介於人與道具(prop)間的東西。攝像機之眼在他們周邊滑動 就好像他們被一個隱形的安全氣囊保護著一樣。

「你不在乎誰擋了你的路,不是嗎」 「ah」 「走開!別擋我道!」 「嘿!看路!」 「哦不,他要把我們都殺了!」 「跑!」 「什麼鬼!」 「oh」 「沒人告訴你怎麼打架嗎?」
「停止這一切,在有人受傷之前」
「救命!我被襲擊了!」 「你還是趴著吧」 「你干涉到我的私人空間了」 「你擋著我道了」 「聽著,混蛋,讓開!」
「你到底在做什麼?」 「這是你的選擇,別放在心上」
那位女售貨員只有很短的記憶,一旦等她出了門,她就忘了男主角之前拿槍指過她,她回到了正受到威脅的商店,然後再次逃離了商店。
「這是個啥?」 「我在戰爭中長大,這沒什麼」 「嘿,這是個醜陋的城市,我的朋友」 「你想嚇唬一個老女人嗎?」 「我的脾氣很暴躁」 「別惹惱我」 「保持冷靜!」 「別做傻子」 「這就是把槍」
如果她受威脅,她就必須離開商店 當她在外頭,她必須再次回到商店。
這個悲劇的星叢,向主人公揭示了人類行動自由的侷限性。
「上帝啊,救救我!」
《平行 I》中的遊戲名
《陷阱》Pitfall 1982
《國王密使系列》King’s Quest 1984
《薩爾達傳說》The Legend of Zelda 1986
《群島》Archipelagos 1989
《上古卷軸:競技場》The Elder Scrolls: Arena 1994
《紀元 1602》Anno 1602 1998
《紀元 1701》Anno 1701 2006
I’m just researching these strange new images which are somehow on the verge of competing with and defeating finally the cinematographic photographic image, so that the era of reprduction seems to be over more or less, and the era of construction of a new world seems to somehow on the horizon, or already here. 我只是在研究這些奇特的,新的圖像,它們以某種方式處在與電影與攝影圖像的競爭並將其最終擊敗的邊緣,因此,複製的時代似乎或多或少已結束,而對新世界的構建的時代似乎在以某種方式即將到來,或已然在此。 —— Harun Farocki: Cinema, Video Games and Finding the Detail | TateShots

Kevin B. Lee《我在哈倫·法羅基研究所駐地期間學到了什麼》(BV15T4y1Q7NJ)
圖像文化的新時刻:從視頻論文的興起到技術生態的拓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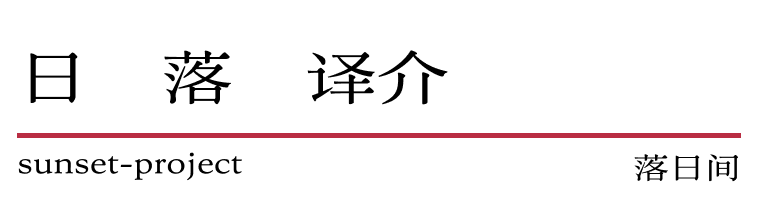
日 | 落譯介計劃 是媒體實驗室落日間對一些有助於思考遊戲/電子遊戲的外文文本翻譯和推薦/索引計劃。(查看網站)
感謝支持落日間的朋友
歡迎讚賞或在愛發電贊助落日間
(PS:落日間的免費電子書寫作計劃的內測已開始,歡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