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隱藏道路”——是指引還是坑爹?
在近期如火如荼的褪色者追逐艾爾登法環的路上,“建言”成為了冒險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們經常會來到一個光影昏暗,地勢險峻,但外貌可疑的探索地點,然後就有一些“三道槓”的建言指引我們前行:“前有隱藏道路”→“前面需要跳躍”...然後就是在一聲慘叫中化作一攤血跡,憤憤不平的撿回丟失的盧恩,給這段建言留下一個“前無馬”的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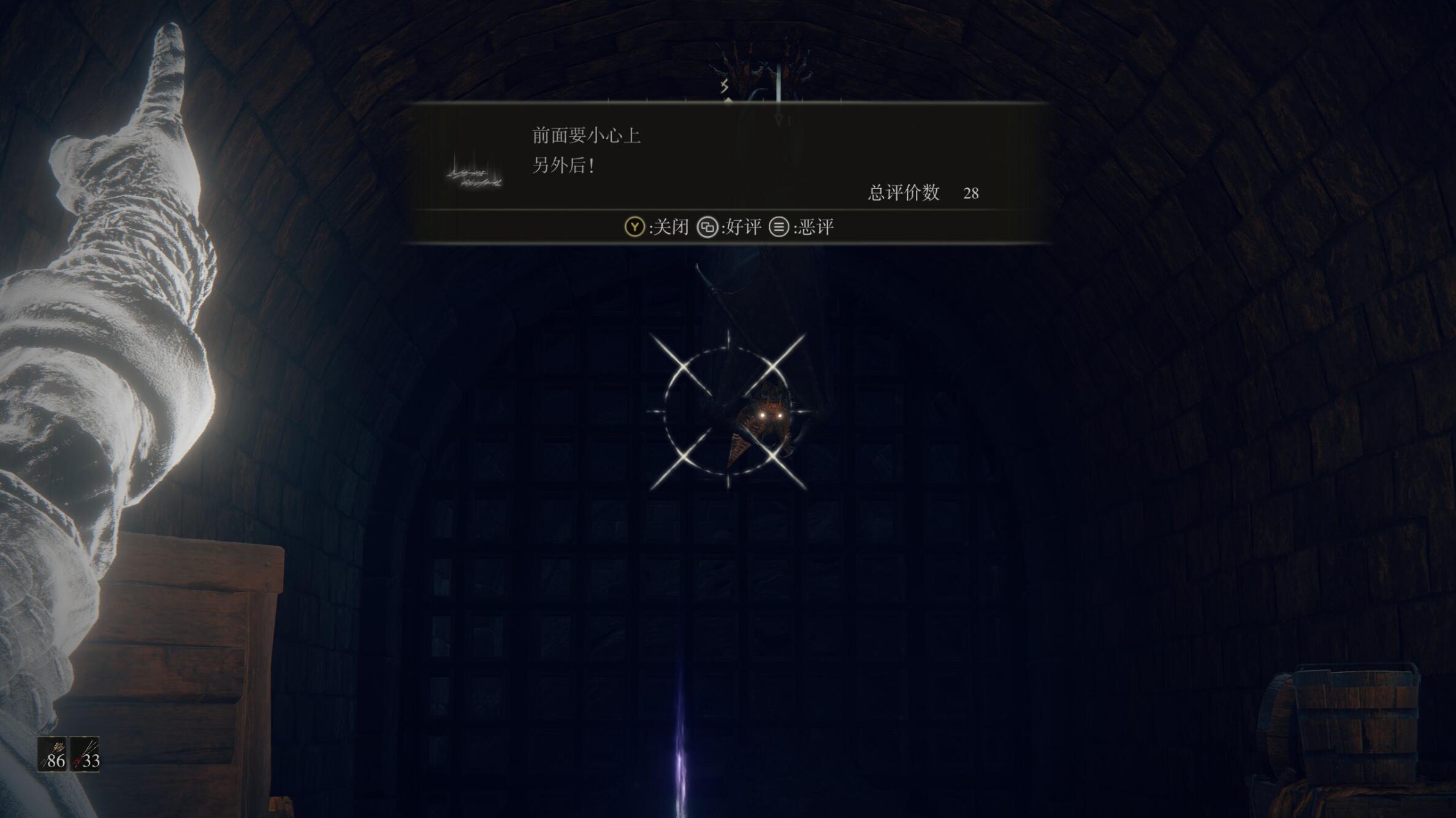
這是每個褪色者都已經所熟悉的場景,當然,這些“建言”也並不都是騙人的,比如在遊戲的開局階段的地圖中可能確實沒有那麼多的“隱藏道路”可供探索,但如果你習慣性的忽視這些建言,就會在魔法學院錯失大量的隱藏路線和其中的戰利品。

事實上,在遊戲世界中留言的“建言”系統,以及“入侵”和“搖人”這些包含“聯機”因素的機制並非是《艾爾登法環》所首創,而是魂系遊戲的“祖傳藝能”之一了——早在2009年的《惡魔之魂》中就有這樣的設定,而從《黑暗靈魂》系列到《艾爾登法環》,這個系統被不斷的加以完善。

除了“互坑”所帶來的趣味性以外,建言系統顯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魂系遊戲天然的弱指引風格下,建言無論內容真假,但其“密度”本身肯定包含了一些信息——比如在圓桌廳正面的臺階下面滿是血跡,就向你暗示了那裡是一個不祥之地,而本作儘管褪色者們擁有了可以跳躍的膝蓋,但在不能騎馬的箱庭迷宮內並沒有能夠穿越地形的強大機動性能,所以每一次你要向下跳躍,很有可能面對的都是短時間內無法回到原路的一條單行道,所以在這個時候,前方的道路是有大量的血跡還是大量的白色建言很有可能就能讓你下定決心是否來完成這樣一次“信仰之躍”。

那麼,除了“引導作用”和“趣味性”以外,建言這個系統本身有沒有其他一些值得我們思考的樂趣在其中呢?
繩子的魅力:建立連接與開放世界的生機
在“引導”與“逗趣”的表面作用之下,建言系統的真正意義在於:它是在社交網絡時代下,玩家與玩家之間互相聯繫的一條“繩索”——這個繩索可以是各個論壇社區的高贊熱門評論、可以是steam創意工坊大佬們製作分享的mod、可以是“單機遊戲”中這些相互的留言與互動,一言蔽之,這是一種連接建立的過程。
棍和繩是人類最古老的工具之一,棍讓不好的空間遠離自己,而繩把好的空間拉近。這是人類最初的發明,是人類最初的朋友;無論人們深處何處,棍和繩都無處不在。
——《繩》安部公房
安部公房,是一個存在主義與超現實主義的日本作家,最廣為人知的是被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家的大江健三郎盛讚,稱“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獲獎的將是他而不是我”——然而安部公房先生於1993年病逝。

儘管這位大家遺憾在在諾獎山巔的一步之遙停下來他的腳步,但他的文字流傳的更遠:在《繩》中他寫下了上文一段包含寓意與哲思意味的語句,成為了小島秀夫監督的《死亡擱淺》這個遊戲最好的精神詮釋:我們用槍械來對抗米爾人與BT的危險;我們用繩索把包裹捆綁在背上和載具之上,然後用繩索來跨越各種地形的天塹,把在末世中天各一方的人群們連接起來;繩與棒成為了《死亡擱淺》遊戲中“陰”與“陽”的兩極,共同為其構建了一種獨特的遊戲趣味——在絕大部分角色扮演遊戲中,這種作為“調和”存在的內容是以美式RPG中的劇情演出、JRPG中的日常內容存在的,所以在這些遊戲其中,我們是建立與“NPC”之間的連接。

但是《艾爾登法環》和《死亡擱淺》不太一樣:我們不僅僅在建立與NPC的連接,同時也在建立與其他玩家之間的連接,而這樣的設定又有一些美妙的地方在於:它在某些程度上賦予了“開放世界”一些“生機”或者“煙火氣息”——在《死亡擱淺》中你可以經常撿到其他玩家遺失的包裹,也可以在郵筒中收到其他玩家為你找回的包裹;你可以使用其他玩家搭設的勾索、橋樑等基建設施,也可以為他人做嫁衣,在危險的路段樹下標語牌作為提示或者鼓勵。在魂系遊戲乃至《艾爾登法環》中,還遠遠沒有做到這個程度的互動性,但“搖人幫忙”與“建言路牌”顯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你進入BOSS房之前,會有建言的打法提示,在你擊殺BOSS之後,會看到了“我做到了!”的自我勉勵。這樣一種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互動”讓遊戲真正打破了第三面牆:我們每個人在遊戲的開放世界中所完成的活動構成了其他玩家開放世界體驗的一部分,這樣最終所營造出來的就是一種——
弱社交聯繫下的“在線”遊戲
在過去的社會學研究中,學者們習慣於以“social tie”(社交關係)的強度來作為標準,將人們按照關係的強弱劃分為各種“圈子”(group),然後根據圈裡(in-group)與圈外(out-group)來區分人們作為一個社會個體在各種信息刺激與社交事件中所做出的反應。但隨著社交媒體時代的不斷深入發展,“弱社交聯繫”下的信息交互與人際交往慢慢成為了一個新的常態——比如以大主播作為社交節點的“彈幕文化”、或者以社區大佬發帖內容為節點的遊戲討論,而在電子遊戲本身中也在呈現著這樣一種“社區化”發展的趨勢,比如《極限競速:地平線》系列。

如果要深入分析《極限競速:地平線》具體在什麼遊戲功能上特別,讓它能夠從眾多賽車遊戲之中脫穎而出(銷量和其他遊戲完全不在一個量級),那麼你會發現無論是比賽模式、功能細節(比如倒車和各種加分)、賽車呈現等等方面,其實眾多賽車遊戲早就屬於互相學習借鑑的一種狀態,屬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然《極限競速:地平線》肯定在技術層面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但也不會是一般玩家可以感知到的內容。

《極限競速:地平線》真正做好的是在於持續的社區化運營與“弱社交關係”的語境建立,這樣一種環境可以給予我一種近似於準社交關係(parasocial relationship)*的感覺——沒錯,準社會關係一般發生在“我”和“媒介”之間,但《極限競速地平線》有著極其多與之相似的特點:無時不刻的廣播中NPC與你的“聯繫”、觀眾&賽事和其他玩家與你的互動、整體上各種賽事與活動所組成的嘉年華構成的“節目”氛圍——這樣共同構成了一種在準社交關係(parasocial relationship)中讓“我”覺得愉悅與安全的氛圍,那就是我可以充分滿足對“遊戲世界”的“窺視”欲的同時保持自身的安全社交邊界(事實上和網上認識有共同愛好的朋友交往也是類似的感覺),總而言之,這樣一種氛圍很符合遊戲弱社交關係下的“網絡遊戲”的玩法設定。
*準社交關係(parasocial relationship)是大眾與媒體人物之間的一種單方面關係。 媒體人物包括名人、真人虛構人物、網紅、動畫人物,無論他們在電視上、還是微博,抖音上。 雖然準社交關係的通常側重於媒體用戶和媒體人物之間的友誼關係,但是也不限於浪漫關係,或者消極關係。

在《極限競速:地平線》中,這種弱社交關係是無處不在,但是又毫無痕跡的——最初級的“社交關係”存在於多人賽事,那麼從PVP到合作PVE或者PVPVE,這些並沒有太多新奇感,但下一步,賽事本身也存在了以UGC(用戶生成內容)為核心的“社交屬性”——那就是自定義的賽道,你可以對任意位置的賽事做出你想要的修改,不僅如此,作為《極限競速:地平線5》重要元素的EventLab創作者套件成為了遊戲中一種重要的可遊玩模式,讓玩家能夠創建自己的路線、遊戲模式和定製汽車。這樣一種模式其實在很早以前,就是業界巨擘暴雪重要的成功奧義之一——光是WAR3的地圖編輯器就間接催生了MOBA遊戲這個興盛十多年的霸權品類,DOTA2的地圖編輯器又曾經讓各種自走棋紅極一時。

所以正是這些基於UGC內容的DIY與分享構成了《極限競速:地平線》世界真正的“社交網絡”——這大概也是目前大量的在線遊戲、在線社區等以人的聚集作為“動力”來源的網絡“聚落”所真正需要實現,但不一定有合適途徑的目標。事實上手機遊戲在某種程度上也很便利於實現這樣一種弱社交關係下的“網絡遊戲”——遊戲只是需要你和“遊戲世界”高度綁定,但是不需要你和遊戲世界中的人高度綁定,這是“弱社會關係”中的“弱”;但另一方面,其他玩家所構成的環境對於則構成了你遊玩的“遊戲生態”,但這樣一種遊戲生態中的“交互樂趣”則因遊而異了,顯然,《極限競速:地平線》至少是在“端遊”中在這一塊完成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獨立遊戲也幹了:META遊戲中玩家之間的連接
事實上,這樣一種玩家之間的連接並不僅僅存在於《艾爾登法環》、《死亡擱淺》或者《極限競速:地平線》這樣的大作中,在一些獨立遊戲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樣一種讓玩家彼此之間建立聯繫的趨勢,比如在前一陣大火的帶有META*和ARG元素的卡牌構築遊戲《邪惡冥刻》。
*meta遊戲又名元遊戲,與一般意義上傾向於強化玩家“代入感”的方式不同,meta遊戲會傾向於讓玩家意識到自己是在“玩遊戲”,會極大程度的強化遊戲作為一個play box本身的存在感,年初的《there is no game: wrong dimension》就是這個類型的典範,而前不久的《風來之國》中冰箱存檔時的臺詞也可以認為是典型的meta元素。這是一個來自於Metafiction(原小說)的概念,最典型的範例大概是《蘇菲的世界》——蘇菲發現了自己的世界其實是一本書,在電影中也有應用,比如科恩兄弟的《巴頓芬克》。

《邪惡冥刻》以一場氛圍詭異的卡牌戰鬥作為了遊戲的開場——我們需要在桌遊風格的卡牌戰鬥中戰勝小木屋的詭異主人重獲自由,但這僅僅是遊戲最表層的“假想”。如果說《邪惡冥刻》是一座冰山,那麼這開頭的“卡牌戰鬥”僅僅是冰山中的一角。事實上在遊戲過程中,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的詭異元素——比如卡牌會說話,會根據你事件中的選擇做出反應:比如“弱狼”會在你將其獻祭以後大罵“叛徒”、白鼬會拒絕接受來自其他卡牌的屬性等,和這些“卡牌角色”還會相互交談,彷彿是困在牌中的“生靈”。

在遊戲中我們每一次失敗都可以自己“印卡”來加入下一次卡牌戰鬥的牌庫中,這張卡我們會取名(也就有了靈魂)!而最重要的是,它也會出現在其他玩家的遊戲中!在第一關的BOSS戰中,BOSS在其中一個階段就會拿出一把由全世界玩家所印製的“英雄卡”——當然其中也包含了很多經驗不足時的送分或者自暴自棄的廢卡,所以本身上反而可能是難度的降低。但重點在於:難得一見的,在一個沒有任何“服務型遊戲”要素也沒有任何“在線內容”的單機遊戲中,玩家與玩家之間的聯繫建立起來了——如果說META遊戲更多的是遊戲製作人與玩家之間的對話,那麼這一次,在《邪惡冥刻》這個對話廳內,你隔著“第三面牆”,也可以“聽到”一點來自於其他玩家所發出的聲響。
無數褪色者們交錯的平行世界,又繪製成了一副怎樣的時空畫卷呢?
在當前電子遊戲的發展趨勢中,“社交體驗”正在成為越來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玩到一個激動人心的遊戲以後,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要分享自己的心情與體驗,這也就是steam平臺真正差異化於其他遊戲平臺的功能(社區),也是我們在各個遊戲社區流連忘返的主要原因(對於很多人可能逛社區的時間比打遊戲還多)。

這種社交體驗的特別之處在於:它需要是一種“弱連接”之下的社交體驗,如果說電子遊戲是一個造夢的舞臺,那麼這個世界中的其他玩家就是我們在冒險世界中踏上征途時的夥伴——沒有任何的利益糾葛,也沒有任何的矛盾衝突,僅僅是分享、(矇騙)與幫助,來放大我們在遊戲中所獲得的體驗外延。而在《艾爾登法環》這樣的遊戲之中,或許遊戲內的系統本身在某些程度上就已經實現了這樣一些“弱社交關係”需求的功能性——我們每個褪色者彷彿身處一個個修復法環的平行世界之中,但又在彼此的世界之中留下了那一個個投影,這樣一些來自於“另一個時空”的交錯,最終在一個更高的維度中,用所有玩家的遊戲流程與遊戲體驗,構成了一副也許只有“艾爾登之神”才能瀏覽的畫卷。